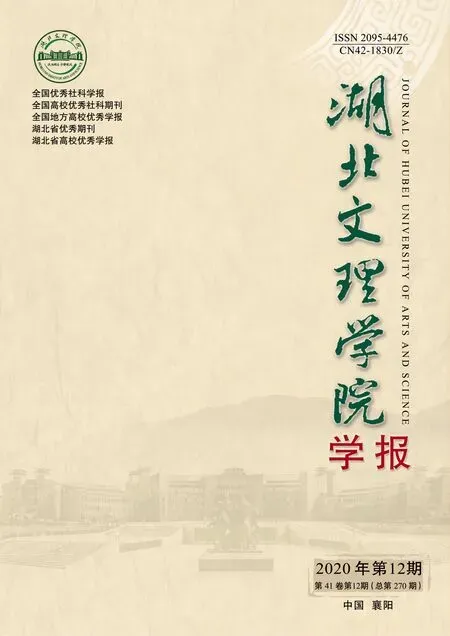楚国名辩思潮与宋玉的辞赋创作
朱佩弦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一、名家与楚国名辩思潮
名家是强调循名责实,以逻辑学的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事物的一个战国诸子学派,其起源较为复杂。它讲求名实相副,和孔子提倡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142是相匹合的;它主张“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和法家、道家刑名之学又是同一的。《韩非子·八经》尝称:“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2]436,认为人的言论必须用事实、功效来验证,通过“行参”“揆伍”以谋其功多,以责其过失;名家“合同异”派中惠施提出“汎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有人认为,这是与墨家“兼爱”说遥相呼应的统一[3]451。但名家区别于其他所有诸子学派的核心,在于它“不像其他诸子学派过多地从现实政治来考量事物,而只是从形式逻辑(名学)上分析”[4],即它更多地脱离实际,混淆具体事物与抽象概念,而仅从已知条件推演结论,如著名的“丁子有尾”“卵有毛”“鸡三足”等“辩者二十一事”,得出的往往是似是而非、口服心不服的结论,所以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名家有着较为精准的评价:“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5]3291讲的就是名家过于纠缠名而忽略了事物之实的特点,因“苛察”而“失真”“失情”。即名家以本意的“名实相副”原则去探讨问题,却因执着于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只求到了理论推演出的“实(物)”,并非客观的真正的“实(物)”。
名家专决于名,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其一是“离坚白”,以公孙龙子为代表,其二是“合同异”,以惠施为代表[6]。“离坚白”见于《公孙龙子·坚白论》:“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而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而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7]77-80公孙龙是典型地将自相与共相进行了形而上的割裂,坚硬和白色是石头的两种属性,分别只能被触觉和视觉所感知,因此就一块石头而言,我们只能同时认识到“它是石头、它是白色”或“它是石头,它是硬的”这两种性质,我们无法从“白、硬、石”三个方面去认识它,所以“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故公孙龙认为“二可三不可”,这既是从“坚石”和“白石”两种认知的判然对立而说的,也是从“坚”“石”或“白”“石”的二分而说的。而且,从本质上说,白、硬也应该是所有的白色物体或坚硬物体的普遍共相,而不应该是依附于石头的自相(虽然一般也要从个体中体现,但是石头这个个体不能代表所有的“白”或“坚”,公孙龙子认为一般可以从个体中脱离出来),所以说“白”“坚”也是二分的。同样,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子在兒说“白马非马”(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详尽的论证和发微,他认为“马”是一类物种共有属性,而白马则限制了马的颜色(“于色有所定”),马是一般,白马是个体,个别的马有白、黄、黑各种颜色,一般的“马”不表示任何颜色,马对于颜色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如果我们只需要马,则黄马黑马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白马却对颜色有肯定也有否定,我们要白马,则黑马、黄马都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归进一般,这是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矛盾性,也是就马的外延来说的。就马的内涵来说,“马”的内涵是马的形,“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马的形加一种颜色,三者各各不同,故“白马非马”。况且,他也说“所定白者,非白也”,即“白”是所有白色物体所共有的属性,只把“白”拿来概括和限定马的颜色属性,则白也并不是真正共相意义上的“白”了,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白”本身也就带有其附属于“马”的自相特性,而不带有普遍意义的共相特性。所以我们说白马非马,其实也是白马非白。他在《名实论》及《指物论》则进一步抽象了其对事物共相和自相的认识,牟宗三认为,公孙龙子所谓的“物”与“实”,分别是客观指目之词和主观论谓之词,分别表示“存在”和“称谓”[8]82,“实”是作为“名”来表达事物的共相的,虽然“实”或“名”很多时候并不能正确反映“物”之存在。如“马”对所有的马和白马的指称和反映,这时公孙龙子就引入了“位”“正”及“唯谓”的概念,将“实”或“名”的所指完全反映到“共相”上去,这也是“白”“坚”独立于“石”“马”之合理内涵。冯友兰也指出:“公孙龙以指物对举,可知其所谓指,即取名之所指之共相也。”[6]
惠施“合同异”的思想则散见于《庄子·天下》篇的“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只有九事,另十二事属于“离坚白”的理论命题)以及《荀子·不苟》篇的“五事”中。在惠施看来,大小长短、高低厚薄、今昔黑白、犬羊卵羽,所有的形态差异、矛盾对立,都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庄子·天下》篇云:“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9]297此即所谓的“历物十事”,要言之即“天地一体”也。此外,惠施“合同异”派还有所谓“卵有毛”“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龟长于蛇”“白狗黑”等命题。“合同异”是针对物体个体而论的,个体有许多属性,但是其属性并不是绝对的,因此泰山可以看作小(与宇宙相比),秋毫可以看作大(与微生物相比),但是大小作为概念则是绝对的,只有具体到物才是相对的,因此惠施认为,至大与至小,只有到了“无外”(无限大,其外再无外物)和“无内”(无限小,其内再不能分割)才是绝对的,但是他们又都是“一”(道或自然)的表现,所以“无外”和“无内”虽然是绝对,但也是在绝对的对立中实现了一种统一。既然具体物体的大小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判然分别,大、小是可以向其对立面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应该就是没有差别的,就是同一的,这事实上强调的是同一性中的差别性,但是差别是可以转化和统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事物都是可以向对立面转换而寻求同一的,所以天和地是一样高的;山与泽是一样平坦的;太阳一到正中就开始了它的日落过程;人一出生就在走向其死亡过程;乌龟在形体上短于蛇,在寿命上长于蛇,这是长短在乌龟身上的统一;楚国的郢都作为具体的地理方位,和天下是对立的,但它作为天下的一部分,又可以和天下同一;鸡从鸡蛋孵出,所以鸡蛋有羽毛(或有孕育羽毛的因素);蛤蟆(丁子)从蝌蚪发育而来,所以说蛤蟆有尾巴,也可以说蝌蚪没有尾巴,因此蛤蟆和蝌蚪都可以说处在“有尾巴”和“没尾巴”之间;白狗的眼睛可以是黑的,那么白狗本身也含有自己的对立面而实现一种统一。因此,惠施的“合同异”派更多地是从对立的差异中寻求统一,甚至在同、异之间寻求统一。而公孙龙子与惠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从统一中放大其中的对立面,并将对立面提炼为一种一般和共性脱离某一个体的内部统一系统独立出来。
名辩思潮在楚国的发展,根据高华平先生的考证,认为分为四个阶段,初期是以老子对“有名”“无名”的思索为开端的;第二个时期是以宋钘入楚开始,形成的楚国第一个名辩的波峰期,以墨辩学派的出现作为其标志,以“盈坚白,别同异”“离坚白,合同异”作为其论争的主题;第三个时期则是以惠施入楚、惠施与庄子之辩以及屈、宋的文学书写为第二个波峰的时期,这一时期惠施与庄子的“濠梁之辩”,庄子与公孙龙子的“鸡三足”之争(公孙龙子虽未有明确记载到过楚国,但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两人曾对“鸡三足”的命题有过争论,因此也应把楚国学者庄子的名辩活动视为楚国的名辩活动),屈、宋对社会现象、君主品行的循名责实的文学批判,都是其典型标志;荀子对先秦名家学派的批评和总结,则应该视为楚国名辩思潮的第三个波峰,此后名家逐渐走向衰落和终结[4]65-69。本文基本赞成高华平先生的分期,并结合名家的基本理论与思辨逻辑,分析宋玉在辞赋书写中受到的名家影响,展现出的名家思想,以期更为准确、全面认识和评价宋玉的辞赋作品。
二、名家思想在宋玉辞赋中的书写
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以及《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宋玉的生活年代略晚于屈原,吴广平先生认为宋玉大致生活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22年[10]19,刘刚先生则通过详细地梳爬史料,认为宋玉“大约生于楚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约在公元前222年卒老于临澧”[11],而学界对于惠施的生卒年,有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的说法[4]63,还有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说法[12],一说后者系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约略推断得出[13],不论我们取哪一种说法,惠施卒年都早于宋玉生年,以惠施与庄子的论争为代表的的楚国第二次名辩波峰早已形成,遑论更早的以宋钘为代表的第一次名辩波峰,宋玉显然或多或少会受到名辩思潮的影响而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展现。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楚国名辩思潮与宋玉辞赋创作的关系:
(一)“循名责实”“正名”与对现实、君王的讽谏、批判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4]2491宋玉辞赋祖屈原而来,在辞方面创作了《招魂》《九辩》等名篇,赋则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诸多作品,但无论是辞抑或赋,司马迁都明言其是对屈原“言约辞微”的以“香草美人”形象展现托喻讽谏传统的沿袭。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屈原、宋玉的辞赋中,都鲜明地使用了以名家“循名责实”评价方法,以对当时楚国的社会现象、君主品行进行批判,显著地带上了名家兒说、田巴“非六王,罪五伯”[4]的思想倾向。如屈原《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15]40-41,《天问》“妺嬉何肆,汤何殛焉”[15]103“齐桓九会,卒然身杀”[15]111“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15]113,《九章·怀沙》“刓方以为圆兮,常度未替”“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15]142-143,《九章·惜往日》“弗参验以考实兮”[15]150等,都是对六王、五伯、当时统治者、贵族名实乖剌矛盾的怀疑与揭露,以及对名实关系的思考及其在美人香草上的托喻。宋玉在其辞赋中,对这类名实乖剌的批判则更多也更为明显:
1.《九辩》
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15]187-188
按:此处以“华而无实”阐发宋玉循名责实的思想倾向。以树木的花与果实为喻,“华”指君主为众人所称之令名,“实”则指君主实际上在施政上的行为,发现君主虽有“蕙”之“华名”,却在施政理念与行为上与其他普通的花草无异,其施政的实质只是相当于平庸的花草,甚至类似于屈原所说的“榝”和“申椒”之类的恶草。君主施政之“实”只能与恶草之“名”相匹,这显然是对君主名实乖谬的一种揭露和批判。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15]191-192
按:此处说的是宋玉对自身名实合一的严格要求,认为如果不能在浊世中做到名实相副,即使在魏阙朝堂,虽有官职之令名,却难以行使该“名”之下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之“实”而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委曲求全,寄人篱下以乞食。换言之,对自身名实相副的自矜,也就是对浊世中其他人名不符实的一种侧写、指摘、批判和讽刺。下例同此者不复赘述。
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15]195
按:结合“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一句,我们认为,宋玉认为自身的节操品行之“实”与相应的称谓的“名”是匹合的,是希望自己能留下这令名的。这依然是宋玉从“循名责实”出发的自矜。
2.《招魂》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15]197
按:据洪兴祖引《文选》五臣注的说法,此宋玉代原陈词,赞扬屈原名实相副,但也可视作宋玉夫子自道,自矜其名实相副,品德高尚,令名远播。
3.《风赋》
按:宋玉在《风赋》中就楚顷襄王“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以及“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16]43-44进行了辩驳,借所谓“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反映了王公贵族的奢靡和黎民黔首的悲辛,对统治者自诩的所谓“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的名实不副的虚伪进行了揭露、讽谏和思考。
按:《神女赋》是《高唐赋》的姊妹篇,描绘的是高唐神女与楚顷襄王的梦中幽会的情景,她“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兮相难”[16]72,塑造了多情开朗却又矜庄自持、以礼自防的女神形象;《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则是宋玉就登徒子、唐勒在楚王面前诋毁自己好色所作出的辩解,分别描绘了宋玉被其东邻的楚国绝世美女攀墙窥视三年而不动心,以及被房东家的女儿主动献身却始终以礼自持,甚至极端地提出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16]117的事实。这说明,宋玉始终注意到进行一切活动需要有名正言顺的“正名”,《汉书·艺文志》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17]1737前文已述,名家本身则有从儒家吸取的“正名”因素,司马谈也肯定了“正名”是名家与“苛察缴绕”“专决于名”的同样重要的基本属性。据此,我们这里可以说宋玉是受到了名家的影响,产生的这种“正名”的以礼自持的行为,认为楚王与高唐神女,他与邻女、房东之女的实际行为应该与他们之间的名分匹配,做到名实相副。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后文讨论宋玉在名家逻辑方法上进行论辩的内容来说明,宋玉此处确实应是受名家影响而非儒家。
5.《对楚王问》《钓赋》《御赋》
按:《对楚王问》是宋玉答辩楚顷襄王质问他为什么不被大家喜欢的原因而作的一篇赋,宋玉举了对应三个知识层级的乐曲来说明问题,认为《下里》《巴人》是需要知识水平最低,最通俗的乐曲,所以其接受度高,郢都城里和者有数千人;《阳阿》《薤露》则是需要中等知识水平的乐曲,能接受的人较之通俗的乐曲要少许多,郢都城里和者只有几十人;《阳春》《白雪》则是需要知识水平最高的乐曲,只有像宋玉这样知识水平的人才能接受,所以郢都城里和者仅有寥寥数人。宋玉借乐曲为喻,表现自己志向凌云、品德高洁,蜩与学鸠之流又如何能够理解他和喜欢他呢?所以他说:“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16]89仅从乐曲上说,宋玉是认为千人之“名”,对应的只能是《下里》《巴人》之实,或曰《下里》《巴人》之名,对应的只能是那千人的知识层级之实;同理,《阳阿》《薤露》,《阳春》《白雪》都有其应对应之实,这其实也是宋玉不自觉受到名辩思潮影响对“名实相副”的下意识表达。《钓赋》则是宋玉与登徒子向环渊学习钓术后对楚顷襄王陈述的对钓术的不同理解,登徒子认为钓术之精在于钓术对客观事物鱼的获取上,所以他认为环渊的钓术非常高明;宋玉则认为环渊的钓术只是形而下的末技,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他把钓术泛化到形而上的,可以比附到广纳贤才、广聚民心以实现人君南面、天下大治的理论或方法上去,所以他说环渊的钓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称焉?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沉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为大王之钓,不亦乐乎!”[16]125这说明在宋玉的名实观中,形而下的技巧之“实”是无法与顷襄王君上之“名”匹配的,顷襄王应该学习上古圣君尧舜禹汤,将形而下的技巧提炼到形而上的“天下大治”之达道上去,这才是与其君王之“名”匹合之“实”。《御赋》,原题“唐革(勒)”,于1972年4月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初被认定为是唐勒辞赋,但古人题篇往往取篇首二字或数字,如《论语》之《述而》《学而》,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生年不满百》等等皆是此例,因此《唐革》篇并不能确定是唐勒所作。后李学勤论证认为,出土文献如张家山竹简的《盖庐》,其篇名也是取篇首二字而作者绝非盖庐(吴王阖庐),又通过对照《唐勒赋》和《大言赋》《小言赋》中人物发言顺序,发现宋玉的对问辞赋体例之一即宋玉固定为最后发言,认为《唐勒赋》应该为宋玉所作,当为《宋玉赋》。[18]朱碧莲先生也持相同看法[19],并与李学勤都主张此赋当改称《御赋》,后吴广平先生编注《宋玉集》则予以沿袭。《御赋》其实与《对楚王问》《钓赋》差不多,都是从形而下的驾马车技巧的优劣论证出发,推而化之到形而上的对天下之驾驭治理之道上去,以国家为车,以圣贤为马,以仁义来驾驭马车。也是从君王之“名”当合“作圣君,以化成天下”之“实”出发的。
(二)宋玉对“离坚白”论点的继承与运用
在《庄子·天下篇》中,惠施所提出的“辩者二十一事”,有十二事属于“离坚白”的理论命题,分别为“鸡三足”“火不热”“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柄”“飞鸟之景(影)未尝动也”“狗非犬”“黄马、骊牛三”“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9]297-298,下面以《风赋》《对楚王问》《钓赋》《御赋》为例,我们结合这些理论命题所提炼的核心来说明宋玉对“离坚白”的接受与运用:
“狗非犬”类似于“白马非马”,即子集概念与总集概念的从属但不相等的情况。按《尔雅》:“未成豪,狗”[20]85,即“狗”是未长出毛的小犬,是“犬”的子集,这个命题是把“小”或“未长毛”提炼成凡是“小”或“未长毛”的动物、事物的一种共相,而不把它视为依附于“犬”的一种自相。“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本质上乍看起来是数学的极限概念,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即通过“小”或“未长毛”来看,“小”或“未长毛”的程度如何区分?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看,我们如何界定这个“小”到“大”或“普遍”的临界点?1分米是不是小?1.1分米是不是小?1.11分米是不是小?到哪一个数值它就瞬间变成了“大”呢?既然这个临界点找不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和“未长毛”有无数种标准,那么每一种标准下的“小”或“未长毛”都可以视作是一种“共相”。此外,如“目不见”“火不热”“指不至,至不绝”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对“离坚白”“白马非马”“狗非犬”以及“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延伸,虽然它们说的都是“名(实)”对“物”的不能完全指示和称谓,但正是因为从它们能提炼出更多独立的共相,所以如此。如“目不见”,眼睛想要看到外界,需要光线、物体等因素,如果没有物和光线,那么我们就不能看到外界,从这个层面上说,“目”仅仅只是所有有眼睛的物种的共相,它不能指涉“观察”这一行为的全部组成要素,即便是“观察”一词本身,也无法指涉清楚。“火不热”是指“火”这个文字只带有其独立的被识别的共相,但是火明亮、炎热等其他组成属性则不能被“火”这个独立的文字所认识。“指不至,至不绝”则是对这种“名(实)”不能准确或完整指称“物”的总结。其他命题大同小异,我们不再赘述。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宋玉在《风赋》中区分的“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就有了其合理的名辩思索的内涵:即“大人之雄”“小人之雌”是宋玉提炼出来的区别于风本身的两种独立的“共相”,它们的外延分别是所有君主阶级之“共相”和所有穷苦阶级之“共相”,是大王的风、庶民的风,它们的内涵分别是“起于青蘋之末”,遍拂深谷、雄岳、丽川、宫墙、苑囿、罗帷、芳草的风和“起于穷巷之间”,历扬蔽庐、草屋、灰堆、尘沙、垃圾、污秽的风,据此还可以分出无数种具有独立共相性质的“风”来,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可以说,“雄风非风”“雌风非风”,两者本身都是独立于“风”的一种共相,在统一中无限放大了这两个差异面的对立特性,用以充分阐释楚王并不能体察下民,与民同喜悲,委婉地陈述了其讽谏的意图,揭露了楚顷襄王“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的名实乖谬与虚伪,认为楚顷襄王实不能与天下黎庶共此“快哉风”。
同样,在《对楚王问》《钓赋》《御赋》三篇赋中,宋玉对不同类型的音乐、不同类型的钓鱼技巧、不同类型的御马技巧都提炼出了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共相,尤其是对于钓鱼技巧与御马技巧就治国之道的比附,这种完全从形上角度去提炼出来的理论,它们虽然离公孙龙子得出的琦怪结论还很远,但确实已经是一种追求统一中对立面的绝对独立了,因为从隐喻上来说,形而下的钓鱼技巧、御马技巧与形而上的治国之道,在整个大的“钓鱼技巧”或“御马技巧”的范畴内,是可以相表里而统一的,而在宋玉的观念里,形而下的技巧都不是真正的“钓鱼技巧”或“御马技巧”,所以他说“今察玄渊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16]122,又说“俗御不足道也,良御不足称也”[16]132。在他的思想里,“钓技”非“技”,“御技”亦非“技”,“钓天下之英才之技”和“御天下之技”也根本不是“钓技”“御技”本身,所以说这又是对“钓技”非“技”,“御技”亦非“技”的重申。另外,“称”其实有“指示”的意味在里面,宋玉说“良御不足称也”其实也是从公孙龙子的逻辑出发,认为“御”不足以道御之“物(实)”的一种说法。也是一种把“御”作为词汇独立于“御”这一“事(实)”本身的思想倾向。
此外,宋玉其他辞赋作品中尚有此类“离坚白”之思想,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全面整党历时三年半,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第一次系统的、广泛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参加整党的党员达到4200万人。这次整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党始终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宋玉对“合同异”论点的继承与运用
关于惠施“合同异”派的理论观点的内涵,我们在前文有过详尽论述,虽未完整阐述惠施“历物十事”,但本质与前文所述例证大同小异,此不赘述。此举《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数篇略作说明。
如前文所述,惠施虽然阐述了统一体内部的对立差异,但是其主旨是认识到了对立统一于整体的特点,是一种辩证法的思维。所以他认为具体事物“大”“小”的相对正可以说明“大”“小”的无差异,所以可以统一,甚至于天地万物之间都通过对立而形成的一种联系和统一,故称“天地一体”。同理,在学界普遍认为的宋玉游戏之作《大言赋》《小言赋》中,我认为宋玉是吸收了这样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的。如《大言赋》中宋玉所描绘之大:
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天,迫不得仰。[16]106-107
其《小言赋》描绘之小则是:
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大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未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16]111
显然这是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极为文学艺术化的表达,“至大”“至小”作为“大一”和“小一”,两者对立而又统一于“一(道或自然)”中,《大言赋》《小言赋》历来视为宋玉所作之姊妹篇,但多以游戏之作视之,从本质上看,其对大小的思辨是完全契合惠施的“天地一体”的。
再说《登徒子好色赋》,宋玉提到的东邻的美女,说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16]80,从儒家的角度去解读,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观念的一种表达,但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惠施对立统一辩证思想在宋玉手中以妙笔生花的描绘所得到的展现,即“长”“短”的对立,与“白”“赤”的对立,都在这位“东家之子”身上得到了最圆满的融合与统一,这是“长短”“白赤”各种对立或异质属性的一种“合”与“同”。另外,从宋玉那段为自己解释的诡辩来说,也显著地在所举意象中体现出了一种“事物包含着自己对立面”的思想,如宋玉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东家之子这样一位冠绝楚国的大美女,三年以来一直在墙头窥宋,自己却不曾动心,这不是说美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不太好或者有害的因素,导致宋玉不愿意去接受或亲近吗?而登徒子的妻子又丑又有着各样的生理疾病和缺陷,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儿子,这不正好从侧面说明了,丑的外表下蕴含着其他更为有利和让人愉悦的因素,所以登徒子才喜欢她,和她恩爱甚笃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不能不说这是宋玉潜意识下犯下的一种逻辑悖论,也可以认为是此时遍及楚国的名辩思潮对宋玉产生的影响所导致的后果。
此外,宋玉其他辞赋作品中尚有此类“合同异”之思想,限于篇幅,亦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宋玉生活的年代,导致了宋玉不可能不受到名辩思潮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有所展示(《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那套诡辩说辞是最为典型和显著的),我们认为,经过名家思潮的影响,宋玉的辞赋成为了抨击时政更为有力的武器,也让其辞赋更富于思辨性和趣味性,可以说,名辩思潮的影响是宋玉文学成就得以确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据此,结合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成为宋玉研究的一个新的角度。今不避固陋,希望本文能作为引玉之砖,引起学界对结合思想史研究宋玉的方法的重视,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新的研究成果,造惠宋玉研究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