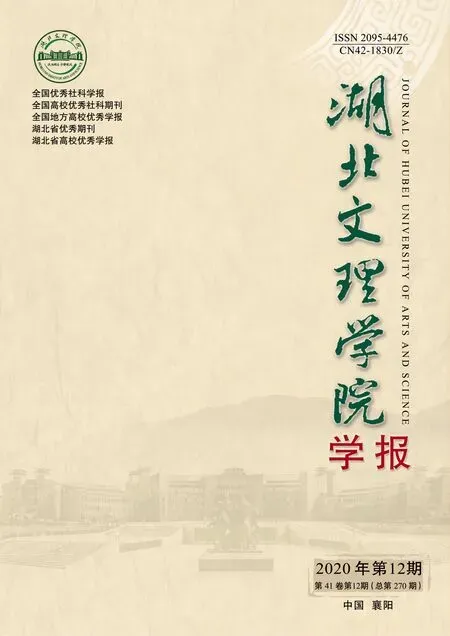基于“万物有灵”的精神救赎
——从《候鸟的勇敢》到《炖马靴》
李翠青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东北大地以其特殊的文化风貌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据一席之地,从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来看,萧红怀着深沉的爱与痛,写下了底层人民生与死的挣扎,萧军、端木蕻良等也都以自身体验传达出对于东北大地的情感,当代作家刘庆的《唇典》则专注于东北小镇的人物和历史,对东北地域文化进行研究。迟子建生长在东北的北极村,宗教文化的渲染赋予了她特殊的生活体验,由此她笔下文字所展现出的是对于生命最原始的尊重。《候鸟的勇敢》和《炖马靴》是作家表现人与自然信仰的新作,在自然信仰的影响之下,小说中人与鸟、人与狼之间对于生命顽强守候的默契,也与作者一贯宣扬的人道主义情怀相契合,人性在世俗的欲望之下不断演变,唯有心存温暖与善念,才可在俗世间舒适行走,实现精神救赎。
迟子建习惯以一种温情的笔调表现东北大地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来,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以深厚感人的意蕴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候鸟的勇敢》在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于中篇榜首,小说从候鸟管护站展开,展现了瓦城的世俗百态,揭露了东北小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阶级的不平等,并对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进行了拷问。而在2019年小说排行榜中,迟子建的小说《炖马靴》获得了短篇小说榜之首,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战年代,父亲与瞎眼狼彼此之间相互帮扶成就了一段可贵的友谊。关注人性与自然是迟子建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者尊重万物生灵,而从小说中人物来看,从张黑脸到父亲,他们都心怀善念,以深沉的悲悯情怀观照自然,并始终践行着生命平等如一的信念。
一、“万物有灵”的自然信仰
中国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对于宗教信徒而言,他们的信仰更甚,在生活中遵守教义,虔诚地信奉神灵。纵观不同宗教在我国历史上的传承与发展,儒、佛、道曾是中国人民的三大信仰和三大精神支柱,而在一些少数民族之中也有原始宗教的存在,我们所熟知的阿来小说中对于苯教的描写以及东北作家萧红笔下的萨满教仪式的展现,这些都是原始宗教的遗存,这些宗教信仰者聚居在偏远地带,他们远离现代化的城市,依然保留着祖辈的信仰。迟子建居住在北极村,在祖国最北端的地区还遗留着少数民族的风俗,作者长期与当地的鄂温克等民族接触,“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1]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迟子建也相信万物有灵,自然间有神灵,如果冒犯,便会有惩罚。这种对于生命普遍的敬畏与尊重也决定了作者的文学观:在小说中诉诸人道主义与悲悯情怀。
在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张黑脸相信“万物有灵”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信仰。张黑脸多年前入山林遇到了虎,在危难之际,一只有着巨大翅膀的鸟儿救了他,从此之后,他性情大变,不再贪恋世俗事,而融入了自然之中,并且拥有了神奇的能力:可以预见天气变化。此时的张黑脸脱胎换骨之后失了人性的模样,他喜欢有翅膀的动物,并视它们为恩人,这样的信仰使他六根清净,一心与候鸟管护站的候鸟为伴。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东方白鹳救助张黑脸,张黑脸救助东方白鹳这一个循环模式展开,最后它们共同留在了风雪中。在周铁牙把候鸟作为谋财工具时,张黑脸却把它们当朋友、知己,在鸟儿受伤不能南飞之际,张黑脸虔诚地祈祷,在对自然的感恩之下,张黑脸超越了人与兽之间的生理阻隔,他将候鸟看作神圣之物,相信“万物有灵”。
《炖马靴》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人与敌手、人与动物的矛盾下,“万物有灵”这一信仰表现了另一种姿态。故事主要聚焦于父亲与瞎眼狼身上。人性与兽性之间有分别,不可以一概而论,人并非全是善良,而兽也有好恶之分,父亲与狼都心存善念,因惺惺相惜的感恩之举相互完成了心灵的沟通。父亲在行军过程中遇到了天生瞎眼的母狼,出于最本真的同情,父亲给予了帮助,为它留骨头,让它解决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饥饿。后来父亲遭到日本兵伏击,困在了山林,母狼的眼睛无法识人,但它凭借多年前的记忆仍然找到了需要救助的恩人。母狼怀孕后,那些狼崽不知所踪,它们大多数像自己父亲那样嫌弃抛弃了母狼,但却有一只小狼甘愿做母亲的灯,照亮母亲的生活,它感念母亲,也懂得保护母亲的恩人,在迟子建笔下,狼是有温情的,通人性,在北方这个极寒之地,共同生存的生物之间有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它们作为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拥有共同的信仰:对自然崇拜,敬畏生命。
二、精神救赎的别样呈现
“阿多诺认为,文字是人类最痛苦的回忆,艺术是一种‘救赎’,它一方面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遭遇到自己的感性身体、欲望和情绪,这正是‘救赎’的意义所在”[2],迟子建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她将自身切实的情绪体验凝练成为普遍、通俗的故事情节,因而往往从最不起眼的小事件中却能挖掘出最世俗的社会病症。迟子建在小说《候鸟的勇敢》和《炖马靴》中,将笔触延伸到了两个普通人身上,他们对万物怀有平等敬畏之心,在涉“罪”之时,以别样的方式宽慰精神世界从而救赎自身。
(一)除罪:自我惩戒
救赎思想来源于宗教,耶稣知晓人性之恶,将自己钉入十字架而换得信徒平安,赎尽污秽;佛教信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以及好人升天堂、坏人入地狱的轮回之说,都是源于自我信仰范围内对所涉罪孽之事的忏悔心态。精神救赎便是要在认识到思想罪恶之后进行心灵洗涤,以此来超脱、升华怨念。
《候鸟的勇敢》中出现了阶级地位相差甚远的两种人:穷人和富人,也就是小说所隐喻的留守人与候鸟人。穷人忙着赚钱而对自然发起进攻,他们侵占、破坏自然,而富人居高位要职,则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职位所带来的利益之便。张黑脸的泼皮女儿张阔说得十分形象“采达子香运往大城市,这是扶贫。大城市人看上去光鲜,可过得不痛快,精神空虚。这也是贫穷。他们没养过这样有生命力的野花。所以对达子香有需求。山里人抚慰了城市人的灵魂,是不是扶贫呢?”[3]78城里人从山里走出去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他们在寒冷的冬天如候鸟一般赶往南方的温暖之地,而在夏天往返消暑。物欲满足之后的他们开始向往一种精神追求,“野花”“野生动物”,这些带“野”的生物以一种极其神秘的姿态与魅力吸引着他们的诉求,所以局长爱吃野鸭,城里人也将山间的达子香视作珍宝。
如果说城里人靠山里的野生之物来填补精神的空缺与贫穷,从而获得天然的满足感,那么张黑脸的回归自然则是在反省后的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救赎。张黑脸原本是世俗之人,他在神鸟救助之后融进了自然。他从前性格开朗,桀骜不驯,“而现在话极少,呆板木讷,似乎谁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3]3张黑脸在失忆之后算是一个六根清净之人,只懂得与候鸟为伴,不念世俗人情,而在遇上德秀师父之后则出现了精神上的波动。张黑脸对德秀师父的感情出于本能的恻隐之心,而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场所,德秀师父的遭际让他体现了世俗男人本应有的担当与责任意识:他想要给予温暖,照顾这个命运孤苦的女人。张黑脸和德秀师父在寺庙旁初尝情欲禁果,寺庙是供奉神灵清净神圣之所,因而他们想到的都是如何接受惩罚,可见都是深谙世俗伦理之人。“欲”是佛之大忌,却是人之常情,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看,“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前面所说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4]生理欲望处于所有欲望最下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张黑脸和德秀师父的“禁忌”之恋却无法逃脱内心的惩戒。他们日夜忏悔,肯定了自身必定走向灭亡的结局,小说的最后部分,两人在暴风雪中为候鸟饯行,是忏悔的最终实现形式,“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3]202在茫茫大雪中空无一人,他们以天地间的一片纯白实现自己的精神救赎。
(二)和解:承袭善念
张黑脸对于世俗生活的回避是通过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他与德秀师父三次激情相拥之后祈求神灵对自身肉体进行惩罚,以此来救赎精神苦痛。反观小说《炖马靴》,在环境恶劣、生存艰难之时父亲因怀有悲悯之心而自省,最终以温和的方式拯救了自身。东北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赤胆忠心和铁骨铮铮的勇气,东三省作为抗日重要阵地自有其深厚的故事意蕴。《炖马靴》中父亲在战斗中不断“炖”敌手的马靴而存活下来,父亲是队伍里负责做饭的战士,他是抗战队伍中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在与敌国对阵之际,在鲜明的民族敌对意识之下,即使是小人物也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在生与死,民族与阶级的较量中,父亲凭借老练的智慧取得了胜利,他拿到了战利品——靴子,这无疑是给久战后的父亲提供了最得力的营养供给。父亲与张黑脸不同,张黑脸被救助之后俨然成了隐于世的人,精神归于自然,而父亲当时身处艰难之地,作为一个正常人,他的首要选择便是活下去。在这场生存斗争中,敌手成了失败者,但他在生命最后也没有放弃战士的尊严,“他从未见过一个人的眼睛会在夜的飞雪中发出那样强的光,锐利,绝望,又不甘”[5]16。父亲与敌手的关系是对立的,而从生命的本能出发,父亲流露出了同情。年轻的士兵即使面对野狼啃食后死无全尸的恶果,仍然握紧士兵的志气,这使得父亲生出了敬畏之心,在敌手流血过多时,父亲用火来温暖他的身体,让他不至于在东北的大雪之夜里过于痛苦地离开,而这些源于父亲精神震撼之后的悔意。那把三八式步骑枪,最终到了母亲手里,这是对小战士未完满的婚姻人生的延续,也是父亲对死去敌手的深深缅怀。父亲在后来的生命征途中找了救赎之道,那便是将善念传承下去,他年复一年地传颂这个故事,逐渐与内心的矛盾和解,抚慰了精神上的歉疚。
父亲对敌手怀有愧疚之情,在感怀中救赎自身,“父亲每回讲完炖马靴的故事,总要仰天慨叹一句: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5]29而正因为父亲留下的“骨头”,瞎眼狼免于饿死,而在多年后父亲得到了它的保护,最后拯救了自身,再次凸显了父亲对传承善念这一抉择的肯定。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充裕起来,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很难切实体会到万物有灵,也无法想象人与兽之间存在的默契。精神上的懈怠也让人们逐渐失去了同情与爱的本能,而当下的人们把过去的故事视为漫谈的传说,口中充满了轻视与嘲弄,浮躁社会之下更难体会善念的存在。而在抗战胜利建国7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更要以过去英雄们艰苦卓绝精神滋养训诫自身,这些精神源于我们本能,却在发展中不断被湮灭,因此更因被唤起,来救赎我们快速发展的思想,体味人道主义关怀。
三、自然信仰下精神救赎的价值阐释
(一)世俗生活的烛照
迟子建的小说着眼于生活中的小人物,如傻子、进城打工的夫妻以及魔术师等,而这些平凡人物身上有着万千人民的共性,真实显现了社会生活百态。小说应当反映现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我们的民族不乏奋斗的历史,专注英雄人物描写的史诗性著作往往场面宏大、振奋人心,但在文学史中同样需要一些作品来展现悲悯情怀与人道主义,而小说中对于人性的书写则使读者获得共情之时发挥感化效应。“在世俗人道主义中,苦难叙事是启蒙取向逐渐向世俗伦理取向和人性取向的演进,其人道主义思想专注于人的生存与自我确认、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展示人战胜苦难、超越苦难而自我获救的精神。”[6]迟子建从小人物出发而写大历史,将眼光投入到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中,以东北地区的人性叙述作为一面澄澈的镜子,来映照温暖与悲情。
关注生态与自然是迟子建一直秉持的写作原则,在近两年的小说《候鸟的勇敢》《炖马靴》之中,作家再次剖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对世俗人性的解读也十分深刻。《候鸟的勇敢》中张黑脸的女儿张阔在父亲变傻之后私吞其银行卡,并驱赶父亲去候鸟管护站做看守人来赚取钱财,甚至不希望父亲变聪明,好起来。周铁牙虽为候鸟管护站队长,却视候鸟为赚钱筹码,毫无爱心。官僚体系层层腐败,官员凭借利益而使地位不断稳固,社会关系更是混乱,不论友情还是亲情都要靠金钱来驱动。穷人要变得富有,富人则要求更加富有,整个社会充斥着交易与虚伪,对于物欲的追求成了当今人们的本性。小说建构了世俗社会之外的一处特殊场所——娘娘庙,在世人眼中庙里的师父神圣、可通灵,是“在夜里不用点灯的人”,这本是人们寻求清净之地,不食人间污浊,周铁牙、老葛却在此处进行着金钱利益的交易,德秀师父的前夫借着法会博取同情从而牟利,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无赖嘴脸进一步映照出了世间人皆向利。瓦城人们在黑暗的金钱交易中生活着,在集体无意识中他们失掉了善良的品格,作者将小城人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剖析,赤裸裸地展现了金钱驱使下灵魂失格、温情丧失的状态,从而在极其真实的叙述冲击下触动人们反思自身。
《炖马靴》的故事发生在抗战年代,与《候鸟的勇敢》相比,人物显得单纯而质朴,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坏人,有的只是各自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他们都用自己的鲜血守护了国家尊严。磨牙士兵因为晚上磨牙影响战友休息而被嫌弃,但在与敌人交战之时,他以一己之身投入熊熊战火,为战友争取了生存的机遇,从而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象,那之后喑哑的磨牙声成了父亲回忆中最难忘的美音。在全民抗战的那个年代里,战士们单纯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而欲望压缩到了最基本的维度——生存。同样可贵的是,在战争之外,战士们怀着惺惺相惜的情感,对他人报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的人格依然是完整的,心尚未被蒙尘,依然纯净、明澈,而正是这一纯粹的情感才让处于艰难条件下的民族得以胜利。
(二)现实附以“神话”的叙事体验
在与少数民族长期生活的体验中,迟子建被“万物有灵”的信仰所浸染,尊重自然生灵,而幼时在长辈叙述中所熟知的聊斋故事开启了迟子建的想象模式,因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会呈现出神话的因素。“在我眼里,能给生灵以关爱,给大自然以生机,给人以善良的神话是万古长青的!”[7]迟子建对自然万物饱含温情,作家信奉神话中的善念,坚信诸类神话教义能够驱使人们弃恶扬善,并在实践中忏悔自身。由此来看,神话故事的特殊效力也为精神救赎的实现开辟了道路,神话故事中耳熟能详的天堂与炼狱的存在建构出了生命在他界的延续状态,是对自身行为的救赎。迟子建小说引入神话因素,赋予了小说超验的神秘色彩,在现实与虚幻的对照中显露人情冷暖。
小说《候鸟的勇敢》中,故事主要围绕候鸟管护站的张黑脸展开,各个情节独立分散,同时又通过“候鸟”融为一体,将东北这一地区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小说是对东北现实世俗生活的反映,其中也包括对生态问题的关照,作者通过加入神鸟这一线索来对人们发出警示。“他眼前有一把巨大的羽毛伞,黑白色,伞柄是红色的,是他此生见过的最华美大气的一把伞。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身红腿黑翅的大鸟,站在他胸腹处,展开双翼为他遮雨。张黑脸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到了天堂”。[3]38东方白鹳从虎口救下了张黑脸,张黑脸因而成为了一个不问世事的“鸟”迷。小说的故事本是极度写实,而在张黑脸与东方白鹳的相处中,迟子建巧妙地设置了超乎常理的情节,使小说空间扩大到了人性与神性的空间,凸显了人与神鸟之间的温情。没有神话传说的民族部落虽然更为现代,但终究会因为缺乏神秘而显庸常。候鸟作为一个隐喻,在小说中候鸟、留鸟与候鸟人、留守人是互相对应的。候鸟冬天南飞,夏天返回,它们本来作为一种贪图享受的存在而被人厌恶,但在一次疫情之中,传闻中的候鸟杀死了骄奢淫逸的候鸟人,而在这时它们成了穷人口中正义的使者。当厌弃的事物因为传闻的某个符号而消失,人们在感觉大快人心的同时必然十分感激那个符号,并用虚无的传说包装它。而候鸟这个在贪官相继离世中出现的偶然因素,使得它具有灵性,人们开始相信,候鸟是正义的使者,是不可侵犯的,而这是自我认知加工的信仰,瓦城人们对于候鸟的信仰出于它杀伐果断的正义身份,也是对神话故事中因果报应的回应。神鸟的现身对于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引导作用,推动着故事人物去发现罪愆,同时对于张黑脸这个边缘化的小人物,作者在纯粹的现实世界之外给他提供了志趣相投的伙伴,消减了主人公的悲剧性。
《炖马靴》的神话因素源于父亲与狼之间超越物种的心灵互通,迟子建坦陈自己的文学观曾经受到小说《聊斋志异》的影响,在聊斋这类小说中,花妖狐怪、神鬼异类通常有着善良的品性,能够与人成为知己,这些生物通人性,富有灵性,且有着优良的道德观念。瞎眼狼是深藏于东北山林的狼,在它缺乏食物濒临死亡之际,受到了父亲这个人类的帮助,而等到父亲遭遇困境之时,它义不容辞地来保护自己的恩人,这是传统志怪小说里的报恩故事,有着神话与民间传说的成分。迟子建的小说是一部描摹抗战真实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中增加浪漫主义成分是使得小说具有神秘色彩的点睛之笔。故事的主人公通过极具人道主义的施授而成功脱险,最后用自己的后半生来传颂善念,实现了对于自我的精神救赎,救赎过程的展开也包含了神话这一因素的铺垫,使得小说的结局更具戏剧性。
(三)悲悯情怀的传承
“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通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8]文学向来要求作家书写人性,从最普遍的故事中揭示人性善恶,满足受众普遍的阅读期待。从《雾月牛栏》《清水洗尘》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的小说总能引起人的心头一震,产生强烈的共情,而这些源于作者对笔下人物细致入微的考察,将最真实的人性加以呈现;而在最近两部作品《候鸟的勇敢》和《炖马靴》中,作家塑造了具有善念的两个好人,他们对万物怀有悲悯之心,这是迟子建小说人道主义情怀的再次延续,由小说人物带动来传承悲悯情怀。
悲悯,是以一种充满善意的方式对人性进行问候,它不是妥协,而是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崇高的尊重。在小说《候鸟的勇敢》之中,张黑脸对候鸟的爱护便是对悲悯情怀的生动阐释。张黑脸在候鸟受伤时给予悉心照料,对于候鸟的关怀超越了自己的孩子,张黑脸精神失常,却比他人更懂伦常,甚至从人类道德关系出发来看待候鸟这对“夫妻”,当蒋进发开玩笑要与候鸟同住时,他郑重其事地说:“那可不行,人家候鸟可都是一对一的夫妻,正是下蛋的时候,你掺和进去,万一下个隔路的蛋,孵出来的东西,人不人,鸟不鸟的,那可咋办?”[3]82-83候鸟尚且懂得一夫一妻制,而以庄如来为代表的官员却在光明正大地养情人,人在进化过程中以种族优越性超越了其他生物,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宰,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丢失了道德尊严,最终不如山林间的鸟兽。常人都笑张黑脸傻,而张黑脸却是懂得知恩图报,他尊敬、爱护候鸟,当他的恩人白鹳受伤不能南飞时,他焦急万分“恩人哪,快些好吧……你受伤的这些日子,你老婆来看过你好几回呢,她在门外召唤你,你听见了吧?”[3]162,当东方白鹳的伴侣送走孩子后,又再次回到候鸟管护站,然而却只看到大雪埋藏下两只白鹳的尸体,在白鹳的引领之下,它们的孩子已经安然抵达温暖的南方,成为出色的候鸟,来年便可以独自飞回北方。树森和德秀埋葬了他们,带着犯戒后的忏悔意识,这对可怜人也留在了暴风雪中。瓦城人向往安逸的生活,然而小镇人们也逐渐忘却了原始的善念,张黑脸是心存善念的怪人,德秀师父是被生活伤害的可怜人,他们被瓦城的亲人抛弃,却仍怀着善念对待一群不相识的候鸟,他们原始、老成,看起来落后于这个正在发展的社会,但仍怀着永不腐朽的悲悯情怀。
小说《炖马靴》的主人公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仍然将自己的口粮分给瞎眼狼,在与敌手针锋相对直至对方死亡时,父亲依然保留了内心的善良,并在每年家族团圆的小年夜将这个故事传承下去,也将善念传承下去。父亲的子孙们有了自己的理想生活,他们忘却艰苦,也不再触碰内心的悲悯,父亲想要给子孙传递善念,留存“骨头”,是对于善念的铭记,真善美并不是特存于古老传统之中的美德,在当今社会,人性更具丰富杂乱,当待人接物之时心存悲悯更显得弥足珍贵。无论是张黑脸还是父亲,他们都谨慎对待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忏悔自己的行为,不论是寻求惩罚还是弘扬善念,他们以别样的方式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精神救赎。
迟子建作为生长在东北地区的作家,对于东北大地有着天然的熟悉,她认同并尊重这里朴实古老的民风,在这个东北小镇,有着不同民族的人,他们有着神圣的信仰,相信“万物有灵”,迟子建根植于这块土地,她将这种信仰灌注于作品之中,无论是张黑脸对于东方白鹳的纯粹无比的感恩之举,还是父亲与瞎眼狼之间的惺惺相惜,都是对于自然生灵的淳朴的敬畏,他们怀着最原始的悲悯情怀,对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施以援助之手,他们审视自身,用最虔诚的态度来实现精神救赎,从而保存了善念。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即使是身处边远小城镇的人们也争相加入这个潮流中,追求金钱至上、崇尚物欲,富人越来越多,而恶行也随之积攒,腐朽的气息让小城失去了原本的光彩,人性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人顽固地坚守善良之心,张黑脸埋葬了候鸟,用最后的善举换得了自己出走的机会,留在了暴风雪之中,父亲则用自己上半辈子的经验向后辈传递着生存智慧。迟子建看到了这座城市人心的崩坏,但作者仍然相信善念,小说中灌注的悲悯情怀也是作者内心的独白,以善念对待万物生灵,在传承善念过程中涤荡灵魂,实现精神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