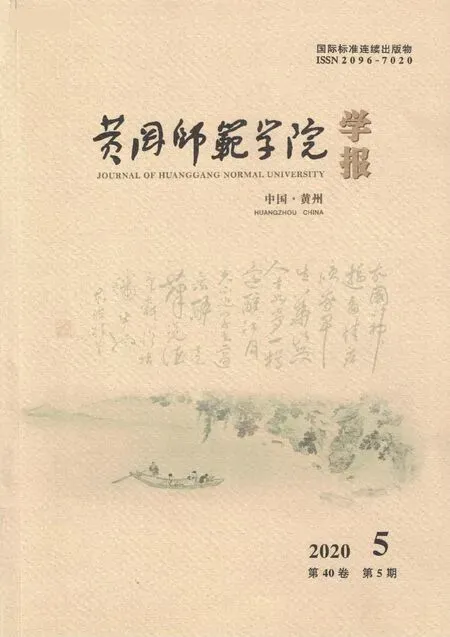试论五缘文化视域中的李贽形象
郭 伟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晚明时期杰出的阳明心学传人、文学家李贽在姚安知府任满辞职后,曾长期寓居黄安“天台书院”“洞龙书院”与麻城龙潭芝佛院等地,专心著书讲学近二十年,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和《初谭集》等。晚年又被当政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其悲剧源于他在诗文中极力张扬的异端思想。一方面,李贽鼓吹个性、肯定人欲,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相悖逆,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他的一生,他的诗文创作不自觉地实现了对传统“五缘”关系的解构,表现了现代人格意识的萌芽。前者因公开宣扬而知者甚众,而后者则深隐于诗文,未见揭橥。李贽的诗歌虽然不多,尺牍杂论却不少,察其诗文行迹,听其独白“心声”,自可得出这一结论。
一、传统儒学视野中的“五缘”关系
在儒学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五伦”,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其中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属于以婚姻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或者说亲缘关系。它并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概括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存在状态,因此,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闽籍学者林其锬教授在整合传统伦理学说和融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缘”的概念,即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1]。其中,“亲缘”居于首位,这种定位与儒学视“孝悌”为一切道德关系的根本或起点的观点基本一致。“地缘”和“亲缘”则等同于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关系。“神缘”和“业缘”乃对“朋友关系”的分类细化。“物缘”涵盖了“五伦”所未能涵盖的物权或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缘”说比“五伦”说更具有普适性和现代性。
与现代社会不同,“五缘文化”在传统宗法社会的表现实质上趋同于“五伦”,即,重视宗族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淡化物缘关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家庭宗族优越于个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经》)的家庭宗族价值比个人价值更重要。“立身行道”虽然也能实现个体人生价值,但问题在于个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存在,终极追求则在“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和“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礼记·大传》)的宏大目标。 传统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宗族之“家”与现代家庭概念不同,农耕经济时代安土重迁的生活惯性和聚族而居的生存策略,导致广义的亲缘关系和狭义的地缘关系趋于重合。传统亲缘和地缘共同构建的村落社群与现代“个人-家庭-公民社区”的基本群己关系模式在本质上存在差异。思想家李贽即诞生在晚明泉州的宗族社群之中。他在家族中曾经扮演的角色正是传统宗法社会“五缘”规范的反映。
二、李贽的“五缘”世界对传统的疏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异端李贽也不例外。其人际交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前半生,读书、中举、宦游,过着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相似的生活。这一时期,他的人脉交往包括以血缘和原始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泉州家族、乡土人际网络,以及以业缘为基础,由求学期之同学、举子试之同年、宦游期之同僚编织而成,从乡土向全国扩展的职业人际网络。其中同学、同年带有广义的地缘色彩,同僚关系则不拘一地,分布于河南、南京、北京、云南等地区。(2)后半生则以接触阳明心学为起点,以中年辞官、客居黄麻为高潮。李贽逐渐抛弃俗务,专心讲学求道,直至被诬入狱、自刎身亡。
(一)前半生:“亲缘”(“地缘”)的被迫全力经营与内心对“神缘”的向往 李贽出身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贫寒的城市塾师家庭,据其外甥苏懋祺《祭卓吾母舅夫》记载:“昔我外祖白斋赠公,诞男五而吾舅居长,诞女三而吾母居次”[2]。由此可知,李贽还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这对于塾师李白斋来说,无疑是一付沉重的养家重担。李贽后来曾回忆往事:“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焚书·卓吾论略》)。“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续焚书·与耿克念》)。之后求学“至年十四……竟以《尚书》窃禄”(《易因小序》),从此失去了集中学习的时间。自二十一岁娶妻黄氏不久,李贽更是不得不为生活而出外奔波。他在《续焚书·与焦弱侯》中曾说:“弟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为此竟陷入“绝粮七日,饥冻困踣”(《焚书子由解老序》)的境地。事实上,李贽多年奔波在外,并没有找到出路。因父亲年老,弟妹也到了婚嫁的年龄,自己又结婚生子,陡增负累,为生活所迫,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应考求仕的道路。中举之后,对仕途不感兴趣的李贽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踏上仕途。在担任河南辉县教谕时,他曾想像北宋邵雍那样筑室百泉,修身养性,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他需要“假升斗之禄以为养”(《焚书·豫约》)。到任后,本欲“闭门自若”(《阳明先生道学钞》附《阳明先生年谱后语》),刻苦探求学问,又因与县令、提学合不来,导致“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卓吾论略》)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不到三月,又离职回乡奔父丧。在丁忧的这两三年里,李贽曾穿着孝服,率领弟、侄辈,参加抗倭斗争。因泉州一带“数年田亩遍为草莽,瘟疫横行,死者枕藉”(《泉州府志》卷七三《纪兵》),故他决定搬迁。然而,祖父去世,次子病死,为消除三年守制的后顾之忧,“权置家室于河内(河南辉县),分赙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卓吾论略》),为了了却三世业缘,他还需把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安葬入土。李贽在泉州期间,辉县饥荒,两个女儿竟相继死去。幸好有好友邓石阳的资助,妻子和大女儿才得以存活。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他的全部心力都在亲缘(地缘)关系的经营处理上。虽然李贽道心颇切,然而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与良师益友、批判武器的缺乏,使得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获得突破性发展。这时的李贽并没有即时留下文字。各种回忆仅见于他晚年的自叙或往来尺牍。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了解到,李贽虽然担负着长子长兄的责任而被迫到处奔波,然而其内心深处并不愿为“亲缘”而放弃对人生之道的探讨。在《卓吾论略》中,他曾回顾第一次做官时的心情,羡慕邵雍能把“求道”摆在第一位:
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
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
(二)后半生:亲缘(地缘)逐渐淡化与以求道为目标的业缘、神缘的逐渐展开 在李贽丁忧结束,携眷赴京任礼部司务期间,他与阳明心学发生了关系。从此之后,在李贽的五缘世界里,以亲缘和原始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泉州家族、乡土人际网络在外在经营和内在关怀上都逐渐淡化,以探求人生之道为基础的业缘、神缘关系网络逐渐展开。与以往总与同僚冲突,缺乏思想切磋不同,李贽在礼部虽然经常和顶头上司“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发生冲撞,不过在探讨王学上却能和李逢阳、徐用检等人打成一片。这正是业缘和神缘结合的结果。事实上,在他未来的人际交往中,职业色彩已逐渐褪去以至于无,信仰、真理所维系的“神缘”则发展成为其“五缘”关系的决定因素。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真正有信仰、有追求的人,无一例外,都离不开同道的接引和相互启迪。李贽“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阳明先生年谱后语》)。后经李逢阳介绍,认识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李见罗,“承先生接引尤勤。”(《答李见罗先生书》)五年后,赴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期间,又结识了焦竑、耿定理这两个最为知心投契的朋友。以焦竑而言,李贽的学问“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续焚书·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李、焦相处时朝夕论道,分别后书信不绝。李贽写给焦竑的信,《焚书》存有八封,《续焚书》存有十六封。《焚书》、《藏书》手稿,亦最早由焦竑过目,焦竑还为两书及《续藏书》、《续焚书》作序。李贽客居黄安后,焦竑从南京过去看望他。以耿定理而言。李贽“与入尧、舜之道”(《焚书·耿楚倥先生传》),亦颇得其启发之力。他客居黄安,一度住在耿家,即缘于两人思想的默契。定理去世后,李贽在《哭耿子庸·其二》中说:“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足见两人情厚。除焦、耿二人外,李贽在南京期间,还认识了王学左派学者王畿、罗汝芳。他在《焚书·罗近溪先生告文》中说:“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再,罗先生者一。……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到南京讲学,李贽认其为师,逐渐接受了泰州学派的部分影响,如“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念。
在云南姚安府知府任上,李贽与罗琪、顾养谦、刘维、李元阳、何守拙等人颇多交往,这种友谊主要不是来自于学术思想交流,而是建立在为政理念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李贽曾为罗琪作《为政篇》,并经常与顾养谦书信往来,如《复顾冲庵翁书》《书使通州诗后》《又书使通州诗后》等。李元阳则盛赞李贽政绩,为其写下《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和《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等诗文。从纯粹职场视角来看,云南任内大概是李贽一生政治实践最充分、业缘关系最和谐的时期。
在客居黄安、麻城期间,李贽彻底摆脱了官场俗务,成了一个潜心治学求道的思想者,或者说,纯粹的学者。他学兼儒、释,熔铸百家,只为探究人的本质,了“此一件人生大事”。他“弃官入楚”的初衷,也正是要“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焚书·复邓石阳》)。这些善知识,既包括儒家知识分子,也包括出家僧众,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分歧,又有共鸣。据《焚书》《续焚书》记载,客居黄麻期间,曾与李贽尺牍往来或有密切交往的人,包括耿定理、耿定向、耿定力、袁宏道、袁中道、焦竑、丘若泰、丘长儒、梅国祯、梅国楼、梅澹然、梅之焕、周思久、周思敬、周二鲁、周贵卿、刘守有、刘谐等,以及火化僧、释无念、常闻、释大智、僧明玉等[3]。在此期间,他的弟弟和女婿庄纯夫曾不远千里看望他,可他大多不愿相见,恐沾染俗缘,妨碍独立。如《焚书》卷四《豫约》云: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乡,独自在此落发为僧时,即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辈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谓已死无所用顾家也。故我尝自谓我能为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诞说大话也。不然,晋江虽远,不过三千余里,遣一僧持一金即到矣,余岂惜此小费哉?不过以死自待,又欲他辈以死待我,则彼此两无且: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劳费,省江湖之风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
何也?彼劳苦则我心亦自愁苦,彼惊惧则我心亦自疑惧;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为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愿遣人往问之。其不肯遣人往问之者,正以绝之而使之不来也。庄纯甫不晓我意,犹以世俗情礼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审如此,则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庄纯甫乎?故每每到此,则我不乐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复来故也。
他在《与曾继泉》(《焚书》卷二)中曾提到出家的原因,表达了大致类似的意思: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在《薙发》诗中,李贽亦表示要尽抛亲缘以证道:
其一:空潭一老丑,薙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其二: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兴粥一瓯。
其三:为儒已半世,食禄又多年。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
在物缘关系上,李贽表现又如何呢?从李贽的生平,我们可以了解其为人,这是一个追求清洁的人,不仅是外在形象上的清洁癖好,还有内在操守的高洁自守。他曾写《高洁说》一文以自我表白。其行与言完全一致,如,他进入仕途多年,子女却有病饿而死者;好不容易做了四品知府,也只勉强糊口而已;在姚安知府任上卓有政绩,却不顾上司荐举,逃入鸡足山读经,甚至直接辞职。这种高洁之士与晚明潜规则盛行的官场贪腐习气全然不合,自然不会汲汲于物欲私利。不过,李贽肯定人类正当的生活利益要求,为此,曾明确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他还认为,“物缘”只是人类生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关系,不需要回避遮掩,“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可以这么说,李贽世界中存在“物缘”,他也理解市民阶层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即对“物缘”的经营,但这从来不是他人生的中心和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仍然保持着原始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的安贫乐道之风。与现代社会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现代观念截然不同。他唯一反对的是事实上“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答耿司寇》)而表面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那种伪君子。在物缘关系上,李贽既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表现出其民主、宽容、理解的现代性一面。
由此可见,李贽的人生轨迹尽管有诸多变迁,然而,其“五缘”观念始终是清晰、完整的,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一方面抱着自己的信念,毫不妥协,甚至连冲突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对父祖竭尽孝养,对妻子弟妹恩爱有加。尽管有时候真情得不到回报,但还是磕磕碰碰地完成了自己应尽的责任。”[4]124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五缘”关系不同,李贽的“亲缘”(地缘)经营是其须尽的责任而并非生命的目的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以探寻真理为基础的“业缘”和“神缘”才是其人际关系的核心。“地缘”“物缘”只是李贽信仰人生中自然形成的客观条件,从未成为他刻意借助和经营的对象,对于这两种关系连带的宗族乡土情结和经济利益追求,李贽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解的,但并未真正认同并深入实践。他是纯粹的真理之子。
三、李贽“五缘”与其人格意识的现代性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离不开“五缘”,或刻意经营,或被迫进入,或自然形成,因为多姿多彩的人生追求而呈现不同的状态。无论外在言行,还是内在信念,李贽都堪称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求道者,最终还成了殉道者。故包括“五缘”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于他而言,在不同时期,或许有所侧重,但其实都只是他探究人的本质、了此生死大事的助缘。这种视诸缘为浮云、一心求道的信仰人生、纯粹人生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与大多数中国人混沌平庸、随波逐流的世俗生存状态是大相径庭的。如同禅宗“身心脱落”“打破黑漆桶”的精神主体,乃是独一无二的“无我”之“我”。李贽尽管不是纯粹的禅宗门人,但他对个体生命本质的紧张探究,他的认真与执着,与禅宗之追求并无二致。这种个体生命的自觉,虽然不是现代学者所研究的“现代性”的主体内涵,却无疑是这一“现代性”形成的前提。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世界体系的观念特征,诸如: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等。在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环境中,李贽思想并没有结晶出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那样的民主政治观念,但他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主张,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思潮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文艺复兴没有直接催生出全部的“现代性”,但它作为启蒙运动的先声,为“现代性”提供了持续生长的土壤。李贽被中国现代学者称为启蒙思想家,原因亦在乎此。毋论其思想,其紧张、生动、悲剧的个体生命史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启蒙。
其次,李贽对“五缘”的具体处理方式,已经表现了他与传统宗法社会“五缘”观的疏离。传统宗法社会的习俗规范与儒家伦理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儒家礼法根植于亲疏差序的宗法社会土壤,故“亲缘”与其首先推而及之的乡土“地缘”关系历来是儒学道德实践事实上的核心地带。晚明士大夫不顾大局,溺于党争,其所结之党,除广涉“业缘”之外,多以“亲缘”“地缘”为人脉根本。虽然士大夫结党以制君权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趋势,在板结的宗法社会土壤上结出的却是苦涩的果实。在这种背景下,李贽最终对“亲缘”“地缘”的疏离、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合法性认同无疑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正如孙隆基所说,“在儒学世界中,家庭中的任何个人——尤其在经济上——被看作是其家庭的一部分,而且通常家庭是不会从经济上(财产所有上)分开的。”[5]55李贽前半生耗尽心力而女儿仍难免饿死,这不仅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统治之下普通士子生存的艰难,而且也刻画出他以一己之力支撑全家,努力维持家族“亲缘”关系的不屈形象。这当然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容易在疲于奔命中迷失自我。“中国文化中,没有合法的个体观念”[5]56,“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个体’从未诞生下来,而是永恒地处于温暖的母胎中,因此,‘个体’也不具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自然更说不上‘个人’的自我扩张、自我开展与自我完成”[5]57。前半生之李贽没有“个人”的自我开展和完成,幸而他有“个体”观念的种子,在后半生得以发芽。
僧、道对“五缘”的认识与处理实践,与李贽大致相似,甚至更激烈,却并没有引起笔者的“现代性”思考,原因在于“李贽虽然出家,但直到最后都没有丧失对社会的关心,没有放弃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探求。如果他作为‘异端之异端’干脆没入个人的悟境,也就不会发生问题了”[4]167,自然谈不上所谓的“现代性”。“现代性”除了有其大致公认的内涵特征,还是一种相互影响、不断生长的过程,是与具体的时空相联系的。佛道两教的“异端之异端”,或致力于个体对空性的精神领悟,或追求个体“身体”的长生不老,都“必须从人情的磁力场中退出才能实现,否则就变成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遂其‘私心’的伎俩”[5]58,其思想观念自然谈不上社会普遍的继承和发展,故而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是不相关的。李贽则是一个正统的异端,或者说,“吾儒之异端”(《呻吟语》),他从来没有退入到纯粹的佛道信仰中去,他抨击程朱理学中那些虚伪、僵化的观念,致力于在主流社会价值观中吹入新鲜而强劲的生气,虽然当时的人们不理解他,然而,他的著作和人生实践却永远活在“现代性”演进的历史当中。
其三,“现代性”的演进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怀疑、不断否定的过程。李贽在不同时期对“五缘”的回应和实践活动,蕴含有紧张的自我批判意识,当然,这不是对“亲缘”责任的否定,而是对陷溺于亲缘而“人生大事未能明了”这一状态的恐惧。这一心理,与其晚年对早年“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这一蒙昧状态的否定是紧密联系的。李贽把早年的这种状态形容为“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因而吠之”(同上)。他用“犬”的比喻把人生中最充实的五十年完全否定了。传统儒家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但他们是根据既定学说和传统规范进行自我反省,本质上不同于李贽的自我立法,自我否定。这种对异化状态的自我警觉,这种在批判旧我中不断自我更新的精神,这种不顾主流众议而敢于自由、独立思考的人格魅力,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贽超越了他的时代。
综上,李贽是晚明时期真正尊重个体价值的“正统之异端”思想家。他在泉州古老的家族文化环境中长大,却毅然弃家剃发,客居黄、麻;身居佛门,却“未尝自弃于人伦之外”(《复邓石阳》)。他对五缘关系的调整与处理是真诚的,是其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体现,是其努力探索人生本质、“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说》)在现实社会关系上的真实反映。李贽与传统宗法社会约定俗成的五缘规范之间的客观疏离状态,体现了萌芽状态的现代性特征。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