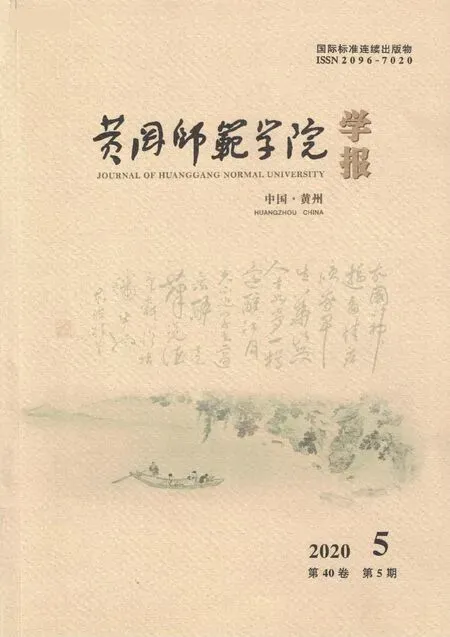老庄身体观及其身体教育实践进境的展开
岳 涛,刘劲松
(1.黄冈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2.湖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身体因作为生命的直接承载而被人类广泛持续地关注。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身体为何者”“身体将走向何处”“生命将如何安放”成为所有的个体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而身体的存在本身,在世俗的、现象的层面,成为人生命存在的直观验证和意义归属,是生命安全感的最后阵地。然而,正如萨特所质疑的那样“现象的存在不是存在”[1]。可见可触的物化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生命本身?生命的本体性是否仅仅表征于肉体的存在?——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似乎都在拷打着以“身心二分”为基调的身体哲学以及在此身体观之下所展开的体育行为,也将身体 “to be or not to be” 的难题,留给了当代人。
在走向“具身化”的身体与运动的反思中,有学者开始探索“我思-我动”的身心共在的“身体图式”[2]。同时,对于身体的“身心一元”东方视角,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如张再林以中国哲学范畴中的“心”作为“生命意向”,而以“身体”作为“生命意向的体现”,从“情”的存在上让身体“身心一元”的本来面目得以凸显[3]。李有强博士从道家身体结构观、功能观及处置观三个维度进行了“身心一元”阐发,并认为“道家与儒家共同完成‘身心一元’的理论阐释。”[4]他们的研究作为对中国身体哲学前瞻的把握,代表着新时代学者们对于东方范式身体认知的有益探索。然而,张再林教授的理论阐发,来自梅洛·庞蒂哲学对东方身体理论的横向融摄,是一种平行的学理观照和定性判断,而非自下而上的归纳;而李有强博士对道家身体观的阐述,是一种创造性描述,例如其对身体观维度的划分,这种划分是否为道家自身内生的维度?道家在自己的语境下是如何谈“身体”的?作为开创中国重身养生先河的道家,是否具备独立成型的“身心一元”身体观而无需与儒家共同完成阐释?这些问题似乎也有进一步明晰的必要。对老庄身体观及其视角下的身体教育实践功夫的挖掘阐述,是从身体哲学史上追根溯源的应然之举,也是从根柢上认识中国传统体育范式的必由之路。
一、老庄身体观的认知显现:从“患身”到“德充形符”
(一)老庄的身体觉醒——身心相离的“忧患” 老庄对于身体的觉醒源于一种对生命存在性问题的忧思。这发端于老子的“患身”思维。《道德经》言:“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5]32在老子看来,无论是处于荣宠之境,还是辱身之境,都足以让人忧惧。在世俗的世界,辱身的忧患自不必多言;然而老子却一反常态地指出,一直为人们所集体无意识地追捧的荣宠,竟然也是足以让人惊怖的——因为在这种生活姿态中,隐藏着巨大的祸患,“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156祸福之间的无常转换几乎是社会乃至人生无法摆脱的诅咒,“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5]23越是荣宠尊优的生活,其危险系数越高。是以老子清醒地看到,无论宠辱与否,都是有身之人的巨大忧患:“何谓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5]32
很显然老子所谓的“有身”是一个高度抽象和哲理化的概念,这背后暗示了一个以肉体形躯来等同于生命主体性的世俗逻辑的巨大缺憾。身体和生命的深度绑定,导致生命的主体性被形躯所定格。在世俗的视域层面,“身体”因为误会而成为“生命”的代名词,生命的本质进而被物化并落入不确定性和有限性的窠臼。根据老子世界观,宇宙间除了无形之大道为永恒存在之外,但凡有形之天地万物,都是有限存在。有身之人也是万物之一,“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正是因为有形,所以作为生命承载体的物化身体必然成为生命的负累,身体意味着对生命本质的限定。有了身体,人们需要衣食等最基本生存物资资料,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有了身体,人们便会有七情六欲,而在老子看来,这些欲求都是将人引向不确定性的根源;有了身体,兕虎、甲兵、水火等等外在事物构成的威胁和负累如影随形;最后,因为有了身体,人之死亡成为必然……而这些,都是因为身体与生命被绑合在一起的缘故,物化身体的有限性成为生命一切缺憾的根源。
庄子也有着和老子类似的警觉,其中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作为一个现世个体在人间世中的生存忧患。人本身作为一个自然个体,其自然之身需要最基本的衣食才能生存,而且还面临着猛兽、疾病等因素的时时威胁;但是若置身于人间世,则一个人不仅要面对来自自然的隐患;更要面对一个无比凶险复杂的群体社会。处于群体社会中的“人”,也即“社会之身”,其自身的属性被人与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定格,如马克思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0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处于人与人的关系所编织的无形之网之中,所以庄子发现有些东西是几乎无法避免和逃离的,包括毁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当然是唯一使毁灭得以发生的存在。”[1]33如萨特一般,庄子看到了人身上所具足的邪恶的、毁灭的力量。他更看到身体在面对人祸时候的无能为力。“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7]169故而他借孔子之口说: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事,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7]144
大戒者,须时时处处引以为忌讳忧患的东西。一个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命”和“义”就是最大的“戒”:父子血亲之爱,是命所注定,永远都是心之牵绊;而君臣之义,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而作为臣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种关系是外界强加而又无法抗拒的。“命”与“义”共同构成绑架个体生命的枷锁,所异者,一个是内在心之枷锁;一个是外在身之桎梏。正因为二者的存在,处于群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便如同枷锁中的囚徒一般随时都有被宰割的可能——这是庄子对于身体的忧思。
事实上,老庄所言的一切忧患,根本上都是世俗生活中“身—心”不能相统合的必然结果。试分析之:
表面上看,老子并无“心”之概念表述,但老子言:“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在此上下文语境中,“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表明“身”在老子的逻辑中,并不能代表生命的主体性。而此言外,真正完整之身必然是肉身和精神(能够意识到“吾有身”、且在“吾无身”预设下依然不丧失生命主体性的存在)同时在场的,如此则身体的内在意义被充实,身体本身也才值得“忧患”,也才有去忧患的知觉主体和价值主体。但是世俗逻辑恰恰是身与心(精神)相分离的,世俗世界不能意识到肉身和生命的逻辑区别,因而简单将作为肉体的物化身体当做生命本身,以致于:
a.将物化身体的缺陷当做生命本质的缺陷,从而丧失对于生命更高层次意义世界的追求。
b.将物化身体的需要当做生命根本的需要,从而绑架生命本质而追求身体欲求之末,将生命置于欲望竞逐的高危境遇。
而在庄子,他已然在概念上实现了身心辩证的突破。天下大戒一者命也,不可解于心;一者义也,身之无所逃。这表明在庄子的“身体—生命”预设中,身心二者是同时都考虑到的要素,都是影响生命本身的重要内容。然而世俗世界之所以有大戒,依然源于二者的不相合:
a.“不可解于心”者,是心对于身的羁绊和相违,身欲安而心不定;
b.“身之无所逃”者,是身对于心的绑架和挟持,心欲自由而身为累。
在这样一种辩证中,庄子分明看到世俗的痛苦所在,那就是要么身违于心,要么心违于身,这都导致了生命本身的不完满。
从根本上而言,老庄二人对于身体之忧患是相同的,相异不过是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他们二者其实都是出于对世俗世界物化身体的认知担忧。正是由于世俗世界在对于身体本身的认知上存在着集体无意识的误会,那么物化身体的逻辑设定必然导致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舍本逐末,指客为主——在身心相离相违的生命历程中,将物化身体的弊病放到最大,弊于世俗的小成而不识大道之体,最终不仅戕害了“身体”,而且被身体所绑架的生命本质亦遭受株连之祸。
(二)老庄“身心一元”的认知定位:“德充形符”的理论推证 鉴于对世俗世界身心相分的身体认知预设的巨大缺陷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命忧患的清晰洞察,老庄道家在逻辑层面展开了“身心一元”的身体原初面貌的理论确证。进而言之,老庄哲学语境中的身体必然是“肉身—精神”同时在场之身,身心不可缺亦不可分。老子所最为推崇之“身体”乃是“婴儿”之身,如其言: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虫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5]149
此语不仅仅就婴儿身体精气充盈、柔和之至的生理状态而言;从婴儿之所以具有虫蛇不伤,凶禽猛兽不害之能而言,其根源在于“含德之厚”。德者,内在之德也,有精神、心灵的指向。那么婴儿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老子言:
“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5]50-51
在这段话中,如“婴儿之未孩”的“我”的心理状态在和世俗之人的强烈对比之下得以彰显:世俗之人追名逐利,对外在于己的事物有强烈的竞逐之心,心在身外,身心从未相安过。而婴儿般的内心世界是混混沌沌,无所分别,身心一体,物我相冥的。概而言之,则婴儿恰恰意味着身心一体的混沌未分之态,物我不别的先天无极之体。
而在庄子,这一辩证被进一步明确化。在《德充符》一文中,庄子有一则经典寓言:一群小猪围着母猪吃奶,而母猪在生完小猪之后就死了,小猪吃着奶发现不对劲,惊惧而走——刚出生的小猪并无分辨意识,其所作出的行为非出于理性判断,而是出于一种天然而有的直觉,没有任何矫饰;那么同样是母亲的身体,生死转瞬之事,形躯并无不同,怎么会出现前者相亲而后者相远的矛盾状况呢?难道是小猪不爱他们的母亲了吗?非也。对于这种现象,庄子解释说:
“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7]192
——原来在小猪眼里的有意义的母亲之身,并非是形体之身,而是有着内在精神(使其形者)贯注的活活泼泼的身体,是有灵魂之身。庄子以此案例说明:只有有着内在精神(内德)充满的身体(形符),才是有意义的身体,此亦“德充符”之原初义与真实义。而这个内在精神一旦失去,身体也就立刻丧失作为“身体”的意义。回看老子所推崇的婴儿之身,“含德之厚,比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恰恰意味着婴儿“内德”(内在精神)的圆满充塞,以及身体的柔和之至,是身心一体的圆融生命状态。且“婴儿”作为生命体之初始状态,也本然地象征着生命的原生之态,“身体”的原初属性本当如此——在这一问题上,老庄的认识也是高度一致的。
二、老庄的身体教育实践——“身心相合”进境中的身心蜕变
老庄从经验乃至事实、逻辑层面都认识到,身体必须作为“身心一元”之体而非单纯物化的肉体形躯,才具备完整意义上生命体的代表资格。这一认知基础决定了老庄对于身体的教育实践工夫都是立足于“身心相合”的身体预设之上的,这是道家开展身体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起点。沿此起点出发,老庄之身体教育开始进入以无为虚静为特色的工夫进境。
(一)“重身”与“恬淡”——身心内收的初始养生境界 老庄以养生为代表的身体教育既立足于身心相合的身体预设,那么迈出养生实践的第一步也意味着需要将人们外放竞逐之心收敛回来,使得身心统合一处。由于世俗的芸芸众生大都生活于集体无意识的名利竞逐之中,且看不到身心相违相离的危害,所以老庄在此层面上所作的前期努力,就是改变人们对于司空见惯的世俗价值的认知,开始反思生命本身的存在性问题。前文已经谈及老庄对于人身体的忧患,其实患身思维本身就是对世人从认知、价值层面展开的身体教育。老庄希望通过祸福难料、多欲害身的警醒,使人们放弃以身捐物的违心生活,开始重视自身的生命载体“身”,放弃对外物的追逐,从而进入一种无为恬淡的生活状态。细述之:
老子的“大患若身”直接导向了他的重身主张,老子言:“名与身孰亲?货与身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5]125“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5]32世俗生活中,人们最喜欢并为之追逐的东西无非名利好货、天下高位。然而在身体与名利、天下的比较与反思中,老子指出:身体的存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其足以让名利、天下变得黯然失色,世俗所奉为圭臬的价值在此比较之下不过是无关乎生命本质的外物罢了。失去了身体,名利、天下都不过是虚无的画饼——身之不存,名利天下将焉附?为何要用贵重之身去博取轻贱的名利天下呢?而庄子更是指出,其实用身体去博取富贵寿善的行为本身也是痛苦且无意义的: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之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7]541-542
求财富之人,苦身疾作,形体疲敝;身份高贵之人,机关算尽,忧心忡忡;高寿之人,神明昏愦,邋遢龌龊地苟活;而为善之人,常多烈士,求善却不足以存己。所以这些所谓的富贵寿善,这些立足于世俗追求的价值观,非但不能导向真正的幸福快乐,还对人的身体、性命带来巨大的危害,况且也不能“活身”。换句话说,并不能解决“to be or not to be”的生命存在性问题。
正是对于以功名利禄为代表的世俗价值观的深度消解,老庄完成了走向以“身心相合”为特征的身体教育的伟大转折——对于外在名利富贵价值观的消解,使世人首次将意义世界的重心由外物而转向自身,将飘荡外放的竞逐之心收敛回来,开始关注和聚焦于自己的“身体”;如此则:
a.形躯不再受名利之心所奴役;
b.心亦不再为身体无尽的欲求而蝇营狗苟。
如此,则“身”与“心”不再相违相离,首次实现统合与回归,这也就意味着“身心相合”境界的进入。
当然,初步收回外放之心的身心统合还是比较浅层次的,但这种状态已然放弃世俗所追逐之物,人之身心状态由追名逐利的劳顿切换为无忧无虑,更直观地说,就是进入了一种无目的性的自然天放状态——老子称其为“无为”,而用庄子的话来说,叫做“恬淡”。老子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言:“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7]411-412“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7]479“遗生则精不亏。”[7]561在老庄看来,恬淡无为的生活样态是自然万物的本然生存状态。“万物之本也。”那么进入这种状态也意味着对于生命本质的回归,所以这种生活状态之于身体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当一个人处于平易恬淡的生活状态中的时候,内心没有忧患,那么外在的病邪之气就不会侵扰身体;其次,那种遗生弃世的隐士生活,天然就是保守精气,不使身体精气亏损的生活姿态——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身体教育的最基本效果已经具备,至少,通过运动锻炼所要追求达到的体育效果已经有了。
当然,正如任何理性的思维和巧妙的方法也难以想象这样一种身体教育的结果那样,理性和巧妙的语言也无法尽述老庄之身体教育的方法。老子和庄子恰恰是通过无为而达到了有为的效果;以一种负向的方法[3],实现了众人汲汲以求的正向的身心安乐健康之目的。如恬淡之主张,看似一种味觉上“没有味道”的比拟,实际暗示了生活放弃了感官刺激,远离了身心牵绊,是无心于事或无事于心的一种身心安然的感知状态,“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 没有忧患和病痛,这不正是最初层次的身体教育所要追求的吗?
另一方面,以恬淡为特色的主张似乎也并非一个“体育”的命题,甚至也并不直接导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为发达肢体、健壮体魄的体育结果。但是,老庄虽不主张更高、更快、更强的身体目标,但却以一种减法思维,成功消减了世俗生活、名利物欲对于身体的戕害与破坏,对于人德行与性格的滋扰与侵染,且在无为恬淡的生活状态中,身体和心灵得到了根本性的滋养与保护,病痛不生,外邪不入,这种结果并不比今人所追求之强健体魄有丝毫逊色。
从重身到恬淡,老庄的身体教育由外求转入内求的全新阶段,也意味着“身心相合”境界的进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身心相合的初始境界而已,随着这种境界的深入,“身体”还将发生更为微妙的蜕变。
(二)“抱一”与“心斋”——身心相合的深入养生境界 如果说恬淡作为一种远离世俗纷争,不再受形劳心忧之苦的生活状态的“身心相合”,那这种状态不过是无意识的,且层次较浅的体认境界,是自然生活的境界。当前许多长寿之乡的高龄老人,他们之所以可以尽其天年,其实是不自觉地符合恬淡的生活姿态而已。但老庄所主张的养生,也就是身体教育的主张并不止步于此,除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天放,老庄更主张通过有意识的“致虚守静”“抱一”“心斋”等独特心法的展开,使人进入更深层次的“身心相合”。老子言:
“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5]25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5]39
“圣人抱一为天下式。”[5]58
在如上文本中,老子提出了几组身心修养的命题:
第一,使魂魄(身为魄,心为魂)相抱相守,使之不要相离。
第二,聚集天地之气,使身体变得像婴儿般柔软。
第三,清洗内心的杂念,使其像不沾尘埃的镜子一般清净。
第四,使内心虚静到极致并持守这种状态,万物虽千头万绪而并作,“我”只去静观其本源。
第五,始终坚持“抱一”的状态。
这是老子对于身心修养之法的描述和阐释。这几组命题从表面来看,它们都不是身体肢体之运动,无任何操作性动作可循,然而每一个主观的个体却可以在自身的“虚静”“观复”中亲身去实践、感知和验证。而且这个过程是身体有意识地参与的,但不表现为运动。换言之,身心相抱相守、致虚守静、扫除杂念都是通过主体性的身体知觉可以实现并验证到的状态,他人虽不能见亦不能触,然养生者自我之身心是可以感知和体会的。值得关注的是,在道家的语境中,这些方法并非像外在操作要领方法一般可以绝然分开,致虚守静之中本身意味着身心相守,倘若不能虚静,则心即外驰,自然有妄念产生,也称不上虚静;且气随意动,心念不守则气亦无法聚集,致婴儿也成为了空话。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层统合的关系,则明白身心相合状态之下,恰如梅洛·庞蒂所言之“身体意向性”,这种“知觉”作为“整个存在的意向”[8]113始终聚焦于自我的身体而不外发,内观身心之静定、妄念不起则心不外驰,内心清朗如明镜,身心在这种笃静中达到一种深度的统合,天地之气得以抟集,身体也会产生婴儿般柔和之至的生命力。至于这种“气”是以何种方式在人体内表征存在,人又是如何觉知“气”之存在?有学者以“气化”现象的身体感知来解释和描述视觉不可见,语言难以描述的“以身观复”为代表的传统“身体技艺”,认为这种“气化”现象是有迹可循的,“需要练习者长时间仔细向身体内默默地、 暗自地体悟和洞察其‘内动感’……唯由身而体认之,方可能及。”[9]以此,我们亦可推知,只要真切掌握了这种“身心一处”的观复、体察功夫,身体的气化蜕变及对此默会觉知的证悟当可如期发生。
庄子与老子在以养生为代表的身体教育实践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具体方法主张的描述上也更为深入。尤其是通过 “心斋”等经典案例的阐发,庄子将人们带入一个身心高度统合的养生境界。详见“心斋”例:
“回(颜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7]137
“心斋”状态的进入,首先需要养生者纯化心志而守一不移,遗忘感官耳朵的外听之能,将主体的听觉专注力聚焦于内心,进而聚焦于呼吸往来之气。如此则内听内守,内心的虚静会让弥沦无际之气聚于体内,那么所聚之气,如同人心所吃斋饭食粮一般,为人之精神心灵供给足够的能量和营养。那么在此身心深度相合的境界中,无论是老子的致虚守静、抟气,还是庄子的心斋之法,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通过虚静凝神以养气。老子言,“专气致柔”;而庄子言“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言语虽繁,而所言之“心斋”亦实指虚空之气也,有学者认为庄子实为中国气功学之真正鼻祖[10],此判断不无道理。
在此境界中,通过对于气的涵养,人之身体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前文所言的“婴儿之柔”为例,这种柔恰恰是生命力潜力无限之表现,如婴儿可以嚎哭整日而嗓子不嘶哑,未知男女之事却可以生殖器时常勃起。老子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5]193越是看起来柔弱的东西,其本身越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表面看似强壮之物,在生命力上已然步入下坡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5]80如此则强壮、坚强之身躯恰恰是生命力走向形躯的极限、即将要衰老的表现——在此意义上,老庄以身心相守为代表的身体教育将在此层次上实现对那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的超越:后者对于身体健康的追求将止步于此,而前者,也就是以“身心深度相合”为特征的身体教育,还将走向更为超拔的境界。
(三)“忘我”与“无身”——“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 随着“身心相合”境界的进一步深入,养生者的身体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而生命本身也将获得升华。在以致虚守静、抟气致柔、心斋为代表案例的身体教育实践中,老庄主张通过身心的相抱相守,以身之笃定与心之静净来实现气的抟集,使之聚于养生者之体——而气之为物,在老子的世界观中,万物皆由天地阴阳二气交感而生:道生混沌一气(道生一),混沌之气化分阴阳二气(一生二),阴阳二气相交而成中和之气(二生三),中和之气生万物(三生万物)。在此逻辑上,气是由道化生万物的必经样态;换言之,气是道与万物之中介——那么作为养生者个人,体内之气每抟集深厚一层,也即意味着离体道更近一步。所以,当人之身心相合进入一个临界点之时,或者说人体之气抟集到一个临界状态之时,身心的蜕变和脱胎换骨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这种临界状态在庄子的许多养生案例中可以见到:
如“坐忘”例: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7]259
又如南伯子葵与女偊的传道案例: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7]231
在坐忘案例中,颜回通过一个忘字诀的层层深入,从开始的忘却仁义、忘却礼乐……最后进入“坐忘”的忘我之境。也就是连自我的形体、自我的知识之心都忘却了,达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天人相合之境。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身心的深度相合,又何有“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呢?根本还在一个“气”上,庄子言“通天下一气耳”,当养生主体进入身心深度相合而物我相忘之际,体内之气与天地之气实现了通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此意义上,天地万物成为我“身”之延伸;而“我”的生命主体性因为获得了“大身”而成为“大心”,因而可以“游乎天地之一气。”——摒弃小我的“身心相合”,而进入“大身心相合”的超越境界,是为“天人合一”。
而在南伯子葵与女偊的传道案例中,通过守字诀的展开,也即“身心相守”境界的逐层深入,养生主可以逐渐摒弃天下外物乃至生活本身,进入到“朝彻”的顿悟、“见独”的与道为一和体验到时空的究竟极致,最后进入到“不死不生”的永恒境界中——那么反观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包括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在内的所有教育行为,人们所孜孜以求的德性、智慧,对于真理的追求,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理论上皆于此际获得实现。而这一效应在《庄子·说剑》篇中可得到诠释:
首先,“庄子”是一个大家所认可的现实中的剑术成就者,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位武术家。“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7]894言其剑术高明。其剑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7]895示虚开利,后发先至是剑法要诀中的精妙方法论,也侧面证实了他的剑道修为。然而,庄子在剑道上的最高境界,却是“无身”“无剑”的。见其“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三论:
“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
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谭,以豪桀士为夹……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
庶人之剑,蓬头突鬓,……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7]896
庄子说剑三论是在劝说赵文王放弃豢养剑客整日斗剑等无益有害行为的背景下展开的。“示虚开利,后发先至”的剑法论证明“庄子”本人显然是一个剑道高手。然而,即便如此,他所最认可的“天子之剑”恰恰不是现实中作为兵器的剑,剑法也不是那个“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的庶民剑法;而是以天下九州为剑身,以四时五行阴阳为法度,可决浮云地纪之“剑”,以此可见庄子的宏大心胸,确然已进入“天人合一”之境。以“剑道”论“治道”,无我无身无剑,心系天下之安而能以剑道喻之,点化愚顽专制的君主放弃无意义行为且能全身而退。这是“庄子”本人在剑道上大成就、大境界、大智慧的体现。
如此,若仅于世俗体育之“健康长寿”“更高更快更强”之目标而比较,则老庄之身体教育结果,亦远远超越于此,甚至可能获得“复归于道”的生命真谛——生命意义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完满与实现,这亦是老庄身体教育之终极落脚点,也是超越性之所在。
三、小结
老庄的“身体”在存在性的忧患中获得关注而显现;究其根源,这种存在性的忧患源于世俗之人的“身心相违相离”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认知误区。推而言之,则“身体”之本然面貌即是“德充形符”的,也就是“身心相合”的,而人类一切的不幸皆源于世俗价值追求所导致的“身心不相合”。老庄所言之“身体”,是有灵魂的身体,也即“身心一元”之体,而非简单物化的肉体形躯。此为老庄所展开一切“身体教育”的认知基础、逻辑起点和方法论。
自摒弃外在的价值而收回外放之心开始,老庄的身体教育实践进入第一个初级的养生境界:身心相安、自然恬淡。如此则不受人事羁绊伤害,外邪不入,病痛不生,身体因此而自然健康长寿。随着身心相合的进一步深入,养生主进入“致虚守静”的养气境界,天地之气因身心之相抱相守而抟集,身体变得更加柔和,获得如婴儿般的强盛生命力。当这种身心相合再进一步深入,进入“坐忘”“见独”的状态,身体之抟气突破身体临界点,身体与天地之气相通融,如此则打破小我,进入“天人合一”的体道境界。依此身体教育实践进境逐级深入,个体生命体验将切实突破和超越身体及健康的范畴,而有希望触及生命、宇宙之真相,开启生命觉悟,而最终破解“to be or not to be”的终极存在性困境。
在老庄“身心相合”进而“天人合一”的身体教育实践中,身体本身的蜕变乃至智慧的开启会随着境界的升华而共同-互根地发生,并最终达到“复归于道”的生命本质。由老庄所开启的“身心相合”的养生范式为身体教育开启了一条内向的、通达生命本质的通道,这种独特性和优越性是以“身心二元”为认知基调的体育范式所不能具备和达到的。也是后者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借鉴、吸纳和融摄的。重识老庄身体观,进而认识老庄在此身体观基础上所展开的身体教育实践,不仅意味着打开身体-健康的另一条可能路径,而且,一种道家范式的身体认知视角及其理论支撑的身体教育形式的存在,对我们突破对身体的物化的刻板认知,拓展体育概念之能指与所指、方法内容之多维,并探索大教育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层次,开掘其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无疑都有着巨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