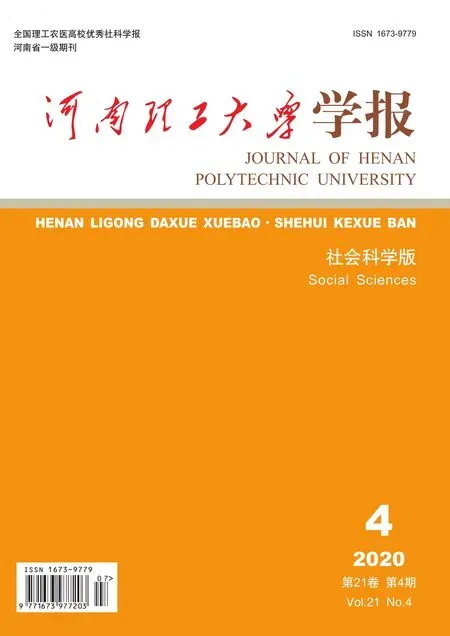明清时期河洛地区列女形象探析
——基于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的考察
杨 洸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列女的定义和烈女不同,是众女、诸女之意,列女按事迹特色可分为节妇、孝妇、烈妇、贞女、慈母、义妇等。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纂修逐渐走向鼎盛,《列女传》所占的比例更在不断提升。嘉庆《洛阳县志》一书“对洛阳地区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记载的较为详尽,注重地方性,所收集的资料也颇为广泛”[1]131,该书中的《列女传》记载了古代河洛地区的列女群体,据统计,共记载了自西汉到清朝嘉庆年间1 876名列女,其中明清时期的列女所占比例最多,约为99.20%。
目前关于区域列女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如:黄建军和谭鑫《论道光〈宝庆府志·列女传〉女性形象脸谱化叙述》、范佳《明清宜荆地区旌表列女探析——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黄连云《清代松潘县“列女”群类型与旌表分析》、杨洸《论〈道光重庆府志·列女传〉中的列女形象》、周毅《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孙利竹《〈承德府志·列女传〉研究》、吕娟娟《清代山东滕县列女群体管窥》、王志跃《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许莹莹《清代闽西客家地区列女群现象分析——以乾隆〈汀州府志〉记载为例》、胡静《清代甘肃列女群的类型分析》以及胡芳和孔繁华《清末民初徐州地方志中〈列女〉的理学观念及其嬗变》等文章分别探讨了宝庆、宜荆、松潘、重庆、安庆、承德、滕县、贵州、汀州、甘肃、徐州等区域的列女情况。而作为十三朝古都和“河洛文化之核心”[2]的洛阳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学术界对古代河洛地区的列女群体一直鲜有研究。坦言之,这是女性研究领域乃至河洛文化研究的一个遗憾。本文以该方志为中心,拟对明清时期河洛地区的列女形象进行研究,力图以此弥补古代洛阳地区女性研究的不足,并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古代洛阳传统社会的文化风貌进行探究。
一、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列女形象的分类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共有三卷,分置于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七和卷第五十八。三卷中所记载的明清时期列女多达1 861人,通过对她们的事迹进行细化、具体化的解读,可将她们形象分为六类,即: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以死殉道,拒辱自戕;极尽孝道,赡养舅姑;吃苦耐劳,刚强持家;教子有方,扶子有成;乐善好施,扶弱济贫。
(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的节妇、贞女
节妇是指那些已婚夫去世,终其一生为夫守节的妇女。而贞女是指那些未婚夫已死,终生不复嫁、守贞至死的女子,《礼记》曰:“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3]322。明清时期,节操对妇女极为重要,“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301的贞节观念深入人心。在《洛阳县志·列女传》所载的女性中,节妇和贞女的数量是最多的,她们在丈夫或未婚夫死后,纷纷走上了守节、守贞的道路,表现出对夫家的无限忠贞。如:
“任恭妻梁氏,十九寡,抚遗腹,苦节七十余年”[5]600。
“李全义妻韩氏,二十二岁寡,无子,家酷贫,或劝子嫁,不可。值年荒,不肯行乞,忍饥昏仆,有族人馈之粟,绝而复苏,卒不死,寿至九十有三”[5]625。
上述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节妇在丈夫死后却要过着几十年孤寂冷清,青灯荧荧的日子,个中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而命运更为悲惨的是那些未婚守贞之列女,她们没有爱情的付出,且没有亲生子女,甚至终其一生未曾与未婚夫相见,却要为夫家守贞一生,如:
“霍文凤聘妻王氏,许字文凤,未及归,文凤死,氏坚志守贞,舅姑为之立嗣以老,乾隆四十一年旌”[5]599。
此外,在县志中还有“一门多节”的现象。一门多节相较于一门一节,显然更容易被政府旌表嘉奖,还能名扬乡里,彰显出家族节义的家风特色。如:
“诸生潘景辰妻刘氏,年二十三守节。子玫甫,入庠,卒,妻董氏,年二十二孀。孙辉曾妻温氏,亦早孀。称三节,旌”[5]585。
“牛从士妻雷氏,二十四岁寡,遗孤世臣甫及晬。伯之子曰世奇,奇亦少孤,雷氏怜而抚之,为娶于高,世奇早卒,高守志。世臣娶于郭,生一子曰相卿,而世臣亦卒,郭亦守志。郭年尤少,有美色,族人谋欲嫁之,郭氏剪发自誓。相卿之之曰文彪,娶于郑,郑氏二十一岁守志。有司表曰四节之门”[5]613。
其实,一个家族出现多名节妇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富有,能够同时承担得起几个节妇同时守节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群体的鼓励和舆论导向,使得她们的精神压力比那些一门一节的节妇大,多人一起守节,便能相濡以沫有了感情慰藉”[6],再者,家族有了守节的榜样,后面的寡妇便不由自主地追随,谁若不守节不仅有损门楣,辱没家风,而且自身也会名誉扫地,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据统计,《洛阳县志》中所记载的节妇和贞女,基本上都是从16~30岁开始守寡,守寡时间最长能达到70多年,文中多次出现“苦守”“苦节”“苦志”等字眼,可见列女守贞节之艰辛,她们用血与泪谱写出封建时代河洛妇女不幸命运凄惨的悲歌。
(二)以死殉道,拒辱自戕的烈妇、烈女
烈妇主要是指那些用死亡等“惨烈”方式来捍卫贞节的列女,其与节妇的主要区别是节妇采取断送幸福或毁容断发的方式来守护她的贞操,而烈女则通过牺牲生命的方式以保全她的贞节。节妇的特点是守节,而烈妇的特色则是殉身[7]247。县志中这些烈妇的数量亦不在少数,她们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夫死殉夫的烈妇,这一类型的妇女因丈夫死亡悲痛不已而立即自杀,为夫捐躯,如:
“贞邱郡主,伊府安惠王之女,下嫁仪宾蔡昇,弘治初,昇卒,郡主即日触壁死,事闻,诏旌其墓”[5]580。
“马义妻苏氏,乾隆乙巳之岁,洛中大饥,义挈妻就食樊城,久不得归,嘉庆丙辰,樊城教匪滋事,义为流贼所戕。苏投井死”[5]641。
第二,夫死后被逼改嫁而选择死亡的烈妇。她们被逼改嫁的原因多为公婆可怜她们年纪轻轻,不忍她们凄苦守节一生;或者是亲属贪恋财物,逼迫其改志另嫁。但她们恪守着“列女不更二夫”的传统礼教,当这一“理想”受到威胁而无法实现时,她们就以死亡的方式来保全自身的名节。如:
“温显祖妻徐氏,二十夫亡,坚志守节,翁怜其幼,令改适,遂自缢”[5]599。
“王开基妻段氏,二十一岁寡,舅受富室子金,谋夺妇志,遂雉经死”[5]612。
第三,受性骚扰后而自杀的列女。她们在遇到流氓、无赖或流寇强暴凌辱时,往往以死亡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声誉,做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生命捍卫节操,诠释了“烈”的意义。如:
“处女书姐,有志操,县东乡孙学成之女也,笄而未嫁。乾隆庚戌初冬,女擣衣于室,其邻牛戌者,踰垣入,以言调之,女奋詈大呼,戌惧遂逸去,女受辱不胜忿,投井中死”[5]610。
“董景行妻郭氏,贼入城,避于方家堂,贼驱之行,氏抱柱不从,贼断其手,死犹抱柱不脱”[5]581。
(三)恪尽孝道,赡养舅姑的孝妇
《女范捷录》曰:“子媳虽殊,孝敬则一,夫孝者百行之源,而尤为女德之首也”[8]47562。公婆相当于妇女的再生父母,是否孝敬公婆是衡量媳妇道德品质的首要标杆。《洛阳县志》中记载了一些列女,在亡夫之后,一方面青灯寂寞,苦守贞节,另一方面恪守孝道,孝敬公婆,她们的形象符合正统价值观, 深为朝廷所重视和推崇。如:
“卢景福妻王氏,景福亡,氏事姑惟谨,曰:‘若稍有不诚,则有负于泉下人矣’”[5]580。
“李本质妻曹氏,夫早亡,姑年逾九十,多病。氏奉孝不懈,后以子裕贵,封淑人”[5]586。
“陶瑞妻姜氏,十七岁寡,守志时,舅已先卒,姑待之虐,欲夺其志,姜刎颈几死,乃已。后姑得末疾,卧榻数年,饮食动作需人,姜氏侍汤药惟谨,姑乃泣曰:‘吾负吾贤妇矣’。姜氏今年六十”[5]632。
当公婆尚在人世时,王氏和曹氏能尽心尽力代夫行孝,体贴入微,奉待姑舅,周到细致,彰显出古代传统的孝德。守节期间受到姑婆夺志、虐待的姜氏,却能以德报怨,在婆婆病重时勤谨伺候,用自己的孝行感动了婆婆,从而化解了婆媳之间的矛盾。此外,一些孝妇面对姑舅病重时,竟然采取“割股疗亲”的孝行,其情状可谓惨烈,令人触目惊心。如:
“黄克孟妻吕氏,为黄养媳,年十五未婚,姑以胃痛叫嚎七昼夜。氏割股肉和药以进姑,立瘥。邑令旌之”[5]597。
“黄来朝妻潘氏,年二十而寡,奉姑舅以孝,其姑尝病失明,艰于药饵,氏刲臂以祷,姑目如初。闻名乡里,旌”[5]603。
“儒家宣扬的孝文化是明清两朝治国之策,割股疗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俨然逐渐成为孝行的表达”[9],其原因不在于此举的医疗效果,而是在于统治者对此举的认同和褒扬。吕孝妇和潘孝妇等守寡妇女通过“割股疗亲”的孝行,不仅可以表达自己强烈的守节志向,还赢得社会的赞扬,更受到地方政府的旌表,获得一些免除赋税的优惠政策。
(四)吃苦耐劳,刚强持家的勤妇
《女论语》曰:“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奢则家贫”[10]57。在古代,勤俭亦是衡量妇女道德的标准之一,妇女勤俭与否往往关乎家庭的兴衰。县志中一些列女在失去丈夫这一重要的经济、精神依靠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来应对“抚孤养老”的残酷现实,手无缚鸡之力的她们只能靠勤劳的双手,独自肩负起赡养公婆、抚育子女的重任,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
“崔尔朝妻董氏,年二十二而夫亡,孀姑老而子方在抱,家徒四壁,纺织、勤耕以奉养,艰苦备尝”[5]603。
“刘法曾妻赵氏,法曾亡而子方幼,氏贫甚,以绩纴自资,备历艰苦,抚之成人”[5]605。
“孙恒有妻李氏,年二十七而寡,家无恒产,抚孤艰辛,舅姑亡,贫不能殓,人咸匍匐救之,常闭门绩至劳瘁,邑令旌其门”[5]604。
家境贫困的董氏、赵氏和李氏,不仅要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而且还成为家庭的顶梁柱,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她们家无恒产,也没有族人的救济,只能靠纺布、女红或种田等辛勤劳动来养活家人,她们那种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吃苦耐劳恒心和顽强持家的毅力可圈可点,是古代河洛妇女中的典范。
(五)教子有方,扶子有成的良母
《女论语》曰:“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于母”[10]55。教育子女成才是女子身为人母的基本天职,而母亲的素质往往会决定子女的素质,而子女的素质往往会决定家族的兴衰。丈夫去世,就意味着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崩塌,列女们想要中兴家族,只靠自己的辛劳打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子女们抚育成才,家族才有崛起的希望。县志中的列女在守节中亦代夫尽了为父之职,为夫家绵延后嗣,教子有方,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有所作为,来慰藉亡夫的在天之灵。如:
“孙国儒妻刘氏,夫故,氏年二十五,孝翁姑,抚弱子,以纺绩供,俯仰教二子,秋阳、东阳俱列庠”[5]582。
“潘鸣珂妻曹氏,早寡,课子有义方,子廷芳、承芳并补博士弟子员”[5]613。
“姬凤翔妻杜氏,二十九岁寡,姑舅年老,营坟建祠,求名师教子,守志五十余年”[5]625。
“县学生宁瑗,妻邢氏。瑗物故,氏哀痛欲绝。舅姑再三慰之,乃泣受命。及舅姑殁,以从子书为嗣,更勉为二人卜葬。尝课子读书,抚而泣曰:‘尔父十四为诸生,有文名。汝虽稚,能不自勉也!’”[5]606。
上述这些良母们在夫死子弱的残酷现实下,化亡夫之痛为母爱力量,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抚养子女和培养人才的双重重任,他们不但在生活上细心照料子女,而且还课子读书,言传身教,使其在学业或功业上有所成就,光耀门楣,谱写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母教篇章,更是充分彰显出河洛地区崇文重教的优良社会风气。
(六)乐善好施,扶弱济贫的义妇
《内训》曰:“吉凶灾祥,匪由天作,善恶之应,各以其类;善德攸积,天降阴骘”[11]725。古人特别信奉“积善祛灾”的说教,认为降福降灾完全是由自身的行为决定,而广施善举可以给个人或者家族带来好运。丈夫死亡就意味着家道衰落,家庭失去了重要的劳动力和精神支撑,只有靠遗孀的双手撑起一片天,古代河洛地区的列女们为了使家宅兴盛,一改颓气,往往乐善好施,扶弱济贫,救苦救难,成人之美。如:
“贡生董重光妻吕氏,于归后,奉孀姑以孝称,夫卒,无子,以姪为嗣,严而有恩,尤识大体,于乾隆三十四年,捐田七十亩为先贤祭田,兼仿范文正公义田遗意,以其余济族之贫者,其族长有骐,为文记其事,立石于家祠前。其他如施棺、施粥善行尤多。乾隆三十九年,旌”[5]602。
吕氏幼年就精于妇道,丈夫死后,上待公婆以孝,下教侄子以严,并效仿先贤范仲淹,捐私田七十亩为义田,用来祭祀祖先、赡养族中贫困者,此外,她还经常施棺济贫,施粥赈饥,称贤乡里,族长为其立文,政府为其旌表。如:
“庞廷选妻贾氏,二十八岁寡,守志好施,时洛阳饥,出粟以赈,今八十有一,子昇”[5]633。
“刘辅臣妻,王氏,早孀,姑病,亲奉汤药,衣不解带,迨姑卒,毁几灭性,又好施与,常出资修建海潮庵”[5]610。
上述列女,其宅心仁厚、高风亮节令人感赞。这些列女普遍具备救苦救难、反哺社会的高尚品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尽管青年丧夫,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却长存爱心,积极参与地方赈灾济贫、修葺庙宇等社会慈善和公益活动,为之一尽绵薄之力。
二、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列女形象的成因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列女形象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美好的,是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而且从文本的叙述来看,列女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出于自愿的。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明清时期传统礼教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与期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代河洛地区的确存在大量妇女坚守贞节、以死殉道、孝顺公婆、教子严格和乐善好施的事迹。这些列女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牺牲欲望、牺牲自我、牺牲幸福以及牺牲生命的悲惨之路,以一种扭曲、自虐和疯狂的方式荣载史册、流芳百世?在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列女奋不顾身地走下去呢?
(一)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发展
宋代以降,贞节观便被专制政府奉为束缚女子思想、规范妇女行为的伦理准则[12]。到了明代,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和在律法,教育上的规范,宣传,贞节观亦得到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其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由原来的士大夫等上层社会扩大到市民底层社会之间,所有闺门女子都需接受贞节理念的教育[13]。在此贞节观教育的影响下,闺门女子须规范自己思想言行,婚前为未婚夫守贞,死后则要为丈夫守节,“贞节观已然成为一个普遍为广大妇女所遵循的信条,也成为了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14]。
清代统治者亦着意大力提倡、宣扬妇女守节观念。顺治、雍正、康熙、乾隆多次下诏,贞节观念较明代在思想、法律等方面进一步得以强化,让“守节成为寡妇崇拜、尊奉和追逐的狂热宗教行为”[15]156,造成了“清代节烈意识之浓厚,节烈行为之普遍”[16]的现象。明清时期,贞节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使妇女守节变成一种内在要求,而《洛阳县志》中的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以死殉道,拒辱自戕等列女形象正是在民间的共识和社会的认可下产生的,她们要么守节、守贞数十年,要么为了保持贞节而捐躯,可见贞节观念已浸透于她们的心中。
(二)贞节旌表制度的盛行
所谓旌表制度,就是“古代政府倡导儒家礼教,对品行高尚的树立如牌坊、匾额、碑刻等标志对其进行表彰与嘉奖的制度”[17],其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
贞节旌表制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18],其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及宋元时期得以不断发展。明朝时期,旌表制度远比前代受重视,太祖、武宗、世宗多次下诏,使得贞节旌表制度和程序得以强化与规范。清政府也非常重视对贞节妇女的旌表,并在程序上大致承袭了明代,且“旌表的门槛不断降低,旌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旌表的手续也不断简化”[18]。
明清时期受旌表的列女人数陡增,“其数量几乎等于以前所有朝代列女总和的40多倍”[19],且施表制度的推行,被旌表的列女能够得到光荣和实惠,如经济奖励或免除本家杂役,使得家中的亲人从中受益,自己的子孙们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此外,旌表制度的盛行,使得列女亦可得到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满足,使她们有了光耀门楣甚至扬眉吐气的机会,“列女在受到封建贞节观念摧残的同时,反而可能较为主动地选择苦志守节,以期获得较高的家族地位、经济权利以及财产继承权”[13]。
(三)洛学的兴盛
洛学由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创立,至南宋时期由朱熹集大成,遂后世多以“程朱”并称,故“洛学在元明清三代也逐渐成为了中原理学的专指,中原因是二程故乡、洛学发源之地,因此在元明清三代,始终是学术文化界的主流”[20]。而“贞节观念是理学(洛学)家提倡礼教思想的重要内容”[12],二程主张“女守贞,男灭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明初洛学家渑池人曹端主张妇女“以柔顺为德,以贞烈为行,切不可自轻其身,以贻父母之辱”[21]194。
贞节观念是洛学(理学)提倡礼教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洛学在河南的大为兴盛,使得女子的贞洁之风在河洛地区大盛,致使“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时女子耳熟能详的理念。此外,“明清时期是妇女道德教育文献的鼎盛时期”[22],如《内训》《温氏母训》《女教经传通纂》《女儿经》等道德教育文献的问世并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利于贞节观念的普及与贯彻,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市面上各类女子规范读物的印刷数量也大为增加,《闺范》《内训》《女儿经》《女论语》《女诫》等有关妇德的经典读物也广泛的传播”[23],推动了妇女对妇德思想的认同和消化,在生活中践行着三从四德的妇德思想。
(四)养老抚孤的考量
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儿女的抚育和公婆的赡养问题是要靠‘家庭’这一社会组织来完成的”[24],况且在贞节风气盛行的明清时期,孝顺公婆、敬爱丈夫和疼爱子女是评判妇女德行的重要指标[25],丈夫死后,孝顺父母、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妻子的肩上,若妻子选择改嫁或立即殉夫,既对不起公婆和儿女,还要受到舆论的指责,背上不孝、不节、不贤和不配为人母等骂名,据统计,在《洛阳县志》中,有42.43%的列女基于养老抚孤的因素,选择苦志守节的方式来代夫行孝或行教,如:“邢文超妻任氏,善事尊长,夫亡,下无遗雏,以姑在苟活,家计寥落,至于断爨,篝灯绩资以为养姑,闾里称之”[5]607;“黄聚星妻李氏,孝事其姑,既而夫亡,誓以身殉,以子弱无依,勉留”[5]605。因此,守节行孝(行教)无疑是列女维持家庭完整的一个方法,也是列女“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一个好手段。
三、对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列女的评价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列女形象是封建礼教的产物,呈现出脸谱化的状态,她们毫无独立人格可言,其情可悯,其行可叹,但她们身上散发出重孝、勤劳、勇敢、仁义、善教等优良品格亦是不能忽视的。
(一)是封建礼教的产物,呈现出脸谱化的状态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的列女形象是封建礼教的产物,是遵照宋明理学所设定的模式进行书写的,呈现出脸谱化的状态,这种脸谱化书写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男权社会和王权政治的。县志中列女事迹的叙述较为简短,最长不过一百五十余字,短则十几字,叙事文本只需将关键情节列出,以突出列女“节、贞、孝、慈、烈、义”等形象,且作者还以程式化的叙事模式来凸显列女形象,即列女形象的书写都有其构成的核心要素,故事情节的基本单位已不再是列女,而是列女在情节中的行为功能,如作者描述节妇们的守节行为大多都是以“某某之妻某氏,某某岁寡,守节(苦志)多少年,旌”这种固化模式展现给读者,而节妇们守节的痛苦、生活的艰辛基本上是没有描述的,造成了县志中“多女一面”的现象。《洛阳县志·列女传》将一个个女性嵌入宋明理学所设定的脸谱之中,并以程式化的情节方式加以叙事,其目的是为宣传儒家封建礼教,巩固专制统治而已。
(二)毫无独立人格可言,其情可悯,其行可叹
县志中的列女毫无独立人格可言,她们的个性完全被礼教所抹杀,她们基本上都是为了公婆、子女和丈夫而存在于世,一些烈妇在丈夫死后立即殉夫,做到了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一些列女,如“朱胄义妻马氏,二十三岁寡,以舅老,不果殉。舅殁既葬,雉经死”[5]611;“杜群妻阎氏,三十岁寡,无子而有二女,数年嫁女毕,雉经死”[5]612,她们在丈夫死后,为了公婆或子女而苟活于世,待公婆死去或子女成家之后,认为自身的价值已完全丧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遂选择自杀。个中缘由虽然耐人寻味,但是她们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这也正是封建王朝构筑的贞节观戕害河洛妇女的结果。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是研究传统时期河洛妇女的珍贵资料,其中刻画的众多列女形象和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形象的历史反思对象,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明清时期河洛妇女受贞节观毒害而扭曲的悲惨人生,亦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礼教的麻木冷酷和灭绝人性。
(三)列女的诸多优秀品质不容忽视
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记载的列女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列女群体的一个缩影,河洛列女们不惜一切代价来坚守节操,她们不仅是封建礼教的产物,更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列女们为了维护贞节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在漫漫长河中度过余生,由于贞节观念严重违反人性,故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猛烈批判和打击。今天研读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其对妇女蠹害和禁锢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但列女身上的传统美德亦是值得肯定与发扬的,亦对现今建设文明家庭甚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些许借鉴意义。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是研究古代河洛地区妇女的珍贵资料库。通过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贞节观念的强化和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河洛地区妇女俨然建立起一套符合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即以理学贞节观作为约束婚姻等社会生活行为的规范。在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明清时期河洛地区出现了包括节妇、贞女、孝妇、勤妇、烈妇、良母、贤妇在内的庞大而复杂的列女群体。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在编修的过程中融入了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礼教导向,其所反映的河洛地区贞节之风,可以说是整个明清时期贞节之风的一个缩影,它向后人反映了传统时代广大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禁锢、压迫和蠹害的历史事实。
——以直省民人为中心
——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