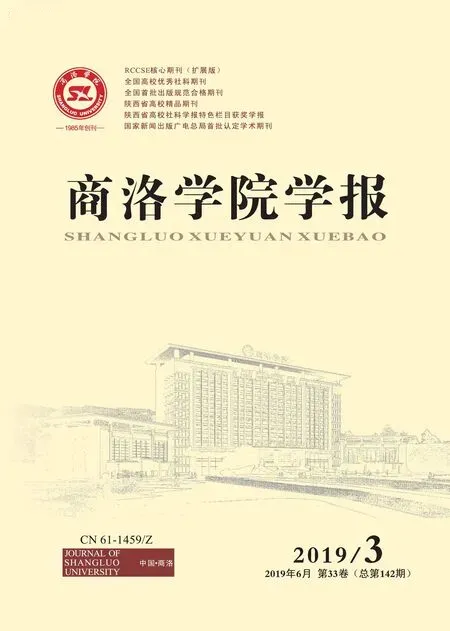贾平凹小说《山本》自然书写的文化原型
李小奇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贾平凹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古文功底深厚的作家,其当下创作与传统经典必然有文脉相承的关系。学界的主要研究中有孙郁的《古风里的贾平凹》,阐述了贾平凹作品的古风古韵[1];刘艳的《贾平凹写作的古意与今情》一文论及古典文学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认为“他的小说常常蕴藉着一种古意袅袅的氤氲气息”[2]。这样的学术洞解为贾平凹作品的研究指出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研究路径。研究《老生》的学者关注并论述了《山海经》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如郭名华《论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的结构艺术》[3],陈思《“新方志”书写——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论》等[4]。《山本》的研究论著中也有学者关注到《山海经》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如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一文,论及《老生》中“自然部分是通过典籍《山海经》来呈现,偏重的还是在人事。而在《山本》里,演示自然的部分被融化到了人物口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5]288。指出《山本》对《山海经》的含融性接受。
已有的研究虽涉及《山海经》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但仅略笔提及,并未深入到作品肌理作出细化的研究,还留下不少可拓殖的空间。事实上,《山本》中的自然书写继承了《山海经》的神话特性,以《山海经》为文化原型。荣格认为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神话原型,他在《分析心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文中强调:“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它是一个魔鬼、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只要创造性的幻想被自由地表现出来,它就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重现。”[6]101据此,本文将从文本出发,厘清《山本》与传统经典间的文脉关系,从而揭示贾平凹对自然的认知与《山海经》所建立的文化原型的关系,见微知著,彰显传统经典沾溉后世的力量,揭橥贾平凹借鉴和运用传统经典的深厚功力。
一、贾平凹与《山海经》的文化渊源
贾平凹对《山海经》有着天然的文化亲近,可以从《老生》这部小说的创作看出他与《山海经》的文化渊源。贾平凹在《老生》后记中说:“《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7]294这句话说明了贾平凹常读《山海经》的偏好,也体现了贾平凹对《山海经》的整体认识。在《老生》中,贾平凹以师生问答的形式(实则是自问自答)表达了自己对《山海经》的理解,那一问就是贾平凹在阅读中曾经产生的疑惑,那一答就是贾平凹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对此作出的个性化阐释。贾平凹对《山海经》的释读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说文解字”。有如下几类。第一类,对文言词语的解释。《老生》引述《山海经》的每一部分都有对字词、语句的具体释义。比如解释“凯风”为“南风”;解释“可以已腑”中“已”为“消除、治愈”之意;“婴以百珪百璧”中的“婴”是“绕、围绕”之意。第二类,对名物的解释。如解释“痹”为“鹌鹑”,是一种鸟;“禺”为“长尾猿”,是一种猴;“石涅”是“黑石脂,古人用来画眉的”[7]140。第三类,运用传统文化知识对某种现象作出解释。如“其音如梧”,解释为:“琴瑟一类的乐器是梧木制作,所以梧指琴瑟,这里是说声音如弹拨琴瑟一样。”[7]249这些解释说明贾平凹对此书的阅读是从基础文意理解开始的,细致而扎实。《山海经》这样的古代典籍,阅读时需要借助训诂书籍来帮助理解。贾平凹解释西山所产“汵石”,是一种柔软的石头,显然是参阅了清代学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的解释:“《说文》汵本字作淦,云泥也,盖石质柔软如泥者,今水中土中俱有此石也。”[8]53喜读,常读,细读,精读,是贾平凹在小说《老生》中写出详实的师生对话录的坚实基础,也是《山海经》对贾平凹影响深远的实在例证。
二是释读地理现象。《山海经》是一部地理著作,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矿产资源、植物种类,以及动物活动,内容丰富,揭示了某些地理现象及其蕴含着的自然规律。贾平凹的解读既洞察自然现象,又探究其内在成因。如其有问曰:南山次山系共写到了十七山,为何九山无草木?其答曰:无草木的山上都有丰富的金玉等矿藏。又如问:西山第二山系十七山中为何有金银铁玉、青碧、雄黄、石涅、丹砂这么多的矿石?解答是:因为这里地处泾渭流域,气候湿润,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矿产自然丰富。问:为何这里奇木怪兽少?答曰:那是因为矿产多,金克木,当然草木就少了;人发现矿藏进行冶炼,人一发达,怪兽就远避了。问:西山经第三山系说的就是现在的青海新疆一带,这里现在是高原沙漠,为何有巨大的湖泊、沼泽,“其光熊熊,其气魂魂”[7]181?解答为:据史料记载,现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原来就是海,有十六国建在海的四周,青海以海命名,那更是海了。说明这里曾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地理巨变,导致了古今地貌的差异。贾平凹对《山海经》在地理、物产层面的解读,体现了他仰观宇宙、俯察大地,对自然规律的深刻体认。
三是释读神话和历史。《山海经》不仅写山水,还写掌管山水的神。在每一山系的最后,都要总述该山系山的数量、距离、山神的形状,以及祭祀的祭品和方法。《老生》中阐释了神话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西山经第三山系有少昊、鼓、葆江、钦、英招、陆吾等等众多天神,贾平凹认为,那是因为西天是充满诸神的地方。即使天帝派诸神来地上治理,但还是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鸟、怪鱼给人类带来灾难;神与神之间也发生战争,也会产生战乱和灾害。对此,贾平凹解释:那是因为世界就是阴阳共生、魔道同在的,两种力量的摩擦、冲突、对抗产生了张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靠这种张力向前发展。贾平凹的解读体现了他对神话的史学观阐释,可见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科学探究精神。
长期浸淫一本书,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从《老生》足见贾平凹对《山海经》阅读之细,用功之勤,思考之深。贾平凹曾说“将来有时间,我要把全本《山海经》都给注解了”[9]。他喜欢《山海经》不是停留在表层的,而是有深度的研究。
贾平凹不仅阅读《山海经》,还从中获得了创作启示。他在创作《老生》时曾三次中断,其间反复阅读《山海经》,又数次去了秦岭,终于获得了启示,将远古神话与当今“人话”联系起来,最终得以顺畅地完成写作。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明确地表示自己期望创作出像《山海经》一样的作品,他写道:“曾经企图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10]284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改变了写成“秦岭志”的初衷,将写作方向转移到风起云涌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但是小说依然有秦岭水文地理的自然写实,有大量秦岭风物的描写。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和语言散点式地呈现了秦岭的物产,尤其是通过塑造麻县长这个人物形象,以潜隐的方式呈现了自己的创作初心。麻县长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秦岭草木斋”。他关注秦岭山中的奇木异草、飞禽走兽,然后采集标本,编写成《秦岭志》;在战乱逃命时还不忘带上自己耗费半生心血编成的《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鸟兽部》。此后,蚯蚓把麻县长慌乱中遗落的纸本藏到了树上的老鸹窝里,并用自己的褂子包好以防雨淋。陈思和亦认为:“《山本》里大量描写秦岭博物风情的段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所在。”[5]288从日常的阅读到获得创作的启示和动力,是一个漫长的、受历史文化浸润的过程;贾平凹深受《山海经》的影响,有意识地通过作品把获得的启示表现出来了。正如荣格所说,原始意象或原型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重现,而这种重现需要一定的条件[6]。对于贾平凹而言,《山海经》及他对《山海经》的极大兴趣和反复研读,都是这样的条件。
二、《山本》与《山海经》
贾平凹的小说《山本》有大量关于秦岭自然风物的书写,表现手法与《山海经》一脉相承。《山本》中的名物及其蕴含的原始伦理意义,“原点—方位—所见”的叙述模式,以及“见则”式神话思维这三个方面,都与《山海经》有极强的一致性。
(一)众博怪异之名物蕴含的原始伦理意义
《山海经》所记山川名物的两大特点是众博与怪异,其蕴含着丰富的原始伦理意义。《山海经》记述名物众多,且形状特性十分怪异。以《西山经》为例。太华山有名叫“肥遗”的蛇,六足四翼。符禺之山“其草多条,其状如葵,而赤华黄实,如婴儿舌,食之使人不惑”[8]21。又如《北山经》第一经记载,有兽名,“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8]89。有鱼名鮨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食之已狂”[8]69。《北次二经》中的鶌鴣鸟,“食之不饥,可以已寓”[8]78。《中山经》所记枥木,“服之不忘”[8]109。《山海经》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这种怪异特征使其形象极具“陌生化”效果,能引起人强烈的好奇心,可以引起读者“‘常格’知觉关照下的审美属性的转化”,最终实现“既成的审美知觉定势的移位和突破”[11]。描述自然名物以人作比,且突出其与人和生活的关系,传达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为自然”的认知理念,还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形成了朴素的伦理观念。
《山本》所记秦岭名物也体现了博与异的特性。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说,在数年里他多次去过秦岭七十二道峪。因他有为秦岭草木立志的愿望,便有意识地收集、掌握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山本》许多章节都写到了秦岭的名物,正如小说中麻县长所编的书那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植物,一类是动物。事实上小说还略笔提及了山上的少量矿产,如窑峪出产石灰,安口青岗洼产煤,三合县的高坝村产水晶等。这些内容看似闲笔,却从多面展示了秦岭丰富的物产资源。关于秦岭物产丰富之记载,古已有之。《书·禹贡》云:“终南、惇物,至于鸟鼠。”[12]宋代程大昌《雍录》卷五云:终南山“既高且广,多出物产,故《禹贡》曰‘终南惇物’也。惇物也者,即《东方朔传》所记,谓‘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而百工可以取给,万民可以卯足’者也”[1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亦有言:“华山为西岳,在弘农华阴县西南,古文之惇物山也。”[14]以上文献都说明秦岭自古以来物产的丰富。贾平凹以浓墨重彩在《山本》一书中为秦岭之“惇物”作出了详实的注解。笔者为《山本》写到的名物作了统计,见表1。

表1 《山本》名物
小说写到七大类秦岭名物,动物类八十四种,植物类一百八十种,以及其它菌类、果类之属,共计二百七十八种。其植物中药草类最多。秦岭无闲草,作家对秦岭药材是有深入考察的,而且了解这些药材的药理、药性。作者写秦岭花类,尤其钟情于兰花,提到了荷瓣兰、水晶兰、素心兰、兰草、蕙兰、蝶兰、麒麟兰诸多品种。《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动植物统共一百三十多种,而《山本》所记数量就多达近三百种,远远超过了《西山经》。虽然小说并没有也不能穷尽秦岭的物产,并不是完备的秦岭志,但是作者借麻县长、陈先生、白起等人物的言行,如数家珍地展现了秦岭的博物,把读者带入秦岭的自然生态场境中,领略秦岭惇物之山的特点。
秦岭生物不仅众博,而且怪异。比如长着狗身子和人脚的熊;有类似象牙的野猪;叫声像老人的鸱鸺;两尺多长,头扁口阔,叫声如同婴儿的山溴斑;长着婴儿手的大鲵;双头的乌龟等。长着羊角猪鼻的羚牛,不仅长相奇特,还会如人一样哭泣,哭起来泪流满面。不仅动物中有怪异者,植物中也有令人称奇的种类。如六道木,其叶含胶质,用热水浸提,可以形成胶冻作凉粉。接骨木的茎皮、根皮及叶散发出的气味只有老鼠才可以闻得到,可使其头昏脑胀致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伦理思想也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文脉,从《山海经》这部上古地理性神话著作延续到《山本》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各有特性,有的可以为人类提供食物,有的可治疗百病,有的提醒或警示人类远离侵害。戚卫红认为:“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生存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强烈的生存欲望促使他们去设想理想的生存境况,希望能够食无忧,穿不愁,物种和谐相处。这种生存理想成为和谐圆融社会理想的雏形,一直绵延在中国的伦理思想中。”[15]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代,人们要想生存就必须学会既从大自然获取所需,又能避免来自大自然的伤害,今天亦然。《山本》在记载秦岭物产的博异中蕴含着自己对《山海经》原始伦理的认同和传递。
(二)“原点—方位—所见”的叙述模式
关于《山海经》的叙事模式,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平面铺排式的较为整齐、清晰的网络状”结构[16],亦有“原点+方位+距离”的论述[17]。从《山海经》的文本可见其叙述模式是程式化的,表现为“原点—方位—所见”的固定模式。如《北山经》:“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多机木,其上多华草……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又北三百里,曰带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兽焉……又北四百里,曰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8]61其叙述模式显而易见,以首山单狐山为原点按一定方位行走,记录途中所识见的山水名物。各经都是如此展开记述的。《山本》这部带有地志性的作品正是以《山海经》为书写原型展开叙述的。
在《山本》中展开叙事的原点是涡镇。不同的人物都以涡镇为原点展开活动,活动的方位在涡镇周边的秦岭山区,距离远近各不相同,都是在行走过程中记述所见所闻以及发生的故事。如写到井宗秀到一百里外的安口寻访周一山,便叙述那里的煤矿和人事。井宗秀带领队伍到银花河打阮天保,经过银花镇西的杜鹃花垭,见到那里满山遍野的杜鹃林,尽管花已落,但花托有碗口般大,足以想见这里满山遍野开满硕大的杜鹃花的壮观景象。杨钟和陈来祥出涡镇寻找井宗丞,两人顺着黑河过十八碌碡桥,翻虎山后崖,下七里坪,穿流云沟,进入桑木县界。在留仙坪见到了高大粗壮的栲树、檞树、树,见到了狼和老虎。井宗丞离开涡镇投奔游击队,所到之处见到很多怪异之物。如游击队在留仙坪北三十里的云寺梁,见到一种熊,长着狗的身子人的脚;鸱鸺的叫声像老人;白蜡虫嫩时白,老了变黑。井宗丞护送红军首长后到兰草镇寻找游击队,在北沟林中寻找吃食,见到了裤裆果、鹅儿肠、狗筋蔓、刺龙包、隔山撬等植物。白起到虎山崖挖草药,有款冬、忘忧草、连翘、白前、锁阳等药草。作品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记述秦岭名物,不同人物的“原点—方位—所见”的叙述模式便组合成一个网状结构,多层次、多维度地展现了秦岭的博物,而这些奇闻看似是在历史叙述中插入的闲笔,却处处体现着作者为秦岭立志的书写意图。
具体到名物的书写顺序和方法,《山本》也吸纳了《山海经》的书写原型。《山海经·西山经》的叙事顺序是先言某山,次言山上有何种植物或动物,再言其状、其生长条件、其奇特功用。如《西山经》中记载嶓冢之山“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8]26。《中次三经》记载一种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8]117。《山本》借鉴了《山海经》的书写序法描述秦岭植物、动物的形状特性。白起跟陈来祥讲自己在虎山挖的药材连翘时这样说:“这是连翘,没长叶子就开花,花黄得像金子,果实还生着的时候是青而圆的,一旦熟了是黄的,大张口。”[10]84小说通过老魏头的眼睛写在涡镇见到的虎凤蝶:“每只虎凤蝶都是小儿手掌般大,身上密密批着黑色鳞片和细长的鳞毛,而双翅则是黄色,上边有虎斑形状的条纹。”[10]156描写动物黄皮子,先状其外形“嘴小,牙尖”,次写其捕食特点:“咬不动羊的皮,咬羊的屁股,有的迅速抓出羊肠子,有的则在羊屁眼上打洞钻了进去吃肉。”[10]271通过对读可见,《山本》与《山海经》在名物书写上的顺序及方法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
(三)“见则”形式的神话思维
“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曰《山海经》,是极其富有象征意味的。它以山海之所经,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的幻想,进而成为百世神异思维的经典。它呼唤着山川湖海的精灵和魂魄,使中国神话幻想在滋生和笔录的早期,就粘附着泥土和方域。”[18]《山海经》的神话思维以“见则”形式呈现,记载见到某物会给人带来某种祸与福的预兆。如《南次二经》“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见则县有大繇”[8]9;《东次二经》:“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其名曰獙獙,见则天下大旱。”[8]100此外还有“见则天下大风”“见则其国多疫”“见则其国多土功“等共54 处“见则”的表述,多偏于灾祸的预见,判定吉祥的较少。《南次三经》言凤凰“见则天下安宁”[8]15,《海内经》言“见则天下和”[8]384。另有鳐鱼、狡、当康,“见则天下穰”,即当这些动物出现时则会有谷物丰熟的好年景。《山本》继承了《山海经》“见则”形式的神话思维。秦岭名物的“异”不仅体现在外形之异,还体现在内质之奇。它们的出现往往是某种征兆,具有某种警示的作用。这体现的是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模式,《山本》亦如是。如涡镇那棵古老的皂角树,有德性的人路过才会有皂角荚掉下来。陆菊人路过掉下两个,井宗秀路过掉下三个。皂角树是通灵的,知道这两个人是有德行的。保安队以三合县茶行分店是红军窝点为由抓了崔掌柜,陆菊人将责任全部揽下,被关了一个月。关押解除后路过老皂角树,树上掉下五个皂角荚。这是皂角树为陆菊人的责任担当、为她的处乱不惊、为她的仁义良善而感怀,五个皂角荚是对她的最高礼赞。没有德行的人就是摇动大树都不会掉皂角荚的。而皂角树的死让所有涡镇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它果然预示了涡镇毁灭的不幸结局。再如处在涡镇西南角的安仁堂有棵婆罗树,镇上一直传说“哪一枝股上的花繁果多,枝股所指方向,来年就五谷丰收”[10]31。麻县长养的牵牛花开了三朵,他认为这预示好事来临。井宗丞命丧崇村之前,路上看到的是水晶兰,这种花又叫冥花,见到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小说还写到了县政府初八日搬迁入驻涡镇,一群平日极少见的极漂亮的绶带鸟飞到了这里。大家都不认识这种鸟,只有刘老庚在深山老林割山漆时见过。深山老林中的绶带鸟有灵,显然有庆贺之意。小说中写道:“这是给谁绶带呢?是给麻县长,还是给井宗秀?”[10]149显然有为情节发展设计悬念之意。陆菊人晚上在月光下看到很少见到的虎凤蝶,盘旋一阵往南飞去,疑惑它们要飞到哪里去?第二天黎明时分,打更的老魏头路过刘老庚家,发现在他家的月季蓬上、院墙的瓦楼上、门楼上都落满了虎凤蝶。吉祥的虎凤蝶一方面预示花生的命运,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她和井宗秀的虎凤姻缘。一只了知凶杀案事实真相的青蛙,连续三天到麻县长看书的石桌上来。正是它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麻县长的注意,最终在青蛙的帮助下顺利断案。剩剩摔伤腿之前,家中的黑猫几次扯着他不让出门,陆菊人当时没有明白这种举动的预兆,故而才有了剩剩的一场灾难。“见则”的书写形式,即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是贾平凹结构小说的基本思维模式,不仅赋予小说极强的神秘色彩,也表达着作者对自然的敬畏。
三、结语
《山海经》衣被后世,贾平凹精深阅读这部传统经典,其精神内核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成为一种内动力,在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山本》以《山海经》为文化原型来书写自然,记述众博、怪异之名物并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始伦理意义;“原点—方位—所见”的叙述模式,以小说人物所历所见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呈现秦岭的博物;“见则”形式的神话思维,则继承了先祖敬畏自然的精神,这些都与《山海经》一脉相承。贾平凹以个性化的创作方式完成了《山本》的自然书写,彰显了《山海经》所建立的文化原型的强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