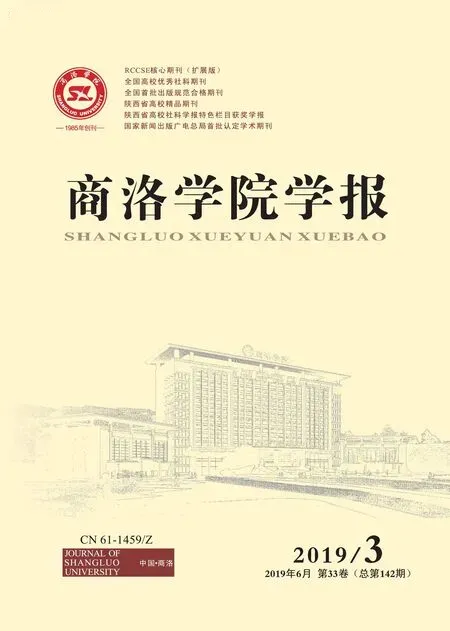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群山绝响》的非史诗性叙写
李荣博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群山绝响》从一个平凡的山村少年元尚婴的初中毕业最后一课开始叙写,到最后被高中劝退完结,故事时间跨度不到一年。以“获得上高中入学资格——高中生活——被劝退”为叙事主线,围绕少年的生活历程,敞开了一方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世界。其叙述却不是典型的、不蔓不枝的线形叙事,而是一座小径不停分岔的花园,在不同的节点上岔开去、荡开去,从而将各色人物、各色人物的各色故事,风土人情、山川景物掌故、人文地理、时代生活场景等万般世事,都纳入到文本叙写中。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情节性,使其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闲谈特色[1]。此时,小说就是说话,就是闲谈,就是街谈巷议,回归到了小说的原初本意。通篇叙述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的历史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反而为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的细节充斥,意趣盈然,高度保真,但却切近生存,深入人心[2-3]。而叙述节点上的荡开与回笼,过渡极为自然,有时甚至使用了意识流手法,使叙述高度符合“说话”与“闲谈”的特质。《群山绝响》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小细节、小丑小怪、小奸小恶、小利小想、小悲小喜。小说敞开的世界,简淡如尺幅水墨,简淡如连环画。
其语言风格也是简淡的,通篇不作愤激语,不作批判语,不作绚丽语,不作惊人语。描人、状物、绘事,聊聊数语,用笔极简,却入木三分,世事洞明。虽然是全知叙述,但讲叙者的声音平和、冷静、舒缓、淡然,不悲天悯人,也不故作高深,通篇无重言,无寓言,无急言,无矫饰语,多口语,既不卖弄学问,也不卖弄思想。
其人物塑造,也是简淡的。从不浓墨重彩地、全方位地塑造人物,很少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也不刻意使用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总是抓住人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细节,以漫画和白描的手法,寥寥数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却不深度开挖人物,无意于人物的复杂和丰满。小说虽人物众多,却个个人淡如菊。《群山绝响》如一杯春茶,虽简淡,却并不寡味。
一、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虽也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文革”这样一个可被看作极端处境的大时代,与同类作品相较,最显见的特点,是其跳出了弥漫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史诗性追求”的窠臼。
萦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心头的史诗情结,虽其来有自,成因却极为复杂。概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始,已为其埋下了根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梁启超赋予新小说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注定了新小说要直面大时代,要直面重大、复杂而深沉的命题,要直面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再加上对本就有漫长史诗传统的西方文学(最直接如“长河小说”)的接受、消化、吸纳;又受中国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式的历史感的浸染,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如李劼人的三部曲)已隐见史诗性的追求。其后,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标举,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以及其史诗性巨著,又为小说界提供了创作效仿的典范。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一方面,“史诗性”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化的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情结;另一方面,“史诗性”又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捆绑在了一起。在新时期文学直至21世纪文学创作中,伴随文学理念、流派追求的多样化,“史诗性”追求已被淡化,但仍是游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史诗性小说,可以说是史、思、诗的高度融合。“史”的维度,追求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再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演进和精神演化的路径,追求摹写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追求对历史实相、个体与整体的人之生存及命运的揭示。“思”的维度,追求对人之欲求与困顿,良知、道德,奋进与堕落等人之复杂性的探求,追求对人的处境性行为、社会化型塑、历史性吊诡状况的呈现,追求天人之际的复杂因缘,追求终极关怀。“诗”的维度,是“史”与“思”的落脚点,强调的是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妙圆融,意境风格上的阔大、幽深,崇高与悲壮。在80年代以前,较长的历史跨度,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重大的历史事件,深沉的命题,杰出而高大的、甚或英雄式的人物,崇高的美学风格,形成了宏大叙事,几成史诗性小说的标配。但随着80年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及思想解放的推进,哲学观念上的转换,文学理念、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差异化,从更深层次来说,源于文学对人类生活及生存真实性深度呈现的追寻,容易导致假、大、空和概念化的宏大叙事、英雄摹写和崇高风格,遭到厌弃。比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宏大性,向民间的、草根化历史,向口述的历史回归;新写实小说向日常性的事件、琐碎生活、平庸人物的平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还原。宏大叙事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从“史诗性”追求中剥离了出去,从而使“史诗性”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不再摹写高大杰出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平凡的人物甚至比平凡人心智更不成熟的幼童、白痴、癫狂者作为刻画的对象,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其次,不再描写或极大消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不再展示或者极大消减剧烈的冲突和悲剧性的争斗,同时弱化情节,或者描写日常化的情节,或者直接进行生活流式的非情节叙写,如贾平凹的《山本》《老生》。再次,不再以时代或民族作为叙述的视野和思考的疆域,而是将其还原为个人化的、平民化的、日常生存的叙述视野,如《平凡的世界》。虽有诸般新变,但是,较大的时空跨度、深广的社会人生蕴含、幽深的思致与人类关切,作为史诗性追求的核心内涵仍然保留着。并且,史诗性追求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热度至今仍未褪却。
《群山绝响》是非史诗的,但以史诗性叙写为参照,却更能彰显其艺术追求上的独特性。首先,史诗性叙写着眼于民族和时代。即便以个人或家族作为叙述的重心,最后仍要归附到民族与时代上,这是由其背后的历史性追求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方可摹写出民族的社会演进历史和精神演化的路径。所以,史诗性的小说要有很大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只有通过时间的跨度才能容纳和呈现历史性因素;只有空间跨度,才能容纳众多人物的生活场域、命运轨迹。《群山绝响》虽然也有时代背景,却并不将批判或讴歌的目标指向时代,并不控诉或讴歌历史,因为《群山绝响》的主旨并不是历史性的和时代性的,而是超历史或者超时代性的。相反,将故事安置在“文革”这样的时代中,恰好可以营造一个极端处境,极端处境中更能彰显文本的主旨,使所标举和所讴歌的东西在这样严酷的时代更显珍贵。时代在此只是衬托,不是主角。所以,《群山绝响》不仅淡化了其时代,也压缩了其时间跨度与空间跨度。故事空间,仅限于“村—公社—镇”;故事时间,也只是从七年级毕业到八年级约一年的时间。一个镇子,一年时间,一段生命历程,却开显了一方世界,一个温暖的人间,这就够了。
其次,史诗性叙写所追求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群山绝响》中也是基本上回避的。既然所标举和所讴歌的是超历史和超时代的东西,那么就不需要直接正面描写最能展现历史性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才是描写的重心。文中虽也提到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事件,但也只是作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和人物生活轨迹的逆转需要,二是为了保证生活真实而无法回避。生活化的、日常性的小事件,小细节,才使作品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真实而切近,动人心魄而又意趣盎然,真力弥漫而又虚灵不昧。例如,元尚婴的爱恋,与马广玲、与苏景兰,都是用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写尽了少男少女微妙的心事。马广玲要元尚婴给她挠痒痒,苏景兰在合唱表演时偷偷给元尚婴炒黄豆,巴山茶山上,苏景兰与元尚婴共同分吃一根麻花。都是微小的事件和细节,却都极富包孕性,尽显内心波澜。元尚婴从邮所赶回学校,在河边送别顾老师,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受到劝退处分,只是他自己不知而已。“苏景兰突然走到元尚婴身边,一拽他的袖子,动作幅度很夸张,导致对方的身子一个趔趄,果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手伸向元尚婴,掌一翻,露出掌心的三个橡皮筋:‘这个送你’。未及受赠者反应,她紧跟着又说:‘你的口琴盒子破了,拿这包扎去!’”[5]298在元尚婴接受了退学处分之后,与同学们分别时,“她发现别人要取伞,便抢先取下自己的红伞,递到元尚婴手里,说:‘这伞不是我一个人送你的,是全班同学送你的。’大家鼓起掌来。‘你已经送了我橡皮筋啊。’‘那你再送回来哦——’‘哦’得几分撒娇,几分柔媚,吃惊了大家——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才这么‘哦’。元尚婴摸出三根橡皮筋,对方早已将大辫子翘到他面前:‘你给我套上——’”这些极简的动作和言语里,不着一个“情”字,不着一个“爱”字,却满满地都是爱恋;无一句心理描写,却尽显幽微心思。画面极简,极淡,极美。《群山绝响》通篇都是这样的小事件、小细节,不够恢弘,不够深沉,却浅白明快,和雅清新。
再次,《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杰出而高大的人物。这类能体现历史趋向与时代纠结的人物,对《群山绝响》是没有意义的。其中的小人物,既不背负历史使命,也不背负庞大的民族、国家重任。他们既不会改变历史,也不会推进社会进程;不会做出巨大的社会贡献,不会成为时代的标高,也不会成为时代的精神榜样。他们太平凡,平凡到他们的歌哭、穷愁、生死,不会被别人注意,如山中藤萝,花开花落,无人欣赏赞叹,也无人萦怀感伤。他们只是被时代风潮携裹着的芸芸众生,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只活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距离大场景、大事件、大人物,千里万里。这些人物,并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却是在世上生活着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人物。
最后,《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深沉的命题、崇高的风格。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靠习惯和朴素的观念,处事、待人、接物,他们没有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活着也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的行为也谈不上多么崇高。从他们身上,挖掘深沉命题的尝试,都不是平视他们,而是在俯视他们;不是活在他们中间,而是高居他们之上。他们也不需被教育、被启蒙、被批判、被歌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历程,并不为政治语境、精英思想所阻,如大河绕山,毕竟东流去。
二、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往往要直面阶级斗争问题。“阶级,作为马克思从经济—政治视角所做的划分,用来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变革的原因,研究历史的发展动力是可以的。但是,阶级能否用来对人进行一种道德和伦理规定?阶级作为经济概念、经济视角,甚至都不能与政治立场直接相连,它的确有对应的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人身上,属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并非不可能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无产阶级(如贫农)很可能不仅没有先进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充斥。但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不仅和政治立场相等同,而且取代了道德,成为对人品行的划分标准”[6]。阶级划分取代了道德甄别,取代了法律审判,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处境中,这个荒诞的逻辑,造成了种种的人间惨剧,在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老生》、余华的《活着》那里,遭到了质疑、批判和嘲弄。
在《群山绝响》中,以阶级进行的政治划分,并不是笼罩一切的,而是浮于社会表面,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角角落落。民间的道德认同却以一种强大的惯性而留存,与严酷的阶级划分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判定,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互补。元尚婴的爷爷,一个虔心向佛的明智通达之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土地、房屋为累赘,本无意于聚敛土地,却因自身多才多艺、为获妻子的肯定而致富。乡邻为度过难关,为换几个大洋而向其抵押土地。日积月累,无意间成为了地主。但从道德上说,他又是一个闻名乡里、为众人内心所感念的大善人。“善人”不是靠伪善的行为博得的社会声誉,而是在长期的施恩勿念、受惠莫忘之后,乡邻内心深处掩藏着的深深地感激,自发形成的道德评价。这说明,在人们内心深处,对人的判定标准,首要的还是道德而不是阶级。在“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轰轰烈烈地运动、批判、赞歌、颂歌,虽看似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笼罩了一切,却无法洗涤人们内心深藏着的良知。这种良知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决定着人们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无论社会处境和个人处境如何,这种良知并未泯灭,思维、行为、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不变的思维、行为、想象方式,就是常理。常理是一种习惯,但不是个人性的、可随时改变的、表面性的习惯;而是长期由深藏的良知决定的,人们的想象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层面的习惯,是从意识思维层面向行为层面的透发。《群山绝响》中的人群,虽无法摆脱严酷的社会处境,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恶,没有酿成令人发指的人间惨剧。他们虽也有自私、狭隘、狡黠或无知,有怪诞有荒唐,有可笑可怜可叹之处,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出于良知和常理,却也有义举、善念善行。上至区委书记、中学校长,下至农民、普通老师和学生,莫不如此。例如,写区委简书记,“他敬重识文断字的人,却无法理解报纸上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报纸上咋说,咱就咋念,实际上就按良心和常理去做就好了。就说汉叔中学的老师们吧,他们是有那么点假装斯文,处事待人也显得吝啬小气。小资产阶级嘛,也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人民内部矛盾嘛。何况他们大老远地来这深山里教书,多数人一年四季只能回家两次见老婆,也实在不容易。总之,对于他们,政治上要敲打,生活上要照顾。”[5]219-220在“文革”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汉叔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以意识形态贯彻一切,而是“按良心和常理”去办事:优待“臭老九”们;低调而又人性化地处理白校长被诬告“破坏军婚”事件;摒弃政治成分偏见选拔元尚婴当乡邮员。他的身上,没有时代赋予的冷硬、严酷和虚假,而是满溢着理解之同情,满溢人情化的光辉。不仅居高位者如此,最普通、最卑微、甚至满身缺点的人身上,也都闪现着良知之光。比如,并不能算好学生和好孩子的田信康,懊恼于,自己不是读书种子却被推荐上了高中,应该去继续读书的元尚婴却只能当农民,所以,在他父母亲支持下,他想将高中的入学指标让给元尚婴;元家父母没接受,还感谢他、送给他住校带饭菜的漆桶。事件虽小,善念却大,光辉动人,满溢温情。
《群山绝响》所塑造的这一方小世界,是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这个小世界被置于“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置于一个允诺了,人与人之间,以阶级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可以相互批判、相互揭发,互相斗争、你死我活的时代。被置于物质上极为贫困、缺衣少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困厄、穷愁、心酸、无奈并非没有落实在成长中的少年身上,但是,真正带给这个少年,影响这个少年成长和心性的,是他周围世界中,人们的良知、常理和温情,这是一个有善有爱、有情有义的温暖的人间。政治环境限制了成分不好的少年,使他丧失了公平的机会,但包括元家长辈在内的人们,以自己的善心,对抗着这个“不公”的环境,通过送礼的方式,想获得上高中的资格,但还是败给了政治大环境。同样地主家庭成分的万水贵,以揭发父亲偷玉米从而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决裂、政治上投机取巧的方式,而获得了上学资格。万水贵的入学之路,虽也艰难而来之不易,但以作践、丑化父亲作为进身之阶,是违背人伦,违背良知、违背常理的;元尚婴的“送礼”之路,虽不合政治程序,却建立在人们的理解、善意和常理之上。最后,入学不到半年,万水贵淹死了,这是否是佛家的因果报应?元尚婴却因此有了上学的指标,但在元家人心中,是有深深地愧疚和不安的,所以,在后来,跑邮的吴小根死了,元尚婴意外当上乡邮员的时候,母亲却哭了;“儿子,你念高中是因为万水贵……殁了;如今要参加工作,又是因为邮递员……唉,唉!为什么你的好运总是要别人先去……呢?你想没想过,这样的好运你该不该要!”[5]286-287这种由佛家因果形成的良知也深深地植入少年的心中。他要去上坟祭拜万水贵。在成为乡邮员后被人嫉妒遭人检举“说毛主席死了”,他遭邮所遣退,又被学校“劝退”,他主动退学了,毫无怨言,因为终获心安。毛主席却果真去世了,时代的大幕拉下,时代的荒诞给予他最后的一击,而少年心智已初步形成:“那‘幸福’二字忽然醒悟了他。幸福,就是不损害任何人”[5]305。虔心事佛的家庭、充满良知和温情的小世界,不仅使少年向善弃恶,也使他充满善念、爱心和情义。他进巴山去祭拜万水贵、赠麻花给每一个同行者的情节,尤为动人。麻花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相当奢侈的食品。但元尚婴觉得,“能同学一场,明天又将被他们带进巴山,都因机缘与情分,值得珍惜与珍重。人生可能就这一次同路,能不能重复那就难说了。”[5]229对待偶然的一次同行者尚且如此,对待身边的亲人、友邻、同学、老师,就更是如此。情义从来都是交互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使少年眼之所见、心之所想、身之所历,都是人间温暖,而非世态炎凉。元尚婴虽活在一个政治上高度严酷、物质上极为贫困的时代,但幸运的是,他的周围世界,是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有良知、有情义、循常理的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完人。他们并不高尚、崇高,但却质朴、良善。《群山绝响》写人物,从来不是贴标签式的,而是从生活真实出发的,描写有血有肉有利益有妄想有缺陷的平凡人。如写区委简书记,录用元尚婴做乡邮员之后的心理活动,写他也动过自己的两个女儿配不配得上这个少年的念头。写苏景兰这样美好的人物形象,也写她的私心和狡黠。“苏景兰离开队伍,提前回家让父母预备饭菜。她走的很慢,果然,没走几步,被老师喊回来,说她忘了带钱。她双手背在身后,欲接不接的样子。顾老师把她的手从背后拽到前面来,又将她的手张开,硬是将七块五毛钱放她掌心。她重复说,‘这不像话、这不像话’,勉强捏拢钱,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就小跑起来,那条粗黑的辫子愉快地飞摆飞扬了,如劲风里的女藤萝草。”[5]261将她细微的、心理活动的“虚”,通过动作和言语的“实”非常精准地刻画出来。但这私心和狡黠却是人之常情,丝毫不影响她的可爱,反而使人物更丰满、更真实。这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不是解剖他们,俯视他们;而是平视他们,观赏他们:这是真正褪却精英知识份子视角的民间立场。以这样的人物和人物的行动构成的小说世界,是日常性的、真实的生活世界。
人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即便小世界深植于大时代。在少年的成长历程中,无论时代洪流留下了多少难以磨灭的痕迹,都没有这个日常性的、真实的生活世界留下的烙印更深。最切近之事物,总是最关乎心性、人格、情感,最能形塑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时代,只是云烟。所以,带有追忆特色的《群山绝响》,舍弃了民族、历史、英雄、重大事件等宏大的元素,书写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小世界,一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
三、隐秀之间,其旨也远
《群山绝响》的非史诗性书写,弃绝了较大的时空跨度、深广的社会人生蕴含、幽深的思致与人类关切。故事时间跨度不到一年,空间跨度不过一镇,故事主线极为简略,用语用笔、绘人绘事极为简淡,意在开显一个少年成长寓于其中的,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和雅的文风、简淡的意境、温情的小世界,仅是小说文本“状溢目前”的部分、“秀”的部分,并不是其“味”的尽头。没有直言,没有说出,在文本之外的部分,即“隐”的部分,才是其“至味”。 作为小说名字的“群山绝响”一词,气势恢宏、悲慨苍凉,与文本中由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风格反差,构成了一个绝大的语境张力场。是什么东西已成“群山绝响”?时代在小说里不是被着意突出的东西;小说里也根本没有能与这个词相匹配的大人物。只能是,这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已成绝响。这隐指当下的世界。与小说中那个处于“文革”中的1976年、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语境中,物质上极为贫困,却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世界相较,当下的世界,社会政治环境上已越发民主和自由,物质上越发富裕充足,但是,不得不承认,道德意识在颓堕,良知、常理、温情的世界已崩塌。“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就易于发现两种人:一是在这些残存的道德的范围之内说话的人,二是那些站在所有这些道德之外的人。”[7]一些人的身上,还有残存的道德;另一些人那里,则彻底无任何道德。政治的民主自由、物质的富足、科学的昌盛并不能增进道德秩序,并不能强化民众内心的良知。而《群山绝响》中,人们虽贫穷,虽迷信,敬鬼、礼佛,却有更为深沉的良知,更为自觉的道德,却能缔造一个温情的人间世界。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当下不得不正视的隐忧。
由此可见,《群山绝响》是蕴含着批判性的,只是这种批判落在小说题目与文本内容构成的语境张力之中,落在空白处,落在不言中。不是直面当今的大时代,做一种宏大而深沉的描绘、剖析、思考、批判,而是以追忆的姿态,简淡的笔调,书写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满溢良知与温情的小世界。以过往的“小世界”来烛照、来批判当下的“大时代”,隐指当下堪忧的道德境况和社会实景。这算得上是“隐微术”了,或许,这也是非史诗性写作的高妙策略,即,以小见大,无言批判,于无声处听惊雷。
四、结语
《群山绝响》以简淡、明快、又不失谐趣的笔调,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小细节,以少年的一段复杂曲折的求学经历,写少年的成长,开显了一个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小世界。虽以“文革”为背景,却非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舍弃了民族、历史、英雄、重大事件等宏大的元素,不涉及深广的社会蕴含。但在小说题目与文本内容构成的语境张力之中,在空白处,隐藏着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和深深的道德隐忧。与以“文革”为背景的文学书写不同,它并不正视时代与历史,不用与惨淡和黑暗交锋,显得云淡风轻、闲雅从容;与诸多成长小说也不同,它没有主人公与社会的激烈的对抗、妥协、心灵激荡,没有迷惘、彷徨、绝望;只有善意的晕染、温情的传递、潜移默化中的明悟。这的确是文本的特异之处,轻灵、而不重浊,如春茶一盏,明透淡薄,却回味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