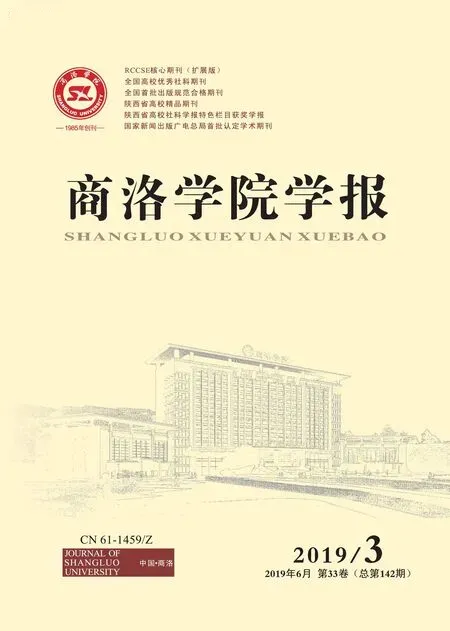从微观叙事审视宏大历史
——论方英文《群山绝响》
张艳茜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陕西西安 710065)
作为陕西第三代作家的领军人物方英文,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的文学之途上,他的创作从没有中断过,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散文,或是长篇小说。他那被称之为“方氏修辞”的语言风格,异于常人,总是寓幽默、诙谐、趣味于语言描述之中,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笔下的风物人情,以及字里行间所展现的神韵与情绪,也都极富个性。方英文的作品因此而具备了鲜明的识别度,其长篇小说《落红》《后花园》,以及近期出版的长篇《群山绝响》,每一部都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读者的普遍喜爱。
因为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很早就读方英文的作品。所以,对我而言,阅读方英文,我可能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体验。在这种状态下阅读方英文的长篇小说,于我而言,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方英文的小说做一场文学之旅;二是用一个文学编辑挑剔的目光,打量方英文创作是否有所超越,以及他自己对创作的思考与追求。
一、基于抒情、表现生活的叙事风格
阅读方英文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和阅读前两部长篇小说《落红》与《后花园》,有着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我们在《落红》中看到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唐子羽的不惑,“某种程度上看透了社会人生的真相,品质善良,有仁爱之心,也有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但这种关怀由于没有什么用场,因而更多地表现为斗嘴、贫嘴或嘻笑怒骂”[1]。在《后花园》看到了主人公宋隐乔和《落红》里的唐子羽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才不遇的“无用书生”,因而玩世不恭,对教条僵化的公务体制不无游戏态度,唐子羽因“学习体会”中夹带了“黄段子”而丢了官位,宋隐乔则在职称考试中“请人捉刀”,致使副教授职称泡了汤。“他们对待爱情都有些‘痴愚’,很执着地追寻心中的完美女神,但这又不妨碍像解决‘生计’般地‘打个牙祭’”,“他的该死的身体,却需要性爱,像他需要吃饭、饮水一样”[2]。
小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映像,好小说往往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创作,无法割裂作者以及时代与作品内容上的联系。尤其当作者投入自己真挚而深切的生命体验,并以情感性叙述的方式去创作时。《落红》和《后花园》并非是方英文的自传体小说,然而,因为方英文是贴着人物去写的,让我感觉不到小说中的人物与方英文之间的距离感。阅读这两部小说的过程,我其实像是在阅读作家方英文本人一样,无论是人物与作家之间设置的时间上的距离,还是人物与作家情感上的距离都似乎贴得很近。方英文在和孔明对话时自己也坦陈:“书里所有人物的身上(包括动植物),都有我的影子”[3]。
《群山绝响》却不同。虽然许多读者或是评论家认为《群山绝响》是一部方英文作品中自传色彩最浓的,作者是将自己体味过的生活进行了艺术升华并表现了出来[4-7]。但是,在《群山绝响》中,无论是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还是与作家自我的距离,方英文都很成功地把握了分寸,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和题材内容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在以往熟悉的方英文文本中产生了阅读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恰是好小说的效果和力量。正如评论家李国平所言:“如果说方英文的《群山绝响》延续拓展了自己博雅温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错。但是你可读出了作者对自己的颠覆?”
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聚散离合、爱恨情仇、怀念理想……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小说家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叙述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其间的人,成为一代一代作家们笔下的主题,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也由此构成了作家的生命真实。方英文用他的智慧和想象,在《群山绝响》中,以干净、简洁、克制的笔调,从日常生活出发,成功地将读者带入到了不平常的陌生地带。
小说从少年元尚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日常图景。故事设置在了20世纪70年代,那其实是属于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小说中的日常是什么?是初中生、毕业生、“地主崽子”元尚婴的心事与忧伤,是少年田信康背苞谷时的两腿抽筋,是元尚婴和田信康对《赤脚医生手册》的一页图纸的紧张与好奇,是供销社的煤油、食用碱、饼干、麻花等等零碎,也是元尚婴母亲缝纫机的踏板声,是过年时贫穷户向母亲找布料“补”衣服,是生产队的麻队长挖空心思白吃队员饭的心机,是不论阶级出身都能围坐在一起吃的那顿年夜饭,是老师们为即将吃到二两肉暗自的欢呼声,是柳会计的算账:“一亩地农业税15 元,不用缴钱,全部折成粮食上缴。苞谷一毛钱一斤,稻谷一毛三一斤。购粮部分:除却常规的统购粮,上级要求咱让国家多购些粮,多购了咱5 582 斤粮……于是,一个劳动日值8 分一厘!”……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散落在每一个生命刻度里的存在,如此琐碎,你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发生就已经结束。然而在作家方英文敏锐的眼里,琐碎的生活,都有着生命的温度,一地鸡毛,却熠熠生辉。日常生活、日常故事,对作家来说,如同险象环生的沼泽地,一旦陷落进去是难以自拔的——将日常生活写进小说而平淡无奇的作家不在少数。但是,方英文却不仅轻易地走出了日常生活的沼泽地,还将那些在我们眼中平凡似尘埃的生活,那些来自生活稍瞬即逝的光芒,用灵性的纸笔凝结成一个个生动的意趣盎然的生活记忆。就连他对日常用品的报价也没有给人感觉琐碎。
方英文说“《群山绝响》的立意就是写出少年时光的纯净,最终定调为抒情。由于该书的故事背景是人民公社时期,小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真实、客观的记录,小到一盒火柴、一个鸡蛋多少钱,人们一天挣多少工分等等都有翔实的介绍,力求让人们从小说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7]在表现日常生活的从容中,方英文笔下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被撕裂开,巨大的伤口深处满是生活的秘密、生活的真实、生活的感动、生活的绝望与希望……一一呈现。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从而完成了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陌生生活”的再现。
二、基于微观、有别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视角
从陕西第三代作家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不再像第二代作家那样,对书写历史与政治,有一种自觉的承担和责任,直接表达创作主体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陕西第三代作家从一开始就撇开了对宏大历史或是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自觉地规避了某些重大的社会历史使命感,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化视角,从微观视角着力表现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以及个体生命的存在境遇。也就是说,在历史与个人之间,他们不再怀有“宏大历史情结”,而是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精神面貌,更强调人性内部各种隐秘复杂的存在状态。
对《群山绝响》来说,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叙述历史的特征,在小说开头部分就已经呈现了:七年级教室里齐声高唱的语录歌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历史场景;就天然规定了元尚婴虽然是班长,但是因出身不好,在那个“重在家庭出身与政治表现”的年代,不能正常上高中;在时间维度上,20世纪70年代,就是一个特定政治和历史以及人文内涵的时间概念。方英文并没有带着“宏大叙事”的镣铐起舞,他没有去关注历史本身的政治化冲突,也没有采用整体性的“叙述历史”视角。打开历史的路径,于方英文,选择是多元的。方英文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零碎的、可感的生活细节和人生经验。“宏大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和生存境遇,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整体性的历史图景无处不在,同时,又被虚化为一种氛围或是情绪,对历史与对政治的反思被巧妙地“悬置”,而人物命运与人性审问成为小说的个人叙事。在作家的理念里,个体的“人”,既是历史环境中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环境的参与者,或是执行者。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因出身问题,元尚婴要想上高中,他的入学申请,要得到生产队的批准,再得到大队的批准,然后是公社的批准,最后还要得到汉叔区革委会的批准。“不准你上高中,人家理由是现成的,正大光明的;你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嘛;若是想让你上学,人家也能马上找出理由,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此‘子女’不难想象,那指标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指标再少,终究有个指标,于是存在着上高中的可能,所以要努力争取。”元尚婴的全家都在为他顺利上高中努力争取着。为了得到一层层组织的批准,需要一个个的盖章。于是,元家“每年腊月的肉票都打发给讨饭的人了。可是今年,不能给讨饭的人了。”母亲得“拿肉票去送礼”。虽然,元家祖父元白了的乐善好施,帮助了许多人,母亲的温厚善良,人缘也极好,加上一份一份困难时期奇缺的物品,盖章得以完成,但是,元尚婴仍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冷静下来。他劝说自己接受现实吧”。所谓成长,就是经历。元尚婴的成长,就是在亲历一份份礼物的送出,在一个个红章子盖上中完成的。方英文在书写这些过程时,文字里飘散着一种乡愁,一种对过早失去的少年时光的追怀与忧伤。
三、基于小故事、展现大格局的人物形象塑造
与《落红》和《后花园》不同,方英文在《群山绝响》中大展宏图,大概不下50 人在这部小说中出场。比如每个层级组织掌握盖章的人:麻队长麻顺篓、驻队干部陈荣,还有学校的全老师、汉叔中学的白校长白有德、汉叔镇的简书记,再有牺牲后还有争议的牛三宝等等。方英文在他们身上用的笔墨并不是很多,他使用了散点式随机性的描写,但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惟妙惟肖。这既是作家方英文的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更深刻的艺术意图。
人物的众多与形象各异,其实正为了寓意谁都不可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旁观者,从而突出了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下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每一个人,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为整体“类”的一部分,他们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以及历史与政治的社会现实。
少年元尚婴有两次看似是偶然的“蝴蝶的翅膀”煽动,给予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因为初中生万水贵的不幸死亡而得以有了上高中的名额、第二次是因为跑邮员吴小根的牺牲而有了工作。第二次的就业机会对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实在太有冲击力。吃商品粮的“男人每月工资二十八块五,我们干一天活儿才值七分五厘钱!”在城乡差别、二元对立的社会现实面前,能有份吃商品粮的工作,每月拿到高出农村工分好多倍的工资,这是每一个乡村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那么多出身好的学生都没有这个幸运,而元尚婴这个“地主狗崽子”却好运从天而降。所以,他被一篇粉笔大字报的揭发而丢了工作,就不难理解了。
小说将这一个“重大事件”用人性中的良知和理性化解掉,犹如黑暗里的一丝光亮,闪着温暖。至于谁写的大字报,元尚婴的态度,也是作家方英文的态度:“没必要知道”。这与电影《归来》中的情节有相似之处,遭遇坎坷和痛苦的男主人公陆焉识对那段历史极力回避不再提起,而女主人公冯婉瑜彻底失忆。的确,我们可以谅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握手言和。《群山绝响》能够在尽力展示“人”在历史和政治环境中的失败和无能为力,同时,又能对这种环境中的人心、人性做以深度开掘,很是难得。这就是《群山绝响》的“小故事”暗含着“大格局”,也意味着这部小说的深度。它为读者提供了如何经由个人化的独特视角,切入历史叙述的缝隙,从而探求小说与历史接合的可能性。方英文的“艺术个性首先来自于他对生活独到的发现,独到的感受和择取。他不像那些文学大手笔们庄严面对历史和现实,正面强攻重大历史题材或重大现实问题,他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是侧身也可能是倒立着观察出了人生的异样。”[3]
《群山绝响》对于历史的审视抹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为读者勾画了一幅瑰丽的图景。有人说读者的注意力是夏天的一支冰激淋,小说要在冰激淋融化之前,把读者搞定。吸引读者的是故事的节奏,是叙事的张力,是语言和细节漫溢的陌生感、紧张感和真实感。《群山绝响》做到了在冰激淋未融化前吸引了读者。“在全球化趋势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文化快餐式消费情境下,文学越来越多地被市场利益所牵制,读者期待文学最终成为人类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8]《群山绝响》正是方英文以抒情的基调、微观的叙事,为读者创造的一个包容历史种种阴暗与善良温暖的文学世界,提示人们反观自身,反思历史,从而获得灵魂的诗意栖居。
四、结语
方英文《群山绝响》全部毛笔写就。这样的写作形式,势必造成工作量翻倍增大,也让我们惊叹并在阅读中感觉到,小说叙述者的定力和沉静。也许,正是这种写作形式,让《群山绝响》有了不急不缓的叙述节奏,行进与停顿自如。可想每天在落笔之前,方英文胸中自有百万兵,关于少年的心事与忧伤,关于历史与政治,关于记忆与反思,都静静潜藏在文本这一编织物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