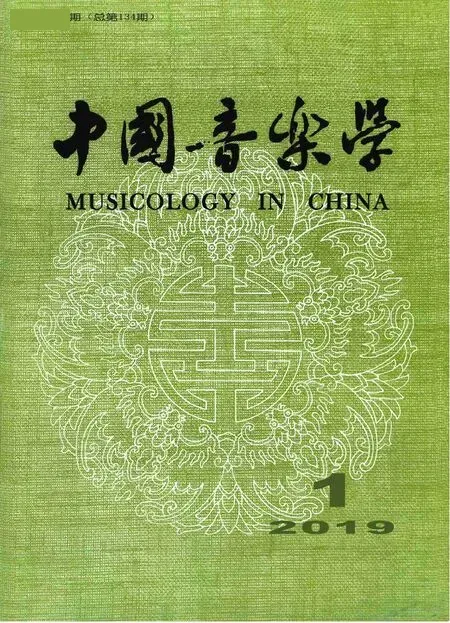《乐书·八音》乐律学错误勘正
——兼论陈旸的音乐水平及《乐书》文献价值
□陆晓彤
北宋崇宁二年(1103),陈旸向徽宗敬献《乐书》200卷,前95卷《训义》阐释儒家典籍中的音乐思想,后105卷《乐图论》记载音乐实践,下设律吕、八音、歌、舞、杂乐、五礼6个门类,其中卷一○八到卷一五○,以《八音》为名专论乐器,共记录乐器条目422条,附图214幅,约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仅就乐器记载的全面性来说,其文献价值卓著。
《乐书·乐图论·八音》①本文使用《乐书》版本为“光绪丙子春刊刻菊坡精舍本”,对勘本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元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以下简称《乐书·八音》)在百余条乐器条目下讨论了乐器与乐律的对应关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陈旸所表达的乐律学的见解存在严重错误,暴露了其本人并不充分的音乐知识储备。相比于《乐书·律吕》中以摘录前人成果为主的内容,《乐书·八音》所呈现的乐律学观念更能体现陈旸本人的乐律学水平。由于这些乐律学观念不是集中论述,而是散见在对各类乐器记载之中,不易被引用、研究陈旸《乐书》的学者发现,故一直未被学界所正视。
《乐书·八音》中反映出的乐律学水平及治书态度,理应作为衡量《乐书》文献价值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通史专著多将《乐书》称为“音乐的百科全书”,然观其知识之可靠性、治书之严谨性,实难担此美誉,学界一直以来存在对于陈旸《乐书》的评价过高的问题。本文以文献学工作为基础,运用乐律学知识,剖析《乐书·八音》中的乐律学错误,为重新评价陈旸《乐书》提供理论依据。
一、治书目的影响下的保守乐律学观念
《乐书·八音》所反映的乐律学理论并不复杂,它没有涉及汉代以来律学家孜孜以求的黄钟还原问题,也不讨论唐宋乐器演奏中与二十八调密切相关的旋宫问题,陈旸对乐律的全部见解,完全基于对恢复周代“先王之制”的不懈追求。因此,他在《乐书》中持有极为保守的乐律学观念,坚持认为五声、十二律才是乐之正道,反对使用“二变”的七声音阶和使用“四清声”的燕乐十六声。
(一)治书目的的潜在影响
《乐书》在编纂之初即立意于“经”的治书目的,影响着陈旸在《乐书》中所表达出的音乐观念,也必然影响着《八音》的整体结构及乐器分类。因此,梳理《乐书·八音》中存在的乐律学问题,必先探求其编纂目的,研读其音乐思想。
《乐书》的内容顺应了北宋复古思潮,鲜明的反映了陈旸意图恢复三代礼法以实现礼乐治国的政治追求,是《乐书》明确表达出的编纂目的。《乐书·序》载明:
臣先兄祥道是时直经东序,慨然有志礼乐,上副神考修礼文、正雅乐之意,既而就《礼书》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祗通先志,诏给笔札缮写以进,有旨下太常议焉。臣兄且喜且惧,一日语臣曰:“礼乐者,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阙一不可也。比虽笼络今昔,上下数千裁间,殆及成书,亦已勤矣。顾虽寤寐在乐,而精力不逮也。”嘱臣其勉成之。臣应之曰:“小子不敏,敬闻命矣。”①《乐书》“序”,第5页。
显然,《乐书》的编纂是在陈祥道授意下展开的。其兄祥道进献《礼书》150卷,升迁为太常博士,遂勉励陈旸编纂《乐书》进献,以期与所献《礼书》合为一代礼乐之经典。《乐书》虽于百年后才在同乡后人陈歧的主持下得以刊刻②详见《乐书》“三山陈先生《乐书》序”:“今年(庆元)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权发遣建昌军事,三山陈侯岐送似《乐书》一编。”,但陈旸当时仍得到了“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③《宋史·列传第一九一·儒林二》,中华书局,2000年,第9915页。的实质性升迁。以献书为仕途晋升之道,是不可能写在《乐书》之中却也真实存在的直接目的。
因此《乐书》的论述内容多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角度,更强调对统治者的劝谏,对胡俗音乐的斥责,以及对“国无二君”“尊卑有序”等忠君思想的维护。其“八音门”并不注重对音乐理论、演奏实践的深入探索,而是处处凸显乐器中蕴含的儒家传统人伦观念,甚至在部分条目中直接忽略乐器形制记载,转而强调音乐对政治的影响。总之,陈旸并不是以编纂“音乐百科全书”或乐器词典为己任,其“为宫廷乐事提供典籍范本”的治书宗旨贯穿《乐书·八音》始终,这也导致陈旸将极为保守的音乐观念贯彻到乐律层面。
(二)反对“二变”,推崇“五正声”
陈旸认为五音是先王制乐之本源,两个变音是后人为追求享乐而增加,“三于五,声为不足;七于五,声为有余”④《乐书》卷一一九《丝之属·雅部》“琴瑟中”,第3页。,“合五音”被陈旸认为是乐器的最优形式。
因此,陈旸明确反对在雅乐演奏中使用含“二变”的七声音阶,他认为“二变不可用于钟律明矣”⑤《乐书》卷一三三《金之属·俗部》“哑钟”,第7页。,编列十四的编磬“倍七音之失”⑥《乐书》卷一一二《石之属·雅部》“玉磬、天球”,第6页。而破坏了礼乐的仪式性使音乐流于世俗,钟磬之乐乃至所有雅乐乐器不应含有变音。故而宋代两类雅乐乐器都因形制“不合五音”受到陈旸“非先王雅乐之制”的斥责,在《乐书》中被逐出《雅部》,降级到《俗部》记载。这两类乐器一类是宋朝新制雅乐器“太一乐”“七星管”“拱辰管”等,陈旸认为它们受后世七音泛滥影响而“溺于七音之失”;另一类则是自周代礼乐设立之初便用于雅乐演奏的古乐器,如七孔埙、七孔笛、七孔籥、七孔篪等,陈旸认为后人在埙、篪等上古乐器流变过程中加设二变之音,影响了原本中正平和的音乐表达,而宋代雅乐沿用“七音”规格的古乐器,则是犯了“不知去二变以全五声之正”的错误。可见,即使该雅乐器自先秦时期既已应用于雅乐演奏,一旦“溺于七音”,即被陈旸认定为不合礼法。
陈旸对七音乐器的反对并未停留在雅乐演奏领域,又以此为标准对文人音乐、民间音乐中切合七音的乐器做出评判。仅用于民间音乐演奏,在宋代已经失传的卧箜篌,也因张有七弦被判定为“郑、卫之音,非燕乐所当用”⑦《乐书》卷一二八《丝之属·胡部》“大箜篌、小箜篌”,第4页。。即便是历来被视为文人阶级代表性乐器的琴,也因张七弦的规格受到陈旸质疑:
七弦之琴,存之则有害,古制削之则可也。……有变宫声,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少宫、少商之弦,岂古人祝寿之意哉?其害理甚矣。①《乐书》卷一二〇《丝之属·雅部》“七弦琴”,第3页。
《乐书·八音》两次对陶渊明“不解音律而畜素琴”②《乐书》卷一四一《丝之属·俗部》“素琴、素瑟”,第7页。的行为大加赞扬,认为应遵循古人“君子无故不彻琴瑟”的原则,表现出陈旸作为文人阶级对“琴”及其背后高洁隐喻的认同。但陈旸又认为七弦琴制应削减为最初由圣人创制的五弦形制,七弦琴并不能表达吉祥祝愿之意,也不符合君尊臣卑的道德标准。《乐书》以“五音”为标准严格分类乐器,反映出陈旸对所谓乐之正道的坚决维护。陈旸坚信符合先王礼乐规范的音乐有稳定政治、和谐民心的功效;反之,则其昭示并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
基于这种思想,《乐书·八音》认为“二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至于这两个变音是雅乐音阶中的变、闰,还是燕乐音阶中的清角、清羽,书中没有记载。这或许意味着“二变”一词在北宋是人所熟知的乐学概念,但依据书中对乐律学理论的整体阐述判断,未载明“二变”,在于陈旸对“二变”的具体音位缺乏清晰准确的认识,其保守的乐律学观念与音乐实践中不同的音阶排列形式无关。
(三)反对“十六声”,推崇“十二律”
陈旸反对“十六声”的观点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十六声”能否应用于雅乐演奏,是北宋时期才开始频繁讨论的礼乐建设问题。陈旸在编纂《乐书》时也受时代潮流裹挟,就这一问题表达了个人见解。他认为十二律才是合乎上古圣人作乐伊始的乐声范围,而四清声的危害甚至可以等同于郑卫之音,“足以使民之心淫矣”③《乐书》卷一三三《金之属·俗部》“序俗部”,第1页。,“比十二律余四清声”④《乐书》卷一三四《金之属·俗部》“方响”,第3页。破坏了两千年来雅乐的正统性。
因此十六枚成编的钟磬、十六管排箫、十六簧笙等雅乐乐器,被《乐书》判定为汉以后乐官“附益四清而为之”⑤《乐书》卷一一二《石之属·雅部》“编磬、离磬、毊”,第8页。;二十四管排箫等则被认为“去四清声以合五音”⑥《乐书》卷一四五《丝之属·俗部》“阮咸琵琶”,第3页。,是不流于世俗的,有崇尚先圣、谨守礼法志向的乐器。教坊燕乐中十六枚成编的方响,民间词调音乐中九枚一组的水盏,也因使用四清声而被陈旸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陈旸在反对十六声的同时,认为又“二十四管备律吕清浊之声”⑦《乐书》卷一四七《竹之属·俗部》“雅箫、颂箫”,第3页。的排箫、“浊声十二、中声十二、清声十二”⑧《乐书》卷一二三《匏之属·雅部》“笙、巢笙”,第3页。的巢笙符合“先王之制”的。据此可知,陈旸是支持乐器音域涵盖十二律清浊正倍之声的,反言之,陈旸所反对的并不是黄钟到清夹钟之间这略宽于一个八度的音域,而是为了维护一种既定的、不容篡改的政治制度而已。
(四)“时代局限”之内外
正如《乐书·序》所载:
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盖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寸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既有宫矣,又有变宫焉,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是两之也,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⑨《乐书》“序”,第9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宫音代表君主,因此保守派的乐律学家认为音阶排列中不能使用变宫;而黄钟作为雅乐之正,不能两分,清黄钟的使用同样不符合传统儒家学者对音乐文化内涵的阐释。陈旸对“二变”与“四清声”的排斥,并不是出于对乐器演奏实践的考量,而是基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宫声与黄钟律所代表文化内涵的重视。这些保守思想受制于陈旸的教育背景及时代局限,并与《乐书》的治书目的紧密相联,尚不必被过度诟病。
但需要正视的是,陈旸身处的时代,乐器制造工艺、乐器演奏技法随着唐乐的高度发展而日趋精湛,律法的探求虽在北宋时期没有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但此前的律学研究也已脱离五音、七律等基础概念的界定,转而向着黄钟还原、管口校正等实用律学领域继续推进,七声音阶的普遍使用已成既定事实,燕乐二十八调也已取代理论性高于实践性的八十四调体系,占据唐宋音乐生活的主流。陈旸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仍固守着五声、十二律才是乐之正道的传统思想,在宫廷雅乐、燕乐、民间音乐等多种演乐场合对使用“七音”“十六声”的乐器大加斥责,这种音乐思想即使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也是过于保守的。
尽管不符合音乐发展的客观需要,上述过于保守的乐律学理论受制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治书目的,仍可以视为是对符合先王之制的正统雅乐过度追求的结果,可归于“时代局限”之内。但是,陈旸将反对“七音”“十六声”的观念简单扩展到乐器形制层面,既不符合音乐演奏的实际需要,又反映出陈旸本人乐器学原理的缺失与乐律学逻辑的混乱。由此引发的错误记载,已经跃出时代局限的包容范畴,而进入学理辨正的层面。
二、对乐器学原理的错误认识
陈旸的乐律学追求,表现为以“五声”“十二律”为标准限定乐器规格、批评与“七音”“十六声”形制吻合的乐器这两个方面,而这种追求背后潜藏的是陈旸对乐器基本发声原理、演奏方法以及编列方式的错误认识。
第一,陈旸盲目地认为乐器的开孔数目、张弦数量可以限定该乐器的音域范围,凡是开孔、张弦、编管、编悬规格为五、十二或其倍数的乐器,即符合“五声”“十二律”的标准,反之则是沉溺于“二变”“四清”,应受斥责。这套判断标准的问题在于,排箫、钟、磬、笙等固定音高乐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判定标准。但就管乐器而言,首先,五音孔乐器在不使用任何特殊演奏技巧的情况下,仍至少可以发出六个乐音——音孔全按时管体翕声发出该乐器最低音筒音。其次,开半孔、哨吹等特殊技巧可以有效扩大管乐器的音域范围,五孔管乐器的音域范围显然可以满足并超出七声音阶的演奏需要。弦乐器方面,无品乐器本身音高机动性较强,改变按弦位置就可以改变音高,即使是一弦乐器,所能演奏的音列也远超五音范围。若以只能演奏五声音阶、不能演奏两个变音为标准,那么五孔、五弦乐器并不符合陈旸的音乐追求。而陈旸对五孔、五弦乐器的极力赞赏恰恰反映了他对乐器发声原理、演奏方法等基本知识的欠缺。此外,既然陈旸不了解弦、管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据此推断他极有可能并不具备乐器演奏的能力。
第二,陈旸对乐器孔位设置、定弦法、编悬方式的判定过于主观。如,陈旸认为六孔篪符合“六律之正声”,十孔篪符合“五声正倍”,但如何能判定六孔篪必为六阳律匀孔设置,十孔篪必依五声音阶设孔呢?这种无根据且不符合乐器原理的判断显然是陈旸的主观臆断。
再如,《石之属·雅部》“玉磬”条:
由是观之,玉磬十二,古之制也。益之为十四,后世倍七音之失也。①《乐书》卷一一二,第6页。
《金之属·雅部》“编钟”条载:
由是观之,钟磬编县各不过十二,古之制也。汉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之牛洪论后周钟磬之县,长孙绍援《国语》、《书》、《传》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为十四。梁武帝又加浊倍,三七为二十一。后魏公孙崇又三县之,合正倍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调,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变、四清言之也。②《乐书》卷一一〇,第3页。
书中记载的多种钟磬编悬方式,可系统划分为按十二律为序编列、按七声音阶顺序编列两类。但《乐书》并未给出十六、十九、二十四枚的编悬乐器是按半音关系编列,而十四、二十一枚为一簨簴必是按七声音阶编列的依据。陈旸对两种编列方式的判定并不是对历代编钟磬编列的方式进行考证、总结后的结果,而是仅依据编列数量对编悬关系做出了主观解释。
第三,陈旸在使用这套错误理论时,不顾上下文已经摘引前人文献中对乐器实际音位的记载,即使《乐书·八音》所录内容已经载明了管乐器哨吹、半窍所能奏出的音高及弦乐器的定弦法、编悬乐器编列方式,陈旸仍罔顾上下文中前人文献对乐器形制的记载,自顾其乐律逻辑,以孔位、弦数、枚数定其音域,继续以上两条中的错误。
如《丝之属·雅部》“七弦琴”条,陈旸据弦数判定七弦琴溺于二变之音,含变宫而有失吉祥之意,认为“七弦之琴,存之则有害,古制削之则可也”①《乐书》卷一二〇,第3页。,而不顾同一条目中“琴又有少宫、少商之弦”的明确记载,显然琴在五弦之外并不是取两个变音定弦,《乐书》摘引内容与陈旸个人乐论前后不符,也印证了陈旸以数量为标准主观判断乐器的定弦方式。《丝之属·俗部》“阮咸琵琶”因张有五弦被赞为“诚去四清声以合五音”②《乐书》卷一四五,第3页。,获得了“则舜琴亦不是过也”的极高评价,但该条小字注文引“太常乐工俗谱”,明确记载了用五弦在一柱、二柱之间演奏“十六声”的按弦方法,若陈旸留意在编纂《乐书》时录入的前人成果,则会发现该乐器既不符合“去四清”,也不完全“合五音”。
又如,“雅埙、颂埙”条:
皇祐中,圣制颂埙,调习声韵,并合钟律。前下一穴为太簇。上二穴,右为姑洗,启下一穴为仲吕;左双启为林钟。后二穴,一启为南吕,双启为应钟,合声为黄钟。颂埙、雅埙对而吹之,尤协律清和,可谓善矣。诚去二变而合六律,庶乎先王之乐也。③《乐书》卷一一五《土之属·雅部》,第5页。
即使书中明文记载了宋代颂埙可以演奏以黄钟为宫的完整七声“清乐音阶”,该乐器仍因开六孔以“合六律”而到了陈旸的褒奖。
《金之属·俗部》“方响”条:
方响之制,盖出于梁之铜磬。形长九寸,广二寸,上圆下方,其数十六,重行编之而不设业,倚于虡上,以代钟磬。凡十六声,比十二律余四清声尔。抑又编县之次,与雅乐钟磬异。下格以左为首,其一黄钟,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吕,五蕤宾,六林钟,七南吕,八无射;上格以右为首,其一应钟,二黄钟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吕之清,六大吕,七夷则,八夹钟,此其大凡也。后世或以铁为之,教坊燕乐用焉,非古制也。非可施之公庭,用之民间可也。④《乐书》卷一三四,第2页。
文中明确记载的方响编列方式,是在十二律外再取清黄钟、清太簇、清姑冼、清仲吕四声,以此便于旋宫,但陈旸不顾后文内容,仍仅按数量将编悬规格十六枚的方响判定为“十二律余四清声”的编列方式。反对“七音”“十六声”的观念,桎梏了陈旸对钟磬编列方式的判断。
《乐书》的编纂与多数古籍相同,是以摘录前人文献为主体,杂以编纂者的个人观点,陈旸个人乐论出现大量与引自他人的文献材料前后矛盾的内容,可见《乐书》的编纂过程极不严谨,陈旸本人的治学态度值得后人反思。
三、以“数字吻合”为标准的乐律学逻辑混乱
若我们将上述错误的乐律学逻辑继续推进,可以发现陈旸在《乐书·八音》中展现出一套自成体系的乐律学逻辑,而这套逻辑的根本性错误可以概括为陈旸对“声”“律”“二变”等基础概念缺乏准确的理解,而将“数字吻合”视为解释乐器与乐律关系的准则,直接导致《乐书·八音》出现大量不合乐学规律,只合数字加减的乐论内容,所形成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如,《竹之属·雅部》“大篪、小篪”条载:
先儒言篪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说,以中声论之,六孔,六律之正声也;八孔,八音之正声也;十孔,五声正倍之声也。盖其大小异制然邪?郑司农有七孔之异论,未免泥乎七音之失也。⑤《乐书》卷一二二,第7页。
在这段论述中,陈旸不仅延续了以开孔数判定管乐器音域范围的错误,还出现了以篪的八孔对应“八音”以维护雅乐规范的新问题。然而,八音仅是我国古代一种乐器分类法,如何与篪的开孔相对应?将同一类管乐器的开孔数先后与音律、乐器分类法、音阶排列相对应,反映陈旸以“数字吻合”为立论基础的乐律学逻辑,至于这些概念所指代的具体含义,陈旸显然并不了解。
《匏之属·胡部》“十七管竽、十九管竽、二十三管竽”条载:
宋朝大乐,诸工以竽、巢、和并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为之。所异者,特以宫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尔,虽名为雅乐,实胡音也。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则兼乎四清、二变,十九管则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⑥《乐书》卷一三一,第2页。
陈旸将十九管笙的笙苗设置,臆想为十二律之外加以七音,但十二律代表的是宋代屡次改乐后设定的绝对律高,七声只是这些音律旋宫转调时在音阶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陈旸将两个不同范畴内的乐律学概念——十二律、七声相叠加,以满足其理论逻辑——数字吻合的需要,愈发暴露出他对乐律学基础概念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那么,竽的二十三管是如何“兼乎四清、二变”呢?按陈旸的逻辑,应是他所反对的“十六声”与“七声”叠加而成,如此才能既包含四清声,又包含两个变音。其自身乐律学体系的逻辑之乱、立论之误,令人咋舌。
同类错误在《乐书·八音》中并不鲜见,现再举一例,“十八管箫”条载:
《唐乐图》所传之箫,凡十八管,取五声、四清倍音,通林钟、黄钟二均声,西凉部用之。①《乐书》卷一三〇《竹之属·胡部》,第3页。
陈旸似乎认为经过他的反复强调,《乐书》读者应该已经掌握了这套乐律学原理,因此书中没有详细记载排箫十八管如何取声才能满足陈旸“取五声、四清倍音”的评定。笔者试图顺着陈旸的个人乐律学逻辑,以数字吻合为标准对此做出解释,即,将两个不相关的乐律学概念五声、四清在正声之外再取倍声,五声倍为十声,四清声倍为八,叠加则正合数字十八。若此推论符合陈旸本人的内在逻辑,那么其乐律学理论的荒谬程度以及陈旸的音乐水平值得重新估量。
四、陈旸自相矛盾的律学追求
陈旸在自身乐律学逻辑内继续深入,提出了对不合礼法乐器加以改正的方法,即去“二变”“四清”以达到陈旸所推崇的“正五音”“合六律”“取用十二律”的律学追求。
(一)“去四清”与“正五音”
陈旸在《乐书·八音》中多次讨论了“去四清”与“正五音”的因果关系,如“阮咸琵琶”条载:
今诚去四清声以合五音,则舜琴亦不是过也。②《乐书》卷一四五《丝之属·俗部》,第3页。
《丝之属·雅部》“琴瑟中”条载:
宋朝太常瑟用二十五弦,其二均之声,以清、中相应双弹之,第一弦黄钟中声,第十三弦黄钟清应。其按习也,令左右手互应。清、正声相和,亦依钟律,击数合奏,其制可谓近古矣。诚本五音互应而去四清,先王之制也。③《乐书》卷一一九,第3页。
陈旸认为二十五弦瑟摒弃了“四清声”的使用,符合“五音互应”的礼乐规范,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首先,除非二十五弦瑟以五声音阶在五个八度中定弦,否则无法满足二十五根弦“五音互应”的要求,而这种定弦方式不符合演乐实际需要。且书中已经载明太常瑟在两均内取声,第一弦与第十三弦皆应黄钟,显然是以十二律为序定弦,与“五音互应”或“去四清”无关。
陈旸认为“去四清”可以达到“和五音”的追求,而实际上,若以五声音阶旋宫转调,则使用夹钟至应钟九均时,皆需取用四清声才能构成完整的宫调五声音阶;若不旋宫,只在两均内建立黄钟为宫的五声音阶,那么四清声中的黄钟清、太簇清两音作为宫清、商清同样必须取用。其根本在于陈旸不懂律与声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不是一个包含或并含的关系,四清声是十二律的延伸,五音则是一均之内不同音高按一定规律排列组合而形成的音阶概念。陈旸对四清声、五音相互关系的叙述,再一次表明他本人基础乐律学知识的匮乏。
(二)“去二变”与“合六律”
同样,“去二变”并不能“合六律”,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若以黄钟为宫,六律中的蕤宾恰是“二变”中的变徵,去二变之后的五声音阶分别是黄钟、太簇、姑冼、林钟、南吕,与六律并不吻合。《乐书·八音》中对六孔埙“诚去二变而合六律,庶乎先王之乐也”的评论,只是强调律与乐器形制两者之间数字的吻合,二变与六律是不同范畴内的乐律学问题。
《金之属·俗部》“哑钟”条:
唐太宗召张文收于太常,令与祖孝孙参定雅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有其七,馀五者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由此观之,近代惟用其七者,岂有他哉?蔽于不用十二律而溺于二变,故也。④《乐书》卷一三三,第7页。
陈旸认为近代钟律不再使用十二枚,而是使用七枚,是陷入不使用十二律,而使用二变的错误理念之中。但是,编钟十二律齐备,本身就是为七声音阶的转调提供了可能,十二律编列的编钟其演奏方法也不可能是逐律敲击,仍要按五声或七声音阶取音,而此时的二变已包含在十二律之中。
不需要高深的乐律学修养即可知:旋宫以后四清声可作不同均之五正声,而被《乐书》推崇的十二律若全部取用必包含二变之音。至此可以发现,陈旸的两个乐律学主张——推崇十二律、五音与反对七声、四清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
结论
陈旸《乐书》自刊印以来,被认为是代表两宋时期最高音乐水平的论乐专著。音乐史学界对这部专著投入了极高的关注,音乐通史类著作更是将其美誉为“音乐百科全书”。溯其源头,应是1984年《音乐学丛刊》》第3辑发表王世襄先生《宋陈旸〈乐书〉——中国第一本音乐百科全书》,王世襄先生在文中首次将“音乐百科全书”这个极具褒奖意味的称谓赋予陈旸《乐书》。但是,对一部音乐专著做出评价的首要依据,应是辨析该文献所载内容是否真实可靠,理论是否学理准确、符合逻辑,对《乐书》价值的评定,也必须建立在深入分析与研究该文献文字、附图内容的基础之上。
陈旸在陈祥道勉励下,意欲编纂一部经学著作,但是,乐书的编纂与礼书毕竟不同,乐书要求编纂者具备较高的音乐修养和丰富的音乐知识储备,否则将会在乐器、乐律等专业论域出现较为浅薄的错误。同时,音乐专著的编纂与类书乐部的编纂也有不同,类书只需分类辑录前人记载,而音乐专著则需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之上,以纂者的专业知识水平保证编纂内容的严谨性、分类的合理性、附图的准确性,以及乐论的可靠性。就笔者所见,现存音乐专著的编纂者,或以记录当朝音乐史实为主,或专精一门深入讨论,绝大部分还是具有一定的音乐知识水平,属当时兼具音乐技能与文学修养的阶层。但是从《乐书·八音》所反映出的乐律学观念来看,陈旸本人并不具备基本的音乐修养,也没有任何记载显示他长于乐器演奏。通过对书中乐律学错误的剖析,可以发现这部被学界誉为“音乐百科全书”的文献编纂者,只是一位毫无音乐修养的儒生。
陈旸在音乐知识匮乏的情况下,仍大肆抒发个人乐律学见解。《乐书·八音》本身没有涉及任何高深的乐律学理论,其乐律学层面的错误浅薄到仅以“二、四、五、七、十二、十六”六组数字排列组合对应乐器形制,解释律、器关系。最为荒谬的是,陈旸在维护自身保守乐律学理论的过程中,甚至都没有理解他本人编纂时所摘引的前人文献,使得《乐书》中大量出现引文内容与编撰者乐论前后不符的问题,暴露出陈旸《乐书》极不严谨的编纂过程及治书方法,这严重影响整部《乐书》的文献价值。由于这些乐律学见解并不集中,陈旸又将这些错误包裹在“数字吻合”的逻辑之下,非深入研究难窥其本质,这两种编纂特质使得《乐书·八音》中的乐律学错误在此前并未引起学界关注。
考量古代音乐专著的实际文献价值,归根到底应建立在记载内容“正确性”的基础上,反之则无益于学术研究。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学界一直以来存在对陈旸《乐书》评价过高的问题,其本源在于对《乐书》具体记载内容的研究仍有欠缺。《乐书·八音》保存前代文献的价值,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其他类书类文献并不十分突出,而书中乐论内容的谬误,则会对研究唐宋两朝乐器乃至整个古代乐器史造成一定的误导,陈旸《乐书》编纂中所反映出并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引起征引《乐书》内容为例证的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