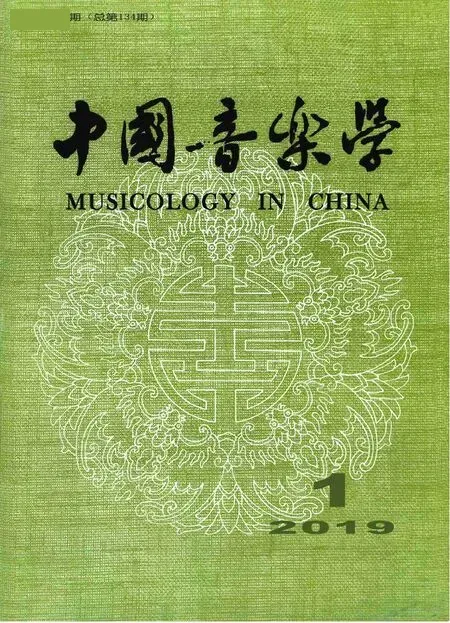“审美参与”:音乐审美经验的身体化建构
□王文卓
从学科形成角度说,美学问题是知识学问题,其理论疆域及概念间逻辑的形成是人类对“情”知识不断进行确认的结果。美学知识的合法性始终与具体审美实践相联系,情感实践的拓展及感性样态的出新必然引起对固有美学概念的反思。当下,对审美经验这一概念的反思与重构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理论问题,主要动力来自于当代美学研究对身体与意识、艺术与生活、通俗与高雅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的反驳。“审美经验的身体化”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学界对音乐审美经验的身体化问题已有探讨,但理论上还需进一步探索并选择合适概念或范畴阐释这种现象。“身体化”仅在现象的一般性层面进行表达,还难以揭示音乐审美“体化实践”(incorporated practisces)①这一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提出,“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是人类记忆实践的两种形式,“体化实践”意在说明身体行为在信息记忆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萧梅曾借用这一概念来阐释身体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中的重要价值。从音乐审美经验的角度说,这一概念将表达出身体的理性积淀与感性表达的基本关系。的丰富性。由此,本文试图借助由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审美参与”(aesthetic engagement)②阿诺德·柏林特(1932~),国际美学会前主席,美国长岛大学荣誉退休哲学教授。“审美参与”是柏林特美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据他本文所述,“审美参与”首次使用于1967年的《经验与艺术批评》一文中。(参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另外,国内美学界对“aesthetic engagement”的翻译有所不同,除译为“审美参与”外,还有学者译为“审美介入”、“审美融入”等。理论阐释音乐审美经验的身体化建构,对音乐“审美参与”的理论内涵、基本形式及理论不足等展开讨论。
一、感性学向身体拓展
(一)背景:感性学批判
综览近年来美学界关于人类感性经验本质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从精神向身体的拓展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建构身体话语成为美学研究突破固有范式的重要途径。当代身体美学研究对鲍姆加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提出的“感性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认为鲍姆加通创设的“感性学”其实并不完善,由于忽略身体的价值,导致了理论建构的偏差。他们所反思的首要问题是:如果身体知觉不在感性范围内,那它属于什么?身体美学认为,经典感性学对人类感性经验的研究是有所取舍的,而这种取舍是在西方启蒙精神及身心二元论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的必然结果。
例如,英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认为,鲍姆加通的美学存在重大失误,它排除了人的肉身性存在及各种官能活动。“哲学必须铭记即使在哲学开始思考之前,肉体早已就是感性的经验的有机体,以有别于置客体于匣中的方式被置于它的世界之中。”①〔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柏敬泽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他由此指出,美学首先是作为肉身话语而存在的。
再如,身体美学学科的建立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同样认为:“鲍姆加通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且旨在感性认识的完善。而感觉当然属于身体并深深地受身体条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感性认识依赖于身体怎样感觉和运行,依赖于身体的所欲、所为和所受。然而,鲍姆加通拒绝将身体的研究和完善包括在他的美学项目中。”②〔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2页。从舒斯特曼所持的实用主义立场来说,身体美学的根本指向是要把美学从纯思性的理论拓展为与生活经验融为一体的身体实践的美学。
(二)“身体转向”与音乐美学
人类内在精神结构的形成及外在世界图景的建构都是要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离开身体,我们就难以理解人类社会的任何现象,包括音乐审美实践。从根本上说,美的尺度是身体的尺度,或者说它来源于身体。人类在触摸、聆听、观看、嗅闻等活动中把自然人化,在把世界按照人的品格进行塑造时,身体感官经验作为“第一门户”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一观念应当成为音乐美学研究的哲学前提。
美学研究中“身体转向”始终没有引起音乐美学研究者的注意,“悬置身体”是汉斯利克以来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造成这种理论缺失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们太专注于西方艺术音乐(以“音乐作品”为核心)的美学研究,而针对非艺术音乐,在理论上难以开拓出新的理论境界,二是当下的音乐美学研究大有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趋势,而在学科元理论的探索上缺乏应有态势。从“身体转向”来审视音乐美学学科,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音乐与身体的关系,这不仅涉及学科研究视域的拓展,而且对一些核心概念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与界定。
西方现代审美理论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地提升和强调了精神层面,而忽视了感官经验在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心灵美学”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而在“心灵美学”基础上生发出来的音乐审美经验论遮蔽了音乐审美现象的丰富性。人类“创造真实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始终与身体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体感性是音乐审美经验的重要层面,它在音乐审美信息的形成、传播及接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身体重要性的认识不能仅从它所具有的技能性着眼(这是“身体工具论”),还应当明确它在建立感性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美学亟需挣脱“心灵美学”的窠臼,进而建立音乐美学研究中的身体话语。
二、“审美参与”理论的基本立场与内涵
在审美实践中,身体具有意向性,而这种意向性具体表现为“审美参与。③王文卓:《论身体化的音乐审美经验》,《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6年第4期,第32页当从身体美学的整体图景来审视柏林特的美学研究时会发现,他重视身体理论,却从不泛泛而谈。柏林特不仅有着丰富的钢琴演奏实践,而且还尝试过作曲,因此他在阐述“审美参与”理论的思想内涵时,往往会以具体的音乐事项为例进行说明。基于丰富的艺术实践,他说到:“审美经验必须作为有意识的身体经验来理解”。④刘悦笛:《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审美参与”理论可以成为在阐释音乐审美身体化问题时较为合适的理论选择。
(一)基本立场
在20世纪后半叶,美学研究对康德(Immanuel Kant)的反叛俨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即“后康德主义”。柏林特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之一,他对西方现代美学作为了十分深刻的反思。柏林特认为,从发生基础来说,西方现代审美理论有着极大的误导性,它本身所受的是知识静观模式的引导,而与审美经验无关。①李媛媛:《审美介入:一种新的美学精神——访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诺德·柏林特教授》,《哲学动态》,2010年第7期,第102页。“审美欣赏已经被典型地描述为意识的某种行为,某种与众不同的意识。这样的解释不仅不适用于审美欣赏,而且是对审美欣赏的歪曲”。②〔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陈望衡校,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因此,“审美参与”首先是站在审美无利害、审美静观的对立面上提出的,其基本指向是要撼动西方现代审美原则在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进而把审美经验研究的理论重心从心灵经验拓展至身心合一的人。
柏林特认为,“参与”是一种有效的经验方式,并且在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审美参与并不只是揭示当代艺术的原则,它同样适用于传统艺术,并充实了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这些原理在启蒙运动和现代美学出现之前就早已居于突出地位。”③〔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李媛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前言,2—3页。“审美参与”的提出代表了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它凸显了身体感官的介入在审美经验中的基础地位,从而把对审美经验的认知从“静态的沉思性想象”转变为“动态的身体化建构”。
(二)基本内涵
首先,“审美参与”理论是一种注重描述与阐释的美学理论。柏林特认为,“哲学家的美学”其实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设想艺术,这种美学是“规定性”的。而“审美参与”则反映了“身在其中的世界”,是以实际的审美活动为基础的,其描述与阐释的对象即包括欣赏者的活动,也包括表演者的活动。柏林特指出,美学的价值在于阐释而不是判断。④〔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第62页。
其次,它突出了审美经验的身体化建构问题。尽管柏林特并不想把自己归入到哪个美学流派当中,但杜威(John Dewey)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对其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明确的。从理论关联性上看,“参与美学”可以看作是杜威实用主义美学的新发展。柏林特认为,审美经验与生活中的其它经验一样,只有在身体知觉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完满实现。他曾就立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移情不仅发生在精神领域,而且身体也参与到了移情过程中。⑤〔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第29页。由此,审美经验的身体化成为“参与美学”研究中的基本主旨。
再次,它注重对审美经验“知觉一体化”的研究。“审美参与”明确了主客体之间动态的经验建构关系,同时认为,这种建构是融入特定情境的,柏林特称之为“审美场”(aesthetic field)。“审美场”主要由四个因素组成:对象、感知者、创作者和表演者,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科技发展等因素。⑥〔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69—70页。在注重与环境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审美参与”的建构性内涵将更为丰富。由于审美情境之文化属性及模态的多样性,“审美参与”的表现形式也将呈现出多样性。
三、音乐“审美参与”的基本样态
把“审美参与”理论引介到音乐美学研究中来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它可以有效修正在以往美学观念基础上形成的音乐审美经验论,进而充分表述身体感官在音乐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作用。身体化建构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具有普遍性,从音乐审美现象的结构看,在生成性与接受性两端都存在值得深入探讨的身体介入现象。
(一)生成性“审美参与”
生成性“审美参与”即音乐表演活动中的身体建构,以音乐声音结构的创造性呈现为基本感性特征。
音乐表演中的身体感性能力与长期的技能训练有紧密关系,技能训练的本质是对肉体运动机能的理性规训。这种规训塑造出表演者在二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身体自由性。柏林特十分重视对表演性经验的描述,指出:“肉体介入音乐的核心是感觉意识的增强。这在表演者的强烈经验中处于中心地位。”①〔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第230页。他描述到:“钢琴家经验到四肢出奇的轻松,身体充满了热切、无拘无束而又很集中的能量,手指则变得绝妙的柔顺。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台强有力而有灵活的乐器。”②〔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第230页。
技能规训使身体具有了文化属性和风格感。在音乐表演活动中,身体能有效解读音乐作品的风格内涵,身体表达的细腻性、程式化运行、自由感均与作品的历史风格密切相关。任何一位表演艺术家都不是“通才”,面对历史上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他们只能在特定的风格范畴内来塑造自己的表演风格,例如,有的钢琴家善于演奏肖邦的作品,而有的则善于演奏李斯特的作品。对风格的认识与表达不是仅发生的意识层面,它更表现在以技巧为表征的身体感性层面上。应该进一步表明,身体对风格的表达表现出一种审美自由感,在具体活动中,这种表达不是认知引领下的过程,它是自律自为的。
“审美参与”在不同类型的音乐表演活动中有不同表现,我们需要对这种差异性进行描述。上文已指出,审美情境的多样性造成“审美参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表演空间的约束、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审美信息的传达方式等对音乐表演中特定身体行为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文化形态着眼,艺术音乐、流行音乐及中国传统音乐是当下音乐生活中的三种主要形态。“审美参与”的差异性在这三种形态的音乐表演实践中有明确表现。
在艺术音乐的表演活动中,身体受场域的理性规束较强。艺术音乐的表演空间是音乐厅,舞台与坐席之间空间分割蕴含主体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表演者的身体行为具有约束力。在审美信息的传达方式上,艺术音乐的表演与接受是在“静听”这一模式下进行的,身体间的直接互动程度较弱。
以摇滚乐为例,在流行音乐表演活动中,身体对节奏的体验与表达表现出一种“原初”的身体感性能力。所谓“原初”的身体感性,就是一种受理性规训较弱的感性经验。从空间结构看,虽然流行音乐的表演环境也存在空间分割,但已不蕴含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在审美信息的传达方式上,表演者与欣赏者可以进行直接的程度较强的身体互动。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表演活动中,“审美参与”的情况较为复杂。就笔者所见所思,认为中国传统音乐表演活动中的身体介入具有整体性特征,从而区别于上述两种音乐文化形态。从传承研习、乐谱韵唱到表演实践,每一环节都有身体的直接参与。萧梅提出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身体维度的三个层面较全面地表达出了这种整体性,下文将论及。
(二)接受性“审美参与”
接受性“审美参与”即音乐欣赏活动中的身体建构。柏林特说到:“欣赏性的介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它取决于时期、风格和艺术形态。”③〔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第42页。从实际的音乐审美活动看,接受性“审美参与”的形式显现与音乐的体裁特征及人与音乐的关系有着直接关联。审美主体与音乐作品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接受性“审美参与”的程度及样式就是怎样的。宏观上可将其划分为两种典型样态:直接参与和隐蔽参与。
从人与音乐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接受性“审美参与”的样式,可以把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引向历史的维度。在此,克罗地亚音乐学家伊沃·苏皮契奇(Ivo Supicic)的理论值得借鉴。苏皮契奇对西方音乐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听众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归纳为四种关系类型:主动关系;“中间型”;被动关系;被动关系的“升级”。④〔克罗地亚〕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周耀群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4—46页。显而易见,在这四种类型中主动关系和被动关系居于核心位置。
他在阐述“主动关系”时说到:“音乐在其中构成集体的行为,例如在原始的氏族公社里,作者是不为人知的,而演出者包括了所有——或几乎所有——参加公社的成员。那里没有完全被动的听众。这些参加者歌唱、舞蹈、拍手或以身体的姿势伴随着音乐,他们都深深地被节奏所影响。”①〔克罗地亚〕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第44—45页。可以看出,在他所描述的这种关系中,音乐成为集体经验的表达。从主体性角度分析,音乐活动表现出一种参与性的建构生成过程。
在阐述“被动关系”时,苏皮契奇指出:“作为创作者和解释者的音乐家个人更多地向听众施加影响。这些听众在音乐上完全是被动的,不参加演出,这些演出是保留给总是更加专业的艺术家们的。”②〔克罗地亚〕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第46页。他进而指出,这种“被动关系”的形成与两个因素关系密切,一是只需听的演出的出现,二是音乐的提纯和听众的缩小。显然,这种审美行为指向的是音乐厅模式,接受性“审美参与”中的建构性因素有所减弱。根据贝塞勒(Heinrich Besseler)的描述,这种纯粹的欣赏者在18世纪中叶的莱比锡就已经出现,那时,中产阶级的音乐活动已经从社交性的礼仪活动过渡到了纯表演性的艺术活动。在音乐厅音乐会中,“人们不再积极参与音乐的表演,而仅仅去听赏了。”③〔德〕贝塞勒:《近代音乐听赏问题》,载《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金经言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34页。音乐厅中的审美活动充分体现了音乐家与欣赏者之间具有冲突性的关系类型。
在“主动关系”与“被动关系”相对比的视野中,接受“审美参与”的程度有了较大变化,一种具有建构性特征,另一种是“不参加演出”的被动接受。那么,“不参加演出”是不是就意味着绝对的“静听”④“静听”由“静观”引申而来。在“观(看)”的基础上引申出“听”,符合西方现代审美经验论的要旨。沿着这样的理论线索,“静听”与审美无功利、审美距离等概念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呢?柏林特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认为:“有些参与模式是直接而显著的,而另一些则较为隐蔽。然而这些都使我们超越了存在于传统态度中的静观享受的心理学模式,走向一种经验的统一。”⑤〔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第32页。从根本上说,处在“被动关系”中的欣赏者仍然表现出身体参与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它较为隐蔽而已。这一描述符合音乐厅中审美经验的事实。
四、“审美参与”对“去身性”音乐审美经验论的修正
柏林特指出:“音乐必定以身体化的方式存在着。”⑥〔美〕 阿诺德·柏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对于艺术经验来说,不仅仅是精神的投入这么简单,还要探寻整个人,而不仅仅是心灵,理智或意识介入的方式。”⑦〔美〕阿诺德·柏林特:《艺术与介入》,第29页。从“审美参与”的基本内涵出发,我们需要修正以往对音乐审美经验的认识。
首先应对在“心灵美学”基础上形成的音乐审美经验论的基本内涵予以明确,“心灵直观”“纯意向性”“静听”等概念是理解这种音乐审美经验论的关键。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k)这样说到:“接纳美的机能不是情感,而是幻想力,即一种纯粹关照的活动。”⑧〔奥〕爱德华·汉斯利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18页。他在此所说的“幻想力”与康德在阐述“构成天才的各种内心能力”时所说的“幻想力”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指出这种内心的精神活动是审美经验的本质。“幻想力”即“心灵直观”,一种“纯粹的关照”。“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⑨〔奥〕爱德华·汉斯利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49页。在汉斯利克看来,“心灵直观”成为开启审美自由的一把钥匙。
西方现代审美理论视野中的音乐审美对象是在距离式的“静听”基础上建构起的“纯意向性”对象。茵格尔顿(Roman Ingarden)在“意向性”前面缀以“纯”字,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主体在建构音乐作品意义时更为突出的填充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它作为心灵经验的本质。梅洛—庞蒂之前的现象学美学所说的“意象性”都在“精神意向性”的范围内,身体是被排除在外的。
“心灵直观”及“纯意向性”命题对音乐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究其理论渊源,二者都与康德美学密切关联。并非听音乐都是在审美,音乐审美经验是一种不涉及任何外在目的,不涉及任何理性分析,而只对对象的形式进行感悟的心灵自由运动,这是把审美静观论“移植”到音乐美学中来的直接理论后果。这样一来,音乐审美经验在理论上就凸显出了一种特殊品质,也决定了汉斯利克以来的音乐美学在音乐审美经验论上的“去身性”特征,其哲学根基是身心二元论。
从历史看,“去身性”音乐审美经验论的形成似乎是有实践基础的,西方18世纪中叶在音乐厅中形成的“静听模式”似乎印证了这一理论。但我们应认识到,安静地听音乐并不是欧洲人的传统,这一模式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具体性,审美对象的特殊性(“绝对音乐”)及审美环境的文化规训(音乐厅制度)是其得以出现的两个关键因素,而中产阶级的音乐活动及启蒙精神的影响为这一模式与特定审美经验论之间的相互连接提供了历史契机。
关键问题是,这种“静听”是不是彻底排除了身体参与呢?尽管音乐厅对行为的规训限制了审美主体身体的自由性,但心灵与身体并不因此而隔断。在外在表征上,身体以隐蔽的方式参与到了审美经验的过程中,例如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依音乐的律动来摇晃身体、用脚打拍子等。这种隐蔽的参与方式同样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表现出身体与声音的同构。
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分析,经验中的身体不是孤立的,它具有超越自我,实现审美普遍性的基本能力,即审美中的“身体联合”。处于同一场域中的“身体联合”使音乐表演者与欣赏者的信息沟通变得更为顺畅。身体的社会化生成了“身体图示”的语境性。基于同一语境,尽管表演者与欣赏者在身体介入音响结构的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只要对音响结构的发生存在类似的前经验或前理解层面,这种“身体联合”就可以发生。因此,绝对的“静听”是不可能的。
音乐厅中的“静听模式”是身心参与的整体过程,这与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所描述的“静观中的身体”具有一致性。“在静观对象时,尤其在静观线条和形状体系时,你总是经验到与你所领会的形式有关的身体张力和冲动,经验到形状的升沉、冲击、撞击、相互抵制等等。而这些,是和你自己领会这些形状的活动联系着的;的确,对象的形式或者对象的联系规律,据他们说,在被领会上,恰恰就是因你这方面的‘身—心’活动而定的。”①〔英〕鲍桑葵:《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去身性”的音乐审美经验论意在表达音乐审美的自律性,但却难以全面揭示人类音乐审美经验的本质。它源于静观美学,而“静观”却来自于知识与道德观念领域。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一直在使用某些概念来阐释审美现象,但它们与具体的审美实践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隔阂”。在这个问题上,柏林特对“哲学家的美学”的分析与批判是深刻的。
五、“审美参与”在非艺术音乐实践中存在的广泛性
诚如人类学者所言:“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极有可能在精微之处解构美学的某些传统理论与固有范式。”②覃德清:《审美人类学:价值取向与方法抉择》,《民族艺术》,1999年第3期,第77页。建构音乐美学中的身体话语并对西方现代审美理论中的某些概念进行反思,首先应该挣脱艺术音乐的局限,把研究视野扩展至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我们可以从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获得诸多启发,从众多个案描述中能看到“审美参与”在人类非艺术音乐实践中存在的广泛性。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梅利亚姆(Alan.P.Merriam)就指出:“要理解音乐行为这一跨文化现象,关于身体产生声音的过程、音乐家的肢体姿态以及听者的身体反应的研究显然非常重要。”③〔美〕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陈铭道校,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身体人类学的发展,一些有影响的民族音乐学家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扩展至身体,对身体的感性记忆与表达、身体的文化隐喻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地理论探索。这里最应提及的是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作为民族音乐学家的布莱金在西方身体人类学领域处于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④1977年由他编辑并出版了一部颇具理论份量的论文集,名为《身体人类学》。他在绪论中指出,身体人类学不同以往的体质人类学,它所关注的不仅是人的生理及生物学特征,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各种变化的社会互动的背景中,那些成为文化的过程与产物的身体的外在化和延伸。这本书随后成为身体人类学领域“社会—文化”研究范式的奠基之作。基于学术背景,他自然要对身体与音乐的关系予以特别关注,布莱金指出:“我们经常在产生音乐的身体运动中,发现一段音乐的表达目的,这些不仅可以在一个人的特性中,而且可能在文化中找到各自的起源。”①〔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马英珺译,陈铭道校,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103—104页。《人的音乐性》对非洲文达人的音乐进行了研究,其中对身体行为与音乐感性表达的关系进行了充分描述与阐述。例如布莱金说到:“文达人的音乐并非基于旋律,而是以整个身体节奏律动为基础,歌唱不过是身体律动的一种延伸。因此,当我们似乎听到两个鼓点之间的休止时,必须意识到:对于演奏者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休止——每个鼓点都是整个身体运动的,包括用受或鼓槌打鼓面。”②〔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第22页。再如:“如果我们把他的表演跟他用手指按孔的身体动作联系起来考虑的话,那么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获得截然不同的意义。”“同一段音乐的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使用紧张/松弛的形式与和声,一种使用身体的‘语言’。”③〔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第13页。
随着身体人类学对民族音乐学影响的深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身体维度是近几年逐渐升温的一个重要议题。萧梅力图通过“身体实践”这一理论路径来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意蕴,她指出:“声音结构的表征与身体动作的过程具有经验的一体性和连贯性。”④萧梅:《“樂”蕴于身——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观》,《人民音乐》2008年第5期,第63页。这一路径不仅突破了以往注重静态性文本的研究模式,而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更新了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本体建构过程的认识。所谓空间维度指的就是乐人在行乐过程中在身体行为上所表现出的空间结构关系。萧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身体维度的三个层面:身体介入音乐活动的象征意义;身体行为与音响结构的关系及音乐分析的多维度手段;从表演、传习的角度明确身体训练之于音响过程的意义及价值。⑤萧梅:《面对文字的历史——仪式之“乐”与身体记忆》,《音乐艺术》2007年第1期,第90页。不囿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视野,她认为很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确立“身体记忆”的重要意义,在注重显性资料所给予的历史线索之外,关注乐人的身体行为的历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边界由音乐向声音扩展,身体成为文化阐释中不可或缺的维度。“用整个身体来听”⑥此概念由法国音乐学家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在其所著的《声音》一书中提出。意味着我们需要突破“听觉唯一性”这一固有观念,把“主体”从听感官延展至整个身体,这种延展既包含在声音信息接受中的生理、声学层面,也有在文化规训后身体表达的文化释义性层面。从身体角度来探讨“听的哲学”是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dhe)的重要理论旨趣,在其“声音现象学”研究中论及了声音经验的“缘身性”(embodiment)问题。他认为人对声音的体验并非仅来自于听觉,还与身体经验紧密相关。⑦参见徐欣:《聆听与发声:唐·伊德的声音现象学》,《音乐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页。这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对听觉经验进行的现象学还原,可看作从哲学层面对“用整个身体来听”的论证。
西方学界对当代通俗音乐的研究同样揭示出身体与音乐审美的密切关联。作为身体美学的创立者,舒斯特曼对摇滚、拉普等音乐体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对这些音乐审美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彻底打破西方现代审美理论的独断论梦想。“由摇滚乐激起的那种更加充沛的和充满肌肉运动感的反映,揭穿了传统审美态度的无利害的、有距离的沉思的根本被动性。”因此,“以一种向身体维度快乐回归的方式,显示了一种在根本上得以修正的审美”⑧〔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页。。针对那些批评通俗艺术的言论,舒斯特曼说到:“他们的批评听起来如此猛烈地喧嚣和刺耳,刚好是由于他们意识到摇滚乐迷人的快感已经从根本是行获得了成功,并且破坏了传统审美形式以及包含于其中的许多保守主义观念的权威垄断。”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第51页。音乐狂欢情境的典型特征就是主体身体参与,这种文化模态所呈现出的审美方式在根本上与西方现代美学所倡导的审美原则相对立。
六、对“审美参与”理论的反思
使用“审美参与”理论可以有效地阐释音乐审美经验的身体化问题,但是也应当清晰地看到这一美学范畴所带有的理论局限性。柏林特提出“参与美学”的核心目标是要解构那些他以为提供了“虚假的明晰”的美学概念,进而确立审美经验的“身心一体论”。从《艺术与介入》《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等著作来看,柏林特与舒斯特曼有着相似的理论取向,他们都是在有侧重地凸显身体。这样一种带有“矫枉过正”意味的理论,一方面使我们感到了理论上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却难免具有了某种缺陷及不足。柏林特对自己的“参与美学”信心满满,“相对论物理学放弃了牛顿一些概念的绝对性,而把这些概念包容进更大的、相对的和把观察者作为部分因素包含于其中的整体性理论之中,也许,美学的发展也应当如此。”①〔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第41页。他的意思是要用“参与美学”来包容传统美学,然而,在其美学研究中到底能为传统美学留下了多大的理论空间,这可能是在他所说的“非功利性之后”②〔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第51页。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这也成为了我们反思的起点。
对身体美学进行过分地批判或放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误读的一面。建构音乐美学研究中的身体话语不应仅强调行为建构的重要性,从感性经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出发,还要在理论上准确定位身体参与的普遍性及与精神建构的关系。如果把所有的音乐审美实践都一味地归结为“审美参与”,同样无法揭示审美经验的丰富性,进而掩盖其应有的超越性内涵。从音乐审美实践的整体观察,有些活动类型侧重于行为建构,而另一些侧重于精神建构。审美的呈现方式与音乐体裁、审美情境有着直接关系,审美主体可以在“行为—意识”之间依活动类型的不同来进行调节。就如舒斯特曼所言,形式可以在更为直接和狂热的身体投入中发现,同时也能够通过有理智的保持距离而发现。③〔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第71—72页。
从上文所述的一些现象可以看出,那些建构在身体“直接参与”之上的音乐审美活动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从音乐体裁上看,这些音乐大多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从人与音乐所建立的“主动关系”来说,在这类审美活动中往往没有明确的艺术分工,音乐的建构者同时也是享有者,他们在创造中拥有着音乐本身。
在以“被动关系”为基础的音乐厅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以“隐蔽参与”的方式进行欣赏。然而应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含有“冲突性”关系的审美类型中,精神建构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尤其在欣赏那些技术复杂且蕴含强烈情感内涵的音乐作品时,精神的超越性内涵将更加突出。从这点来说,“静观美学”又有着局部的合理性。
国内的身体美学研究几乎是作为“心灵美学”的对立面而出现,这种理论取向是有偏差的。事实上在舒斯特曼那里,身体美学不仅不与传统美学对立,而且要以传统美学为基础。舒斯特曼指出:“身体美学很明确地拒绝把身体外化为一种与精神割裂开的物体,拒绝将身体与人类体验的活跃的精神相分离”④〔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6页。。他进一步说到:“我事实上是把身体美学视为对传统美学的一个拓展而不是解构。”“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些观念不能被接受,但并不是放弃美学全部的传统和结构。”⑤〔美〕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学术月刊》2007年8月,第23页。从发展的眼光看,身体美学对传统美学所实施的是一种“改良运动”,它在理论上的建构性要远大于解构性。
综上而言,“审美参与”在音乐审美经验中具有普遍性,同时还应看到“审美参与”在不同类型的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样态,以及它背后所隐含着的身体美学与“心灵美学”的关系问题。在任何类型的音乐审美活动中,身体建构与精神建构都是并存的,合二为一的,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身体,而忽视精神,当然更不应该剔除感官感性在音乐审美经验中的现实存在。从主体审美能力的角度分析,在行为与意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主体会以审美实践的具体形态为前提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目的性”的感性定位,这是人类感性智慧的重要表现形式。
结语
随着“身体转向”的深入,作为中国美学主流形态的实践美学也表现出批判地吸收的理论态势,研究者不断对马克思著作中隐而未彰的身体理论进行开掘,欲拓展出实践美学的身体之维。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来改造身体美学,为其进一步提升理论品质提供了哲学前提,在理论上既可高扬人类审美经验的超越性,也保证了审美经验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就如当代实践美学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实践的这种“具身性”,保证了实践的现实性。①张玉能:《实践转向与身体美学》,《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88页。
我们应充分重视实践美学研究中的这一理论动向,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坐标,可以成为进一步阐释音乐身体美学相关问题的思想基础。人类声音实践的历史积淀不仅生成了“音乐的耳朵”,也生成了具有音乐性的身体。身体感性是人类音乐审美经验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身体图示”的合规律性是实现情感与形式相融合的基础。在人与动物“连续性”这一视线上,总是存在着生物性与社会性、本源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应该认识到,身体快感不仅不与审美的超越性对立,而且始终彰显出培育人类高级情感能力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