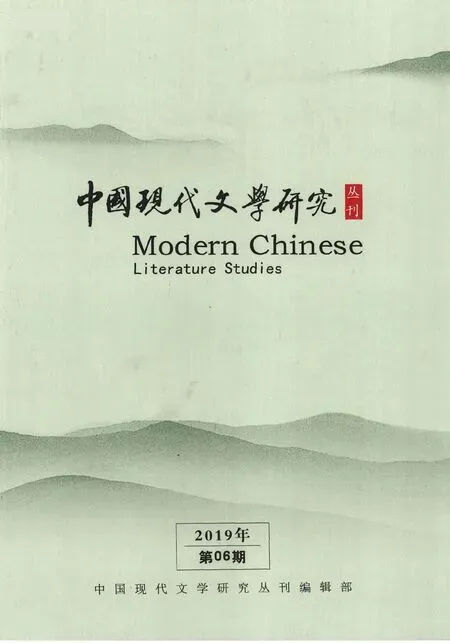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
李 玮
内容提要: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新文学在革命的挤压下发生意义危机。不同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鲁迅在南/北的政治空间之外打开了文学时空。他强调新文学的边缘性特征,破坏新文学的专业化边界,重建否定性的虚无文学主体,赋予新文学以文学内部的革命性。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努力,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样的选择。
引 言
近年来,鲁迅研究努力突破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框架,重新审视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这一努力的显在表现即是:有别于启蒙范式凸显“五四”前后的鲁迅,革命范式着重谈论1930年代的鲁迅,许多鲁迅研究者开始重视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在反思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历史关系的问题链中,鲁迅在遭遇国民革命的挑战时所呈现的复杂和矛盾的面貌,成为推进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的重要资源。
不同于前人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讨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问题,本文更关注文学如何切入政治的问题。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革命给新文学带来意义危机,面对对于新文学参与“复辟”的质疑,鲁迅既反对胡适等人继续文学建设的观点,也没有直接参与革命,而是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对“文学”和“革命”进行双重反思,由此,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表现出有别于“五四”时期和“南下”之后的独特性。区别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他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打开了不同于南/北政治空间的文学空间。通过推动新文学从“中心”走到“边缘”,从“纯化”转为“杂化”,从“本质化主体”转换为否定性的“虚无主体”,鲁迅赋予新文学在政治革命之外的革命性,“再造”了新文学的意义和传统。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历史线索,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提供了既区隔政治革命又面向政治革命的另一种选择。
一 南/北之间新文学的意义危机与“再造新文学”
1925年9月,胡适到武汉大学重申“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批判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复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争呈现的已非文言或白话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文学”如何“革命”或“复辟”的问题。
此次演讲,胡适仍然在文学内部中谈论文言、白话孰优孰劣。针对章士钊“青年从《尝试集》学习诗歌律令”的讽刺,胡适强调建设新文学需要“努力,修养”,以及“深刻的观察,深刻的经验,高尚的见解”。显然,胡适执着于新文学在“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并期待进一步的文学建设。他选择“南下”发表这次演讲,有意争取“军阀势力”以外的支持。不过,令胡适始料未及的是,南方的革命青年在反对章士钊的同时,也把胡适和章士钊视为同党,将《尝试集》与“复辟”等同起来,认为他“替章士钊出死力”,“此次恐怕不是来讲学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运动复辟的……我想你不久又或有个《尝试集》出版了”。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适在善后会议、女师大学潮中的一系列表现让青年感到“失望”。但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1924年后,南北政治矛盾激化,军阀政治凋敝,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南北和谈破裂,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酝酿北伐。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势力之间,政治摩擦频现。如蔡元培描述说:“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人的神经,又与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下,学生运动、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动员的对立面,政府巩固统治,推行保守政治。在南/北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无法回避“如何政治”的问题。新文学的价值被重估,包括文言、白话之争在内的文学问题都被转换为“革命”还是“复辟”的政治问题。
章士钊此时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与他“打压学生运动”,“整饬学风”,“崇尚读经”,“恢复旧德”一脉相承,“含有政治的目的”。对于章士钊的“复古”,鲁迅的反应与胡适不同。对章士钊引发的文言白话之争,鲁迅不以为然,认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他并不认为民国十四年章士钊的一系列文化方针仅是文化层面“开倒车”,而是将之与民国四年的“复辟”相联系,在政治层面加以理解,“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想来总要取其一端……”
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对新文学的审度同样来自政治上的考虑。早在1923年,有着中共背景的《中国青年》(上海)就开始批判新文学“纯文学化”和“精英化”的倾向,呼唤打破专业壁垒,向社会政治敞开。恽代英让作家“从空想的楼阁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邓中夏要求“新诗人应该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以“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表达对新文学的质疑。到了1925年前后,对新文学的质疑转化为“否定”。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文学家有什么用?”的问题被提出,“文学”整体的功能也被质疑。。曾经新文学队伍中的主要成员相继自我否定或被否定。茅盾在1925年表示“在这里,实际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艺观”。郁达夫被质问“可不可以把这些银灰色的附属物一刀斩断了呢?”更有对文学革命“革命性”整体的否定,在上海的刊物上有文章认为:“文学革命只不过革了一个形式,思想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其中,胡适首当其冲受到批判,“曾作文学革命先锋的胡适之……引起述古的倒流”。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反驳章士钊,重申“新文学意义”,已经不合时宜。他在“文学”内部谈论文学问题的方式,他对南北问题的回避,让他的新文学在1925年前后的南北之间进退失据。一方面,胡适慷慨激昂地反驳,“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他与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英美派”(包括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相互呼应,推进新文学建设,强调“文学”的“纯洁”和“高尚”。另一方面,胡适捍卫“纯文学”,因其精英化、保守性,被认为是参与“复辟”,维护“当局”。
在“建设”和“否定”之间,鲁迅开始“再造”。正是1925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分道”。鲁迅有意针对“艺术之宫”的建造,批判胡适等强调“文学性”的论点,并将之与保守政治联系起来。由此,鲁迅开始反思新文学的问题。当胡适执着于新文学的继续推进和巩固时,鲁迅“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呼唤“崭新的文场”“真的新文艺”。他有意破坏新文学的建设,推进“新文坛”分裂,推动新文学回到社会边缘,重新召唤文学青年,重提“思想革命”,推动文学向“政治”敞开。
鲁迅在1925年前后对“文学”的“处置”,改变了他在文学革命发生后强调积累和创作的姿态。如在1920年前后《新青年》分裂时,鲁迅虽然认为“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但仍期待“积累”和“建设”,希望“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1923年鲁迅仍在新文学内部执着于文学的建设,认为“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但是到了1925年,鲁迅期待的是文学边界的破坏,希望“加多破坏论者”。他对青年只管创作表示失望,认为“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并“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1925年前后政治风潮对鲁迅文学观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鲁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在南/北的政治结构中否定文学革命。针对“文学家有什么用”的提问,鲁迅一方面表示对“所谓的文学家”的否定,指出“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可以“感动别人,启发后人”。鲁迅既破坏又捍卫“文学”,探讨新文学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第三样”的可能,这使鲁迅既不同于1925年的胡适,也不同于南北的政治双方。在应对南北政治的同时,鲁迅通过“再造”新文学的时空,试图建构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文学主体。
二 退回边缘:重建新文学的空间
怎样构建“崭新的文场”?鲁迅首先通过空间上退回边缘来实现。梁实秋曾经描述1925年前后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鲁迅否定了这一说法。不过,1925年前后“新文坛”的“分裂”显而易见,而鲁迅的作用极为关键。“分裂”的开端是1924年10月《晨报副镌》编辑的更换。此事与南北之争密切相关,“因为《晨报》后台老板研究系人物,虽可在北洋军阀面前大谈科学与文艺,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们带来的政治主张和思潮,已使《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
政治影响的另一面,是文坛内部的“破坏”。鲁迅曾说,早在易主之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意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鲁迅口中的“留学生”是徐志摩,而“学者”指陈西滢。在鲁迅看来,文学观的分裂导致《晨报》易主。徐志摩的确在《晨报》上发表有关“法郎士”(Anatole France,引者注)的文章,在文中强调以此种“艺术的天才”,解决新文学“粗糙”的问题。鲁迅对此种文学态度甚为不满。鲁迅以《我的失恋》讽刺徐志摩的创作,此事成为《晨报》孙伏园辞职的导火索。既知徐志摩等与《晨报》的私交,又知孙伏园已经位置不保,却还出言讽刺,鲁迅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促成分裂。并且,《晨报》本来是鲁迅发表文章最主要的平台之一,甚至被当作周氏兄弟文坛成名的关键,此时鲁迅的行为更像是放弃越加保守的“主流文坛”。
不仅是放弃《晨报》,鲁迅对销量大、地位高的刊物均表示不满。远离《晨报》后,鲁迅推动《京报副刊》创刊,参与筹办《语丝》。但《京报副刊》和《语丝》销量大增后,也显出保守姿态。鲁迅认为“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对于《京报副刊》,鲁迅也说“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对孙伏园编辑作风的保守化表示反感。孙伏园接管《京报》后,虽然在用稿上不排斥最初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老人”,但对于“新人”的稿件也已渐渐不甚接受。鲁迅于是表示《京副》也开始摆架子。他转而与这两份刊物拉开距离。
与此同时,鲁迅更多地青睐文坛边缘的“小周刊”,并努力自办刊物,召集青年。他预设一个“浩大而灰色的军容”作为对立面,认为只有“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鲁迅以其对“大”的放弃和对“小”的选择,为“新文坛”设置了“新”与“旧”,“灰色”与“闪光”的“区隔”,以此重新构建以边缘、反抗为特征的文学空间。
于是便有了1925年鲁迅自办《莽原》等刊物的出现。鲁迅自办刊物,并非要形成新的势力和中心,相反,当1920年代中期老一辈作家批评青年创作位于“水平线下”时,鲁迅有意召集“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他说,“我总想自己办点刊物。只有老作家总是不够的,不让新作家起来,这怎么行”。相较于形成一个具有自足性、体系化的“文学场”,鲁迅办刊物更像是消解“文学场”。他放弃中心刊物,回避销量倍增的刊物,纠集“乳毛还未褪尽”和“水平线下”的边缘力量。
这个“边缘”是反抗“中心”的“边缘”。鲁迅期待“小周刊”以“起哄”和“撒泼”的姿态存在。“起哄”和“撒泼”与胡适提倡的“严肃的态度”恰好相反。如果说后者是对新文学经典秩序的认同,那么前者就是对该秩序的破坏。有学者指出“鲁迅提出的战法,也是他对青年发出的召唤,召唤一种打破‘隐隐然不可动摇’之常态结构的主体重建能力”。鲁迅不仅要求青年“撒泼”,也希望“导师们”也“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当然“起哄”和“撒泼”不仅仅是破坏新文学,它更意味着以“边缘性”生发文学、文化革新的活力,使文学能够“毫无忌惮”。
鲁迅通过退居边缘,为新文学创造了一个反抗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属于南方(革命阵地),也不属于北京(北洋政府)。它在“旧文坛”的边缘,既反抗新文学的精英化和纯粹化,也抵制着革命对新文学的“否定”。它在以“边缘性”表达来自文学内部的“否定性”力量。
三 破坏边界:重提“思想革命”
在空间上推动新文学退居边缘的同时,1925年前后鲁迅一方面阻碍胡适等人对于新文学专业化进程的推动,破坏新文学的线性发展;另一方面重提“思想革命”,打破“文学”的专业化边界,推动新文学的“杂化”。
针对胡适和陈西滢所提出的“高尚”“纯正”的文学标准,鲁迅偏偏呈现“不纯洁”“功利性”的创作过程,说自己的创作“挤”出来的。胡适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认为“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他鼓励学生以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建设振兴民族。作为呼应,陶孟和提出了“救国的文学家”的说法。鲁迅将这些观点联系起来,认为过于专业的发展,将制约精神的能动性。他说青年从“艺术之宫”“研究室”中出来后,“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
当文学的专业化进程转化为前辈、后辈的代际转换时,对青年创作“不成熟”的批评是新文学建设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如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就刊登了江绍原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编辑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份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也刊出文章应和。鲁迅则以自己的创作为青年辩护:“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
破坏新文学的“文学性”和“专业化”,是为了恢复新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的“功能性”。鲁迅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诸如“进入艺术之宫”等问题,归结为“中了‘老法子’的计”。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说过的‘思想革命’”。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此时强调“思想革命”是延续启蒙道路,这种理解成就了“启蒙鲁迅”的连续性。不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新青年》上的“思想革命”是在谈论新文学的革命路径时被提出的。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对文学革命做进一步说明:“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傅斯年进而推陈,“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而论”,“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转变”。
并不能说,新文学发生的最初动力就是“思想革命”,也不能说鲁迅重提“思想革命”仅仅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但显然,重提“思想革命”为“文学”走出“艺术之宫”提供了路径。相较于“文学性”,鲁迅强调“思想性”是为了模糊新文学的边界,以“新思想”重新恢复新文学与“新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当“文学革命”止步于白话和文言机械的语言分野时,鲁迅以“思想革命”重启“文学”更新的脚步。
鲁迅在“文学的标准”之外重提“思想的标准”,推动了新文学的“杂化”。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重提“思想革命”让鲁迅在文体上产生了“杂文的自觉”。“杂文”的“文学”身份得不到承认,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虽然鲁迅也知道“杂文”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原因便是对于“文学性”的反抗,对“思想”的重视。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并对自己的文学选择进行了修辞化的描写:“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邱焕星曾分析“重启思想革命”促成鲁迅的“热骂”,由此促成审美转换,增加文学的批判性。从雅正的文学走向热骂的文学,鲁迅将“思想”的标准和指向重新引入文学,由此打破新文学的“文学性”中心论,由此沟通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
四 重回“革命之前”:创造虚无文学主体
“思想革命”只是鲁迅敞开“文学”的路径之一,“从新做过”并不是重回《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它不仅指向对新文学的反思,而且指向对“革命之后”的反思,并由此避免直接进入“革命文学”。在鲁迅提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的同时,他表达了对于“轮回把戏”的恐惧,其中便是有“革命的轮回”,“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当“革命”的主体是另一种本质化的“思想”或“文学”时,“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只能再次中“老法子”的计,陷入革命—革革命无限的循环。《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走向“文学复辟”,“启蒙”走向“规训”,便是此种“革命”的必然后果。
应该注意到,1924年到1926年鲁迅文本中文学主体,较之1917年到1924年文本中的文学主体,有了很大不同。在《故乡》(1921年创作)、《阿Q正传》(1921—1922年创作)等小说中,“我”洋溢着启蒙主体的自信,并以此审度他人的“失败”,如《故乡》中的“我”定义了“闰土”“杨二嫂”的“悲剧”,并预设了“悲剧”克服之“路”。启蒙主体有着政治行动的力量,它/他以对启蒙对象的遮蔽、“代言”和“规训”为特征。国民革命前期的“我”缺少主体自信,充满了否定性,特别是自我否定。“失败”和“孤独”是该时期主体的特征,小说《孤独者》(1925年创作)中“我”只能反观另一个“我”——“魏连殳”,经历和否定他“失败了的胜利”,从直面他的“死亡”中“出走”;《伤逝》(1925年创作)中的“我”(涓生)在亲手扼杀了另一个“我”(作为涓生镜像的子君)后,从她的“死亡”中“出走”……
这种主体模式于《野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主体的它/他经历了自我否定后,抛却了线性历史,放弃了明确阵营,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无地”和“虚空”。“我”以“野草”自比,“野草”既是“我”,也是“文学”。“野草”以及《野草》集中许多文学主体意象存在于本质化时空之间: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空间上的“明”与“暗”,甚至本体层面的“生”与“死”之间。它/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线性时间(从过去到未来),只能凭依“过去”确立自己的时间。虽然“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朽腐”,但“我”对这“死亡”和“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它/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属于“地狱”,也不属于“黄金世界”,“彷徨于无地”。在时间上的虚空“死亡”,在空间上的虚空“无地”,正是“再造新文学”时间上逆转,空间上退避的“内面”。
正如鲁迅描述他这段时期的创作,他一方面“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另一方面“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在国民革命前的“文学”和“政治”之间,鲁迅说:“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再造新文学”的主体既非“回到文学”,也非“政治超越”,而是左右批判、否定,甚至自我解构,反本质化的“无所有”(“无时”“无地”)。木山英雄关注到鲁迅1926年8月之前两年间,即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创作,包括《野草》《孤独者》等创作,以及“杂文的自觉”,他也指出该时期鲁迅文本中的“自我”“无论向左向右都无以迈出步子,无论何物最后均无法自己完成”。但恰恰是这种无所归依的“无”,表达着强烈的左右批判的否定性,或者说革命性。
鲁迅在国民革命前期创造的“无所有”,与竹内好分析“革命之前”的鲁迅的“无”相互呼应,表达着一种面向政治又不同于政治的“革命性”。1925年前后鲁迅的确在重新编织辛亥革命之前的“回忆”或“青春”,沟通起所有“革命之前”(辛亥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由此积蓄起“革命”的动能。在他的文本中频频出现对辛亥革命前的“杂忆”。一是辛亥革命之前所写的文章,“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二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心理演化为新的“文学梦”。鲁迅感慨“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辛亥革命前盛行的“复仇”心理在国民革命前被转化为文学意象,便有了《复仇一》《复仇二》。在《希望》一文中,他将“复仇”等革命心理转化为“虚妄”中寻求的“逝去的”“青春”,作为重启革命性。
将“文学”的时间反拨到“革命之前”,以“虚无性”表达“否定性”,这使得鲁迅再造了一种既“革命”又拒绝“革命”的新文学。它既否定了胡适积累建设的文学发展道路,也否定了“文学”奔向新的本质论的发展道路。它将“文学”嵌入无法成为“完成式”时间中,“文学”由此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只能在不断地“功能化”中确立自身。
五 “转向”之外的“徘徊”——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再造新文学”
“再造新文学”是针对国民革命前期“文学如何革命”的问题而产生的。“再造新文学”既不满意于新文学对政治“回避”,也没有直接“转向”。它的时空不属于“南”,也不属于“北”,而是在南/北之间的“边缘”地带;既不在革命时间之外,也不在革命时间之内,而是在“革命之前”。它在“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向历史”中创造了一个“徘徊”的“时空”,以“边缘化”“芜杂化”和“虚无性”成就“文学”既“反对复辟”又“超越革命”、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位置。
在国民革命前期,“徘徊”并不是普遍的选择,甚至并不能成就连续性的历史。当国民革命带来对新文学政治功能的重估时,放弃“文学性”,拥抱“革命性”成为许多作家的选择,新文学的骨干如文研会、创造社的重要成员纷纷向革命“转向”。曾经强调“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执着于新文学“建设”的胡适也被“革命”纠正。1926年到了苏联的胡适表达了对革命运动的景仰。胡适开始对“文学革命”进行自我否定,反问“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由是,他否定了新文学和整个的“新文坛”,他说“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于是,胡适“好久不谈文艺了”。
鲁迅也面临“转向”的压力。首先,青年更多地奔向更为实际的国民革命,“再造新文学”难成气候。《莽原》的问题不仅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而且“现在则并小说也少”。鲁迅认为“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所以不做文章了”。《莽原》原有的主要作家先后“南下”,韦素园去国民军第二军任翻译,向培良去武汉任《革命军日报》编辑,尚钺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莽原》,各种期刊“哪怕是处在敌对地位的,材料都异常枯窘”,因为“到实际运动起来的时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无暇做起了”。
其次,边缘性、反抗性的“再造新文学”面临“革命”的“收编”。《国民新报》,作为国民党在北京的机关刊物,就联络鲁迅。受到邵元冲之约,鲁迅常有稿寄去,还介绍了韦素园前去编副刊。当韦素园去国民革命军工作后,1925年12月2日,鲁迅去往《国民新报》报馆,即日起与张定璜同任乙刊编辑。革命的《国民新报》在北京形成新的势力,鲁迅也进入革命文坛中心,被作为当之无愧的新的“权威”,或“头领”。
再次,革命改变社会的直接效果也影响着鲁迅的选择。在他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不仅与国共两党有了直接的交集,而且开始将实际的军事斗争置于“文学”之上。在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他开始借孙中山的逝世发表看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这是因为他“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认为“现在的强弱之分”,“在有无枪炮”,“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
似乎一切都在“革命”的席卷下不可避免地“转向”。“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成为连续性的历史。国民革命改写了“文学革命”的意义,连胡适都开始以“文学革命”成就“国民革命”说明新文学的价值。不可否认,鲁迅自己也被“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历史”的裹挟,参与线性历史的行列。北伐起兵后,鲁迅在谈话中表示对“光明的将来”的确信,“有存在,便有希望”,“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由此摆脱了徘徊、寂寞和绝望的状态。1926年6月17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表示,“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此后我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走向“乐观”“热闹”,鲁迅由此“南下”,完成了“转向”的历史。
不过,在连续性历史的缝隙中,我们仍应该注意“转向”之外的“徘徊”——国民革命之前鲁迅对“新文学中心”的放弃和对进入“革命文学”的犹疑。在“徘徊”的过程中,鲁迅再造了以“边缘性”和“芜杂性”为特征的新文学,以“虚无”和“绝望”为时空的“新文学主体”,在南/北之间,在“纯文学”和“革命”之间所创造的“第三样”可能。“再造新文学”并不能如“革命文学”那样产生“内圣外王”的“革命主体”,促成“有结果”的“革命”。相反,它以非南非北的“空间”区隔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队,以“徘徊”在“革命之前”逃离历史目的论的时间掌控。当只有进入“历史”才被认为是“成功”时,“文学史”被反复重写而陷入循环后,鲁迅在国民革命之前的新文学“再造”,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循环之外提供第三种选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