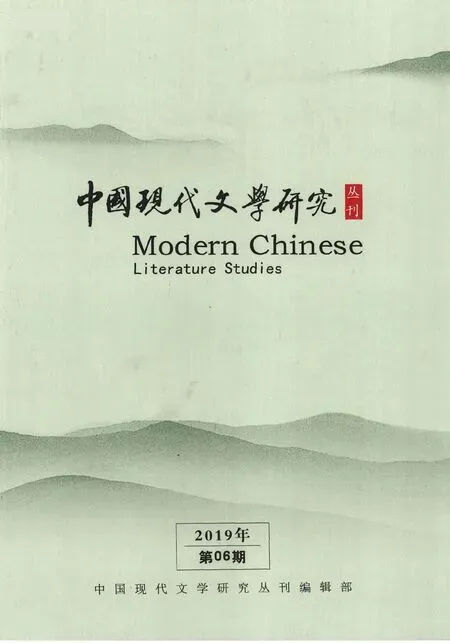从边缘中生出知识和美①
——重评王小波及其写作
刘月悦
内容提要:王小波写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边缘”和“脱序”,一直以来对王小波的解读,诸如自由主义英雄、草根偶像等,都是对其“边缘”立场的生发和误读,但误读本身也证明了“边缘”写作的丰富性。王小波在权力延伸的最微末的“边缘”处进行写作,使其作品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品格和多维度的解读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王小波的写作在当时表征着文学生产机制的裂隙、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在当下,“边缘”写作则提供了文学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可能路径。
有论者指出,近年来的王小波研究落入了两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一种倾向于建构性的“自由”,另一种倾向于解构性的“虚无”。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小波是一个悖论式的人物,他以边缘身份自处,却从边缘处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中心,他以小说家自居,却更多地被理解为思想家。因此,以任何一种绝对化的理论来框定王小波,本身都是对其悖论性的消解。
笔者试图以“边缘”立论,考察王小波的特异与悖论。边缘,既指王小波“文坛外高手”的身份,也指福柯权力理论中权力运行的边缘地带。由此出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各色各样的权力如何牵引着王小波从“边缘”走进“中心”?他的作品又如何在二者的张力间自处?在经历了诸多正误和偏差之后,我们今天如何回归“边缘”,从文学的角度重新理解王小波写作的意义?
一“边缘”与“英雄”
众所周知,王小波引起成规模的关注是从他的早逝开始的。在所有关于王小波的纪念和研究当中,最常被提及的是他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建构和存在方式。王小波之死引起的祭奠如此之盛大,与其说是对拥有的褒扬和歌颂,不如说是对匮乏的叹息和愤怒。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和“自由”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发生了微妙的转义和置换,原本简单地指称作者与文学体制之间松散联系的“自由”,结合他从人民大学教师的岗位辞职、长时间未被文坛发现和接纳的经历,引申出脱离体制、栖身于文坛之外的“自由”形象,而后又与他作品中呈现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互为注解,最终勾画出一个孑然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英雄王小波。
事实上,这里说“自由”,毋宁说“边缘”。王小波的“边缘”,本来是他处在权力运行的末端,并始终不曾深入到权力运动之中,王小波的“自由思想”正是根植于此,在他的小说中多有对“边缘”的思考和表达。
艾晓明在《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中指认“‘我’与 X 海鹰是革命时期那种虚构的有害的性意识的牺牲品”,认为王小波将“性”这件本来最形而下、最不需要理智的事,当作在那个“狂信”的、“不理智”的时代的争取精神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载体。但事实是,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大多数并没有处在权力所打压的中心。以《黄金时代》为例,“王二”和“陈清扬”,一个“除了上山放牧和在家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另一个是住在山上、众所周知的“破鞋”。从小说一开始,他们都是“边缘人”,而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而言,从生产队逃跑过、偷越国国境、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陈、王二人所受到的惩罚,可说是不可思议地轻了,仅仅写了交代材料,经历了几场并不太严酷的批斗会。与王小波之前、之后的同主题作品相比,《黄金时代》都显得太不激烈。若是要直陈暴力对人性的压抑,自然应当树立更为激烈、残酷的矛盾冲突,越紧张越好,王小波没有这样处理,正说明了他并无挺身抗暴之意。另一个佐证是,《黄金时代》里的性爱描写常常充满诗意,比如:“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裙筒,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有一只老水牛在一边看。后来他哞了一声跑开了,只剩我们两人。过了很长时间,天渐渐亮了。雾从天顶消散。陈清扬的身体沾了露水,闪起光来”。与其说是反抗,倒不如说,王小波将性爱之美和自然之美结合在一起,让两个“边缘人”更加边缘化,边缘到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地步,从而远远地超脱在斗争年代之外,把原本处在中心的,放置到边缘,而将被排斥到边缘的,放置于中心,在中心与边缘的倒转中,满纸的“伟大友谊”和“出斗争差”如此地蓬勃和鲜活,而政治的严肃和道貌岸然则成为缥缈的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集体的受难记忆和共同想象不同,王小波笔下的感官如此盛大,在强大魅力的照耀之下,“文革”的苦难似乎也被消解了。港版《黄金时代》出版时题为《王二风流史》,虽然以博人眼球为主要目的,却也道出了点“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况味。
《我有阴阳两界》在身体书写上既与前作一脉相承又别具一格。“阳痿”的“小神经”王二仍然是一个“边缘”人物,他与前妻离婚,别人把他当太监看待,他因此住进了阴暗封闭的地下室,沉默寡言,离群索居,这是他的“阴界”。后来他遇到了性格阳光的小孙,小孙治愈了他的“阳痿”跟他结婚,别人不再以异样的目光看他,于是他重返楼上的“阳界”。可这个“阳界”似乎并不让他感到欢喜,他不再能够享受“阳痿”和“小神经”的特权,必须应付阳界的一切事物,躲避开会,躲避工作,还得毕恭毕敬地应付小孙,给小孙“洗裤衩”,阳界的一地鸡毛禁锢了他,他的精神世界失去了自由,仿佛倒成了“阴界”。“病态”和“正常”,“阴界”和“阳界”,正是“边缘”和“中心”,这在小说中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不断地流动和转化,身体的困扰和精神的困扰在这里延异,互为表征。因此,戴锦华将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爱故事视作“历史的‘精神分析’或权力机制的‘精神分析’”,将之视为“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
然而,在“自由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王小波的“边缘”性被削弱,而战斗性被不断地夸大了。“边缘”在关于“自由”的转义之中变成了“中心”——在权力的中心被权力所压迫,于是王小波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抵抗权力的战斗者形象。他的作品也被反复解读,提取其中的“反抗”意象。1998年 5月,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大部分作者属于文学界以外的人文知识分子。与论者的身份相一致,书中对王小波的思想评价远多于文学评价。知识分子们在惺惺相惜地悼念的同时,也流露出对社会、历史的沉痛和不满。在这本书和由它引起的解读和评论的中,王小波的“自由”被有意无意地转义为抵抗革命暴力,并被放置在“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的自由知识分子序列当中。而这一序列背后隐藏的逻辑,则是自由主义英雄的追封和加冕。
朱学勤的论述直截了当:“1998年言说王小波,不在于他作品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我看不出他已经到了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步),而在于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大陆以外读者的阅读反馈也能佐证他作品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远甚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梁文道曾在访谈中说道:“当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们应该是那时最‘红’的了。由于环境不同的关系,让我跟内地许多同代的同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王小波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王小波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我总觉得自己小时候就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所以他的启蒙作用还要看是在什么环境。”
知识界对王小波反抗者和文化英雄的形象的塑造和“误读”,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论述颇多,如黄集伟的《从暧昧到狂欢——小波流传史》就将王毅的另一重身份——国林风书店策划人纳入考量,推演由他一手策划的这场人文知识分子集体悼念王小波的文化事件背后的商业操作意味,指出“那些未竟稿、写真集中的王小波早已不再是那个怀有纯美文学梦想的王小波。在纸质恶劣、编排随意的写真集中,王依旧傻憨憨地笑着,可那笑容已被改造为货真价实的商业秀”。而笔者想要指出的是,王小波超出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脱序,也就是他的边缘性。这种“脱序”是多维度的,他脱离的不仅仅是秩序和体制本身,也脱离了暴力与反抗的二元对立,洞察到反抗也是暴力的组成部分的王小波,也脱离了反抗本身。他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不是伤痕文学主将们的清算和批判,也不是后来的新历史主义作家们常用的以个体的小叙事来抵抗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身在其中又不被裹挟的清醒者的智慧和审视。与此同时,他也脱离了精英的启蒙欲望,他既不以精英自居,也未曾将启蒙当作己任,“王二”这个普通不过又带着市井痞气的“代号”最能体现他“沉默的大多数”的自我定位。他常常讽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想要匡扶正义、哀叹人心不古的“中古遗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反对以任何形式向人们灌输哲学(《思维的乐趣》)。他所强调的自由,是思维的自由,他所崇尚的“人文精神”和“精神家园”不是启蒙式的冠冕堂皇和正襟危坐,而是独立思考得来的思维的乐趣、智慧的乐趣(《思维的乐趣》),是创造美好事物时的体验。正是这种多维度的脱序,保证了他的边缘性,保证了他能够从微观的角度观察权力的运行,保证了他对暴力的清醒,从而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而一旦赋予他反抗者的形象,他就脱离了边缘的位置,也就脱离了他的自由产生的根基。
张颐武曾经谈到他和王小波的一次交往:“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这微笑里有一种对人们的幼稚的超然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以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我们是他的一面镜子,帮助他看透自己,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他看透我们自己。”知人论世,张颐武所描述的王小波超然但并不高高在上,智慧但并不自以为是。将王小波塑造成斗士和英雄,以特定的意识形态解读、框定王小波,与王小波的自由思想格格不入地赋予了他特定的价值观和固定的形象,正是另一种话语强权,他们所赋予王小波的“自由思想”,无非是权力实践和弥散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以“自由”来标榜王小波,却让他进入到权力话语的逻辑、商业的逻辑之中而丧失了自由。
二 “边缘”与草根
2002年的“五周年祭”是“王小波热”的又一高潮。这次充当排头兵的是在王小波刚刚去世时态度暧昧的媒体。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两家刊物均在2002年4月用大幅版面推出纪念专号。这一轮的“王小波热”与之前不同之处在于,1997年的王小波祭将“边缘”解读为“反抗”,而这一次,“边缘”则被解读为“草根”。
《三联生活周刊》以“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为题,登载《一个自由分子》《增熵时代的自由分子》《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等八篇文章。《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这一专题不单纪念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更是推出了他的一系列“自由分子”继承人。“知识”二字的剔除,凸显的是文化上的去精英化和对启蒙主义的告别。所以,在这期策划中,出现了貌似不和谐的两种观点,一面是连岳、李红旗等人讲述的王小波对自己的影响,心甘情愿地以王小波的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则是陈嘉映、盛宏、邓正来等人在《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中“不要把王小波评价得过高”,“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等欲将王小波请下神坛的言论。事实上,二者背后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就是社会话语权力的转变和“草根”的崛起。
时间从王小波逝世的1997年进入了新世纪,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启蒙神话宣告破灭,网络普及带来的轰轰烈烈的草根时代正在来临,掌握权力话语的,正在从知识分子,转变为“草根”民众。对英雄王小波的祛魅正是对自由主义的复魅,更为亲民、普通的知识分子而非文化英雄的王小波,更符合“草根”时代的自由主义,这一自由主义与八九十年代的保守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又颇有区别。连岳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更多指向的只是不受约束、自在随性的生活状态,从保守自由主义更退一步,蜕化为某种中产阶级式的犬儒主义:“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
《南方周末》的专辑以“沉默与狂欢”为题。卷首的《沉默与狂欢》。一文最能体现刊物的意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文坛中的“名门正派”对王小波的态度归结为“多数人对王小波没有看法,因为‘不感兴趣’”。但一读之下不难发现,这篇以“忠实记录”为愿望的文章,其实主观色彩颇强,更不乏话语强权,不仅对“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王朔)这样话外音很明确的答复故作不解,连“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李洱)的评价也忽略不计,只因李洱同时认为“小波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创见,小说比随笔的成就更大”,至于其他的批评意见,更是不加解释地被划定为“基于误解的批评”。与此同时,用更大的篇幅记录网络青年们对王小波热情洋溢的崇拜“狂欢”和媒体批评的盛况,从而制造出与“沉默”的文坛的鲜明对比,并且将这种对比升级到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的层面:“狂欢的人群试图开启沉默的阴霾,然而众峰无言,各据一方,天际仍没有雷声滚过……”《南方周末》利用媒体的话语权在这里实施了一种“双向的暴力”,他们将“精英”暗示为“权力”,从而塑造出权力对“自由”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将王小波的“自由”解读为与“草根”的亲近,赋予“草根狂欢”以正义性。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在开篇文章中,选用“精英嘴脸”这样尖刻的词汇与“自由分子”形成对立。《三联生活周刊》与《南方周末》同属都市文化类刊物,他们的读者群是新兴的“小资”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这一正在中国城市中兴起的新阶层,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有强烈的发言欲望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发言,但却并不掌握话语权力。他们以“草根”自居,认为正是“精英”们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使他们成为主流话语权力的“边缘”人,于是他们选择了具有话语能力而被主流话语所忽视的王小波作为自己惺惺相惜的代言人。而1990年代关于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解读中被忽视的“有趣”和“思维自由”这时候重新浮出水面,为新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另外的解读空间:“在这个时代,做一个自由分子意味着社会地位提高,可以从质量生活中品尝滋味;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想点儿别的,反对‘无趣’。”从这一意义上讲,“草根”倒是比“文化英雄”更贴近王小波的“边缘”本质。
误读随即而来。在新一轮的想象与塑造中,在当时尚属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阵地的网络上,对王小波的追随和崇拜其势汹汹,不少人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称,表达对王小波的崇敬之情而又借王小波以自重。在将王小波的“边缘”划定为“草根”之后,他们以一种“向下拉平”的方式理解和重塑王小波,满足他们“不断地形塑一些具有文化义涵的流行符号如罗大佑、周星驰、王小波、卫慧等构造其消费主体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需求。王小波出现在这个名单中显得既突兀又理所当然,在启蒙陷入“绝境”的时代,他们将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理解为放荡不羁,将王小波的反讽与周星驰的恶搞相提并论,将王小波的调侃等同于玩世不恭,甚至在王二的身上,他们读到更多的只是性的压抑和狂想。他们仍然强调王小波对他们的“启蒙”,但却并不是精神上的启迪蒙昧,而是文字层面上亦步亦趋的模仿。在反对英雄主义,信奉草根逆袭的网络文化中,1990年代的王小波热中被遮蔽的“凡人”“王二”的一面被放大和解读,成为网络上王小波追随者们的自我表达和想象。
新世纪的王小波热已经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化消费无异。如果结合数年以后,占据网络文学半壁江山、最为火爆的网络文学类型“玄幻文”“小白文”中读者们如何将屌丝逆袭的心理需求代入到主角不断地修仙升级当中,应当更能理解看似光鲜体面实则步步为营的小资和中产们是怎样在阅读和追随王小波的过程中完成“一份强者的姿态,一份弱势的认同”的自我指认。
三 重新审视王小波:边缘写作的力量
王小波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他的作品无疑成了当代文学中不能忽视的经典,他本人更是大众文化的聚光灯笼罩下的super star,如今的王小波,已经从他曾栖身的边缘走进了中心,在文学体制之内,任何一本当代文学史,都不能忽略王小波;在文学体制之外,王小波也拥有大量的拥趸。但对于王小波而言,这些荣耀不但迟来,而且充满了吊诡的讽刺。张颐武在纪念王小波逝世十年的文章中就曾指出“他终于等到了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阴阳两界”此时成为一个绝妙的谶语——在阳间的王小波,身处不被人关注的“阴界”,却享有思想与写作的自在“阳界”,辞世后的王小波,他的肉体去到了阴间,但他的作品却走到了聚光灯下的“阳界”,而他的思想,却在种种误读中失去自由,犹如去到了“阴界”。王二故事里“边缘”和“中心”的倒转,如今真实地发生在了对王小波的解读当中。
那么,当我们抛去这些误读、神化,或者说是控制,回归到文学本身去考察王小波,他的写作对于当下文坛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笔者认为,王小波和他的文学写作令人惊异地以超强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年代被解读、被建构、被想象,这其中虽然不乏文学场外的媒介、资本、政治等力量的功绩,但从文学本身而言,“边缘”的丰富性正是王小波的价值所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知识背景的接受者,都能够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有所斩获,都能够在自己的视域内解读王小波的“边缘”,不管是正读还是误读,都足以证明其丰富。那些处在权力中心的文本,意义过于确定,不管是建构还是解构,都呈现出明晰的指向,而王小波的“边缘”书写,因为处在权力力量最微弱的末端,也因为王小波本人的超脱与智慧,而成为了“思维的乐园”,具备丰富解读的可能。
我们或许可以将王朔与王小波做一对比。王朔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最早的自由写作的作家,在王朔之前或者与他同期,大部分作家栖居在体制内部,属于一体化的文学生产体制的组成部分,受文学体制的规训和制约。而王朔自称“写作个体户”,他在文学体制之外开始写作,成了文坛的“边缘人”,他的写作较少受到文学体制的制约。但是,王朔虽然相对地置身于文学文学体制之外,却投入了商品经济市场的怀抱,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导向进行写作。而王小波不但是“文坛外高手”,也尽量远离了市场的影响,用“减熵”的方式写作,不屑于大众和流行。并且,王朔其实很快就进入了文学生产机制之内,而王小波直至去世,仍未得到主流文坛的注意和认可,以一个“备受文坛排挤”的“文坛受难者”形象离世。总之,王朔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消费和消费文化的引导制约,进入文学体制之后,则受到文学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影响,游走在二者之间。而王小波的写作,则是真正边缘的写作,文坛和市场都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也就意味着两个场域的力量对他的影响都很微弱,在这样的“飞地”进行书写,他的写作也因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如果我们将目光延伸到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传统,那么王小波的“边缘”不仅仅在于他不隶属于当代文坛,更在于他是一个不曾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另类。这或许也正是王小波生前未能进入主流文学批评家视野的原因。与王小波同时代的当代作家,多多少少都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王小波的写作非常意外地跳脱出了新文学的传统,即便“痞气”如王朔,仍然有着另类而暧昧的批判和启蒙的渴望。而王小波的写作有对性惊世骇俗的直白表现、有唐传奇一脉相承的志怪传奇、有奇崛雄伟的想象,但所有这些,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言,都是旁逸斜出的;新文学的关怀在于超越人性的局限,达到主体的解放,而王小波却怀疑这种理性改造,特别强调人的“感观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他也怀疑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情结,他的写作不试图劝导和改造任何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他的写作都没有办法纳入到新文学的谱系当中,也就无怪乎他生前并未被文坛所接纳。而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对王小波的定位通常是“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写作”“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写作”,实际上都是无法分类的分类,无一不指向其边缘性。
王小波所栖身的边缘,还照见了当时文坛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机制出现裂隙,作为文学生产的主体,作家的身份从一体化的组织管理变为多元栖身,他们不再是总体性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的“螺丝钉”,而是在庞大的、制度化运行的文学生产机器之外自立门户,悄悄地进行着文学生产。而在作家身份的改变背后,有着更为强大的逻辑,王小波所代表的“边缘”作家的存在,意味着文学叙述从国家行为转变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暗示着国家—社会—文坛—作者之间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再放大一点来说,他暗示着的是1990年代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转变,国家对个体控制的弱化,使得脱序和边缘成为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
福柯的权力理论告诉我们,边缘是更大的空间,在各种权力延展的最后之处,更能洞见权力的运行。王小波的“边缘”写作,因为其“边缘”立场,成就了对权力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具有超然的思考和智慧,从而具备了不断地被丰富解读的可能。他在远离权力处生发出尽可能脱离外在力量控制的智慧、知识与美,展示了作家个体如何真正地面向文学写作,提供了当代文学一种难能可贵的书写姿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