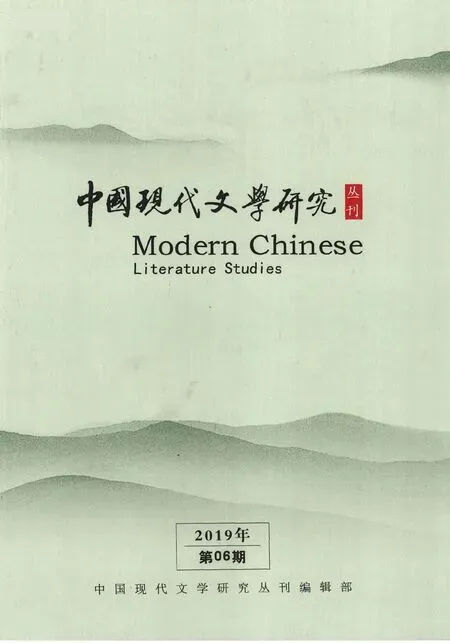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民族主义”索隐
王 侃
内容提要:1905年,林译长篇历史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出版。这部译著是为响应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的号召,它在多个修辞层面上呼应了晚清政治变革的巨浪中复杂的民族主义话语,用意曲折,颇多暗示。从思想、文体、译笔等方面,以特定的修辞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观念曲折地纳入译本,并曾给予周氏兄弟以所谓“暗示”。
一
190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长篇历史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该书原著是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原著题为Ivanhoe(《艾凡赫》)。
林译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自不待言。这以有人在1935年的论断为极致:“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大约是《茶花女遗事》之外最被人熟知的林译小说,并着实地影响了诸多杰出的现代中国作家。凌昌言在《司各特逝世百年祭》中如此称道林纾对司各特的译介:“……林琴南先生便用耳朵替代眼睛来发现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的‘《史记》笔法’;并且由于他的介绍,司各特便和嚣俄、仲马成为三个仅有的中国所熟悉的西洋作家。中国读者对于这位‘惠佛莱说部’的作者的认识和估价,竟超过莎士比亚而上之。……因此我们可以说,司各特是我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而他的介绍进来,其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司各特给予我们新的刺激,直接或间接地催促我们走向文学革命的路上去;司各特是直接或间接地奠定了我国欧化文学的基础了。”这番评价,几将林纾、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定义为近世中国文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
如此这般的评价颇多,不必一一罗列。不过,在诸多评说中,周作人的说法似乎别有深意,他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回忆说:“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这段话,除了进一步让人认识到林译小说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确存在的深刻影响之外,还应特别留意到的是周作人所说的“暗示”。周氏兄弟究竟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暗示的意味”,并因此使这部小说在他们那里“特别的被看重”?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问世后的一百余年间,各种研究、评说可谓纷纭,周作人的这段话也常被征引,而周氏兄弟所说的“暗示”却意外地几乎没有“特别的被看重”。
林译小说虽然被誉为“无一不寓革新国社,激劝世人之微意”,但若细究,《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才是对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之呼吁的正面、深切的响应。林纾对于“政治小说”或“译印政治小说”的呼吁有高度的认同,直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表面上看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从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历史小说’这个名词是晚清文人的发明,也是晚清众多次文类的一种,似乎颇受读者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和梁启超经由日本引进的新文类‘政治小说’有关”。因此,如果说周氏兄弟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看到了“暗示”,其一应是在“历史小说”的文体表象背后看到了“政治”。
司各特在英国文学史上就被认为是Historical Romance 这一文体向Historical Novel这一文体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尤其被认为是Historical Novel(历史小说)的始作俑者。Ivanhoe(《艾凡赫》)的副标题就是“A Romance”。Romance(罗曼司)有类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传奇”和“演义”。李欧梵认为,“如果用英文来翻译‘演义’这个文类,较有对等意义的是Historical Romance”。可以这么说,《艾凡赫》是一部基于历史故事的传奇性演义,最多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历史小说,即把历史小说化,在其中增进虚构和通俗的成分。林纾的合作者魏易不可能不懂得Romance的文体含义,但在拟定中文书名时他们仍然弃用“传奇”“演义”一类的文体标识,而使用了“略”。略者,行略、传略的简称,是传记文体之一种。正是这一有意的误用,才能看出林纾将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与太史公、班固、《汉书》《史记》相提并论的曲折用意。林纾的这一比附,不仅仅如郑振铎所说的“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自他以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或者如林纾弟子朱羲胄所说的“自先生称司各德迭更司之文,不下于太史公,然后乃知西方之有文学,由是而曩之鄙视稗官小说为小道者,及此乃亦自破其谬囿,属文之士,渐乃敢以小说家自命”,实际上,至少就《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而言,林纾的这一比附是试图有意地屏蔽它作为Romance的传奇特性(尽管这并不容易做到),有意地引导读者不先入为主地将其视为“演义”,视其为一种发端于“野史”“稗说”的想象性叙事,从而悄然将其坐实为“史传”,默许为“有正史可稽”的历史叙事。因为,“政治小说”虽为小说,但就“政治”的某种刚性要求而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样的政治小说,如果“不自诩为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叙事还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需要一种暗示性的隐微修辞,来混淆“正史”与“戏史”之间的界线。林纾的这一坐实或默许,很明显,便旨在突出地强调《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作为政治小说的某种“刚性”,从而使读者留意这一“刚性”,进而避免仅将其作为英雄美人式的通俗、香艳、奇情小说的消费性阅读——如前所说,尽管这并不容易做到。
二
梁启超昌明“政治小说”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降临之际。其用途、其目的在于“强启民智”,新一国之民,从而配合由康、梁维新派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保皇立宪),以达成“保国”“保种”,甚至“保教”之最终结果。林纾服膺于康、梁,自谓“叫旦之鸡”(《不如归·序》),效誓致力启蒙,视译书为“爱国保种之一助”(《黑奴吁天录·跋》),且高度赞同康、梁所倡之“立宪之政体”(《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即使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共和政体欲现之际,他仍然于忧戚深重的“不眠”中题诗“景皇志事终难就,可亦回思戊戌曾?”以缅挽早已宣告失败的改良主义运动。
时至晚清,如何于大变局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朝野上下、仁人志士就此作出的思谋和举措,掀动了史无前例的壮阔的民族主义浪潮。如列文森所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列文森所说的,是一个价值的空间层次不断递减、不断缩略的过程,是一个将价值关怀从虚缈的抽象概念里不断撤回抽出、最终聚焦于国家、民族、种族等实体概念的过程。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下,在丧权辱国的经年忧愤里,在如今所谓的现代性焦虑中,“民族主义”是各路人士在图谋“保国保种”时的根本性的话语架构,是当时一切政治实践的宰制性的驱动力,是当时所有政治派别共同的核心价值面向。梁启超有言,“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脑中”,“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换言之,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当时可资进行政治动员、救亡图存的最高和最终的依恃。
然而,晚清不同的政治派别在对“民族主义”的理解、阐释和认同中发生了对峙性的分歧。同样是为了“保国保种”,革命党人则强调“排满归汉”的前提,攘外必先安内,视“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孙中山于1903年组成“中华革命军”时,也将“驱除鞑虏”视为“恢复中华”的先决条件,他是年在檀香山所作《敬告同乡书》中称“革命者志在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赫然在“革命者”和“保皇者”之间划下鸿沟。汪精卫在其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奠基性论著之一”的《民族的国民》(1905)一书中强调了由单一民族(汉族)构成的国家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强调“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章太炎更是认定,“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所以,虽然同奉文化保守主义,以章太炎为领袖的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目的则是排满,是“‘以国粹激励种性’,其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反对外来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为着推进‘逐满复汉’的民族革命”。这与以康、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泾渭分明、冰火不容。在章太炎的推动下,邹容、陈天华等更是从“种界”立论,从所谓进化的立场强调汉族相对于“西伯利亚人种”“蒙古人种”“通古斯族”(满人)的种族优越性,强调了民(种)族区隔、华夷之辨这一属于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用于“激励种性”的“春秋大义”。他们不约而同又理所当然地征引《左传》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排满的战斗口号。概言之,革命者皆把“排满”与“民族建国”相联系,视“排满”为实现民族建国、完成“振兴中华”梦想的第一要务。
作为对峙的另一方,梁启超以其首创的“中华民族”的提法来应对革命党、国粹派的诘难。“中华民族”的观念强调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写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力主化除满汉畛域,填平民族鸿沟,坚持认为“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乃是“平满汉之界”,特别在1903年游历北美后,受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的影响,“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大民族主义”的提法去弥合由激进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民族裂隙。梁启超反复倡导“新民说”,此“新民”之“民”,国民之谓,这表明他试图努力用“国”的概念替换“族”的概念,强调“国”的概念高于“族”的概念,因此,在“保国”的危难关头,族与族的矛盾不是第一位的,应该被搁置,甚至应该被化解。康有为则从“文化群体”的概念出发认定满汉同一,他的《辨革命书》一文认为,“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一部分,“纯为中国矣”。由此,他坚持“满汉不分,君民同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一生致力于“天下大同”,他的“乌托邦‘大同世界’充满着激进的平等主义和普济众生的思想”,一切有可能造成不平等、歧视、仇恨的人类制度都是应该被消除的,国家的界限在他那里都是要被超越的,更遑论民族或种族的界限。无疑,康、梁的民族主义立论,是与其“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在逻辑上相匹配的。
林纾的民族主义取向,不仅表现为他作为古文家所持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而且,“梁启超为提倡‘新小说’而展开的高度政治化的斗争,事实上为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种‘道’,由此也为其打开了一片天地:民族救亡成为了当代的‘道’”。因此,他译书之所欲助,是为“爱国保种”。进一步地,他对当时及未来的中国民族架构的设想,全盘得之于康、梁的民族主义主张。他对于康、梁的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不仅在思想上是贴伏的,还在翻译过程中有自觉的、有意的语言跟进。譬如,“《黑奴吁天录》中‘世界得太平,人间持善意’被译成‘道气’;‘上帝创立的国度’则被译成‘世界大同’,以回应康有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大同书》”。
林纾对“排满”的反对和对汉/满对抗的焦虑,便是周氏兄弟在“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中看到的“暗示”。撒克逊人/诺曼人对抗的历史局面,影射了汉/满对抗的现实局面。显然,周氏兄弟在这两组具有同构性质的民族对抗的叙事中看到了林纾的曲折用意。
司各特所处的18、19世纪之交,尤其是《艾凡赫》(Ivanhoe)初版时的1819年前后,正是欧洲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代国家形态和“政府体制”形成的初始阶段,对“国家认同”的趋附正在超越对民族身份的强调。对于这个时期的英国来说,由于邻国的拿破仑作为欧洲霸主正进行着野心勃勃的、试图征服欧洲的侵略扩张,战争频发,因此,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国家主义使命使英国内部长期以来的民族对抗、民族矛盾渐趋缓和,出现了一个虽然脆弱但却稳定的民族和平时期,达成了一个可称之为“英国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19世纪,不仅英格兰人,“许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也接受了这种英国民族意识,但也有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苏格兰民族或者威尔士民族,但他们共同拥有对英国国家和英国帝国的忠诚”。司各特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展现的鲜明的苏格兰特性,都足以让苏格兰人视其为本民族的文化英雄。但《艾凡赫》(Ivanhoe)的创作,却表明司各特在国家/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双重立场,或如卢卡契所说的“中间道路”:他既坚信自己是“纯粹的苏格兰人”,同时也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个多民族统一政体下的国家公民,以“英国”为名的“大民族”之一员;他唯一的一部不以苏格兰为背景的小说就是《艾凡赫》,这部讲述中古时代民族对抗的历史小说,戏剧性地以民族矛盾的消弭收尾,它实际上被司各特用以影射和劝谕19世纪英国内部的民族现状,这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司各特所有作品中最受争议的一部。而对于林纾来说,他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经历了被征服、被欺凌、被奴役的漫长的百年历史,“劫后”的撒克逊人如何放弃了复仇,看似不可化解的民族世仇最终如何化干戈为玉帛。
三
1066年,诺曼人在著名的黑廷斯战役中获胜,终于彻底征服撒克逊人,成为不列颠的统治者。如今一般称诺曼人是法国人,其实不尽然。诺曼人实际上史称维京人,祖居斯堪的那维亚,他们是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侵扰并殖民欧洲沿海和不列颠群岛的探险家、武士和海盗,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的广阔疆域,而欧洲的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古英语中“wicing”这个词首先出现在6世纪的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的诗歌中,意思就是海盗。他们剽悍、野莽、愚勇、好战、残忍且诡计多端,有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无与伦比的快速越野渡海能力,有无数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他们通过大肆的杀戮和劫掠,逐步征服和控制了欧洲的部分领土和人口。所谓的“诺曼人”(Norman)是指9世纪始占领法国北部、建立诺曼底公国的维京人及其后裔,而作为词源的Norseman/Northman(古斯堪的那维亚人/北方人)则将他们作为北欧异教海盗的身份彻底地铭入了自己的历史。
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尚武、野莽、残忍且最终以少胜多征服明朝的满族人,与诺曼人或可一比?甚至,他们善于模仿、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为我所用,从而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和国家统治的特性都如出一辙,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统治中施加了欺凌性的种族压迫。(有人就曾指出:“使林纾感到震动的还在于此书叙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受到异族压迫,广大农民沦为农奴,原撒克逊封建主也受到了征服者的欺凌。”)撒克逊人和汉人,都分别是本土的原住民,都有发达的文明,有先进的制度和技艺,但他们共同的命运是:都被品性野蛮、文化粗糙的民族征服了,且都被统治达百年以上。有清一代的中国,何尝不是劫后的撒克逊?这一富于冲击力的类比效果,无疑,林纾看到了,周氏兄弟或许也看到了,至少被暗示到了。
1903年5月,林纾和魏易在京师学堂译书局合译出版了德国人哈伯兰所著《民种学》(从英国人鲁威的英译本中译出)。这本译著被称为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发端之作。而这部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学/人类学著作,在闪烁其辞间并不过多掩饰其关于文明有高低、人种有优劣从而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关键论断。更早一些,严复在《天演论》(1897)中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焦虑表达中,暗含了当时国内各派对于“劣”的民族地位的自我默认。林纾是在由严复主事的译书局翻译《民种学》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此书是《天演论》的衍生品。他在译序中称,迻译此书是“尤愿读是书者知西人殖民之心”,其爱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心迹昭然。此前他译《黑奴吁天录》(1901)时,且译且泣,且泣且译,实是从白人对黑奴的欺凌中发现,“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可见,他对于种族欺凌、民族压迫是有着从文学到学术、从经验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的痛切认知和迫切忧患的。但微妙的是,《民种学》中关于人种、种族的分类说,却有别于革命派的理论来源,它在某种意义中抵冲了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诸如“西伯利亚人种”“蒙古人种”“通古斯族”的分类说。显然,在爱国保种的、共同的民族忧患中如何寻求解放路径、寻求什么样的解放路径,林纾的思路是自觉地与革命派划界的。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两个月后的纪念文章中曾提到,“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沈雁冰的这个说法,常被后人征引,以证明林纾对原著的“忠实”,以及其所译版本的“可靠”。现在看来——尤其是这部小说有了后续若干个中文译本后,这个说法非常不可靠。众所周知是,郭沫若早就指出过林纾的这个译本“误译和省略处很不少”,只不过郭沫若的注意力被司各特的“浪漫派的精神”所牵制,被英雄美人的Romance元素所吸引,并未在“误译和省略处”过多徜徉。
关于《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误译和省略处”,刘小刚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的民族主义》(《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一文有不少可资借鉴的论述。不用说,林纾的这些“误译和省略”,大多有着民族主义的话语考量。从这一角度切入阐述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专论并不多见,刘文自有其敏锐、独到之处。但刘文对林纾的“误译”的某些判断多少带有猜想成分,而其关于林氏之“民族主义”取向的理解和阐述尚有用力不到之处。实际上,如果摒除翻译过程中语用学维度的错讹和出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译者对原著所作的结构性改写,只有这样的改写才具有无可辩驳的故意和别有用心,由此出发所引向的阐述才更可能切中肯綮且逻辑清晰。
比照刘尊棋、章益翻译的《艾凡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和项星耀翻译的《英雄艾文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最大的结构性改写是放弃了原著将艾凡赫(Ivanhoe)作为唯一核心人物的结构性设定,而原本处于准隐性状态的人物——狮心王理查一世强势浮现,不遑多让,在译本里与艾凡赫构成了结构中的双核心。在刘、章译本和项译本中,理查一世的行止更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绿林游侠气质,在叙事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不在场”的半隐匿状态,只在叙事临近尾声、在比武大会后的高潮处一跃进入公众视野,这符合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惯于将“中等人物”设为主角、“重要历史人物”设为陪衬的结构模式,在这一点上,刘、章译本和项译本是更为忠实的。而林译本从书名的改动中就明显能看出其试图隐去艾凡赫作为中心人物的“结构性改写”的用意。在林译本中,虽然没有为理查一世添加外部情节和人物动作,但通过叙事暗示、通过笔墨分配(比如在叙述理查一世率军攻打诺曼城堡时,林纾一改古文的雅致和俭约,使用了《水浒传》式的战争场景描写,用墨重,且笔致通俗、引人入胜)以及在其他人物的言谈中有意凸显其盖世英雄的形象(如艾凡赫的父亲塞德里克在数次谈及理查一世时语调、措辞、情感的处理,林纾颇为用心,有对原著的刻意偏离),从而达到不断申示理查一世的“存在感”的效果,使其在正式亮相前就呈现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在叙事高潮处一跃进入公众视野前即已早早跃然纸上,由此,这一人物便不断上升到与艾凡赫这一中心人物同样突出的结构性地位,造成双核心的人物结构形态。
这一结构性改写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无疑,林纾全面领会和全盘接受了司各特的“民族和解”的创作用意。甚至,他还欲扬先抑、欲擒故纵地使用“劫后”这样的语言修辞来突出强调、强化了撒克逊人与诺曼人(林译“脑门豆人”)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所谓“劫后”,道尽了国破家亡和国仇家恨的深重况味。然而,即便民族对决如此尖锐,但民族仍然要和解,冲突仍然要解决,矛盾仍然要消弭。如何解决?如何消弭?理论上讲,这一方面需要艾凡赫这样出身撒克逊贵族的、极富感召力且又“深明大义”的英雄、骑士的示效,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查一世这样的“明君”的雄才大略和恩典惠施。艾凡赫在“民族大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约束、自我要求,与司各特从一个苏格兰人的立场出发所企望达到的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颇多精神上的共性,因此,艾凡赫这个人物自然是他的用力之处,是结构之核心,并且是唯一的核心,与此同时,因为早在司各特出生前近一个世纪,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已建立,“君主”的重要性反而不需要强调,所以理查一世不必列为故事主角。但林纾不一样,他所追慕的立宪理想其时正处焦心之状,对于他来说,既有此前变法失败带给他的现实挫折感,又有革命、共和的新政主张带给他的话语和精神压迫。既寻求内部的民族和解,又坚持保守的君主政治,出现一个双核心的人物结构设置,就显得顺理成章和可以理解。
“狮心王”理查一世率领各路英雄重夺王位的故事,在林纾的译笔下浓墨,理查一世因此得以尽显雄才大略之形象。与此同时,艾凡赫的父亲、撒克逊遗老塞德里克不禁对理查一世表达敬佩之心时,在其赞辞中,林纾有意添加了“有人心,有天良者”的说辞。实际上,理查一世是个只醉心于十字军东征以建立个人武功的君主,对朝政漫不经心,刘、章的译本称其“时而宽仁放任,时而又近乎暴戾”,项星耀的译本称“这位国王的个人品德和军事声誉已深入人心,尽管他在政治上并无深谋远虑的方针,有时宽大无边,有时又接近专制独裁”。而林译毫不犹豫地抹去了理查一世的这些重大的人格或性格缺陷,使其陡然成为一个几无瑕疵的完美君主。(但有意思的是,在林译《十字军东征三部曲》的后两部——《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中,林纾又让理查一世恢复了其冷酷、暴戾的性格。)毫无疑问,在林纾的理想中,既要民族和解,又要君主政治,而一个雄才大略、战功显赫且讲仁义、有天良、得人心的“明君”,是摆脱现实困境、解开历史死结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或许,光绪在林纾心目中勉强算是“明君”,即使不是,“君位”仍然是政治设制中不可或缺的首项,因为“明君”仍然是可以期待的,而且,就像塞德里克最终不介怀理查一世的诺曼人身份一样,林纾希望读者、民众也不必介意君主的满人身份。
英国的民族发展史,给林纾的启示和震撼是很大的。在他看来,因为“杂种”——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融合(包括种性与文化的融合),才使得英国成为“今日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剑底鸳鸯·序》)。此前不久(1902),梁启超更是认为,经过民族融合的、“其保守之性质亦最多”的“盎格鲁撒逊人”是白人中之最优者,“故能以区区北极三孤岛,而孽植其种于北亚美利加、澳大利亚两大陆,扬其国族于日所出入处,巩其权力于五洲四海冲要咽喉之地,而天下莫之能敌也。盎格鲁撒逊人所以定霸于十九世纪,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这些深切的感慨,既是对当时第一殖民强国的英帝国之民族、种性问题进行深入的历史考量之后所发出的震撼回声,也是针对其时国内复杂的民族主义态势所作的努力辩解。巧的是,卢卡契对司各特的研究结论,有着和他们颇为一致的认知。按卢卡契的说法,司各特“高兴地发现,英国历史中最动荡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平息下来,转到一条光荣的‘中间道路’上。正是这样,在萨克逊人和诺曼人的斗争中产生了既非萨克逊族也非诺曼族的英国民族;在血腥的玫瑰战争以后,也同样产生了都锗王朝、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盛世”。司各特在《艾凡赫》中传达的民族妥协意向,在苏格兰一直颇受争议,同时也不断促发人们思索,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的当下,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情形似乎又回到了司各特的时代,这些争议和这些思索正在复苏,重新出发。但无疑,司各特的民族妥协主张、“中间道路”的立场,深得林纾之心,因为林纾也相信,温和的改良主义是实现中兴的唯一道路,这自然也包括,在抵御外侮的大环境下以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方式爱国保种。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晚清各派关于未来中国的民族架构的想象,林纾在司各特的原著中读出了所谓的“八妙”,而他的这个译本,实际上达成了更为深层的另一妙。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