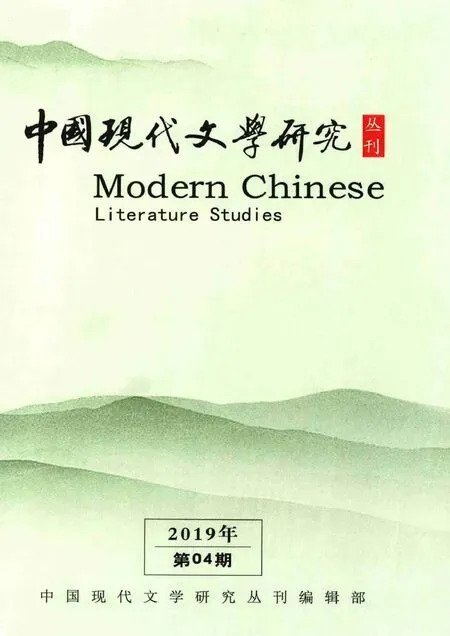在烟火尽头书写寓言
——鲁敏小说论
樊迎春
内容提要:鲁敏在对人间烟火的熟稔掌握背后带着强大个人风格的消解幻象、试图拯救或放飞自我与他者的寓言书写。这是鲁敏个人的创作追求,也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尝试。论文首先讨论鲁敏人物独特的“出生即成年”状态,即没有童年和少年,也缺乏成长痕迹的成年姿态;接着讨论鲁敏对创作主题的挖掘,她“以虚妄试错”,深刻展现了城市折叠后的人类精神和物质困境的机械复制以及虚妄自上而下的抵达;最后讨论鲁敏在对人间烟火的详尽描述之中展现出的艺术特点,略带悲剧意味的美学特质隐藏着独特的抵抗质地。结语指出鲁敏上下求索,在中西同质的现代性进程中缔造自己文学世界的“弥赛亚”,她的“寓言”独树一帜,携带着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
当《奔月》里的小六“主动失踪”的时候,《镜中姐妹》里的小五可能刚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小五有名有姓,小六却始终面目模糊,但毫无疑问,小六是小五精神上的亲姐妹。在对人生的经历与挣扎中,2017年的小六实现了对2003年的小五的“超克”。即便如此,历经漫长的创作生涯,小六显然依然没有抵达作家设定的创作彼岸。
鲁敏深谙人间烟火。自称“托生乡野,寄居都市”,从东坝到金陵,在仅仅四个小时车程的距离中鲁敏铺陈了自己的人间俗世,却也是真实而风格独具的文学世界。写邮票大小的家乡村庄,写跨越世代的城乡历史,甚至写百年风雨的民族史诗,在中国当代作家笔下从来都不罕见,鲁敏铺陈的世界的独特之处便尤为重要和必要。而使得一个作家的创作独具意义的更在于作品透露出的旨归与意趣。鲁敏对人间烟火的熟稔显然不足以支撑她的意义和独特,她之为当代优秀作家更多落脚于对这人间烟火的纯熟驾驭之后,对烟火之中的你我与他生命的另类体察,更在于她在更高更远处看到了烟火尽头的困境与废墟。鲁敏在对困境与废墟的突围中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一种消解幻象,试图拯救或放飞自我与他者的“寓言”书写。她在与既往概念的对话中创造和坚守了自我的文学特质,在数量众多的作品中透视了永恒的人际隔膜与人生虚妄,伴随着特有的忧郁美学气质,最终抵达“鲁敏式”的寓言世界,也对当代文学创作现场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 出生即成年
鲁敏的创作力是惊人的,不仅在于她作品数量的庞大,也在于她书写体裁的丰富和书写人群的广泛。鲁敏灵活地游弋于短篇、中篇、长篇之间,更在丰富到让人吃惊的人物群体中游刃有余。我们习惯于作家描绘社会画卷,呈现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但总有一个或一类人物作为主导故事进程的隐含作者存在,比如金宇澄的上海人物、莫言的山东农民、苏童的江南男女,虽然也丰富多彩,但始终带着作家个人的鲜明印记。鲁敏的特别在于其不同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多元与包容,乃至截然不同。从富庶的商人到贫穷的保洁,从机敏的贩毒人员到单纯的热心青年,从绝望的母亲到不遗余力的父亲,从有癖好的少年到自我满足的白领……鲁敏罕见地涉猎了当下以及过去、都市以及乡镇各个阶层角落里的男女老少。可贵的是,鲁敏对他们从来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真的将他们塑造成主角,赋予他们现代的心理描写与整全的人物性格。鲁敏将自身的性别、年龄、出身、地域隐于人群,代之以丰富错落的个人创造的文学景观。我们当然可以以此赞扬鲁敏高超的写作技艺,但深入阅读却也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共有的“鲁敏性”。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和影视都需要借助“青春”市场的支撑,我们依赖这一庞大的群体,其实是依赖一种年轻的经验,而大荧幕与小荧屏也几乎全部以年轻人的故事为主导,配之以烘托主角形象与气质的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乏和厚重的长篇小说一样的,从头至尾讲述某个人物平凡却伟大的一生的作品,但着重突出的依然是其青年时期的奋斗与成就。这是自《青春之歌》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开始的“成长故事”谱系,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坚定勇敢的革命者是特殊年代的文学要求。对当下社会来说,不论贫穷或富贵,在现代社会生活接踵而来的压力中逐步认清自己的位置,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所有文学人物共享的“现代成长模式”,这甚至也成为当下训练有素的读者或多或少的阅读期待,文学批评场域也随之生成了相应的文学话语,比如生活的“失败者”,比如“未老先衰”,比如“逃离”,比如“回归”。我们在诸多优秀作家的笔下一次次见证都市新鲜人的希望、失望、成长、衰老,和父辈对革命年代的小说的阅读一样,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与记忆。但鲁敏不一样。
阅读鲁敏的作品,我们深切体察了众多角色的真实心理与人生轨迹,但鲁敏却并不是讲年轻人在乡镇或城市的成长故事,在绝大部分故事中也并不以上帝视角为他们寻找答案和出路。以“旁观者”来形容鲁敏的创作姿态显然失之冷漠,但相比于推动和促进,鲁敏确实更像在做陈列与展览,也正是在这样的中性动作之中,鲁敏的人物披上了独特的外衣,笔者生造为“出生即成年”。即在鲁敏笔下,她的人物没有童年和少年,自出场便呈现出成熟稳重的成年状态。哪怕是明确的生理性少年儿童,也始终以成年的方式出现和行事。鲁敏笔下这些人物的这种“成年的姿态”也不光指生理成长痕迹的缺失或仅仅是心理的成熟,同时包括更为痕迹鲜明的被现代社会规训过的“社会性成年”。换句话说,鲁敏笔下的人物鲜少纯真幼稚,也不标榜理想正直,不以年少或天真做掩护,也不以公平或正义做外衣,在故事伊始便以成年人的逻辑架构讲述成年人的残酷或冷漠故事。
在最新的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中,鲁敏收入了十个短篇故事,稍显喧闹和猎奇,但似乎又都是我们可以碰见的生活故事。趋炎附势的社会盲流,围炉夜话的都市朋友,坦诚自然的男女商谈,你情我愿的婚姻利益交换……生活在早已魔幻现实化的当下,我们的感受都如本雅明所经历的现代性,不再被经验,而只是被体验①,读者已很难再在某些故事中找到“震惊”。鲁敏也无意于此着力,但她却让自己的人物于这现实中同化,他们在“出生”前便完成了对纯真和少年的告别,直接进入成年状态,充满着对青春与年少经验的排斥,以对安全感和社会融入的拆解,进入连妥协都省略的放弃状态,将所有的孤独、隔绝、不公与非正义坦然接受,理所应当到让人胆寒。《大宴》中对容哥这一不明身份的人的集体盲目恰恰是最为理性的崇拜,每个人都意识到容哥比市长更有用,大家蜂拥而至不是跟风,而是博弈论意义上的经济人行为;《坠落美学》中对牛先生按顺序追逐空姐的理解和默认,对外遇和出轨的淡然都显得合情合理。鲁敏将这种观念轻描淡写地置入她的故事中,普希金所说的那种“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意和鸡汤,都市文学中多余人、失败者的挣扎和不甘,甚至是政治正确的对底层的悲悯和代言,在鲁敏这里都被悄悄掩埋,鲁敏书写的是成熟的、理智的、默认所有的规则和潜规则的、坦诚相待的、成年人的生活故事。
《六人晚餐》无疑是鲁敏的力作。张清华和孟繁华在评价“70后”作家时曾指出,和“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80后”的“情感共同体”相比,“70后”只是单纯的“身份共同体”,他们是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②。我们都在呼吁文学告别宏大叙事,但我们似乎同时又明白,失去历史、记忆等重要元素,文学始终难以寻找自己坚实的根基或可以立身的位置。我们默默将对当下个人与情感的书写同样归于社会历史,而文学这种对当下人们精神的关切也显得更有“当代性”③的意义。《六人晚餐》的创新可能正在于其对传统的“历史”和即兴的“当代性”的兼顾与有力互动。这种互动不是单纯地在时间线上从1990年代写到今天,而是由生在其中的“70后”乃至一代人以“出生即成年”的姿态完成,鲁敏正是在此番情境描摹和人物身心双重困境的建构中尝试赋予作品隽永的价值与意义。
在《六人晚餐》中,如果有所谓的时代背景,那么1990年代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市场经济兴起等问题无疑显得鲜明而重要。但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历史之所以重要可能并不在于对所谓的大事件的记录,而在于这些大事件中卑微个人的命运之改变与不可逆,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表面可视的故事与真实不可见的故事之间的差异,是这差异之中蕴藏的微妙与不可知。从不同人物的视角看同一段故事并不新鲜,但鲁敏分别以晓白、晓蓝、珍珍、丁成功、苏琴和丁伯刚为主角讲述的故事却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或者事实真相是什么的解答,而是萦绕在这六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情感的孤独与人性的隔阂。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默默坐在同一张饭桌前,各怀鬼胎却又殊途同归。在晓白渴望父兄之爱和温馨的家庭氛围时,晓蓝追逐的是时代定义的虚妄的成功;丁成功不合时宜地坚持着一份天使般的信仰,妹妹珍珍却真诚热烈地热爱着俗世的点点滴滴;苏琴在道德的压力和身体的本能之中挣扎,丁伯刚于浑浑噩噩处借酒浇愁。他们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原生家庭皆祸害”的始作俑者,四个孩子完美契合了鲁敏“出生即成年”的设定,他们在内心独自进行波涛汹涌的自我建设,对彼此却从未坦诚,从未信任。如果时代和命运的变化形塑了过于鲜明的生理成年,那么这种对彼此情感与内心的封闭才是真正可怕的“成年”状态。晓白的怯懦与绝望、晓蓝的虚荣与悔恨、丁成功的孤寂与悲剧、珍珍的懵懂与扭曲,配合着苏琴的掩饰与羞惭、丁伯刚的伪装与失败,共同描画了日趋没落的旧厂区里最后的生活故事,却也描画了这六个人乃至人类整体无法逃避的生活尽头的悲凉与困境。
小说中有两处动人的“郊游”场景,一次是清明节两家人一起去上坟,因为谈及去世的亲人而格外热烈,本没有交集的两家人因为对疾病与死亡的共同追忆而格外亲近;另一处是小说结尾,两家人完成江葬后野餐,因为有了新生者与新死者,时隔多年的团聚显得沉重而温馨。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跨越了十四年的两家人在何种意义上达成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是四个孩子彼此人生阅历的增加与思辨能力的变化吗?是苏琴完成了对自我的批判,丁伯刚恢复了智识走向清醒了吗?其实还是因为最庸俗的新生与死亡。在丁伯刚和丁成功的死亡之外,晓蓝的孩子出生,正如多年前共享疾病与死亡的记忆,两家人再次在生命的无常与流变中妥协。技艺高超如鲁敏,依然逃不过如此庸俗的转折。如果丁成功和丁伯刚都活着,晓蓝能实现自己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丁伯刚可以开始过正常的人生,晓白可以实现和母亲的交流与和解吗?少年的问题始终以“成年”的姿态横亘于所有人之中,一次意外掩盖了不受时代背景与生离死别影响而存在的人类情感的隔膜与障碍。这是鲁敏于《六人晚餐》和个人创作之中始终悬置的问题,是所有“出生即成年”的主人公们孜孜以求的生活迷思,而鲁敏本人也未曾真正解决。
二 以虚妄试错
在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成年人物、搁置了不曾解决的问题多年之后,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奔月》中,鲁敏迈入了全新的阶段。我们惯常见到都市中疲惫者计划着甚至实施着逃离,但终究无效,或是回归,或是走向极端的死亡,或是以某种精神的救赎实现对庸常生活的重新理解与拥抱。细腻自然如爱丽丝·门罗,在饱受好评的小说集《逃离》中也始终无法走出日常的精神迷障。鲁敏在《奔月》中的突破因而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对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古老问题的全新回答,更是承继了自《镜中姐妹》和《六人晚餐》起就持续困扰作家与读者的文学难题。
鲁敏其实是以长篇的体量将一个都市白领主动选择消失的故事建构为了两种环境中两种人群生活的互动与隔绝。当我们都开始质疑“诗和远方”之后,鲁敏以一探究竟的勇气往前走了一大步,她当然是试图解释真正的逃离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更多的是以真实的案例展现了郝景芳笔下的“城市折叠”,将《六人晚餐》遗留的人情隔阂迁移至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格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④,小六的逃离和既往所有无效失败的故事一样归于虚妄,但鲁敏的奔月故事正于此推向前进:不断以虚妄试错。“试错”原意是指在解决某些问题时,根据已有经验,采取系统或随机的方式,去尝试各种可能的答案。这其实是一种仅适用于比较简单和答案范围较窄的问题解决的社会学方法,鲁敏化之为绕指柔,不仅在失踪故事的大框架中纵向挖掘,同时穿插细小线索牵引的脉络,看似淡然而不经意,实则左冲右突、双管齐下,从外部与内部的不同视角中寻找冲击实质的可能,试图解决难题于无形。
小六显然是当代都市女性的典型代表,有着不错的工作和薪水,有安稳的家庭和朋友,甚至还有一段不必较真的婚外情。但小六同样身处“出生即成年”的境况,面对母亲的心理扭曲与父亲从始至终的缺失,小六不曾“成长”,她登场之初便处于被黑暗的河水吸引的阴冷状态,也顺其自然有了真实漫长的逃离。如果小六的这种逃离是对全然陌生生活的追逐,她在“乌鹊”所进行的活动却全然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发达市场经济时代”的机械复制。熟悉的异性追求,自然形成的闺密朋友,微缩版的职场竞争,小六作为大城市的有“经验”者,有着上帝视角的居高临下。她的烦恼困扰并非来自新一轮的友情或爱情,而恰恰是来自这新一轮的无望的重复,低配版的家人、朋友、情人、职场,却是同样的创伤、猜疑与钩心斗角,小六的逃离正是从一个困境逃入另一个困境。吊诡的是,小六的困境却是舒姨一家的希望,是林子的心动,是钱助理的帮手,是聚香的明灯。
房东舒姨一家看似携带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失智老人、独生家庭养老,等等,但在故事持续的发展中,更为触目惊心的伤痕才逐渐显现。本应远在美国的独生儿子其实可能就在同一座城市,却是非死不能相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非正常关系,不管是1990年代的丁成功和晓蓝,还是当下大城市的小六与小县城的小哥,统统卷入这种没有出口的旋涡。从《六人晚餐》到《奔月》,鲁敏其实明确告诉了所有读者,血脉相连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膜是跨越时间与空间始终存在的难题,子女承受的成长的伤痛终究要反噬父母与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在人与人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中,我们缺失的那一课始终没有补上,作为最初的也最为重要的原生家庭,这种缺失为“一代人的爱与怕”埋下了悲喜不明的伏笔。
小时候,我外婆家有个邻居姐姐,你跟她特别像,尤其是笑的时候,一圈白牙齿。小时候我吃萝卜,她都替我啃皮,啃得一圈子牙印,我就顺着她的牙印吃,觉得更好吃了。刚才我打瞌睡醒来,突然见到你,你在笑,一圈白牙……⑤
当小六放弃了城市里体面的工作和丈夫,以近似杀人犯的诡异形象来到乌鹊时,林子却因为“一圈白牙”这样天真的理由爱上小六,开始一场不问来处的爱恋。这种场景近乎青春偶像剧,也成为鲁敏创作中不多见的温情。但总是让所有角色即刻成年的鲁敏并不愿意让这种温情泛滥,林子需要小六最基本的坦诚,但林子的人之常情恰恰是小六逃避的起点。正因为感受了城市生活与人情世故的倦怠才有了被黑色河水的吸引,才有了陌生之地的重新出发。林子的“青春偶像剧”注定成为小六实验之下的瑕疵品。
得了,不要假装这里头有什么玄妙的哲学奥义,诚实一些吧——事情的后半部分的走向,并非像买一根棒棒糖那样只是临时起意,事实上,它们一直埋伏在她体内。从小到大,她都能感觉到那份逃逸的欲望,跟她的身体一起发育成长,好比长期的生理准备——前面二十八年的每一天,可能都是为之在做着曲折的、草稿式的准备……⑥
小六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冷冷然的无情之态,对那边的世界,对抛下的亲人友爱以及一己之在,她竟毫不伤感,亦无愧疚,好像全身都上了最高级的麻药,明明知道这一刀下去,必会皮肉破绽、鲜血溅流,却无一丝痛感。这令她惊骇,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辨识感,好像是慢慢磨出光亮的铜镜,镜中逐渐显露出一个有棱有角、面目诡异之我。⑦
成年的小六在无意中实现了自己二十八年的逃逸愿望,但伴随着这种愿望的并非对美丽新世界的幻想,而是“冷冷然的无情”,这是一种意外实现的消极的逃避,是对亲情、友情、爱情皆无留恋与希望的虚妄。小六携带这份无解的虚妄抵达乌鹊,本身是对另一种生活的天然“试错”,抛弃来路,但问今日。关心舒姨和籍工的精神状况,关心超市的垃圾与清洁,周旋于林子的爱慕,伪饰着对聚香的友谊,当下此刻的真实也在慢慢走向新的虚妄。鲁敏对这种“虚妄试错”的直面并非只此一例,在短篇小说《细细红线》中,优雅大方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寻求中午休息时间在一个低档的小餐馆做粗重的兼职,两个小时纯粹的体力劳动让她觉得安心惬意,不仅心情开朗,睡眠也好了起来,就像小六在超市里打扫厕所,却开心到独自唱起了歌。海子那句“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其实饱含着沉重的悲凉,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小六的这种“体验生活”式的得意却带着天生的优越感,隐藏着对既有社会阶层的极大冒犯。但不能否认的是小六和图书管理员都从此间获得了灵魂的栖息与安慰,封闭绝望的生活以此打开了一个微小的缝隙。从另一个世界携带而来的虚妄以“试错”的姿势在此获得了释放、解构乃至重新的结构,“被试”的生活本身转换为一种突破与融合的探索之地。
可惜的是,此番试错掀开的缝隙在阳光完全直射之前便有闭合的趋势。舒姨一家沉重难耐,图书管理员终被发现,而小六在如火如荼的试错中走近了另一个身份。她对聚香的“养成教育”其实是带着前述的革命小说的“范导者”模式,在少女聚香这里,爱情和婚姻可以美好,但人生的效率和准确更胜一筹。于是小六的“薄被子”的故事才让聚香如醍醐灌顶。婚礼上的聚香悄悄对小六说,“要没有你的点拨,我大概还在傻不拉叽地痴等着我那初中同桌呢”,这也成为压倒小六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六五脏六腑一阵灼痛,从聚香宣布怀孕以来,所有的负疚、罪过、夹杂着酸涩的记忆,汇流为深渊般的旋涡。她头一次这么厌恶自己。她照着洗脸镜,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举起右手,耳光响亮,腮上五只粉红色的巴掌印如胎记般触目,久未响起的婴儿啼哭声又来了,由远及近,亲昵无忌地撒着娇,像要扑到她的怀里,像要诉说对她的依恋与向往。镜子里的小六泪崩如泉。⑧
至此,小六在乌鹊终于完成了自己以虚妄进行的试错生活。舒姨一家的亲情隔阂、林子的爱情游戏、超市里的职场竞争,统统在闺密聚香的“养成婚礼”中达成融合。与之对应的是,小六原本生活的城市,起初坚信小六未死的丈夫贺西南两年后对另一个女人下跪求婚,和小六有着露水情缘的张灯彻底沉迷于自我虚构的世界,小六母亲则仍然沉浸于既往相同的幻想,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继续,小六终于和自己一直抵抗的一切融为一体。这是城市折叠后的机械复制,这是虚妄自上而下的再次抵达,这是来自《六人晚餐》时代的困境于《奔月》时刻对“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的再一次征服。“试错”终究是“错”,鲁敏和她的人物一起,铩羽而归。
三 烟火尽头
沉迷于一群“出生即成年”的人物形象,不断以虚妄试错生活,看似冷漠的鲁敏恰恰极为眷恋人间万事万物,并以惊人的笔力将它们书写得淋漓尽致。
《百恼汇》算得上是俗世人生的大观之作,年老患病的父母,面临拆迁的房屋,三兄弟三妯娌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经历,鲁敏以一个大家庭的一段短暂生活写尽了人生百态。她一直擅长写父爱缺位的家庭和女儿,如《镜中姐妹》《墙上的父亲》《惹尘埃》,及至《六人晚餐》《奔月》,鲁敏总是将男性力量的衰弱与众多伤痕关联。在《百恼汇》中,男性人物众多,却个个挣扎在失势的边缘,偏瘫的父亲、懦弱的大哥、丧失性能力的老二、无法说服妻子生育的老三,鲁敏极其残忍地将整个家庭中的男性气息毁灭,取而代之的是在焦虑烦恼中苦苦挣扎的女性群体。和男性人物不同的是,她们审时度势,目标明确,为了自己的生活和需求苦心经营。但不论是哪种人物、哪种品性,鲁敏以之为媒介,更多着力的是他们身处的人世生活。房屋拆迁、赡养老人、子女升学、工作变动、夫妻生活,鲁敏不厌其烦,捕捉其间的善恶美丑。《百恼汇》显然出色地完成了基本的任务,但也失之生硬和单调,文学如果单纯地作为现实生活的临摹或转述显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百恼汇》之于鲁敏,是书写题材的完美呈现,却不是艺术与文学追求的典范,鲁敏将未完成的任务与追求埋藏在了其后的诸多作品中。
在稍早些的名篇《伴宴》中,鲁敏塑造了一个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坚守自我价值观念的琵琶乐手宋琛,但作为“最后的人”,她和她的知音都难免向资本低头。小说的结尾虽然落入窠臼,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真实的世界样貌。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之外,在高雅脱俗的民乐之中,仍然是你来我往的俗世烟火。《隐居图》算得上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一次集中而典型的表达。大学时期的恋人时隔多年后在男方的家乡县城重逢,女方已经是投资公司的老总,男方却颇有潦倒之感。虽然早已各自成家生子,身份地位的差异还是牵扯出当年的相爱与别离。一方对艺术理想的追逐和另一方对世俗成功的信仰构成的矛盾萦绕在鲁敏的多篇作品中,鲁敏的态度也多有暧昧摇摆。但她终究是书写“成年人”的故事的,《隐居图》也是对《伴宴》主题的一种承继和更为清晰的表达。在物质生活的压迫之下,对理想与艺术、对固执与清高,鲁敏总是表达着尊重、羡慕,以及转身之后对现实的妥协。鲁敏可以写出完美的挣扎过程与妥协的终极真理,“整个时代的默契”是“晋升、出国、买别墅、换车子、替孩子择校、投资、广结人脉”,这是大多数人追求的“欣欣向荣之感”,鲁敏也尽职尽责地将这些“欣欣向荣”铺陈到众多故事之中。但鲁敏总是不安分的,文学人物的妥协从来不是她的妥协,她极力在真实之下挖掘文学虚构的宝藏。人潮拥挤之中,鲁敏试图穿越葱茏的人间烟火,发现新质:
但他仍然抱着少女,他慢慢地抚过她的背,仔细地体味那光滑中的生涩。他决定,他拿定主意,他也有把握:接下来的时间,直到两小时结束,他就要一直这样抱着圈圈。他愿意通过耳语告诉圈圈:这也是性,这就是性。最美妙的,最新鲜的。……
床上像石雕一样偎着的一男一女,身子光光的、白白的,就那么毫无遮拦、无动于衷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⑨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为了曾经爱过,为了久别重逢,为了再次诀别,在最后这一刻,放下偏见与坚硬,抛却身外之物,还原为一对有情义的、软弱的人。⑩
正是黄昏时分,暮色灿烂而消极,那群鸽子就在对面的屋顶上。玲珑的身姿,纤巧的不停转动着的脑袋,饱满弧线的腹部,何其优雅而异样的美!它们起飞,它们落下,它们梳理羽毛,它们斜着身子在空中交错,它们突然从视线中飞走。
这骄傲而不规则的飞翔、失控般的消失——他妒忌!⑪
在对尘世人生的熟稔与器重之中,是满溢出来的清新情怀。和《伴宴》的失败一样,这些情怀终究也归于失效,宋琛最终承受了被观看与被嘲讽的命运,钟点房里即将进行一场羞耻的检查,久别重逢的大学恋人要各自回归令人厌烦的生活,孤独的退休老人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真实的人间,朝朝暮暮的日常烟火不息,鲁敏在尽情描绘之后,总要尝试于众声喧哗中找寻到不一样的生命瞬间,哪怕只是一点点:钟点房里赤裸的拥抱是“正午的美德”,高级酒店里诀别的搂腰是瞬间释放的真情流露,深夜起自阳台的飞翔是对自由最后的触碰。情怀的所有者们还是享受了片刻的宁静与高贵,正是这片刻成为孤独心灵的延展空间,成为鲁敏追逐的奔腾不息的生命的出口。
鲁敏对这种片刻的眷恋携带着一种忧郁的美学气质。在最初一批表现现实的作品获得好评之后,鲁敏才缓慢地转战自己的故乡资源“东坝”,在诸如《风月剪》《思无邪》《离歌》这样的作品中,鲁敏以极为潇洒的姿态甩掉了先前的包袱,赋予东坝的世界别样的气息。这气息中有沈从文式的悠远宁静,又多了鲁敏自己的人性观察。宋师傅的不合群,来宝的至纯,三爷的真情,无不带着乡村特有的质朴,却也带着被这个世界亏待的深沉的悲凉。鲁敏将她的人物放置于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的夹缝之中,进而衍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既沉重又轻盈的人间至味。“东坝”系列作品以及之后的城市暗疾系列,再到更新近的《拥抱》《枕边辞》《坠落美学》,鲁敏总能在烟火之后让那些高贵的片刻充满浓烈的身世之感,忧郁、悲凉,以及“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⑫的宿命慨叹。
这种充满悲剧意味的美学特质让鲁敏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质地,看似简单,却饱含自古希腊戏剧沿袭而来的崇高美感,饱含鲁敏看尽烟火后的真实意图:这种忧郁美学和或深或淡的情感印证正是对既往宏大时代浪潮与激烈戏剧冲突呈现的大起大落的切实抵抗,是对滚滚红尘充斥的无尽虚妄的切实抵抗,是对不断的自我迷失、自我否定的切实抵抗。抵抗的行动终究是为了穿越烟火去看、去拥抱,去看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去拥抱所有人贪恋的人间情爱与灵魂自由。鲁敏一番跋涉,依然暴露了自己的心之所向。
四 结语:寓言及其携带的
鲁敏笔耕不辍,她用众多作品铺排的文学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笔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巴黎,那些“出生即成年”的人物正以虚妄的姿态在挣扎中寻觅“弥赛亚时刻”。本雅明在论述“寓言”理论时指出艺术在衰微的、充满灾难与痛苦的现代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是寓言,他认为只有在极度的黑暗、痛苦和腐败没落中,才能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呼救,拯救才会到来,而寓言就是对这末世人生进行救赎的天使。寓言的价值在于它揭示出人们对历史的理想化和美化是一种幻觉,并以废墟体验把握住了否定的历史经验。在本雅明的理论中,寓言就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在现代艺术的分裂、现代社会的异化中,积极承担起了拯救的使命⑬。相比于本雅明对于弥赛亚的痴迷和乌托邦的幻想,鲁敏举重若轻,她在中西同质的现代性进程中书写了自己的“寓言”:让成年状态的人去试错,让烟火尽头的悲剧去抵抗。鲁敏在中国时刻上演魔幻现实的当下,在社会、经济、文化的罅隙中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细微的透视,她试图通过书写捕捉俗世人生层出不穷的海市蜃楼,在烟火尽头归拢历史洪流中纷飞的爱与痛,用以缔造自己文学世界的“弥赛亚”:失败、放弃;释怀、和解;消失、重启……鲁敏从不拘泥于消极或积极,潇洒地让隐喻和象征如讽刺和反转一样飞舞,手脚并用地上下求索。
《镜中姐妹》里,春华成了被丈夫背叛却不得不妥协的失意女人,秋实嫁作“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妇,大双远赴边疆,小五仍然苦苦挣扎在尘世,这个家庭的五朵金花,唯有小双长眠地下,永远年轻;在《奔月》中,小六对林子说,“对日子里那些平常景象,我既满心尊敬又难以忍受”,小六如萤火虫一样,美丽善良却难以驾驭。小五的决绝之后仍有小六的无畏,但鲁敏在内心里或许是偏爱死去的小双的,因为如小六一样勇敢的那些人,出生即成年,以虚妄试错,以自我为饵,看到的无非仍然是时代面目之下的人心粗糙,人与人的隔绝,庸常生活的不朽,爱的质感的湮灭。略显忧郁的鲁敏,在她尽述的烟火尽头实践着自己的“当代寓言”。这种“鲁敏式寓言”同时携带的时代问题在于,在文学的社会功用不断边缘化的当下,这样的书写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效的?在多大意义上可以为读者提供认知生活与世界的新的方法?是否可以在文学的意义上为那些出生即成年并时刻被虚妄裹挟的人寻找到出口,或者,至少可以提供些许精神的慰藉?是否可以疗愈泛滥的人心粗糙、人际隔膜,或者,实现对自我与他者的精神困境的点滴救赎?鲁敏以大量的作品,以小双的长眠和小五、小六等人的遭际,以充满悲剧气质的美学探索给出了试探性的答案。这种答案是作家给出的可能性,或许也是骚动当代文学创作乃至当下社会的又一地鸡毛。
注释:
①张旭东:《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页
②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③陈晓明曾著文讨论“当代性”问题,《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④鲁迅:《希望》,《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⑤⑥⑦⑧鲁敏:《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38、47、309页。
⑨鲁敏:《正午的美德》,《与陌生人说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269页。
⑩鲁敏:《隐居图》,《小流放》,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⑪鲁敏:《铁血信鸽》,《伴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⑫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歌词,《南下专线》,2011年。
⑬[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