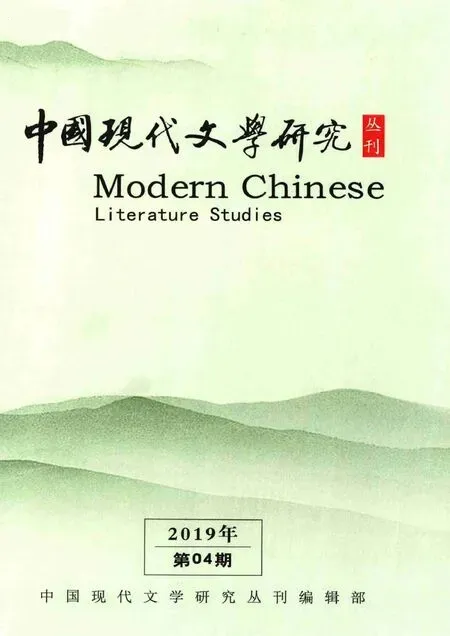鲁迅“意见”的辩证法与政治“幽灵”※
陈红旗
内容提要:将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历史化并“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就会看到鲁迅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经验之于左翼作家的启示。鲁迅认为:左/右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之间矛盾纠缠关系的复杂性,他真正担忧的是“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多种可能性;他强调左翼文艺界必须扩大文艺战线和再造“精神界战士”,希望“左联”多培养一些能够引领文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确证了左翼文学的核心命题——“文艺大众化”,也确证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导者和启蒙主体——左翼知识分子,而他与其他“左联”盟员的多重矛盾印证了左翼文艺思潮中政治“幽灵”的广泛存在,也印证了个体的公民政治之维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政治之维的纠葛互动。
讨论鲁迅之于中国左翼文学嬗变的意义,必须讨论其《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文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以及当时中国文化政治分裂的关系。而探讨鲁迅的《意见》与左翼文学以及是时中国文化政治分裂之间的关系,必须破除将文学和政治层面上的“左”与“右”相等同的误识,因为政治上的“左倾”极有可能演变为文学上的“右倾”,反之亦然。同时,还要破除将鲁迅视为“左联”领袖的迷思,鲁迅与周扬等人的多重矛盾,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鲁迅“意见”的“不重视和抵触”①,以及“左联”党组成员对鲁迅的阳奉阴违,都证明鲁迅在政治层面上根本就不是“左联”的领袖,他只是一开始就站在“左联边上”②而已。对于这一点,鲁迅在《意见》中已有所暗示,他点名批评昔日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攻击的“无聊”就是一种旁证。鲁迅尽管在政治层面上对“左联”的影响有限,但他在文学层面上对左翼文学的发展和演进是有积极助推作用的。在这里,只要我们将《意见》历史化并“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连接《意见》的生成与左翼文艺界之间的密切关系,重拾《意见》与鲁迅寻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运思理路,就会看到鲁迅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经验之于左翼作家的启示作用,也会看到政治“幽灵”对鲁迅与其他“左联”盟员之间关系的深远影响。
一 从“左翼”转为“右翼”的多种可能性
众所周知,在左翼文学的发轫期,“左”与“右”已经构成了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更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来捍卫他们的文学主张和阶级立场。然而在鲁迅看来,左/右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之间矛盾纠缠关系的复杂性,闭门高谈阔论“彻底的主义”,既容易使左翼作家走向“Salon 的社会主义者”的歧途,也会令左翼文艺界迷失自己的核心命题——从“大众化”到“化大众”。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艺界的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具警示性和辩证性的真知灼见。
在《意见》没有发表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非常喜欢以左/右的二元对立来表明革命文艺界与自由主义作家等的势不两立。比如,郭沫若强调说:“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了的时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存在。”③成仿吾也斩钉截铁地表示:“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④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在1928年,距1923年革命文学的发难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间,他们开始依据政治立场、革命态度和身份认同上的“正确与否”来决定对其他作家进行赞美、褒扬,抑或批判、贬斥,他们对作家思想上的左/右的纠葛纠缠和互动相生作出了并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论定”。1928年之后,他们明确提出要以“无产阶级意识的有无”为标尺来审视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能看到这些左翼文学发难者评价文学尺度的根本变化,但这种变化和导引是否有利于左翼文学的发展呢?显然并不一定,事实上,态度太过激进的评论只会给进步作家带来反感情绪或惊吓效果,由于创作受限而导致蒋光慈在1930年退党就是一个明证。
透过《意见》可知,鲁迅对“左翼”的理解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左翼运动”并不相同,他认可的是左翼文艺运动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一样内蕴的“进步”倾向,且是果戈里式的思想“进步”倾向而非高尔基式的政治“激进”倾向。显然,鲁迅的公民政治思维与创造社等的二元对抗逻辑和非彼即此的排他性很强的阶级斗争思维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更多的是依据其公民政治立场来审视革命文艺界或曰左翼作家的思想倾向等问题的,并依据其自身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独特感知,在《意见》中首先表达了对“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深切担忧。他认为左翼作家“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就会变成“右翼”作家⑤,即丧失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改造黑暗社会的价值取向,甚至变成一个过于看重利益、只顾自己“便利和舒服”的投机知识分子。其实,早在192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就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发现,那些希望革命的文人在革命到来后反而会“沉默”“失望”或“迷失”,这样的例子中外皆有。比如清末的南社就是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慨叹于汉族被压制的事实,愤怒于满人的“凶横”,所以渴望着“光复旧物”。然而民国成立后,南社文人反倒寂然无声了,这是因为他们妄图恢复“汉官威仪”的理想破灭了。又如俄国十月革命时,很多革命文学家一度非常惊喜,但他们的浪漫幻想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于是诗人叶遂宁和小说家索波里相继自杀,而小说家爱伦堡更是走向“反动”⑥。是故鲁迅在《意见》中告诫“左联”盟员说:“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⑦这确实是他的一个重要提醒。审视“大革命”以后的风气可知,作家已经不太好说话了,因为你的言论不是被看作“进步”就是被看作“反动”;但实际上所谓“左翼”与“右翼”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作家的身上得以呈现,即往往是合在一起且可以相互转化的,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这是鲁迅对左翼作家思想倾向驳杂情形的一个科学认识。
与此同时,鲁迅在《意见》中对革命作家自视甚高,情状的批评可谓意味深长。鲁迅认为,“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向来高于普通民众,往往将自己看作“民众之师”“启蒙之师”乃至“帝王之师”,但鲁迅看到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力所不逮,甚至从破除迷信的层面来看,知识分子话语的效用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正如《祝福》中的“我”回答不了祥林嫂所问的困境一样。沿着这种理路,鲁迅认为政治比文学更容易得风气之先,“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是一个“题目”⑨:“名”或“影”。这就意味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不一定是“左翼”作家。以是观之,当鲁迅告诫“左联”盟员要有准确的自我认同时,他等于进一步消解和颠覆了那种“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⑩套用德里达的说法,鲁迅所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中心主义”。这种“文学中心主义”背后的“等级秩序”造成了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的分裂,也造成了左翼作家/右翼作家的二元对立等级分明。信奉阶级斗争论的郭沫若、成仿吾等激进作家甚至以文艺宣传论、文艺革命论和文艺斗争论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学/有产阶级文学的分野,并以阶级划分来判定一个作家的立场、地位和等级。这种做法固然为中国现代文坛探讨文艺与身份政治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却因为简单的二元对抗思维而忽视了作家精神世界的多变性与国民精神的复杂性,乃至把无产阶级文学视作与“五四”新文学(就更不要说古典文学)几无关联的全新的文学形态。然而,在鲁迅看来,“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无产文学”其实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是跟着无产阶级社会势力的成长而成长的,它并不能由革命作家凭空臆想出来。这也是他再三强调左翼作家要与“实际”相结合、不要眼高过顶的原因之一。
当然,鲁迅对于左翼作家的告诫未尝不是一种自我警示。鲁迅是一个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社会批判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20世纪前期所有的革命运动,如反满、共和、五四、北伐等,而这些革命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他所希望收获的“龙种”,这就使得他的思想难免带有“虚妄”色彩,但他依然选择与黑暗社会进行抗斗,并探索人间的“生路”。在这种选择和探索的过程中,鲁迅又是孤独和疲惫的,所以他总是努力与进步团体谋求合作,来实现其“化大众”的现代性追求,进而“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⑪。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创造社、太阳社等“围攻”后依然在1930年参加主要由后者构成的“左联”的根本原因。不过,参加“左联”并不意味着向错误逻辑和等级观念“妥协”。这在鲁迅是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比较他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与《意见》发表时期的言行可知,虽然它们有所变化,但骨子里是一致的,且运用的都是辩证思维。比如,尽管鲁迅与很多“左联”盟员有过嫌隙和矛盾,但他在选择与“左联”这样的组织或其他文艺团体合作时,从来没有简单依据“左”与“右”的标准来判定“何者为战士”,为此他在《意见》中仍把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视为“战士”,也愿意与他们组建“联合战线”,只是提醒他们要把枪口对准“旧文学旧思想”和“旧派的人”。鲁迅的这种行为并非仅仅出于大度,而是源于其开展“实际的社会斗争”的需要;同时,这无疑彰显了其理性考量和人生抉择背后的行动哲学。
二 制造“战士”与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诉求
在陈述了自己最担心的“左翼”作家容易变为“右翼”作家的问题之后,鲁迅在《意见》中重点强调了对旧社会和旧势力开展斗争的策略——必须坚决、持久不断且注重实力。这里,鲁迅以新/旧的二元对抗表明了左翼文艺界与旧思想观念进行斗争的核心与关键——必须吸取过去运动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⑫这种观点体现了鲁迅对“斗争”长期性的准确认知和韧性战斗精神的高扬。日后,当鲁迅在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他对于“左联”的提醒仍然是决不能停止对反动者的“血的斗争”,且要将反法西斯主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⑬地具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去。至于斗争的主体当然是战士,也正是因为很早就意识到了战士的稀缺性,所以鲁迅在《意见》中一再提醒左翼文艺界必须扩大文艺战线和再造“大群的新的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说的“战士”并非意指军事战场上的“士兵”,而是富有反抗精神的“精神界战士”。这种“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之源要追溯到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1907年鲁迅作《摩罗诗力说》,其笔下的摩罗诗人是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如拜伦、彭斯等。鲁迅将这些摩罗诗人视为人间的“精神界之战士”,并明示他们的优秀特质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⑭。由于鲁迅极为看重“战士”勇于反抗自身奴隶地位的精神特质,所以他塑造了一系列叛逆的先觉者形象,如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绢生(《伤逝》)和“疯子”(《长明灯》)等。这些先觉者以他们的狂狷冲击着“吃人”的封建文化礼教,为后世读者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抛开这些文学层面的精神界战士,鲁迅认为在文艺战线的实际斗争中更需要专业化的“精神斗士”,他在《意见》中解释说:“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可以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⑮鲁迅对于文艺斗争与精神界战士的关系的阐析,既通俗易懂又闪耀着通透的智性之光。梳理鲁迅从《摩罗诗力说》(1907)到《意见》(1930)再到《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的精神理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抓住了解决文艺斗争问题的根本,其意见和建议也进一步令“左联”盟员明白了培养“青年战士”的重要性。
拥有“精神界之战士”之后,就要明确战斗的对象——“旧文学旧思想”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判断来自鲁迅对他以及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那场内耗极大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反思和痛悟。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是新文学者之间斗得不亦乐乎,“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这里的“旧派”固然意指以鸳鸯蝴蝶派、学衡派、甲寅派“余孽”等为代表的文化守旧派,更意指着依然奉行封建专制和迷信观念的民众或独裁者。就后者而言,鲁迅作于1928年的《太平歌诀》和《铲共大全》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进步思想文艺界与封建专制或迷信观念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太平歌诀》中,鲁迅转引了《申报》上记载的三首“歌诀”,它们分别是:“(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⑯这些歌谣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对革命政府的不信任和对革命者的感情淡漠,另一方面体现了民众轻信谣传的愚昧和无知。当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兴奋于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的幻象时,当他们全力高扬群众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时,鲁迅所看到的却是庸众的盲从和麻木。在《铲共大全》中,鲁迅同样从《申报》上的一则通讯——《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入手,通过通讯所记载的看客们拥挤、扰攘、喧闹着观看女共产党员尸体的情景,批判了铲共空气“为之骤张”⑰背后所隐含的统治阶级的屠夫行径,也批判了看客们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和死亡之上的劣根性。的确,与其在左翼文艺界内部相互“扭打”,还不如多去批评国民“收买废铜烂铁”的冥顽不灵和揭露武人“大买旧炮和废枪”⑱的阴暗心理。
有了“精神界之战士”并不意味着斗争可以不讲策略,为此,鲁迅在《意见》中提倡一种“韧”的战斗精神。所谓“韧”就是不能学清朝人把“八股文”当“敲门砖”的办法,作为一个工具,“敲门砖”用完了就会被丢掉,这就缺乏持续性。反证于进步作家的创作情形可知,很多人出了一两本诗集或小说集后就销声匿迹了,这种战斗方式显然是无益于启蒙中国国民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为此,要想在文化上取得成绩,就必须具有“韧”的战斗精神。这是鲁迅强调“韧”的精神的表层原因,而深层上鲁迅是在暗示“左联”领导层要珍惜战士的生命,因为战士的不易得,所以战士的生命也就变得极其“宝贵”,为此鲁迅从不轻易鼓动战士去流血和牺牲。当年,鲁迅曾被留学生政治团体——光复会抽签选中回国刺杀清朝大臣,但因他担心自己死后母亲无人赡养⑲而被取消了暗杀者资格。他又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⑳。鲁迅的清醒和理性使得他总是在估量着战士的价值和“壕堑战”的必要性,这既体现了其独特的政治意识和感觉结构,也体现了其作为非纯粹的政治家的特点和独异性,更展现了其充满悖论思维的革命观和政治观。
在属意于培养“青年战士”的同时,鲁迅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词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显然,这里的“枪法”意指的是一种有效的文艺批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应该说,提倡马克思主义批评不仅是革命文艺批评界的一大主张,更是一个批评家是否“向左转”的重要标志。当鲁迅被后期创造社的小将们“围攻”时,他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有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者来“狙击”自己的要害,进而让他能够在文艺批评领域获得质的提升。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渴求,一方面证明他在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方面也证明他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今天,我们尽管可以指责鲁迅轻易相信“苏联道路”的“轻率”,却不能否认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认同和体认之于左翼文学得以“飞跃”的推动效用。换言之,虽然鲁迅对于创造社的“感谢”——“‘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㉑——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当他身体力行地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和创作时,尤其是在反驳新月派批评家的“宏论”时,他是真切感受到了左翼文艺界培养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迫切性。
之所以如此,还源于鲁迅对当时常见的两种文艺批评方式的厌恶,其中一种是喜欢一棍子打倒所有非革命者言论的酷评,另一种是喜欢用超阶级的人性论抹杀文艺阶级性的“新月社式批评”㉒。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成仿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梁实秋。鲁迅讽刺成仿吾的批评俨然“李逵”似的做法,“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㉓,不问青红皂白只管“排头砍去”;又批评成仿吾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㉔喜欢摆出“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凶恶面孔,其结果只会令人感到惊惧。如果说,鲁迅对成仿吾的某些观点还存在矫正之意的话,那么他对新月派的批评要彻底得多。他认为梁实秋在与左翼文艺界论战中败下阵来之后,竟然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党”或“去领卢布”㉕,这其实是想借“主子”的政治势力来绞杀左翼作家和左翼文艺运动,其心理实在太过阴损和可怕。为此,鲁迅希望“左联”多培养一些能够引领文艺青年的“真正的批评家”,能够“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㉖,因为只有这样的批评家才能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正向批评和裂变能量。
三 左翼文学核心问题的再确证与政治“幽灵”的无处不在
在明了上述问题之后,鲁迅相信左翼文艺界自然会形成“联合战线”。对于“左联”以及进步文人之间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鲁迅并无异议,他所要提醒的是:“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㉗。这不仅指出了“联合战线”的必要条件和“小团体”风气的害处,还等于再次确证了左翼文学的核心命题——必须大力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也是“左联”的首要任务乃至根本目的。
这里,我们无意于夸大鲁迅之于“左联”的领导作用,但事实上“左联”确实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下属单位㉘,并开展了相关活动。这就在客观上验证了鲁迅《意见》的有效性。以文艺大众化问题为例,鲁迅的智慧很早就体现在他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上。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鲁迅并非独特的一个。事实上,晚清的近代思想家就已经产生了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此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强化,左翼文艺界已经在理论层面上给予“文艺大众化”主张以充分认可。比如成仿吾强调,“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㉙。瞿秋白则认定,“革命的和普洛的文艺自然应当是大众化的文艺”㉚。此后,“左联”不但将大众化看作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㉛,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并依此确认了左翼文学的发展理路,这与后来《讲话》中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立是有内在关联性的。不过,这并非我们所要强调的重点,我们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于“工农大众”的态度和立场。与左翼文艺界在提倡文艺大众化过程中对“工农大众”作为主体性存在的认识有所不同,鲁迅向来对庸众的法西斯心理和国民劣根性抱有警惕性,为此,他即使在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时,也不主张“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反而提醒左翼文艺界“大多数人不识字”。这不但预示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艰难,还包含着对庸众愚昧行为不可控性的警示。因此,鲁迅所说的“目的都在于工农大众”并非等同于左翼文艺界要消解自己的主体性,这里他是要以左翼知识分子为运动主导者和启蒙主体的。显然,鲁迅对待大众的态度和看法与很多“左联”盟员是有明显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同样彰显了鲁迅思想的前瞻性和辩证色彩。
进而言之,只有深刻理解蕴含在《意见》中的这种辩证逻辑,我们才有可能充分解开鲁迅与“四条汉子”等的矛盾谜题,以及他对“未来”担心的缘由。事实上,鲁迅对于所谓的真理和“将来的黄金世界”总是持怀疑态度,他早就说过:“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㉜当后期创造社发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倡导“普罗文学”并奉日本福本主义理论主张为圭臬时,他看到了自以为真理在手即可训诫他人想法背后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所以他说:“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㉝这意味着鲁迅所害怕的,是当某些“真理在手者”领导大众建立起未来“黄金世界”后,这世界会因为不再需要革命而将并未“战斗到底”的“同路人”㉞流放乃至“杀掉”。李霁野晚年回忆说:1936年4月冯雪峰在上海会晤鲁迅时,鲁迅有一天同冯雪峰开玩笑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我吧!”㉟这种“玩笑”不仅体现了鲁迅对“同路人”命运的一种预见,也体现了其独特的“政治学”:“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政治’生涯。这种政治,有时候看起来却那么不像政治,只不过是给‘正常’的社会和秩序‘捣捣乱’而已;有时候又具有极为严肃的面孔,看起来像是与旧世界的决战,只不过转瞬之间,又把可能隐藏其间的‘权力’中心主义,转换为民众‘权利’的网络主义。”㊱所以鲁迅对于庸众的劣根性是充满警惕的,对所谓“大众领导者”利用他的情形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并不信任这些领导者。而对于“左联”积极开展的政治运动的疏离,自然就成了他作为一个“非政治家”对文学主体性消解现象的抗议和不满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鲁迅固然把自己视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但他并非“极左”㊲,他所持的多是公民政治思维,即对不合理的社会问题或文艺界现象均持批评态度,而非基于群体立场、集体意志和阶级政治之维来发声;同时,他对任何冠冕堂皇的“主义”“学说”“概念”和“政治表态”均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个人主义观、公民政治思维和强烈的怀疑精神使得他与周扬等“左联”党组成员之间一直存有深深的隔膜,这才是他被后者有意架空和日渐疏远的根本原因。
可话又说回来,鲁迅与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毕竟存有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因此,他始终不放弃“左联”这个平台来为文艺青年提供成长机会和文艺阵地,进而为左翼文艺界培养了大量新人。而在参与“左联”活动时,鲁迅还是起到了“清醒剂”的作用,令半政治化的“左联”没有走向更“左”的排斥“同路人”的错误道路,进而成为当时进步文坛最富凝聚力的文学组织。在这种意义上,鲁迅与其他“左联”盟员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源于什么“权力斗争”或“仇恨政治学”㊳,而是源于其辩证思维及其抓取核心问题的优异能力和超前意识。当鲁迅的公民政治立场与超前意识遭遇“他者”不成熟的现代意识、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烂熟的“主—奴”心理结构时,他的“矛”不可避免地与周扬等人的“盾”撞击出惊人的火花,从而映照了一代人升降沉浮的政治命运和“辩证法”这一思维方式的“幽灵”㊴特性。反过来,也正是这种辩证法所凸显出来的理性思辨力量,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左翼文艺思潮中“幽灵政治学”㊵的无处不在,以及鲁迅之于左翼文学嬗变的多重意义。
注释:
①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5页。
②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1921—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③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1928年3月15日,第3号,第1页。
④㉙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第一卷第九期,第6、6页。
⑤⑦⑧⑫⑮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萌芽》1930年4月1日,第一卷第四期,第23~25、25、26、26、27~28、29页。
⑥⑨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35、134~135页。
⑩德里达:《立场》,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⑪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6页。
⑬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⑭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⑯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⑰鲁迅:《铲共大全》,《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⑱鲁迅:《“皇汉医学”》,《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⑲[日]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⑳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㉑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㉒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注释〔2〕。
㉓鲁迅:《“题未定”草(五)》,《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㉔鲁迅:《〈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1930年5月1日,第一卷第五期,第330~331页。
㉖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㉘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㉚瞿秋白:《“我们”是谁》,《俄国文学史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11月15日,第1卷第8期,第4页。
㉜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㉝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㉞鲁迅:《竖琴·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6页。
㉟李霁野:《悼念冯雪峰同志》,《李霁野文集》(第1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㊱张宁:《论鲁迅的“政治学”》,《文史哲》2015年第2期。
㊲毕克官:《盟主鲁迅也是左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
㊳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
㊴[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㊵李杨:《“经”与“权”:〈讲话〉的辩证法与“幽灵政治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