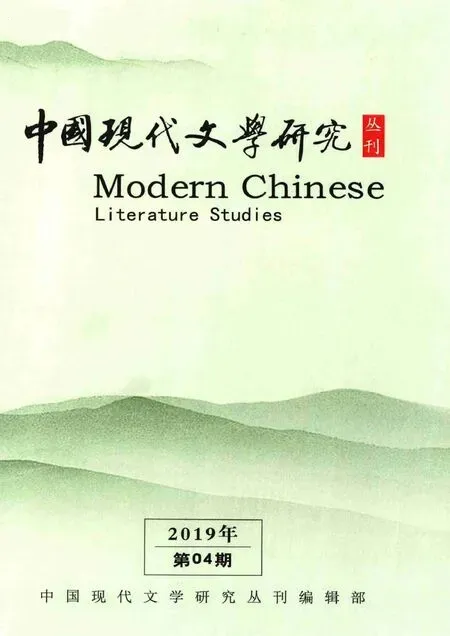穆时英教育背景考
——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资料为中心
王 贺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作家,穆时英的生平事迹如教育背景、经历等,已有若干研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利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资料,重新探究穆时英在光华附中、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等校的从学经历,对部分疑点再行予以考证、辨析,填补其间的空白之处,并澄清目前研究、叙述中常见的一些问题,以为学界提供关于穆时英教育背景的较为系统、全面、准确的知识。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穆时英的生平事迹如教育背景、经历等,已有若干研究,但也还有不少疑点、讹误。以其教育背景、经历而言,据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等资料记述,穆时英中学阶段曾读修能学社,而接受大学教育,则是在光华大学,记述相当简略,常常给人一种穆时英只在修能学社与光华大学二处读书的印象。其实不然,据笔者考察,穆时英的从学经历委实复杂、曲折,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以下即围绕着此一问题,结合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作一尽可能系统、深入之研究,包括对部分疑点再行考证、辨析(或证实,或证伪),填补其空白之处,以为学界提供关于穆时英教育背景的较为系统、全面、准确的知识。
一 修能学社与光华附中
关于穆时英入读修能学社一事,《穆时英年谱简编》有如此记载:
1926年 14岁
中学上修能学社,据穆丽娟说,穆时英小时候非常聪明,总能考前3名,但在穆时英的笔下,小说里那个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主人公书法和珠算能力都让父亲失望。穆的父亲还是相当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里给穆时英和穆时彦专门请了个英文教师,她是个老姑娘,还带着自己的保姆住在穆家。①
因为没有其他资料佐证,这里假定穆时英胞妹穆丽娟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这家修能学社(抗战中易名为储能中学),由上海钱业公会总董、宁波慈溪人秦润卿发起创办,专门招收“徘徊失学”的同业子弟。自1923年夏成立后,聘邑人冯君木、沙孟海、陈布雷等人任教,开设国文、英文、算术、书法等课程,实施中等程度的职业教育。而穆时英的父亲长期服务于金融业,且与秦润卿是同乡,送自己的孩子去修能上学是很有可能的。但穆时英在此读过多久?是否由此而完成整个中学阶段的教育?要回答此二问题,还得从其光华附中经历说起。
查1928年6月出版、穆时英本人参与编辑的《光华大学戊辰年刊》所公布的“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名单上,便有副级长穆时英的大名。另一方面,穆氏旅港时,曾发表《上海之梦》中引老同学的上海来信:“我们一同经过八年的母校光华已被人放了一把火烧得连草也没有一根了。”“我”自己又说:“在沪西,我过了最无忧无虑的八年,我认识蜿蜒于它的平原上的每一条小河。”仿佛说明其就读光华的时间,应在八年之数。同时,我们还知道,其正式入读光华大学的时间是在1929年秋,按当时光华规定之学制,大学须读四年,由此再往前推四年,我们可以考定,自1925年9月7日②开始,时年十三岁的穆时英,已在光华初中一年级上学了。与此同时,有研究者曾在台北木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室查见1925年9月入学的光华大学新生名单,其上就有穆时英的大名,而其“就读年级学科”为“一年级”,应即初中一年级,先前的“出身”(教育背景)则为“家塾初中”,③甚为模糊。
为何此档案不径记“修能学社”,穆氏既在家门口的修能学社读初中,何必又要转至沪西的光华附中从头念起?有研究显示,修能学社实行精英教学,学费相当之高,“甚至超过当时上海的部分优质中学”如南洋中学校、麦伦书院、徐汇公学等,④但这时穆家家道尚未中落(其《旧宅》一文,记叙了十六岁——实为十五岁,亦即1927年——父亲的黄金交易所生意破产而使整个家庭陷入黑暗一事),应该还可以承担得起。但穆时英究竟何时就读于修能?且其持续了多长时间呢?“修能学社的学制为初级四年,高级二年,预科二年”,“学生年龄在十一岁到二十岁之间,根据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分甲乙两组”。⑤而穆时英在十三岁(1925)时既已入学光华附中,则其就读修能学社的时间最早应不会超过1923年,该年正满十一岁,符合修能学制,事实上,也是在1923年7月,修能才正式成立。据此推断,穆时英就读修能的时间为1923年7月至1925年夏。台北档案里的“初中”二字,也说明穆在修能接受的是初中阶段的“初级四年”教育,但其并未完成,也正因这一从学经历较短而中辍,或亦缺乏学历证明,加之该学社创办初期,推行类似于旧式“经馆”的教育模式及“特种教法”,所以便被模糊处理为“家塾初中”,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至此可见,本节一开始所引《穆时英年谱简编》之记录有误。
二 入读圣约翰大学
当1928年6月⑥,穆时英初三毕业,其照片和名字,与其他负责编辑这本专门由大中学毕业生筹办且具纪念性质的《光华大学戊辰年刊》的同人一道出现,说明其早在光华附中之时,就已大出风头。同年9月,其顺利考入本校高中一年级。孰料高中只读了一个学期,穆时英就结束了在光华附中的学习,不久,又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一所知名的教会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各大中小学校师生上街抗议,圣约翰也不例外,因不满美方校长卜舫济杯葛抗议运动,该校近六百名师生遂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决定另外成立一所大学,这就是后来的私立光华大学。校名中的“光华”取“日月光华”之意,旨在光大、复兴中华。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光华大学与其前身圣约翰大学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然而,这种局面之下,穆时英何以弃光华而入圣约翰?又,其为何只读高中一个学期,便能入读圣约翰?
除了光华大学以古典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可能让这位爱好新文学的少年人备感压抑之外,⑦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缘由。《新命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40年12月20日出版)所载署名“重绿”的《一年来的中国文艺运动》⑧,便道出了另一方面的内情:
当他(王按:即穆时英)十八岁时,便脱离家庭,只身漂流各处,有三四年的时期,没有受到家庭的接济,这时他已开始对文艺有特殊的爱好,在中学时期,即致力于创作,以稿酬所入作为学膳之费。因为他资质聪慧逾人,所以他的欲望也与时俱增,在光华高中时,他便起了躐等的念头,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埋头勤习英语,他英语的深湛的修养也许就在此时打定基础,在圣约翰大学没有多久,又回到光华,一直到毕业。
“重绿”乃是穆氏友人,可能较为熟悉这段经历。而按照前引穆丽娟的说法,她们家里给穆时英和她的另一位哥哥穆时彦,很早就请了专门的英文教师;这位女教师常年住在穆家。打小儿的补习,修能以及光华初中、高中的学习,可能让穆时英的英文水平,远远超出了一般同学,加之已经崭露的文学才华,都刺激着穆时英去大胆跳级、投考圣约翰,孰料他一考即中,遂于1929年春季正式注册入学。而这一点,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穆时英学籍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在圣约翰这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穆时英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交流》。这部小说取材于北伐战争,聚焦于革命与爱情与之冲突,翌年由作者自费出版、上海芳草书店印行。小说末尾,还有这样的自注:“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作于怀施堂”。其中的“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显然是写作完成的时间,而“作于怀施堂”则交代了其完成地点,这里的“怀施堂”也正是圣约翰大学内的一栋建筑物。相关史实之考证及有关此书之文学批评,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但有趣的是,在圣约翰的第一学期结束之后,亦即1929年秋,穆时英又转入了光华大学。转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如果说在光华附中读了半年高一便升入圣约翰,已经令人意外,那么,他在圣约翰读了半年之后,又转入光华大学的行为,则不免让人费解。他何以要如此往复?又是怎么做到的?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尽管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私立大学招生较为灵活,学制也较有弹性,但是否已经到了允许正式注册在籍的大学生随时更换学校的地步?稍对近现代大学史、教育史有所了解的读者,绝不会就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在穆时英进入光华大学时,是否重新参加考试?此前其所拥有的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学习经历,是否够资格参加考试?
三 任诚推荐穆时英进入光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保存的一通手札,可为我们分析、解决上述问题,亦即穆时英如何由圣约翰大学转入光华大学一事,提供部分的解释。
这通手札的作者是数学家、教育家任诚先生。任诚(1984—1953),字孟闲,江苏江都(今隶扬州市)人,先后任教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等处。编著有数学教材多种,并为教育部起草师范课程标准。其六弟任中敏(二北),是近代研究词曲之学的大家。两兄弟专攻之术业虽有异,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则一也。但与任二北不同,大哥任诚早逝,因此几乎声名不著。
任诚此信,以墨笔缮写于“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校用笺”之上,首尾共七行,有上款,作光华大学“招生委员会”,落款有其署名“任诚”及日期,下并钤印,无标点。信中所谈者,正是推荐穆时英入读光华大学部事。为方便讨论,兹校录原信如下:
兹有学生穆时英,愿作本大学作特别生,虽未具有招生简章第二条甲乙两项资格,但其程度尚能相当,拟请准予入学特别试习,不胜感何。此致招生委员会 公鉴
任诚谨啟 八月廿一日
据上文可知,此信作于1929年8月21日(以本年之开学日期推算,此一时间应为西历),内容简明、晓畅。穆时英以不符合当年光华大学“招生简章第二条甲乙两项资格”,按常理无法入学,但是,由于穆时英此前已考入圣约翰,证明“其程度尚能相当”,所以,任诚函请本校招生委员会准予其入学做特别生,也便有了理由。
的确,据《申报》报道,这一年光华大学大、中学部的第一次入学考试,吸引了男女生四百余人远道而来,可谓盛况空前,而大学部的考试,除各种笔试外,还有由教务长亲自上阵,逐一接谈的口试,竞争尤为激烈。穆时英如果不做特别生,而以同样资格参加光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恐怕也未必能够顺利考进。究竟任诚的推荐是否管用呢?须知这位推荐人,约于1928年年末接受光华大学训育主任(亦称“群育主任”)之聘,翌年3月中旬正式到校办公⑨,可谓光华新人。其五个月之后的推荐,效力又如何呢?
事实证明,任诚的推荐是有效的,不久,穆氏顺利入读光华大学。任诚的推荐之所以能发生作用,至少应有下述两点原因。其一,任诚虽系光华新人,但职位比较重要。训育主任一职,在光华仅次于校长、副校长、各学院院长,算是要角,因此,负责学籍注册的同事恐怕不好驳他的面子。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年大学部的招生,除去正式生之外,还吸收了不少特别生和试读生,穆时英恰好符合做“特别生”的条件,又何必拒之门外?
但任诚之履历,在穆时英学籍档案中,记作“上海中学初中部”“教员”,而其与穆氏之关系为“师生”,似有问题。透过上文分析可知,如果任诚是上海中学教员,则其与穆氏无师生之缘;要有师生之缘,又须是在穆氏入学光华以后。因此,这一关于任诚的身份及其与穆时英关系的两处记录,必有一处为误。可是,我们看任诚写信用纸,是“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校”的专用信笺,显示出其曾为上海中学教员的身份,而且,据有关资料显示,其兼任光华等校职务之前,亦曾任教上海中学,因此,我们在这里无法排除其在光华任职时,尚在上海中学任教这一可能。
那么,有问题的就是“师生”关系了。但会不会是其在光华任职在前,而到上海中学在后,因此“师生”关系亦无误?又,此信笺及其相关记录,会不会是任诚为了回避其利用职务之便推荐他人就学而作出的“障眼法”?限于资料,暂只得付之阙如。
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有:穆时英入光华大学做“特别生”,即便不参加入学考试,还须具备哪些条件?“特别生”这一特殊身份,究竟有何意义?其后,穆氏从“特别生”变成正式学生,又需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满足什么样的要求?⑩
对任诚推荐穆时英进入光华大学一事,目前也只有华东师大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光华大学:90年90人》一书有所记录。其中,题作《作家穆时英》的小传宣称:“1929年春入读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秋季在上海中学教师任孟闲的推荐下以特别生免试转入光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⑪但如上所论,任诚的“上海中学”教师身份是存疑的,不过,即便不能完全确定任诚此时的全部身份,其在撰写推荐信时,正出任光华大学训育主任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任诚以何种原因推荐穆时英入校,穆氏在光华大学所修科系究系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还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尚需另作讨论。因此,为求严谨审慎起见,笔者建议将这里的记叙,改作“秋季在任诚(字孟闲)的推荐下以特别生转入光华大学文学院”。因为,正由于任诚推荐得力,穆时英最后才得以重返光华,做起了光华大学生,而这学期光华的开学日期为1929年9月14日。⑫
四 毕业还是肄业?
光华八年,对穆时英的影响之大,无论如何形容,似乎都不过分。作者不仅将自己在光华期间的所见所闻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而且,在散文《别辞》中,一再深情地说:“我是在光华里边生长的”,“我是那么深深地爱着光华呵!”
对于其在光华大学的毕业时间,一般并无异议,咸认为是1933年夏。实际上,参核光华校史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准确地定位为1933年6月12日。⑬1933年6月出版的《癸酉年光华年刊》,即载有该刊编辑、本年毕业生穆时英所撰《别辞》一文。此文虽未收入《穆时英全集》,但近年已有学者整理、重刊,据此文可知,穆时英确于此时毕业离校,因此才有告别师友之“别辞”之作。
不过,当时穆氏究竟是毕业还是肄业,换句话说,他是否顺利获得了学士学位,长期以来并无坚实的结论。《穆时英年谱简编》1933年条下记:
在穆时英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去世。
这一年夏季,穆时英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据他朋友康裔回忆,穆曾在新雅茶座上亲口告诉他,他大学时的功课之差,为全班之最,老师见他,无不摇头叹息,毕业时,由于他接连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一跃而为“知名作家”,所以光华大学对他的毕业考试,是在人情下通过的,他自己戏说是“作家的内幕消息”。
(黑婴曾说穆时英因为需要自谋生计,大学没有读到毕业。经与穆丽娟核实,还有穆时英身穿学士服的照片为证,黑婴当属误记。实际是同在光华大学,低穆时英两年的大弟穆时彦在父亲去世后,怕给家里增加负担,自动辍学。据讲,当时穆家还没有穷到供不起学费的地步。)⑭
显然,这里年谱作者主要采信的是康裔和穆丽娟的忆述,而放弃了黑婴的“肄业说”。但在当时报章的文坛新闻、动态上,穆时英是从光华肄业而非毕业这一事迹常能见到,如《出版消息》第3期(1933年1月1日出版)“作家的消息”,述“穆时英”近况时即有“仍肄业于光华大学,日常生活有家庭供给之”的表述;该刊第16期(1933年7月16日出版)载彭雪华《漫谈宁波的几个作家》则谓:“穆自发表《南北极》后,一跃而为当代名作家。现闻尚肄业于光华大学,年仅二十二岁。”可谓相当一致。作家黑婴的忆述也指向“肄业说”。
然而,从《别辞》及其他多种资料来看,仅就学习时间而言,穆时英的确完成了在光华本科四年的学习,至于其是否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固然富有争议(有肄业、毕业二说),但“毕业说”也并非全无证言,除康裔、穆丽娟、重绿等人的证言之外,素为学界不甚注意的穆时英大学毕业时戴学士帽所摄照片,便是一重要证据。
此照片如泛泛看来,似是一般图像资料,其实并不寻常。首先,其曾与《别辞》一文,同刊1933年6月出版的《癸酉光华年刊》,照片左边并有穆时英的个人信息,除姓名、籍贯外,其中一项即为“文学士”,与本页另一人(获“商学士”)形成对照,说明穆氏在当时不仅已顺利毕业,且获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其次,站在质疑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幅照片及其配套的文字是否属实?特别是照片本身,是不是穆时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从而找人借来学位帽服拍照留念,假充毕业?
应该说,将此照片视作一项重要证据,是传统意义(而非“新文化史”意义)上“以图证史”的做法,此取向往往会强调图像本身所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下述三点情况:1.穆氏此时已是中国新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2.其本人十分珍惜自己的荣誉(为此,曾不惜时常同小报报道、流言蜚语展开斗争——虽然穆氏对参与此种斗争的热情远逊鲁迅);3.这一刊物是公开印发给全校师生阅读(可能的读者还有家长、一少部分社会人士)而非给穆时英一个人私人收藏,那么,上述质疑的合理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由此图像资料,而参证其他关于“毕业说”的文字资料,足见此说不谬,而所谓的“肄业说”只是一传说而已(此说所以流行,如何流行开来,值得另外研究)。《穆时英年谱简编》在形成相关判断、记载时,固然缺乏深入、透辟的分析和论证,但就其对事实本身(即穆时英自光华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的记述而言,无疑是准确、可信的。在其叙述之中,唯一的瑕疵是将“文学士学位”误作1949年后通行的“文学学士学位”。
五 结 语
结束对穆时英教育背景的考察,总结我们所得全部研究结论,可分述为以下四点:
1.1923年7月至1925年夏,穆时英在修能学社接受初中阶段的教育,学制为“初级四年”,然其并未完成学业。
2.1925年9月7日,其转入光华大学附中初中部,学习三年,直至1928年6月30日毕业。
3.1928年9月,其又进入该校高中部学习,但只读了一个学期,到了次年春季,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4.在圣约翰也只读了一学期,复经任诚推荐(时为1929年8月21日),于1929年9月14日转入光华大学,学习四年,直至1933年6月12日毕业。
至此,只剩其小学阶段的教育经历还是一空白之处,限于资料,目前我们无法进行哪怕最为简要的说明,只能留待以后搜集、发现新的文献资料时,再予探勘。
但透过上文的研究、叙述,读者应可发现:穆时英的教育背景不仅相当曲折、复杂,而且,在这曲折、复杂的过程中,其与光华大学(包括附属中学部)的渊源,最为深厚。穆氏所以取得令人瞩目之成就,原因当然复杂,但光华本身的环境、条件是一重要因素。
在其入读光华附中、大学期间,胡适之、徐志摩、梁实秋、田汉、吴梅、钱基博、吕思勉等新旧人物,皆曾到此任教;受邀前来发表讲演者,则有鲁迅、丁玲等人。彼时之光华,可谓孕育俊彦的沃土。本文所论穆氏之外,其同学潘光旦、沈祖牟、俞大纲、储安平、赵家璧、予且(潘序祖)、周而复、田间(童天鉴)、夏鼐、杨宽、张允和等,在学术研究、文学与艺术、教育教学等领域,或已开始崭露头角,或打下坚固基础,此后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他们成群而来,结队而去,而今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附 对本文研究资料的进一步说明
1951年10月,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等校)被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该校的遗产因此也被后者部分地继承了下来。本文所赖以研究的档案资料便是其中之一。回想起来,当笔者偶然读及《光华大学:90年90人》一书,实感意外,因其中对穆时英入学经历的叙述,不同于此前所有著作,而且言之凿凿,似非掌握严格、坚实证据者不足以道。
其后,有缘与这篇小传的作者、华东师大档案馆馆员吴李国先生晤面,始知其为撰写此文,竟查阅过许多一、二手资料,的确是行家里手。此后,承乏吴先生慷慨协助,遂得以有机会查阅该馆所藏光华大学旧档(特别是其中的穆时英学籍档案及任诚手札),复经与笔者搜集的其他资料参核,再三考证、辨析,先前许多疑团,始得涣然冰释。是次与吴先生的相识,让我欣悦地收获了一位来自同行的友谊,也激发了本人重新探究穆时英教育背景、经历的热情。
在此之前,就穆时英教育经历一题,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学者曾依光华大学校刊、新发现穆时英集外文等材料,做过一些研究,但说法不一,莫衷一是。直至吴文问世,在穆时英如何进入光华大学及其当时的身份若何这两个问题上,才算是有了新的突破。由于种种原因,该文并未对其叙述提供任一资料、证据,也未能专门研讨,难免使人心生疑窦;另一方面,诸如其进光华附中、圣约翰大学就读等教育背景,至今仍鲜为人知;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亦未予处理。但将穆时英其前其后所有教育经历联系起来,予以考察,既饶富趣味,给人以一波三折之感,又可为学界提供相当之参考,于是,笔者便萌生了撰写此文的念头,但既有吴文在前,自不敢掠美谓为己力,拙稿只可被视作对吴文的一个详尽注释,幸祈读者诸君察鉴。
注释:
①⑭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55页。
②据张耕华主编《光华大学编年事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可知,1925年9月7日,光华大学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
③秦贤次:《储安平及其同时代的光华文人》,《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笔者亦曾就相关问题,与秦贤次先生多所讨论,但仍未敢信服其就穆时英从学光华大学经历之结论。
④⑤代四同:《上海钱业公会修能学社初探》,《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2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5~66、67页。
⑥据张耕华主编《光华大学编年事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可知,1928年6月30日,光华大学举行本年度大中学生毕业典礼。
⑦对此,笔者的博士论文《穆时英文学新论》(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版)有较详细之论述,有意者可参考。
⑧关于“重绿”此文的初步研究,请参拙撰《“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其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⑨⑫⑬张耕华主编:《光华大学编年事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6,64,133页。
⑩关于光华大学1929年秋季招收“特别生”一事,目前只有一条材料,即《申报》1929年9月24日第28版《临窗的榻位》,该文称:“光华大学这次招收女生,有一百一十一名之多。其中除去正式生外,还有着特别生和试读生。”(张耕华主编:《光华大学编年事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但具体如何招收“特别生”,此文语焉不详。
⑪吴李国:《作家穆时英》,汤涛主编:《光华大学:90年90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