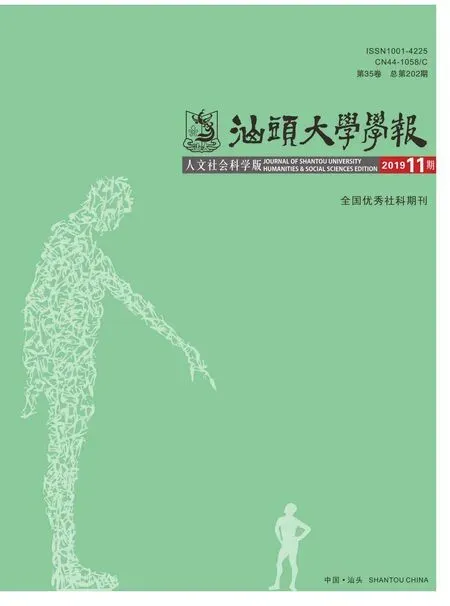论王骥德《曲律》的戏曲文体思想
徐燕琳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王骥德《曲律》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戏曲理论专著。它系统总结了元明以来特别是明代戏曲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门类详备、论述全面、组织严密、自成体系”[1]6,在戏曲文体思想上也颇有贡献。
一、《曲律》里“体”的含义
《曲律》一书,计有31 次提到“体”字,用法多种,含义丰富。其中有指曲调的类型的,如《论调名第三》所言无考之“古体”;有指诗歌之“体”的,如《论韵》说的“近体”、《论巧体》说的“巧体”。有指用韵的,如“用此体,凡平声每韵各赋一首”[1]203。有指整体风貌的,如“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1]256“体裁轻俊”[1]315“体调流丽”[1]317等。有指情节、主旨的,如“元人杂剧,其体变幻者固多”[1]247、“《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1]252等。又将“体”和“用”相对,如谓:“不贵说体,只贵说用。”[1]192这所谓“体”“用”,霍松林主编《中国诗论史》认为,“‘体’为物之形,‘用’为物所寄托、蕴含、透露的情韵”[2]。郑传寅认为,王骥德所说的“体”指的是外在的形迹;“用”指的是内在的精神[3],都涉及王骥德对戏曲文体的认识。
王骥德对“体”的用法,最多的是取“体制规范”之意。符合其“体”规范的,他称之为“得体”,否则“非体”。如称《琵琶记》的落诗“得体”,“每折先定下古语二句,却凑二语其前,不惟场下人易晓,亦令优人易记。”[1]224“非体”,包括用混了南北曲“韵”[1]244、【集贤宾】次调起句用八字[1]343等情况。王骥德也有“变体”之说,如谓《拜月》以两三人合唱,改变了南戏曲“每人各唱一只”的做法为“变体”[1]256。
王骥德认为的曲“体”,有不同的分法,如“文词家一体”与“本色一家”、“北剧”与“南戏”、“大曲”与“小曲”等。《论家数》说:
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1]154
“文词家一体”与“本色一家”对应。这里的“体”,是体貌的“体”。后文又说,“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二者不必偏废。如《琵琶记》者,“小曲语语本色”,“大曲引子……未尝不绮绣满眼,故是正体”,又批评《玉玦记》“大曲非无佳处”,而“小曲亦复填垛学问”,看来他所说的“正体”,关键是要求“小曲本色”[1]154-155。即:雅俗兼参,本色、文词合宜。二“体”之中,作者认为最优秀的作者是梅鼎祚、汤显祖。《杂论》有:
问体孰近?曰:于文辞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华掞藻,斐亶有致。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余则修绮而非垛则陈,尚质而非腐则俚矣。[1]332
《论剧戏》将“北剧”和“南戏”对称为不同的“体”,称“剧之与戏,南、北故自异体。”[1]206《杂论》称为“南体”“北体”:
余昔谱《男后》剧,曲用北调,而白不纯用北体,为南人设也。已为《离魂》,并用南调。郁蓝生谓:自尔作祖,当一变剧体。既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后为穆考功作《救友》,又于燕中作《双鬟》及《招魂》二剧,悉用南体,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也。[1]364
此言“北体”“南体”“剧体”,将北剧北调,与南词南调相对。可见认为它们是当时戏曲文体中体裁的两种。
此外《论过曲》亦将“大曲”“小曲”分为两“体”,分别要求。一个“宜施文藻,然忌太深”,一个“宜用本色,然忌太俚”[1]212。
二、《曲律》对戏曲体裁的认识
王骥德《曲律》一书里,并没有出现“文体”字样。从“体”字的出现和用法看,有文体学的含义,但也不限于文体学,其使用不拘一格、灵活自如。以王骥德对“体”的认识和理解,结合文中论述,他孜孜以求的,是戏曲体裁格式的规范,也就是文体的规范性。
(一)以“律”“法”匡正曲体,明确和强调戏曲规范
冯梦龙在《曲律》前的《叙》说,《曲律》的创作背景是作者云涌,“翻窠臼”“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也有创新太过、脱离了“曲律”即戏曲的规范,“乖体”的情况,以至“饾饤自矜其设色,齐东妄附于当行”[1]1,失去了戏曲这一文体正常和正确的作法。
王骥德《曲律自序》说明是书主旨:“曲何以言律也?以律谱音,六乐之成文不乱;以律绳曲,七均之从调不奸”[1]7,他要求“以律谱音”“以律绳曲”。《论曲禁》重申:“曲律,以律曲也。律则有禁。”[1]177《杂论》强调:“曲之尚法,固矣。”[1]264为此,他讲声律,说词调曲调不同,说南、北之律一辙,他赞扬沈璟“于曲学、法律甚精”,称赞“作北曲者,每凛凛遵其型范,至今不废”,批评“南曲无问宫调,只按之一拍足矣,故作者多孟浪其调,至混淆错乱,不可救药”,“不寻宫数调之一语”“开千古厉端”(《论宫调》)[1]92,爱憎好恶,十分清楚。
再看《曲律》一书对“律”和“法”的强调。全书中,“律”“法”二字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各达到90 多次。
先讨论“律”。“律”字,除了作为书名、作为“一律”“律诗”等固定用法,一般有两个意思:一是音律;二是律法。
其一,“律”字指“音律”者,有“声律”“律吕”“音律”“六律”“十二律”等这类名词,也可以单独使用,如“非字字合律也”(《杂论》),如“然古乐先有诗而后有律,而今乐则先有律而后有词”(《论宫调》)等。
其二,“律”字指“律法”“规范”者,如“曷其制律,用作悬书”(《自序》)“子信多闻,曷不律文、律诗,而以律曲何居?”((《杂论》))
其三,“律”字也兼有音律和律法的意思,如书名《曲律》中,既讲音律之法,又进行音律的规范。王骥德说:“曲何以言律也?以律谱音,六乐之成文不乱;以律绳曲,七均之从调不奸。”(《自序》)[1]7即是认为,“律”,既是谱“音”的规则,也是规范“曲”的方式。按照他的说法,“律”字单独使用时,只要是指音律、声律等意思,都具有“律法”“可以律之”的性质。
在“法”字的使用上,意思有几种:
其一,具体的方法、途径。如“章法”“字法”“句法”,以及“半字之法”(《论调名》)“旋相为宫之法”“古调声之法”“古谱曲之法”(《论宫调》)“反切之法”(《论平仄》)“唱法”“过搭之法”(《论用事》)“取务头法”(《杂论》)“歌法”(《杂论》)等等,王骥德列之甚详。
其二,由具体的方法、途径之“法”而来的泛指的规范、规则。如“布法益密,演数愈繁”(《自序》)“夫作法之始,定自毖昚,离之盖自《琵琶》《拜月》始。”(《论宫调》)“曲之尚法,固矣”(《杂论》)“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词隐之持法也,可学而知也;临川之修辞也,不可勉而能也”“夫临川所诎者,法耳”“然为法苛刻,益难中之难”(《杂论》)等。也有合具体的作曲唱曲方法、广义的规则规范二意者。如“乖其法,则曰拗嗓”(《论平仄第五》)。另外尚有“程法”“古法”“遗法”等,可指以上二意。
其三,师法、学习。这也是承接前面二意而来。王骥德认为,曲法应该成为师法的对象,因此《曲律》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用四平声字,此以中有截板间之故也,然终不可为法”(《论平仄》)。《论引子》说:“《宝剑》引子,多出已创,皆不足为法。”
在当时曲律废弛、“乖体”横行的乱象之下,明确、强调曲的“法”和“律”,就是要明确和强调戏曲的文体规范。因此,王骥德将作曲的要义分解成具体的不同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从规则讲授、古今演变、南北不同、品评比较等各个方面,逐一耐心讲解。比如《论平仄》,先述源流,然后说明“识字”是作曲的基础,反切是识字的先声,继而具体讲解四声,讲入声在南北曲的不同,讲“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韵》”的荒谬。然后讲“词曲之有入声”的妙处,说明南曲“不得以北音为拘”,又具体说其用法,举《琵琶记》《玉玦记》等例子,引沈璟的话,说明四声的具体使用。又说:“至调其清浊,协其高下,使律吕相宜,金石错应,此握管者之责,故作词第一吃紧义也。”[1]97-99
在《论阴阳》中,他将“阴阳”理论引入曲论,说明这是北曲《中原音韵》的组成,而南曲“久废不讲”“其法亦淹没不传矣”。他从道理到实例,具体分析字的阴阳、平仄、清浊的各种情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音律和谐[1]103。在《论声调》中要求曲调清、圆、响、俊、雅、和、流利轻滑而易歌。如何做到呢,他提出“其法须先熟读唐诗”,得“声调之美”[1]15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的来看,王骥德的论述,无一不是在批评和建设,说明曲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怎样是好的,好在哪里,怎样不好,为什么不好,怎么改进等。诚如其所言:“吾姑从世界阙陷者一修补之耳!”[1]375
(二)坚持曲本位,坚持曲体之“正”
明代的文学批评对文体比较重视,许多人认为是文章的首要问题。吴讷《文章辨体凡例》说:“文辞以体制为先。”[4]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认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4]77胡应麟《诗薮》说:“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5]21。他的意见是,文章的体裁,就是它的“本色”。只有本色的作品,才是当行。明代的戏曲家也提出,曲体与一般诗文文体不同。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认为:“词与诗,意同而体异。”[6]
王骥德对曲体的重视,对曲与诗、词文体不同的关注,体现在他对“曲本位”以及曲的“正体”的坚持。
《曲律》全书始于“曲源第一”“南北曲第二”,终于“曲亨屯”,其思路是从单纯的曲的创作出发,涉及和扩展到戏曲整体的创作和风貌。也就是说,他对戏曲文体的基本理解,是融合了音乐性和文学性的“曲”。
在《曲源第一》里,王骥德对戏曲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王骥德认为,“曲,乐之支也。”他对曲的乐源的理解,并非一般单纯的笼统的“古乐”,而是类似《康衢》《击壤》等这样有内容、有思想、能歌唱的乐歌。汉乐府、六代歌辞,进而合乐可唱的唐绝句,发展为《忆秦娥》《菩萨蛮》等,至宋词,金章宗时扩展为北词,元代发展为北曲。他认为,南曲乃入明后在元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兼美善、声调之致,为曲的顶峰[1]21。
王骥德以文体之间的递承嬗变的思想来解释戏曲的发展。文体递变,这也是许多明代批评家的共同思路,如胡应麟《诗薮》认为“诗之体以代变也”,又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5]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别流。今二家之辞,即譬之李杜。”[7]王骥德亦提出:“后《三百篇》而有楚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古杂剧序》)王骥德认为“南曲”为“北曲”之“变”,这个意见与胡应麟非常相似。胡应麟谓,戏文盖元人杂剧之变,“而元人杂剧之类戏文者,又金人词说之变也。杂剧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独戏文《西厢》作祖……至元王、关所撰乃可登场搬演。高氏一变而为南曲”[8]。
南戏的产生未必在杂剧之后,也并非杂剧的变体。胡应麟、王骥德称“南曲”为“北曲”之“变”,不符合历史事实①王骥德在《杂论第三十九下》里有“金、元之南北曲”的说法,能够对南曲的产生时间有所认识。曰:“《关睢》《鹿鸣》,今歌法尚存,大都以两字抑扬成声,不易入里耳。汉之《朱鹭》《石流》,读尚聱牙,声定椎朴。晋之《子夜》《莫愁》,六朝之《玉树》《金钗》,唐之《霓裳》《水调》,即日趋冶艳,然只是五七诗句,必不能纵横如意。宋词句有长短,声有次第矣,亦尚限边幅,未畅人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极之长套,敛之小令,能令听者色飞,触者肠靡,洋洋纚纚,声蔑以加矣!此岂人事,抑天运之使然哉。”《论部色》又引《梦游录》云:“唐为传奇,宋为戏文,金时院本、杂剧合而为一,元分为二。杂剧者,杂戏也。”估计前述“北曲变而为南曲”的说法是以文体递变说对南北曲的一种机械套用。。王骥德对曲的发展的梳理中,没有涉及表演因素,也是一短。但是,总的来说,用变化的观点来审视曲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王骥德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曲”是诗词之“变”,但却是从诗、词而来的一种新的文体。这是他超出胡应麟的地方。在他的概念框架下,王骥德提出,“曲”是与诗、词完全不同的文体类型,作法不同、风格不同,不能够以诗、以词为曲。他说:
今吴江词隐先生又厘正而增益之者,诸书胪列甚备。然词之与曲,实分两途。(《论调名》)[1]31
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诗人而以诗为曲也,文人而以词为曲也,误矣,必不可言曲也。(《杂论》)[1]284
曲与诗原是两肠,故近时才士辈出,而一搦管作曲,便非当家。(《杂论》)[1]296
王骥德对以诗为曲、以词为曲的现象非常不满。他举例说,汪道昆作曲,是下“胶漆”词。王世贞【塞鸿秋】【画眉序】之曲,“用韵既杂,亦词家语,非当行曲”。【画眉序】和头的第一个字,“法用去声”,却云“浓霜画角辽阳道,知他梦里何如”“浓字平声,不可唱也。”[1]296他坚持认为,“词之与曲,实分两途”“曲异于词”,不可“以词为曲”,也不可以诗为曲。这事实上是以坚定的态度,维护了戏曲文体的独立性。
(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的“剧戏”观念
虽然《曲律》的关注以曲为本位、以曲为戏曲的主体,戏曲的表演性、舞台性并不是论述的重点,但是,王骥德清醒地认识到,同时也明确地提出,戏曲的形成和它的特点,乃是“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1]255。《杂论》曰:
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喜笑,未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如今之戏子者。又皆优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习现成本子,俟主人拣择而日日此伎俩也。如优孟、优旃、后唐庄宗,以迨宋之靖康、绍兴,史籍所记,不过《葬马》《漆城》《李天下》《公冶长》《二圣环》等谐语而已。即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鸣呼异哉![1]255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首先,王骥德考察戏曲的发展认为,古代戏曲的雏形,不过古优人自创甚至即兴的诙谐滑稽,并无戏曲文本创作。在“古之优人”的表演这个阶段,包括先秦优孟、优旃的“葬马”“漆城”,后唐敬新磨的“李天下”、宋优人的“公冶长”“二圣还”等等,都不属于真正的戏剧。即使如《西厢记》,也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这样简单的故事讲述和演唱。其次,他认为,“剧戏”的形成是在元代,以剧本的出现为标志。他强调必须有“现成本子”即文字形态的、成型的比较完整的剧本。因元代词人“林立”进行创作,故“剧戏”“至元而始有”,“始称作者之圣”。这即是强调了戏曲的文学性,同时突出了戏曲文体的创立过程中,文学创作所起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三,他认为,“剧戏”②《曲律》所谈的“剧戏”,或以“剧”为杂剧、“戏”为南戏传奇,或泛指戏曲,甚至单独的“剧”或者“戏”字,也可泛指戏曲。,是由“曲”“白”“歌舞”三要素组成。由艺人“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将曲、歌、舞结合起来,文学性与舞台性结合起来,搬之场上。此处所说的“剧戏”,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的“真戏剧”的概念已经非常接近,是比较清晰、趋向成熟的戏剧观念了。
(四)“北剧”“南戏”的文体辨析
王骥德《曲律》认为“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总论南北曲》)[1]25。在“剧戏”的框架下,《曲律》将戏曲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北剧”和“南戏”。《论剧戏》提出:
剧之与戏,南、北故自异体。[1]206
南北戏曲文体之分,是《曲律》从一开始就反复阐明的观点。王骥德对南戏、北剧两种文体的划分,沿袭了文体递变的思路。在《曲源第一》里,他说,金时的“北词”《西厢记》等,在元代扩展体制、协调声律,成为“北曲”,即元杂剧。“北曲”使用北方的弦索和语言声调,不合适南方人。于是到明代时,“又变为南曲”,其风格“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他又说,南北鼎立的局面之后,南曲日盛,北曲渐微[1]20-21。
《曲律》综合了胡翰、吴莱、康海、王世贞各家意见,在《总论南北曲》部分从辞、地、声等方面,对南北内容、风格、演唱、伴奏等的不同进行了讨论[1]26(见表1)。

表1 《曲律·总论南北曲》各家论南北不同
对于北剧、南戏的体裁差异,书中有不少具体意见:
第一,南北语言不同:“北曲方言时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语所被者广,大略相通,而南则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则不能通晓故也。”[1]246第二,南北语音不同。这首先是北方语音中入声已派入平、上、去三声,南方还保留着入声,因此不能以《中原音韵》强制要求。王骥德说,入声在曲中变化多样,非常必要,“不得以北音为拘。”[1]98第三,南北用韵不同:“南曲之必用南韵也,犹北曲之必用北韵也,亦由丈夫之必冠帻,而妇人之必笄珥也。作南曲而仍纽北韵,几何不以丈夫而妇人饰哉。”[1]370-371王骥德认为,南曲用南韵、北曲用北韵,这是理所当然、不可更改的,如果乱用,就像男女异装一样荒唐。第四,南北用字不同。王骥德举例说,“者”“兀”“您”等字以及北韵“惟北剧有之,今人用在南曲中,大非体也。”[1]244第五,南北脚色不同。如《论部色》说,南戏的名色与元杂剧不同,作用也不一样。[1]226第六,南北风格不同。王骥德认为,北剧沉雄,南戏柔婉。在写作风格上,北剧看重篇章结构,南戏对句字比较注意。北剧的特点在气骨,南戏则是色泽[1]236。北词“如沙场走马,驰骋自由”,南词则“如揖逊宾筵,折旋有度”。他也客观地评述了两种风格的不足。认为前者容易“芜蔓”,而后者易倾向“局蹐”。因此除了要求南戏北剧符合自己的文体风格外,在创作中还要求详略得当,结构有力。[1]286第七,南北唱法不同。《曲律》称:“南戏曲,从来每人各唱一只,自《拜月》以两三人合唱,而词隐诸戏遂多用此格。毕竟是变体,偶一为之可耳。”[1]256第八,南北制题不同。王骥德根据他看到的资料总结说,杂剧命名经常三字标目,“南戏自来无三字作目者,盖汉卿所谓《拜月亭》,系是北剧,或君美演作南戏,遂仍其名,不更易耳。”[1]254
(五)对“南曲”的侧重和强调
虽然王骥德对南、北剧戏都有不少比较和讨论,但是,他作《曲律》并非为了平分秋色,实则是为南曲而作。《自序》首先强调曲律的重要性,继而陈述说:
惟是元周高安氏有《中原音韵》之创,明涵虚子有《太和词谱》之编,北士恃为指南,北词禀为令甲,厥功伟矣。至于南曲,鹅鹳之陈久废,刁斗之设不闲。彩笔如林,尽是呜呜之调;红牙迭响,秪为靡靡之音。俾太古之典刑,斩于一旦;旧法之澌灭,怅在千秋。[1]8
王骥德认为,北曲已经有了《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等明文规范,矩度严密,有章可循。同时,北曲和以弦索,若曲不入律,可以通过音乐鉴别,故作北曲的人可以“每凛凛遵其型范,至今不废”。而南曲“无问宫调,只按之一拍足矣,故作者多孟浪其调,至混淆错乱,不可救药”[1]92。他说,北曲作者,如王、马、关、郑等,“创法甚严”,而且“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踰越”。但是作南曲的人,从高明、施恩等人开始,就立法不严,“平仄声韵,往往离错”。他对此痛心疾首:“作法于凉,驯至今日,荡然无复底止,则南君不得辞作俑之罪,真有幸不幸也。”[1]260他批评道:“唐三百年,诗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词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兴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铮铮者指不易多屈,何哉?”[1]250
王骥德《曲律》的论述,时时结合南曲(包括南戏、传奇)来进行。他对南曲的重视,一方面符合当时理论不足、规则混乱、制作无序的状况,一方面也师承徐渭的意见。徐渭在《南词叙录》里为南戏抱不平:
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予尝惜之。客闽多病,咄咄无可与语,遂录诸戏文名,附以鄙见。岂曰成书,聊以消永日,忘歊蒸而已。[9]239
王骥德早年师事徐渭。王骥德曾与徐渭比邻而居,“仅隔一垣”。师生相得,往来频密。徐渭“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王“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徐渭对王骥德非常欣赏,《四声猿》的创作过程中直接征求了王骥德的意见。王骥德对徐渭及其作品则推崇备至,奉为南词第一人①虽然王骥德说“于南词得二人”,将汤显祖也列了进去,但是,纵观《曲律》全书,他对徐渭无一微词,而对汤显祖多处批判。见《论须识字》、《论讹字》等处。他对汤显祖的意见主要是在音律上。,称其“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曲律》中有四处言及徐渭,笔笔深情,笔笔崇赞。他说:“吾乡徐天池先生,生平谐谑小令极多……大为士林传诵。今未见其人也。”[1]199又将徐渭列入“今日词人之冠”[1]332。他誉徐渭为当代越词的领军:“吾越故有词派……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1]316,317,颂扬无以复加。王骥德对徐渭充满真诚的崇敬和怀念,《论俳谐》尚以“今未见其人也”淡淡道来,至《杂论》部分,则用充满感情的话语长篇书写:“先生逝矣,邈成千古”“刳肠呕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1]321。真情流露,溢于言表。
王骥德作《曲律》时无论年龄还是学术都已成熟,更能理解其师的思想和经历。我们将王骥德《曲律》与徐渭《南词叙录》的序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曲律》向《南词叙录》的致敬:
第一,创作缘由。徐渭《南词叙录》序称:“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王骥德《曲律》序称:“元周高安氏有《中原音韵》之创,明涵虚子有《太和词谱》之编,北士恃为指南,北词禀为令甲,厥功伟矣。至于南曲,鹅鹳之陈久废,刁斗之设不闲。彩笔如林,尽是呜呜之调;红牙迭响,只为靡靡之音。”第二,自身情况。时徐渭“客闽多病”。王骥德称:“余且抱疴,遂疎握椠……左持药椀,右驱管城。”第三,创作目的。徐渭序称:“咄咄无可与语……聊以消永日,忘歊蒸而已。”王骥德称:“世路莽荡,英雄逗遛,吾藉以消吾壮心。酒后击缶,镫下缺壶,若不自知其为过也。”
由王骥德对徐渭的高度评价和深厚感情,以及两篇序文思想、经历甚至语言结构上的相似,可以发现徐渭对王骥德《曲律》创作的巨大影响。徐渭“夷狄之音可唱,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的质问,也很可能影响了他的学生和后继者王骥德。可以看到,徐渭《南词叙录》主要是针对南戏名目的记录,而王骥德则从南戏、传奇所缺的曲律、曲法着眼,既是补南戏传奇缺乏曲律之缺憾,纠正时弊,同时也是为了继续徐渭的事业,为南戏传奇立法,令其开创的“南词”理论和实践发扬光大。
正因如此,王骥德将“南曲”作为文体之一,放在戏曲发展的大背景下,梳理它的渊源流变。他特别提出,南曲不能盲从《中原音韵》。他认为,《中原音韵》“故为北词设也;今为南曲,则益有不可从者。”他强调:“盖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从其地也。”[1]116“南曲之必用南韵也,犹北曲之必用北韵也。”[1]370-371王骥德摈弃“天下翕然宗之”的《中原音韵》,鼓吹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南方之音(韵)”,这在当时,是非常的革命,也是作为徐渭的后继者对南戏艺术的有力维护。
此外,《论腔调》也谈到南曲腔调变迁。王骥德认为,南曲的腔调风格最初“浑朴”“渐变而之婉媚”。他介绍了“海盐”“昆山”腔的情况,介绍了几十年的新兴的“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等声腔,以及他们演出的情况。但是他并不满意,批评“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严厉批评当时“世争羶趋痂好,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的怪现状。[1]133-134
王骥德同样对“气趋东南”、南盛北颓的情况作了描述。“始犹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何元朗谓:更数世后,北曲必且失传。宇宙气数,于此可觇。”[1]21这些意见从“史”的高度,对南戏传奇的演变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样成为《南词叙录》的有益补充和推进。
三、《曲律》对戏曲体貌的意见
(一)倡“本色”,论“文词”
本色之说,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明代李开先、徐渭、何良俊等戏曲家为了反对当时戏曲创作的流弊,纷纷倡导天然本色。本色论,是王骥德戏曲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戏曲体貌的基本要求。
《曲律》记载,王骥德的老师徐渭“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独不喜《玉玦》,目为‘板汉’。”从徐渭《南词叙录》提到“本色”的情况来看,徐渭的意见是,戏曲既不能俚俗,又不能有时文气,必须符合戏曲的文体规范,如其言:“《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9]243徐渭认为,这不是作曲,而是粗暴移植的腐臭时文。
许多批评家也谈到郑若庸《玉玦记》“失体”。臧懋循《元曲选》序谓:“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至郑若庸《玉块》,始用类书为之”,意思以类书为曲不合适。王骥德认为“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则失去了曲的清空之美[1]173。徐复祚《曲论》也批评这样的堆垛饾饤,“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10]237,而“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畯红女闻之而趯然喜,悚然惧。”[10]237-238
《香囊》《玉玦》这类作品,王骥德将其列为与“本色”相对的“文词家一体”,实则作为批判对象,以倡导“本色”的观点[1]154。但是,王骥德所言本色也是比较客观的,并非绝对禁止“文词”和“学问”。在《论剧戏》中,王骥德说:“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意思是,“本色”即是当行,是戏曲文体规范的的要求。同时他也认为,“本色”“当行”与“大雅”“雅调”“词藻工”相对,后者同样是构成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但是戏曲具有演出性,不是“案头之书”,不能“学究”。[1]207
王骥德举了汤显祖《南柯记》《邯郸记》的例子,说明“本色”和“丽语”应该相互参错,巧妙搭配:
临川汤奉常之曲……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溪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1]307
他甚至将“组艳”的《西厢记》和“修质”的《琵琶记》作为本色之至。他说: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1]252
《西厢》《琵琶》标准太高,一般人不好学。作为一部旨在说法、传道、教授天下的律书,王骥德的意见是,如果一律使用本色,“易觉寂寥”;而如果纯用文调,则伤于琱镂,应该兼参之,用得其所,用得恰当。具体来说,大曲引子可以文词优美蕴藉,小曲不必[1]154-155。在《论过曲》中,他再次强调:
过曲体有两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1]212
王骥德对“本色”的“谐里耳”,有不少论述,认为“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妇,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始称通方。”[1]212“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1]272但是本色、“质”“谐里耳”不是“太俚”“非腐则俚”[1]332,不是仅仅“凑插俚语”“张打油”[1]229,也不是一味“粗豪”[1]265。《曲律》具体讨论了一些作法,说明怎样是“本色”,怎样不是;哪些用得好,哪些不好。如:
夫《琵琶》久用本色语矣,(“岂忍见公婆受饿”)饿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韵为快耶?[1]229
(《琵琶》)“书寄乡关”二曲,皆本色语,中着“啼痕缄处翠绡斑”二语及“银钩飞动彩云笺”二语,皆不搭色,不得为之护短。[1]257
王骥德进一步说明,“本色”与“文词”都不能绝对,不能偏废。本色太过,“易流俚腐”。而文词之病,在于“太文”,就是失体了。
王骥德的意见,“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戏曲是要写人物、写故事、写现实生活的,必须要体贴人情物理,代为陈说,不能自说自话。他并非一昧反对戏曲语言的文采,也不机械地提倡俗俚,“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1]154-155
(二)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
《曲律》不同于以往许多曲学著作的原因,是它超出了单纯论曲的做法,将戏曲的舞台性、演出性纳入了研究范围。他说:“词藻工,句意妙,而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1]207但这并不代表对戏曲文学性的排斥。“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是王骥德对戏曲体貌要求的重要理论贡献。
王骥德以昆山腔为“南曲正声”,斥南曲末流“江河”日下、“婉媚极矣”,痛心疾首“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而世争羶趋痂好,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1]133-134世人缺乏辨识力,“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这话说得很重,表明的意思是:尽管戏曲是要搬演的,要让人听得懂、看得明,要本色当行,但是,并不是众人叫好、个个盲从的就是好的戏曲。这是该书第一次提到“大雅”。
紧接着,《论须读书》贴心地提供了令戏曲创作趋于“大雅”的方式:
词曲虽小道哉,然非多读书以博其见闻,发其旨趣,终非大雅。[1]152
王骥德的意思,词曲是“大雅”之声,一般人是不能作的。他明确地说《曲律》“不为担菜佣、若咬菜根辈设”[1]375。他以词曲为“文人能事”[1]392,创作者首先得是“文人”。这与《太和正音谱》记载赵孟頫强调“行家”“戾家”的划分,强调杂剧乃“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的文人曲观一脉相承。他自己即是以词曲为人生寄托,倾力为之。曾作《别友》云:“上皇都不辞劳,原不为谒候门卖弄风骚。逍遥,成越鸟,只待赋三都觅个修词料,并燕市西来结酒豪。”[1]392又说,元代士流耻于为教坊乐工修改,故当时的戏曲多猥鄙俚亵、悖理不通[1]245。
强调读书、强调“大雅”,是王骥德的一贯思想。比如香雪居《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中,他批评“绘图似非大雅”,“俗工”“益憎面目”[1]452;评语谓:“实甫要是读书人,曲中使事,不见痕迹,益见炉锤之妙。今人胸中空洞,曾无数百字,便欲摇笔作曲,难矣哉!”[1]456读书,王骥德认为是直接提高创作者水平的重要方式。怎样读呢?他说,需要读历代诗、词、曲的经典作品,从《诗经》《离骚》、汉乐府、汉魏六朝及唐诗,以及《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一直读到金、元杂剧诸曲,甚至还需要读古今诸部类书,熟读博参,“博蒐精采,蓄之胸中”。文学经典、各方面知识积累丰厚了,将其“神情标韵”融入自己思想,配合宫商律吕,则写作时自然就有“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奔腾千里。他赞扬“胜国诸贤,及实甫、则诚辈,皆读书人,其下笔有许多典故,许多好语衬副,所以其制作千古不磨。”他批评学而未通者“卖弄学问,堆垛陈腐,以吓三家村人”,就是根本没有读到书的精髓,不过将读书作为炫耀的手段、吓人的本领。“古云:‘作诗原是读书人,不用书中一个字’,吾于词曲亦云。”[1]152
在对“大雅”的论述中,王骥德借用了当时许多诗学思想。所谓“熟读”,是明人重要的学诗法。如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熟读”“博取”“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11]1,胡应麟《诗薮》也有“熟参《国风》《雅》《颂》之体,则《郊祀》《房中》若建瓴矣;熟读《白云》《黄鹄》等辞,则《相和》《清平》如食蔗矣”[5]14等说法。王骥德又将诗歌的审美移诸戏曲。《论声调》认为曲是否“美听”,即美感表现,取决于声调。王骥德将“曲之调”比喻成“诗之调”,以公认最为富于生命力、最俊朗豪迈、“音响宏丽圆转,称大雅之声”的初盛唐诗歌作为曲应该效仿、追求的标准和对象。对于中、晚唐诗以及宋元诗歌,王骥德认为渐趋而下,若“以施于曲,便索然卑下不振”[1]157-158,因此不必学、不能学。这也借鉴了当时的诗歌批评。
王骥德对初唐盛唐的追摩,渊源有自。他在《杂论》中将严羽的诗论作为当行本色论的创始,提出玄而又玄的“妙悟”“大乘正法眼”让创作者自行去体会。在具体如何作曲这件事上,他也多有借鉴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成果。[11]
如论路头,《沧浪诗话》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诗辨·一》)《曲律》称:“故作曲者须先认其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论家数》)
论师从,《沧浪诗话》称:“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诗辨·一》)《曲律》称:“……及汉、魏、六朝、三唐诸诗……俱博蒐精采,蓄之胸中。”(《论须读书》)
论读书,《沧浪诗话》称:“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辨·一》)《曲律》称:“须自《国风》《离骚》、古乐府及汉、魏、六朝、三唐诸诗,下迨《花间》《草堂》诸词,金、元杂剧诸曲,又至古今诸部类书,俱博蒐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其神情标韵,写之律吕,令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与剿袭口耳者不同。”(《论须读书》)
论熟参,《沧浪诗话》称:“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诗辨·四》)《曲律》称:“其法须先熟读唐诗,讽其句字,绎其节拍,使长灌注融液于心胸口吻之间。机栝既熟,音律自谐,出之词曲,必无沾唇拗嗓之病。昔人谓:孟浩然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秦少游诗,人谓其可入大石调,惟声调之美故也。惟诗尚尔,而矧于曲,是故诗人之曲与书生之曲、俗子之曲,可望而知其概也。”(《论声调》)
论上下,《沧浪诗话》称:“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此乃是从顶头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诗辨·一》)《曲律》称:“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论剧戏》)
在《曲律》中,他以文人身份、诗学角度,倡导传统文艺审美中的雅、才、情、致等观念,一再提到“大雅之士”,将他们与一般的“优人及里巷小人”[1]241“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郑、卫诸风”[1]249“烟云花鸟、金碧丹翠、横垛直堆,如摊卖古董,铺缀百家衣,使人种种可厌”的“小家生活”[1]268-269相对。因此《曲律》里的一些意见,也能够反映他欣赏的的风格:第一,作曲如美人,须色色妍丽,事事衬副。[1]362第二,词曲应该妩媚闲艳,不尚雄劲险峻。[1]363第三,曲以婉丽俏俊为上。[1]288-289第四,意新语俊,字响调圆;有规有矩,有色有声;烟波渺漫,姿态横逸;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1]183
由于《曲律》的创作主要针对南曲,而王骥德对南北风格的讨论中已经为南曲定下基调,即“雅”。书末《论曲亨屯》,列出了王骥德欣赏的若干情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和当时的文人旨趣:华堂青楼之中,名园水亭之旁,有雪阁、有画舫,花柳轻拂、微风送爽,月色郎朗。美人启动娇喉,少年曼声歌唱,伶人知音晓文,名士雅集,丽人相伴,诗篇相与,走笔新声,有美酒香茗,有明烛珠箔,倚箫合笙,有慷慨的主人,有勤快的奴仆,有精美的篇章……这果然是文人才士理想的创作环境、赏曲生活呢。
《曲律》一书以“说法”的态度,来“传”曲之大道①《曲律·杂论》称:“既取余故所赋曲曰《方诸馆乐府》者卒业,辄拍几叫绝,谓:‘说法惟尔,成佛作祖亦惟尔!庄生有言:道在荑稗,在蝼蚁,信哉!其识吾言简末。’戏为笔此。”毛以燧《跋》记载,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释:《曲律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375 页。。作者王骥德鼓舞“壮心”,不惧“俾高者驾言为小乘之缚,卑者贳辞为拘士之谈”,“左持药椀,右驱管城”,“制律”“创法”以“严”,“用作悬书”,目的是要“人持三尺,家作五申,还其古初,起兹流靡。不将引商刻羽,独雄寡和之场;《渌水》《玄云》,仍作《大雅》之觏”[1]8-9。他以曲为己任,“穷其元始,究厥指归”,“精探逖揽”、筚路蓝缕,历十数载而成《曲律》,可谓其半生心血结晶。天启三年(1623 年)“先生病,入秋忽驰数行”,将刊行《曲律》之事委诸挚友毛以燧,曰:“寖久法不传,功令斯湮,正始永绝,吾用大惧。今病且不起,平日所积成是书,曲家三尺具是矣。子其为我行之吴中。”毛以燧遵嘱付刻,“方在校刻,而讣音随至,兹函盖绝笔耳。”[1]380
作为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戏曲理论专著,吕天成谓《曲律》“起八代之衰,厥功伟矣”[12]207。朱东润称王骥德“直为一代巨眼”[13]221,“无幽不显”[13]222。综观全书,王骥德对“体”的认识,对戏曲规范的强调,他的“剧戏”观念、他“大雅当行参间”的戏曲思想,以及坚持曲本位,坚持曲体之“正”,他对“北剧”“南戏”的文体辨析,以及重视南曲、倡“本色”、论“文词”等文体实践都深可赞叹。可以说,《曲律》一书是当时戏曲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古代戏曲文体观念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