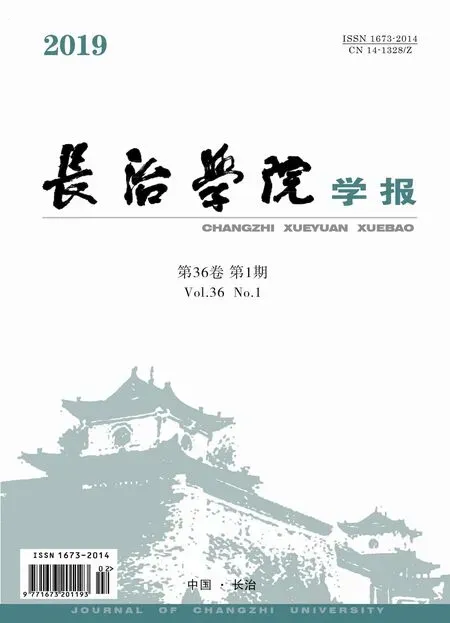浅谈中晚明江南地方生员力量的崛起
王丹妮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广东 广州 510055)
过去与生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以及社会阶层的研究。日本学者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二是“地域社会”中乡绅力量支配问题。西方汉学界主要集中于对中国传统绅士的研究和对科举考试及其“社会流动”的考察。以往研究重清代,轻明代。重视把握绅士的上层,即缙绅,忽视对绅士下层的研究。文章拟就对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地方①“江南”的概念,文章采用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中的概念界定: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生员②生员,即绅士的下层。既指中央国子监的“国学生员”,同时也指获得最初一级功名的地方政府学校的学生。我们俗称“秀才”。在地方事务的参与、中晚明社会新局势下的新动向、易代之际的文化坚守等方面对其群体活动进行分析与探讨,凸显江南地区生员层在中晚明以后社会中的影响力。
明季江南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且科第兴盛,形成庞大的士人群体。而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发生普遍性变化,作为士绅群体下层的生员层,经济状况逐步恶劣,与士绅群体的上层因在利益方面形成对立,进而相对独立出来。同时,根据陈宝良的考察,明末全国生员数为497031人,加上三氏学及综学生员,大致50万,约占人口的0.38%—0.46%。[1]215-216可见生员人数在明中叶以后的庞大。面对如此庞大的生员基数,作为其仕进之途的科举制度,在录取数量上并未有所明显增长,因而在生员身份持有上相对稳定。再加之明中叶以降,学校建设废弛,多数生员从学校流入社会中。及至明末,生员人数大增,作为文化重地的江南地区,更是形成众多的生员社团,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到全国。
一、参与地方事务的常规性活动
按照明代制度,士各有分。绅士入仕,担纲家国大任。生员则在明朝被认定为不应参与国家事务。然而,生员作为初级功名持有者,在地方社会中具有一定威望,他们以道自持,参与到地方性事务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饮酒礼、乡约宣讲类公共事务
洪武年间由官方规定,乡饮酒礼作为一种民间礼仪。从洪武五年推行之时,即有生员参与其间。由府州县长吏主持乡饮酒礼,而诸生可与与礼之宾共同推选与礼宾客。此外,生员还参与春秋二仲丁祭祀先师或乡贤祠祭丁。明代松江曾是国学生员的何良俊记载“余新入学时,每一祭丁,则众议沸腾。有轻俊好讥议者,临祭时常以文通神主置于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谓斥去之者”。[2]143另外,生员也参与到地方讲乡约之事,并且对于约正、约副人选,有权与学官在公堂共同商议,共同推举。生员频繁参与到一些地方事务中,提高了生员在地方上的威望,进而在地方事务中的参与得到民间公众认可。
(二)地方社会中的各类具体事务
首先,表彰先贤,勉励后人,生员均有权参与推举乡贤、节妇。“有未举者,诸生商榷举之;举之未正者,商榷请废之”。[3]18第二,生员可以自由出入衙门,一是包揽词讼,嘱托公事。二是评判官员,甚至左右地方官的升黜。第三,明代生员按照正常程序,通过具呈民间利病,而参与地方事务。当然,生员作为已经拥有初级功名的知识分子,在乡里间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每当乡里有徭役争讼之事,往往由生员出面调解。此外在明代,地方官员在任期间热衷编纂地方志,认为这是一项记述当地历史沿革、表彰地方先贤、发掘弘扬地方文脉的重要文化业绩。而编纂方志过程中,生员在其中承担了大部头的实际工作。生员参与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也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对生员力量的认可。
(三)生员与言责
朱元璋创立明帝国后,对生员参与朝政显示出抗拒与排斥。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禁例共计12条,期望生员能够潜心修学,远离政治。明确规定“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4]452生员虽受禁例约束,却往往有以身试法者来挑战这样的权威。在明中叶以后,出现不少生员上书议论政事之状况。天启年间,魏党专横,生员于此不平者甚众,尤其南方生员更为活跃。嘉兴县贡生钱嘉征参魏忠贤十大罪疏,道“忠贤封公,膏腴万顷。”[5]81生员言事在明中叶以后,虽朝廷屡有禁令,但以身试法者不胜其数。“生员言事,卧碑有禁。而吴下弟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赃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6]14b-15a可见,生员通过上书言事等渠道实现个人的声音表达,尤其是江南地方生员的活跃,他们以道自任,试图以此将个人政见渗入到中央,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期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二、书院、讲会与生员社盟
相较于缙绅可以仅凭一己之力便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而言,生员层则需要借助群体和舆论的力量在明代地方社会中产生作用。中晚明大量兴起书院、讲会以及生员社盟,生员都参与其中,并对地方社会产生影响,甚至于这种影响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而遍及全国。
书院之制,明代无设明制。明初虽有书院,其风不盛。明正德间,王守仁聚集生徒讲授良知之学于江浙两广之间,书院之风兴盛。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在江南落成,“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7]6032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时江南士人们独立批判意识的萌生。明代学者大多在书院兴讲会,设坛讲学。在这些讲会中,江南各地方生员纷纷闻声而附。书院及其所属讲会,事实上起到了向生员灌输知识、儒家道德的功能。而一些学者在书院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持清议,俨然成为在野政治力量活动的中心,而这股力量的兴起离不开生员庞大群体的支撑。明代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间、万历初张居正当政期间、天启年间三次禁毁书院,无不说明当政者对书院怀有一种疑惧心理。
自古以来,公论出于学校。到了明中后期,学政废弛,公论转而出于社盟。生员社盟干预政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声气”与“清议”;二是通过社稿或选政,把持科举进身之阶。[8]32-33明代士人的文会多种多样,至嘉靖、万历以后,明代士人会文已蔚然成风,在当时多是为了改变学校败坏,挽救士风、士习。至崇祯朝更是文社四起。明末学者张履祥曾言“其以文社鼓煽,岁穷乡邃谷,无不至者,好曰声气”[9]17b张溥创设的复社在生员中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10]83明末的生员社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代政局,明末学者吴麟徵有言:“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份。”[11]2生员纷纷入社,将其看做是仕进之途。社盟声望,于此可见一斑。
三、晚明学变
学变,主要指生员群起闹事,而实际上,伴随晚明社会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传统社会内生的诸多问题不断出现,“学变”并非无端生事,大多事出有因,对社会不平之事提出抗议。学变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而生员在其中则是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乐年间,便有生员骂内使的案例。[12]781到了晚明,生员闹事,学变不断,直至明亡。成化十九年,太监王敬以采办药材、书籍至江南,大肆其恶,至及于士类,激起三学师生愤怒,“诸生乃大噪”。苏州府学生员赵汴“指敬面而骂之”,道:“汝辈扰害百姓不已,又欲害吾儒生耶?”事后,赵汴等二十人以此坐罪。[13]451隆庆元年,无锡知县韩应元以某事不厌众心,导致诸生大哗,面加唾辱。是年,常州李知府亦为五邑诸生合击,“几毙于市”。[14]8a万历年间主要是反对矿监税吏,万历二十年,浙江嘉兴府学生员吕协祖等因嘉兴府通判征税过于严酷而发生暴动,城内400余人群起响应。[15]404从以上文献中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俗语云:不平则鸣。生员学变都是事出有因的,并非无理取闹,反映出生员层对于现有社会状况或者当局者的一些不合理举动所表现出来的逆反与抵抗。
四、易代时空下的文化影响力
回看明末清初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地区的遗民群体,顾炎武、黄宗羲、归庄等众多易代名士,大多是只具备低级功名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表彰明末抗清志士和遗民的民族气节和忠义大节。他们在易代环境中创设文化阵地、以诗文会友,著书表彰气节之士、通过参与光复旧朝的实际斗争中践行士的文化担当与对道的坚守。正是他们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表达,有效弥合了易代时空下士人与新朝统治之间的隔阂,与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谋而合。可以说,很多只具备初级功名的生员群体在易代鼎革之际于文化传承上产生强大而久远的影响。
顾炎武,昆山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崇祯年间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在明覆亡之后,投入光复旧朝的战斗中。顺治六年,惊隐诗社于江西吴江成立,顾炎武、归庄等都参与其中,是政治意味极为浓厚的社团之一。他们于此抒发感怀旧朝之情,以名节相砥砺。秘密进行抗清活动。他于全国各地奔走联络,结交各地正身之士,交流学问,砥砺志节。他还曾六谒孝陵。在复国无望之时,拒绝清朝官方的招揽。他用自身行动践履了士之致于道的担当,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如果不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就不只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要维护儒家文化的道统,维护大节不亏,这是天下士子、普通百姓必须坚持的大义。
黄宗羲作为明遗民,与顾炎武有近乎相似的易代际遇与表达。他终生坚守明遗民的身份,不仕新朝,并在文化领域造就卓越的贡献,著书立说、表彰先贤。他为谢泰阶写的墓志铭也表达了他在文化意识领域的坚守与标榜。他说:“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又说:“自有宇宙,祗此忠义之心,维持不坠,但令凄楚蕴结,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无字为成亏耳。君之子孙,可置勿悲。”[16]213谢泰阶临终将平生所著一烧了之,有人以为可惜,黄宗羲认为不必以有字无字为成亏,谢泰阶的忠义之心应予表彰。
归庄,昆山人,明末诸生,与顾炎武相友善。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在昆山参加抗清起义,后失败。他将自己居所名为“己斋”,意与新朝划清界限。在他的诗文中,抒写对前朝眷恋之情,表明自己反清复明之志的诗文不胜枚举。他在《元日三首》中如是说:“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终有气干霄”[17]66他的作品《悲昆山》[17]38,更是展现了清军南下欺凌百姓的血泪场景。
顾炎武、黄宗羲、归庄等出身江南的易代名士,他们通过自身的遗民实践、对抗清志士和明代遗民的民族气节和忠义精神的表彰、对文化创造方面的孜孜不倦,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江南地域的局限,产生广泛影响。清朝官方对此也逐步加以认可。康熙十七年,康熙帝决定明年开博学鸿儒科,招揽天下名士。乾隆年间,张廷玉总裁、万斯同主笔的《明史》得到清朝的颁布发行,后来又专门编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上升到纲常名节的理学范畴,从意识形态上对一大批抗清志士和明代遗民给予肯定。清朝通过对抗清志士和明代遗民的认可和表彰,使社会意识形态达成统一,成为清朝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结语
在明中后期时,面对社会普遍性变迁,江南地区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区域,生员群体显现出自己在地方社会中强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参与在地方社会中的常规性活动,通过书院、讲会以及社盟活动等群体性活动操纵社会舆论,实现对自身身份的标榜,对儒家道统的传承。行至晚明,在江南地区大量兴起的学变,则是生员群体通过相对激愤群体性活动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不满,体现了其在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与声音表达,是江南地方生员势力膨胀的重要表现。易代之际,江南地区的遗民名士致力于坚守儒家传统文化与适应新朝之间所进行实践,更是与清廷的官方行为之间有效弥合进而统一。总而言之,江南地区的生员群体,在中晚明以后的社会中呈现蓬勃力量,并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以明代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