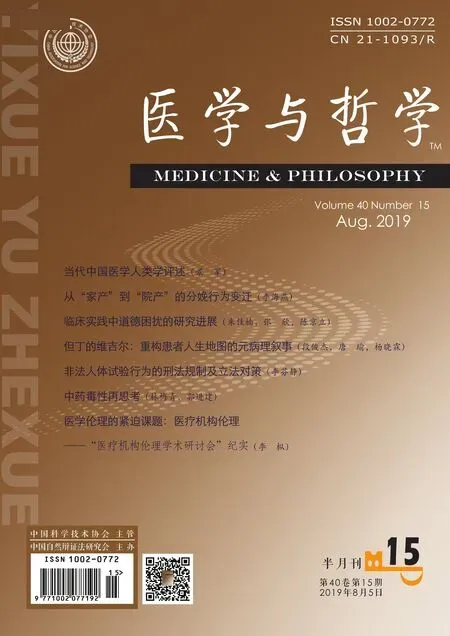对象化、非对象化的道与针灸
张 雯 李 瑞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表现为突出语法,而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更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通过语法把握语言这种方式是极其对象化的。然而,“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不变的本质,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普遍化的东西”[1]70,从而形成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哲学的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都是对象化的思维。到了现象学,摧毁和消解西方的存在论历史,提出“现象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放弃一切现成理论构架,返回到人的直接体验中去,对于海德格尔,这就意味着回到人实际生活体验的原发视野中”[2]403。
西方医学具有西方哲学影响下的科学思维特征,是一种科学对象化思维,通过将外在世界充分对象化来实现人的掌控,然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正好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本身是非对象化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医在技术上从非对象化主导转变为对象化主导,导致针灸的物化。
1 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道
1.1 对象化
对象是与“主体”相对的客观存在。对象化是指将与主体相对的一切存在固定化,使之成为一个确定的、固定的对象。是主体对客体不断物化与外化的过程。对象化是认识论的必经过程,是人认识世界的必然要求[3]286。《吕氏春秋·察今篇》中刻舟求剑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从掉的地方做标记去寻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对象化行为。人的经验总是有所作为,总是不停地寻找对象,导致对象化。
1.2 非对象化
非对象化不是将“世界”看成一个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人在世界中“浑然处世”的主客未分的生存情境和生活状态。它既非客观的实体,也非主观的境界。主体客体完全没有分开,不是把物当作客体,而且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是一种更原本的认知方式。非,是一种否定式的命题,亦是老子的“反”思维。反即返也,反面即返回也,意味着我们在反面和返回中把握出“道”来。
康德[4]在《纯粹理论批判》提出“transcendental object=x”。邓小芒将“transcendental ”翻译为“先验的”。牟宗三将其翻译为“超越的”,即超越的对象x,他提出时间是没办法对象化、分主客的,时间是流动的,就好像孔夫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一样,当盯着某个时间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
海德格尔[5]在《康德书》中提出“非对象化”概念,在《存在与时间》用锤子说明了一种“上手状态”,“例如用锤子来锤,并不把这个存在者当成摆在那里的物进行专题把握,这种使用也根本不晓得用具的结构本身”。而且“对锤子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子的动作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这种上手状态就是非对象化的,在这种状态下,并没有把锤子当作客体,反而是意识不到它存在的,越是这种状态下,锤子反而用得“得心应手”。
港台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6]指出海德格尔entgegenstehenlassen或e-ject是“使一物成为对象成为可能的东西”,是“超越主客对应关系的特殊的对象”,是“以其自己而展现其自己”。他认为这是“主客未分、物我为一”的状态。但是他与海德格尔不同,“他从主体出发,将此境界看成人的虚静状态,在此心境,物我合一,也是非对象化的”[7]。
张祥龙[1]256引入现象学,他提出现象学是“面向事情本身”的一门学科,他将“道”诠释为“非对象化的境域”,他指出“人的经验总可以有所作为,总可以期待视域的合作,而向各个可能的方向转化、特化、确定化或异化,被实现出来;一实现出来它就异化了,说出了一个‘什么’”。他进一步说明非对象化的状态是一种“在反思之前,对象化之前,在主客区分之前,也就是胡塞尔讲的边缘视域状态。生活里头的吃饭、穿衣,你都是在边缘视域里完成的,你根本不是拿它当个对象,根本不去注意它,它自动就出来了。一句话,对于观念化的东西、对象化的东西,我不计较它,我无视它,但是我并没有消除它,它潜藏着”。
林光华[3]344-345引入张祥龙的理念,对老子的文本进行阐释,并提出老子之“道”有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两种,她指出常道与非常道分别对应非对象化的道和对象化的道,她指出对象化的道是由常道派生而来的供人们利用的规律、原则与方法,它有死、有名、可违,而非对象化的道是创生万物并使万物按其本性生成发展的先在者与恒在者,它无死、无名、不可违,她提出老子之道的非对象性,两者并非对立,而是道的两种不同状态。
笔者试着将“非对象化”概念引入中医来,还原我们忽略的古代中国哲学本有的智慧。
1.3 道之对象化
道之对象化是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去把握“道”,包括数理、逻辑、概念、推理等。林光华[3]288解释对象化的道在整个《道德经》里具体表现为“规律之道”、“处事之道”与“治国之道”,三者分别代表了老子在认识论、人生论与政治论上的主要观点。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弱者,道之用”,“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都是一般的规律与方法。后世以数理逻辑建立的学科亦是对象化的,特别在西方科学思维影响下的当今中国的学科,如后文提到的逻辑学、诠释学、语言学以及现代针灸学科如实验针灸学都有很强的对象性的特点。
1.4 道之非对象化
“道”本身是在主客二分之前就存在的,“道”是“恍兮惚兮”的,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固定的,这一特性可以概括为“非对象化”。林光华[3]286提出“非对象化之道不是为任何人、任何社会而存在的,它本来如此,纯任自然,人们可以感受它、领会它而生活得更智慧、更有意义感,但却始终无法将其对象化、具体化与固定化”。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的“道”就是非对象化的道。我们常说的“体道”和“悟道”也都是在这样主客合一的状态下得以实现的。
1.5 非对象化走向对象化
恰如《老子》第一章所言,“非对象化”之道必然要走向“对象化”之道,“道生一”第一步就是创生。“道”生出了“一”,也就有了“名”,就开始走向对象化了。“随着人的产生,语言的不断逻辑化与理性化,人对世界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不可说的道被分解式地说出来,非对象化的道会走向对象化,成为可供人认识与利用的一般的道,即人们常说的规律、原则、方法等。”[3]288如《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与万物建立关系的过程,是从一开始的混沌,到逐渐将其对象化,去摸索其中的规律与方法,然后将这“对象化的道”应用于实践中。由非对象化走向对象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万物。
2 对象化的道在针灸中的应用
2.1 西方文化指导针灸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体系渐渐渗透,西方在经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法学、历史等众多领域兴盛,中医界也不断引进西方人文学科,对中医原典的解读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尝试。如语言学,贾春华[8]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认为中医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中医经典理论;逻辑学,包括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演绎推理的传统逻辑方法,数理逻辑、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等基础逻辑方法,以及以基础逻辑作为研究工具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和认知逻辑的当代逻辑方法,孙超[9]在《逻辑学研究方法在中医领域中的应用》有详细论述,本文不赘述;特别是西方哲学引入,如上文提到的现象学,用其来沟通中国哲学,进而用来指导中医原典;如诠释学,借用现代诠释学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开创了中医诠释学,如邢玉瑞[10]用诠释学来解释《黄帝内经》,张涛[11]用诠释学来解释《伤寒论》;考古学,使用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中医理论,如李成卫[12]用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解释《伤寒论》并指导临床疾病的研究。虽然以上部分中医经典理论并未直接涉及针灸,但是可以用其理论来指导针灸,同时有待学者将其理论在针灸上进一步结合与应用。
这些都是将中医抽象出具体概念,从语言、逻辑、考古、哲学等不同的角度,将中医经典作为特定的对象,将其对象化解释。
2.2 西方医学解读针灸
西方医学包括人体解剖学、系统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病理生理学、医学免疫学等都广泛应用于针灸的研究中,学科与学科的交流以及多学科的交互打开了针灸研究的新方向,开拓了针灸研究的思路,带动了针灸的发展,但是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引导下的科学思维,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对象化的,它将人体各个层面分别对象化,来实现对人体的掌握。
2.3 实验的方法
“实验研究是根据客体目的,利用仪器和设备对研究对象进行积极干预,人为地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以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上对其进行观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方法。实验中人们处理的是在人工控制下自然的或特定条件下的医疗研究过程。”[13]实验研究设计基本要素是处理因素、受试对象、实验效应。上述基本要素,针灸以及引入的技术都是通过实验者将其对象化而进行的。
2.4 临床的方法
现今针灸临床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回顾性研究、序列试验设计、单个病历研究、针灸的临床核查。几种方法皆是以观察者作为主体,以研究过程为对象,如随机对照试验以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为研究对象,将两组疗效差异进行比较的试验方法;队列研究是以未发生研究结局的队列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队列的研究结局发生率进行测量和比较的试验方法;回顾性研究是以特定时间段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回顾性观察的试验方法;序列试验设计分为研究时间前瞻性和回顾性,前者是以某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前瞻性的干预措施,并进行前后对比,总结疾病发展变化规律或疗效观察的试验方法;后者将现有的病例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整理,总结出临床诊治规律或观察疾病的变化规律的试验方法;单个病例研究是以有个体差异的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的疗效的试验方法;针灸的临床核查是以特定患者或特定疾病为研究对象,评价治疗方法与治疗结果的关系的试验方法[14]。
上述除了研究对象是一种对象外,涉及到的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亦是主体观察的客体,即对象。西医指导下的临床试验都是科学化思维下的产物,都是主客二分,对象化的思维。很像一种上帝俯视的角度,不仅区分了客体,也拉开与客体的距离,强调过滤掉人的主观性。
3 非对象化的道在针灸中的应用
3.1 内经以意和之
《灵枢·九针十二原》“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汉代名医郭玉亦说:“医者,意也。”中国哲学是非对象化的,中国哲学影响下的中医思维是意象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对中医理论的把握,一定是酝酿出来的,是“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的。意和的状态,并不将理论化的物当作对象,而是主体客体不分的状态,是内化于心的状态,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一种妙境,是非对象化的。
3.2 导引行气
针灸之妙,在调神与气。为了提高针灸临床,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导引对针灸人是有所裨益的。导引能更好地体会经脉循行,它来自人的直观体验,是主客合一,是非对象化的,非“二手资料”(非他人经验亦非理论抽象)。恰如高式国先生[15]在《针灸穴名解》一书中所言:“对经穴之认识,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又复察其流注敛散,而知其性能。其中妙义,俱由自觉而知。”导引能更好锻炼医者自身的身心,不仅能激发经气和腧穴的开合,更能疏导经络气血流注和协调脏腑平衡,这样能更加灵敏细微地沟通天地;导引之目的,在于使人归于“中庸”,一个拥有中庸气质的医者,能“空空如也,叩其两端而竭焉”,更好地了解病情,能更好地沟通患者。
更好地沟通天地,沟通病人,从而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这种情况下,针灸、经络,天人都不是医者的对象,而是合一的,是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也即非对象化的。这种状态下,也就是《老子》所说“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境界,亦是达到《内经》“上工守神”的境界。
3.3 临床体悟
即使在内经里不乏对疾病规律性总结,如“十九病机”,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如“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如“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而在临床体悟中,真正理论至此活了起来,一定是医者在临床上反复实践,将理论不断内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医者并不将理论当作对象,不是拿着这个理论去观察,而是已经内化于心,在这个非对象化过程中,然后某天突然地恍然一悟,将其运用了起来。或者是得出的某个经验,也在对象化的观察积累下,最后开花的一定是非对象化的点睛,是中国人常说的“悟性”得出的“心法”。
4 两种优劣势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就提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有欲”和“无欲”都是观道的方式,两者“同出而异名”,所以临床上两者都很重要。但当今过多的,是对象化的道,是站在一个制高点审视客体,它将主体与客体划分开来,拉出一定的距离。
对象化的道能提炼出理论高度的一般性的东西,可以总结为规律、方法、规则。它可以被认知而且可以直接用来遵守。这个很重要,是理论总结性和经验性的东西,能够用来指导临床,但仍停留在下工境界。
非对象化的道很难把握,它不可完全认知也不能直接拿来遵守,它“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它“随物而赋形”,但是可以去“体道”和“悟道”,是物我合一的。在人的实际生存经验中,最根本、最深刻的现象都是主客不分、非对象化的[3]467。要达到上工境界,这才是关键的一步。
我们需要并驾齐驱,更需要多多返回到非对象化的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圆从而完满。
5 启示:复归非对象化
对象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万物,但是要达到对物“出神入化”的使用状态,应该要不断返回到非对象化中。
张祥龙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援引海德格尔锤子的例子,他指出当以一种非对象化的方式使用锤子时,它的“物性或存在本性才能当场揭示和牵带出来”,并且指出“越是不意识到它的物质对象性,越是出神入化、冥会暗通地运用它”,他指出这种物我关系,“越是具有原在与世界的那种开启和保持住的存在论域的关系”[2]98。他还着重指出“‘以德配天’意味着只有人的生存形态才能通天”和“人间体验为理解之根”[2]348-349。我们在“穷理”之后,当“尽性”,方可“达于天道”,方可“至于命”。
黄龙祥在《开启〈黄帝内经〉之门的密匙》系列讲座中,提出“中国文化常提的‘心法’‘悟性’,如书画、古琴、养生、武术的高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物我一体’,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里讲的,不能也很难从逻辑入手”。恰如陈寅恪所说“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16]。
林光华[17]提出:“人应该不断复归‘恍兮惚兮’的非对象化之道,从根本上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同庄子的‘葆光’,虽然‘不知其所由来’,但它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的,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如果越来越对象化、技术化、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化,就会离这个活水源头越来越远。”
针灸活动不仅需要大脑,还需要身心的参加,通过治身与神,有一个“生气通天”的身心,才能进入“身心合一”的状态,才能以心印心,更好地“意会”。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针灸原典,临床上也更容易治神。一百年前作为社会底层的针灸人在民族虚无与文化自卑中,被迫做出匆忙的选择。而今,当好好审视中国哲学自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不至于未来针灸史之“针灸生在中国,长在西方”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