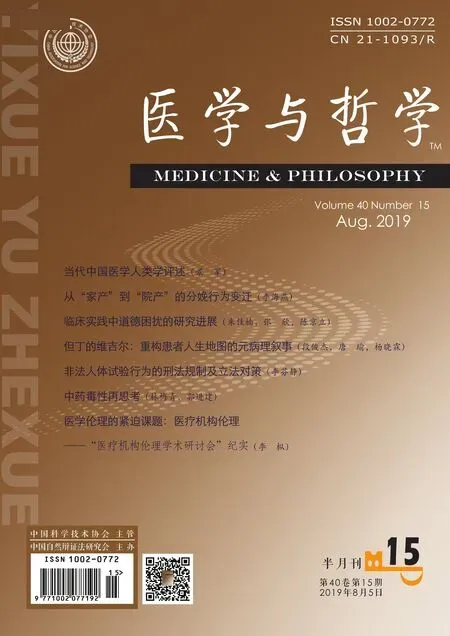当代中国医学人类学评述*
景 军
1 必要的说明
按照学科分类的国际惯例,人类学由四大部分组成:一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考古学,四是体质人类学。在当代中国,人类学列为社会学和民族学二级学科,考古学划在历史学,语言人类学纳入民族语言学和语言学大类,体质人类学归在生物学、法学人类学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门类。换言之,人类学被界定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早期中国人类学却是一门四个组成部分齐头并进的统一学科。例如,李济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将人体测量数据与中国城池建造和姓氏演变相结合,系统分析了汉族形成的轨迹[1]。 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过人类学的凌纯生[2]回国后在松花江赫哲族研究中专门记录了赫哲族的语音、语法、语汇。 在前往英国进一步钻研人类学之前,费孝通[3]在清华大学师从于史禄国,分析过史禄国提供的华南人体质数据和日本学者收集的朝鲜人体质数据。 其他一部分人类学家,如林耀华、罗香林、芮逸夫、吴定良、陶云逵等人,都曾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人体测量研究[4]。 对优生学、历史学、民族学及人类学都抱有浓厚兴趣的潘光旦[5],依据传教士和医师观察记录,剖析过旧时国人生活陋习与堪忧的国民健康水平之关系。
在老一代人类学家中,许烺光先生取得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可谓一座挺拔的丰碑。他于1939年完成一项关于北平警察送治精神病患者住院的社会调查[6]。 数年后,许先生[7]依据他在云南记录的一次霍乱爆发情况,用英文撰写出版《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 在英文版《驱除捣蛋者》一书中,许先生[8]重新分析了云南霍乱记录并把香港爆发的一次鼠疫流行情况作为比较。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先生还就性犯罪与人格、华北人的饮食、滇西屠夫行会以及美国精神病院改革等议题发表了一系列医学人类学英文期刊论文。
2 必要的陈述
解放后,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社会科学一度陷入磨难,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转入复苏,人类学逐步依靠家乡人类学、重访人类学以及没有中断的少数民族研究得以重建。但严格地讲,中国医学人类学是在改革开放一段时间才开始兴起。更为严格地讲,过去10年才是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迅速发展期。若以在中国知网检索相关论文数量而论,1980年~1989年全国只有3篇医学人类学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其中一篇由人类学研究者撰写,内容属于介绍范畴,另外两篇由卫生政策和医学教育研究者撰写。1990年~1999年全国共有24篇相关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其中3篇由人类学研究者撰写,内容属于学科介绍和既往研究回顾范畴,其余21篇均由中医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精神医学、卫生政策以及跨文化翻译等领域的学者们撰写。由此可见,医学人类学当时在人类学外部反而更受重视,比较有影响力的医学人类学文章作者包括精神医学教授杨德森和中医名师马伯英。
在2000年~2009年,全国共有59篇相关论文经由学术期刊发表,包括人类学研究者撰写的39篇论文,但其中大多数属于介绍性、综述类及意义或作用的论述,只有12篇期刊论文是依据田野调查完成的研究成果,调查方法和分析策略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健康知信行问卷、医疗资源统计分析、患病率分析、疾病负担排序和医患关系分析。
在2010年~2019年,全国共有180篇医学人类学期刊论文发表,而且绝大多数由人类学研究者撰写,其中50多篇基于系统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了患者需求、乡村医患关系、影响健康行为的文化因素、多元医疗体系、仪式化医疗、患病经历、病友组织等议题。
另以学位论文作为判断依据,2002年~2009年,全国出现10篇以医学人类学作为主题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位论文,其中8篇由人类学专业学生撰写。中国知网相关文献检索还显示,2010年~2019年,全国共有32篇相关博、硕士论文提交,其中29篇由人类学专业学生撰写。需要补充解释的是中国知网收录的博、硕士论文并不全面,但至少说明相关博、硕士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这部分医学人类学博、硕士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民资医药、健康观念、健康教育、戒毒机构、巫医现象、精神病患者、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以及吸毒问题。由医学生撰写的5篇医学人类学论文涉及民族医药知识传承、中医诊断方式、身心护理以及医学起源。
若换一种方式表述,中国医学人类学从饥荒年代过渡到健康发展期,在2010年~2019年,经由学术期刊发表的医学人类学论文远远超过之前3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总量,同期提交的相关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现大幅度增多趋势。鉴于此,中国医学人类学近年来的进步值得肯定,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相当受限,大致百人而已,队伍可谓短小精悍。
上面提到的学位论文数量在过去10来年明显提升,离不开医学人类学课程设置在部分院校的常规化和教师对学生更有力度的指导。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中医人类学课程。开设医学人类学课程的机构如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责任教师郭金华,哈佛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责任教师赖立里,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责任教师景军,哈佛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责任教师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责任教师包括哈佛大学博士潘天舒和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朱剑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责任教师包括中山大学博士程瑜、清华大学博士余成普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张文义);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责任教师杨晋涛,北京大学博士);厦门大学中医学院(责任教师吴荣,中国科学院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责任教师邵京,芝加哥大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化历史学院(责任教师包括东京大学博士王建新和协和医学院博士张庆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责任教师常姝,哈佛大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责任教师张实,云南大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责任教师高一飞,中山大学博士);云南中医学院(责任教师贺霆,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博士)。另外,中山大学设护理人类学课程,复旦大学设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课程,上海中医药大学设中医药人类学课程,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医学院以及广西医科大学分别设有体质人类学课程。
3 必要的理念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民族学、新闻学,甚至图书馆学而言,人类学在中国无疑处在边缘学科位置,医学人类学则属于这门边缘学科的边缘分支。以研究机构规模或学生培养数量而论,医学人类学确实在一门二级学科中属于一个规模非常小的分支。然而,中国医学人类学近年来在发展条件相当受限的情况下却取得了长足发展。医学人类学绝非医学,而是用人类学理念和方法,从事有关医学知识、医疗实践、就医行为、健康理念以及卫生制度等议题的社会文化研究。
人类学最基本的一个学科理念当属文化多样性。假如说人类语言的多样化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典型概况,那么影响人类健康的诸多饮食习惯则是对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高度重合的形象比喻。文化多样性理念广泛适用的研究议题之一是医疗多元性(medical pluralism)。在这一领域,中国医学人类学已取得的成果可谓丰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民族医学的多样性和中国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学多样性的重视。尽管我国教育体制仅仅设置中医学、蒙医学、藏医学、维吾尔医学、壮医学、傣医学六大门类民族医学专业,但是其他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自己的医疗传统。很久以来,现代化思潮对民族医学构成严峻挑战,反映在对民族医学科学性的质疑。很有意思的是数年前发生废除中医签名运动和网络热议,而少数民族医学并未遇到来自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质疑。正如一位研究民族医学的青年学者所指出,少数民族学者反而坚定地将民族医学视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
就医疗多元性研究而言,可以称为经典的成果包括乌仁其其格[10]有关蒙医文化的研究, 何群[11]关于鄂伦春民族过度饮酒的研究, 程瑜[12]对水族民族医学实践的观察研究, 徐义强[13]有关哈尼族治疗仪式的调查, 赵巧艳[14]对侗族收惊疗法的讨论, 张实等[15]发表的迪庆藏族老人就医行为研究以及赖立里[16]有关中医科学性焦虑的论文。 尤其是杜娟[17]有关泸沽湖摩梭人药物知识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这个研究围绕有关药物植物青尖刺的讨论,将民族药物学、民族史学与医学人类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属于一篇医学人类学的佳作。
跨出国门的医疗多元性研究较早见于贺霆[18]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开始的中医西传系列研究,其中之一分析了中医传到法国的源头和不同针灸学派对几千名法国针灸师的影响。 在云南中医学院任教后,贺霆协助云南中医学院成立了一个中医西传博物馆,专门展示法语针灸书籍、针灸会议老照片、针灸诊所记录、针灸用具、人体穴位图等实物。另外,土族学者胡军[19]在美国埃默里大学完成的医学人类学博士论文,虽然集中针对了迁移到美国的老挝苗族患者接受西医治疗的依从性问题,但也仔细地讨论了老挝苗族的医疗传统、患者对西医和传统医学的态度以及在美国就医的文化障碍。胡军[20]还就白人儿童和苗族儿童阑尾炎穿孔的悬殊比例问题,在美国最顶尖的临床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颇具文化评判精神的文章。
医疗多元性研究还包括在“海外民族志研究”系列之中。所谓“海外民族志研究”是北京大学高丙中[21]在2009年提出的一个学科发展观,也就是组织更多的中国人类学家走出国门从事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到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其他部分高校,先后派遣了百余人前往境外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随之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发表的期刊论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在此仅仅试举两个与医疗多元性相关的研究。例一是任杰慧有关中医在泰国的研究;例二是崔佳有关中医在美国的研究。
目前,在河北大学任教的任杰慧等[22]曾先后3次前往泰国研究中医立法过程。通过研究,她发现中医在泰国受立法保护程度超过其他国家(除却中国),覆盖了中医行医的合法性、中医院的合法性、中医学校的合法性、医药费纳入报销制度的合法性以及进口中药材的合法性。任杰慧认为,中医在泰国的整体立法得益于中医社团的不懈努力,尤其通过常年不断的善举行动,包括义诊、赈灾、捐款、布施,使得中医实践与泰国民众的功德观保持共鸣。
目前,在青岛大学任职的崔佳[23]曾在美国麻省综合医院针灸科和几个诊所坚持了为期1年的研究。 为了弄清楚美国人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的人口规模,崔佳分析了2012年美国国民健康访谈调查数据,发现至少接受过一次针灸治疗的美国成年人口比例达6.4%,过去12个月内接受过针灸治疗的成年人比例达1.7%。若加上儿童,12个月内接受过针灸治疗者近350万人。在所有接受过针灸治疗的成年患者中,79%的患者认为针灸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在12个月内接受过针灸治疗的成年人中,女性占70%,白人占78%,上过大学的人数占57%。可见,接受针灸治疗的美国成年人群以女性、白人、教育程度较高者为主[24]。 笔者所在团队还发现美国针灸师以白人为绝大多数,为推广针灸疗法和降低费用,经常使用集体治疗方式,比如在一个诊室同时为6个~7个患者针灸。笔者所在团队认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接受针灸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患者对医疗多元性的接受。2012年,美国人中有2 200多万人学习瑜伽、气功、太极拳,1 000多万人接受各种流派的按摩治疗,1 900多万人接受传统脊椎正骨疗法,340多万人接受顺势疗法。所以,中医针灸在美国受益于多元文化氛围[25]。
4 必要的差异
相比卫生经济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或预防医学,医学人类学按照人类学学科传统对田野工作的期待是以上学科无法比拟的一种方法论要求。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被称为人类学的看家本事,甚至成为人类学学科认同的最主要标识。假如某些人类学家从不从事田野工作,注定会被戴上“安乐椅人类学家”的头衔。人类学要求学者至少要有一次长期浸泡在田野工作点的经历,通常长达一年时间。所谓田野工作点即是人类学研究场域,在田野点工作不能仅仅依靠问卷,更不能在收回问卷后就匆匆离开。
留在田野点从事长期观察研究的好处在于深切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细节,聆听当地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或情感讲述研究者希望了解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当地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记录在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核对获得的原始材料,根据季节的不同或各类节日探究人们在不同时间段之内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规律。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在于融入和悟性。融入包括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甚至同享乐或共同参加重大社会活动。悟性在于利用融入的过程培养出经验性直觉,最终也许能够从人们讲话的潜台词、表情的复杂、反常的举动,甚至眼神的暗示,看出一些关键性问题。至少笔者了解的社会学不会提出诸如此类的期待。长时段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者必经的成年礼,也是为以后短时段田野工作打基础的历练。
在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田野工作显得好似落伍,还有可能被视为一门边缘学科才会膜拜的迂腐策略。其实,正是在尊崇大数据的时代,充满观察机遇并可以培养悟性的田野工作,越发显现出它的特殊魅力。例如,有关大学生献血的期刊论文在中国知网可以找到180篇,在万方数据库可找到190篇,其中属于实证研究的论文大多依据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涉及大学生对献血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典型的研究工具是标准化的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KAP)问卷。大学生是中国无偿献血事业的主力军,每当寒暑假,高校集中的大城市血库就会出现一定程度“血荒”[26]。 所以坚持对大学献血意愿和动机的研究有其一定的必要。KAP问卷的标准化便于数据对标,可以根据地区的差异、学校的不同、男女的性别、年级的高低以及时间的推演,对意愿和动机有所比较。但是这样的研究并不能展示出大学生献血的组织机制和组织文化。
一直到2010年前后,大学生献血制度严重依靠行政化社会动员,由各地血液管理办公室下达指标,指标分配一旦到达高校,校方用行政手段动员学生献血。例如,根据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2012年下达的任务,复旦大学献血指标按照本科生11%比例(共1 835人份)加以核定。按照以往惯习,复旦大学试图用学生辅导员制度达标,没想到出现在社交网络的一篇奇文将矛头指向一名学生辅导员。该文题目是《敬告复旦大学:我是同性恋,既没有献血的权利,也没有献血的义务》。被指责施压学生献血的辅导员亦在网络空间回复:“真是被黑出来了。我突然间就成了众矢之的,真真令人蛋疼菊紧。”导致网络热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复旦大学明文规定学生奖学金的评审包含四项优先条件,其中之一是献血。当时在其他一些高校,学生献血还可以加分。直到2014年,笔者通过一次大学生学术夏令营活动得知,全国仍有14所国家级重点高校为学生献血加分,每学期献一次血,平均成绩点数(grade point average,GPA)加分力度可达0.1分 ~ 0.5分。
一部分高校在2004年前后开始抵制献血与奖学金、保研或学习成绩挂钩,转为依靠学生红十字会替代学生辅导员动员献血的角色。目前,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余成普先生[27]曾花费两年时间在一所大学观察学生红十字会组织的每一次献血动员活动和每一个采血现场。他发现不同学科或年级的学生献血意愿和动机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同伴压力的大小。总体而言,学生红十字会将献血视为与校内其他学生志愿组织友好竞争的契机,但会员们动员献血的能力因人而异,有的同学比其他人更能够巧妙地通过人缘关系使用同伴压力动员献血。考虑到这所大学历年都在高校献血标兵之列,余成普的研究至少揭示了两个道理。其一,在献血意愿和动机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大学生献血的组织方式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学生自己组织的献血活动照样可以保证献血指标的完成,而且要比行政化方式更能体现志愿精神。
大学生无偿献血无疑是对“肉身经济”的抵制。所谓肉身经济是指物质刺激、商品理念以及市场行为对人体组织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的侵入[28]。 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有的地下血液买卖在中原地区变为公开血液交易市场,最终导致几万名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无偿献血相关法律的出台禁止了全血采集的商品化,但仍然允许有偿的血浆采集。又如,中华骨髓库自建立以来一直鼓励自愿无偿捐献的原则,至今已入库保存265多万人的测试血样和志愿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与此同时,我国居然还有一个“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在各地从事脐带血交易,一方面向产妇兜售保存脐带血的有偿服务,另一方面从收购的脐带血中提取造血干细胞。再如,国家在多年前就禁止了人体器官移植使用囚犯器官的做法,但一部分医生和学者却认为有鉴于器官移植需求过大,国家需要允许医院为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提供经济补偿。这种补偿的危险性使补偿标准有可能从象征性或低额度的补偿演变成为重金赎买。
概而言之,人体器官、骨髓、血液,乃至于母卵细胞,都可以通过医疗科技手段实现再利用。但就其社会文化意义而言,归途只有两个,要么变为生命商品,要么变为生命赠予。从英文gift of life 转译过来的“生命赠予”,如果直译就是“生命礼物”。既然是“礼”就有一个赠予与回馈的礼尚往来问题。针对如何回馈生命赠予的问题,人类学青年学者孙璞玉[29]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一个“生命伦理互惠”概念。 孙璞玉所言的这种互惠的确存在回赠,但不是发生在捐献者与受益的患者之间,而是在组织捐献的公共机构和捐献者之间。例如,组织动员造血干细胞捐献卓有成效的中华骨髓库受到政府的肯定和受益人的感激。在征集到365多万份库存、咨询了近80 000名患者,并为临床提供造血干细胞8 000多例的过程中,骨髓库领导和职工也被捐献者的生命赠予精神所感动,所以当捐献者有求医需求之际,他们会凭借机构影响力或个人在卫生界的人脉,为捐献者提供帮助,从而完成回馈。
孙璞玉[30]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注意到,目前全国各地至少有59座遗体和器官捐献者陵园,江苏省最多,共有7座。在安徽合肥等地的遗体和器官捐献者陵园提供免费骨灰生态葬。此类陵园内设立纪念墙,上面刻有捐献者的名字, 一些纪念墙还刻上捐献器官的名称。建立捐献者陵园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红十字会的努力和捐献者家属的意愿,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通常与普通陵园连接。每年清明的集体缅怀纪念活动相当感人,已成为在捐献者家属、挚友和其他参拜人中间传播生命赠予精神的平台。生命赠予可以得到回馈的道理就在其中。
5 必要的主位
在人类学研究中,另外一个涉及方法论的研究取向是对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的区分。客位是指研究者,客位研究也就是指研究者用科学手段捕捉客观存在的努力,将影响研究对象的物质世界和精神存在的客观条件视为研究的核心。这一研究取向对研究者的期待是保持客观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左右,包括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主位是指研究对象,主位研究也就是指研究者尽可能从研究对象的视角或情感去理解客观存在,听取当事人观点,尊重当事人的描述和判断[31]。 主位研究尤其要求研究者重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表达,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了解,熟悉研究对象的话语及生活世界,通过观察和参与观察,理解研究对象思考问题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视为研究的核心[32]。
人类学当然也重视客位研究,但对主位研究的偏好更强一些,所以最高境界的人类学造诣可以说是对意义和情感的准确阐述。所有人都活在客观的世界,同时活在意义和情感的世界。没有意义和情感的世界,等于人之终结。在这一点上,人类学更像心理学。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情感世界之探究面临各种障碍,需要用具体方法克服。例如,一个中美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10多年前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校生的健康状况产生了极大兴趣。研究团队首先使用健康调查问卷在5所打工子弟学校请在校生作为填答人,问卷有关健康意识、知识、态度与行为的选项全可以做出量化分析,具体选项和问题包括身高、体重、每天是否刷牙、是否吃早饭、是否知道长期食用煎炸食品的危害、体育锻炼的时间和频率等。这个团队对问卷材料分析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流于老生常谈,也就是研究发现了这种或那种不利于健康的问题普遍存在,需要改变。继而,这个团队将研究问题设置在儿童如何看待自我健康的问题,分析策略变为挖掘流动儿童自己的健康意识和主体性表达,使用的研究工具是Photo Voice调查法[33]。 这一被中国学者称为“影像发声”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组织调查对象拍摄照片并对照片展开讨论的方式收集有关信息,进而形成质性分析基础[34]。
在北京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影像发声调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第二次是2014年。参与调查的孩子们第一次共有12名,第二次共有35名,合计47人。孩子们有关食品的照片和讨论内容显示,在校吃零食的问题相当严重,但孩子们将其归因于学校营养餐的乏味和单调。至于孩子们缺乏体育锻炼问题,儿童在电动车飞驰的胡同里面踢足球的照片和有关学校缺乏运动空间的讨论说明孩子们并不讨厌体育锻炼,但是安全的体育活动空间缺位。孩子们还拍摄了农村进城打工者生活区域大批垃圾乱放的照片,但也用校内垃圾的照片表示承认自己也有过错。孩子们对这些问题的影像捕捉和语言阐述代表着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直觉反应,同时体现着主体性的诉求[35]。 借用笔者同事郭于华之言,孩子们提供的照片属于持续来自底层的声音[36]。相比之下,标准化的健康问卷包括的那些问题并不在孩子们的兴奋点。
重视主位主体性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一旦被医学界的合作者得知,反响多为不以为然,时而情绪激动,也有积极肯定或产生心灵共鸣的时候。笔者在此仅以庄孔韶的戒毒研究和张玉萍的老年人嫖娼研究为例。这两项研究的源头都是国家防治艾滋病的行动。回顾历史,2001年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艾滋病问题的起跑线。当时的中英艾滋病预防与关爱合作项目在云南省和四川省铺开,合作协议有一条要求指明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必要。在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海洛因一度泛滥,部分彝族群众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开始吸毒的经历与贩毒有一定关联,甚至卷入了一些家族(又称家支)。政府推动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带有相当程度的恐吓成分,将艾滋病的严重性推到极致,但效果不佳,知晓艾滋病危害反而导致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严重歧视。同时未能起到震撼吸毒者下决心戒毒的功效。
庄孔韶在一名彝族学生帮助下前往凉山地区,拜访了一部分远见卓识的彝族家族头人,其中为毒品泛滥痛心疾首的头人们认为,大讲科学道理和危害的艾滋病宣传(有些是汉字传单)几乎无用,为了族群自救,他们商议用习惯法和在神山面前盟誓的办法戒毒, 同时激活和调动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习惯法和民俗教育等文化资本,一方面用于戒毒工作,一方面鼓励围剿贩毒分子。庄孔韶随后展开的研究是一次行动人类学尝试。彝族家族头人动用古老的“虎日”战争歃血盟誓仪式,而战争的对手不是通常的敌人,而是“白粉”海洛因,他们在1999年的“虎日”仪式戒毒大获成功,于是鼓舞了其他家支[37]。庄孔韶提前开始了人类学调研准备,及时拍摄了2002年的又一次“虎日”歃血戒毒仪式[38]。由于头人和群众动员起来,戒毒成功率堪比世界前列。古老的歃血盟约需要牛猪鸡牺牲,戒毒者当场饮血酒,在石头上摔碎酒碗,表达誓死戒毒决心。按古老的习俗,重大诺言失信者只有自尽才可挽回个人、家庭和家支的尊严,或者远离家乡永不归还。纪录片杀青后在京播放,部分观者看后显得情绪激动,甚至气愤。项目办的英方经理强烈表示,这个电影有逼人自尽的意味,而且太血腥。有的国内预防医学专家则表示,决死的誓言自不必当真,一些官员认为这是在搞迷信活动。相比之下,丽江电视台非常理解人类学重视地方知识的作用,他们当时冒着“宣传迷信”的污名,在丽江电视台连续播放七天《虎日》,小凉山各地彝族的头人们观看后说“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会做!”播放电影时删减了一些“血腥”镜头,彝族的头人说,为什么要删呢?!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于是随后许多年,小凉山的虎日戒毒宣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再现迷信论。现在,虎日盟誓戒毒成为了彝族地方文化力量战胜人类药物成瘾性的杰作,显示了人类学在恰当的时机可以展现的公益效应与应用力量[39]。
通过艾滋病研究,庄孔韶还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剖析了性工作者的组织形态。另外,庄孔韶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一起从民间信仰、民族文化、宗教情节、生死观念等多重视角研究过临终关怀涵盖的一个双重命题,即医学理念与文化理念在生死问题上的碰撞。在庄孔韶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者,如嘉日姆几、富晓星、李飞、张有春、雷亮中、和文臻、黄剑波、孙晓舒、刘谦、张庆宁、方静文、宋雷鸣等人,纷纷进入了艾滋病和其他公共卫生研究领域。
如果说庄孔韶制作的戒毒影片让人看得心跳过速,那么张玉萍[40]的研究则让人能够在略带风趣的跨学科对话之中产生共鸣。张玉萍的田野点在湘西一个小城市,研究对象是嫖娼的老年男人和买春的中年妇女。 在研究启动时,这个城市已有200多名老年人感染艾滋病。张玉萍田野点是被现代城区建设挤压成为一个相当隐蔽的老街区,名为南门口。在这里,张玉萍了解到,老年男性和中年女性都知道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渠道,也知道使用安全套的益处,更懂得性交易在别人眼中是可耻行为,但小小灯红酒绿依旧,交欢的愉悦盖过健康的忧愁。一位老年男性告诉张玉萍说,艾滋病可怕,死也可怕,孤独、无聊、缺爱更可怕。还有一位老年人甚至吐露,农村的老婆不会像现代女性那样叫床,以至于认为用手敲打床铺就是叫床。
张玉萍“蹲点”的南门口好似一出诡异的超现实主义剧目,其中的男角欢畅一番之后挪到一楼一凤的门口,帮助里面的人防范警察的突袭,女角也不一定每次都做性交易,而是在轻微抚爱之际聊天拉家常,问寒问暖之势,全然一对老夫妻的模样。这个研究让公共卫生界人士既感到有些恼火,又能从中发现人之为人的共性。这个研究还说明,艾滋病在边缘人群的流行绝非仅仅因为边缘人群缺乏相关防范知识,艾滋病知识教育和恐吓性质的宣传,其功效充其量限于艾滋病流行的初期。其后,唯科学主义的劝导或急功近利的危言耸听必然失败。
6 结语
中国医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得益于四个主要推力。第一是通过翻译引进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和实证研究。其中,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卫生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学生的培养,对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41]。 第二是一部分人类学家在2001年开始主动介入到艾滋病防治项目,从吸毒、卖血、性产业、女性生殖健康的角度研究艾滋病的流行,除却中文论文还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英文文章[42]。 第三是重视中国民族医学传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多样化,在跨文化的视野内解读田野调查材料[43]。 第四是走出国门取得的田野工作成果,除却胡军的老挝苗族依从性研究和贺霆的中医西传研究,吴咏梅用英文发表了日本老人照护研究[44], 高良敏[45]的坦桑尼亚艾滋病研究也已成稿。
中国医学人类学进一步发展具备如下几个条件。首先,它已有其他国家医学人类学发展经验作为参照系。另外,它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作为铺垫,可以成为理论升华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医疗多元性提供着大量而又丰富的研究素材,可以作为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继续开发。还有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疾病谱转型伴随着医学实践紧紧并联社会文化变迁的诸多重大问题,可以使得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更具社会相关性。最后是高校已经有一部分医学人类学专业人才培养机构,虽然数量尚待增加,同时机构能力需要提升。
虽然还有很多的努力尚待做出,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进步绝非相关者的自我想象。发表这种言论的学者一定没有研究过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进程,反而是在无聊地品头论足。尽管存在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者同其他地区的同行一样,也是以探究人类健康、疾病苦痛、医疗制度及人类的生物文化适应性为主,所从事的研究绝非医学科学的配角,也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研究,而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系统审视和阐述人类健康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