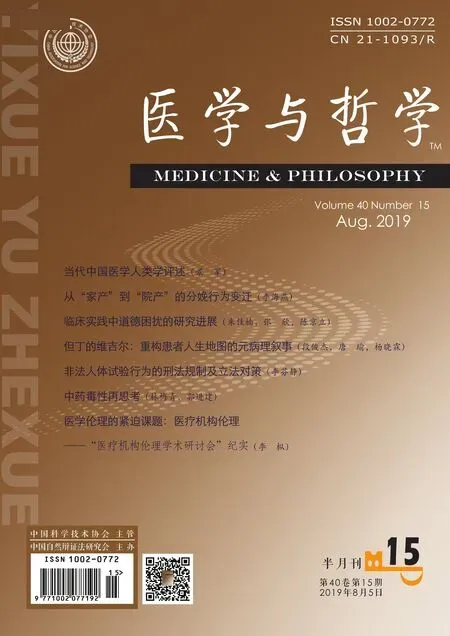但丁的维吉尔:重构患者人生地图的元病理叙事*
段俊杰 唐 瑜 杨晓霖
慢性病和重症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结构出现断裂,就像突遇暴风雨,失去“航行目的地和地图”的船只,患者的故事也遭遇了“叙事触礁”(narrative wreckage),不知故事将如何发展,结局会如何[1]。换言之,患者的故事突然混乱了,如果不去想办法找回故事发展路线图,患者将无法继续航行。这种人生地图的消失和生活意义的断裂正如但丁(Dante)在《神曲》(DivineComedy)里提到的人生中途走进的幽暗森林。被疾病挡住去路、被困在医院里的患者对前路感到迷茫和恐惧。遇到幽暗森林的但丁是幸运的,在他被困之时,维吉尔(Virgil)犹如天降的神兵出现在困顿的但丁面前并承诺指引但丁走出幽暗森林。
幽暗森林里只有猛兽和黑暗,没有人文气息。当但丁呼唤人文时,代表人文主义的维吉尔出现了。但丁由维吉尔带领游历地狱、炼狱,并最终由贝雅特丽奇引导进入天堂。如果患者是走进幽暗森林的但丁,那么,谁将成为引领但丁走出森林的维吉尔?患者不仅失去了地图,还必须适应自己作为患者的新身份。在新身份接受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来自他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2]。丧失地图使患者不得不通过故事来学会用另一种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3]1。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对他们的经历和现实的认可。
医生与患者,或者说维吉尔与但丁的关系首先是故事讲述者与倾听者的关系。正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言,“经历不是对一个人而言发生了什么,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他所做的事情”[4]。给予患者时间与空间去讲述“他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如何应对”很可能能够帮助他们改善疾病经历[5]。在分享故事和观察别人对故事的回应的过程中,患者学会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人生。这些患病故事的讲述和倾听合力创设一幅新的人生地图,构建的这幅新的地图才能让患者重新感知与这个世界的关系[3]3。
迷失在幽暗森林里的患者需要的不是牛顿,而是兼具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的维吉尔。然而,在强调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现代医学中叙事传统已经丧失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医生逐渐成为代表科学的牛顿。在维吉尔缺位的临床环境中,患者故事不被倾听,这使得一些叙事能力强的患者,比如著名文学家、医生、记者、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理论家主动去寻求医生之外的“维吉尔”——通过撰写自己的疾病故事来寻求患病之后的人生意义。不具备创作能力的患者阅读元病理叙事时,也能够遵循元病理叙事模式,向合适的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藉此,重构新的人生地图,在治愈身体之前实现对精神和心理的最好疗愈。
1 自我病理叙事
伏尔泰(Voltaire)曾经嘲讽医生职业:“医生是给他完全不了解的患者开出他并不怎么了解的药物去治疗他了解得更少的疾病的人。”当代医生高度依赖医疗器械和检查仪器,对作为主体的患者几乎不了解。除了在与患者交流时,多倾听患者的故事之外,还有一类叙事作品可以帮助医生增进对患者的了解,那就是患者自我疾病叙事。正如萨克斯(Oliver Sacks)所言,“在诊病时,我们获得的是解剖、生理和生物学智慧;在为生病的人问诊时,获取的却是关于生命智慧”。许多作家医生如葛文德(Atul Gawande)、维吉斯(Abraham Verghese)、马什(Henry Marsh)、奥弗里(Danielle Ofri)、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卡兰尼提(Paul Kalanithi)和弗兰西斯(Gavin Francis)都认为只有将医生叙事和患者叙事并置起来研读,才能走上通向医学和生命真相的正确路径。
在这一语境下,患者叙事出现并大量出版,构成疾病叙事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患者撰写的非虚构疾病回忆录或自传叙事的出现与社会科学的情感转向趋势相一致,带动了医学叙事从医生到患者视角的转向,促使医药从业人员对患者故事报以关注、尊重、理解的态度。如医学人类学家卡里茨库斯(Vera Kalitzkus)所言,患者故事让局外人理解他们病痛的感受,这种痛苦不是外表上能观察到的,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它们提供了患者疾病经历的个人和社会背景,也给如何应对疾病提供了决策依据。
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John Donne)很善于藉由诗歌传达疾病之痛。多恩认为疾病“要么同时摧毁身体和灵魂,要么既不能打败身体,也打不败灵魂”。多恩的病中之歌教导我们在临床语境下必须重视患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只重视客体的身体器官,不关注主体情感与语言的诉求,不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对于患者而言,真正战胜疾病,首先不能迷失自我和自我的人生地图。医生只有在医患沟通过程中采用“主体间性的路径”,设法进入福柯所谓的“患者内在的病态意识”[6],设法采用患者的视角去看待疾病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并引导患者顺利地度过人生重要的转折期。
我们把患者撰写的第一人称非虚构疾病日记、自传或回忆录称作“自我病理书写”或“自我病理叙事”(autopathography)。与自我病理叙事相近的还有一个术语,叫“autosomatography”,称作自我身体叙事,大多涉及疾病与身体残疾,如普莱斯(Reynolds Price)的《重生:打败脊椎里的恶魔》(AWholeNewLife:AnIllnessandaHealing)、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的《当呼吸化作空气》(WhenBreathBecomesAir)和墨菲(Robert Murphy)的《沉寂的身体》(TheBodySilent)等。自我病理叙事者通过自我疾病叙事描述罹患严重、慢性或不治之症的过程中的各种苦痛经历,可以达到四重目的:(1)可以为疾病去污名化;(2)可以帮助其他患者接受他们的状况;(3)可以获取他人的同理与共情;(4)在于对当前不完善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状况进行批判[7]。
根据霍金斯(Anne Hunsaker Hawkins)的说法,濒死状态下却不敢正视死亡、否定死亡可能是病理叙事的特点,但绝不是自我病理叙事的特点。因为自我病理叙事书写的过程正是认清生命意义的过程。霍金斯将患者自我患病经历书写分成医学共鸣(medical syntonic)和医学失谐(medical dystonic)两种类型[8]。前者是对医学的肯定,赞扬医学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后者的主要基调则在批判医学的局限性以及医学的非人性给患者造成的困境。笔者将这两种类型分别称作“医生与患者的和谐型叙事”和“医生与患者的失谐型叙事”。霍金斯发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患者自述基本上都是医生与患者间的和谐型叙事,而90年代之后,这一风格发生了逆转,失谐型叙事开始占据上风。
然而,这两种类型主要侧重于医患关系和患者对医疗体系的评价。事实上,在这两种类型的叙事之外,还出现了一种中间类型。它更倾向于关注自我病理叙事者本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医患关系并非其中心议题。比如,麦克连(Teresa McLean)撰写了两部关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的自我病理叙事作品,一是关于糖尿病的《金属器乐即兴演奏》(MetalJam:TheStoryofaDiabetic),二是关于癫痫的《发作》(Seized:MyLifeWithEpilepsy)就避免谈论医患关系和对医疗体系的批评。
威廉·奥斯勒曾言:“医学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也是充满可能性的艺术。”医学的不确定性为患者寻求疾病解释和意义提供了可能性。除了病痛与死亡之外,对他们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命运的随机性。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以后会怎样?所谓希望/绝望,归根结底,是患者为自己的疾病讲述的一个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他获得/失去直面恐惧的勇气和行动力——不仅是对抗疾病的勇气,也是面对死亡的勇气。
2 元病理叙事
在“自我病理叙事”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格莱厄姆(Peter W. Graham)认为,文学家作为一类特殊群体的患者,他们本身具备深厚的故事讲述技能,他们比普通患者讲述的故事要更加精准简明,这类患者可称作“元病理叙事者”;与疾病经历相关的作品,也就是作家对“自我生病状态进行的深刻分析”,可以称作“元病理书写”或“元病理叙事”。本文认为元病理叙事作者不限于文学家,有创意叙事素养的哲学家、医生、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理论家也可成为元病理叙事创作者。为方便论述,笔者将元病理叙事者也称作作为患者的作家叙事者。
元病理叙事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最早的元病理叙事者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作家阿留斯(Aelius Aristides)。在他的诸多旷世杰作中有一篇名为《圣者传说》(SacredDiscourses)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讲述他所患的诸种疾病。他认为身患疾病是神赐予他的机会,使得他能和医药与治愈之神埃斯克莱皮厄斯(Asklepios)之间形成非同一般的医患对话关系。医神会托梦给阿留斯,告诉他针对自己的病症应该如何进行治疗。通过撰写《圣者传说》,阿留斯得以寻获自己患病之后的人生意义并正视死亡,在那个时代这种作品实为稀有之作。
讲述和写作自己的疾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达到精神治疗作用。女社会学家和小说家哈丽雅特在年轻时就被诊断出尿道肿瘤,被迫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卧床休养。因而,她从患者视角撰写了《病房中的生活:病弱之人杂记》(LifeintheSickroom:EssaysbyanInvalid)。患者的故事所使用的语言与医生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科学语言交流风格迥然不同。然而,这些故事却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透过直接经历者的视角观察疾病的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阅读患者的疾病回忆录或疾病虚构叙事,医务人员能更好地进入患者的视角和世界,聆听和感知患者的心声,更好地实现医患之间的视域融合[9]。
叙事是生病的主体找到他们患病前后生活间精神连结的方式。在临床语境下,患者需要通过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故事,与他人或自己交流精神层面的想法。元病理书写为作家患者提供了一个探索人类生存状况的独特机会,通过把作家的患病经历、与医护人员的交往和住院感受变成他们作品的主题,作家的身份得以多元化,他变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他是疾病的知情人,也是自己和读者心理状况的调节者。
病历书写或记录原本指的是医务人员记录下的关于患者患病经历的重要资料。但元病理叙事者通过努力创造“最好的文学文本”将病历记录变成了文学叙事形式。阅读作家患者的元病理叙事可以帮助医学生了解这些疾病的知情者和经历者的身体症状,也能帮助他们理解临床现实中患者的心理状态——情感、认知、视角、预期、思想等。同时医生若能鼓励普通患者阅读作家患者的元病理叙事作品,也能达到帮助普通患者了解疾病对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找到共鸣,甚至激起他们讲述和创作自己的疾病故事的欲望。
著名的元病理叙事主要有赛吉维克(Eve Sedgwick)的《关于爱的对话》(乳腺癌)、瑞曼(Rachel Remen)的《厨房餐桌的智慧:治愈你的故事》(克罗恩病)、昆德兰(Anna Quindlen)的《真情无价》(卵巢癌)、魏玛(Joan Weimer)的《后背之语:教会迷失的自我讲述故事》(背部损伤)、巴特勒和罗森布罗姆(Butler and Rosenblum)的《癌症的两种声音》(乳腺癌)、萨义德(Edward Said)的《格格不入:一部回忆录》(髓细胞性白血病)、埃里斯(Carolyn Ellis)的《最后的协商:一个关于爱、失去与慢性疾病的故事》(肺气肿)[10]。
首先,我们发现,元病理叙事为第一人称叙事,但叙事者不一定为患者本人,而有可能是患者的至亲和密友。如昆德兰的《真情无价》讲述母亲卵巢癌的患病经历和死亡过程,母亲“正在疾病和死亡之间摇摆。我讨厌在没有治愈希望的前提下,医生还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去提取、去活检、去穿刺、去测试、去化疗、去手术……”。昆德兰认为现代医疗不但没有出现引领患者走出幽暗森林的维吉尔,没有给予患者生命的地图,反而让患者成为痛苦不堪却不能选择死亡的喀戎。
其次,元病理叙事作品也不限于非虚构作品。在当代元病理叙事的创作热潮中,我们发现一部分作品具有一定的创意性和虚构性,介于疾病文学和疾病自传之间。赛尔泽(Richard Selzer)承认自己在撰写《起死回生》(RaisingtheDead)这部元病理叙事作品时,他运用了想象力建构出一个他认为在他军团病发作昏迷期间可能发生的故事,因而,这个与疾病经历相关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性。同样,根据萨克斯(Oliver Sacks)自己的说法,他的《单腿站立》(ALegtoStandOn)也是某种与神经疾病相关的小说叙事。
此外,元病理叙事中的医生疾病叙事也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撰写自我病理叙事深刻意识到了临床语境下维吉尔的缺失,在未来的医生生涯里尽量成为患者的维吉尔。著名的散文家蒙田(Montaigne)说他只相信那些患过自己患的这种病的医生。元病理叙事传递着不同职业、身份、国别的人的共同经历,它们必定通过各种形式影响我们。当医生成为患者,医生关于疾病的生命医学视角不得不与疾痛的个人视角合并,产生某种张力,激发他们寻求疾病书写这一媒介来反思医生职业和医患关系。关于医生元病理叙事的更详细论述可参照笔者近期已发表的《当医生成为病人》一文[11]。
普尔曼(Philip Pullman)说:“真实的故事能够滋养心灵,增强患者对疾痛的忍受力。它们让思想充满信息,内心充满希望和力量。”为了能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维吉尔式的指引,牛津大学的阿伦森(Jeffrey Aronson)与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的霍尔-克里夫德(Rachel Hall-Clifford)合作设立了一个网站,将比较有名的患者撰写的近400部元病理自传叙事作品分门别类地展现在网站里(http://www.patientstales.org/home)。元病理叙事者藉由叙事医学理念的推广成为了医生之外的维吉尔。
3 元病理叙事对作为维吉尔的医生的呼唤
许多患者或家属认为当代医生被训练成干预危机的专家,他们只在手术、化疗和放疗时短暂出现,机械地处理完手术和治疗步骤之后就像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转向新的患者。在这个精密的医疗体系里,医护人员不能给予患者持续关爱,没有意识到在手术刀下、在射线下、在化疗中的患者是有感觉、有知觉、有感情的主体。他们与医生不是机器与机器的关系,而是维吉尔与但丁的关系。患者需要维吉尔式的引导,重新发现人生故事、意义和地图。在维吉尔式医生缺席的状况下,许多元病理叙事者通过“医生与患者的失谐叙事”来呼唤临床实践中医生维吉尔的出现。
葡萄牙作家何塞(José Rodrigues Miguéis,1901年~1980年)二战时被流放美国,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治疗期间与该医院一些医生有过接触。在他的元病理叙事《半张脸面对死神微笑的男人》(AManSmilesatDeathwithHalfaFace)中提到:“我与这些陌生人(医生)在一起,他们对我一无所知,跟我更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对于他们而言我只是一个来医院的病例,引起他们临床好奇心的一个对象。我不存在,我只是一连串的症状。”[12]
在康威(Kathlyn Conway)的《平淡人生:疾病回忆录》(OrdinaryLife:AMemoirofIllness)里我们也可以读到医生无视患者的故事:“布雷克曼医生跟一个实习生谈论了我的状况——以前被诊断有淋巴网状细胞肉瘤(Hodgkin's disease),乳腺癌早期,左乳房切除,没有发现淋巴结……”医务人员满眼满嘴都是客观的疾病(disease),而没有患者作为主体所体验所感受的疾苦(illness)。这里涉及对疾病的两种不同视角的理解。对于医生而言,康威的疾病只是医生日常工作中面对的小事件,却是康威人生面临的大危机。对于收到癌症诊断的患者而言:“从听到诊断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一个封闭的圈子,这个圈子将病人与他/她以前的正常日常生活隔离开,与过去那个正常的自己隔离开,与那些他们所爱的人们隔离开;在那个封闭的圈子里,病人就像一个来自不同物种的生物。”[13]
弗兰克在他的疾病回忆录描述他被告知罹患胃癌的一幕时说,医生除告知他这个结果之外,再也没有开口说话。医患之间的会谈就结束了。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医院给了他一个医院版本的身份,他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医生眼中口中的“p53基因突变型精原细胞瘤”。当弗兰克遇到了幽暗森林,而维吉尔却迟迟未出现,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凯旋和人性的落幕”。精准诊断和客观描述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但从人文的角度而言,这是医生职业素养的彻底失败,因为他完全无视对方的情绪反应。如果患者的治疗感受、患病的痛苦和体验,医生全然不知也全然不顾,那么医生看到的只是患者的瘤子,而非患者。
遇到幽暗森林的患者期待出现在他的对面的是一位懂得指引和与他一起面对困顿、化解恐惧的维吉尔,但出现在对面的只是一位冷冰冰的科学家,他的头脑和语言里只有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学和疾病分类学。医生认为患者遇到幽暗森林是患者个人的事情,对患者采取的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活生生的个体变成了被动接受各种机器检测和机器治疗的对象,变成客观存在的需要维修的物体,医患关系变成了“主体的我与客体的它”(I-It)的关系[11]。许多医学生会用医学世界语言称呼患者,如“三床的糖尿病足”、“四床的MI”、“五床的MDS”。这些医学专业语言称呼让我们戴上盲目的眼罩,使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贫乏,也越来越缺少对患者苦痛的理解力。
前文提到的瑞曼是一名肿瘤科医生,是一名慢性克罗恩病患者,在自我病理自传《厨房餐桌的智慧》中她结合医生与患者的双重身份,分享自己的感受与思考。故事谈及生命力、自由、如何打开心窗、生活里的盲点等,这都是维吉尔所能带给但丁的。由于瑞曼的独特身份,她深深意识到要拥有健康,不能单靠药物、手术刀以及作为科学的医学,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触碰也必不可少。因而,瑞曼写到:与一个人交流的最基本、最有力的方式是倾听。也许,我们能给对方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关注,尤其是发自内心的关注。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听到心里去。很多时候,关注比理解还重要[13]。
对于医生而言,要成为但丁的维吉尔,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倾听患者的故事。将患病的故事讲述出来并被周围的人理解,尤其是医生理解的那一刻起,患者就已经找到了将患病前与患病后的故事连贯起来的方式。瑞曼在找到自己的维吉尔之后,意识到作为患病的医生、受伤的治愈者双重身份的自我,不仅要充当自己的维吉尔,还应成为其他患者的维吉尔,呼唤现代医疗中缺失的维吉尔再次出现。对她而言,疾病是她人生中的动力,重要的不是外在的治疗过程,而是疾病的内在过程。这种对维吉尔的追索不仅在瑞曼的内心里被唤醒,也在其他遭受疾病挑战的患者的内心中唤醒。这种追索驱动着瑞曼一路向前,不只是为自己疾病的治愈——更是为患者群体的治愈。最终,瑞曼不仅成为临床医生,也成为了医学教育者。
在弗兰克的幽暗森林时期,医生没能成为引领他走出幽暗森林的维吉尔,弗兰克只好自己去寻找维吉尔。弗兰克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著名作家将患病经历变成回忆录和自传,成为引领弗兰克的维吉尔,如罗德(Audre Lorde)的《癌症日记》和阿尔索普(Stewart Alsop)的《死缓》。因而,元病理叙事的意义在于在维吉尔式医生缺席的情况下,充当但丁的维吉尔。女性主义学者古芭尔(Susan Gubar)患癌之后不仅充当自己的维吉尔,还成为癌症患者的代言人,通过《子宫被切除的女人的回忆录:遭遇卵巢癌》讲述她与卵巢癌的抗争过程,与其他患者一起探讨患病的意义,积极寻求新的人生地图。之后,古芭尔还为《纽约时报》专门开设Living With Cancer专栏。古芭尔的文字对于身处疾病之中的人而言是一种安慰,就像幽暗森林里温暖但丁,并让他充满希望的维吉尔。通过专栏,古芭尔帮助了大量患者、护理人员和专家。
古芭尔的新作《阅读和写作癌症》讲述了文字如何成为患者的维吉尔,对癌症患者的治愈产生积极影响。这是一部具有启发性的实用作品,她鼓励患者进行阅读与写作,阐明写作阅读对癌症产生的积极作用。古芭尔引述了伯尼(Fanny Burney)的日志,托尔斯泰(Lev Tolstoy)和艾门罗(Alice Munro)的疾病自述,以及大量回忆录、小说、绘画和照片,向读者们阐明这些关于疾病的文字如何引领患者走出幽暗森林,在加深患者对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的理解的基础上,绘制新的人生路线图。
4 结语
倘若没有维吉尔,但丁可能将在幽暗森林中徘徊,在惊恐中彻底失去自我,彻底失去人生的地图。维吉尔在幽暗森林中代表的是人性,他首先能让在虎豹和黑暗面前惊恐万分的但丁感到人性,然后是情感与理智。罹患慢性病或重症的患者首先要遇上能够引领他们走出幽暗森林的维吉尔,才能在认清生命意义的前提下,在代表家人的贝雅特丽奇的陪伴下继续人生旅程,最终进入天堂。医生本应成为维吉尔式的人物,然而,当代医生职业素养中人性的缺失让医生无法承担维吉尔式的责任。这时,有一定人文素养的患者通过撰写元病理叙事开始了自救的过程。
作为科学的医学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形式论述理论,而自我疾病叙事或元病理叙事以第一人称的主观经验形式诉说自身感受。阅读和撰写元病理叙事可以抵制人性的泯灭,呼唤维吉尔的重现。疾病叙事告诉我们只要移动自己的视角,故事里的人物就会成为代表人文关怀和人生指引的维吉尔,故事将引领你采取一种人文的、共情的、伦理的态度重新理解一切。医护人员不仅要为患者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还必须引导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人生意义和死亡有正面的认识。因而,医生在病房里或诊室里也应承担维吉尔的角色。医生可以按照自己对这些不同类型患者的疾病叙事的了解,向有阅读能力的患者推荐相关读物,展开全人的、以情感关怀为中心的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