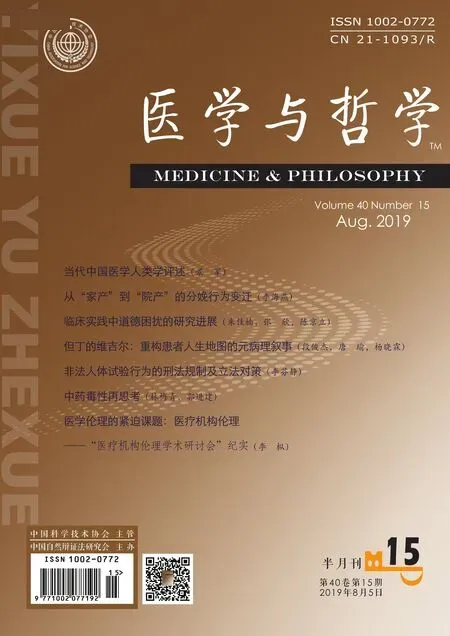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王悦婷 刘玮玮
身体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方式,是人类身份和法律意志载体的唯一体现[1]。我国著名学者张再林[2]曾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性的哲学,这一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明代哲学家、儒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就是一种围绕“身”与“心”展开的哲学思想。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王阳明认为人的身与心是一体的,不能够割裂两者而单独分析其一,基于身心一体的观点,他进而提出了身心同修的修身论[3],并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对其进行扩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对于当今我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即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及其对现代医学的启示予以梳理和阐述。
1 人我身体观:万物一体论
如前所述,身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呢?王阳明对此主张万物一体论。万物一体思想从先秦时期就为各家学派所推崇,各个思想流派都将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加以阐释,并通过精神的灌注,来阐发其万物一体的思想。先秦儒家将“仁民爱物”作为“天地人”一体的表现,提出“由己及人”的“仁”学思想,只有将他物和自我的一致性充分地扩充和体认,才能将仁爱推己及人。这种对万物一体的体认,更多是来源于儒家一以贯之的“一体之仁”思想,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同情”心理。宋明时期,理学家明确地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宋明理学家张载更是将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体而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同胞,所有的事物都是朋友[4]。在将万物一体思想扩充发展时,理学家们将仁爱的思想杂糅进宋明理学之中。道家也主张万物一体的思想,并用“道法自然”来解释万事万物发生和发展的变化,用“道”将万物统一到一起,用“自然而然”的观念将万事万物的发展统一到形而上的高度,使得人以超脱的眼光看待万物的发生和发展,指导人生实践。道家认为,作为个体的“我”存在于这个世界,只要“我”存在着,就意味着不可避免与世界中人与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每一个个体都绝非是绝对孤立隔绝的。王阳明的人我身体观吸收了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同时又将道家的“道”以“心”化之,借此将他人之心和自我之心打通,肯定了人心与自心本体上的一致性,并将那些被私欲蒙蔽的人心单独予以阐释并加以区别,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肯定了人心和自心的同一性,为其为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修养功夫提供了实现的依据[5]。
王阳明在《大学问》里开篇即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之后他又提到大人之学,应该是去除蒙蔽自己的私欲,不断扩充德性,重新融入天地万物的唯一途径。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直指人心,更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王阳明认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他将人与万物一体归结为人心容纳万有、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心灵体验与境界。他的身体伦理观将天地万物看作是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6]。万物一体将人(精神)与物(物质)如何统一做出了解释,也将人的精神世界纳入身体伦理的范畴。
而在“心”上来说,人心能够包容世间的“万有”,每个人都可以用心去感受世界,获得自身的情感体验[7]。王阳明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正是基于“万物一体”的理论前提,使得人心及其感觉具有相通性,所谓“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能将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当作自家之人,能将他人视为自己。人和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存在着千差万别,个性的不同让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产生“分别心”,如果过分地强调差异,就会和周围的人产生疏离,进而就无法在道德上成为“大人”。“大人”出于本原的仁心,可以将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同自己的道德心连接起来,消除自己和他人、外物的差别,从而祛除本心上的“私欲之蔽”[8]。这和王阳明所说“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出一辙。
由此,王阳明举例论证了万物一体视野下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也具有相同性,“吾一人之视,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这说明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感觉、体验是相通的,面对同样的色、声、香、味的感觉大体上趋于一致,这种感觉基础上的相通性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面对寒冷、饥饿、疼痛等感觉,不同人的感受是相通的,由此将他人与自己的感受用“心”这个媒介连为一体,将人与我、人与物间的联系打通,为他 “万物一体”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佐证。
“万物一体”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中的经验事实。也并非通过理性证明才知其为真,而是通过一种存在于每个人的本心之中的深切感受,让人们立即就知道事情就是如此(“当下即是”),它无法与人身体所表现出的快乐、愤怒、悲伤等普通情绪相分离,这一论点与程颢对天理的体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具有相似性,如此通过身体感受到的“仁”就是意识。这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它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动性。王阳明打通了每个人生物意义上感觉和直觉的一致性,进而将心与心之间的差别打通,上升到意义层面的平等,为实现心的超越和体悟提供了可能性[9]。
王阳明通过人我身体观借此阐发出道德之仁的一致性:每个人的内心良知和他的心灵是相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被个人的欲望蒙蔽,使得每个人向外扩充的“仁”千差万别,但这并不能妨碍达到他人与自身和谐为一的圆满境界,这种一体之仁可以无限地扩充,直至天地万物,使得后世学者在关注客观世界的“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万物“一体之仁”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局限于关注人的安身立命,更注重心的修养和体知。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诸如《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西方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等相关研究中得出,西方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提到了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但其更多的是用宗教伦理和法律来规范彼此。西方将宗教视为人与人之间的缔结,而现实的法律使得其更看重个体作为独立的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于王阳明将“天地人”视为一体的思想。较之于西方哲学思想,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解释了人与物的统一性,而且解释了人与我的统一性。
2 自我身体观:身心合一论
如果说在人我身体问题上王阳明提倡“万物一体”论,将人心和自心、自己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那么,在自我身体问题上,王阳明提倡“身心合一”理论,就是为了进一步契合自己的身心。
先秦儒家就有修养身心的传统,《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认为“心”的修养是做一切事的开端,是一个人成事之本,至于如何养“心”,汉儒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人们出生时,就有“义”和“利”两个方面。利是用来养身的,义是用来养心的。董仲舒更重视人心的修养,并给出了“重义”的修养论。但这种修养身心的办法还是将二者割裂区别对待,而并未直接对人的身与心如何实现一体化做深入的解释。王阳明的心学将心作为体认万事万物的途径,他认为心不仅是道德情感意义上的发动体,更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将身与心的关系打通,才能构建一个统一的意义世界,才能进一步将“知”与“行”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在继承以往思想家“天”、“地”、“人”一体关系的基础上,又将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的一体性阐释得更加透彻。
王阳明身心合一的观念为他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切实的基础,他提出的“心外无物”,将外在之物还原为根植于身体的“心”。王阳明认为:“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他认为心体的作用对外部世界也具有某种依存性,“我的灵明离却天地万物鬼神,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只有当人身心一体时才能发动道德情感,进而实现知行合一[10]。可以说,“心”与“知”,“身”与“行”是相互对应的,强调“知行合一”即是一个人的“身心合一”。人是一个身心俱存的生物机体,很难将两者分开来对待,而“身之主宰便是心”。
王阳明的“心”不是禁锢在身体之内的心,不是“血肉之心”,而是恰恰以一种“具身化”的方式存在,它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人的一切知觉、感觉之中,它是和身体融为一体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就如梅洛-庞蒂[11]“不是我有身体而是我就是身体”这一论断所言,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存在,而不是纯粹的思想的幽灵[12]。所以,正是有这种切实的感知与体悟,人才能真正获得作为最为本己的“此在”之我的确证性,并最终也使那种“万物皆备于我”之我的本体论成为了可能,由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
“心即是理”和“心外无理”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观点,“心外无理”将“理”根植于人的内心,以人的天性为依据,体现了人内心的思维导向,这样将人服从于内在的“心”,把“身”和“心”作为统一的生命体去看待[13]。王阳明主张心理为一,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它包含“心理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身体哲学思想,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
从他的论述中,可知“心”不仅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具有物性,最重要的是心具有神性,兼具形神两方面的属性,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非若世之想象讲说者之为。”“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发动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认识与体察通过行为外化出来,心能够成为一个人的主宰就在于心是包含在之中,和身融为一体的。换言之,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能,追求圣贤既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责任,也是其天赋的人权,个体是否去做以及能否达到,这又完全取决于主体性能否确立以及主体意识能否高扬。王阳明的这一观点不仅为后人身心同修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人们追求更高的理想人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以及《胡塞尔哲学研究及困境的反思》等过往的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现象学也提到了身和心的问题,西方的现象学和王阳明在自我身体观上都属于一种先验哲学,这两者都认为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学无法衍生出“道德意识”,也没有一个准确肯定的诸如“心体”的超越实体。只是与西方现象学的先验知识理性这一观点不同的是,王阳明的先验哲学是基于一种内在的先验意识,即儒家的德性良知基础上的哲学。
3 修身养生观:身心同修论
在自我身体观上,王阳明认识到了人的身心具有同一性,两者不能割裂开来,不能养身用一个方法,养心又去用另一番功夫。既然人的心已经内化于身,那么养身的同时需要养心,修心的同时也自然能够达到修身的目的,在修身养生问题上,王阳明显然主张身心同修论。事实上,王阳明的身心合一论已经彰显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他将“心”作为道德的来源,倡导通过“身体”的修养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更好地实现道德修养。
首先,就修身而言,虽然身体的感官和肢体的基本生理欲求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但是如果受到过多的物欲干扰则会导致人心陷落、蒙尘[14]。王阳明认为良知所引导的方向就是世间的大道,是至善。而现实中,被蒙蔽的良知使得这种善没办法扩充出去,修身的目的在于抑制外在欲望对于自身德性的干扰,修身的途径在于扩充人的良心,将“良知”身体力行地表现出来。“心得其宜之谓义”。“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说明了人的行为应合乎理性的准则,修身的核心就在于根据“良知”的指引去身体力行。
与此同时,修身也离不开修心,心对于身具有控制和主宰作用,也是道德的终极根源,在王阳明看来,心体只有处于廓然大公、清明澄澈的状态,才能正确感应万物。他将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比作“眼睛容不得些尘沙”[15]。在修心的具体实践上,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在事上磨炼功夫,“致”的本身既是一个知的过程,也是一个行的过程。在致良知的过程中,得以去除蒙蔽,恢复良知,明心见性。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对身心同修的最好阐释,“知”是人内心的体认和感知,而“行”则更多地借助于个人的亲身实践,“知行合一”的实质是将“心”所体认到的“良知”通过“身”来加以实践印证。他将人的认识和实践相统一,并提出了“知之未行,只是未知”。他认为,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知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去除蒙蔽,先正其心才能发扬良知。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身心同修的实践观。他强调,人们从思想动机的萌芽,到实践进而完成的过程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身心活动过程。为了实现身心的和谐与统一,我们必须在知与行的统一中实践,以回归真实的和谐状态[16]。
《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何谓真正的知与行。王阳明进一步举例,例如,知痛,绝对是当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他的肚子饥饿了。王阳明认为,知是心的本源,心自然能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便是良知,是与身体力行分不开的[17]。王阳明坚持知行合一,同时也是在肯定身心同修的方法,知行合一也是阳明学身心同修论的实践观。
王阳明的身心同修论摒弃了传统儒家将修身和修心分别对待的修养观,将两者的修养功夫视为一种功夫,简化了修身的过程和步骤,却又赋予了修养身心更丰富的内涵,对后人的修养身心的方法论提供了新方法,也对传统儒学的修养方法做出了有益的补充[18]。
西方学者也关注到了人的身心修养问题,西方基于笛卡尔“主客二分”的宗教传统思想,认为人的“心体”属于超验的部分,不可以被改造,而身体作为具身的存在,可以进行改造。这种思想显然将人的身心割裂开来对待。而王阳明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两者的关系打通,为身心同修提供了可能性。
4 王阳明哲学思想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4.1 基于万物一体的换位思考
王阳明哲学思想对现代医学存在诸多有益启示,其首要启示就是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中学会换位思考。《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门诊患者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前三位分别是:医疗费用占40.0%,技术水平低占16.1%,服务态度差占13.8%[19]。这说明在患者就诊过程中,医生态度不好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医生服务态度差与其对患者缺乏同情和疏于沟通是密不可分的。医患之间一旦缺乏共鸣,沟通不畅,其矛盾势必加剧。例如,如果患者多问几个问题,医生就会有一些不耐烦情绪;又如,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没有给予患者和家属以安慰,这些都是导致医患纠纷的隐患[20]。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告诉我们,人心及其感觉具有相通性,正所谓“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能将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当作自家之人,能将他人视为自己[21]。患者受疾病影响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焦虑和烦躁。反之,如果医生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患者的情况和情绪,就会对其产生同理心,患者就会感到温暖,从心底里信赖医生,医患关系自然和谐。
之所以强调医生的换位思考能力,是因为医学的本质乃人学,它不仅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生理状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价值、幸福、人生意义和尊严的肯定。将人文精神注入医学就是要让医生意识到患者是一个既有生理需求又有精神追求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简单地在治疗过程中把患者看作机器。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所指出,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不能简单理解为“态度好”,它表现为医生对患者身心的关怀、生命的尊重、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认同,是医务人员发自内心地想方设法为患者治好病[22]。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医生具备同理心,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患者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恰恰又为当前我国一些医生所欠缺。
事实上,《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表明,患者认为医护人员解释问题态度好的比例为79.3%,认为医护人员倾听诉说病情认真程度好的比例为81.3%,仍有两成的医护人员未能耐心地向患者解释问题、倾听患者诉说病情[19]。
王阳明的基于万物一体的人我身体观解决了临床上的“同理心隔阂”。如果医生能够从万物一体的角度对待患者的话,就能真正理解患者的状况和切身感受患者的痛苦,让医生先在认知上和情绪上与患者产生共鸣,同时再将对患者状况的理解反馈给患者,从而提高医患沟通的效率,为医学注入人文精神。当然,作为患者及家属,同样要从医生的角度考量治疗的过程,推己及人,给予医生更多的信任和理解。
4.2 实施身心一体的医学关怀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医学的启示之二就是医生对患者的身心予以全面的医学关怀。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取得了飞跃发展,但同时也给临床诊治带来了新问题,很多医生过于关注检验指标和实验数据,这种“唯科学主义”看似很科学,实际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建立在西方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片面强调“身”的机械修复而忽视“心”的情感体验,这一切使得我国不少医生没有过多地将患者的切身感受加以考量,他们往往只见疾病,不见患者,缺乏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使得医学与人文疏离,医患关系日渐物化而缺乏和谐。
现代医学发展实践表明,关注患者的身体和心理感受不仅是获取判断疾病的依据,也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重要途径。王阳明“身心一体”的哲学思想为医生对患者的医学人文关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身心一体的视域中,“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关注与体验具体的活着的身体,帮助人们更科学地审视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境遇[23]。因此,有效的医患沟通不仅使医生更详实、全面、准确地了解患者及病情,而且也促进医患间情感交流和彼此的信任。患者一旦产生对医者的信任,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患者躯体的治疗作用有时甚至大于药物的治疗作用,它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信念。
就此而言,王阳明的身心一体思想促进现代医学方法论的转变,医生由关注患者的病情转变到关注患者的身心感受,这不仅是对医患关系问题的深层次探讨,更是对医学人文精神的一次新的注入。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仅需要医护人员对其身体予以诊疗,更渴望得到心灵上的安抚和精神上的支持。因此,基于身心一体的原理,医护人员应对患者的身心予以全面关怀,将患者视作朋友甚至亲人,主动、热情、无私、心甘情愿地安慰和关怀患者,这不仅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之一,也是医生的一种境界。
4.3 强调“知行合一”的医德履践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对现代医学的启示之三就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医德履践。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需要医生具备高超的医学技术和卓越的沟通能力,还需要医生具备高尚的医德。医德是调整医务人员与患者、医务人员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特殊表现[24]。树立良好的医德风尚,有利于医务人员积极从事医学研究,医治患者疾病,关心患者身心健康,转换医学模式,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德不仅仅是树立一种正确的道德认知,它更多地表现在对道德的履践上,要求医生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将医生的医德扩充到更为广阔的道德发动领域,同时也对医生的医德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为医生加强自身道德品质和修养提供了理论导向。为了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当前我国医生尤其需要加强这三个方面的道德实践:第一,医德首先体现在医生的进取精神上,而进取精神表现在对专业学科的积极探索,以及攻克医学难题的勇气上,通过这种探索医生方能更好地解除患者的痛苦,这不仅是医术提升的问题,更是医德实践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二,医德体现在医生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责任心。医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想办法解决患者的病痛,承担起救死扶伤的职责和使命。即便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病例也不能推卸责任,要积极安排会诊,或是转诊,而不致延误患者;不收住、诊治并不是自己专业的患者。第三,准确慎重地向患者告知病情,并给予必要的心理安慰,发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配合医生诊疗,同时增加其信心和决心。总而言之,医生在专注学科技术的同时,也要对患者怀着诚心、耐心、同情心、同理心,廉洁行医。唯此方能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而这一切都需要付诸道德实践,每一位医生都要做到知行合一。
显然,虽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其仍对当前我国解决医患矛盾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当然,我们在高度肯定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思想诞生于古代,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王阳明认识本心的开悟思想受不同个体的影响具有特殊性,致良知的实践方法由于受个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认知,且并未指出真正意义上具体认识良知的实践途径。所以,在认识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合理内核为今人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