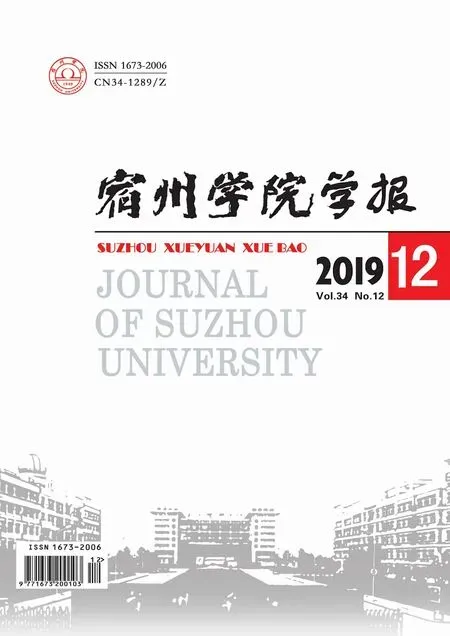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中心”
——以赛译本《水浒传》为例
陈珊珊
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1 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
生态翻译学起始于本世纪初,并在最近几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它兴起于中国,取向于文本生命,关注于译者生存,致力于翻译生态,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1]”。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种生态学视角或者生态学方法的翻译研究。它注重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主要从生态翻译的角度出发,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方法和现象进行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之后的七、八年间,他和其他研究者们主要是对理论的架构方面进行研究。“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的产品,符合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步伐。从新的角度来看,它也是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延伸,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从单一学科视角到跨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1]
近几年该理论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胡庚申[1]、许钧[2]、李亚舒[3]等主要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理论架构和相关焦点方面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对该理论做了一些应用性的研究,如刘艳芳[4]、孙迎春[5]、焦卫红[6]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大多选取生态翻译学中“适应选择”和“译者中心”两个焦点对相关文本进行解读,也有一些涉及到其他焦点,其中胡庚申曾尝试使用其中几个焦点解读傅雷的翻译思想,但“事后追惩”和“三维选择”等几点没有用到,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该理论只能解释好的现象,却不能对译者的行为进行约束,且多是从大环境方面来阐述。
2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中心”
2.1 译者中心的内涵
“译者中心”的内涵是由“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译者发展”构成的一个三元合一、辩证互补的思想体系。从翻译层面上看,“译者中心”是指译者主导,主要是为了凸显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也就是翻译活动中的一切翻译行为,如译者的“选择适应”与“适应选择”等,都需要由译者进行判断和决定。从翻译伦理层面上看,“译者中心”指的是译者责任。这主要是指译者需要在践行生态观、协调关系以及保持生态平衡与维护生态和谐等方面负责。而从价值论层面上来看,“译者中心”就是指译者发展。一方面,译者要适应并建构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译者也要改变自身的翻译生存状态,提高翻译能力,从而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在自身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7]。
2.2 生态翻译学与“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者之间的关系。从翻译角度来说,他/她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翻译活动只有在译者的主观意识和主导作用从头到尾都能完成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译者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动点上,既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也是翻译得以不断实现的基础所在。
“译者中心”的提出,旨在突出译者自身的中心地位及其主导作用,并试图从“译者中心”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新的描述和阐释,最终形成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译者中心”思想是考察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念,生态翻译学通过“译者中心”确立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作用、责任意识与主体发展,从而使翻译研究真正做到尊重译者和回归译者。“译者中心”思想随着生态翻译学“谁在译”的逐步延伸,不断拓展和运用,逐渐形成了“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译者发展”三者合而为一的辩证互补共同体[8]。
从译者行为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不难发现,翻译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适应与选择的现象。“译者中心”的取向是“翻译过程”和“翻译操作”,或者“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活动[9]。“译者中心”从本质上说,强调的是翻译“回归译者”,修正长期在翻译研究中只见“文”不见“人”的偏颇译论,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找到真正的“家园”,也就是要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中心”指的是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而不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中心”。
3 赛珍珠译本《水浒传》中的“译者中心”
翻译者的问题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由生态翻译学主要研究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之间关系这个特征决定的,因此生态翻译学倡导以人为本的“译者中心”,认为翻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是翻译成功的关键。
3.1 历史背景与赛译本《水浒传》中的“译者中心”
赛译本《水浒传》自1928年开始翻译到1932年翻译完成并出版,历时五年。殖民强权与中国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引起的中西文化争论,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歪曲和诽谤,都使得赛珍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它要求赛珍珠有选择性地向西方诠释中国,以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
赛珍珠对政治并不热衷,但是目睹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等多次社会变迁,她意识到穷苦的人民最终都是受害者。她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观察当时中国所有的政治变动。虽然她也未能明确地预见中国国共两党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她称赞共产党领导的才是“真正的农民运动,而以前的一切革命都不是。”[10]
赛珍珠结婚后曾在安徽省宿州市居住了五年。其间,她与许许多多普通农民群众成为了朋友。作为中国老百姓的贴心人,她真真切切地了解到了中国农民最真实的生活情况,“穷人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付出最多,所得最少。他们真实的生活离大地最近,交织着生与死,微笑与眼泪”[11]。赛珍珠亲眼目睹了中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也见证了他们与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难的抗争。他们的纯洁、善良和坚定深深打动了赛珍珠,让她决定以中国老百姓作为翻译和文学创作的主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衰败、无能和颓废暴露在西方世界面前。于是他们开始歪曲和诽谤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尊重和欣赏中国人及其文化。但赛珍珠出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深深的爱,并没有站在西方群体的文化偏见之中,她选择用翻译和创作文学作品来反驳西方的偏见,展示真实的中国。她努力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赛珍珠的这种内在情感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完美释放,“我最大的兴趣和乐趣总是在于人,因为我和中国人住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当我被别人问起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是这一个,也不是另一个,而是人。我们无法像描述自己祖先一样更详细地描述他们。我贴近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出于这个原因,我不喜欢那些作品把中国人描述为怪异荒谬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展示这个国家真实的一面。”[10]
在西方世界肆意诋毁中国人民和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赛珍珠开始通过文学创作和翻译将中国文化带入中国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特殊的历史语境向西方人展现客观而真实的中国。赛珍珠在中国的经历形成了她自己对世界、人类、社会等诸多事物的价值观,特别是她对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所有这些影响了赛珍珠翻译的主观选择,并在她的“译者中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 赛译本《水浒传》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
赛译本《水浒传》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水浒传》版本的选择和翻译文本的操控。赛珍珠在选择《水浒传》版本的时候,是在20世纪20年代,《水浒传》主要有六个版本,即百一十回《英雄谱》、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百二十四回《水浒传》、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七十回本《水浒传》。但是赛珍珠选择了七十回本《水浒传》。这一方面说明七十回本影响大、评价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赛珍珠作为译者“选当译之本”的主体中心性。到目前为止,《水浒传》的翻译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最引人关注且饱受争议的是赛译本《水浒传》。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中心”作用,这使得赛译本在诸多版本中脱颖而出。赛珍珠对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同情,决定了她对七十回本《水浒传》倍加青睐。另外,赛译本删掉原著结尾梁山好汉的悲剧结局的相关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11]。
第二,《水浒传》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赛珍珠本人是她翻译的主体,这给她的翻译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例如,她采用了直译优先的异化策略以及陌生化策略[12]。赛译本《水浒传》的译序提出“我尽可能直译 ,因为我认为汉语的风格与这题材极为匹配 ,我所要做的唯一努力便是使译文尽可能地与汉文相似 ,因为我希望不懂汉语的读者至少能依稀觉得他们在阅读原著。我尽力,尽管我未必能做到,保留原著的意义与风格”[10]。在西方肆意诋毁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东方文化遭蔑视,西方文化占主流,而赛珍珠却尽可能地保留原著的原貌,保持原作的语言和风格,展示最真实的作品和最真实的中国,她这种挑战以西方语言为权威导向的翻译惯例的做法也正体现出赛珍珠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的“译者中心”。她努力塑造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
第三,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立场选择。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一般来说,译者对待原语和译语会持三种文化立场:第一种立场倾向于认定原语文化,第二种倾向于认定译语文化,而第三种则是对两种文化的平等认定。采取第一种文化立场的译者往往会采用异化策略,第二种立场的译者会偏向于选择归化策略,而持第三种立场的译者就会将异化与归化策略相结合。赛珍珠选择使用直译优先的异化策略以及陌生化策略,恰恰体现出她认定原语文化的文化立场。这一点在序中的引言部分也有间接的体现[11]。这些都反映出赛珍珠对文化立场选择方面的“译者中心”。
4 结 语
生态翻译学是对翻译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这一兼容东西方思想的理论角度解读,既可以为研究赛译本《水浒传》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助于对赛译的深入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维度,对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