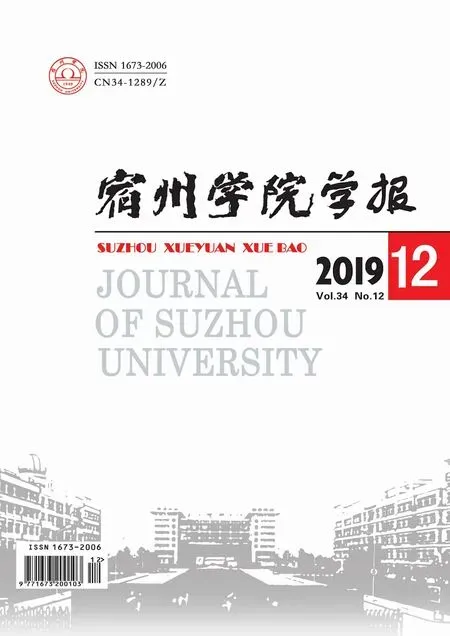《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物形象分析
李 红,陈 晨
1.宿州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宿州 ,234000;安徽工程技术学校,安徽宿州,234000
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个“孤独者”谱系。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些孤独者作为独异个人站在庸众的反面出现,似乎摆脱不了被淹没乃至被虐杀的命运[1]81;从《呐喊》到《彷徨》,孤独者的形象与命运有统一的一面,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早期作品中那尖锐的、挑战的狂人和烈士逐渐被痛苦的愤世者、中年的往事追忆者以及失去了往昔的自信、失望而伤感的厌世者所替代[1]91。孤独者的命运除了被淹没被虐杀之外,似乎也出现了在回忆或无聊的生活中沉沦这种较为温和的可能(如《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而终以激烈的自毁来复仇的《孤独者》可以说是这一谱系中的终结篇。《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形象与命运,是鲁迅对这一谱系小说的某种总结。在《孤独者》之后,鲁迅基本上也没有写过此类小说(只是在《故事新编》的某些篇目中,似乎还能看到“孤独者”的影子,如《铸剑》中的黑衣人)。文本通过对《孤独者》魏连殳的人物形象分析,探索鲁迅对孤独者的终结态度以及对孤独者命运的终极思考。
1 人物形象与心灵自我
小说《孤独者》是鲁迅“独异个人”小说系列的终结篇。对于这篇小说,鲁迅曾直言不讳地说:“那是写我自己的。”[2]的确如此,文中展现的魏连殳这个人物形象与人们知道的鲁迅十分相似:个头都不高,有些枯瘦,经常绷着脸,很严肃,神情看起来有些阴郁冷漠,同样孝顺长辈、溺爱孩子,都是吃过洋教的异类,都敢于反礼教、作抗争,都同样被流言追随、打击,被不理解的民众敌视、攻击。可以说“魏连殳是鲁迅与世界的对立关系中体验最为痛切、悲哀、愤怒的那部分的外化,并结合着他对中国式的绥惠略夫命运的思考,结合着纠缠鲁迅心灵的死去了的朋友(如范爱农)的影子。”[3]就连魏连殳经历的殓葬祖母、被流言与恶意包围等情节都来源自鲁迅的亲身经历,甚至一些细节,譬如小孩子拿一片草叶说“杀!”也是鲁迅在其他作品中记录过的、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情节,直接拿过来用的。
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气质像魏连殳如此酷似鲁迅。可以说,《孤独者》灌注了作者的灵魂,是鲁迅对早期启蒙主题痛苦地自觉疏离与回归,反映了作者孤独挣扎的内心。鲁迅翻译过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极为赞同书中的观点:“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4]138魏连殳的形象既是一个在庸众包围下绝望地进行着抗争的启蒙者,也是鲁迅心灵自我的外现,是一个和鲁迅一样一边孤军奋战一边寻找战斗意义的孤独的怀疑论者。
2 希望与绝望
2.1 绝 望
比较《呐喊》与《彷徨》中的孤独者,像狼一样长嚎的魏连殳是最为绝望的一个,也是对绝望进行反抗得最为激烈的一个。小说的开始是送殓场面,结局也是以送殓场面收尾。小说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匹受伤的狼”“长嚎”的情节也同时出现在小说的开始与结局部分:“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5]125-137小说中,鲁迅用“一匹受伤的狼”来形容魏连殳和“我”,是有意为之的。“狼”,代表的是一种反叛的精神,与驯化的、温顺的“狗”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狼与狗象征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与文化。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狼似的人物不容于世,被孤立、被敌视、被攻击、被驱逐,摆脱不了似乎是注定的悲惨命运。“魏连殳便是这样一只狼,一头闯入了一个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嗥叫、绝望,直至死亡。”[3]
魏连殳的绝望始源于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异类感。作为一个“吃洋教”的“新党”,他自动地被孤立,“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 ,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5]123但是魏连殳出人意料地全盘答应了众乡亲对于丧事的要求,开始的时候却“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5]123使得“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5]124然而,“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5]125
鲁迅在这里着重描写了魏连殳在祖母灵前的那种镇人心魄的、狼似的“长嚎”,这种嚎叫似乎一直盘旋在小说中间,极富质感,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定格在读者的脑海里。那种绝望的嚎叫,是魏连殳对祖母逝去的深切伤心,也是他长期压抑、孤独情感的一种宣泄,更是对置身于“铁屋子”却不自知、不觉醒、自甘麻木的庸众的一种哀悼。此时的绝望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
2.2 希 望
可在这悲哀之中,魏连殳还没有完全毁灭希望。这是因为魏连殳爱孩子。魏连殳给人的感觉是“冷”,文中多次提到他在黑气里闪闪发光的双眼,冷冷的神情,即使是在和文中的“我”这样一个同情者或者说是另一个孤独者这样一个同类相处的时候,他的态度也仍是冷冷的。但是在孩子面前,魏连殳的整个气质立马就变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5]127他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魏连殳这种热情,这种对孩子的爱,应该源于新式教育的结果和其未被污损的人性,也因为在他看来,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们总是好的,天真,孩子仍有希望。若后来变坏了,也是受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是被大人教坏的。此时,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他也曾一度把孩子看作是绝望中的希望,他对孩子特别的热情正是他反抗绝望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正是因为希望的存在,才有了反抗绝望的必要,希望一旦幻灭,反抗绝望也终将被绝望所湮灭。
2.3 毁 灭
终于,在希望与绝望的拉锯战中,绝望占了上风。文中,魏连殳最终用自我毁灭来回答自己对希望与绝望对抗的终极追问。“我”曾多次与魏连殳讨论孩子的天性,魏连殳把孩子当作希望,认为孩子的天性是好的,而“我”意见正好相反,提出了没有坏根苗就没有坏花果的观点。有趣的是,“我”与魏连殳似乎都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只是魏连殳的不坚持是痛苦地承认了希望的“不曾有”,而“我”的不坚持是表达了希望的“或许有”。“我”没法证明孩子的天性是好的,选择乐观的观点只是情感的需要;而魏连殳却有足够的证据承认希望的幻灭。魏连殳来看我时说起一个很小、甚至还不很能走路的小孩,拿一片草叶指着他说“杀”的事情,他深受打击,原先坚持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被现实颠覆了,“儿子正如老子一般”,孩子也可以像大人一样“都不像人”。[5]132魏连殳曾天真地以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5]129但情形怎样呢?大良、二良那群孩子拒绝了他,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启蒙主义者对民众自甘麻木现状的失望,已是一种巨大的无奈与悲哀,而对民众未来的希望的幻灭则是一种彻底的绝望。
连殳,与“连输”同音。鲁迅是想以此指出这些零余的启蒙主义者注定孤独战斗并注定失败走向绝望的命运吧。魏连殳在给我的信中也这样说:“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5]134这封极富鲁迅风格的信件是魏连殳绝望的绝命书,魏连殳由此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彻底绝望,以及由彻底绝望导致的对生存意义缺失的追问,这种追问的结果是以自毁来复仇。小说中间的情节里,魏连殳 “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5]135当了杜师长的顾问,然而魏连殳仅仅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就改弦更张,放弃了其启蒙主义的理念吗?回答是否定的。启蒙主义者一旦清醒,即使想要哄骗自己再去昏睡,也是做不到的。魏连殳在生命后期的转变是用自我毁灭来向这个无法被启蒙的冰冷愚昧世界的最后复仇,是用自我毁灭来承担这一代启蒙者未能履行启蒙任务的责任。魏连殳死时“不妥贴”地入殓,“口角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可笑的死尸”[5]137。启蒙主义者欲罢不能,明知无望,却注定只能前行。
3 终极追问与圆形结构
在评价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时候,鲁迅曾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4]141在《孤独者》中,鲁迅把人的灵魂中的两面性用两种声音表现了出来,鲁迅设置了一个魏连殳的同情者“我”(申飞)作为小说的叙述者。“申飞”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小说中申飞的境遇也同鲁迅的经历极为相似:因为“我”同情魏连殳,所以与之来往,为其奔走,结果这些却成为当时报纸抨击“我”的依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流言纷飞,压抑的氛围令人窒息,“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了上课之外,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嫌疑。”[5]131可以发现,这里的“我”很像鲁迅自己。可以说,“我”与魏连殳,小说的叙述者与主人公,这两个人物形象展现的是鲁迅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鲁迅内心存在的两种不同声音。鲁迅刻意调整了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安排它们在文章中形成数次交汇与反诘,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生命意义进行终极追问的结构。鲁迅内心的挣扎与犹疑也由此得以展现。这种追问通过代表鲁迅心灵的不同侧面的“我”和魏连殳先后发生的三次争论表现出来,这三次对话所提出的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悲凉,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指向那无尽的绝望。
3.1 第一个问题: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
“我”和魏连殳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孩子说起的。虽然话题是讨论孩子,但最终争论的却是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两人最初的观点相反。魏连殳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是好的,有希望,希望在孩子,而人的坏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存在改造的可能性。而“我”认为不然,人的本性不是环境造成的,人之初性本恶,“根苗”就是坏的,无法长出好“花果”来,因此没有改造的可能性,没有希望。两人从人的本性角度辩论人的生存有无希望,探讨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结果,两人的观点都被对方颠覆,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结论,而这正说明鲁迅自己的内心也很矛盾。
3.2 第二个问题:孤独是境由心生还是宿命
“我”和魏连殳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孤独。在同情者“我”的眼中,魏连殳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裹了起来,一次,“我”见到魏连殳惨淡的模样,劝说他应该看开一些,并提出孤独处境是由内心决定的观点,境由心造,要学会调整心态,尽快适应环境。魏连殳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谈起了他的祖母:祖母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他父亲的继母,虽然生活在一起,可祖母是孤独的,祖母也是不被理解的。当魏连殳终于咀嚼回味祖母的一生,理解了她的孤独,忽然发现这种亲手造成的孤独独自咀嚼竟是一种普遍的宿命:“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5]133。魏连殳否认了境由心造,认为孤独是不可改变的宿命,是注定的,且会代代相传。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刻画了旷野中狼嗥的“我”,这象征着“我”承继了魏连殳的命运,成为注定的孤独者。到这里,读者就会发现,祖母、魏连殳还有我都是孤独者,虽然三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有了孤独的传承,就像家谱一样,也存在一个“孤独者”谱系,代代相传。那么这种传承的机理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没办法变的?孤独到底是境由心生还是宿命?鲁迅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这是鲁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追问。
3.3 第三个问题:你为什么活
他们两人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更加深刻。最后魏连殳来求“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还得活几天!”就走了,“我”虽没说上话,可这句话却像火一样烙在了心上。一个晚上,“我”正想着魏连殳的时候收到了他的来信:“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5]134于是,两人之间争论的第三个问题出现了:你为什么活?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进行了追问。从“我”的视角,结合魏连殳的经历,鲁迅认为人有三种活法:第一个层次,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信仰而活,最初的魏连殳就是这样的活法,这也是庸众把他当作异端的原因。第二个层次,为爱我的人而活。此时的魏连殳不可能为理想、追求而活着了,因为理想已经完全破灭了。但“有人愿意我多活几天”,可能是来自父母、亲友的爱与期许,有了活下去的动力,魏连殳说,“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5]130。可是,结果,爱他的人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或者人们不爱他,不再对他寄予希望了。此时的魏连殳虽然绝望,可仍在反抗,因为他还想活着。最后,他被推到了第三个层次:为敌人而活。你不愿意我活,我偏要活着给你看!活给不愿意我活着的人看!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这样鲁迅就通过代表内心的两种声音相互交错的反诘与追问,最终给文章建构了一个由祖母到魏连殳,再由魏连殳到“我”的孤独者命运的圆形结构。小说既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也是以“一匹受伤的狼”始,以“一匹受伤的狼”终。“送殓”是魏连殳对祖母命运的继承,“一匹受伤的狼”则是“我”对魏连殳命运的继承。形式上,两次继承形成了闭合的圆形结构,本质上,两次继承似乎都没有完成,因为孤独者命运的承继没有终结。这个圆是没有划满的句点,但沿着这个孤独者谱系的轨迹,人们似乎依稀能够预见那些后来的孤独者们的命运,可以说魏连殳与“我”的对话与讨论是对孤独者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4 结 语
小说中的“我”与魏连殳一样都是孤独者,是鲁迅心灵的不同侧面。鲁迅通过魏连殳与“我”的对话和讨论,对孤独者的生命意义进行了终极追问,建构了一个前后照应,看似闭合的圆形结构,表现的却是孤独者代代相传的似乎无法摆脱的被离弃乃至被伐害的命运。在这种命运里,魏连殳的形象是一个代表,他是照着鲁迅自己的影子所画:他阴冷而决绝的形象,他对希望的追寻,于绝望中的反抗,以自毁而做的复仇,表现的正是鲁迅的心灵自我。在这里,鲁迅放弃了“听将令”[6]文学的呐喊,笃行起忠实于自我心灵的写作。因此,《孤独者》更接近鲁迅的内心,其艺术表现的形式也更加能体现出鲁迅的艺术主张,而通过对魏连殳这一孤独者中的代表人物形象,展现了鲁迅对孤独者的最终态度以及对孤独者命运的终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