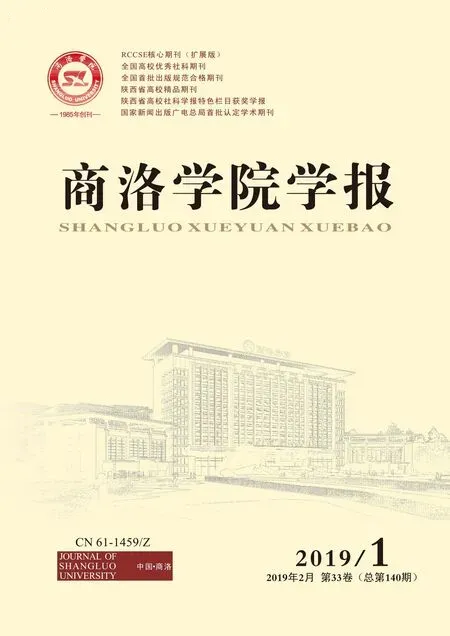从《郑伯克段于鄢》看《左传》的仁学史观与叙事策略
张勇
(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左传》亦文亦史,这使得《左传》中的人与事游走在想象与真实的“灰色地带”。《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就是一个典型,他究竟是一个残忍的“心机鬼”,还是一个仁爱的权力场中人?这是《左传》解读中代表性的分歧,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左传》文本的构造方式、《左传》记述的史实真相、《左传》作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解读者对《左传》所蕴含的儒学思想理论逻辑的把握程度。这些原因交错在一起,使《左传》的解释矛盾迄今未息。
围绕以上几方面,以《郑伯克段于鄢》为对象,从儒学的“仁学”理论与实践视角来解读郑庄公的历史形象,尝试以儒家“仁学”史观与“中庸”方法“体贴”《左传》的著述实践,一方面对《左传》作者的著史标准做出深化理解,另一方面尝试对《左传》的解读纷争做出理论的融合,力求化解《左传》解释的内在矛盾。
一、《左传》作者的仁学立场
《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作者是谁,这是一个迄今尚未定论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左传》思想主题的基本明确。有学者总结道:“《左传》一书,叙事议论,归本于礼……德和礼是《左传》作者臧否人物、评议成败的依据。”[1]甚至有学者说:“《左传》是一部道德因果指南,一个预言体系。”[2]因此,不论《左传》作者是谁,是一人还是多人,《左传》作者的儒学思想是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如果沿着儒学思想的逻辑展开,那么道德动机必然成为《左传》作者究心于此道的开端。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这个道德动机的开端,就表现在《左传》作者对“郑志”问题的诘问与显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左传》作者有一段历史评论,曰: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3]14
杨伯峻对“郑志”解释说:“郑志者,郑庄公之意志也……此言郑庄公养成叔段之罪,意在诛之,书法探其本心言之。”[3]14杨伯峻认为《左传》作者就是要通过“郑伯克段”揭露郑庄公纵容叔段,陷之于罪恶,然后诛之务尽的道德动机。杨伯峻对郑庄公道德动机的解释可能失之偏激,这个问题下文再论。但杨伯峻看到,解读郑庄公的“道德动机”是我们把握《左传》“书法”,读懂《左传》的重要门径。《左传》“书法”蕴含着《左传》作者的历史观念和叙事策略,而解读郑庄公的“郑志”就成了破解《左传》作者儒学历史观的突破口,也是直指《左传》作者“仁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儒家思想源于周代礼乐文明,开创于孔子,孔子以“仁者,爱人”及“克己复礼为仁”等仁学内容概括它。在孔子的仁学思想里,仁是我们与世界共生共荣的存在本质,爱是我们对待这种共生性事实的情感态度。因此,仁爱是人类的道德起源与道德情感,仁爱实践就是内化与外推这种差等有序的共生性关系,对个人来说,即是由“忠”而“恕”的修养历程。在现实生存中,每个人对私欲的征服(克己)、对道德秩序的坚守(复礼)是我们的人格使命。儒学的历史观中,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人与世界共生共荣的仁爱大同:历史的前进历程,就是从自我的仁爱觉醒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充满挑战,我们需要“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4]99的品质引导自己,才能实现道德理想。因此,在儒家看来,历史的前途取决于我们道德“仁心”的肯认(recognizing)与实践,这种道德“仁心”就是《中庸》所言的“唯天下之至诚,则可以与天地参”[5]的主体精神。
结合儒家仁学理论与考古成果,解读《左传》作者的著史立场,可以看出:《左传》作者是对儒家“仁学”有着深刻体悟的历史学家,《左传》作者笔下的“郑志”,就是《左传》作者所体认的儒家“仁爱”之心。
首先,《左传》作者已经表现出对儒学思想的自主发挥与深入理解。杨伯峻认为,《左传》作者“其人可能受孔子影响,但是儒家别派。”[3]33对《左传》作者的儒学思想倾向,现代学者明确指出:“总的说来,《左传》的思想倾向基本是属于儒家的,左氏宣扬的是儒家的政治主张,维护的是儒家的道德规范。”[6]50对《左传》中的儒家思想内涵,史继东更深入地解释道:“虽然认为《左传》是一部道德指南或预言体系可能有点过分了,但确实有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贯穿全书。这是一部高度道德化的历史,它认为历史的发展应该符合道德的要求,并且把这一观点渗透到具体的叙事中。”[7]85这个“道德原则”就是:“以德聚人心安天下,最终是要让天下纳入礼的秩序中,德礼一体,实际上就是《左传》构建理想政治秩序的最佳模式。”[7]45
但不可否认,学者们也都看到了《左传》儒学思想的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并不影响《左传》作者对儒学思想的深刻把握。第一,虽然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君子人格的自觉、外化的“忠恕之道”是仁学思想的核心,但《左传》是历史书,它要臧否人物以匡扶世道人心,因此,《左传》中“仁”的概念并未高频出现,《左传》更关注的是让、忠、信、敬等交往伦理范畴,这是儒学实践中“情境伦理”的要求,它体现了儒学实践中的“经权”辩证精神。第二,“《左传》认为,只要以德行事,礼的规范就能得到保证。以德立身者,必然守礼……《左传》经常从礼仪形式的背后去评价人的内在道德。”[7]48《左传》的“德礼”关系,与孔子所言“仁礼”关系并无不同。况且,《左传》已经将“礼”与“仪”作了区分,使“礼”与“德”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赵伯雄说:“左氏在‘礼’与‘仪’的区别上与女叔齐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左传》的这种思想,也正与孔子相通,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子不是明明在说,对于礼,我们不能仅注重外表的形式和礼物之类物质的东西,更要注重礼的本质上的功能吗!”[6]58
《左传》作者立足于历史现实,以“德”“礼”为标准臧否事件与人物,“仁”字虽不是《左传》的高频词,但并不意味着“仁”的精神不能成为《左传》的著史灵魂。就像孔子日常“罕言利与命与仁”[4]101,但这并不意味着“仁”在孔子思想中不是思想核心。《左传》以“德礼一体”为著史标准,但如果没有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德礼”精神只会散漫无系,道德理想与现实历史交互作用从而恢复礼乐文明的目标就不能在著作中体现出来。如果说《左传》作者属于儒家“别派”,也许只能说《左传》作者面对战国时代的新情况,在复兴礼乐的文化使命中,对儒家“仁学”的关注与实践重心与孔子儒学有所不同罢了。
其次,《左传》作者对“郑伯克段”的史实取舍中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仁学道德史观。最新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文献《郑武夫人规孺子》,为研究郑庄公与武姜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最贴近史实的依据。郑庄公继位前,郑国具有深厚的贵族民主政治传统,武姜曾经在武公质于卫国的三年之间,独立支撑了郑国的政治局面[8]。郑庄公继位初年,君权虚弱,母后权重,他所依靠的是祭仲这样的少壮派贵族,而武姜依靠的是旧贵族集团的支持,郑庄公实为“弱君”[9]。因此,郑庄公对母弟二人的妥协并不是欲擒故纵的阴谋,而是现实的权力格局使然。但是,《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文本,将“郑伯克段”的动乱起笔于庄公“寤生”这样的偶然事件,因这一偶然事件引起了武姜“恶庄而宠段”的情感错乱,并最终酿成了郑国的政治内乱。《左传》作者将郑国政治的贵族民主传统与母强子弱的现实权力背景隐而不写,这种叙事取舍,表现了《左传》作者鲜明的著史意识,也突显了“伦理情感”对历史运动的支配作用,这是儒家仁学道德史观使然。对此,史继东指出:“《左传》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整个事件按照道德的发展水到渠成。在这个故事中,叙事者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对人物行为的道德意义作后果的评价,而是把道德意义作为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7]85因此,深入《左传》作者的仁学史观,透彻地展开其“仁学”理论逻辑,是我们准确解读郑庄公人物形象与叙事策略的关键。
二、《左传》的叙事策略
儒学的道德史观里,“智、仁、勇”的仁心肯认与伦理实践是历史治乱的真正奥秘。因此,智慧而纯粹的仁爱情感是《左传》“郑伯克段”事件中历史叙事与人物塑造的隐秘原则。
其一,以“爱”的情感作为历史运动与历史叙事的开端。在“郑伯克段”中,事件开篇的“初”字有其深意,有研究者指出:在《郑伯克段于鄢》中,“初”字起着说明“事发于青萍之末,引领事件原因的功能。”[10]“初”字后紧接的事件过程是“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3]9《左传》作者一气呵成,将母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政治动乱归根于一场偶然的难产与姜氏对二子截然相反的隐秘情感。很明显,《左传》作者以“初”字指明,郑国的这场动乱就发端于一个母亲昏愦的“爱”之情感,她既没有真正地爱自己的长子,更没有智慧地爱自己的小儿子,只是因为“寤生”的偶然事件,她远离了“智、仁、勇”的仁爱原则,但她贵为母后,她的一念之差而陷国家于危乱。《左传》作者将“郑伯克段”的原因归结于一个母亲对血缘之爱的偏私就是要告诉人们,智仁勇的仁爱修养与实践就是历史治乱、吉凶祸福的奥妙所在。
其二,以“仁爱”情感作为历史运动与历史叙事的归宿。“郑伯克段”一文中的“颍考叔舍肉感庄公”情节,实则是《左传》作者表达仁学史观而独具匠心的叙事安排。
对于颍考叔舍肉情节,清人林云铭认为它极为突兀,认为颍考叔就是一个“局外人”,但又说这“局外人”的出现是《左传》作者自有深意的安排,林云铭曰:
通篇只写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人赞叹作结。意以公等本不孝,即末后二着,是他人爱母施及,与公无与,所以深恶之。此言外微词也。[11]
林云铭的话暗示着,颍考叔情节只是《左传》作者为了刻画郑庄公的虚伪而安排出来的,这一情节甚至可能是《左传》作者因抒情(“深恶之”)需要而虚构想象的。
“颍考叔”的出现的确突兀,如果去掉这个情节也不会损害“郑伯克段”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但郑庄公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单薄,整个事件就少了耐人寻味的启发,少了的“味”是什么呢?就是道德情感的修养对人物命运、历史治乱的深刻价值。《左传》作者“独白”式地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3]15-16
《左传》作者续写“颍考叔舍肉”情节的意义在于:《左传》作者认为,“克段”之后,郑国的变乱还未真正结束,因为郑庄公的内心还很“乱”。在儒家看来,情理和谐、内外相安才是社会历史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论语》中孔子“吾与点也”之叹的文化意义。在“郑伯克段”中,郑庄公虽有“孝爱”的道德情感,但也有现实权力争夺的“算计”,其仁爱情感并不纯粹,但因为颍考叔“纯粹”仁心(“纯孝”)的启迪,最终使其母子二人和好如初。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参与者道德仁心的觉醒与升华,最终在人心和乐、伦理合情中真正结束。在《左传》作者看来,这才是“郑伯克段”事件应有的结局,否则这段历史只是欲望的泛滥与你死我活的残杀。这样的历史不能给人类以启迪与希望,而只有道德情感的“纯粹”才是最终引领历史风暴中的所有人走出欲望黑夜的“灯塔”。这段奇诡的叙事情节,是《左传》作者其于仁学史观的精心构造。
三、仁爱“中庸”修养与“郑伯克段”的解读原则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64“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它也是孔子“求仁”的辩证方法。对认识主体而言,“中庸”原则要人保持“空空如也”[4]89的心理状态和“勿意、勿我、勿固、勿必”[4]87的理性态度,从而使主体保持对骄激情绪与偏见的警惕。这样才能将逻辑与历史、人道与天道“执中”地贯通起来,从而将人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给以“同情的理解”。一个具有“中庸”境界与方法的历史学家,他要以“体贴”的态度,看到人类在逻辑与历史中的生存复杂性,并且体验到生活世界中爱与恨、共生性与排他性、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生存张力——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仁爱本性与历史情境张力的矛盾统一体。因此,他必须以戒慎恐惧而又平静中和的本体体验坚守仁爱的信念,同时对历史情境中的每个角色给予“仁道”的同情。他的历史写作要持论“平正”,他需要戒慎恐惧而又平静中和地“体贴”写作对象,既要洞察到“人心”的复杂软弱,也要看见“道心”的微妙光明。智仁勇相统一的中庸境界与方法是一个历史学家必备的主体能力(同样,也是读者读懂历史的主体能力)。“郑伯克段于鄢”的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就体现了作者的“中庸”修养与历史解读原则。
首先,“郑伯克段”的历史叙事跌宕而节制,体现了中正平和的叙事风格。在作品中,当叔段日壮,少壮派的祭仲等人一次次地呼吁郑庄公尽快出手,他却一次次地犹豫,直到其母弟内外勾结要袭郑时,他才出兵。至于“克段”的结果,《左传》也只写到“大叔出奔共”便告结束。《左传》为何只写到“大叔出奔共”,而不像《公羊》《谷梁》写庄公杀死了叔段?首先,郑伯可能的确没有杀死叔段,杨伯峻引证说:“郑伯于隐十一年犹云‘寡人有一弟,不能和谐,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段实未死。”[3]14这是儒家仁爱修养使然:一方面,仁学的“爱人”原则要作者保持人道的同情,尤其对手足相残的人伦惨剧在记录时要有节制平和的态度,要有同情爱人之心;另一方面,从仁学的“中庸”境界看,“郑伯克段”事件中的叔段有罪(“不弟”),但郑伯也应受到批评(“不兄”)。《左传》作者评论《春秋》经说:“不言出奔,难之也。”杨伯峻研究《左传》书法时,指出“出奔”为有罪之词,但《左传》作者“若书段出奔共,则有专罪叔段之嫌;其实庄公亦有罪,若言出奔,则难于下笔,故云‘难之’”[3]14。杨伯峻对《左传》作者良苦用心的体会是恰当的。《左传》作者就是要将批评与肯定、含蓄与明确几种对立的态度全部囊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既维护着“为尊者讳”的礼制,又隐含着对庄公仁孝不纯的批评;既揭露了叔段逾越人伦的罪过,又在节制的叙事与事因的发掘中给以同情。作者对事件中的所有人都给予“同情的理解”,这种“中庸”的辩证评价的确难于下笔,《左传》作者仁爱的中庸境界与历史解读方法是我们理解“郑伯克段”叙事策略的钥匙。
其次,《左传》作者的“中庸”修养与方法,使《左传》笔下的郑庄公呈现为道德情感与私欲交织、个人情感与伦理情境紧密融合的立体形象。在“大叔出奔共”后,庄公软禁其母,不久“既而悔之”。这些情节往往被人理解为《左传》作者为了表现郑庄公虚伪至极、玩弄阴谋的个性,这其实是仅从艺术效果角度所做的审美判断,如果站在儒家“仁学”修养境界来看,郑庄公就是一个“天理”“人欲”交争的伦理困境中人。他的内心虽有“人心”的无奈、犹豫,甚至守护权力的狠辣,但也有仁爱“道心”的微妙闪光。这种对人的辩证认识,使作品中的郑庄公显得格外真实。对“郑伯克段”中郑庄公的“仁爱”本性与道德实践的复杂性,苏轼分析道:
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爱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段于鄢”。以为当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然则圣人固不使至此也……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12]67
苏轼认为,庄公深爱其弟,但他却不智地破坏了仁爱的法则(“而郑庄公贼之也”),这导致了叔段贪婪无极的恶果,以至于即使圣人在世也无法阻止其兄弟反目。苏轼站在“智仁勇”的仁爱“中庸”境界体贴古人,发掘出郑庄公内心世界的人性之爱,同时也看到郑庄公错误的仁爱实践在历史情境中导致了这场手足悲剧。苏轼对仁爱道德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与冲突的体会极深。苏轼在其著名的省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12]34《左传》作者对“郑伯克段”事件中的人物评价时,就体现了“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的“中庸”辩证原则,作品对郑庄公的复杂评价也体现了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仁学修养。因此苏轼说只有《左传》作者才把握了孔子写作《春秋》的“圣人之意”。体贴“智、仁、勇”的仁爱至德之艰难,一个人就会中庸辩证地评价或书写历史,“中庸”修养与方法是《左传》作者展开历史叙事的隐秘原则。
四、结语
以“郑伯克段”为例,运用儒家“仁爱”理论,可以使《左传》的解释从碎片化的解构性解读中“挽救”出来。美国学者李惠仪说:“《左传》的评论只针对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行举止,而非其本性。”[13]68“后世许多评论家都确信《左传》有一贯彻始终的崇高的道德标准。虽然在我看来,这个标准非常含糊。”[13]75李惠仪的解释代表了一种现代解构方法,但对于儒学经典《左传》而言,意识形态教化是其著述的隐含使命。因此,它的写作必然带有价值建构的意图,保持一种建构性的解读方法,也许更能贴近《左传》写作的本意。
从《郑伯克段于鄢》中,可以看到,“郑伯克段”中的每个人都因“爱”而“粉墨登场”,儒家的仁学史观与“中庸”修养深刻地塑造了“郑伯克段”的历史叙事。《左传》作者以“智仁勇”的仁爱修养对历史给以“同情的理解”,读者也应以这样的修养“体贴”古人,从而认识历史真谛并实现天人贯通的升华,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左传》教化人心的儒家写作目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体现了作者的儒家道德唯心史观,但儒家仁学的中庸境界与辩证方法,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幻、寓奇诡于庄严的风格;作品读来,血腥杀伐气少,温柔敦厚情多,表现出儒家经典作品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品格,这也使得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传散文呈现出经学为脉、经史文相融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