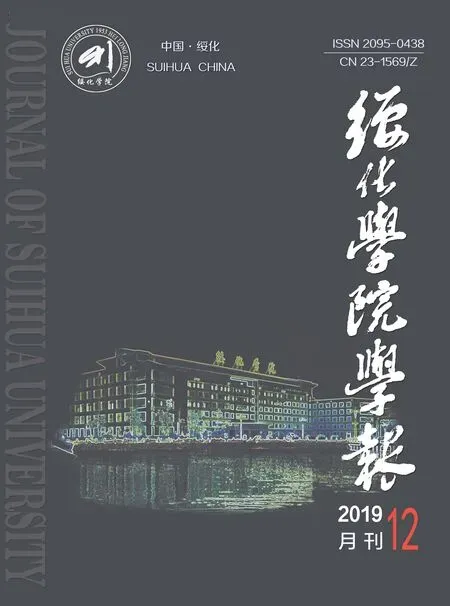论电影《霸王别姬》意蕴的多义性
刘靖云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文学意蕴的多义性在一些大型的叙事性作品中经常出现。由于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丰富、复杂,作品的形象也可以同时承载多方面的意义,文学意蕴也就自然具有多义性。”[1](P94)
电影《霸王别姬》正是这样一部意蕴丰富、具有多义解读空间的经典艺术作品。影片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霸王别姬》,于1993年上映,于2005年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影片虽然以程蝶衣和段小楼的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作为全片的叙述主线,但是在时长近三小时的叙述中却丝毫没有落入欲望化、低俗化或空洞化的窠臼,反而凭借其意蕴的多义性,凭借对人生社会和文化的形而下与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吸引了不同阶层、审美趣味的观众,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因此,探究影片《霸王别姬》的意蕴的多义性与深刻性,对于理解《霸王别姬》如何成为经典,乃至认识经典的大型叙事性作品在意蕴上的共通性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解读《霸王别姬》的丰富意蕴:个体层面——对生存的挣扎与对情感的渴望;社会层面——政治历史的变迁;文化层面——京剧的兴衰。同时,在每一重意蕴当中,又分为形而下意蕴——具体的情感观念、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形而上意蕴——普遍永恒的精神体验和哲理思考。
一、个体层面:生存与情感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情感纠缠维持了大半辈子,从民国初期的相识到文革之后在舞台上的重逢,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不疯魔,不成活”的痴情绝恋以最后的自刎得以谢幕。——这种具体的情感观念和纠葛过程属于形而下意蕴。
而在程蝶衣的这种独特而疯狂的痴恋背后,其实隐含了个体生命的某些真相,即个体对于生存的挣扎和对情感的渴望,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个体的异化、情感的缺失不平衡对个体心灵所造成的创伤。——这种普遍永恒的精神体验属于形而上意蕴。
影片在展示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情感纠葛时,不仅细致地表现了两人具体的情感变化过程的形而下意蕴,还致力于挖掘具有普遍深刻的人性内涵的形而上意蕴。
(一)生存的挣扎。程蝶衣同性恋情结的背后透露出人类对于生存的挣扎与无奈。程蝶衣的同性恋情结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和后天性别的扭曲异化密切相关。影片中的开头用大段的镜头表现了程蝶衣的性别扭曲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因素。程蝶衣并不是天生具有非正常的性取向,而是为环境所逼、为生存所迫。蝶衣本来认为自己是“男儿郎”,并非是“女娇娥”,然而这种潜意识的本能阻碍了他演旦角的成功之路。在他本能地又一次唱出“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经理听了这唱错的台词转头就走,师兄眼看蝶衣的旦角之路就此毁灭,拿起一烟斗往蝶衣嘴里捣,直到鲜血直流,蝶衣才终于唱对了《思凡》的戏词,即“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蝶衣的唱戏前途是保住了,然而他的性别意识却不可逆转地扭曲了。戏成全了程蝶衣,让他不再为温饱而发愁,并为他带来了无上的风光,但是也毁灭了程蝶衣,让他陷入了不为世俗接受的畸形之恋中。
如果再联系到影片开头程蝶衣为了唱戏而断送的一根手指——其母为了让年幼的蝶衣能被戏班子负责人关师傅收下为徒,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用菜刀砍下了阻碍蝶衣唱戏表演的一根多余的手指。综合来看,生理上的摧残尚在其次,更可怕的是心理层面的性别意识的颠覆,为了生存程蝶衣可谓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现实生活中的观众未必都有性别意识的扭曲,但是却都有普遍的为生存而挣扎的经历。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与命运抗争,付出极大的努力与沉痛的代价,不论是肉体之上的奔波劳碌,还是心灵之上的扭曲与创伤。正如影片中关师傅所说,“人要自个儿成全自己”。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成功,也正是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人类普遍的母题——生存之战。萧红的《生死场》被鲁迅所赞誉,原因之一也在于它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2]。人类为了生存而迸发出的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量,蕴含了无限的张力和伟大悲壮的色彩,然而同时人类也多少被生存环境所部分地无奈的异化、妥协。
(二)情感的渴望。程蝶衣的同性恋情结的背后透露出人类对情感的普遍渴求、以及当渴求无法满足时心灵的异化。程蝶衣之所以对师兄产生同性之恋,不仅和他为了唱戏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性别意识有关,还和他对情感的渴求和在情感方面的失衡有重要关系。程蝶衣在亲情方面是缺失的。电影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揭示了程蝶衣的内心世界:功成名就的蝶衣始终无法释怀亲情的缺失,他的母亲把他送到戏班子之后就再没来看过他,他不知道母亲的地址,却一遍遍地让人替他写信,然后独自一人把信烧掉。而在友情方面,戏班子的小伙伴知道蝶衣是妓女所生,对蝶衣进行侮辱欺压。蝶衣唯一的朋友只有维护他的师兄,为了帮程蝶衣练功偷工减料而被罚到雪地跪了一夜的师兄。亲情和友情的缺失,让孤独无依的程蝶衣把所有情感倾注在自己百般照顾的师兄身上。
影片中菊仙和程蝶衣虽然是几十年的情敌关系,但是他俩其实都是对感情的无比渴望和热忱恰恰是最相像的。菊仙虽然在世人眼中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妓女,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女子对情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和奉献。爱情是菊仙的生命和信仰。当菊仙一旦下定决心和段小楼成亲时,她便一生无条件地追随段小楼,无论贫贱。但是当文革时段小楼说出不爱自己这样绝情的话时,她的信仰破灭了,她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爱情。原著《霸王别姬》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3](P3)为开头,然而在这个宏大的故事中,最有情有义、对感情最为执着和渴望的却是作为妓女的菊仙和作为戏子的程蝶衣。
影片中的情感纠葛虽然独特,同性之恋和异性之恋交织在一起,但是从菊仙和程蝶衣身上反映出的对情感的普遍渴求却是人类普遍永恒的精神体验。生存固然是生命个体基本需求,但有此远远构不成生命的真谛,孤独无依、情感的匮乏有时比死亡更可怕。作为生命的个体,亲情、友情和爱情构成了一个人在情感层面基本的需求框架。当一个人在情感方面获得了这三者的满足,其情感方面往往处于平衡之中。反之往往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疯狂补偿。程蝶衣的情感正是情感极度匮乏与失衡者。这种沉痛的无奈,影片用一幕幕或残酷、或温暖的镜头表现了出来。
陈凯歌在拍摄电影中反复强调,“我拍电影时反复对摄制组的同志说:‘咱们不可以耍花活,咱们要做的,一定要和自己对人生、对人的思考有关’”。[4](P112)影片对程蝶衣的同性恋情节的揭示就体现了陈凯歌的这种坚持,即影片并不着重刻画同性恋本身或者窥探欲望本身,并没有借此“耍花活”而哗众取宠,而是着重探索同性恋产生背后的深刻人性因素。这便从生动具体的形而下意蕴上升到对形而上意蕴的探索之上。如果说形而下意蕴赋予影片以生动性和感染性,那么形而上意蕴则赋予影片以深刻性。正如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的人心的秘密。”[5](P11)
二、社会层面:政治历史变迁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情感纠葛和命运沉浮固然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其背后所经历的时代变迁、政治变幻却使得俩人的遭际具有深刻的时代历史内涵。在影片《霸王别姬》近3小时的播放时长中,跨越了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历史。从民国、抗日战争,到共产党掌权执政、文革、改革开放,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人生经历被深深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种对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传达构成了社会层面的形而下意蕴。
程蝶衣和段小楼作为历史潮流中的芸芸众生,其情感、生存、遭际乃至心境品格,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出历史的语境。——这种个体受到社会、政治历史拨弄的不可抗拒性,构成了社会层面的形而上意蕴。
程蝶衣和段小楼相识之时,均是懵懂小儿,此时正值民国。前朝大太监张公公仗着在清朝时期积攒的财富,风光无限,俯视众生般地看着唱戏的角儿程蝶衣和段小楼,程蝶衣在张公公的屋中看到琳琅满目的宝物正是张公公财富的象征。然而数十年后,程蝶衣再见张公公时,却发现昔日听自己唱戏并且对自己实施性欺凌的这一权贵,此时却坐在大街上,衣衫褴褛地拿着破碗,神情呆滞地乞讨。张公公的荣华和落魄正是清朝遗老被历史彻底吞没的一个缩影。
随着外敌的入侵,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生活轨迹和情感命运也受到波及。抗日战争时,程蝶衣为了营救出坐牢的段小楼,给日本人唱了戏,这让重视气节的段小楼无比气愤,不惜与蝶衣断绝关系。在日军侵占中国的时期,底层的普通人民在日军面前不得不让三分,日军在中国横行霸道,具有无上的权势。有的人铮铮铁骨不畏强权,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委曲求全,而有的人对日本人谄媚做了汉奸。没有人能置身这一时代的风云变幻之外。
共产党赶走日军之后,国内刚太平不久,又兴起了文化大革命。表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的影视片段也有,但是表现文革对于人性的摧残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表现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的影视片段却不多。影片《霸王别姬》通过段小楼的前后对比,血淋淋地表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尊严的毁灭性打击。段小楼曾经大义凛然地瞧不起程蝶衣给日本人唱戏,哪怕这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但是段小楼却在文革风波之中,丢失了自己的气节。他在被批斗时,被逼得揭发了程蝶衣和袁四爷的特殊关系,撇清了和妓女菊仙的关系,引得菊仙绝望自杀。在文革面前,人性和尊严被践踏。段小楼在年少气盛的时候,面对欺负调戏菊仙的恶霸,为了恫吓对方,段小楼用砖头狠狠砸了自己脑门,而脑门却未流血。而文革时期,段小楼被抓去问讯拷打,红卫兵用砖头再砸他的脑门时,一股鲜血却顺着他的脑袋流了下来。这一画面象征了段小楼已经无法如年轻时候那样无所畏惧、具有反抗黑暗的勇气和能力。他老了,他的尊严也将在这场风波中被消蚀殆尽。文革,这是无数人不愿提起的伤口和往事。巴金在《忏悔录》中深深忏悔了自己为了活下去所不得不做的违心之事、违心之话。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有的成为时代风波的受害者,有的不得不在某种程度成为施害者,还有的人二者兼具。但无论怎样,这段记忆将被历史所铭记,这段教训将被后来的人们所吸取。
每个人都脱离不了固有的时代,每个人都免不了被时代拨弄而浮沉的命运。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情感和命运受到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影响,由此折射出个体在历史的潮流面前的渺小与无奈。而反过来,透过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一生,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也可从中得以窥见。这也正是《霸王别姬》在某造成的上具有气势磅礴、包容万象的史诗性的特点的原因。
三、文化层面:京剧兴衰
影片从段小楼和程蝶衣对待京剧的态度辐射开来,以宏大的视角表现了京剧在不同时期的盛衰和各式人物对京剧的坚守与传承,从而使影片具有浓厚的戏味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而影片的上映时间——1993年,这一时间点也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20世纪90年代,也正是京剧徽班进京的二百年,在这百年发展的过程中,京剧在经历了辉煌的同时也遭受了世人对它的冷落。这部作品因时而生,很好的将中华传统戏剧文化之精髓成功地被导演搬上了银幕,有力地将这一文化进行了传承与发展。”[6]
影片中程蝶衣与段小楼作为京剧艺人,其事业的上升与低潮,以及这背后折射的京剧的兴衰史,构成了文化层面的形而下意蕴。在京剧兴衰荣辱的浪潮中,各色人物对京剧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构成了文化层面的形而上意蕴。
(一)程蝶衣、段小楼与京剧。程蝶衣和段小楼结缘于戏——一个饰演楚霸王,一个饰演程蝶衣,同时也在《霸王别姬》这出戏中了结两人的缘分——蝶衣假戏真做,拔剑自刎,放下了对段小楼的感情,也放过了自己。
程蝶衣和段小楼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京剧的态度。程蝶衣入乎其内,把戏剧当成了人生,把人生过成了戏剧,所谓“不疯魔不成活”。段小楼出乎其外,把戏剧和人生分得清清楚楚,唱戏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师兄小楼为了生存放弃自己的科班所学,改行卖西瓜,而程蝶衣却可以为为了自己的事业据理力争。在程蝶衣的身上可以看出艺术家的精神骨髓,为了唱戏可以不要生活不要身体,只要灵魂的救赎。”[7]
(二)京剧:从民国到文革的发展兴衰史。京剧开始于“徽班进京”,于1840年前后成为继昆曲之后在全国风行的主要剧种,于同治光绪年间达到第一个顶峰,“同光十三绝”正是京剧盛世的有力体现。民国时期京剧的热度依旧不减。影片《霸王别姬》正是从这里开始叙述。当时的贵族、有钱人喜欢听戏,如影片中的大太监张公公、戏霸袁四爷,民间百姓也喜好听戏,戏班子在空地随便摆个场子,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唱得好的还会受到打赏。这两种谋生渠道保证了京戏戏班的存活和繁荣发展,正如关师傅对其弟子劝勉的:“你们算是运气好,赶上了京戏的好时代!”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动荡,中国国内有政党之争,外有列强日本等侵略。然而京剧却在动荡的时局下依然蓬勃发展。文革时期,京剧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旗下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京剧名角由于不服“管教”或者“看着不顺眼”而受到红卫兵的迫害。影片中即有一段文革时期程蝶衣为了捍卫京剧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据理力争的对话。随着程蝶衣一把火烧掉曾经的京剧华服,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辉煌时代随之结束。影片中通过具体场面不动声色地描绘出京剧的盛衰过程,也在无形中表达了对京剧辉煌时代的缅怀和对京剧衰落的惋惜。
(三)兴衰荣辱中的传承与坚守。然而,在此过程中,影片却通过各式人物对京剧的态度表达了对国粹艺术的尊重。首先,京剧得以传承,离不开兢兢业业把京剧作为毕生事业的这类人。关师傅虽然只是一个小戏班子的负责人,但他对于京戏有着高度自觉的传承精神和敬畏精神。到临死的一刻,他仍然声音洪亮地向学生示范《霸王别姬》的唱法,可谓为京剧的传承工作耗尽毕生心血。程蝶衣秉承师傅的教育,对徒弟依旧严苛。当他看到自己徒弟好高骛远、只肯投巧时,蝶衣恨铁不
成钢地鞭笞了徒弟。其次,京剧的传承离不开热爱京剧的一群人。“袁四爷”的人品或者生活作风姑且不论,但他对国粹的态度却令人动容。慧眼识珠捧红蝶衣,固然证明其对京剧的沉迷,然而在被批斗赴刑场的生死时刻,袁四爷还不忘走着四方戏步,高傲地走向死亡,这其中体现出的对于京戏深入骨髓的爱恋却让人肃然起敬。正是有这样一批懂得京剧艺术、把艺术看得如同生命一般珍贵的人,京剧才能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时期,都能放射出不朽的艺术之光,让后人得以领略富有魅力的京剧文化。
结语
影片《霸王别姬》在对程蝶衣和段小楼几十年的情感纠葛的叙述之中,蕴含了对个体层面的对生存的挣扎和对情感的渴望,历史层面的社会变迁、文化层面的京剧兴衰的三重意蕴,蕴含了对人性、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层面的深入思考,这种意蕴丰富性和深刻性是影片《霸王别姬》成为艺术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体现了诸多经典的大型叙事作品在意蕴上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