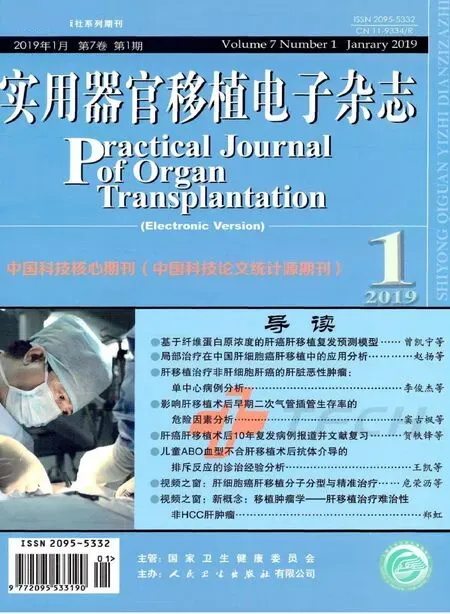心脏死亡供肝质量对移植肝的影响
许蜂蜂,蓝海斌 ,王华翔 ,杨芳 ,蔡秋程 ,刘建勇 ,江艺 (.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肝胆外科,福建 福州 5005; .蚌埠医学院教学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肝胆外科, 福建 福州 5005 ; . 解放军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 福建 福州 5005)
随着肝脏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以及肝移植术后受者管理的进步,肝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措施[1-2]。但随着等待肝移植患者数目的增加,每年因患者自身疾病的进展和供肝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正逐年增加。自90年代初,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的推广有效地扩大了供肝来源,虽然应用DCD供肝已经被证明可能增加移植后肝功能衰竭、肝动脉栓塞以及胆道并发症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的风险,但是等待移植期间的高病死率迫使患者在死亡或非理想供肝肝移植之间做出选择[3]。供体年龄、脂肪变性、冷-热缺血及再灌注损伤、高钠血症、病毒感染和肿瘤等均可对供肝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筛选高质量的供肝对移植术后肝功能的恢复、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1 供体年龄
供体年龄在肝移植质量评估中饱受争议,研究证实供者年龄越大,受者术后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缺血性胆管病变和死亡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越高[4]。2014年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上提出,年龄50 ~ 65岁可作为边缘供肝应用于肝移植中[5-6]。一般认为<50岁的供肝可安全应用于肝移植,研究人员认为供体年龄>60岁是导致移植失败的最大危险因素,由于老年肝脏的再生能力较弱,易受肝脂肪变性、冷-热缺血时间及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影响,术后血管、胆道并发症等并发症甚至与严重的丙型肝炎复发之间存在相关性[6-8]。但是,欧洲国家在边缘供肝方面对年龄的要求逐渐降低,扩大供肝池使得终末期肝病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并且现医疗技术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改变、老龄化速度减慢、肝再生能力强,在肝源短缺的情况下,高龄供肝逐渐被移植专家接受[9-10]。Firl等[11]和 Mayo 等[12]研究显示,DCD供体年龄与缺血性胆道损伤没有相关关系,尚且有数据分析高龄供肝与低龄者供肝两组之间移植受者生存率没有明显差异[13]。而且Firl等[11]研究表明,随着供体年龄的增加,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呈线性增长。但是,DCD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并没有增加,而且与低龄供体的风险一致。有学者提出在没有严格匹配供受体的情况下,儿童供肝因移植术后出现小肝综合征不建议应用于肝移植。Emre等[14]研究表明,供受者肝体积相匹配时儿童供肝应用于成人受者是安全的并可获得良好的效果,并认为当供肝重量与受者标准肝重之比>0.4时儿童供肝与成人供肝应用于成人受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受者的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采用严格的供体和受体选择标准的情况下,供体年龄本身并不是导致肝移植失败的危险因素,所以供体年龄并不是DCD肝移植拒绝的理由。
2 脂肪变性
脂肪变性增加肝移植术后肝功能障碍发生率,是肝移植失败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15-16]。超重或肥胖者易患脂肪肝,Schlegel等[17]研究发现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可能是DCD肝移植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体重指数>30 kg/m2与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18]。其原因为脂肪变性降低线粒体膜电位,导致线粒体功能退化。库普弗(Kupffer)细胞活动增加,肝血窦被破坏和缩小,这些变化使得肝细胞在冷缺血期间的细胞损伤增加。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脂肪变性会诱导肝脏的微循环和细胞变化,可能导致肝细胞坏死[19]。此外,脂肪肝的再生潜能也受到损害以至于脂肪肝不被移植专家接受。有学者认为,供体体重指数>25 kg/m2,应行病理检查明确脂肪变性的类型和程度。在组织学上,将脂肪变性分为小泡性脂肪变性和大泡性脂肪变性,又将大泡性脂肪变性分为轻度(< 30%)、中度(30% ~ 60%)、重度(> 60%)[18]。小泡性脂肪变性供肝可安全用于肝移植,不会引起肝移植的不良预后,可安全用于肝移植。与小泡性脂肪变性相比,大泡性脂肪变性更易对肝脏造成损伤,且与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障碍(primary nonfunction,PNF)、胆道并发症和丙型肝炎病毒复发有关[20]。中度大泡性脂肪变性(30% ~ 60%)被认为是导致移植物存活率低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应谨慎用于肝移植。研究表明,只要将冷缺血时间控制在8 h以内,合理选择受者,>30%脂肪肝也可获得良好结果[21]。重度脂肪变性是移植后肝功能衰竭的显著高危因素,不推荐使用,除非作为过渡性供肝。专家研究证实采用“无缺血”供肝方式移植>90%的大泡性脂肪肝受者术后无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原发性移植无功能不全等并发症。打破了大泡性脂肪变性超过60%的供肝不能临床使用的禁区,但对肝脂肪变性的准确评估仍然至关重要[22]。从外观上可粗略评估,脂肪变性肝脏颜色偏黄,边缘圆钝,而正常肝脏颜色较红润,边缘锐利,但具体程度仍需病理检查[23]。
3 冷-热缺血/再灌注损伤
DCD被认为是扩展标准供肝的途径之一,与DBD相比,DCD增加了热缺血损伤时间,增加了术后胆管非吻合性狭窄并发症的发生率。热缺血时间(donor warm ischemia time,DWIT)是器官从灌注不足〔收缩压<50 mmHg(1 mmHg=0.133 kPa)〕开始,到灌注液进入肝脏,肝脏内部温度降至4℃的过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进行性缺氧和持续低血压阶段。冷缺血时间(cold is chemia time,CIT):灌注液进入肝脏,肝脏内部温度降至4℃到术中肝脏开始恢复血流供应的过程[11]。Ilmakunnas等[24]研究表明肝损伤随着缺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导致受者病死率增加。长时间的热缺血时间会导致PNF的发生率升高并增加胆道并发症的发生,这是因为热缺血时间对敏感的胆道上皮细胞造成严重损害。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冷缺血时间是DCD肝移植存活率低下的风险因素,主要是因为内皮细胞激活引发一系列联级反应,导致微血管血栓形成和局部缺血,导致形成胆管狭窄、胆道坏死和胆管炎,最终导致胆道并发症[25-26]。Van等[27]认为经历热缺血后再经历冷缺血使DCD供肝易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IRI)。IRI是指缺血后恢复血流,原本受缺血损伤的器官更容易进一步加重损伤[28]。IRI 是引起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或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的最主要因素,炎症通路、免疫系统激活和自噬等作用,最终致肝细胞损伤。研究发现胆管上皮细胞对IRI的敏感性比肝细胞更高,因此冷-热缺血及IRI增加肝移植术后胆管并发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或远处的肝癌微转移[29-30]。随着技术发展,各种灌注保存液的出现,降低冷-热缺血/再灌注损伤造成的并发症的发生率,甚者何晓顺等[22]提出“无缺血”供肝,直接去除IRI这一过程,以最接近生理条件状态下移植给受者,移植术后肝功能情况较现有的供肝保存方案好。但冷-热缺血时间仍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热缺血时间<30 min和冷缺血时间<12 h供肝可安全应用于肝移植。
4 高钠血症
有报告示高钠血症与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PNF和移植肝初始功能不良的有关[31]。DCD供体常存在神经、体液调节功能失常,水电解质平衡紊乱,Renz等[32]将高钠血症定义为血清钠水平超过155 mmol/L,可增加肝功能不全及再次肝移植发生率,这与严重细胞损伤有关[33-34]。Powner等[35]研究发现,高钠血症可引起肝细胞内呈高渗状态,从而造成肝细胞肿胀、受损,导致使用高钠血症的供肝会显著降低移植物及患者的生存率,并且是肝移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高钠血症供肝与移植术后并发症之间并没有明显相关性[36]。Akoad等[37]和 Cywinsk等[38]等曾报道接受供体血清钠≥155 mmol/L的患者与接受<155 mmol/L的患者相比,术后肝功能及各种并发症没有统计学意义。故血清钠浓度并不是放弃供肝的主要因素,但是,在选择供体时血清钠<155 mmol/L仍是最佳选择[39]。
5 肝炎病毒感染
免疫抑制剂的出现使得肝移植成为挽救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方法,专家认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大多数移植术后仍需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乙肝病毒阳性及丙肝病毒阳性的供体常不被接受,认为病毒感染阳性肝移植有更高的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除此之外,有学者研究报道强烈的免疫抑制会促进丙肝复发并造成肝炎活动处于较严重的程度[40-41]。有学者认为,移植丙型病毒阳性供体决定其复发的主要因素是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 RNA阳性,而且供体年龄、脂肪肝以及使用脉冲剂量的皮质激素治疗急性HCV引起的排斥反应会增加HCV RNA定量值,降低受体存活率,增加整体病死率[42]。但 Ballarin 等[43]和 Trotter等[44]多位专家研究表明,HCV阳性供体的生存率与HCV阴性供体生存率相似,尚有研究显示HCV阳性供体移植到HCV阴性受者后有更高的复发风险但是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且丙肝阳性受者可获得良好的结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丙肝阳性供体可能受益于丙肝阳性受体。在肝移植中使用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供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肝移植受者本身大多数为乙肝病毒阳性患者,移植术后仍需要终生的抗HBV治疗。研究人员发现,HBsAg阳性供体与阴性供体在手术风险及移植术后并发症无明显差异且存活率相似[18-19]。HBsAg阳性供体的使用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即使是在HBsAg复发也能够再次控制它。因此,病毒感染阳性供体在严格筛选移植受体下,可安全应用于肝移植并且扩大供肝池[45]。
6 肿 瘤
高龄供体逐渐成为边缘供肝来源之一,其是否存在肿瘤,术前往往都是不清晰的,虽然肿瘤通过移植肝脏播散案例十分罕见。但医生必须考虑肿瘤细胞转移到受体,接受具有未知癌症病史的供肝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决定。在2003年研讨会上,肿瘤被认为是移植后肿瘤复发的风险因素之一,118个胶质母细胞瘤、黑素瘤、绒毛膜癌和肺癌被认为是对供体的绝对禁忌。就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而言,除了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外,其侵略性通过血脑屏障,使得肿瘤播散;对于乳腺癌和结肠癌等常见癌症,特别时疾病晚期(结肠癌阶段T3或乳腺癌T1c)被认为是绝对禁忌,但早期疾病可能是允许的,取决于确切的肿瘤阶段和无病间隔[46]。
综上所述,DCD作为边缘供体的一种手段,供体年龄、脂肪变性、冷-热缺血及再灌注损伤、高钠血症、病毒感染和肿瘤等对移植术后并发症均有影响,在优化获取供肝技术及严格遵循供受体选择标准下,使得 DCD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得到改善。因此,筛选高质量的供肝对移植术后肝功能的恢复和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