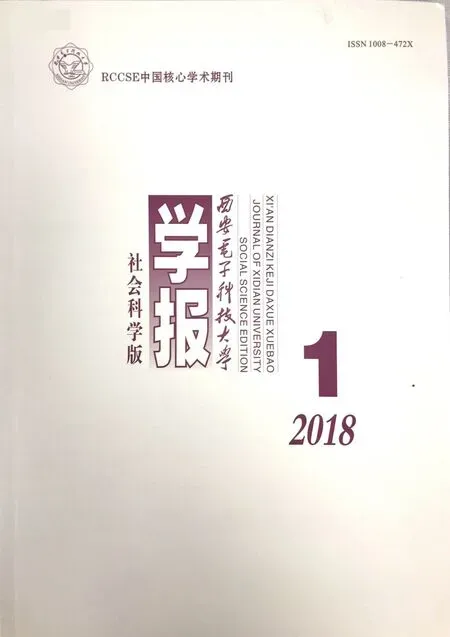论《呼兰河传》童年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李帆
李帆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童年视角的成功运用使《呼兰河传》具有了一种文本独特性。首先,《呼兰河传》舍弃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线,树立中心人物的叙事方式,而是用童年视角将看似零散的事件串联起来,从宏观叙事到局部聚焦,由面到点地描写了小城人们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其次,以儿童视角为主体叙事的同时,夹杂着成年人历经沧桑后的批判眼光,二者灵活变化,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三,萧红在作品中对故土进行了一种认同的反思,以儿童视角表达了对故土人情和人性的深沉关注。
《呼兰河传》;萧红;童年视角;叙事策略
《呼兰河传》的特色之一就是童年视角的成功运用。萧红在作品中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透过敏锐的儿童眼光描绘了呼兰河的风土人情,用充满诗意的童心来捕捉日常生活的片段,对当地传统旧俗和人情冷漠进行了控诉。童年视角的运用使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文体特征,影响并决定了作者的叙事策略,本文拟就《呼兰河传》所采用童年视角进行分析,并探讨基于童年视角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一、童年视角下的回忆性叙事与散文化结构
(一)儿童视角与“回忆性”叙事
《呼兰河传》用儿童视角去描写故土与童年的小说。有人认为,童年视角叙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叙事策略,是一种与成人视角不同的叙事策略。目前获得较多认同的一种解释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1]。萧红以“儿童眼光去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从而打造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展现不易被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2]。
《呼兰河传》舍弃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线、树立中心人物的叙事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创造出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3]。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大量回忆性小说的叙事都呈现散文化的特征,与这种回忆性叙事相伴的是童年视角。儿童思维是发散式、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善于捕捉片段化生活场景,这与回忆性叙事零散化、抒情化的特征相契合。成年萧红用情感将儿时零散而丰富的片段串联起来,初读时零散,反复阅读才能形成一个对整体的印象。
(二)以情感为主线的散文化结构:从宏观叙事到局部聚焦
《呼兰河传》采用了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视角转换的方式,叙事从宏观叙事到局部聚焦,从面到点,既描写了呼兰河城的全貌,也浓墨重彩了描绘了几个重点人物,全面而又具体地展示了小城风貌与人情世故。
《呼兰河传》第一、二章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以宏观方式描写了呼兰河这个东北闭塞的小城里人们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第一章以城内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为主线,描写了标志性的学堂、大泥坑、扎彩铺等,展示了呼兰河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保守麻木的风物人情。第二章描写了呼兰河的民风民俗以及一些精神盛宴: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的娘娘庙大会。前两章以风俗景观描写为主,但作者重点通过风物来重点写人,宏观地描绘了当地人自私、麻木与冷漠的人性。
从第三章开始,出现了“我”这个中心人物,叙事从广角式叙述转入局部式聚焦,并突出描写了几个重点人物——第五章的小团圆媳妇、第六章的有二伯、第七章的冯歪嘴子。这些不同人物和场景之间其实是缺乏有机联系的,并没有形成起承转合的因果关系,而全都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我”成为了一个贯穿整个叙事作品的线索人物。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把各个零散的故事片段聚合起来,控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封建习俗对人们的戕害。
二、童年视角为主的复合视角
回溯性叙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或隐或显的成年叙事者的声音,因为童年视角的作品永远站立着它的创作者——一个已经成年的作家。《呼兰河传》以儿童视角为主体叙事的同时,也夹杂着成年人历经沧桑后的批判眼光,二者灵活变换,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对比:童年视角与成年视角中的“后花园”
第三章童年视角观照下的“后花园”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灵气和诗意,洋溢着朴野的童真童趣。“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4]54。我和祖父读诗歌,最喜欢“两个黄鹂鸣翠柳”喜欢“人面桃花相映红”,因为我喜欢吃,听到黄鹂、桃花就想到“梨子、桃子”。用儿童的心理和眼光去观察和体验世界,才能获得如此多的乐趣。“只有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子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4]55。幕天席地的天人合一,洒脱不羁,这种对自然的体验通过儿童视角传递给读者,描述了一个成人向往的却不能倒回的儿童世界。萧红将自己童年的美好记忆和幸福体验刻入这一画面中,使读者能够与主人公感同身受,领略到那亲情的温暖和童年的快乐无忧。
当童年视角进行叙事时,画面活泼生动、充满童趣;而转换为成年视角的时候,生活本身的沉重、荒凉便被凸显出来。在第四章中,在成人理性视角中的“后花园”,则是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第四章多个大段均以“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开头。妙趣横生的后花园反复以“荒凉”的面貌出现,“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4]92。
(二)穿插:童年视角叙事中夹杂了成年视角
在《呼兰河传》的某些段落中,作者也穿插运用了全知叙事。作家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第一人称叙事中短暂地放弃第一人称有限式叙事视角,改而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式叙事视角”[5]。
为了让读者对团圆媳妇婆婆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五章穿插了大量婆婆个人的内心独白描写。为了给团圆媳妇治病,婆婆找来了云游真人抽贴。抽贴容易,可是每帖十吊钱却着实让婆婆心惊。她不禁想起了从前养鸡赚钱的艰辛,她简朴一辈子,被豆秧刺了手指甲,指头肿的像冬瓜,却也舍不得花三吊钱去买红花。但是为了给团圆媳妇治病,竟然拿出了五十吊钱。愚昧无知的婆婆一心想要把团圆媳妇规整成一个好媳妇,她把团圆媳妇折磨病了,又心痛地拿出钱来给小团圆媳妇求神治病,来之不易的钱都拱手让江湖骗子敲诈糊弄。
这里有大量的心理独白表现了婆婆的内心冲突。按理来说,第一人称“我”是无法洞察婆婆的内心世界的,只有全知全能视角才有这样的权力。因为萧红急切地需要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来影响读者的判断,所以才有了这样对人物心理的揣测分析,叙事视角也就随之具有了全知叙事的成分,但叙事主体仍然是“我”,叙事基本视点并没有发生转移。
三、反思与重现:童年视角下的情感表达
童年视角运用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作者对故土人情的深沉关注。呼兰河是萧红出生长大的地方,萧红对呼兰河的印象主要源自于她童年时期的记忆。《呼兰河传》书写了呼兰河乡民们生命意识的麻木,在儿童视角的关注下,隐藏着成年萧红的深深叹息。对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故土与童年记忆,哪怕残酷冷漠,也总会带有一丝余情。
(一)童年视角下的情感表达的陌生化与疏离化
通过儿童的眼光去观察成人世界的自然与人事,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留白”。例如第五章的小团圆媳妇之死,萧红用一个幼稚小姑娘的眼睛摄录下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画面,和成人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两次童年视角的运用格外引人注意。
第一次是“我”初见小团圆媳妇时,大人们议论小团圆媳妇太大方不像个团圆媳妇,而我觉得小团圆媳妇“怪好的”。我请她去我们草棵子里玩,她说:“我不去,他们不让。”以童年视角去描写小团圆媳妇,表现出小团圆媳孩童般的天真烂漫,不是大人眼中的那个不知羞、大模大样的小团圆媳妇。第二次出现在用大缸给小团圆媳妇洗澡——这是全书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开水烧滚了,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来了。“我”没有在外面看热闹,却来找小团圆媳妇玩,给她一个玻璃球和一片碗碟。小团圆媳妇趁着婆婆不在,用手指甲弹着这玻璃球,好玩心理和一般少女无异,但婆婆一来,马上用破棉袄把她没头没脑地蒙起来。在用滚烫的开水给小团圆媳妇洗澡时,“我看了半天,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满脸的汗珠,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张红纸。我跟祖父说:‘小团圆媳妇不叫了。’”
作者并没有悲恸地去描写小团圆媳妇如何被开水洗澡活活烫死,而周围看客们如何冷漠无情,她并不凌驾于人物之上,也不悲悯自己笔下的人物,而只是透过“我”这个未通人情世故的小女孩的眼睛,描述所看到的一切。没有强烈的情感倾诉,读者仍能感受到封建愚昧思想如何虐杀着人的精神和肉体,并进而去反思造成这悲剧背后的原因。儿童视角的“有限性”为读者留下了大量想象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二)童年视角下的怀旧题材与精神还乡
为了表现童年记忆与怀旧情结、实现精神还乡的心理需要,萧红对以往经验的零碎材料进行了理想化的“重新建构”。《呼兰河传》以优美传神的笔触状写了当地很多美丽的风景民俗,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作者的回忆。萧红用了大量笔墨去描写呼兰河傍晚美丽奇幻的“火烧云”,那美丽的颜色和多变的形状,装点着呼兰河黄昏的天空,也丰富了呼兰河人傍晚片刻的悠闲时光;比如七月十五日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4]35。热闹的野台子戏,接姑娘唤女婿,说媒探亲闲话家常。回娘家看戏的姑娘,给娘家的姐妹送礼,表面上似乎并不亲热,其实内心早已沟通着了,也不大吵大闹,只在夜深人静,轻轻把早已准备好的东西送至姐妹面前。萧红让这些“往事”在重构中得到了“新生”。
(三)充满悲悯的反思:批判及怀念
《呼兰河传》一方面对当地保守落后旧俗和冷漠人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呼兰河人守旧,补牙抓药只愿意去“李永春”药店,哪怕有更现代化的牙医和拔牙技术;呼兰河人不思进取,东二道街的“大泥坑”给呼兰河人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呼兰河人一年中抬车抬马,可是没有一个人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萧红反复强调“一个也没有”:“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呼兰河人冷漠,缺乏同情心。偶尔遇到一个不幸的人,刚想着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咬什么?’仆人答:‘咬一个讨饭的。’说完了也就完了。可见这讨饭人的活着是一钱不值了”[4]14。
另一方面,萧红对于很多生活其中的人民饱含了同情之心。比如冯歪嘴子,老婆死了,留下了两个孩子给他,在别人眼中,这个小儿子非死不可。这孩子一直不死,大家都觉得惊奇。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他照常地负者他那份责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就这样得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4]30。
她写涮粉的人:“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4]82。
她写拉磨的人:“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磨坊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越打越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声,没有同调”[4]86。
《呼兰河传》是萧红对个人童年生活的一段回望,通过童年视角,复现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那个保守落后的东北小城和当地人们的生活。萧红对于故乡既进行了批判又满怀眷恋。在她回忆故乡的时候,以祖父和后花园为中心的童年往事,在记忆中被美化和强化;而家乡落后愚昧的习俗又让她痛惜,那里的人们麻木愚昧却又浑然不知地生活着,不知生活意义所在也不去思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盲目又自欺,僵化而又无趣,如蝼蚁般保守而封闭地艰难生活着。这些矛盾对立使得呼兰河这片土地更加立体丰富起来,表现了作者既怀念又痛心惋惜的复杂情感。
[1] 吴晓东.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78.
[2] 邹东方.论萧红小说儿童视角叙事的审美特征[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2.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4] 萧红.呼兰河传[M].成都:巴蜀书社,2014.
[5] 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1.
本文推荐专家:
张国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写作与文艺学。
王馥庆,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
The Discussion on Narrative Strategy in Childhood's Perspective of Hulan River
LI FAN
Owing to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Childhood Perspective”, Hulan River possesses the uniqueness of text. First of all, instead of taking the plot as the main line and establishing a central figure in traditional novels, Hulan River, from macro-narration to local focusing, describes the real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step by step by putting a series of sporadic events together with “Childhood Perspective”. Secondly, along with “Childhood Perspective” taken as narrative subject,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adults is included in the work, and the flexi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perspectives makes more abundant connotation be conveyed. Last but not least, deep concerns about the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y are expressed with “Childhood Perspective” by the reflection on the identifying with the native land in the literature.
Hulan River; Xiao Hong; childhood's perspective; narrative strategy
I207.42
A
1008-472X(2018)01-0104-04
2017-12-18
李帆(1981-),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