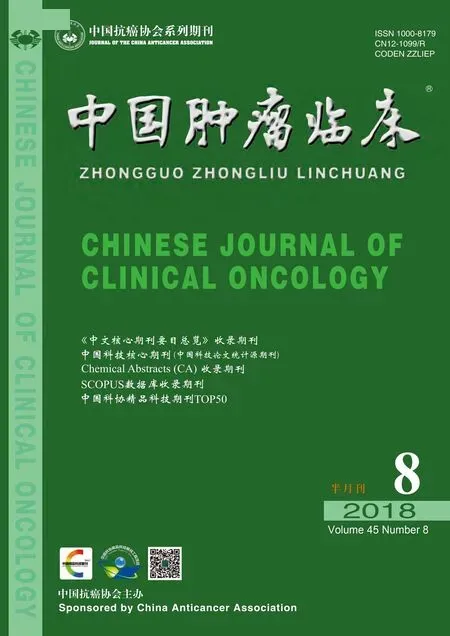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2013年至2016年应用镇痛治疗药物使用趋势分析*
癌症患者的病程中,疼痛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80%的恶性肿瘤患者受其影响,严重降低了生存质量[1]。据统计约1/4新诊断恶性肿瘤患者,1/3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3/4晚期肿瘤患者合并疼痛。药物治疗是缓解疼痛的最常用方法,WHO在1986年发布了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我国于2011年发布《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1年版)》,同时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每年定期发布成人癌痛指南,对癌痛药物的合理使用提出了规范化要求和评价标准。本研究对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2013年至2016年镇痛治疗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镇痛药物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医院处方分析合作项目》数据库中2013年至2016年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患者用于镇痛治疗药物的门诊处方及住院医嘱处方数据。镇痛治疗药物包括《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1年版)》和NCCN指南中提出的镇痛药物及辅助镇痛药物。
1.2 调查方法
每月随机抽取3~4 d日期,周末节假日除外,每季度共10 d,每年4个季度共40 d生成随机抽样日期表。每年按照随机抽样日期表抽取40 d门诊和住院处方数据,采集内容包括:地区、医院名称、时间、处方来源、诊断、药品编码、药品名称、规格、给药途径、金额等。本研究提取2013年至2016年共4年肿瘤患者镇痛治疗药物使用数据,利用Excel软件对处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排序等。
1.3 评价指标
采用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DDD)为指标的分析方法,本研究DDD参照《中国药典》(2010年版)、《新编药物学》(第17版)及WHO网站数据的规定,未收载的以药品说明书为准。按照药品的通用名称统计镇痛治疗药物的用药金额,计算用药频度(DDDs)及限定日费用(defined daily cost,DDC),并进行排序分析。DDDs=该药年销售总量/该药的DDD值。DDDs越大,说明该药临床使用频率越高,从而反映了其临床应用趋势。DDC=该药年销售总金额/该药的DDDs、DDC表示该药的平均日费用,是评价药品销售金额的指标,反映药品的总价格水平,其值越大说明该药给患者造成的经济负担越重。序号比(B/A)=某药品用药金额排序值(B)/该药DDDs排序值(A)。用来衡量某药用药金额及用药频度的同步性。B/A越接近1,说明用药金额与频次同步性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一致>1,说明药品价格较低,临床应用率较高,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序号比<1,说明药品价格较高且临床应用较少,经济效益大于社会效益。
2 结果
2.1 镇痛治疗药物使用及金额基本情况
本研究肿瘤患者共3 398 441例,其中使用镇痛治疗药物的患者429 663例,占总例数的12.6%;肿瘤患者的药物总金额为39 391.29万元,其中使用镇痛治疗药物的金额为603.01万元,占总金额的1.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患者比例基本保持平稳,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见表1。
2.2 不同类型镇痛药物的使用情况
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镇痛治疗药物在癌痛治疗过程中使用和金额的比例,阿片类药物使用量占总数的77.4%,金额占总数的90.9%,居于首位。其中抗惊厥药在2013年至2016年中使用量和使用金额有所增加,非甾体抗炎药的使用量有所下降,其他各类型镇痛治疗药物在各年度使用情况基本平稳,具体各年份使用情况,见表2。

表1 2013年至2016年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患者镇痛治疗药物使用和金额比例 %

表2 2013年至2016年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患者不同类型镇痛治疗药物使用和金额比例 %

表2 2013年至2016年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患者不同类型镇痛治疗药物使用和金额比例 %(续表2)
2.3 DDDs、DDC及B/A的统计结果
2013~2016年间,镇痛治疗药物的DDDs排名变化不大,排名靠前的5种品种分别为芬太尼贴剂、艾司唑仑、羟考酮口服剂型、吗啡口服剂型和吲哚美辛栓剂。大部分药物的DDC值变化不大,反映其价格基本稳定,其中DDC值≥100的药品为丙帕他莫、喷他佐辛、布托诺菲、羟考酮注射剂及吗啡栓剂,DDC值≤10的共有11种,其余13种药品DDC值位于10~100。2013~2016年各类镇痛治疗药物的B/A值大部分接近于1,其中位于0.5~1.5的共有17种,占总药物种类的58.6%,其中B/A值最低的为丙帕他莫,最高的为艾司唑仑。大部分镇痛治疗药物的B/A值变化不明显,其中芬太尼贴剂、艾司唑仑、阿米替林变化较大,具体各药物统计情况,见表3。

表3 2013年至2016年中国10家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患者镇痛治疗药物的DDDs、DDC及B/A
3 讨论
3.1 肿瘤患者镇痛药物治疗的整体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强调对疼痛的治疗[4]。口服吗啡被广泛接受为一线药物,治疗中度至重度癌症疼痛[5],2009年数据显示,阿片类镇痛药的全球消费量中有90%以上发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6],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尽管倡导重视疼痛治疗,其普遍性仍有限[7-8]。癌痛控制在我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发展,无论在吗啡消耗量还是医务人员接受专业培训从而规范化治疗上均有很大提高。WHO将吗啡消耗量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癌痛患者是否得到合理止痛治疗的重要评价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镇痛药的患者占全部肿瘤患者的12.6%,镇痛药金额占用药总金额的1.5%,2013年至2016年各年度使用镇痛治疗药物患者比例和镇痛治疗药物金额比例变化趋势不大。从研究结果上看,我国近4年镇痛治疗药物使用金额和品种基本趋于稳定,但仍可能存在镇痛药物剂量不足或认识存在误区的情况。一项针对北京地区癌痛患者的调查显示,仅11.6%的患者表示了解癌痛知识,52.4%的患者只是部分了解,高达36%的患者不了解,同时有66%的患者仍有重度及以上疼痛,对既往癌痛治疗的满意度也仅为13%[9]。因此还需要从医患双方来加强我国镇痛治疗的力度和合理性[10]。
3.2 各类镇痛药在不同程度癌痛患者中的应用
本研究对不同类型镇痛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根据癌症疼痛规范化治疗及NCCN指南要求,对癌痛的药物治疗采取三阶梯治疗原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on,CDC)指出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供应量持续升高,1999年至2014年美国处方阿片类药物的销量几乎翻两番,但美国报道的疼痛程度并未完全改变。在这段时间里,因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也随之增加[11]。2015年“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估计,仅在美国就有1 250万例不当的阿片类药物处方,其中阿片过量导致33 091例死亡[12]。
尽管阿片类药物广泛用于治疗与癌症有关的疼痛,但完全缓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某些情况下,非传统的可称为辅助镇痛药的药物可以与阿片类药物联合给药[13]。有研究表明,阿片类药物联合非甾体抗炎药及辅助镇痛药物可以提高镇痛效果,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14]。本研究结果提示目前癌痛的治疗仍以阿片类药物为主,且2013年至2016年使用量及金额趋于平稳。非甾体抗炎药物近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由于该类药物具有天花板效应,长期使用对肝肾毒性较大,因此指南中限制了该类药在癌痛治疗中的使用剂量。在辅助用药方面,本研究发现抗惊厥药在4年中的使用量和使用金额有所增加。近年研究发现抗惊厥药物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特别是对放化疗导致的神经损伤所致的疼痛效果较好,许多癌痛患者伴有神经病理性疼痛,辅助抗惊厥药可以有效提高镇痛效果,符合国内和国际治疗指南推荐标准[15]。此外,许多晚期癌症患者发生疼痛时,抑郁、焦虑发生率较高,适当使用抗抑郁药物及镇静催眠抗焦虑药物可以有效改善心情、促进睡眠、解除忧虑和抑郁,增强阿片类镇痛药的镇痛效果,产生直接镇痛作用,从近4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两类药物的使用量和金额趋于稳定。
3.3 镇痛治疗药物的DDDs、DDC和B/A分析
从DDDs结果中看出,芬太尼透皮贴剂由于用药方便、作用持久、生物利用度高及不良反应少等优势,近4年排名居于首位,而DDC值相对较好且B/A值>1,说明该药物并不会给患者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口服羟考酮和吗啡均为强效阿片类药物,根据WHO三阶梯治疗原则,首选口服给药,从DDDs数据可以看出,这两种药物仍为癌痛治疗的主要药物及应用类型,符合癌痛治疗原则。有研究显示,从治疗效果方面分析,芬太尼透皮贴、口服羟考酮及口服吗啡在晚期癌痛治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相似,成本效果比较表明吗啡片和羟考酮更佳[16]。其他药物方面,哌替啶由于其药理作用特点,镇痛效果不及吗啡的1/10,且成瘾性强,因此美国疼痛协会和安全用药实践研究所不推荐其作为癌痛患者疼痛治疗首选[17]。有研究指出,哌替啶的临床应用仅限于对其他阿片类药物过敏或不能耐受的患者[18]。本研究DDDs提示哌替啶在近4年的使用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本次统计中丙帕他莫注射液和喷他佐辛注射液DDC值较高且B/A值较低,提示该药可能给患者造成较重经济负担,临床应谨慎选择。在新剂型方面,羟考酮注射液和吗啡栓剂在近年逐渐被临床接受,硫酸吗啡栓剂适用于无法口服给药的恶性肿瘤患者[19],但从数据分析仍不及传统镇痛药物在使用频率和经济效益方面有明显优势。
综上所述,我国镇痛药物的使用基本符合WHO三阶梯治疗原则,同时逐渐联合辅助镇痛药物提高治疗效果和减轻不良反应,个别品种可能存在经济效益不理想情况,需要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考察。在镇痛治疗过程中,仍要摸索镇痛药物的使用规律,给予癌痛患者充分治疗,减轻经济负担,提高生存质量。
[1]Dababou S,Marrocchio C,Scipione R,e t al.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for Pain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Cancer[J].Radio-graphics,2018,38(2):603-623.
[2]卫生部.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1年版)[J/OL].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电子版),2012,5(1):31-38.
[3]陈新谦,金有豫,汤光,主编.新编药物学[M].第1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64-179.
[4]World Health Organizaton.Defniton of palliatve care[EB/OL].http://www.who.int/cancer/palliatve/defniton/en/,2017-10-28.
[5]World Health Organizaton.WHO Model List of Essental Medicines[EB/OL].http://whqlibdoc.who.int/hq/2011/a95053_eng.pdf,2017-10-28.
[6]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Availability of Internationally Controlled Drugs:Ensuring Adequate Access for Medical and Scientific Purposes[EB/OL].http://apps.who.int/medicinedocs/documents/s21969en/s21969en.pdf,2017-11-02.
[7]Lohman D,Schleifer R,Amon JJ.Access to pain treatment as a human right[J].Bmc Medicine,2010,8(1):8.
[8]Gwyther L,Brennan F,Harding R.Advancing palliative care as a human right[J].J Pain Symptom Manage,2009,38(5):767-774.
[9]王薇,曹邦伟,宁晓红,等.北京市癌痛控制20年进步与挑战—北京市多中心癌痛状况调查(FENPAI4090)[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14,20(1):63-74.
[10]王湘,宁晓红.关于改善我国癌痛控制的思考[J].中国新药杂志,2014,20(17):2057-2060.
[11]Chang HY,Daubresse M,Kruszewski SP,et al.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of pain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2000-2010[J].Am J Emerg Med,2014,23(5):421-431.
[12]Smith DE.Medicalizing the Opioid Epidemic in the U.S.in the Era of Health Care Reform[J].J Psychoactive Drugs,2017,49(2)95-101.
[13]Carlson CL.Effectivenes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ncer pain relief guidelines:an integrative review[J].J Pain Res,2016,9:515-534.
[14]Portenoy RK.Treatment of cancer pain[J].Lancet,2011,377(9784):2236-2247.
[15]邵月娟,王昆.辅助镇痛药物在癌痛治疗中的应用进展[J].中国肿瘤临床,2015,42(10):530-534.
[16]钱嘉.多瑞吉、美施康定和奥施康定在晚期癌痛治疗中的成本-效果分析[J].临床合理用药,2016,3(9):63-64.
[17]Institute for Safe Medication Practices.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making it safer for patients[EB/OL].https://www.ismp.org/profdevelopment/PCAMonograph,2018-02-02.
[18]Latta KS,Ginsberg B,Barkin RL.Meperidine:a critical review[J].Am J Ther,2002,9(1):53-68.
[19]俞丽华,刘孟娟,王增.阿片类癌痛治疗药物制剂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物警戒,2014,11(1):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