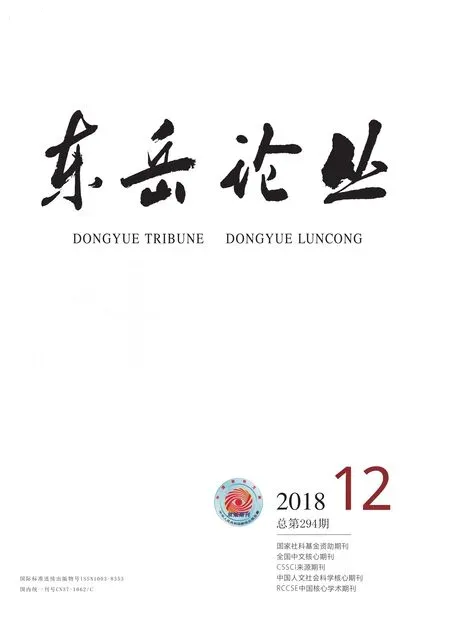“红色经典”的历史本体基础及其叙事规律
李茂民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红色经典”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讲述革命英雄人物的革命故事和光辉事迹,呈现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规律。在“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故事和光辉事迹从未遭到质疑,一直作为真实的存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鼓舞和激励作用。然而,近年来“红色经典”的真实性却遭到了部分人的肆意调侃、抹黑、诋毁和质疑,并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播和发酵,诸如“刘胡兰精神有问题”“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邱少云的事迹不符合生理常识”“半夜鸡叫是造谣”“刘文彩的水牢系编造”。这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真实性的调侃和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质疑已经蔓延到学术研究领域,在近年来所谓“红色经典”的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红色经典”文本与当事人的回忆录、历史档案等文本的比较,认为“红色经典”的文学叙事并不像作者所声称的那样是真人真事的记录,而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其真实性大可置疑。这种质疑会导致对中国革命历史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怀疑,因此,指出这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红色经典”的真实性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解答,就非常必要。
一、“红色经典”的文化研究及其问题
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是近年来“红色经典”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文化研究者看来,“红色经典”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红色经典”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或操纵下的艺术虚构。只是由于“红色经典”作家往往都声称自己的创作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是对于自己或战友的革命斗争生活的记录,所以就导致当时的读者把“红色经典”误认为是真实的历史。

宋剑华通过比较《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不同当事人对该事件的回忆录发现,那些“亲历者”对于同一个事件,往往各执一词,彼此出入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回忆录是按照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艺术夸张来书写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作为英雄的原型能够通过佐证小说情节的真实性获得利益。这就足以说明当事人的佐证并不可靠。如果这些当事人的佐证不可靠的话,那么作家的“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声称就是虚假的[注]宋剑华:《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范本——关于小说〈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2期。。在宋剑华的研究中,不仅《铁道游击队》是这样,其他“红色经典”如《白毛女》《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也是这样,基本上都是“想象”大于“史实”的艺术虚构,其虚构的方法和途径包括“民间传说的故事改造”“历史事件的人为提升”“主观想象的随意发挥”等等。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红色经典’的叙事原则,是‘戏说’历史而非‘忠实’历史,‘戏说’只是一种审美愉悦,它并不代表革命历史本身。”[注]宋剑华:《“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4期。
这种研究的思想方法和观点明显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认为,“旧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往往试图再现作者的原意、他的世界观、当时的文化背景,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性;而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形式和叙事结构,割断了文学与历史的联系,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有自己的局限。如何在文学研究中恢复历史的维度并且避免“旧历史主义”的弊病呢?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研究应当研究的是文学文本与它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揭示文学生产背后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等决定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语境,不是历史本身。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本身是不可通达的,历史只存在于对历史书写的文本之中,包括回忆录、人物传记、历史档案、会议文件等,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搜集和爬梳重建文学生产的历史文化语境,并在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和理解。这种研究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根据什么价值观或根据什么背景来决定某一语境或某一系列语境优先于其他语境呢?强调语境并不能够解答阅读和阐释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求助于语境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人可以获有真正的语境,这些语境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各样,充满疑问的。语境和我们所研究的本文之间的关系组成阐释中难以解答的问题。”[注]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进一步说,这个重建的历史文化语境可能只是研究者主观任意的东西,受到其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表面看来,新历史主义强调了文学和历史的联系,但由于它所说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一种研究者重建的历史文化语境,所以它实际上抽空了文学背后的历史,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新历史批评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对文学与历史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二项对立式提出了怀疑。”[注][美]吉恩·霍华德:《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见[爱尔兰]塞·贝克特等:《普鲁斯特论》,沈睿、黄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红色经典”的文化研究从思想方法到研究结论都与新历史主义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这种研究抽空了文学背后的历史,专注于研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把文学文本所写到的人物和事件与当事人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历史档案、会议文件等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揭露出“红色经典”的艺术虚构性质和意识形态操纵机制。既然这些“红色经典”只不过是艺术虚构和意识形态操纵的产物,那么其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红色经典”的文化研究由此走向了对历史本身的质疑,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但关键的问题是,“红色经典”所反映的历史并不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历史本身就在那里,回忆录、人物传记、历史档案和会议文件都是文本,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各种敌对势力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取得了革命胜利。在这个历史的某个阶段和某个局部,革命也许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但就历史的总体性而言,中国革命获得了彻底的胜利。“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不是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挫折和失败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革命胜利这一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红色经典”就是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的艺术叙事。“红色经典”的文化研究在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结论上,都存在着价值观问题。
二、“红色经典”的历史本体基础
在文本和历史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坚持文本背后存在着历史,并且坚持历史的优先性;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对于重述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来说,不是“艺术拯救了历史”,而是中国革命历史造就了“红色经典”;不是意识形态操纵着“红色经典”的生产,而是历史本身决定着“红色经典”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并不是文学生产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最终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既然这样,那么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由经济基础来说明。这个经济基础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实践关系,就是文本背后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所以,是历史本身决定着意识形态,决定着“红色经典”的生产。
什么是历史?所谓历史,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人类过去所经历以及所创造的一切;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思考。前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本体,后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识。“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可改变,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从本体的角度言,历史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对历史,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增损它的分毫。但从认识的角度言,历史又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注]刘昶:《人心中的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上述对于“历史的本体”和“历史的认识”所做的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本体”是过去曾经发生的外在于我们的客观的东西,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实践关系。由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经验的局限性,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对历史本体的绝对认识和把握,我们所获得的只是个人对于历史本体的局部的片面的记忆和思考。历史的本体是存在的,但它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说它缺席,是因为它已经过去;说他在场,是因为它规范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和思考,并通过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和思考显现自身。这样,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不是听任个人好恶的胡思乱想,而是向历史本体的不断趋近和靠拢。
再进一步看,历史的本体又可以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历史事实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规律则是这一个个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和发展趋势。就历史的认识而言,历史的记忆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记忆,而历史的思考是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无论是历史事实的记忆还是历史规律的把握,往往都通过叙事保存并流传下来。这种叙事包括历史叙事和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二者具有重要区别。一、历史叙事所书写的往往是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历史规律;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所书写的不一定是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只要一个事件能够显现出历史规律、构成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那么它就可以进入文学叙事之中。二、历史叙事更注重历史事件的梗概和骨架的确凿无疑,以保证历史的认识更贴近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叙事更注重人物的真实感和叙事的完整性与合理性,以保证历史规律的形象化呈现,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合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非常重要。
“红色经典”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可以书写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像《保卫延安》《红日》等,也可以书写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局部性和个别性事件,像《铁道游击队》《红岩》等。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件,只要进入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之中,就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成分。这种想象和虚构包括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活动等细节的东西,甚至也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和事件。但这种想象和虚构不是作者主观任意的东西,而是有着历史的依据。这个历史的依据就是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实不是历史中的某个具体的个别的事件,而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是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本身决定着“红色经典”的艺术想象和虚构。艺术虚构是通达艺术真实的必要途径,而其前提就是这种艺术虚构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基础上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才具有真实性,给人以真实感。
这个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不可认识的,在“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它一直在场,甚至并不缺席。作为缺席的在场的历史只是一种遥远的历史,因为年代久远,许多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已经湮没无闻,即便历史叙事也只能凭借道听途说以及想象重建历史事件之间的链条和联系。而“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并未远去,它仍然可以触摸和感受的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同时也包含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规律,或者说体现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规律。这个作为历史本体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不是叙事的产物,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的“红色经典”,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红色经典”所产生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连续的,没有断裂。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和延续。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无从谈起,操纵或规划着“红色经典”的“虚构”的意识形态更无从谈起,当然也就不会有“红色经典”。与其说“红色经典”是当时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和操纵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客观反映。罗广斌、杨益言说:“《红岩》这本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为革命献身的许多先烈,是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概括、叙述的工作。”[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1日。曲波说:“《林海雪原》的问世,首先应归功于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时代,和党所培养出来的时代英雄。我自己只不过把英雄们的斗争事迹作了一点文字的记载而已。”[注]曲波:《关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冯德英在谈到《苦菜花》的创作时说:“作为一个被先烈们用生命保卫着和成长起来的革命后裔,我只不过做了一点比之英雄们的光辉业绩逊色万倍的小事。”[注]冯德英:《我怎样写出了〈苦菜花〉》,《解放军文艺》,1958年第6期。这就充分说明,是历史的本体,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决定了“红色经典”的文学叙事,“红色经典”叙事归根结底只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反映。
三、“红色经典”的叙事规律及其价值意义
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给“红色经典”的革命叙事提供了坚实的地基,决定了它的叙事规律,赋予了它真实性和价值意义。
首先,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决定了“红色经典”所讲述的故事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就中国革命的历史本体而言,既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也存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规律。“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故事,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事实的讲述,也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规律的讲述。就某一部“红色经典”来说,它所讲述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个别的和局部的革命斗争事件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并且力求通过这一革命故事的讲述,来呈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规律。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不同阶段、不同战线、不同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的讲述,这些“红色经典”共同组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画卷,共同呈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规律。在这个画卷中,党所领导的人民和人民军队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全面反映和表现,《红旗谱》反映和表现的是农民在农村展开的革命斗争,《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城市展开的革命斗争,《铁道游击队》所反映和表现的是铁路工人在铁路线上的斗争,《林海雪原》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人民军队在林海雪原上的斗争,《红岩》所反映和表现的是被捕的共产党人在监狱里的斗争。革命斗争无处不在,每一个具体的革命斗争事件以及所取得的胜利都构成了最终革命胜利的一个环节和链条;每一部作品对于革命斗争的书写都成为对于革命历史规律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故事都成为一个隐喻和象征,它隐喻和象征着革命胜利是一种历史必然规律。
“红色经典”的这种隐喻和象征性质决定了它所讲述的必然是一个从失败走向胜利或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革命故事。在这个革命故事中,主人公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成长,革命力量由弱到强,革命的敌人最终走向灭亡,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或预示出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像《红岩》和《铁道游击队》这类作品的艺术虚构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就《红岩》而言,其文学文本与历史事件本身相比存在着很多艺术虚构成分,历史事件本身是由于重庆地下党领导的麻痹大意和工作疏漏,致使包括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在内的133名地下党员被捕入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在狱中,很多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受尽敌人的各种酷刑,最后只有二十几人侥幸逃脱。这个事件无疑是重庆地下党所遭遇到的严重挫折和失败。由于起初作者的写作只是着眼于事件本身,使《红岩》小说的初稿写得很不好,“既未掌握长篇小说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未能表现先烈们的斗争。”作者通过到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参观学习,认识到“写‘中美合作所’必须从全局出发,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经过反复的重写和修改,“最后,作品终于摆脱了低沉压抑的气氛,出现了较为高昂的基调。”[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1日。这样,《红岩》就把重庆地下党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改写成一个地下党人坚持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当作者拘泥于事件的真实的时候,作品显得不够真实;当作者从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进行一定的艺术虚构的时候,作品才显得真实。这是因为,《红岩》所讲述的不仅是重庆地下党员监狱中的对敌斗争故事,而且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链条和环节,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决定了《红岩》所讲述的只能是革命胜利的故事。经过这种艺术虚构,《红岩》成为了“红色经典”中的经典。如果说《红岩》文本所表现的是一个革命从挫折和失败经过斗争走向胜利的故事,那么《铁道游击队》所表现的则是革命力量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故事。尽管作为《铁道游击队》原型的几个当事人对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的回忆彼此有着很大出入,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品所描写的事件是纯粹的虚构,相反,倒是可以证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是确实发生过的,只不过各个当事人的记忆在细节上有所偏差。由此看来,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于个别和局部事件以及细节的艺术虚构,是“红色经典”叙事的需要,也是“红色经典”获得真实性的必然途径。
其次,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决定了“红色经典”必然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也称为元叙事,就是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叙事,这种叙事通过知识的合法化建构了一个总体性和目的性的历史。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宏大叙事,利奥塔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做是‘后现代’。”[注][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显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总体性和目的性的历史是由宏大叙事所构建的,既然这样,那么取消宏大叙事,用各种不同的小叙事取而代之,就能够达到解构总体性和目的性的历史的目的。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指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注][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不是叙事建构了历史,而是历史本身决定了叙事以及叙事的方式,那种试图通过解构宏大叙事而否定总体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国革命胜利就是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历史观决定了“红色经典”必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从内容上看,“红色经典”所讲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斗争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这个故事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红色经典”的革命故事之所以这样讲述,是因为其背后有着连贯性和统一性的历史本体,并且这个历史本体是总体性的目的性的。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红色经典”属于螺旋式上升的叙事结构,在故事的开端,革命总是处于低谷,革命的主体尚未成熟,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也就是故事的发展,革命的主体逐步走向成熟,革命力量逐步壮大,最终迎来的革命的胜利。贯穿于故事发展过程的是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和斗争,这种对立和斗争同时也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其结局是正义的革命力量对非正义的反动力量的胜利。这种叙事结构的故事开端和故事结局是不重合的,它不同于中国古典叙事的圆型叙事结构,也不同于此前三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如《子夜》《家》《骆驼祥子》的悲剧性的结局。“红色经典”的这种叙事结构正是中国革命历史中阶级关系和革命斗争的反映,或者说,正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阶级关系和革命斗争决定了“红色经典”的叙事结构。
从叙事视角来看,“红色经典”都是第三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全能视角,它无所不在,这样更能够呈现出对象世界的整体性。也就是说,“红色经典”正是通过全能视角,把所叙述的革命历史事件的整体性呈现出来。由于“红色经典”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隐喻和象征,所以任何一部“红色经典”所呈现的不仅是它所描写的革命历史事件的整体性,而且是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性。虽然“红色经典”作家都声称作品所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他们在叙事中所使用的都不是第一人称视角,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是一种受限制视角,它只能写主人公所亲身经历的,对于主人公而言,世界的整体性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这种视角无法呈现出世界的整体性。与作家的声称相比,叙事视角本身更能说明“红色经典”的真实性问题。“红色经典”作家的声称事实上处于文本的整体性之外,他这样声称的目的,是想要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其实,作品的真实性无需作家的声称来保证,历史本身就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
总之,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历史的丰碑,“红色经典”的文学叙事只是这座丰碑上的碑文。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镌刻着革命英雄的革命故事和光辉事迹。在“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它是对于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的缅怀和纪念,是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途径和方式,也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望。它感召着年轻一代,使他们成长为革命的主体,投身于那个延续下来的总体性和目的性的历史,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是“红色经典”在其产生年代的意识形态价值意义。在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中,总体性和目的性的历史遭到了否定和质疑,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红色经典”作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也遭到部分人的否定和质疑。这种否定和质疑表面看来所针对的是“红色经典”,其实质所针对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历史本体是不容否定和质疑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延续下来的历史之中。虽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在逐渐离我们远去,但“红色经典”作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理解和通达中国革命历史的途径。这就是“红色经典”在当下的价值意义。正因为如此,所有否定和解构“红色经典”真实性的声音都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