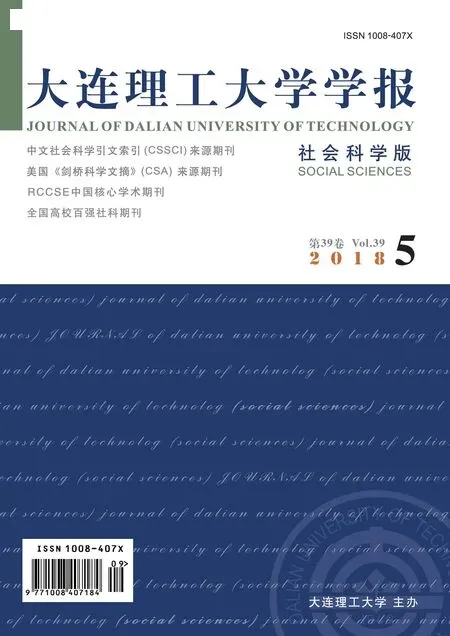是非曲直,当有明断
——新表达论视角下的道德断言阐释
梅 轩, 刘 龙 根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一、引 言
近些年来,道德断言业已成为语言哲学及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顾名思义,道德断言主要是指就某一现象做出“对”“错”“好”“恶”等道德性判断的语句,如“助人为乐是美德、坑蒙拐骗遭唾弃”。表达论为一种阐述道德语句之意义的理论,主张道德断言之所以能够意谓其意谓,根本原因就在于所“表达”的内容,而不在于所“描述”的内容。换言之,真诚地做出的一般断言表达关乎世界的信念,而真诚表述的道德断言则表达了断言者的态度。
在阐释道德断言时,各种形式的传统表达论虽说主旨大体相同,但是在具体细节上仍然存在诸多差异。例如,最早形式的“情感论”主张,断言“X是好(或坏)的”就相当于表达对X有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态度[1]。随后的普遍规定论将断言“X是好(或坏)的”分析为“(不)做X!”[2]。而“准实在论”则认为道德断言投射情感态度,不表达命题[3]。毋庸置疑,传统表达论对道德断言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化,研究者开始对传统表达论的某些观点进行反思,并且提出各种质疑。在众多的质疑中,以下两点尤其富有挑战性:其一,各种形式的传统表达论在某种程度上均属于非认知论范畴,认为道德断言仅表达非认知心理状态而不表达命题。然而,道德断言真的不能表达命题吗?其二,传统表达论均承认说出道德断言相当于表达相应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意在鼓励或批判某些道德性行为。那么,道德断言表达的这种态度又是如何与道德行为相联系的呢?近年来,新表达论思潮的涌现,为打破传统表达论的桎梏,进而为解决诸如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文章拟聚焦上述两个问题,探讨新表达论对于道德断言的解释力。
二、新表达论的缘起与要义
新表达论最早由Bar-On在2004年提出,旨在阐述“坦承”的语义[4]。所谓坦承指的是普通的一般现在时第一人称心理状态归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坦承常用于表征第一人称特许使用的自我认识,具有独特的认知确定性。例如,“我此刻很难过”仅适用于第一人称“我”,而且听者听到这句话就能认知并确定“我难过”的事实。此外,坦承与人体的自然表现如鬼脸和呻吟具有相似性,直接表达(而不是描述或报告)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我此刻很难过”直接表达当事人“我”的心理状态——“难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道德断言与坦承颇为相似。首先,道德断言通常也是断言者特许使用的自我认识,具有认知确定性。例如,除非在特殊语境中,否则无人询问断言者为何说“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已成社会共识)。其次,道德断言直接表达断言者的心理状态。例如,说出“偷窃是错误的”这句话就直接表达了断言者反对偷窃的心理状态。因此,正如许多哲学家业已证实的那样,原本用于阐释坦承之语义的新表达论也许同样适用于道德断言[5-7]。
在新表达论者看来,坦承和道德断言都同一般描述性断言存在相似性。不过,阐释这种相似性的前提条件是先要做出下述两种区分:(1)a-表达与s-表达的区分;(2)断言行为与断言结果的区分。
就第一种区分而言,a-表达指的是,在行动层面上,某人通过有意向地做某事来表达某种心理状态。给一个拥抱、呼一声“你在这儿!”、说一句“很高兴见到你”均是表达相逢之喜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某人可以通过说“我(不)喜欢X”来表达对X的认同与否,也可以通过使用非言语行为来表达对X的好恶。重要的是,a-表达是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拥有者以及表达媒介之间的三维关系。a-表达要求言者具有做某事的意向,最基本的情形是:言者通过实施某个意向性行为自发地表达自己当前的心理状态。这与s-表达形成对照。所谓s-表达,指的是在语义层面上,语句(以言语或思想形式)通过规约型表征形式表达抽象命题。句子“外面下雨了”表达命题:在时间t地点p下雨了,说出这句话的人典型地表达了在某个时间某地下了雨的信念。与a-表达不同,s-表达是表达式与其意义之间的语义关系。由此可见,言者a-表达信念,语句s-表达命题。
除了区分a-表达和s-表达以外,区分做出断言的行为与断言行为的结果同样重要:前者a-表达心理状态,而后者s-表达特定命题。例如,做出断言“草是绿色的”行为a-表达信念草是绿色的,而这一断言行为的结果s-表达命题在现实世界中草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两种区分,可得出新表达论的两条基本要义:
(1)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相似:道德断言s-表达成真或成假命题,因此,既有真值、否定形式,亦可嵌于条件句、可进行逻辑推理等。
(2)道德断言亦有自身的特殊性:做出道德断言的行为实质上a-表达了断言者的动机状态。动机状态明确了做出道德断言与产生道德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新表达论的两条要义可知,新表达论以一般描述性断言为参照系来诠释道德断言,将道德断言的内容一分为二,既保留了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的共性又突显了道德断言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新表达论究竟如何既保留共性又突显特殊性的呢?
三、道德断言与描述性断言的相似性
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具有成真性与可嵌于复合句的可能性。
道德断言是否具有成真性曾备受争议(尤其是在表达论发展初期)。早期表达论者认为道德断言只表达情感不表征世界的特性使其解卸了成真性。譬如,传统情感论的核心为:道德断言无关乎论述真假,只是表达情绪或情感。因此,道德语句就其本身而言缺乏描述意义或事实意义,仅具有“情感意义”。情感意义是指道德语句常被视为表达不同的情感,目的在于激发差别反应,或通过参考某词句的历史因果链使人产生情感反应的倾向[8]。如句子“偷窃是错误的”不表达成真或成假命题而是表达在道德上不赞成“偷窃”的情感。再如,传统准实在论者主张,道德语句不表达命题,而是投射情感态度。在他们看来,心理状态可分为两类:一种为可以表征世界的心理状态(又称为范式信念),这种心理状态可能成真或成假;另一种为不表征世界的心理状态(又称为范式愿望),这种心理状态不存在成真或成假的特性。而道德断言所表达的心理状态属于第二种,即非表征性范式愿望,因此,道德断言不具有成真性。但是,无论是传统情感论还是准实在论均饱受质疑。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日常道德语篇中,道德语句常被嵌入成真谓词之中(如“张三关于偷窃的论述成真”),从而可判定真假。由此可知,道德断言并非如传统表达论者所声称的那样不具有成真性。
新表达论者认为道德断言具有成真性,这与当代绝大多数语言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黑根纳蒂认为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句子的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确定,继而能够判断其真假[9]。譬如,若要断定“猫在桌子上”这句话的真假则需考虑时间和地点这两个语境要素。若在时间t地点p,某只特指的猫的确位于某张特指的桌子上,则为真;反之则为假。道德断言成真性的判断则相对复杂。从某种意义上看,说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就相当于在正常状况下“应当”实施该行为。因此,吉伯德将道德断言的真值判断转换为对应当行为的考量,而在他看来,直截了当地应当归赋是“计划”[10]:某人之所以判定“救助落水者是正确的”成真,是因为若处于当时语境、了解当时实际境况、具有当时心理状态,此人“计划”采取救助落水者的行动。吉伯德的计划论虽然标新立异,但同时也是晦涩抽象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采纳。目前,语言哲学界应用较普遍的是“真之紧缩论”。该理论因其紧缩掉成真谓词的本体论属性而得名,说“S成真”并非表明S具有真之特性,而是断言S本身。说“偷窃是错误的为真”相当于说“偷窃是错误的”,表达去引号命题偷窃是错误的。由于道德断言表达的是断言者的态度,因此判断某道德断言为真则赞同断言内容,为假则不赞同或反对。据此,若认为“偷窃是错误的”为真,则认同“偷窃是错误的”,反之则不认同或反对。真之紧缩论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化繁为简,将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联系起来。换言之,真之紧缩论不但承认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的相似性,突显了道德断言能够表达命题、具有成真性等特性,还指出了道德断言能够表达言者态度的个性特征。
倘若承认道德断言具有成真性,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断言的真值条件是什么?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在语义上相似,在真值条件上亦相似。广义上说,一般描述性断言的真值条件可表示为一组可能世界。句子“草是绿色的”的真值条件是在某些可能世界中草确实是绿色的。倘若在另外一些可能世界中草不是绿色的,那么在这些世界中句子“草是绿色的”则不可能成真。同样,道德断言的真值条件可表征为一组相关道德标准。句子“偷窃是错误的”的真值条件是:依据相关道德标准,偷窃的确是错误的。那么,这个“相关道德标准”是什么?根据广义卡普兰主义的观点,表达式的意谓与语境和评价境况相关。因此,“相关道德标准”可分为两类:由语境提供的道德标准(简称为语境标准)与由评价境况提供的道德标准(简称为评价标准)[11]。若评价境况恒定,那么道德断言的意谓与关涉语境的道德标准相关。依据语境标准如盗窃需受惩罚,那么,句子“偷窃是错误的”成真。根据评价标准,道德断言检测某一道德标准是否满足特定条件,正如一般描述性断言检测某可能世界是否满足特定条件(如只有草为绿色的可能世界才满足“绿色”这一条件)。因此,只有“偷窃是错误的”满足“错误”这一条件才为真。“若某人为了本国安全窃取了即将被运送出境的密盒”,在此评价境况中,“偷窃是错误的”显然不满足“错误的”这一条件,因此就会成假。
2.道德断言可嵌于复合句:弗雷格—计奇难题的消解
如何分析嵌于复合句的道德断言是学界面临的一大挑战,其中最令人头痛不已的要数弗雷格—计奇难题。该难题一经提出则广受关注,哲学家们穷思竭虑进行了各种尝试,虽成果颇丰,但至今仍未得出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新表达论的诞生或许为这一难题的消解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所谓弗雷格—计奇难题,最初源于计奇和塞尔对早期非认知论派关于道德断言言语行为观点的驳斥。黑尔认为,称X为“好”就是赞扬X,由此可知“好”的意义。但计奇反驳道,这种观点很容易让人以为只有用于“赞扬”时“好”才意谓“好”,那么如何解释“好”在疑问句、否定句、条件句中的意谓,在这些语句中“好”显然不一定表示“赞扬”(例如,没有人在赞扬X时说“X不好”)。于是他推断,“好”在复合句中必然意谓有别于“赞扬”的其他内容。但矛盾的是,“好”在复合句中的意谓似乎必然与其在肯定直陈句中的意谓相同,因为肯定直陈句是其疑问句的答案、其否定句的对立、其条件句的前件或结论[12]。塞尔对黑尔的驳斥更加复杂,他认为在日常意义上,只要“好”以正确的方式与“赞扬”相关联即可,并不需要在任何句式中均意谓“赞扬”。塞尔虽然并未明确解释“正确的方式”是何种方式,但从他对“承诺”的论述可见一斑。他认为“我不承诺做X”意谓着针对X“我不会实施承诺的言语行为”,而“X是不好的”则并不意谓着针对X“我不会实施赞扬的言语行为”。因此,他总结道:“好”在肯定句与否定句中的意谓差异迥然。塞尔的驳斥与计奇的观点在本质上大同小异,同样论证了非认知论者拒绝承认道德语句无论嵌于或不嵌于复合句均与简单句意谓相同[13]。他们的论述虽然赢得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同时也引发了弗雷格-计奇之惑:如何确保道德词句如“好”或“X是错的”(至少)在(某些)嵌入语境中与其在简单原子句中意谓相同?
针对弗雷格—计奇难题,目前主流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信奉—语义学[14]。这里的信奉包括信念和态度。根据信奉—语义学观点,道德断言复合句的语义由其子句所表达的心理状态以及连接各子句的组合规则所决定,可表征为关涉心理状态的函数[15]。例如,“非”的语义可公式化为一个从心理状态至心理状态的函数,此函数将句子P表达的心理状态与其否定非P表达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条件句的语义可表征为一个从心理状态对至心理状态的函数,将由任何句子对(P和Q)表达的心理状态与由其得出的条件句(如果P,那么Q)表达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然而,主流方案远非完美。首先,此方案无法解释复合句中的逻辑推理问题。例如,为何综合考虑(1)和(2)就能推出(3)?其次,主流方案会导致激进语义修正论错误[16]。具体地说,为了使该方案同样适用于仅包含一个子句为道德断言的混杂句,只能假定混杂句的其余部分所接受的语义处理与道德子句相同。但是,这样做会更改混杂句中非道德性子句的语义,因而证明是行不通的。举例如下:
(1)若说谎是错误的,那么让弟弟说谎也是错误的。
(2)说谎是错误的。
(3)让弟弟说谎是错误的。
新表达论区分道德断言与一般描述性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正是这种区分为攻克弗雷格—计奇难题提供了可能。概括地说,弗雷格—计奇难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确保道德断言在断言或非断言语境中保持恒定的语义内容。因而,表达论者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允许道德断言具备某些语义特性,既能使其在非道德性语境(如描述语境)中具备类似于非道德断言的逻辑功能和句法功能,还能保留其表达非认知心理状态或态度的特性。为此,新表达论倡导的命题-组合语义学方案应运而生[17]。根据命题-组合语义学观点,道德断言复合句的语义由其子句所表达的命题以及连接各子句的组合规则所决定。因此,若道德断言s-表达抽象命题,那么不论在何种语篇或语境中,均可将其自由地内嵌于复合句。也就是说,道德断言在(非)嵌入语境中均可保持恒定的语义内容,这是因为句子语义并不取决于是否内嵌于复合句,而是取决于所表达的命题。而且,也正是命题才能解释为何一个简单道德断言可以表达不同的态度。例如,句子“偷窃是错误的”在嵌入或非嵌入语境中s-表达同一命题偷窃是错误的,但在肯定句中表达的是谴责偷窃的态度,在否定句中表达的是不反对偷窃的态度,在疑问句中表达的则是对偷窃持怀疑态度。综上所述,若采用命题-组合语义学方案来应对弗雷格—计奇之困,信奉—语义学方案面临的两个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四、道德断言的个性特征:表达道德动机
依据新表达论,道德断言除了与一般描述性断言在语义上具有共性外,还具有其个性特征,即做出道德断言的行为实质上a-表达了道德动机。那么,具体地看,道德断言是如何a-表达道德动机的呢?
目前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认为,道德断言本身无法直接激发道德动机,但是由道德断言而形成的道德判断却可以激发道德动机。那么,道德判断如何激发道德动机?针对这个问题,道德动机内在论和外在论提供了各自不同的答案。
内在论者认为,真实的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若某人由衷地判断他应当做φ,那么他必然具有做φ的动机[18]。因此,某人不可能做出了真实判断却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依照该判断而行动的倾向。根据是否允许废止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的联系,内在论在形式上又有强式与弱式之分。强式内在论主张,某人假若由衷地判断自己应当做φ,那么就具有极强的动机做φ。现代哲学家大多不赞成采用如此“强式”的内在论观点,因为有时候即使有了正确且真实的判断,仍可能不产生道德动机。因此,相较于强式内在论,弱式内在论的势头更劲,而术语“内在论”通常指的也是弱式内在论。弱式内在论主张:某人假如由衷地判断自己应当做φ,那么就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动机做φ。这种动机可能会激发行动,也可能会因为与之相悖的愿望或诸如抑郁、意志薄弱等心理状态而消失。支持内在论最有力的证据是道德动机会随道德判断的变化而变化。若某人判断做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么他有动机做φ;若他随后发现做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么他很可能取消做φ的动机。因此,在内在论者看来,道德判断即可诠释道德动机,无需借助其他因素。
与内在论者的观点相对,外在论者坚信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偶发性的。在外在论者看来,某人关于做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判断不足以激发他做φ。为了使某人具有做φ的动机,还需要一个外在于道德判断的独立动机状态[19 ]。那么,这个独立动机状态是什么?史密斯认为某人之所以倾向于做他判断为正确的事情,是因为有某种愿望存在,这种愿望有两种形式:涉词愿望(desirededicto)和涉物愿望(desiredere)[20]。若受涉词愿望驱动去做φ,那么这个愿望就涉及正确概念;若受涉物愿望驱使去做φ,那么就不涉及正确概念。简言之,根据涉词愿望,某人意欲做φ是因为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根据涉物愿望,某人意欲做φ不一定是因为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也可能因为φ具有某些道德相关特征,而这些特征通常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所具有的特征。他主张,外在论者所寻求的独立动机状态正是涉词愿望。也就是说,在外在论者看来,道德判断和涉词愿望共同作用才能激发道德动机。
一直以来,内在论和外在论两方阵营纷争不断、各执一词。不可否认,两者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亦有各自的局限性。首先,内在论无法适用于无道德论者(amoralists)。无道德论者对任何道德现象均无动于衷,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而无法像常人那样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内在论者虽确信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若无道德判断,又何来道德动机?其次,外在论也并非完美无瑕。外在论者认为激发道德动机的独立动机状态正是涉词愿望。实际上,这并不可信,因为一个心地善良且意志坚定的人不可能总是受到涉词愿望的激发。相反,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羁绊如个人前途、亲友安康等,因而不可能自始至终坚决做他判断为正确的事情。综上可知,无论是内在论还是外在论均有其掣肘之处。因此,为了系统论述道德动机,要么弥补上述不足,要么着力另辟蹊径。新表达论者选择了后者。
根据新表达论,道德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a-表达动机状态,即通过有意向地做某事来表达某种心理状态。也就是说,断言者做出道德断言不但表明有做某事的意向,还表明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若能阐明断言者的意向与信念就可阐明道德动机,而道德动机信念-愿望模型恰好能做到这一点。
信念-愿望模型又称休谟动机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是信念与愿望共同作用的结果[21]。信念是指相信某行为是达成某期望目标的途径,亦称为途径-目标信念;而愿望即表达论者所谓的意动状态。途径-目标信念受理性驱动,即某人之所以倾向于做φ是因为做φ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例如,之所以相信“救助落水者”是达成“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因为在理性上“救助落水者”通常符合“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一道德准则。但是,单凭信念不足以产生道德动机。试想一下,若信念足以产生道德动机,那么具有相同信念的人就会受到相同方式的激发,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例如,针对“救助落水者”这一信念,有些人亲自下水进行救助,有些人呼唤他人前来救助,还有一些人虽具有这一道德信念却无任何行动倾向。因此,若要产生道德动机,除了信念,还需要一个先在的愿望。
能够促成道德动机产生的先在愿望主要有3种:利己愿望、利他愿望和道德愿望[19]255。首先,若施事者S具有利己愿望来达成某一目标E,那么E是S的专有状态。其次,若S具有利他愿望来达成某一目标E,那么E是除S之外的其他人或集体所专有的状态。仍以“救助落水者”为例,若S救人是为了美化个人声誉,那么促成S产生救人动机的是利己愿望;若S救人是为了拯救他人性命,那么促成S救人的则是利他愿望。最后,若S具有道德愿望来达成某一目标E,那么S判断E具有一组道德特性,而且S意欲表现这些道德特性。道德特性通常包括正确、错误、好、值得称赞等。若S判断救助落水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他意欲做他断定为正确的事情,那么促成他救人的则是道德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利己愿望、利他愿望和道德愿望3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携出现。比如,S救助落水者不仅是因为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还可能因为救人既可挽救他人性命也可美化个人声誉。
综上可知,只有途径—目标信念与先在愿望共同作用才能产生道德动机,两者缺一不可。而道德断言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表达言者信念,还表达言者的意动状态,这间接表明说出道德断言相当于表达道德动机。
五、结 语
概言之,仅凭传统表达论或描述语义学均无法正确全面地阐释道德断言之语义特征。一方面,传统表达论者假定表达论是论述关乎道德或伦理性断言的语义理论,而道德断言发挥其表达论功能且保留其意义的唯一途径是将非认知心理状态内置于道德断言的语义之中。然而,正是这种假定曾使得传统表达论深陷于泥淖而穷途末路。另一方面,描述语义学是论述描述性断言的语义理论,而描述性断言并不具备道德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描述语义学无法论述道德断言的表达功能。而新表达论试图打破传统表达论的惯性假定,力图结合描述语义学的优势,在阐释道德断言时,将其表达论功能与其语义内容分割开来,从而突显道德断言的自身特殊性并保留其描述性语义特征。尽管新表达论的这种分割似有“一劳永逸”之嫌,但对确定道德断言的真值、攻克弗雷格-计奇难题以及诠释道德动机却不乏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