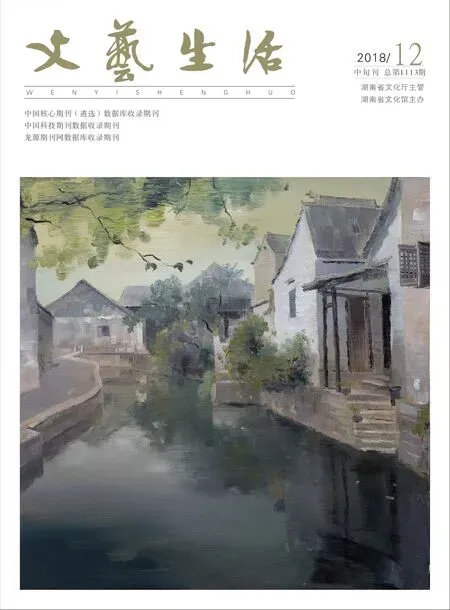情从教起,一往而深
——论杜丽娘的女性教育
王千平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绝大部分女性被传统礼教束缚和压迫,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①的传奇作品《牡丹亭》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于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杜丽娘。下文拟以《牡丹亭》中杜丽娘所受的教育为切入点,探讨杜丽娘所受教育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结果,从而一窥杜丽娘人物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动因。
一、教育方式
在杜丽娘成长的道路上,既有父亲严格要求的家庭教育,也有塾师陈最良迂腐呆板的家塾教育,还有杜丽娘的自我教育。
(一)家庭教育
杜丽娘的父亲杜宝是其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杜宝在剧中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情和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杜宝作为父母官,恪尽职守,心系百姓,身上寄托着汤显祖的政治希望;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用封建礼教束缚女儿的心性,但同时又极其重视女子才学,显得与传统伦理稍有出入。
作为南安太守的杜宝深知读书识字、培养才学的重要性。在《延师》中说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②在《训女》一出中,得知女儿“白日闲眠”③后便训斥她道:“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理,父母光辉。”④可见杜宝对女儿教育的严厉,但同时又可以看到杜宝并不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主张女儿多读书,这点使他异于传统的封建大家长形象。
杜宝在女儿学习教材的选择上也是几经考虑的。在《延师》中,陈最良问杜丽娘读过什么书,杜母说道:“《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⑤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选择《诗经》的原因:一是《诗经》首篇《关雎》表达的是“后妃之德”,自然适合女子学习;二是《诗经》为四言,朗朗上口,方便记诵,易于学习;三是学诗是家传。杜宝自诩为杜甫后人,杜甫曾言“诗是吾家事”,学诗自然是正理,所以《诗经》必然是女教的首选教材。
(二)家塾教育
陈最良作为杜丽娘的家塾老师,可以看做是其父亲杜宝家庭教育的延续。陈最良是不得志的穷秀才,也曾担任过私塾老师,后来“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⑥,不可否认的是,陈最良在教育方面是有一些经验积累的。《牡丹亭》中《闺塾》一出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杜丽娘接受家塾教育的场景,也是明清时期塾师教学的缩影,有一定的现实代表性。
在《闺塾》一开场,就描写了陈最良认真备课的场景:
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念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也。⑦
紧接着,汤显祖描写了陈最良教学的具体过程,先是学生向塾师道万福,接着塾师讯问学生对新课的温习情况:“昨天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⑧课程结束以后,还要“模字”,即为练习书法,这样才算完成一天的教课任务。
陈最良思想上的迂腐,导致他在杜丽娘的教育上多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解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对《诗经》这一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理解帮助杜丽娘打开了追求自我和爱情的心门,后文将展开详细论述。
(三)自我教育
杜丽娘的自我教育主要通过读书实现。杜丽娘自幼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和学习氛围。杜丽娘自己也勤奋好学,从父亲杜宝言其“无不知书”⑨,柳梦梅初次在梦中与她相遇称“淹通书史”⑩等等皆可看出。
同时,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知杜丽娘阅读、了解的书籍既有《诗经》《四书》等儒家经典,也有《题红记》《西厢记》等爱情故事。儒家经典的阅读当不奇怪,但是那些讲男情女爱的戏曲故事必定是得不到父母允许的。作为足不出户的大小姐,杜丽娘应是自己偷偷找来阅读,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偷偷地看《西厢记》一样。可见杜丽娘自己作为一个活着的独立的人,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杜丽娘受到的教育既有来自父母的严厉要求,也有家塾的先生教授,更有自我主动追求的阅读教育;既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也有自身对爱情的想象和探索,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目的的教育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泱泱河海,共同造就了对情一往而深的杜丽娘。
二、教育的结果及意义
来自父母、塾师以及自我的教育在杜丽娘身上产生了各种化学反应,使她深刻封建礼教的烙印,也使她用生命去追求自由和幸福,共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从而受到后世人的推崇和喜爱。
(一)认同家风,知书达理
封建家庭的礼教教育在杜丽娘自幼的成长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其没有完全的反抗和拒绝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如在《婚走》一出中:“(生)便好今宵成配偶,(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⑪在《如杭》中,杜丽娘说:“七步才,蹬上了寒宫八宝台。”⑫写出了科举在杜丽娘心里的重要性。也正如王志武所说“出于认知和阶级的局限,杜丽娘身上打着深刻的封建阶级烙印”。⑬
另外,传统封建教育也使得杜丽娘知书达理。杜丽娘在见到老师陈最良后马上提出要为师娘做一双绣鞋,在《延师》中:“莲步鲤庭趋,儒门旧家数”“(旦拜)学生自愧蒲柳之姿,敢烦桃李之教”⑭,可见杜丽娘对老师陈最良是极为尊敬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杜丽娘名门闺秀的气质。
(二)偷期密会,一往而深
在《闺塾》一出中,陈最良按照传统儒家的“正解”将《关雎》解释为“后妃之德”,并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后妃例子,强调“有风有化,宜室宜家”⑮,试图将《诗经》中所表达的感情追求纳入到儒家伦理道德之中去。对于这样的阐释,杜丽娘表面上似乎是接受的,但是却有自己的另一番理解。剧中借春香之口说道:“读到《毛诗》第一章……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⑯在杜丽娘看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见圣人对于情爱是从不回避的,也就是“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而且“今古同怀”,自己怀有圣人一样的情感,难道不是非常正常的吗?在这里,汤显祖通过春香之口表达出了杜丽娘对于情爱的萌动,《诗经》中隐含的对男女情爱的描写和歌颂,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杜丽娘封闭禁锢的心门。
同时,杜丽娘通过自我教育而受到的现世经典的熏陶也成为了打开她心门的另一把钥匙:“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后皆得成秦晋。”⑰在对《题红记》《崔徽传》的理解中,杜丽娘也得出了与阅读《关雎》相似的体会:“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⑱,这也正是杜丽娘对“圣人之情”的自我阐释。对于生活在晚明的杜丽娘来说,《诗经》是儒家经典,是读书教材,而《题红记》《崔徽传》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戏曲作品,是现世民间文化的代表。私塾教育和自我教育勾起杜丽娘心中深藏的情爱渴望,《诗经》《题红记》和《崔徽传》等杜丽娘自我教育的内容,将她的情感与传统相勾连,又与现实相融合,从而使她的内心感情外现化和现实化,为后面游园时被迷人春色所惊埋下伏笔,更成为她为情一往而深的重要原因。
杜丽娘作为明清女性在文学中的投影,她的家庭教育和家塾教育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她自己对情感的渴望和人性的追求主导着她的人生走向,成为了封建规训下的以情反理者。本是规避人的封建礼教在人性最本真的至情面前被击碎,使得一名弱女子穿越生死,终成眷属,这大抵也是汤显祖想告诉世人们的哲思吧。
注释:
①(明)沈德孚.顾曲杂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⑭⑮⑯⑰⑱(明)汤显祖,徐朔方,杨笑梅.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1,10,10,21,16,33,33,11,55,206,218,21,34,48,54,54.
⑬ 王志武.汤显祖和爱情悲剧《牡丹亭》[J].陕西教育,1983(0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