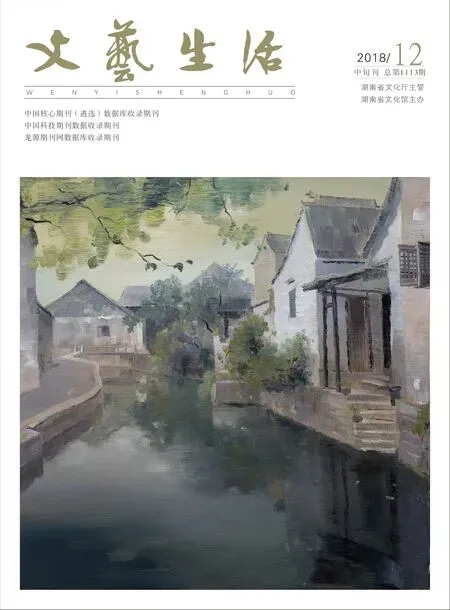双重边缘的困境
——解读於梨华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葛 玥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无锡214000)
我国台湾地区旅美作家於梨华一直被称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她的作品一直以旅居海外留学生和学者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她笔下人物往往游移在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文化之中,通过透视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和故土的美国化,在辛酸的对应中感叹“无根的一代”,《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一、美国与华人
漂泊海外的华人在光鲜外表下,常常有不为人知的苦闷烦恼。一方面与原先熟悉的文化场域渐行渐远,而在新的地域里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只能作为异质文明里的“他者”,心底或多或少都交织着多重无法言说的情怀①,折射出身处异国文化的漂泊和孤独。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回忆自己的留学生活,首先是辛苦的工作。在父母亲朋眼中的轻松工作拿着美金的形象大多来自对美国的想象,华人在美国想打开自己的天地着实不简单。牟天磊的回忆中也很少涉及与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可以想见,当时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并不容易。而对于自己故土家园的人和事的认同是华人在美国紧密联系的纽带,美国与华人,始终还是不能交融在一起的对立两面。在美国,成家的人请留学生们吃饭,留学生永远不是主角,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这种聚会可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最需要得到温暖的群体最常收到冷漠,这种状况常常让人更为唏嘘。所以,这种聚会的结局也往往是“肚子虽然满了,心还是空的。”
天磊在美国没有体验到美国对自己的温暖,这是他与美国文化始终格格不入的原因,处于美国文化边缘的天磊迫切渴求自己本土文化对自己的认同,回国后却再度迷失。
二、旧习惯与“洋”土地
在美国时刻思念着故土家园的华人们,回到熟悉的土地却找不回自己梦想中的亲近,一方面,“洋化”的自己很难接受旧式传统,另一方面,“洋化”的故土也让自己失去了原本的归属感。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活习惯根深蒂固。牟天磊回国后,面对“饭局文化”“面子文化”的极度抗拒已经说明了他已经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洋化”了的自己,让他与脚下的土地之间存在着不可消磨的距离。
故土的“洋化”让天磊极为反感。饮食方面,在美国生活的牟天磊坚持自己做中餐吃,而回到台湾竟很难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而餐馆里各色三明治和咖喱饭一应俱全,似乎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要往美国文化靠近;娱乐方面,第一饭店里连柜台的人和管电梯的仆欧都讲英文,书店摆在进门的台子上是美国当时的畅销书,种种“洋化”的景象让天磊很不是滋味,于是“洋”被他反复地用嘲讽地语气说出来。
可见,他所谓的思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向往,仅作为一种情感、精神支撑存留在心里。当他们回到故土,会发现自己在熟悉的家园仍然处于文化的边缘,不能认同也无法得到认同。
三、“中国根”与“美国梦”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主要的女性人物有四个,这四个女性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一个美国梦的破碎过程。眉立是天磊的初恋,她伴随着天磊度过一段最单纯和美好的时光。最终,眉立选择在台湾结婚生子,衣食无忧。天美曾一心想要出国,在不能成行后,选择与不符合她先前择偶观念的定亚结婚,这两人代表着中传统伦理价值观中的女性价值取向。
意珊与眉立截然相反,她是正在做“美国梦”的代表。佳立便是天美和意珊曾经的参照物。可是佳立说“有些女孩大学毕了业,就在台湾安安心心的嫁了人,雇了一个老妈子,她们也许没有我的硕士学位,但实际上她们真比我聪明了几十倍。”②意珊出了国,可能就是下一个佳立,留在国内,可能就是下一个天美。
四个女性的人生,一方面是“中国根”与“美国梦”在人生追求和生活理念上的差异和冲突,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梦”的破碎过程,正如天磊说的,在美国学到的,是不做梦。身处美国的作家本人,能够看到更真实的美国,也经历了更为伤痛的“美国梦”的破碎,所以写出来也就格外真实和深切。
於梨华笔下的留学生,大多都处于在北美文化和自己本土文化中游移的状态。身处美国,他们只是挣着美金和华人圈子交往的华人;身处故土,他们是镀着金装的美国留学生。这种矛盾的体验,让他们无法融入任何一种文化,只能在二者边缘进退两难,成为失根的一代。
注释:
①肖丽花,程丽蓉.透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看华人眼中的“美国梦”》[J].温州大学学报,2013(03):67.
②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