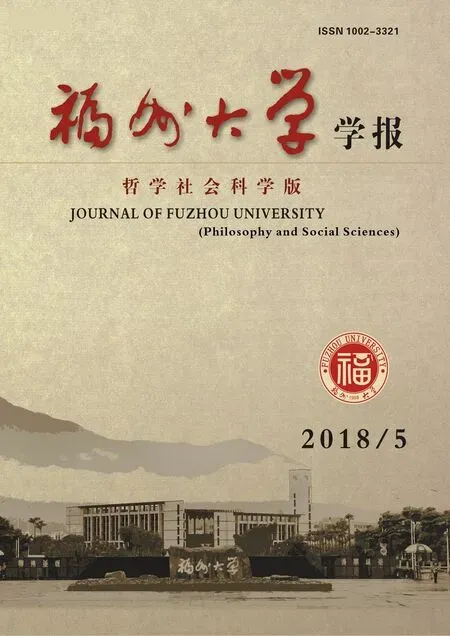论唐弢的散文文类观
——百年中国散文的文类研究之二
林 羚 吕若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鲁迅影响下的散文文类观
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唐弢先是以“鲁迅风”的杂文家面貌登上文坛,后又以新文学亲历者的身份参与了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成为一名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史家。这种特殊的文学活动和经历在唐弢的散文创作与文学史编写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既有承继,又有创造,并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唐弢很重视鲁迅这把战斗的“匕首”。他曾这么说过小品文:“这些东西往往倒象刺,正人君子们有的是疮疤,惟恐被刺到痛处,总觉得有些不放心。这一点不放心,正是小品文的成功。”[1]而鲁迅则说:“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2],能多留一块缺陷,就要让那些专造自己舒服世界的人不舒服。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唐弢的创作,这一块小缺陷,一个小疮疤虽然无法一击制敌,但如果忠实地“把一枝一节连起来,也就接近整个社会了。”[3]唐弢说:“我有笔如刀”,若要以此制敌,这把刀“是必须讲究一点使法的。”[4]在题材上,唐弢认为既要从现实生活中广泛取材,也可以运用历史题材来扩充表现的范围。题材虽然有新有旧,但它们“在作用上,对于现实的针砭,却是完全一致的”[5];在内容上,若珍珠不以大小,而以真假为前提,那么文章也不该只论短长,而应该“以内容的好坏为前提。”[6]好的文章就不应做成“游戏文章”或“花瓶文学”,而应该与社会现实相连,体现出一点“时代的眉目”[7];在语言上,咬文嚼字时需要仔细、审慎,用字遣词应该“简练、明澈、清楚、正确、质朴”[8],以求“质朴无华,落笔不多,意境自远”[9];在写法上,要讲究批评与骂的方法。批评应该在“是非之处落笔”[10],骂并不是乱骂,而是“捉住破绽而细数之的痛骂”[11],挠不到痒处的批评,或是图一时之快的谩骂都是不可取的。不难看出,唐弢的这些“使法”与鲁迅的散文主张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虽然受到鲁迅的影响,但唐弢也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并非完全复制于鲁迅。一方面,唐弢比鲁迅更重视杂文作为文学一员的合法地位,并为之辩护。对于杂文取材混杂,唐弢指出:“杂文的取材,的确是很广泛的,它也弄文墨,也讲科学,也谈社会,也刺政治,倘以为这样便该从‘文艺作品领域’赶出,则取材于社会、政治、科学的小说、诗歌、戏剧,也将站不住了。”[12]杂文就像与大菜相对的小吃、小菜,判别二者的关键在于“要吃,能吃,合于卫生,可以消化这几点上”[13],不能因为它无所不谈、篇幅短小就否定它的文学性,将之驱逐出文苑。“小品文也是文艺体裁的一种,如果戏剧的发达妨碍不了诗歌,诗歌的发达妨碍不了小说,则小品文也决不会妨碍小说、诗歌、戏剧之类的发展的。”[14]“小品文的所以杂,所以无所不谈,正足以表示它反映整个社会,具备了文艺作品主要的条件。”[15]虽然唐弢晚年的时候有说过:“能不能入于艺术之林或者会不会写进文学史,那是无关宏旨的事。”[16]但这只是相较于杂文的艺术性而言的,并不是说杂文的合法性不重要。唐弢通过寻找杂文与其他文类之间的共通之处,努力为之寻求合理的依据,论证了杂文“杂”的合法性,证明了“我们需要大家伙,也缺不了小东西”[17]。不同的是,鲁迅更专注于“文学上的‘小摆设’”[18]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杂文要能够为现实的斗争贡献力量,“生动,泼刺,有益”[19],有着“时代的眉目”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唐弢对于散文内部各种概念的理解更为简单、宽泛,并试图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出这些文类的基本特征。鲁迅在为自己的文章命名时“颇为踌躇”[20],对于杂感、短评、杂文等文类很少做“是什么”的判断。而在唐弢看来,“是什么”一直是他尝试解答的问题。唐弢在《〈生命册上〉序》中认为:“回忆往事,记述当前的生活,算是叙事散文;借一点因由,发抒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诗;以议论为主,评骘社会,月旦文明,那就是社会杂感了”[21];在《〈晦庵随笔〉后记》中说:“大抵凝聚而集中地加以一击的,是杂文;兴之所至,随意而谈,比较散漫以至无所准绳的,是随笔”[22];在《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中则表示:“闲散飘逸,偏于抒情味的是小品文,凌厉峭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23]不可否认,唐弢有文章分类的意识,如果不加以区分,“不成了北京新年风俗里吃的‘杂拌儿’了吗?”[24]尽管对这些文类概念做条清缕析的归纳的确有助于读者大众的理解,但有时也会存在矛盾之处,造成一些混淆。
以小品文为例,在《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中,唐弢强调的是小品文的抒情性,它与战斗性的杂文相对。但在给袁蓉芳的信件中则说:“比如杂文(现在兴行的文艺性杂感)原是散文的一种(鲁迅称之为小品文),即散文中议论性强的一种。”[25]小品文则更偏向于议论性,并与杂文、杂感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诚然,小品文的含义是丰富的,能够兼顾抒情和战斗的两面,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要简练地概括一个复杂的文类实属不易,它很有可能会突出其中的一面,而失掉全面。而鲁迅又是如何看待小品文的?鲁迅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26]《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骚赋之后是小品,“江湖派”诗也是鲁迅所谓的小品,反而是当时特别受重视的明清小品“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27]的文章。鲁迅对于小品文的谨慎思考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更多是表现出一个持续寻找的动作。用唐弢自己的话说,“鲁迅自己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结语号(。),他没有在文章里做结论,只是从生活的具体感受出发,在形象思考的同时作了细致的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事物的真相。”[28]
但凡对支离破碎的国家、动荡不安的社会有所触动,并未患上“逃世病”的青年,都不会“吃、碰、和”[29],奉行“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30]的麻将哲学。唐弢说自己无法保持缄默,置之不理,“有时候有感想,有时候有意见,对不合理现象要抗争,要掊击,并且想立刻给以反应,这就使我爱上了杂文这形式。”[31]鲁迅的“匕首”和“投枪”正好契合并引导了唐弢的创作。唐弢的散文文类观若与鲁迅相较,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及之处,但他侧重于继承、发扬、宣传、战斗,“去弹动七弦琴里那根绷得最紧的弦线”[32]的一面是必须肯定的。
独特的“书话体”散文
唐弢说:“一个作者没有自己的风格是可悲的,同样地,一个作者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不能摆脱它,突破它,不断地发展它,那将是更加可悲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往往意味着:作者终于用亲手制成的圈套,紧紧地将自己套住了。”[33]因此,散文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不能总被框定在一个范围内,在“像”和“模仿”的圈子里打转。“如果千篇一律,并无不同,我写的也就是鲁迅写的,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何贵乎有我的这些文章呢?”[34]所以,除了战斗性的杂文,唐弢还创作了一类能够代表自己个性风格的文章——“书话体”散文。
对于“书话”,唐弢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书话”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35],“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书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36],“它是散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37]这些内容大致概括出了“书话体”散文的基本特点,同时也隐藏着一条重要的信息——唐弢的“书话体”散文并非横空出世,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唐弢自身的个性特点、审美倾向、知识体系、生活感悟,以及文学活动经历等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唐弢的有意为之,对古代题跋、序文等文体的了解,对抒情性散文的喜爱,文学史家、藏书家、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便都成为唐弢“书话体”散文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养分。
首先,唐弢喜欢并看重序跋。唐弢喜欢读序跋,爱“这作者的一得之见”[38]。多年的读书习惯使他拿到一本书时,总会先看目录和序跋,以便把握全书的精神。唐弢说:“我以为序跋是书的灵魂,而对这种文体的开合自如,随意发挥,或酣畅恣肆,或亲切婉约,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39]在写作“书话”时,他曾努力尝试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40]。在《晦庵书话》中,唐弢似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即常常引用这书中的“灵魂”。这就为“书话体”散文为何类似于古书后边的题跋找到了依据。另外,抒情性散文更容易融合唐弢自身的特点和生活经历。《投影集》问世后,唐弢的文章呈现出了“感抒性”的一面。宗珏说:“一部《投影集》就在展示着作者怎样在‘鲁迅风’底影响下,一步一步在发展其独特的风格。”[41]这些带着抒情色彩的文字有唐弢颠簸生活的痕迹,有他对自己内心的解剖,“至少它反映了一个时期内我的思想深处对于生活的探求与思索。”[42]唐弢创作的战斗性的杂文很容易让读者想起鲁迅,但他抒情性的散文却让我们更容易看见唐弢自己。这种抒情倾向正是唐弢“注意自己”“记住自己”的证据。[43]所以,唐弢说他的“书话体”散文有一点观点,有一点抒情的气息。这背后体现出的是,“书话体”散文很好地展现了唐弢文章背后那个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书话体”散文完全契合唐弢作为文学史家、藏书家、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具有显著的个人气质和风格特征。现代文学中也有作家写作书话,如《西谛书话》《知堂书话》《阿英书话》等,但却鲜有作家能像唐弢这样,调动自己所有的学识、经历、身份等各个方面,用“大手笔写小文章”。他以书为基础,打通了书里书外、今时旧事,将各类文学体裁,各种书图人事都熔于一炉,既谈了客观史料、文坛掌故、版式装帧,又带有抒情的气息和肯綮的批评,极具知识性和艺术性。姚春树先生称唐弢的“书话”“表现了他作为一位藏书家、文学史家和杂文家的统一。”[44]作为文学史家,唐弢介绍了许多初版本的书籍,如李霁野的《影》、章川岛的《月夜》等,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黄裳指出:“最先留心收集新文学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基础的,是阿英。但注意新文学出版物的版本,系统的加以评论记述的,则不能不首推风子”[45]。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他的一个重大长处,就在于十分熟悉这段文学的历史背景”[46]。唐弢记录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家轶事和文坛掌故,如唐弢与郁达夫的往来,《春蚕》《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印行的实际情况等。作为藏书家,他不仅畅谈了藏书家、藏书票、藏书印,以及购书的经历,还穿插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趣事;作为一位博实的学者,他还谈了版本学、书籍装帧、民歌等其他内容。唐弢说罗黑芷“以柔顺的笔调,写灰暗的人生,作品不多,却又不能使人轻易忘记”[47],哀叹、惋惜中带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唐弢还说毛边本比精装本好,“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48],批判气息又不自觉在评书过程中流露出来。唐弢的“书话”“以文济史,导杂归纯”[49],各种文类、各种学识、各种身份都在唐弢评书、话书的过程中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正如樊骏所说的,唐弢的“书话”“较之一般的史料文章,多了葱郁的诗意,显然出于作家化了的学者的手笔;较之一般的艺术散文,又分明包含不少书本典籍方面的知识,还不时闪烁出精辟的学术见解,又只有学者化了的作家才写得出来,是作家的文采和学者的才识的美好结晶。”[50]
唐弢有意做“书话体”散文,认为“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51],它并非唐弢自谦时的所谓“闲书”。唐弢发展了散文的体式,使“书话体”这一形式“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52]。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鲜明的文体意识,又体现出观点精辟,偏重知识,富有抒情气息的一面。唐弢认为梁遇春另辟蹊径,走的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53]而“书话体”散文随写随刊、横贯文史、畅聊古今,何尝不是走快谈、纵谈、放谈的路?不可否认,唐弢确实受到过鲁迅的重大影响,“可是却不能为了这样,就单纯的认定作者仅是鲁迅先生底作风的承继人,而无视了他的发展”[54]。
文学史中的散文文类观
在194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唐弢开始着手《鲁迅全集》的补遗工作,同时也创作出了一系列“书话”。而“他正是以这两者为起点,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和研究工作。”[55]可以说,鲁迅杂文的影响和“书话”中所说的一些思想与唐弢后来的文学史编写工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意思的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客观的文学史写作面前,鲁迅杂文的影响和带有更多唐弢个人色彩的“书话体”散文的痕迹依然能够在其编写的文学史中找到较为清晰的印迹。
《晦庵书话》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唐弢后来的文学史编写倾向。在《书林即事》中,唐弢说:“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56]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中,有两条重要的编写原则:“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57]唐弢的文学史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与“书话”中所说的研究问题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从期刊中去发掘时代全貌的观点几乎完全吻合。进一步来谈,以具体事例更能说明这种前后的关联性。在《骈肩作战》和《“怎样研究”丛书》中,唐弢回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向读者介绍了“左联”和“社联”之间的紧密联系,介绍了“社联”成员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和“左联”成员钱谦吾(阿英)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在当时发挥的先声作用。唐弢提出:“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些,把《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也不妨说,这又是当时中国文化领域内站在不同岗位上左翼文化人互相团结的第一个标志了。”[58]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左联”的活动面很广,但它与“社联”“剧联”“美联”“记者联”之间都是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彼此之间并肩作战的。唐弢以原始刊物为基础,把“左联”,乃至整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都回归到特定时代中去,尽可能地呈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在介绍“左联”时,花了大量的篇幅去交代“左联”成立前的历史背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论争,及其存在的局限性等。“左联”成立的必然性,以及它在当时出现的意义就在还原到时代语境的过程中不证自明了。“书话”中的“左联”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中的“左联”尽管在面貌上不尽相同,但在论述方式和思维表达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唐弢的文学史也与鲁迅的杂文倾向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万平近曾指出:唐弢“反复说明‘以作家作品为基础’并不是把文学史变成作家论的汇编,而是密切结合时代发展,把作家作品嵌入历史之中。这实际上同鲁迅所主张的‘史总须以时代为纲’,‘不至于将一个作家切开’相吻合”[59]。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在“三卷本”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将七十多万字的“三卷本”缩减为三十五万字的“简编本”虽然会舍弃一部分作家作品,但“其重点便很突出。”[60]现以“简编本”为例来论证唐弢文学史中与鲁迅杂文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就徐志摩来说,从“三卷本”到“简编本”,能够代表徐志摩主要成就的抒情诗在文学史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1983年,唐弢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中评价徐志摩:“譬如徐志摩就有长处,他写的一些诗和散文,我看有成就,他的诗《山中》《再别康桥》,散文《翡冷翠的一夜》,写得都好。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应当肯定。不过这个人思想很浅,不能因为说他有长处,就什么都好。”[61]而徐志摩“思想很浅”的具体表现是什么?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给出了答案——“代表徐志摩艺术成就的,是那些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抒情诗。”[62]唐弢肯定了徐志摩抒情诗的价值,但同时也指出了它“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的弱点。唐弢十分看重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在晚年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唐弢还想着“看来现在还不是做诗的时候,倒是应该写点杂文呢”[63]。唐弢自始至终都关注着现实社会,充当着一名“放火者”的角色。作者不能患有“逃世病”,作品中不能只有自己的喃喃自语,而应该具有现实社会的内容就很自然地成为唐弢进行作家作品分析的重要参照。除外,唐弢的文学史还指出了林语堂的不足之处——“多数文章停留在‘说说笑笑’上,虽具有一定知识性,时代性却愈来愈淡薄。随着时间的推移,林语堂片面地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并对左翼文学运动采取对立谩骂的态度。”[64]林语堂闲适、幽默的小品在三十年代就受到鲁迅、唐弢的批评。鲁迅曾做《骂杀与捧杀》《读书忌》《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有关林语堂的批评文章,称其“赞颂悠闲,鼓吹烟茗”[65]。唐弢也曾呼吁,我们不能做林语堂式的“游戏文章,”不能让这种闲适之风独占了小品文的圈子。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正是抓住了林语堂式的小品文时代性不足,未能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弱点进行叙述的。鲁迅和唐弢所强调的文章要有“时代的眉目”始终都是唐弢文学史中一条重要的评判标准。
虽然唐弢的文学史是集体创作、分头执笔,并非唐弢个人的创作,但最终定稿的人是唐弢。通过言传身教,他的学风、文风对整个编写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编写主张和修改意见常常被采纳,青年工作者们对于自己执笔的部分也经常在唐弢的指导下反复斟酌和修改。“(唐弢)不但把握全书的方向和内容,而且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学风和文风影响全组,特别是年轻同志。”[66]所以,尽管是集体创作,唐弢的个人主张还是能够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作为指向的散文文类观
鲁迅所主张的关注现实社会,要体现出“时代的眉目”,“书话”中传达出的注重原始期刊、初版本等第一手资料都是唐弢散文文类观的重要内容。但当唐弢的散文文类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弢的文学史观,并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史编写相融合时,这种主张也就超出了个人的范畴,具有了“史”的意义。
当时,有些编写者参与过1958年的群众性大编教材,全组中“以论带史”的氛围较为浓厚。“以论带史”往往以文艺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容易陷入“以论代史”的境地,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文学史编写原则。而唐弢所主张的是注重史实,以作家作品为基础,走“论从史出”的路子。唐弢对文学史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史首先应该是一部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所谓文学史,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历史,是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书”[67]。文学史一方面是讲求客观的史学,另一方面是要进行艺术批评的文学,“归根到底,是个史和论的关系问题”[68]。只是在唐弢看来,史实应该摆在首位,作家作品,以及一系列原始材料才是文学史编写的出发点,而“论”要从“史”中得来,要以“史”作为参照。虽然唐弢的文学史不可避免地叙述了不少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但它“创立了一种文学史著的风格,即在叙述历史时,用客观的态度。”[69]这种文学史观逐渐被大家认可,在现今的文学史编写工作中同样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回过头来看唐弢散文文类观中一些观点和见解时就能发现,这不仅仅是唐弢个人散文文类观的问题,它同时也具有了为文学史书写指示方向的重要价值。
令人好奇的是,在权威政治和客观文学史面前,唐弢的散文文类观是如何在文学史中得到相对实现的呢?首先,作为权威的政治并不排斥客观真实的历史。有时候“‘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70]。当有人指出唐弢的文学史模模糊糊,“不敢讲真话”时,唐弢的回复是:“但我们没有讲假话。”[71]唐弢的文学史主张用“春秋笔法”来讲真话,即在把握整体史实的前提下,将个人的倾向都寓于文学史叙述之中。唐弢文学史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极其丰富的史料作为支撑,“这显然是这部书的作者们有意识的追求。”[72]书中尽量让史实说话,而唐弢所说的话,唐弢自己的散文文类观就隐藏在这些史实的背后。其次,唐弢个人的文学主张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潮流相契合。唐弢认为:“现代文学史历史短,过程清楚,现实主义是主要的”[73],把现实主义作为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主线是合理的。而在唐弢的散文创作,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中,“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唐弢认为战斗是杂文的生命,作家应该迎难而上,到有火处去取经,做愈人头风的文章,“倘使击着了坚强的石块,一定有迸裂的火花,倘使钻着了结实的木头,一定有冒腾的热气;只有散沙和朽木,这才随手零落、消灭,连声音都没有”[74]。如果是文学史写作,就“应当以生活为主体,以反映生活主体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编写文学史。”[75]唐弢思想中的这种面向现实生活的战斗精神顺应了现实主义的发展潮流,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是并行不悖的。再回过头来看看唐弢自己,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学史研究都有表达感性诉求的一面。从《投影集》中能明显看出,除了战斗的杂文,唐弢还偏爱“便于发抒”[76]的叙事抒情散文,颠簸生活的痕迹最容易体现其中,使唐弢的文章呈现出“感抒性”的色彩。从文学史研究来看,唐弢谈到严家炎时曾说,自己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只是“从生活里得来的感性知识比他多一点而已。”[77]与其他编写者不同的是,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他的研究往往会将自己对那段历史最真实的体验、最深刻的洞见不自觉地融入文学史写作中去。樊骏曾指出:“与研究对象的异常贴近,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便利,却也难免造成自己和别人不一定都意识到觉察到的限制——难以拉开自身与研究对象的距离,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他们,进而作出历史的评价。”[78]所以,一定程度的感性书写对于唐弢的文学史来说是必然的,“他的研究因此也就不是一种学院式的思辨探讨,而是带着全部情感与生活丰富性的创造性的劳动”[79]。那么唐弢的散文文类观不断在文学史中映现也就合乎情理了。
文学史是允许个人存在的,即使是以客观严谨的面目呈现的文学史。文学评价的困难在于衡量和评判的标准并非来自于某种理论、政策或条文,而在于“大半是来自我们的阅读经验”[80]。文学史难以做到绝对客观,那么在文学史研究中,唐弢的感性诉求也就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于我们进入具体的‘历史情景’,是有好处的”[81]。这些具体情景中的 “许多细节,许多体验,有时可能比概括性的结论更重要。”[82]《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中所叙述的郁达夫就带有唐弢浓厚的感性色彩。先对比《晦庵书话》,唐弢对郁达夫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诚恳,热情,带着点名士风度。但我又觉得在他身上有许多矛盾,似乎始终没有脱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长衫:他对环境抱着强烈的不满,想起来反抗,又不免颓然而止。”[83]而到了文学史中,唐弢又是如何表达郁达夫身上这股典型的名士气的?他引用郁达夫的旧体诗。唐弢不反对新文人做旧体诗,但也不大赞成在现代文学史中谈论旧体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中,却谈到了郁达夫的旧体诗,称其作用是“以补充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的情愫,使文章显得跌宕多姿,更富感情色彩。”[84]唐弢曾说郁达夫的旧体诗是“达夫凄苦如仲则”,表达出他个人的感性,但在文学史中,不得不多加一句评判:“感情颇不健康”;他在肯定“这些旧诗在散文中不但是有机而和谐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感情最浓烈的部分”[85]时,也要说《沉沦》“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86]。文学史容得下唐弢的这点感性,才使郁达夫传统士子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这种笔法、这种唐弢式的处理方式在权威政治和客观的文学史面前显得更为珍贵。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也出现了其他的文学史写作,作者们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但“问题在于突破的方向,均选在突破政治上;因而越突越偏,劳而无功,或适得其反”[87]。原因何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唐弢本’就像一颗老树一样,既有老干,又有新枝”[88]。而编写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铲除“老干”上,而较少把注意力放在对“新枝”的继承和发展上。
事实上,在散文文类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观是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条重要的伏流。根据万平近的回忆:“那时参加编写的同志都感到,个人编写的文学史,虽有不同的长处和特色,但也难免有个人视野和掌握资料的局限,而‘大跃进’年代用‘大兵团’作战方式‘争分夺秒’编出文学史,往往流于粗制滥造。”[89]但在“政治第一”“政治唯一”的编写环境下,这点零星的个人视野,这种强烈的个人主张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回顾唐弢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唐弢极具文体特色的“书话体”散文依旧受到读者推崇,他有一副“左翼”青年的风貌,同时又具有读书人本质的一面。作为杂文家的唐弢虽然始终没有走出鲁迅,但“书话体”所传达出的内涵又恰好是他偏于文化随笔的气质而非战斗者的意识。当带着唐弢气质的文学史在新时期重放光彩的时候,它刚好迎合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宽容的文化风气,“老干”和“新枝”都在这股潮流中得到洗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章能够做到既有继承和发扬,又有突破和创造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唐弢的散文文类观却慢慢建构了他的文学史观,并在历史的考验中逐渐创立了一种文学史著的风格,并对现今的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注释:
[1][3][6][8][11][12][13][14][15][17][30] 唐 弢:《唐弢文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1,159,157,304,209,150,144,155-156,155,156,285页。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21][22][24][31][33][34][35][36][37][38][39][40][42][47][48][51][52][53][56][57][58][77][83] 唐 弢:《唐弢文集》第五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7,159,217,96,34,70,128,241,247,101,182,73,247,72,454,487,241,240,292,711,142,297,141,363页。
[5][9][10][23][29][63][74] 唐 弢:《唐弢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3,384,375,379,312,547,117页。
[7][19][26][27][65] 鲁 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01,431,431,232页。
[16][61][67][71][73][75][76] 唐 弢:《唐弢文集》第九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31,419,378,371,389,632,14页。
[18] 鲁 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1页。
[20] 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25] 唐 弢:《唐弢文集》第十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18页。
[28] 唐 弢:《唐弢文集》第七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32] 唐 弢:《唐弢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41][43][54] 傅小北、杨幼生:《唐弢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51,251,251页。
[44] 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
[45][46][50][55][59][66][78][7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175,178,165-166,112,114,189,272,111页。
[49] 杨 义:《唐弢书话境界》,《群言》1996年第5期。
[60][69][88] 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9,938,937页。
[62][64] 唐 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2,316页。
[68][72][8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123,120页。
[70][80][81][8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0,75,13,14页。
[84][85][86] 唐 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98,199,196页。
——探析文类与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