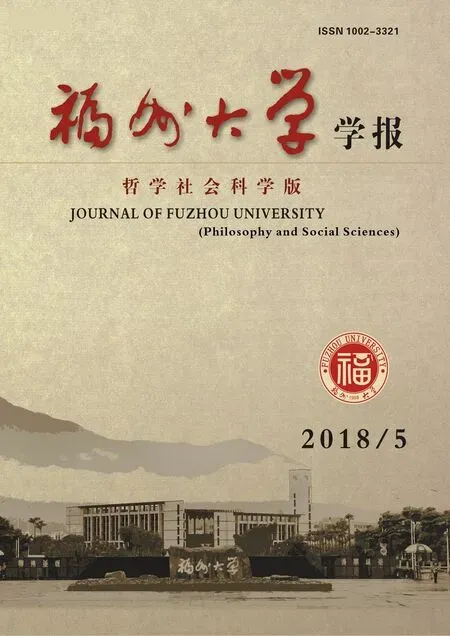列宁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批判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对封建专制制度进步性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阶级本质。列宁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批判与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糅进了新的时代所提供的背景材料。在列宁看来,民主就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同时,民主也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但它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列宁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批判就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
一、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资产阶级否认现代议会制度的阶级性,认为议会制度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自然的和唯一合法的方式。列宁,同马克思一样,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揭破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1]历史地看,相信一般民主万能,而不了解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了解其历史局限性,这是普遍流行于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又表现得特别顽固。因为大资产阶级同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发动者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利害关系,他们从自身的阅历中知道,这个国家是阶级的国家,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必须宣扬国家的全民性、超阶级性。而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点,他们把议会民主制理想化、偶像性而顶礼膜拜。因为他们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偏见很顽固,所谓“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等等,便是他们“真诚的”追求。[2]对这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指出,“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3],有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主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同样,在旧式的议会民主的范围内,无产阶级是不能够充分地彻底地表达自身的阶级利益的。为了帮助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列宁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进行了阶级的分析。
资产阶级宣称他们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列宁则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即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它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普选权、议会、立宪会议等等形式都无法改变事情的实质。一方面,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它随时可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即被剥削者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戒严等等,这时民主的实质便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是“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的,大多数居民在通常情况下便因此被排斥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了。所以,列宁说:“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5]
资产阶级宣称他们的国家是最自由平等的国家。列宁则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6]“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但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是一句空话。因为它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则对他们设置无数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7]如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平等”“纯粹民主”就是骗局,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8][9][10]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不是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的“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11]
资产阶级宣称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体现,立宪制度、法治原则是人民权利的保证。列宁则反对抽象地谈论宪法和法治。因为首先的问题是哪个阶级的宪法和法律。“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2]其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真正承认宪法权利的保证在于争取这些权利的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只能以斗争的胜利来证明。所以列宁说:“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13]反封建斗争胜利后,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成了反封建斗争的主要的和直接的受益者,新的法律、新的制度便首先是为保护这个新统治者的利益而设制的。资产阶级宪法虽然规定了主权在民,规定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但一旦人民真正要行使这些权利时,他们马上就会发现宪法的异己性质。
正是从阶级分析入手,列宁抓住了议会民主的要害:“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者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看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14]
二、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在揭露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同时,列宁还对它的统治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真正的阶级统治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议会之外”进行的。[15]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任何一个议会制国家,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都是在幕后进行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而议会则专门为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16]资本家阶级统而不治,这是人类历史上政权管理的一种全新现象,由于资本家阶级退到了幕后,资本的力量不是被削弱而是增强了。无论管理者自身的桀骜不驯还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通常情况下都会使管理者成为政治牺牲品,而资产阶级则可以稳坐江山。同时,资产阶级创造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阶层行使着事实上的国家治理职能,它的出现更增强了政治家的傀儡性质,但却更巩固了资本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更换部长的意义极小,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附他们。这支队伍被资产阶级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17]在这种机制下,资产阶级不仅不再害怕而且希望把工人阶级的一些代表吸收进来,因为这样既无损于其阶级利益,而且还更增强了政权的“全民”色彩。当然,它吸收工人代表是有条件的。列宁分析说:“资产阶级是这样并且仅仅是这样允许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它的机关、享受它的民主的:它(1)把他们加以过滤,把革命者淘汰掉;(2)用纠缠的办法‘捕获’他们,把他们变成官吏;(3)用金钱收买的方法捕获他们;(4)用巧妙的收买包括阿谀奉迎、向他们献殷勤等捕获他们;(5)用‘工作’‘缠住’他们,吞没他们,用成堆的‘公文’、用改良和小改良的污浊空气窒息他们;(6)用小市民的那种够得上‘文明’的庸俗的安逸生活腐蚀他们……”[18]资产阶级的这种统治机制在民主共和国中发展到了极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19]“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能使这个权力动摇。”[20]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虽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争取到较多一点的权利,但在这个旧框子里却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本阶级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议会民主制的结构性弊病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实践的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也指出了“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出来的议会制的缺点”。首先,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制存在着结构性的弊病。对此,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社会批评家们的批评。[21][22]其次,“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己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23],这除暴露出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外,也反映了议会脱离群众的弊病。[24]一方面,民主制被局限于民主“选举”[25],选举一结束,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随之完结。另一方面,议会成了“清谈馆”,它无力或不愿同官僚机器对抗。当它只是在监督的名义下通过一些软弱无力的决议和建议时,政府便谦恭有礼、笑容可掬地把它们束之高阁;而当它试图表现出对官僚机器的“无礼”时,它则有可能遭到粗暴地解散的命运。议会按其产生的本意讲,应该是与政权相对抗的民意机构,但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封建势力的灭亡,议会也失去了它的革命性质而日趋官僚化乃至成为保守势力的营垒。再次,议会机构本身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和金钱交易,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的讨价还价和勾结分赃行为。
列宁对议会民主的批判是历史主义的。他并不否认议会制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的进步作用,也并不认为议会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无所谓的。相反,列宁多次指出:“社会民主党并不以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为理由而放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是从历史观点来看待‘推崇’资产阶级制度的。”“它从来不讳言,而且永远不会讳言,它推崇民主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同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制度相比较而言。不过,它是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仅仅当作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来‘推崇’的,把它当作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方便的舞台来推崇的。”[26]“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27][28]一句话:“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29]即与以前相比较,议会民主制是进步的,而与以后相比较,它又是应当被否定的。
三、沙皇俄国从未建立起真正的议会,只是产生过“立宪幻想”
列宁对议会制的批判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原则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剖析了俄国的现实。或者勿宁说,列宁对议会民主的猛烈抨击的目的恰恰是针对俄国现实的,是为了彻底破除俄国人对议会民主的膜拜心理而做的革命化的解释。因为列宁的斗争舞台在俄国。
用铁腕启动俄国欧化进程、推动俄国改革的彼得大帝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决心改造俄国人,使之由牲口变成人,由孩子变成大人。[30]马克思后来曾称“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31]后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也一直具有极浓的封建专制色彩。正如列宁所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在这里,“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俄国的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32][33]正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度一直没能成形。
在1905年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沙皇政府起初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以前召集国家杜马。按照设计,这是一个纯粹咨议性的机构,因为它根本没有限制沙皇的权力,而仅仅是为了讨论和拟定法律草案而设置的,法案最后须上报沙皇批准,沙皇有权决定拒绝与否。列宁就此评论说,历史雄辩地证明,只要权力仍掌握在君主手里,那么和君主权力并存的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咨议性会议。这“不是在制定宪法,而是在制造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咨议性议院”。[34][35]1905年8月6日公布的沙皇宣言和《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国家杜马选举条例》法令“确实是反映浸透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野蛮、暴虐、压榨的一面‘镜子’”。[36]咨议杜马在革命洪流中破产,沙皇被迫发布了一个“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完全立宪的宣言”[37],即(1905年)10月17日宣言,并许诺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但沙皇及保守势力并不甘心让出权力,竭力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去,而且事实上确实又夺回去了。
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俄国共召开四届杜马。从本质上看,第一、二届杜马“就其权限和对国务会议的关系来讲”并没有摆脱“专制官僚机构的毫无作用的附属品”的地位,[38]但是,毕竟在第一、二届杜马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39]。也就是说,杜马并不安于“附属物”的地位,并不希望成为一个驯顺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很快就被解散了。随后的第三、四届杜马已完全成了沙皇专制制度的一部分,或者说“干脆是反革命杜马”[40]了。不过,国家杜马毕竟保存下来了,立宪制度的进程毕竟开始了,沙皇制度没有再回到赤裸裸的专制制度上去,就这个意义上说,从无限专制到改行君主立宪的过渡进程没有中断。但如果说杜马“不是纸板做的杜马”,不是“虚假的立宪制度”,那也仅仅是说,第三、四届杜马反映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它的决议是同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形势、物质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相符合的,因此就不是说空话,而是付诸实行”[41]。就历史发展来看,国家杜马没能成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它没有起到真正的“立宪”作用。“立宪”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立”首先要有“立”的力量。所以,严格说来,俄国还没有建立起议会,“只有米留可夫的幻想”。“应当进行革命斗争来争取强有力的议会,而不是通过软弱无力的议会来争取革命。现在俄国如果没有革命的胜利,那么议会(国家杜马或类似的东西)中的全部胜利都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42]因为“专制政府用宪法‘逗弄’俄国人民已经有好几年了。眼看就要把这个宪法‘差不多全部’给人民了,可是马上又变本加厉把从前的一切专横、警察的暴虐和不法行为拿了出来”,“颁发了两三道命令、宣言、指示,旧的专制制度就重又支配一切”。[43]这就是列宁的评价。俄国的政治有它自身的传统和发展逻辑。国家杜马就是国家杜马,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西方意义上的议会,如果牵强比附,就难免陷入“立宪幻想”,从而把词句(议会、议院)看作本质,把招牌看作内容。这无疑对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不利的。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但它迟迟没能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一个没有合法权威的时期、一个近乎无政府的时期,各阶级、各种社会势力都在尽力争夺社会资源,争夺合法性。仅存在了八个月的所谓共和国事实上并未能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议会共和国。在社会与政治的动荡中,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病——即将过去时代的和即将到来时代的以及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时期的弊病——都浮到面上来了,这一切都必然地被记到试图按照议会民主原则塑造自己的临时政府——尽管它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权威——的账上。这样,人们看到的俄罗斯民主共和国,既有议会民主不完善所带来的流弊,又客观上放大了议会民主制自身固有的弱点。正如列宁在批判议会民主制时所说,“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度的这些弊病已经显露出来了。”[44]
于是,俄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困境——历史将证明这也是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即它尚未享受到议会民主之惠,却已感受到议会民主之害。俄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任务便是要解开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要克服因没有议会民主或议会民主发展不足而产生的祸害,另一方面又要跨越议会民主的局限性。超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便是列宁面临的严峻挑战。列宁接受了挑战,他决定在俄国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跨跃。
历史给列宁提供了契机。在列宁抨击资产阶级议会制、鼓动革命的同时,俄国工人阶级在罢工和革命中创造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引起了他的关注。列宁在苏维埃一出现就抓住了它的实质和核心,并在此后反复不断地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论证。于是,一个代替那被否定了的议会民主制的新型民主的肯定形式的轮廓便逐渐凸显了出来。[45][46]社会主义民主在革命后的苏俄找到了它的制度依托和新的运行机制。
注释:
[1][14][16][18][20][29][44]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83-84,44,186,12-13,18,44页。
[2][3][4][8][9][11]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8,492,244,61-62,488,247页。
[5]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6][7][10][21][22][24]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5,83,327,100,84-85,100页。
[12][32][38] 《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124,212页。
[13][37][43] 《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8-309,308,378页。
[15] 《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17]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0-161页。
[19][23][25]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162,162,286页。
[26][34][35] 《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263,67页。
[27] 《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2-73页。
[28] 《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283页。
[30] П. Н. Милю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кой курытуры, т.3, париж, 1930, с.183.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33][36] 《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173页。
[39]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4页。
[40][41] 《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3,319-320页。
[42] 《列宁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5-106页。
[45] 蒲国良:《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6] 蒲国良:《列宁与苏维埃民主的最初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