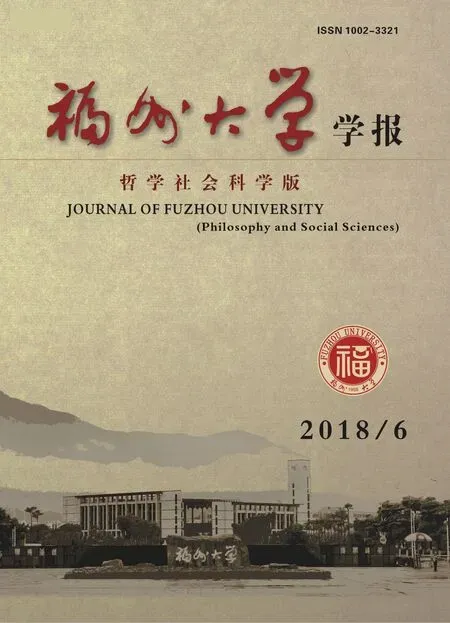周作人对《水浒传》的新见解
宿美丽 张可礼
(1.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2. 山东警察学院, 山东济南 250200)
检阅研究周作人的大量论著,不难发现,关于周作人对古代文学的论述,日益受到重视,在周作人与六朝文学、晚明文学、清代文学等方面,均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关于周作人对《水浒传》的论述,学术界至今基本上没有涉及。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涉及小说《水浒传》的内容。这些散文或专门谈论《水浒传》,或征引《水浒传》的若干细节作为散文创作的材料。综观这部分散文,可以发现周作人对《水浒传》的一些新的见解。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不以小说研究名世,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学问之广博与渊深,正因为此,他对小说的认识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评价《水浒传》中的人物,具有时代的特点。他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对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本给予充分肯定,看重读者的阅读体验。他较早地关注《水浒传》中有关的民俗方面的内容,并加以阐释,富有知识的趣味。
一、基于“人道”的立场批评《水浒传》
1914年,周作人以“启明”为笔名,在《绍兴教育会月刊》发表《小说与社会》一文,文章以文言写成,探讨了中国小说的源流,关于小说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小说并非直接作用于社会政治,而在于人心,以小说辅益群治,改良社会,必须先经过“陶铸性情”的步骤。这是周作人对中国小说最早的一篇评论。这篇文章以史为纲,简略论述,没有展开对具体作品的论述与评价,却确立了他日后评价小说的两种倾向:既认为小说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对社会产生功用;又注意小说艺术的独立价值。而强调小说艺术的独立价值,又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有益。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吸取改良派的小说功利观念而又注意文学的独立性,放在1914年的背景——文学改良之末,文学革命之前这个时段之下,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独立见解,这个评价应该不为过。
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以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文坛,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受到新文化运动发起人胡适的高度称赞。《人的文学》提出了人道主义的观点,以人道主义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学,将古代文言和白话小说分成九类反人道的内容,第六类就是以《水浒》为代表的“强盗书类”。文中的功利文学观念与《小说与社会》一脉相承,同样着眼于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人道主义”。明清两代,《水浒传》经常被视为鼓励造反的“贼书”而遭到毁禁,周作人沿用了这种说法,而批判的尺度变成了西方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用人道主义的立场考察小说,明显感受到小说中“反人道”的思想倾向,认为如果不加以甄别,只会贻害世道人心。随着观点的展开,又对立论进行补充,“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1]运用假设,对反人道的传统作品进行价值归纳,指示了运用传统的道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肯定了《水浒传》,周作人从启蒙的角度对小说进行思想评判,表面上看两人的观点相左,实际上共同构建了对文学传统的批判。所以,《人的文学》不仅没有引起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内部论争,反而大大地推动了文学革命的进程。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中,称誉《人的文学》为 “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2]。
在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对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强盗书”,没有继续展开反人道的追问,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却给予了解答,这表现在《水浒里的杀人》一文中。此文指出《水浒传》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人生观和态度,而这种人生观与态度是“要不得的,与民族的生命有极大的关系”[3]。他将《水浒传》的态度归纳为两种“病”——轻视人命和对女人和小孩的“他虐狂”,把《水浒传》的思想概括为两种“病”,值得重视。以“病”来批判《水浒传》的思想,周作人是现代第一人。《水浒里的杀人》所揭示出来的思想,正是他倡导“人道主义”的反面教材,周作人对此种反面教材一直保持警惕。1944年周作人出版了自编散文集《书房一角》,1945年推出了自编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前者收散文《小说》一文,后者收《小说的回忆》一文。1949年创作的一篇散文题目干脆就叫《水浒传》。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知堂回想录》里有《读小说》一文,重点谈到小说《水浒传》。从40年代到60年代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的这四篇涉及《水浒传》的散文,互相引述甚至重复彼此的观点,基本的观念和评价的尺度没有变化,前后对照起来看,很容易发现内容的一致性。四篇文章中关于《水浒传》的观点,与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一脉相承,也可以看作对《水浒里的杀人》一文的细化和补充。
《水浒里的杀人》只引李逵为例,而《小说的回忆》则将两组人物对比来谈,他们分别是鲁智深与李逵、武松与石秀。前文指出李逵漠视人命的杀人要不得;后文除了李逵之外,又将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武松、石秀。对于李逵的评价前后两文没有变化;后文指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可怕的原因是两个人都杀了自己的嫂子,但其中也有上下之分,武松杀亲嫂是为了报仇;石秀杀盟嫂却是为了表白自己。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表露了其“凶险、可怕以至可憎”的面目,但两人的相同之处都是“惨杀犯奸的女人”,表现了《水浒传》作者“对女人憎恶的程度”。这样一来,武松的行为也就暴露了其残忍的一面。周作人肯定鲁智深,因为鲁智深不曾胡乱杀人而表现出一派赤子之心。《水浒里的杀人》曾引述20世纪30年代青年作家废名、梁遇春的评论表达对武松的不满;《小说的回忆》则对这种不满做出周作人自己的解释,前后两文引证的小说故事情节不同,但对武松的评价却没有因为时间和评论人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早就得到极高的评价。明末清初人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的成就在《三国》《西游》之上,就是因为《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的突出成就。“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4]金圣叹首次提出对《水浒传》众多人物的看法。他把《水浒传》中的人物分成上上、上中、中上、中下、下下几个等次,每个等次都对应若干人物。定为上上的有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阮小七、杨志、关胜等人。上上人物中,又推武松为首,是“天神”一样的人物。“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通过对武松与鲁达的比较分析,武松的地位显然在鲁达之上。石秀与杨雄是结拜兄弟,虽然小说中杨雄的地位比石秀高,但金圣叹推石秀为中上,杨雄仅列中下。宋江是梁山好汉的头领,但金圣叹极尽否定,对他的评语是令人“深恶痛绝,使人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与时迁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归为一类,“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金圣叹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对小说人物给出了不同于著者的理解,他的小说人物批点具有态度鲜明、判断斩截的特点。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对女人和对儿童的具体作法来评判人物的高下。金圣叹对李逵评价甚高,认为他当得起《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批语,而周作人却不喜欢李逵,因为李逵滥杀无辜,甚至对一个小孩儿也不放过。金圣叹定石秀为中上,而周作人却认为石秀是可憎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假公济私杀害女人。金圣叹推武松为首,周作人对鲁达评价最高,因为他虽然“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5]。以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来作为评判《水浒站》人物的标准,可以看出周作人鲜明的 “人道主义”立场。《水浒传》确有反人道主义的内容。周作人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二、基于阅读者的立场观照《水浒传》
周作人虽然揭示了《水浒传》反人道的思想观念,但并没有因此否定《水浒传》的价值。他的小说价值观,特别注意从阅读的角度去立论,十分重视读者的体认。
最早站在读者立场去评价小说,利用小说评点与读者对话,教给读者阅读小说之法的,当首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他评点《水浒传》,开创了传统评点小说的模式。周作人一生服膺金圣叹,虽然不同意他对武松、李逵的赞颂,但却充分肯定他评点小说的读者立场 。同金圣叹一样,周作人善于从个人阅读的角度,站在读者的立场来认识、评价小说。
周作人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明确表示拥护。他在1944年自编的散文集《书房一角》的《小说》一文中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是为初学指导,养成了解鉴赏之力,与名师指点不异。”早在1934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周作人的挚友刘半农在《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中,就称赞金批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好处,特别对初学者来说,金批本有必不可少的帮助作用。十年之后,周作人的看法并没有简单重复刘半农观点,而是进一步对金批的好处加以具体说明。如果联系周作人的其他散文作品,就会发现周作人不仅明确肯定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贡献,而且也采用了小说评点的方法来评价小说。
周作人之所以肯定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主要依据是评点对读者有益,而他本人就是直接的受益人。周作人在1926年写的散文《我学国文的经验》中宣称:“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6]根据此文的叙述,周作人的祖父是前清的翰林,对小说的见解很开明:“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思路通顺。”受祖父的影响,周作人还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小说阅读。《小说的回忆》一文中,又重申了《我学国文的经验》中说过的话,“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7]。《谈金圣叹》一文谈到自己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期间,通过读金圣叹“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8]。《我的杂学》宣称通过看小说养成“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的能力,能够自己看书作文。周作人不止一次回忆自己作为读者读小说的经历,通过自己的散文把“我的阅读经验”分享给其他读者。在这里,“我”不是高高在上的作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周作人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谈论小说,其方法正来源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中说自己“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肯定小说具有开启心智的作用。周作人也在散文中反复申说小说在自己写作道路的指引作用,特别是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
金圣叹在评点小说中不仅采用了读者的角度,而且特别注意揭示自我对作品的感受。读者阅读评点的小说,会受到作品和评点者的双重感染,有助于养成提高鉴赏能力。这种能力往往表现在审美感受、情感表达上,是文学审美心理的具体表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明示了这种审美心理。他对文学有如下的定义:“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感到愉快的一种东西。”这个定义具有“不太正式的意味”[9],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三个要素:文学运用的是美的形式;内容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读者能感到审美愉悦。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文学作品。对第三点,周作人特别举《水浒传》为例加以说明:“从前的人们都以《水浒》为诲盗的小说,在我们看来正相反,它不但不诲盗,且还能减少社会上很多的危险。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想复仇,但等他看过《水浒》之后,便感到痛快,仿佛气已出过,仿佛我们所气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气愤也就跟着消灭了。”周作人把上述现象称之为“祓除作用”。从文学鉴赏活动来看,这种复仇心理的替代正是作品感染力的表现,也是阅读过程中常见的审美心理活动。1932年李长之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书评,盛赞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表现了“健全、正确”的识见,并将其归纳为值得注意的五个方面,其中两个方面都与小说文体有关:“文学的特性是感情的,除了为说出外,没有目的”;“文学的用处是消气,是平气,而不是挑拨。”李长之所谓的“消气”“平气”,正是阅读审美心理的作用。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让愤怒的情绪得到平息,紧张的心理得到放松,也就是获得了审美的愉悦。
从自我的阅读经历入手,引导读者达到审美鉴赏,周作人发现了《水浒传》的独特社会作用。在《水浒与红楼》一文中,周作人比较了《红楼梦》与《水浒传》两部古典小说。他对两者同样看重,并不厚此薄彼,虽然“要看重《红楼》一点”是通常的看法。他之所以将两书并称为“两条大台柱”,给出的理由仍然是读者欣赏的角度:“(《红楼梦》)里边的公子小姐们的性情生活,与老百姓颇有距离……不及梁山泊的男女可以了解。”[10]并进一步指出《水浒传》戏文远远超过《红楼梦》,足以证明老百姓对前者的兴趣。1944年,李长之在《中国文学》上发表《水浒传与红楼梦》一文,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将两部小说并称为“伟大的作品”。李长之立论的角度,与稍后周作人的读者视角构成互补。二人评论的角度不同,结论却惊人的一致。结合前文周作人对《水浒传》小说人物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对《水浒传》的人物虽有微词,但并没妨碍他从整体上肯定小说。周作人在1919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唯一没有列入批评目录的古代小说就是《红楼梦》。周作人在散文中对《红楼梦》的思想、人物颇多赞赏之词,但从《水浒与红楼》可以看出,他对后者的肯定并不以贬低前者为条件和代价,对前者思想的批评并没有否定其艺术价值,否定小说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他的理性而客观的批评态度对今天的批评者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从文化习俗方面观照《水浒传》
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将自己涉猎的读书领域分成八大类,第三类“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对习俗颇为留心。根据《知堂书话》辑录,他除了对叙写故乡绍兴和北京的历史风俗的作品特别留心以外,还大量涉猎了古今中外许多具有相关内容的作品,同时安特路朗的文化人类学不仅带给他了解古旧民俗的兴趣,也给了他一种探究的方法。根据周作人的介绍,安特路朗研究民俗特别擅长从前代典籍中搜寻材料,按照类目重新编排,得出自己的结论。从周作人作的三篇与风俗相关的《水浒传》短文来看,他对《水浒传》中涉及的风俗,特别留意,也使用了安特路朗的探究方法。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水浒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作者、渊源、成书、流传、内容 、续书等方面,没有发现有人从习俗角度来探究《水浒传》中蕴涵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周作人首次以杂谈的笔法,论述了《水浒传》中的诗歌、唱喏、酒望子体现的习俗方面的内容。
在短文《水浒的诗》中,周作人说:
书中最有意思的倒是有些人唱的山歌,如三回五台山挑酒汉子的好似虞姬别霸王,五回瓦官寺道人的你无夫时好孤凄,十五回黄泥冈白胜的公子王孙把扇摇,五十回勾栏里白秀英的定场诗皆是。末了这一篇全文云:新鸟啾啾旧鸟啼,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金圣叹特别称扬,批注云,俗本失此一段,可谓食蛑蝤乃弃其螯矣。因此怀疑是他所加入的,但是这歌实在不差,不但若即若离的关合本题,也含有讽世之意。
金圣叹批点的《水浒》对这四处诗歌有详细的评点。他称赞这些口头文学是“妙绝”之文,不但指出诗歌本身的好处,而且点明其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推进情节的作用。“第一首恰好唱入鲁智深心坎也;第二首唱出崔道成事迹也;第三首恰好唱入众军汉耳朵也。”[11]这些诗歌或正写或反语或类比,富有民歌的特色和风调。金圣叹重视评点这些口头文学,称赞《水浒传》“每每横插诗歌,如五台亭里,瓦官寺前,黄泥冈上,鸳鸯楼下,皆妙不可言”[12]。周作人特别引用了金圣叹对第四首的批点,指出了此诗的价值,肯定诗歌在小说中的合题和讽世作用。1929年周作人的《娼女礼赞》一文,曾用第四首诗引入话题,揭示了娼女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原因。《水浒的诗》全文仅三百多字,同样不惜笔墨引用全诗,可见周作人对此诗的偏爱。短文仅仅就白秀英的妓女身份指出诗歌的批判作用,如果与《娼女礼赞》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这首七言定场诗蕴涵的文化人类学内容。
周作人读《水浒传》是相当细致的。他发现《水浒传》里有些唱喏。如何理解这些唱喏,前人未予关注。为此,周作人特别撰写了《水浒里的唱喏》一篇短文。周作人见识广博,短文从乾隆时太仓顾雪亭《土风录》、范啸风《越谚》、顾铁卿《清嘉录》、宋人《虏庭事实》和宋人笔记等古籍中寻找证据,又听故友马幼渔讲故乡宁波风俗、方言,从读音、民俗和戏曲等方面探讨唱喏的内容和方法。唱喏在《水浒传》所叙写的时代十分盛行。但确切的加以解释,如何读,内容是什么,怎样的方法,周作人还从《老学庵笔记》发现了材料,在《怎么唱喏》中给予解释。此文最后说:“《水浒传》里的那些唱喏终于也弄不清它的真相,只能笼统的解释作打躬罢了,作揖也还未必,因为宋朝官妓也都是声喏的。”[13]由于所见史料的限制,周作人对《水浒传》里的“唱喏”的动作,只能做出“笼统的解释”,但如何读音因为材料的缺乏只好存疑。看来周作人在阅读《水浒传》时,不仅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同时对发现的问题的解释是相当严谨的 。
《酒望子》列举了《水浒传》中的酒店招牌,在小说中第三回、第二十八回多次提到酒店门口的酒旗、草帚儿。这些当时的招牌名称不一,形状各异,却能够反映当时酒店的规模和某些习俗。周作人对酒望子的历史、名称、分类作了一番钩稽。他从子书、笔记中找到佐证,引用《韩非子》、明代杨慎《丹铅总录》的说法,对酒望子进行分类,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而且通过古今对比,证明酒望子与现代招牌的渊源,从而得出富有趣味的结论。
四、结语
1949年周作人在散文《红楼梦》一文中,提出了如下三种阅读作品的方法:“其一是站在外边,研究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其二是简直钻到里边去,认真体味,弄得不好便会发痴,一心想念林妹妹,中了书中自有人如玉的毒了。此外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描写的巧妙,却又多注意所写的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14]周作人讲的这种“平凡人的读法”虽然主要针对的是读《红楼梦》,其实他读《水浒传》,大体上也是采用了这种读法。周作人虽然采用“平凡人的读法”,但由于他学识渊博,善于独立思考,因而他阅读《水浒传》的水平却远在“平凡人”之上,有独到的新见解。他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从《水浒传》中读出了其中存在的病态的人生观;他受金圣叹的影响,站在读者立场,从读者的感受,肯定小说的价值,尤其肯定金圣叹的评点对引导读者参与小说价值生成的意义;他重视民俗,受文化人类学的启发,发现《水浒传》中的诗歌、唱诺、酒店招牌等内容,并探讨这些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边角余料”中隐含的世相和古旧风俗。周作人向来以散文名世。从今存他的著述来看,没有学院式的有关《水浒传》的长篇大论。他的见解全是散见在多篇有关《水浒传》的散文中。他的阅读作品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的新见解,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注释:
[1]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 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3][5]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6,376页。
[4][11][12]《金圣叹批评〈水浒传〉》 (上),刘一舟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18,175,175页。
[6]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7页。
[7][14]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8,809页。
[8]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9] 李长之:《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李长之文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文章最初发表于1932年10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
[10]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13]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