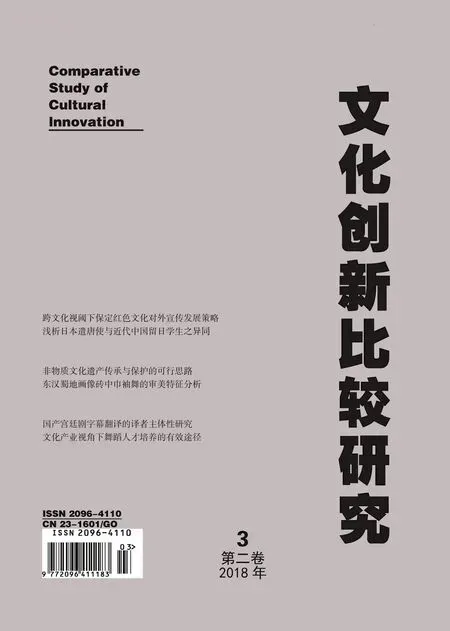“等待”中的女性他者
张海燕 赵静春 毛海涛
(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北沧州 061001)
引言
哈金以长篇小说《等待》一举获得1999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成为该奖项设立50年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华裔作家,《等待》以十八种文字在25个国家出版。2000 年哈金又凭此书荣获福克纳小说奖,美国笔会的颁奖词中称他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孔林等待离婚的漫长过程,“序”里倒叙分居17 年之后的第二次“对簿公堂”(1983年),之后按时间顺序讲述:60年代的故事主要围绕孔林结婚、父母亲去世、对原配淑玉心怀感激;70年代的故事主要描述“等待”离婚的过程,发生在女朋友吴曼娜身上的事为主,先后被介绍给孔林表哥孟梁和魏政委、又被孔林病友杨庚强奸、以及孔林和淑玉第一次“对簿公堂”(1973年);80年代的故事讲述了淑玉进城离婚、定居,孔林回乡卖屋接女、再婚生子;结尾处孔林重回淑玉处寻求慰藉……
下面借助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的女性他者理论,解读刘淑玉与吴曼娜这两位处境悲惨的女性他者形象。
1 波伏娃的女性他者理论概说
对于“他者”(the Other)这一哲学术语,《第二性》的译者陶铁林给出定义:“‘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体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而作者波伏娃在书中提出一著名命题:“女人是他者”。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他者”本身的地位进行了探讨。波伏娃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角度阐明妇女的他者性质,全面勾勒女性他者的主要特征:不仅具有内在性与被动性,而且存在消极性和异化状态;更为突出的女性“他者还具有绝对性与纯粹他性。纵观女性的发展就是漫长的他者历史,在这持续的过程中,女性他者一直作为“次等族类”被排斥在文明之外。“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inessential)。”如此说来,女性成为他者的前提是男性率先把个人确定成主体,又从自己视角出发来定义次要者和主要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长期以来,社会各个阶段均不可僭越地实行男权统治。于是乎,女性始终处于一种附属和被支配的地位,难以逃脱他者的命运。
波伏娃用存在主义理论来解释女人的文化身份和政治地位,最早也是最清醒的认识到广大妇女在既有的文化秩序中备受压抑的现象,严厉批判强大的父权制传统,试图改变女性他者们消极的特性与无奈的命运。
2 “原配”刘淑玉的女性他者命运
孔林的原配淑玉是出生于4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女性。作为传统女性她身上背负的更多来自生理性别的挤压,例如生育、性生活还有体力差异等。恰与波伏娃所观照的历史中女性他者状态一样,女性为传统观念所困,内在深深植入他者属性,默认命运的种种强加,甚而根本不具备超越现状的可能性。
首先是落伍的外在特征。与自己丈夫孔林的白净细嫩英俊不同,淑玉干瘪瘦小老相;一个鼻子上架着黑边眼镜,另一个却裹着小脚、打着黑色的绑腿;男的是儒雅的知识分子,女的是土气的乡下妇女:这对夫妻太不般配了!哈金有意标示她的“缠足”,给淑玉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落后,保守,活在过去的时代里。
其次是非正常的夫妻生活。淑玉之所以能够嫁给孔林,是因为他妈妈生了重病,家里的房子破旧不堪,孔父迫切需要一房儿媳来照管家务。“孝子”孔林万般无奈地接受了这门亲事,可在情感上从未接纳这个新娘。结婚二十多年孔林从未让淑玉来驻地探亲,而且自女儿降生,他回家两口子也是分开就寝,这样过了半辈子。
第三就是被离婚。大概是女儿出生的同时,孔林的感情世界里出现了吴曼娜。虽然心头纠缠着亲情与恩情,一直在进行道德自我谴责,但最终敌不过改变僵死生活的强烈念头,孔林开始了“解放”自我之路——闹离婚,一闹十八年。
在淑玉身上体现出女性他者的内在化与固有性,她没完没了的重复地做着家务劳动,丝毫不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工作,似乎这些注定只由女性来做。波伏娃指出“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甚至面对被离弃丝毫不抱怨,还是本生(淑玉的弟弟)不忿为她叫屈:“(姐姐)她在孔林家生活了20多年,像头哑巴牲口一样伺候他们。她伺候那个病婆婆直到老太太去世,再伺候公公直到他去世,然后一个人将女儿拉扯大。她的男人还活着,可她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而当被人问起时,淑玉却说“他们从来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 就是这样在私人领域——家庭中,传统女性备受压迫却不自觉。男人们被社会分工打扮成养家糊口的主角,而实际付出更多的女人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被贴上所谓的“贤能、贤惠、温柔体贴”等标签,心甘情愿成为附属品。
令人痛心的是,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吴曼娜心力交瘁、重病缠身,都没几天活头了;淑玉反倒返老还童了,脚步轻快,性情开朗,充满活力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她感觉到了孔林有意重修旧好,有可能又一次需要她来撑起他那一地鸡毛的家庭时,淑玉变得自信起来,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憧憬。女儿孔华说“您应该看看我娘的样子,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孔林说“告诉她不要等我了。我是个没用的人,不值得等”“爸,您这是何苦呢?我们都会等着您的。”淑玉在等待,她在等待什么?终其一生在等待什么?
3 “女朋友”吴曼娜:女性他者被异化
现代女性吴曼娜更多受到社会性别的困扰,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他者的异化状态进行描述:女人被男人异化,先是成为客体,甚而被当作无生命的物,也就是意味着被物化。正是异化使女性意识分裂,真实自我逐渐丧失,最后被异化为“非我”。这完全是男权制社会使然,在众多男人眼中:“女人是财富和猎物,是运动和危险,也是保姆、向导、法官、调解者和镜子,所以她是这样的他者:主体通过她超越他自己而不为其所限,她与他相对立而不予以否定;她也是这样的他者:她让自己被占有而仍不失为是他者。”
吴曼娜与孔林虽然被大家公认为一对儿,事实上她最可悲。三岁失去父母成了孤儿,从八岁开始想成为天使,生命简单、淡薄,二十多枚毛泽东像章是她唯一珍藏的物件。怀有天使梦想的吴曼娜日渐被庸常生活挤压变形。
先是与董迈初恋的失败。吴曼娜刚来到这所部队医院护士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正值妙龄充满活力的女孩。当她遇到第一个追求者董迈,很快热恋起来。可无论如何吴曼娜都不能接受恋人的亲吻,二人的关系难以深入和稳定,结果不堪忍受北国严酷气候的董迈转业回上海,与表妹结婚,吴曼娜后悔不已。这一方面是由于部队医院的严明纪律,更主要的是外在的文化赋予她的道德感和名誉感阻止她顺从身体的欲望。
最主要的是对孔林的等待。被董迈抛弃后,吴曼娜慢慢爱上孔林,进而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这个一样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男性。对孔林“离婚”一次次无望的等待把她剥琢成“无可救药的泼妇”,陷入凡俗生活的套路里;甚至当遭受杨庚的强暴后,她都无法讨回公道,自己反而沦为众人的笑柄。即便结婚后也无幸福可言,44岁的高龄孕育双胞胎、强烈的妊娠反应、生产时的巨大痛楚,这些扭曲了她正常的性情;接下来哺育孩子,她更是不堪重负,身体越来越糟,坏脾气也加剧了;坠入活力耗尽,时日无多的悲惨结局。
此外吴曼娜被杨庚强奸、被介绍给孟梁、被魏政委选择。杨庚是男性暴力的符号性人物,孟梁代表凡俗的庸常生活,魏国洪代表制度权力。吴曼娜在 “等待” 的愿景中无数次接受命运的嘲弄,不仅与孔林同样面对体制的强力,还要忍受男女性别差异带来的创伤。
4 结语
《等待》中,刘淑玉、吴曼娜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两个女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演绎着不同的人生,她们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这是由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造成的。“当一个人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处境,实际情况只能是低人一等。因为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带来的机遇较少”。 女人的悲剧性就在于每个个体在坚持个人抱负的时候,不可避免与强制性处境发生冲突。女性主体都自认为是主要者,而处境偏偏把她定义为次要者。当然,波伏娃也批判了女性自身,如果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永远不可能占据主体地位;默默无语的她们得到的仅仅是男人想赐予她们的,从未去争取,一向在接受,那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也是无救的。所以说女人不应该只做一个受排斥的、沉默的他者。
苦苦相恋十八年最终在一起,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孔林第一次对吴曼娜大发雷霆,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医院后面的小山漫无目的地走,昔日二人幽会的地方呀,而此时的他想 “等了十八年,却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等了十八年,等来了一场该死的婚姻,自己是个头号大傻瓜”; 淑玉在等待孔林重回身边,吴曼娜在等什么?等死!虽然小说采用开放式的结局,但可以预测,女性他者的地位不会改善。
不要再等待!
[1] 西蒙·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哈金.金亮译.等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3] 罗义华.《等待》中的道德问题和哈金的批判指向[J].外国文学研究2010(6):112-119
[4] 卫景宜.社会转型与伦理的困惑:再论《等待》的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