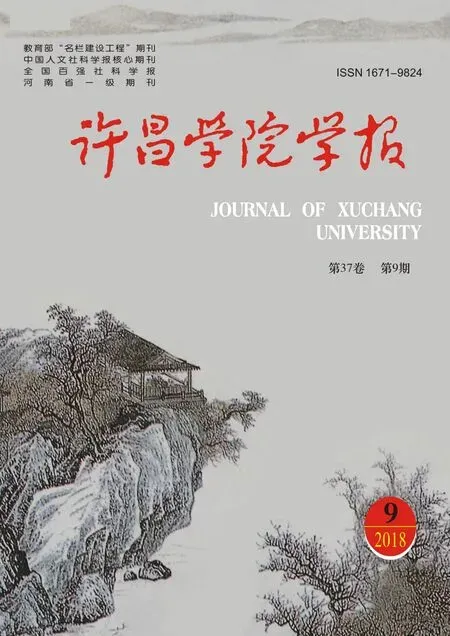“所乐乐吾乐,乐而安有淫”
——以“乐”为核心的邵雍诗学观念
庞 明 启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400065)
邵雍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理学家,位列“北宋五子”,但与其他四子不同的是,他同时以诗人自居,并非常自得于自己的诗人身份。他看重“诗言志”的本体认知,赞美《诗经》所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不仅没有将作为经典的“诗三百”与后世诗歌进行功能的对立而厚此薄彼,而且毫不轻视诗歌的娱乐作用,并将其与诗教的道德色彩结合起来,借此提高娱乐的重要性。他把诗歌看成是个人与他人、万物连接、沟通的纽带,也看成是体道与娱乐相辅相成的唯一途径,诗、道、乐三者在邵雍那里是密不可分的。
一、《诗画吟》《诗史吟》《史画吟》:有德之乐诗歌观念的集中体现
邵雍《诗画吟》《诗史吟》《史画吟》三诗,集中从儒家诗教的高度谈论诗的功用。其《诗画吟》曰:
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诗者人之志,言者心之声。志因言以发,声因律而成。多识于鸟兽,岂止毛与翎?多识于草木,岂止枝与茎?不有风雅颂,何由知功名?不有赋比兴,何由知废兴?观朝廷盛事,壮社稷威灵。有汤武缔构,无幽厉欹倾。知得之艰难,肯失之骄矜?去巨蠧奸邪,进不世贤能。择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借江山清润,揭日月光荣。收之为民极,著之为国经。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悦,此所谓和羹。既有虞舜歌,岂无皋陶赓?既有仲尼删,岂无季札听。必欲乐天下,舍诗安足凭?得吾之绪余,自可致升平。[1]482-483
这首诗谈的是《诗经》的功用,里面含有传统儒家诗教的许多说法,比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论语·阳货》中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及《诗·大序》中的“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等等。在此基础上,邵雍进一步引入了他的观物思想,包括观自然、观历史、观宇宙,从中得到历史和宇宙发展运行的规律法则。之后,他又把以诗观物与诗乐舞一体以及《诗经》原始的祭祀功用结合起来,以“人神之胥悦”“必欲乐天下”的和乐作为至高无上的最终目的。诗的观物性能及诗人的观物所得,通过诗乐舞的结合及其在祭祀中的应用——娱人娱神,达到感人心、告神明的目的。由此,邵雍不仅借《诗经》提高了自己所独创的观物思想的地位,而且提高了他所信奉的“和乐”的生命境界,以诗娱乐便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变成赞天地造化的大功德。
《诗史吟》曰:
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伯时,其人长如存。百千万亿年,其事长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齐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训子孙。可以尊万乘,可以严三军。可以进讽谏,可以扬功勋。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亲。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可以赞天地,可以感鬼神。规人何切切,诲人何谆谆。送人何恋恋,赠人何勤勤。无岁无嘉节,无月无嘉辰,无时无嘉景,无日无嘉宾。樽中有美禄,坐上无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无埃尘。忍不用大笔,书字如车轮?三千有余首,布为天下春。[1]483-484
此诗认为,诗歌是内心节奏和生命节律自然而然的感发,因此诗史就比刻意惩恶扬善的史笔更具真实性。无论是诗画还是诗史,邵雍都在强调诗歌如实客观而又直指本真的观物功能。只不过诗画是对历史、宇宙的全方位观照,而诗史的观照对象仅在于历史,但和诗画一样,诗史功能的最终旨归也在于调和夫妇君臣之义的人伦秩序和天地鬼神的物理秩序,具有一种含纳万有的泛道德性。不过在此诗最后,邵雍却把诗史的落脚点集中在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人之间的和乐上。需要注意的是,邵雍所谓的“诗史”和我们一般而言的杜诗那样记录史实的诗史不同,它还含有诗歌本身的发展历史这一层面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个人,无论是记时事还是记心事,其全部类型的诗歌都可以纳入诗史范畴当中。于是古往今来的酬唱诗、送别诗、宴饮诗这些产生于日常人际交往,用来娱人娱己,具有直接和乐功能的诗歌便被邵雍着重提出来,作为和乐的诗歌核心属性最为直观的见证。邵雍由兼综史事之诗、心史之诗的大诗史缩小到人际之诗、宴饮之诗的小诗类,再进一步缩小到自己的诗,最后逆向地把自己所作诗歌以及诗歌本身的和乐真诚功能收摄到诗史当中去。且看《诗史吟》结尾四句:“忍不用大笔,书字如车轮?三千有余首,布为天下春。”大字写诗是邵雍平日快意作诗的习惯性行为,如其《大字吟》曰“诗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笔抄”[1]349,《安乐吟》曰“小车赏心,大笔快志”[1]413。“三千首”是邵雍对自己所作诗歌的经常性称谓。其《击壤吟》曰:“击壤三千首,行窝十二家。”[1]461《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曰:“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捻白髭。”[1]561而“三千首”又是孔子删诗以前原始《诗经》的数量。“春”也是他经常用来形容和乐状态的词语,他常常将饮酒、作诗等自适行为所营造的内心和乐之“春”引申到万物和乐的“天下春”上。如此一来,层层缩小以至最后落脚到自己那些以和乐为基本精神的诗歌之后,他又旋即将其放大到诗史的宏大视野中,娱乐的小道也顿时进入人间与宇宙的大德序列中。
其《史画吟》曰:
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状情与记意,二者皆能精。状情不状物,记意不记事。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体用自此分,鬼神无敢异。诗者岂于此,史画而已矣?[1]485
此诗题为《史画吟》,实际上是合起来论诗史与诗画的,却又并非《诗史吟》《诗画吟》二诗的简单叠加,而是论诗歌的叙事与描写功能,叙事、描写分别对应着诗史、诗画。邵雍认为诗的叙事、描写主要是记事之意、状物之情,也就是关注事物的所以然而略其所当然,即抓住背后的各种因果联系。显然,这是理学家格物致知的诗学观,反映了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不同,邵雍是以前者自命的。综观邵雍的全部诗歌,其中固然有大量的说理议论诗,但也有不少情趣盎然的写景抒情诗,而绝少叙事诗。邵雍写诗讲究快意、率性,从来不曾苦吟,对事物的叙述、描摹都采取遗形取神的态度,该诗中所谓的“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就是这种作诗方式的反映。又有所谓“体用自此分”,即重体轻用,重本质而轻外在,也是一样的道理。邵雍采用这样的方式作诗,使得他的诗歌完全摆脱了思虑之苦,即便通篇说理也能达到快意适性的目的,而那些生活情趣诗则更加洒脱爽利。无论如何,诗只要能“言志”,便不失快乐,即如其《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八十所言:“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欢喜时。欢喜焉能便休得?语言须且略形之。胸中所有事既说,天下固无人数殊。更不防闲寻罅漏,尧夫非是爱吟诗。”[1]530
以上三诗主要谈论诗之德而又兼重诗之乐,将乐提高到了道德的层次,有德之“乐”是邵雍核心的诗歌观念。这个“德”范围很广,既是人伦秩序之德,又是宇宙秩序之德,与“道”别无二致。现代研究者也注意到邵雍诗学中“乐”的重要性,如张海鸥先生根据《伊川击壤集自序》中邵雍自陈“《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惟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认为他的快乐诗学包括“自乐”和“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两方面,并总结出三有、四不原则[2]26-31。刘天利先生认为“乐”是邵雍诗一大主题,是北宋社会繁荣和邵雍本人心性修养共同作用的结果[3]54-58。诗歌是大德大道的载体,而写诗本身又是如此快乐,能自乐、乐人、乐时,乃至与万物同乐,修德载道便与娱乐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
二、友朋、风月、天机:邵诗之乐的三个层次
笔者将邵诗之“乐”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友朋酬唱的知己之乐,二是收管风月的自然清欢,三是觉悟天机的通达理趣。《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四十一曰:“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得时。风露清时收翠润,山川秀处摘新奇。揄扬物性多存体,拂掠人情薄用辞。遗味正宜涵泳处,尧夫非是爱吟诗。”[1]522说的大致就是这三个层次。
(一)友朋酬唱的知己之乐
邵雍《观诗吟》曰:“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1]416《读古诗》曰:“闲读古人诗,因看古人意。古今时虽殊,其意固无异。喜怒与哀乐,贫贱与富贵。惜哉情何物,使人能如是。”[1]406这与他的观物思想、诗史思想是一致的。诗歌能够“曲尽人情”,即使古今时殊事异,依然能够通过读古人诗而知古人意,进而通过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而尚友于古人。而对于同时代人来说,诗歌当然更是结缘、交游的绝佳媒介。爱好作诗,又喜欢不断在诗中展示自我形象的邵雍,在交友方面自然从诗歌中获益良多。邵雍在《答客》中说:“人间相识几无数,相识虽多未必知。望我实多全为道,知予浅处却因诗。”[1]229可见诗歌已经成为这位道学家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虽然邵雍说其诗只能反映他思想的“浅处”,富弼却认为从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中能够看出他的“全道”,《弼观罢走笔书后卷》诗曰:“黎民于变是尧时,便字尧夫德可知。更览新诗名《击壤》,先生全道略无遗。”[4]卷二六五3369富弼还在和邵雍《安乐窝中好打乖吟》中讲述了邵雍自卫徙洛、乐道安闲、不应举荐、甘守贫寂、治史吟诗、与己交好的经过,曰:“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贯穿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4]卷二六五3367富弼将“吟诗”作为他“乐道安闲”的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与“探古”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也从侧面说明了诗歌在二人交情之中所占有的分量。富弼诗歌现存较少,《全宋诗》中收诗23首,而《伊川击壤集》中附载他与邵雍的唱和诗即有12首,占二分之一强,成为除司马光而外附载诗歌数量最多的诗人,而现存邵雍与富弼的唱和诗更是多达16首。诗歌像一面照鉴表里精粗的明镜,不仅可以作为二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使得地位悬殊的两人毫无滞碍地相互了解,引为知己,更直接见证了二人诚笃的友谊。
邵雍《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三十七自述对交友的热衷及其在老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诗歌能为他处理好这些交际事务,曰:“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喜老时。好话说时常愈疾,善人逢处每忘机。此心是物难为动,其志唯天然后知。诗是尧夫分付处,尧夫非是爱吟诗。”[1]522“分付”就是委托、交付的意思,他把说好话、逢善人这些事情都委托给诗歌去办理了。《闲居述事》六首其五叙平居与友朋欢会的情形,曰:“清欢少有虚三日,剧饮未尝过五分。相见心中无别事,不评兴废即论文。”[1]238其中“论文”大抵亦指唱和及品评诗歌而言。作为长者和师者的邵雍,其苦心孤诣的道学成就吸引着大量的慕名而来者,《宋史》本传曰:“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5]卷四二七9949而他之所以能表现得“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一接以诚”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够以“观物”“言志”的坦诚态度与四方的拜访者诗酒酬唱,从而宾主相得,让人产生彼此无殊、异常亲切的感觉,即如《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三十所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对酒时。处世虽无一分善,行身误有四方知。大凡观物须生意,既若成章必见辞。诗者志之所之也,尧夫非是爱吟诗。”[1]520邵雍的交游面极广,郑定国先生统计说,“总计雍之交游者约可得近二百人”,“其交游至好二十六人”[6]上册24-25。在洛阳本地交游圈中,闲退耆宿、世家大族、各级官吏与之皆有交往。此外,他还有不少寄诗、与慕名而来者的唱酬诗等等,反映了他有着远远大于洛阳本地的交游圈。其唱酬活动也较为多样,包括宴会、出游、赠答、送别、代简等。
(二)收管风月的自然清欢
邵雍在《自作真赞》中自我评价道:“松桂操行,莺花文才。江山气度,风月情怀。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自注曰:“丸谓太极。”[1]375“松桂操行”指始终如一的品格,“莺花文才”指歌咏自然美景的诗才,“江山气度”指远见卓识和透脱襟怀,“风月情怀”指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弄丸,指玩味易理。从该诗中能够明显看出,邵雍把自己的诗人身份和理学家身份看得一样重要,而且研究易学和吟咏诗歌、欣赏美景都是本着愉悦身心的态度,即所谓“弄”,这在北宋理学家中堪称异数。二程评价道:“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往时来’(按,邵雍将《自作真赞》收入自传文《无名公传》中)之类 。”[7]45明确表示对邵雍这种治学态度的不满,其实这正证明了邵雍是一位很接地气、很有人情味的理学家。二程又评价道:“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言来,直是无端。”[7]45“雪月风花未品题”出自邵雍《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一。这也正反映了上文所指出的邵雍通过诗歌将娱乐提高到了道德的层次。与《自作真赞》相似的自我评价还有《尧夫吟》,曰:“尧夫吟,天下拙。来无时,去无节。如山川,行不彻。如江河,流不竭。如芝兰,香不歇。如萧韶,声不绝。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风,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风流,又激切。”[1]473在此更是专门以吟风弄月的诗歌才能为自己的身份定性。
邵雍不厌其烦地在诗歌中表达对风花雪月等自然美景的喜爱、依赖、领悟,认为其乃人生一大乐事。他还以风月主人自命,反反复复声称自己有着“收管风月”的权力,而诗歌正是他的“权杖”,如《自况三首》其二曰“满天风月为官守,遍地云山是事权”[1]246,《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曰“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捻白髭”[1]516,《花月长吟》曰“花逢皓月精神好,月见奇花光彩舒。人与花月合为一,但觉此身游蕊珠。又恐月为云阻隔,又恐花为风破除。若无诗酒重收管,过此又却成轻辜。可收幸有长诗篇,可管幸有清酒壶。诗篇酒壶时一讲,长如花月相招呼”[1]265。为什么诗歌能够赋予诗人“收管风月”的权力呢?因为诗歌能够将自然的美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并赋予它们更加灵动鲜活的气息和不随时间衰败的永久魅力。面对美景,诗人除了拥有收管的权力,还有报答的义务,诗歌也正是这种权力义务的统一体。邵雍屡有“幽人自恨无佳句,景物从来不负人”[1]201(《和商守西楼雪霁》)之类的叹息,又说“无涯负清景,长是愧非才”[1]213(《过永济桥二首》其一)“烟轻柳叶眉闲皱,露重花枝泪静垂。应恨尧夫无一语,尧夫非是爱吟诗”[1]523(《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四十二),觉得愧对自然无偿无私的恩赐,诗人若是不能用和美景相匹配的美好诗歌投桃报李,就只能落得忘恩负义的恶名。不过,邵雍多半时候还是非常相信自己有着灵性和诗才,完全当得起风月主人的称号。他自认为天生具有这样的“风月性情”,会不由自主地显露出天机自得之处,于是所有的愧怍都会在不经意的瞬间烟消云散,所有的负担也会一下子涣然冰释,转变为无可名状的欣喜和飘然洒然的轻盈,故曰:“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何尝无对景,未始便忘情。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天机难状处,一点自分明。”[1]231(《闲吟》)
邵雍当然也意识到,作为一个理学家如此喜爱诗歌、狎昵风月并不是符合常规的举动,所以他有时会将自己在这方面的浓厚兴致称为“风流罪过”,如曰:“月恨只凭诗告诉,花愁全仰酒支梧。月恨花愁无一点,始知诗酒有功夫。些儿林下闲疏散,做得风流罪过无。”[1]265(《花月长吟》)“既称好事愁花老,须与多情秉烛游。酒里功劳闲汗马,诗中罪过静风流。”[1]325(《年老逢春十三首》其十)然而这只是戏称而已,并没有二程所指责的“侮玩”那样严厉认真。“风花雪月”的意思在青楼妓馆盛行的宋代早就变味了,虽然邵雍从来没有染指其中,但他所谓的“风流罪过”也隐然含有这方面的戏谑,这也成为二程指责其为“侮玩”的口实。不过邵雍毫无忌讳地在诗歌中比花月为美女确有越雷池之嫌,如其《恨月吟》曰:“我侬非是惜黄金,自是常娥爱负心。初未上时犹露滴,恰才圆处便天阴。栏杆倚了还重倚,芳酒斟回又再斟。安得深闺与收管?奈何前后误人深。”[1]267将月亮的阴晴不定比作嫦娥的爱负心,让爱慕嫦娥的人也就是赏月的诗人徒费等待之苦,于是引起诗人的怨恨来,觉得真应当把这样负心的女子收入深闺,以便长相厮守,而不是让人如此枉费痴心。又,《愁花吟》曰:“三千宫女衣宫袍,望幸心同各自娇。初似绽时犹淡薄,半来开处特妖娆。檀心未吐香先发,露粉既垂魂已销。对此芳樽多少意,看看风雨骋粗豪。”[1]267此诗意淫的成分与前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诗中只有一个负心的嫦娥,此诗中却有望幸心切、各逞娇媚的三千宫女。望谁之幸呢?当然是皇帝。然而此处携樽相对的却是邵雍本人,为之魂销、百般怜惜的也是邵雍本人,其中该有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意,读者只有慢慢体会了。
尽管如此,邵雍认为这些都是他独特的心性之乐的书写,并没有不合理或者过分的地方,“所乐乐吾乐,乐而安有淫?”[1]459(《无苦吟》)因为对自然景物的爱赏是一种高雅的“清欢”,“小车芳草软,处处是清欢”[1]310(《寄三城旧友卫比部二绝》其二)。既然如此,便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贪婪的质疑和其他任何损害,“稍邻美誉无多取,才近清欢与剩求。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且无忧”[1]211(《名利吟》)。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邵雍便毫不讳言对包括花月在内的一切美好自然景观的痴恋,不仅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去享受,并且不断宣称“无涯逸兴不可收”[1]242(《秋日饮后晚归》),“游心一向难拘捡”[1]250(《十七日锦屏山下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游兴亦难拘日阻,梦魂都不到人间。烟岚欲极无涯乐,轩冕何尝有暂闲”[1]245(《和祖龙图见寄》),等等,坚信“贪清非伤廉,渎幽不为辱”[1]210(《游山二首》其一)。所以根本不存在二程所说的什么“侮玩”的忌讳,一切都是对精妙诗思的陶冶、对奥妙心性的发扬。
(三)觉悟天机的通达理趣
邵雍诗歌叙事、描写的成分较少,议论的成分较多。有的议论能够结合具体的形象、丰富的想象和新鲜的比喻,显得生动活泼。有的议论则是屏除任何具体形象直接说理,类似于押韵语录。与“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8]1418(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的扬雄相反,邵雍是以浅易之语写精深之理。但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邵雍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除了节奏感、韵律感强,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浅显易懂之外,还洋溢着智慧、灵动、爽朗的气息,使得读者亲切地感知到一位洞明世事、通达性理而又趣味横生的智者、长者形象。邵雍《放言》诗曰:“既得希夷乐,曾无宠辱惊。泥空终日着,齐物到头争。忽忽闲拈笔,时时自写名。谁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1]225他拈笔作诗纯粹出于一种难以名状、发自肺腑的希夷之乐,是为了抒发和愉悦自己的性情,力求摆脱佛家泥空、道家齐物的条条框框,即事即理,即景即情,一派真诚。这正应了他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说的:“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1]180
综观《伊川击壤集》,所照之物、所起之志的范围是没有局限的,包括说理、写景、抒情、叙事、说易、咏史、咏物、养生、博物等各种题材,从我到物,从风花雪月到天地宇宙,从当前眼下到古往今来都包揽无余。虽然他曾经游历四方,居洛时也偶有远游之举,但晚年他深居简出,活动范围一般不出洛阳城,大部分时间是在安乐窝中读书、治易、闲行,而他之所以仍能有如此开阔的眼界和诗思,是基于由近而远、由我而物、见微知著的理学家的思考。他的《二十五日依韵和左藏吴传正寺丞见赠》诗从悟道的角度谈“心骛八极,神游万仞”的体验,曰:“上阳光景好看书,非象之中有坦途。良月引归芳草渡,快风飞过洞庭湖。不因赤水时时往,焉有黄芽日日娱?莫道天津便无事,也须闲处着功夫。”[1]253首联“上阳光景好看书,非象之中有坦途”,指冬至是悟道、观物的好时节。上阳,即一阳初起的冬至时节,此时万物欲生未生,犹如天地初始时的鸿蒙希夷状态,这是邵雍认为的最佳悟道时刻,即如其著名的《冬至》诗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1]489非象,是指似象非象、一片混沌的道的状态,同时也是就冬至而言。颔联“良月引归芳草渡,快风飞过洞庭湖”,是写神游天地的想象之词。颈联“不因赤水时时往,焉有黄芽日日娱”,谈的是体道、悟道之乐。赤水,古代传说中的水名,出于昆仑,此处当指天地的尽头。黄芽,本指炼丹鼎内的黄色芽状物,炼丹家认为是铅的“精华”,用作丹药的基础。因为黄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所以内丹书籍也常借用为静中有动的象征。同时它又与先天的混沌状态有关,《性命圭旨》曰:“以其为一身造化之始,故名先天;以其阴阳未分,故名一气,又名黄芽。”[9]利集148尾联“莫道天津便无事,也须闲处着功夫”,神游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洛阳天津桥畔的安乐窝。“闲处功夫”,是指写诗、体道、治易等一系列修身立德行为,邵雍又称为“隐几功夫”。
邵雍在诗中写神游四方的诗句还有不少,其意在阐明他的先天易学的特点,他认为先天易学最能够体现出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仿佛创世之初的混沌、太和,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邵雍喝酒追求微醺的状态,写诗追求灵感偶然迸发的瞬间,这些行为特点都与他的先天易学的治学体验一脉相承。二程评价道:“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机。”[7]42邵雍也说自己的诗歌泄露了天机:“每用风骚观物体,却因言语漏天机。”[1]517(《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十二)他写诗歌咏花月美景也是要将天机泄露出来,帮助人解决面对自然时的困惑,弥补好景不长久的缺憾,“把酒嘱花枝,花枝亦要知:花无十日盛,人有百年期。据此销魂处,宁思中酒时?若非诗断割,难解一生迷”[1]330(《嘱花吟》)。因此,他甚至认为用诗歌揭示自然万象的奥秘就是在代天言说,“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可爱时。已着意时仍着意,未加辞处与加辞。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无限说,尧夫非是爱吟诗”[1]529(《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十八)。所以,邵雍的诗中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欢乐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觉悟天机的通达理趣,“因通物性兴衰理,遂悟天心用舍权”[1]208(《贺人致政》),乃至冥会天心的融怡和乐,“才沃便从真宰辟,半醺仍约伏羲游”[1]328(《太和汤吟》)。
三、快乐与吟诗:圣贤事业的体现
邵雍总是自得于常人所拥有的一些最基本的生理属性、生活条件,而且乐不可支,如《喜乐吟》曰:“生身有五乐,居洛有五喜。人多轻习常,殊不以为事。吾才无所长,吾识无所纪。其心之泰然,奈何人了此?”其后自注曰:“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见太平,五乐闻道义,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1]335这背后的思想资源很容易追寻,来自春秋时期一个叫荣启期的隐士,刘向《说苑·杂言》曰:“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为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10]卷一七429这样说来,邵雍似乎仅仅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乐天派,不足为奇,然而实际上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条件太过基本,一般人很难从中发现快乐并发自内心地享受它,而这就需要圣贤的修养功夫了。他的诗歌不断地描写所享受的这些快乐,使得自己因而成为天下一等一的人物。如《自在吟》曰:“心不过一寸,两手何拘拘。身不过数尺,两足何区区。何人不饮酒?何人不读书?奈何天地间,自在独尧夫。”[1]356《多多吟》曰:“天下居常,害多于利,乱多于治,忧多于喜。奈何人生,不能免此。奈何予生,皆为外事。”[1]376所乐之事遍地都是,而能够随手取来以资快乐的,邵雍自信天下之大,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又如《偶得吟》曰:“人间事有难区处,人间事有难安堵。有一丈夫不知名,静中只见闲挥麈。”[1]364区处,即分别处置、处理;安堵,即安居而不受骚扰。这就解释了快乐的事情这么多,而人们普遍不快乐的原因在于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些难以处理和叫人不安的事情,但邵雍却总能自处于闲静无事的境地,其自身形象便一下子高大起来。邵雍以生而为人、为男子、为丈夫而快乐,但他却又自命为十分人、真男子、大丈夫,这便与圣贤无异了。其《责己吟》曰:“不为十分人,不责十分事。既为十分人,须责十分事。”[1]427又有《十分吟》对“十分人”做了解释,即具有“直须先了身”的“十分真”,以及“事父尽其心,事兄尽其意,事君尽其忠,事师尽其义”的“十分事”[1]475。“十分人”的标准非常高,连司马光这样的当世伟人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九分人”[11]卷一八201而已。“真男子”与“大丈夫”意思相当,出于《感事吟》中“能言未是真男子,善处方名大丈夫”[1]454二句,而这位“善处”的“大丈夫”指的就是他自己。而他认为“可谓一生男子事”的是“写字吟诗为润色,通经达道是镃基。经纶亦可为余事,性命方能尽所为”[1]525(《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五十四)。润色,就是润色鸿业、歌咏太平,“写字吟诗为润色”与邵雍在诗中一再塑造的太平闲人的自我形象是一致的。要写出真正润色鸿业的诗篇并不容易,这需要诗人本身从内到外散发出太平盛世中乐道安闲的气象,而“通经达道”不过是基础,“经纶”世务更不过是“余事”。这种论调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出自邵雍独特的圣贤观念。
诗在邵雍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可以悟道,可以言志,可以娱情,是成圣成贤的必要途径之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功能和类型上,邵雍并没有把自己日常所作的各种题材的诗歌与作为儒家诗教经典的《诗经》区分开来,甚至将自作之诗与诗三百、诗三千等同看待,这一方面可以看作他的圣贤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那种“不立固必”、古今无殊的对于“诗言志”本质的价值体认。哪怕有时候他会自谦地说“林下闲言语,何须更问为?自知无纪律,安得谓之诗”[1]364(《答人吟》)“林下闲言语,何须要许多?几乎三百首,足以备吟哦”[1]451(《答宁秀才求诗吟》),但也免不了将自作之诗和《诗经》比附一番。他有时会担心自己写诗的兴趣过于浓厚,构思过于轻易,所写诗歌数量过多,质量良莠不齐,但马上又戏谑地自我安慰道:“久欲罢吟诗,还惊意忽奇。坐中知物体,言外到天机。得句不胜易,成篇岂忍遗?安知千万载,后世无宣尼?”[1]463(《罢吟吟》)邵雍将自己的诗歌比作诗三百的始祖诗三千,和他称自己的易学越过文王、孔子的后天学而直承伏羲的先天学的态度是一样的,将吟诗与治易都看成前无古人的立德事业。在“三不朽”当中,立德是先于立功的,不过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宋代这样看重科举为官的时代里,士人多以建功立业、得高官显爵为贵,即便是追求立德的理学家也罕有轻视功名富贵的,而邵雍却认为治国平天下的经纶事业与“写字吟诗”“通经达道”的修身立德事业相比不过是“余事”。难怪二程对此批评道:“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言来,直是无端。”[7]45
余论
在程朱眼里邵雍是理学家中的异端,这不仅在于他重象数而轻义理的易学研究倾向,还在于他对吟诗的热情、对快乐的信奉以及通过诗歌对快乐的大量歌咏。除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二程评价他“直是无端”以外,他们还用“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7]45来评价邵雍那种似乎与理学家身份极不相称的快乐。朱熹也评价道:“看他诗篇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来厌了。”[12]卷一〇〇2553“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已劳攘了,至邵康节云‘真乐攻心不奈何’,乐得大段颠蹶。”[12]卷三一798将他的诗与乐和孔颜之乐明确区分开来。尽管从道的角度来说,程朱“未尝以圣学正门庭许他”[13]卷三29,但他们对他诗中的快乐及由此所展现出的坦荡胸襟和开阔境界却表示一定的赞赏,并称之为“人豪”。程颢评价邵雍诗句“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曰:“真风流人豪!”[7]413朱熹评价其诗句“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曰:“可谓人豪!”不仅如此,针对学生“近日学者有厌拘检、乐舒放,恶精详、喜简便者,皆欲慕邵尧夫之为人”的话,朱熹严厉地斥责道:“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后敢如此!”[12]卷一〇〇2542说明朱熹肯定了邵雍不拘一格的快乐是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的,在“道”上给他留有一席之地,不像二程那样简单地以“无端”二字将其一笔抹杀。此外,朱熹师生间的对话也透露出邵雍的快乐精神在朱熹的时代并不缺乏追随者。而后世的追随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从理趣相生的角度来评价邵诗之乐*早在南宋,陈知柔就认为杜甫、白居易诗中豪放通达之处“未若邵康节‘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尤有味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五第47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明末袁宏道说:“余尝读尧夫诗,语近趣遥,力敌斜川。”(《西京稿序》,见《袁宏道集笺校》下册第14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清代陈文述说:“余于宋人诗,最爱邵尧夫,盖其胸次旷达,矢口皆和雅之音,自然之极,纯乎天籁。……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鸢飞鱼跃气象。”(《书邵康节诗后》,陈文述《颐道堂集文钞》卷一〇,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06册,第49页。)所谓“味”“趣”“鸢飞鱼跃气象”皆与乐相关,亦与理尤其是儒学之理相关。,这就大大提升了邵雍诗中快乐的道德品格以及这种快乐对开拓诗歌意境的作用,并赋予其诗一定的诗史地位。伴随这些评价的是南宋魏了翁,元代吴澄,明代陈献章、庄昶、唐顺之等理学家一浪高过一浪的邵诗崇拜热潮,以致四库馆臣认为自宋至明存在着一个“击壤派”,这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