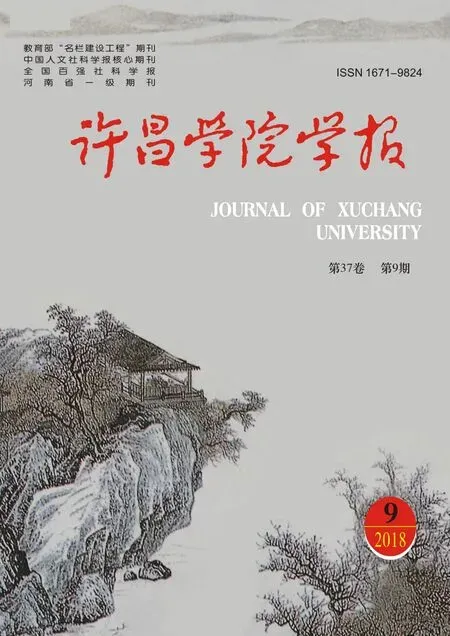刘颂的封建论与西晋武惠之际的政局
吴 南 泽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西晋武帝末年至惠帝初年,外戚、宗王等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政治日益动荡。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期中,刘颂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人物。据《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刘颂是西汉广陵厉王刘胥之后,年少时以“能辨物理”著称,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出任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又以“真平居正,兼明法理”迁廷尉*按《北堂书钞》卷五三《设官部·廷尉》“刘颂明法理条”载晋武帝诏云:“黄门郎刘颂,真平居正,兼明法理,可议郎守廷尉。”。后因故外任淮南相,至晋惠帝时回朝长期担任三公尚书*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汉成帝时始置尚书三公曹,主断狱,魏晋皆沿用此制。。刘颂掌管刑狱,“号为详平”,时人将其比作张释之,惠帝时所上论刑法的奏疏也为时论所称美。刘颂的学术思想背景,史书中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刘颂本人亦不事著述,《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其文集三卷。从仕进履历来看,他大抵应属于深明法理、以吏干知名的一类人物*《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云:“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李善注引王隐《晋书》载傅玄之言云:“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其家族世居广陵,主要可能是受到南方汉代旧学学风的影响,另外淮南、吴越一带的黄老思想传统在刘颂政论中也有所体现,这在西晋中叶崇尚放达、望白署空的士林风习中独树一帜。
刘颂出任淮南相后,“在官严整,甚有政绩”,尽管终武帝一朝再没有回到朝中任职,但他对朝政仍然十分关注,屡屡向武帝上疏陈为政之要。清人赵翼曾评价《晋书》各传所载表疏赋颂之类,与所叙传主事迹皆有关系,“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页。。这一观点是基于传统史书编写的体例,但《晋书》完整收录刘颂在武帝末至惠帝初先后所上数道论政奏疏,涉及制度、政治、刑法、文化等方方面面,时间上跨武帝、惠帝二朝,保存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为今人理解当时的政治剧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关于封建制度的议论,与西晋武惠之际的政局关系极为密切,本文拟以此切入分析,试图在前人较少注意的地方揭示一条理解当时政治的线索。
一、西晋前期的封建制度
西晋初年,封建宗室及诸王就国是政治上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可参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王安泰:《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本田済:《魏晋における封建論》,《人文研究》1995年第6期;渡邉義浩:《「封建」の復権―西晉における諸王の封建に向けて》,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0辑第4分册,2005年2月,后收入氏著:《西晉「儒教国家」と貴族制》,汲古書院2010年版。。曹魏时代对宗室的防制非常严格,所谓“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1]591。曹魏禁锢宗王,结果使帝室孤立无援,作为篡位者的司马氏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魏末就有大封宗室的举动。咸熙元年(264)司马昭为晋王时,命裴秀建立了一套相当严密的五等爵制,对诸国的大小、官属、军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参见《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及《太平御览》卷一九九《封建部》二。。但具体的实施似乎比较简略,所封诸侯仅具有爵位名号,并未实际就国,王国官制也没有建立,胡三省以为“魏王操置名号侯以赏军功,虚封自此始矣。今虽复五等爵,亦虚封也”[2]2486。咸熙元年的五等封建,主要是司马昭为保证禅代顺利进行以及为晋朝建立后的人事安排所作的布置,这种意图也体现在晋初的分封当中。
西晋初年大规模封建宗室共有三次,分别在泰始元年(265)、咸宁三年(277)及太康十年(289)。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元年大封宗室的具体情形如下:
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幹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珪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陵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3]52
按《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及卷二四《职官志》,泰始元年分封将诸王国、公侯邑依据户数多少,各定为大国、次国、小国三等*按制度而言,《晋书·地理志》载诸王国邑二万户以上为大国,邑万户以上为次国,公侯国邑万户以上为大国,邑五千户以上为为次国。但考诸王本传,泰始元年的分封中,除安平国四万户外,实际上并没有户数达到二万的王国。《晋书》卷三八《宣五王·平原王幹传》载,司马幹封平原王,食邑一万一千三百户,即称为“王大国”,而封为次国者,如燕国邑六千余户,梁国五千余户。因此笔者推测在泰始分封中,王国区分大小所执行的实际标准应当是大国万户、次国五千户。另据杨光辉先生研究,泰始初郡公户数最高仅三千,《地理志》所记制度不确。参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36页。。考察泰始所封诸王国的规模:司马孚咸熙分封中封为邑万户的安平郡公,泰始元年进为安平王,邑四万户;司马幹咸熙时封定陶伯,泰始时封平原王,邑万一千三百户;司马亮咸熙时封祁阳伯,泰始时封扶风王,邑万户;司马伷咸熙时封南皮伯,泰始时封东莞王,邑万六百户;司马骏咸熙时封东牟侯,泰始时封扶风王,邑万户;司马望咸熙时封顺阳侯,泰始时封义阳王,邑万户;司马肜咸熙时封开平子,泰始时封梁王,邑五千余户;司马晃咸熙时封西安男,泰始时封下邳王,邑五千余户;司马瑰咸熙时封固始子,泰始时封太原王,邑五千余户;司马珪咸熙时封浈阳子,泰始时封高阳王,邑五千余户。不难看出咸熙与泰始两次分封之中的规律,司马孚在宗室中辈分最高,兼有卓著的人望与才干,对魏晋禅代也有重要贡献[4]196-197,故位遇殊盛;其他宗室成员,大体上泰始分封的大国为咸熙时的侯伯,次国为咸熙时的子男,其余小国咸熙时可能未封爵位。有研究认为,在晋初的分封中,司马孚一支最盛,所封诸王中,不仅没有武帝司马炎的子孙,甚至连司马懿一支封王人数也不如司马孚一支[4]199。这一观点单从封王人数角度出发,倘若结合政治形势及封国大小等因素考虑,或许值得商榷。
司马昭在咸熙二年建立了天子衮冕、旌旗、车驾、百官等,距离禅代只有一步之遥。司马昭与只愿做周文王的曹操不同,这一系列举动并不是为司马炎的继任铺路,而是为自己当皇帝所作的准备。在咸熙分封之中,受封侯伯者有司马幹、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及司马望五人,除司马望外的四人均为司马懿之子,而且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三人均曾出督方镇,掌控镇守洛阳的重兵及战略要冲[5];司马孚一支仅司马望一人受封为侯,其余受封子男者,大多以酬庸的性质为主。可见,咸熙分封在进德酬功的表象之下,恰恰可能是为了区别亲疏,建立以至亲宗室拱卫帝室的封建体制,使之在新王朝的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柳春新先生认为,司马昭之所以颁授五等爵制,是基于禅代的形势,确定晋王主导下忠于晋廷的职官系列,咸熙五等制确定的功臣爵序,构成了晋初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参见:《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12~215页。。
但司马昭在咸熙二年八月暴病身亡,晋武帝的继位略显仓促,尚来不及对司马昭的人事布置作出调整,所以泰始分封的格局基本上以咸熙分封为基础。到咸宁三年时*晋武帝之所以在咸宁三年这个时间点上着手调整分封,可能与咸宁二年武帝病危时朝中有拥立齐王攸的密谋等政治风波有关。详参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晋武帝开始着手调整宗室的分封。《晋书》卷三《武帝纪》云:
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伷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3]68
咸宁分封的目的首先是移封就镇。咸熙、泰始之际广开封建的名义上是以封建王国的力量拱卫朝廷,但晋初诸王并未就国,朝廷利用宗室控制地方,主要还是依靠魏末以来都督出镇的方式。西晋咸宁时,朝议以为应遣诸王就国,落实封国藩屏帝室的作用。但出镇的宗王封地与都督区往往不同,所以当时人设计了“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的制度,即通过调整封地,使出镇宗王的封国与所督地区相协调,唐长孺先生称之为“综合古之方伯、连率和宗王出镇现状而制定的奇特制度”[5],日本学者越智重明也认为,西晋宗室诸王对封国的支配,是诸王结合都督、四征将军、刺史等官职的结果[6]。咸宁三年调整分封,主要是使原已出镇的几个大国的王通过移封就镇的方式,完成封国与方镇的匹配。
其次是调整封国规模,“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为小国”[3]744,这一新封建格局具有几个特点:汝南、琅邪、扶风三国为大国移封,故改为大国;平原、梁、赵、乐安、燕五国为司马懿子孙,故仍维持原本规模;齐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原规模不详,但从齐王攸在咸熙时获封安昌侯推断,泰始初齐国应为大国,而且咸宁三年,武帝又“以济南郡益齐国”[3]1134,齐国规模的扩大,超出一般诸侯国的制度范围,这或许与武帝对待齐王攸外尊内忌的心态有关;晋初所封“特大国”安平、大国义阳,随着司马孚、司马望父子在泰始年间相继去世,其房支在宗室内部影响力大不如前,均被降为次国,其他宗族成员的封国则一律降为小国。
再次是调整王国的制度体系。根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咸宁三年调整封国,规定“非皇子不得为王”,以及诸王支庶“各以土推恩受封”。同时设立分土罢军及中尉领兵制度,王国按照大、次、小,分别置三军至一军不等,均由朝廷派遣的中尉领兵,大国从始封王之孙袭爵开始罢下军,曾孙袭爵又罢上军,次国亦从始封王之孙袭爵开始罢下军,使各国“皆以一军为常”。按照这样的制度设计,每一世皇帝皆有皇子封王,宗王则会不断转变为疏亲,王国的力量随着世代的传承逐渐削弱,诸王的子孙除继承王位的嗣子外,皆无法获封王爵,有利于封建王国的实力始终向帝室一系集中,进而长久地稳固王朝统治。
咸宁分封延续了咸熙、泰始分封区别宗室亲疏的做法,使帝系一支至亲宗室的地位凌驾于其他房支之上。太康十年的分封进一步巩固了此种帝系本位的封建原则,据《晋书》卷三《武帝纪》记载:
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为西阳公。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3]79
此次分封主要涉及晋武帝诸子,一方面沿用咸宁分封中“移封就镇”的方法,分别改封三名皇子司马柬为秦王督关中、司马玮为楚王督荆州、司马允为淮南王督扬州,“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3]81,另一方面新立数名皇子及皇嫡孙为宗王。此次分封,贯彻了咸宁时确立的“非皇子不得封王”原则*太康十年分封中,始封为王的仅有武帝诸子及惠帝长子。按“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一语中的“立”,实际上是改封的意思。司马迪为司马允之子,咸宁时继嗣早夭的始平王裕,太康十年改封为汉王;司马仪(“仪”《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作“义”,疑误)则为司马玮之子,太康分封中继嗣早夭的毗陵王轨,二人均非始封王。。晋武帝在太康十年这个时间点上封建诸子并非偶然,武帝登基时,皇子寡少幼弱,并不能与其他宗室成员抗衡,也无法承担出镇地方职责。武帝暮年,惠帝愚鲁不慧的特质逐渐显露,武帝需要分封更多皇子,充实帝系的实力。出生于咸宁年间的皇子司马乂、司马颖、司马晏等当时年龄大约在十岁左右,已可以受封为王,而且按照宗王假节之国的成例,他们在年纪更长之后也应当领兵出督方镇,成为拱卫帝室的力量,保障政权顺利地过渡到嗣君惠帝的手中*日本学者安田二郎曾研究武帝泰始九年“采女”的实质,认为武帝有所谓“天纵至孝”之性,遭遇司马昭及王太后丧各“深衣疏食”三年,此种禁欲生活导致皇子出生的空白。而武帝早已认识到惠帝之不慧及诸皇子之寡弱(无论数量或是年龄),出于增加至亲宗室人口的目的实行采女策,欲为嗣君司马衷建立宗子维城的稳固体制。参见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版,第67~76页。太康十年获封的武帝诸子,都是在采女策实施之后出生,可以印证安田氏的观点。。
二、“任势而不任人”的封建论
晋武帝通过咸宁、太康间的分封调整,似乎建立起了一套“本支别干,蕃屏皇家”的稳固封建体系。但时任淮南相刘颂对此提出了担忧,《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记载他在淮南郡时上疏武帝: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藩。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3]1294-1295
西晋泰始、咸宁、太康三次大封宗室,封建王国的规模超越了秦汉及曹魏,但就制度本身而言还称不上完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吴、蜀两地的封王。西晋统一天下之后,对吴蜀故地的治理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太康中,广陵人华谭曾进言晋武帝:“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3]1450吴、蜀名义上虽已臣服,但两地的政治传统及文化风俗与中原迥异,特别是孙吴政权长期割据江东,形成了一套从皇帝到百官的完整政治体系以及独特的政治文化,太康时吴国归降未久,可谓“易生风尘”之地。晋武帝对吴国故地的治理基本采取了因循放任的方式,“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3]71。
但对吴政策中存在一处巨大隐患,即“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此“东南六州”,周一良先生曾认为是《晋书·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但周先生也曾指出,“论东晋南朝之地理形势,不能置益州不顾”*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周一良:《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考察羊祜针对伐吴所作的战略设想,“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3]1018,再结合《武帝纪》所记载伐吴的六路大军,“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西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3]70,可知在晋人伐吴的实际部署中,梁、益二州确实极为关键。益州是江南地区的门户及根本保障,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王濬顺江而下、兵不血刃的楼船部队,就发自益州。相比之下,青兖二州距前线较远,并不是主要的交战区。所以刘颂所说的“东南六州”,应当是伐吴之战前线,亦即长江流域益、梁、荆、豫、徐、扬六州。平吴之后,西晋仍以前线将士戍守江南,即所谓“内兵外守”,在清静放任的方针之下又隐含着对三吴地区的防范。这有可能引发吴人的猜忌,反而成为引发动乱的因素。蜀地的情况刘颂并未详细说明,但应也存在与吴地类似的情况。
太康十年分封诸皇子时,吴王晏八岁,成都王颖十岁,年纪幼小的皇子并不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政务只能掌握于朝廷委派的内史*按《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十年分封时,晋武帝改诸王国相为内史。手中,这样一来等于将吴地视同一般郡县,政事取决于朝廷,脱离了原本的政治文化及秩序,容易造成当地人的不满,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刘颂建议,吴蜀两地封王,“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使当地政治、选举、兵役诸事“内外各安其旧”。对吴、蜀而言,除了国君变为晋朝的宗王以及名义上成为晋朝的附庸外,不改变其任何原有的政治传统与制度,贯彻因循简易的原则以安抚当地,而不应加以过多的干预,使朝廷与新附之国上下相安。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治理方式,实际上既要顺应风俗人情,又要遵从朝廷王法,对封君抚御下情的政治能力及经验要求很高,非年长宗王不能胜任。
吴蜀两地的封王及治理,反映出西晋封建制度的总体缺陷。在咸宁分封中,朝廷确立了王公就国的制度,但当时“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3]745。其中原因,刘颂说“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在西晋封建制度下,王公没有治权,“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晋武帝在践阼之初,曾经授予诸王自选国内长吏官属的权力,《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称“其仕在天朝者,与之国同,皆自选其文武官”*按《晋书·职官志》此段所记,实际上是东晋渡江之后,依据“泰始初故事”重建王国制度,所以此段记载正可以印证西晋初的封建政策。,卷三八《琅邪王伷传》《梁王肜传》《齐王攸传》等传皆记载了此事*诸王之中,齐王攸反对此事的态度最为鲜明。在当时立储之争的背景下,齐王攸仍然有留在京师的强烈意愿,一旦封建制度完善,诸王就国,齐王攸亦势必离开政治中心,失去继承帝位的所有可能。所以齐王攸身为宗王,却有反对封建制度的倾向。据《晋书》本传记载,齐王攸不仅反对诸王自选长吏,认为“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而且太康中受诏就国时也尝有“吾无匡时之用”之叹,都与其政治处境相关。。当时确实有一些宗王自行任免了王国官吏,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一政策并未长期落实,大部分王国的国相等长吏还是由朝廷任命,王国的实际治理也由国相负责。如《晋书》卷五二《阮种传》云,阮种迁平原相,“为政简惠,百姓称之”,晋武帝亦称赞“二千石皆若此,朕何忧乎”。平原国政务全出自国相,与平原王幹基本无关。可见当时诸王国虽有封建之名,本质上仍是郡县的体制。
刘颂对比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制度,提出“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郡县制下,守相令长由朝廷派遣,代表人君意旨治理地方,庶政事无小大皆依从于朝廷,所以是“任人”之制,其所施政令容易与地方实际情况相抵牾,故“小政理而大势危”。封建诸侯则不同,所封宗王即为一国之君,能依据实际情况“从俗而治”,即便地方风俗与王法相违,但因为顺应民情,百姓安乐,不会招致怨愤,是“近多违而远虑固”的“任势”之制。
从历代政治得失的角度,封建制也明显优于郡县制。三代均“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为帝室之藩屏,所以国祚可达数百年之久。秦朝罢侯置守,帝室孤立无辅,所以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实行郡国并行之制,汉朝的盛衰也与诸侯国的强弱相关,汉初诸侯国力强盛,所以朝廷能依靠藩国平息诸吕及七国之乱。景武之后削藩推恩,诸侯仅食租俸,藩国有名无实,而王莽得以篡夺汉鼎。东汉光武帝虽广封子弟,但诸侯国本质与郡县无异,国祚也不长久。至于曹魏,更是禁锢宗室,使“神器速倾”,天命为司马氏所取。所以刘颂谏言武帝,当天下统一、海内太平之际,广开土宇,完善封建邦国的体制,建立晋朝长久统治的基础。
按照立嗣以嫡以长而不以贤的原则,圣主贤君必不世出,所以国家的治乱安危与辅臣有十分直接的关系。刘颂提出“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所谓“任臣”的“任”应源自黄老之学“因任”的思想。刘颂认为理想的政治形态应当是“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与黄老学派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君主处至尊之位,以威柄权术任使群臣,所以尽忠公、守本任者称为“任臣”;反之,为臣而操弄权柄,使臣重于君,如《管子·明法解》所谓“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必有“劫杀之患”“乱亡之祸”,所以韩非也说“万乘之患大臣太重”[7]84。刘颂所说的任臣与重臣均指执掌国柄的大臣,二者治乱成败截然相反,原因在于任臣尽公、重臣树私。但是人臣非皆忠贤,倘若没有稳固可靠的机制维系君臣之分,在国势危殆的时候,任臣也会有转化为重臣的可能。这种机制就是完善的封建制度,刘颂称“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所谓建邦之“理”,即“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周代封建公侯,享国可长达数百年之久,封国世代相传,诸侯视封国为己家,故能君民同心,藩国根基深厚,在下能使地方政通人和,在上则能为王室的辅翼。封建诸侯、广树藩屏,帝室一旦有难,诸侯率兵勤王。国基稳固,重臣没有篡逆的可乘之机,也不自怀猜疑之心,故能竭忠诚而变为任臣,这样“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所以“无向不可”。西周自宣王以下,至于东周赧王,上无贤君,下无名臣,但“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即是明证。
那么,怎样的封建制度才算完善呢?刘颂举周汉二代制度加以分析,指出周代封建特点是“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大国方圆虽不过百里,但是“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即便国君受诛,也必有嗣君继位,所以“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周王室因而得以长存。汉代则不然,君侯失道受戮,封国随之消灭,又或封君无子,也要除国。刘颂认为汉制之弊是“不崇兴灭继绝之序”,导致封建体系不稳固,天子孤立无援。
刘颂以周汉两代的制度为鉴,指出西晋的封建存在两方面缺陷:其一是“亲疏倒施”,西晋三次大封宗室,泰始分封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所封主要是疏亲宗室,后来在咸宁、太康分封中,晋武帝开始着重分封以诸皇子为主的至亲宗室。但对于疏亲,武帝则采取了转封、削藩、推恩等手段,逐步削弱其封国的实力。刘颂认为,亲疏固然不能无别,但是“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西晋武帝时期,尚未有封君因罪受戮而除其国者,但疏亲宗室无子除国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例如《晋书》卷六四《武十五王传》记载,新都王该咸宁三年始封,太康四年薨,时年十二,无子国除;汝阴王谟,太康七年薨,年十一,无后国除。刘颂建议武帝以封地远近的方式来区别亲疏,无论国君受诛还是无子,只要有始封君的后裔,不计亲疏远近,皆可取为后嗣;如果确实后继无人,则虚封其国,待皇子生即可出继其统胤,“兴灭继绝”,使“下无亡国”。其二是诸侯国力寡弱,晋世封国,大者虽千里之广,但“国容”多而“军容”少,不具备藩卫帝室的能力。西晋王国大多有完整的文官系统,据研究,西晋大国国官最多约五十余人,加上属吏可达数百人[8]。相比之下,王国军制则十分不完善,如《晋书·职官志》记载:“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西晋诸王就国并非常制,如荀勖所言,“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3]1154,即便后来通过移封就镇的方式调整封地,诸王就国时所部兵力也主要是都督所统辖的军队。多数王国可能只配置少量“守土”的兵士,并没有真正置军。王国虽地广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刘颂建议,完善封建制度的当务之急是扩充王国军力,发展农垦,以使仓廪充实、百姓富足、兵力强盛,其次才是营建宗庙社稷、服章宫室及礼乐制度等。在王国政事方面,应当给予诸侯王充分自主的行政权力。除内史、国相由朝廷任命外,其余生杀断狱、兵刑钱谷诸事,均应决于国君。这样,封建制度得以完善,诸侯国势力强大、根深蒂固,成为朝廷稳定的基础,“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综合来看,刘颂主张封建制优于郡县制,主要从两方面立论。从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诸侯作为封国的君主,应对土地及人民直接负责,并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法令,租税赋役也均在藩国境内进行,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避免在郡县制“法令出一”的原则下,区域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及冲突。更重要的是,从天下安定的角度来看,封建制也优于郡县制。在当时人眼中,周代及汉初封建藩国拱卫朝廷的体制是维系王朝稳定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案。单方面削弱诸侯国的自治权及兵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制诸侯叛乱,巩固统一的局面,但这就有可能走上汉魏禁锢宗室的老路,甚至可能重蹈秦制的覆辙。一旦诸王国“法同郡县”,当地人便应向西晋朝廷输租服役,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吴蜀等地,长距离的力役必然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这也是吴蜀被称为“易生风尘之地”的原因之一。在封建制下,“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动乱的潜在风险,维系天下的长治久安。
早在泰始初年,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西晋封建制度的缺陷。当时段灼数度上疏晋武帝,认为魏末司马昭所建五等爵制,“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揉,例受茅士。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他主张除太宰安平王孚、司徒义阳王望、卫将军齐王攸三王应镇守京洛,“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而且封建子弟,势必使诸侯国地广兵强,“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3]1349。显然,这与刘颂的封建论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当时段灼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晋武帝的重视,其关于封建制的主张也未付诸实施。那么,时隔二十余年,刘颂为何再度提出相似的封建论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武惠之际的政治形势
西晋太康年间,政坛上最为显著的一项变化是以杨骏为首的杨氏家族的崛起。杨骏是晋武帝第一任皇后武元杨皇后的叔父,第二任皇后武悼杨皇后的父亲。他与二弟杨珧、杨济以外戚身份进入西晋的政治中心,是在咸宁二年十月悼皇后册立之后。当时晋武帝逐渐疏远贾充等勋旧,着意扶植杨氏的势力*据《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武元杨皇后传》,泰始十年元皇后临终之前,“虑太子不安”,请求武帝立叔父杨骏之女为后。学者指出,悼皇后的册立及杨骏兄弟在政治上的崛起,与元皇后的遗言关系不大,而是与咸宁二年的政治风波相关。当时晋武帝身患重病,朝廷中一度出现拥立齐王攸的密谋。在这场风波中,贾充处境颇为微妙,他的两名女儿分别嫁给了惠帝及齐王攸,但他在立储问题上态度模糊,没有表现出对惠帝的全力支持。这也使病愈之后的武帝失去了对贾充的信任,转而扶植外戚杨氏。参见权家玉:《西晋杨骏一族的崛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杨氏兄弟凭借武帝的宠任迅速升迁,所谓“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2]2576。至太康年间,晋初的元勋重臣如贾充、山涛、荀勖、冯紞、王濬等以及重要的宗室成员扶风王骏、琅邪王伷、齐王攸等相继去世,加上张华废黜、卫瓘逊位,太康末年政治中枢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力真空,这为杨氏一族的崛起与专权提供了外部条件。
当时虽有“三杨”之称,但杨珧、杨济二人性格谦退,对家族的贵盛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杨珧“以兄贵盛,知权宠不可居,自乞逊位”;杨济则曾力阻杨骏排挤汝南王亮的阴谋,曾言“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不尔,行当赤族”,试图寻求外戚与宗室之间的势力平衡*见《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珧传》及《杨济传》。。二人均能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也因此被杨骏疏远。杨骏为人嚣张跋扈、专任亲私,当时人视其为“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病危临终之际,杨骏凭借着“亲侍左右”的身份,利用阴谋达到了专权的目的。《晋书》卷四〇《杨骏传》:
及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小闻,见所用者非,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曰:“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喆,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诏成,后对廙、劭以呈帝,帝亲视而无言。自是二日而崩,骏遂当寄托之重,居太极殿。[3]1177-1178
武帝晚年,晋初的佐命元勋多已辞世,亦未指定顾命大臣,朝中并无足以威服百僚的重臣,是以“朝臣惶惑,计无所从”。杨骏亲侍武帝左右,擅自改易朝廷公卿的任免,多树置其心腹私党。武帝病重清醒的间隙了解实情,意识到外戚的势力急剧膨胀,近乎不受控制,所以有意召还已出督豫州的汝南王亮与杨骏共同辅政,希望借助宗室的力量抑制外戚专权。但这已起不到多少作用,杨骏及悼皇后趁武帝弥留之际,擅定遗诏,命杨骏依伊吕周霍故事独自辅政,排挤汝南王亮。当时武帝已口不能言,只能被动接受这一事实。
按杨骏所定遗诏,他在晋武帝临终之前所带的一系列职官应当为侍中、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领前将军。其中侍中掌“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3]733,由于位在近侍,所以杨骏得以利用侍中的身份接近武帝。太子太傅一职辅佐太子,东汉旧例,每少帝立,皆有公卿权重者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同古代冢宰总己之义[9]。武帝崩后,惠帝继位,杨骏因此“正位上台,拟迹阿衡”,进位太傅、录朝政,“百官总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皇的辅政大臣,独揽朝政大权。
众所周知,晋武帝之所以登上帝位,主要是继承了父祖的基业。如刘颂上疏所说:“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构成西晋前期政治主体的功臣、宗室、魏氏旧臣等大多是父祖旧人,晋武帝将外戚势力引入政局,最初是为了制衡元老重臣,建立自身的政治班底,他对待杨氏兄弟也显示出了格外的优遇及宠任。但杨骏权势日盛,使“公室怨望,天下愤然”,或许超出了武帝所料。在太康末,晋初元老相继去世,宗室逐渐成为了与外戚抗衡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时人的言论中有所反映。如孙楚曾谏言杨骏:“今宗室亲重,藩王方壮,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傅咸也曾说:“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分别见于《晋书》卷四〇《杨骏传》及同卷附《杨济传》。
太康十年,晋武帝曾一度患病,《武帝纪》关于此次疾病的始末及程度语焉不详,只在当年十一月时有一条“帝疾瘳,赐王公以下帛有差”的记录。《武帝纪》整个太康十年的纪事中,正月至三月及七月至九月完全空白,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一现象与武帝患病相关,但可以推断当时武帝的健康状况应已大不如前。前文提到,晋武帝从咸宁三年开始,已经着力推行区别亲疏、以帝室为本位的封建政策。太康十年,武帝可能正是预计自己不久于人世,也意识到外戚势力的威胁,希望借助宗室的力量巩固帝室,所以病愈之后,武帝立即加快了分封皇子的进程。根据《通鉴》系年,刘颂的上疏也就在太康十年十一月武帝病愈之时。
所谓“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刘颂上疏晋武帝,提出完善封建制度的主张,正是基于当时外戚专权的状况。他强调以封建诸侯为依凭,与异姓大臣形成“相持之势”,无论储君贤愚,都能保障政治机器的政治运转。可见刘颂提出封建论的目的,是为了在武帝去世之后,愚鲁的惠帝有可靠的制度以保障政权的顺利过渡及延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支配结构归纳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基于合理规则的制度,基于传统的权威,基于对个人魅力(charisma,又译作卡里斯玛)的信仰。真实历史中的支配形态,乃是这些纯粹类型的混合或变形。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韦伯所谓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在政权建立之初或许能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一旦政权的奠基人去世,其实无法保证继承人也有同等的权威或者管理国家的政治能力。这一观点对于理解西晋政治颇有启发,刘颂正是鉴于武帝临终、政治权威可能面临消失的情形,提出引入某种“合理制度”,以保证统治的继续。。那么,刘颂关于封建论的构想收效如何呢?据本传记载,他的奏疏上达晋武帝之后,武帝诏答:“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而《通鉴》的说法则是“帝皆不能用”。刘颂关于封建制的主张十分理想化,难于具体实施,制度的调整及完善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病重之际的晋武帝即使有巩固宗室力量的考虑,也没有可能将刘颂提出的理想制度付诸现实。
刘颂上疏之后不到半年,晋武帝去世,惠帝继位,杨骏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不久之后,贾氏一族作为新的外戚崛起,贾后联合楚王玮诛杀杨骏。随后汝南王亮回朝辅政,并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王繇为尚书仆射、兼典军大将军、领右卫将军。这一结果表面上看,是宗室诸王排除了专权的外戚,全面接管军政大权,但其实丝毫没有起到拱卫帝室、稳定政局的作用,其手段也不比杨骏高明。
杨骏辅政时,自知“素无美望”,意欲结纳人心,“遂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当时孙楚、石崇、羊亮等士人先后提出劝谏,但杨骏皆不能用。杨骏受诛之后,最初由东安王繇“专断刑赏,威震内外”,史载其一日之间,诛赏达到三百余人[3]1123。不久东安王繇因为与汝南王亮的矛盾遭到排挤废黜,而汝南王亮为了“取悦众心”,同样滥行封赏,所谓“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3]1326,因诛杨骏之功获赏者多达一千八百余人,甚至远超过东安王繇主政之时。
汝南王亮虽然分派宗室成员占据军政要冲,宗室内部充斥着诸王的争权矛盾及相互倾轧。汝南王亮忌惮楚王玮的功勋及威望,先是命裴楷代任北军中侯,欲夺取楚王玮的禁军兵权,随后又与卫瓘密谋以遣诸王就国的名义,将楚王玮排除出朝廷,但反而被楚王玮联合贾后及外戚贾模、贾谧、郭彰等所杀,由此揭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余论:刘颂封建论的思想史意义
西晋的历史发展,总体上是皇权、功臣、外戚、宗室等几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斗争及此消彼长的历程。刘颂的封建论提出时,政治正处于皇权及功臣力量衰落、外戚权势接近顶峰,而宗室正在崛起的趋势之中。武帝死后,杨骏旋即受诛,宗室诸王全面掌控朝廷军政大权。但政局从此进入了长期的动乱,刘颂后来也卷入了诛杀楚王玮的政治密谋之中。可以说,刘颂的封建论在西晋政坛中基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其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不应忽视。
秦汉以来,主张封建制和主张郡县制是两大对立的思想潮流。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一制度由李斯主导,但当时仍有许多人倾向于沿用封建诸侯治理东方的宗周成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王绾等建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反对,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认为诸侯之间相互战伐而不为天子所制是东周祸乱的根源,于是始皇遵从李斯之议,推行郡县制以治理天下。至始皇三十六年时,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李斯认为在封建制度下,诸侯皆蓄私学,各树法令,与秦朝统一法制的原则相悖,不仅再度表示反对恢复封建制,而且提出焚书之议。
秦始皇虽然以郡县制统一天下,但这种天下如一的制度主要由以李斯为代表的秦法家倡导,当时关东地区的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认同周代封建诸侯的制度。如吕思勉先生所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10]55-56刘邦建立汉朝后,也曾有在东方推行郡县制的设想,但汉初君臣吸收亡秦强行统一文化与制度的历史教训,能容忍区域文化的差异,以郡国并行的方式,针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郡国并行的本质就是东西异制,这一制度避免汉朝重蹈亡秦覆辙,巩固了汉帝国的统治[11]66-107。
经历了两汉及曹魏四百余年的历史演进,郡县制成为主流的政治制度,但时人对郡县与封建各自的利弊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汉魏二朝防制宗室,导致朝廷孤立无援,无力应对权臣的篡逆。魏齐王芳正始年间,曹冏作《六代论》,历数夏、殷、周、秦、汉、魏六代政治得失,提出“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近则有宗盟藩卫之固,远则有仁贤辅弼之助;盛则有与共其治,衰则有与守其土;安则有与享其福,危则有与同其祸。夫然,故能有其国家,保其社稷,历纪长久,本枝百世也”,认为曹魏以前的五代,治乱安危、国祚短长,无不与当代封建诸侯的情形有关。诸侯强大,封建之势根深蒂固,则国祚长久,反之诸侯微弱,朝廷无以制乱,则国基易倾。曹冏直言,魏氏虽受汉禅,但并未吸取秦汉败亡的教训,而且变本加厉地禁锢宗室,“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1]592-594。当时曹爽与司马懿辅政,曹冏欲以此论使曹爽感悟,倚靠封建宗室的力量防卫司马氏,但曹爽未予理会,终致败亡。但这也反映出,汉魏宗室力量衰微,使当时人意识到治理天下不能完全离开封建诸侯的体制。
西晋的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汉代郡国并行制的特点,武帝设计的推恩制度及转封宗室的举措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模仿汉制而来。推考刘颂对封建制度的论述,他主张“反汉之弊,修周旧迹”,体现的是比秦汉制度更为古老的政治传统。诚然,刘颂对周制的描述,不免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他注意到西晋封建体系中带有的汉制旧弊,因而劝说晋武帝广封诸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赋予诸王充分的自主权,使诸王成为封国的实际统治者,改变西晋封建名为诸侯、实为郡县的现状,凭借宗子维城的体制维系王朝统治的稳定。
西汉贾谊曾说“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封建诸侯的势力过于强大并不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汉代封建诸侯的同时,又力图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即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2]2237。秦汉之际反对封建制或主张削藩的思想,主要是有鉴于周末“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12]364的历史,与法家强调法令出一的政治理念存在或隐或显的联系。诚然,诸侯国自主权的扩大,会在某些方面及一定程度上分散专制皇权,但如所谓“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3]1339,魏晋之际主张恢复封建制的思想潮流,其实是倾向于皇权政治,以保障王朝统治的稳固为最终目的*渡邉義浩认为,东汉末年“儒教国家”崩溃,社会上出现大幅认可诸侯军权及治权的思想主张,主要是为了对抗汉末异姓诸侯权力过大的问题,总体上倾向于国家的集权。参见氏著:《「封建」の復権―西晉における諸王の封建に向けて》。王安泰也提出,西晋五等爵制是以确保皇室权力为目的,参见氏著:《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第28页。西欧类似的历史现象也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如苏珊·雷诺兹所论,西欧12世纪以后出现的以封君、封臣关系为代表的那种封建主义,并不是王权微弱、无政府状态的结果,相反它是国家机构加强、法律制度发展的产物。参见Susan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 Oxford: Clarendon, 1996, p.33.。
刘颂提出,封建诸侯体系的完善,是现实政治运作的保障。天下事物纷繁复杂,以君主一人之力必然无法周览,所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所谓“事势致之”,刘颂曾提出,封建制是“任势”而非“任人”或“任智”之制,一方面体现在地方政治的因地制宜,另一方面则是朝廷对诸侯的因势利导。朝廷以封建诸侯为基础,设官分职、完善考课之制,君主不须事事躬亲,而是以因循无为、垂拱任下的方式治国理政,即可以简驭繁,使政事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运作。这种政治主张也体现在当时其他一些封建论中,如段灼以为,封建诸侯形成使“天下服其强”的“磐石之宗”,皇帝即只须“弹琴咏诗,垂拱而已”[3]1339;陆机《五等论》也说“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3]1476。刘颂、陆机等士人具有深厚的黄老学术思想背景,他们提出这些重视封建制度的政治主张,也十分接近黄老学说中“因循”的思想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张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思想倾向,代表了法家与黄老两种政治哲学。魏晋之际封建论的流行,与当时出现的黄老思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王晓毅先生指出,汉建安至魏景初,汉代经学衰落,“名法”的思潮居于曹魏政治的主导地位,该思潮放弃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将儒家伦理与刑名法术全部视为治国的权术,崇尚因势利导的“因循”原则,应当视为“黄老”复兴[13]。黄老之学在汉初作为经国治世之方曾兴盛一时,后因儒术之独尊而失去其显学的地位,作为政术的黄老之学似乎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黄老的影响实际上极为深远,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黄老的“思想遗产”几乎无所不在,其崇尚因循任势、重视君臣秩序的政治哲学和思想方法,往往在当时人的政论中有所体现[14]。刘颂的封建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在现实政治的层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它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汉魏时期天下大乱,定于一尊的传统经学以及儒教之治走向崩溃之后,黄老之学在思想领域呈现复兴的态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在黄老之学中寻求思想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