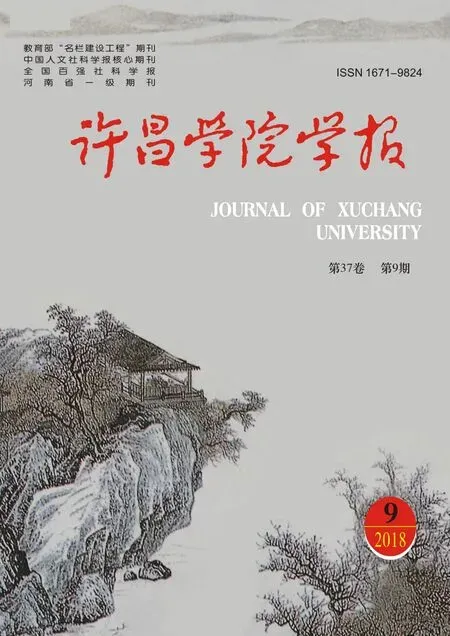清代常州文人吕星垣简论
刘 晓 娜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诗曰:“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1]盛赞常州地区文化兴盛。如其所言,清代常州地区确实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常州画派等文化群体均享誉于全国。乾隆、嘉庆年间,以“毗陵七子”为代表的常州文人,在当时文坛更是名扬一时。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云:“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唐。”[2]极力推崇洪亮吉、孙星衍、杨伦、黄景仁等人的诗歌。但同作为“毗陵七子”的赵怀玉、徐书受、吕星垣虽然著作颇丰,名噪一时,后世却声名不彰。
吕星垣(1753—1821),字映微、叔讷,号湘皋,常州武进人,廪贡生,由镇江府丹阳县训导仕至直隶河间知县。吕星垣工诗文,擅书画,又喜唱戏观曲。其所留著作颇丰,有《白云草堂文钞》(以下简称《文钞》)七卷,《白云草堂诗钞》(以下简称《诗钞》)三卷,杂剧《康衢新乐府》十出,小说《后红楼梦》三十回存世。如此才学却被埋没,不免令人惋惜。今笔者不揣浅陋,就吕星垣生平家世及文学创作成就略做申说,就教于学界同道。
一
武进吕氏是当地望族,名人辈出。吕星垣五世祖吕宫是顺治四年状元,由翰林秘书院修撰仕至大学士。吕宫通经济之学,在朝为官策对得体,竭忠尽瘁,关心民瘼,享誉于朝野。他虽然位极人臣,颇受顺治皇帝倚赖,但始终能够洁清自矢,不滥用权力。他屡充考官、读卷官,门生甚众,江南考官数十年皆为其门生故旧。为避免徇私,六子不试于其门生,均以诸生老,可见其家风之清白正直。吕星垣曾祖吕均和祖父吕灏亦无功名,但吕氏一门家境殷实,慷慨好施,至祖父一代始有中落。父亲吕扬廷智勇兼备,慷慨好施,待人真诚,有治剧应变之才。父辈影响所及,吕星垣亦性情纯笃,气骨清峻,有孝友之内行、济事之外才。
母亲钱氏一脉,亦是常州当时的名门。段庄钱氏,从明代东林党领袖钱一本开始,历经七代,家族中都有人科举高中,走入仕途,创造了钱氏一族的辉煌。吕星垣大舅钱维城在乾隆十年高中状元,更让这个家族的荣誉迈向了顶峰。除了科举功名之盛,钱氏的文教家风亦值得称道。吕星垣幼年曾随外曾祖父学习,闲暇时替外曾祖父抄写《东林纪事》,作家书、答问四方,外曾祖父谓其母曰:“此儿吾家宅相也。”[3]外曾祖钱济世,即钱一本的后代。东林党人忠正憨直的性格,就这样通过家庭教育影响了吕星垣。吕星垣外祖钱人麟熟悉前代掌故及一郡文献,扶持地方文教,著述颇丰。钱维城与其三弟钱维乔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对吕星垣诗文、戏曲、书画造诣等方面影响很大。此外,吕星垣同辈中,钱孟钿、钱伯坰、钱履坦,皆为常州当时有名的才女、文人,吕星垣自幼与他们往来唱和,在感情交流的同时,无形中也接受了钱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钱氏一族的文化血脉,在吕星垣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受良好的家教熏陶,吕星垣自幼便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以诗歌闻名乡里。同里洪亮吉、孙星衍、杨伦既是其少时的玩伴,亦是其诗酒唱和的师友。他们秉持着常州文人共有的文化自信,各负兀傲之志,以为他日当有所建树。然而吕家、钱家相继没落,重振家声、光耀门楣成了吕星垣不可推卸的使命。多次应举赴试,却屡荐不售的现实阻挡了他科举仕进之路。乾隆四十八年,吕星垣以贡生入国子监读书,四年期间,结交了曹仁虎、程晋芳、王太岳等名士,文采备受肯定,名声益显。他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并获佳卷,却因才高被考官怀疑而不被录用。所学虽富,却始终没有获得功名。
为生活所迫,吕星垣曾靠文才生活。京中国子监读书四载,多以鬻文求生。青年时期,先后游幕于浙江学政彭元瑞、大理寺卿王昶幕。足迹所及,多有诗文相证,如《彰德府昼锦书院劝捐文》《游天平山记》《步虚坛听松记》《涉县重修文昌宫碑记》,既将眼见之景留于笔墨之间,又足证其在游幕期间对地方文教的重视。吕星垣用世之才也在这时得以初步展现。乾隆四十六年,黄河仪征青龙冈决堤,阿桂奉旨治河,正值大雨,土方崩溃,当局咨访善策。当时吕星垣正在河南,任彰德府昼锦书院讲席,他建议以滚塘法治汛。阿桂采用其法,收效卓著,乃赞其曰:“君非梁园赋客,乃马周、张齐贤一辈人物。”[3]
国子监肄业后,内廷诸公皆劝其留京,吕星垣以侍奉孤亲为由辞谢,后辗转于江南各地从事教学。客浙江盐运使卢崧幕时,吕星垣兼任崇文、紫阳书院讲席,校阅课文之外,则与同道讲究盐法,尽陈鹾政利弊,用世之才益得彰显。任紫阳书院监院期间,吕星垣与山长钱大昕,共有“经师人师之目”[3]。吕星垣亦时以所作请教于这位学术大家,可见其为学之谦恭。当权以其才盛,欲与保荐,吕星垣以孤亲年老力辞。至此,吕星垣两次因侍奉孤母,放弃仕进机会。在执教期间,他还创作《后红楼梦》供老母消遣时光,孝心可表。母亲钱氏弃世之后,吕星垣又先后任青浦训导、海州学正,关注地方文教,培植士林,获誉一方。
吕星垣晚年因查丈境内沿海淤地有功,被优先升用,掣签得直隶真定府赞皇知县,后历充邯郸、河间知县,最终卒于任上。为官期间,奉直隶总督方受畴命作杂剧《康衢新乐府》十出,为嘉庆皇帝贺寿。该剧甫一出世,便获誉颇高,可见其戏剧才学亦被认可。其治剧之才、娴通河务之能,在此也得以真正发挥。方受畴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评价吕星垣:“才具明敏,办事练达,平日留心河务。”[4]可见吕星垣受其父辈影响,关心时事,有经济之学,绝非空读诗书之辈。
二
“道存无显晦,权重在文章”[5]。虽仕途上坎坷崎岖,大器晚成,但所谓官场失意,文场得意,早在吕氏为官之前,他就已经因诗文而名扬一时。的确,让吕星垣留名后世的,也是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他在古文、诗歌、戏曲、书画、小说等各个方面均能独标一格,自有建树。
常州散文传统,自明代唐顺之起,至嘉庆时期的阳湖文派,一直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毗陵七子介于其间,对常州地区古文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吕星垣是当时的古文名家,时人常将他与韩、柳并称。七卷《文钞》收录散文103篇,内容丰富,文体多样。其古文的具体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识丰富,识见超远。毗陵七子大都有文集传世,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古文生力军,钱维城和钱维乔亦有文集传世。受地方文化影响,再加上深厚的家学底蕴,吕星垣长于古文自是情理中事。他十二岁参加童生试,知府“奇其文,拔前茅”[3],遂入书院从刘大猷先生课作文。十三四岁家居,读先秦两汉书,始肆力于古文。在京读书和四方游幕的经历,也扩充了其识见。所见所学,落实于笔墨间,使之在作文时能够揽笔立就。如《府兵论》介绍府兵制的产生、因革、利弊,能了然于本末终始,行文精密,纪律严整,可为全史断制;《复张瑞书观察》与友人谈论河防的治理问题,能指陈利弊,切中要害。如此种种,可证星垣之学识广博,才思敏捷。
气势清雄,不落窠臼。丰富的学识使吕星垣散文呈现清雄的风格,他的古文大多直抒胸臆,气脉贯穿,读之令人酣畅淋漓。如《樊哙论》《王猛论》为古人正名,皆能独抒己见,议论犀锐;《连山归藏辩证序》《赠充裕上人序》笔锋纵横跌宕,直道本意。但吕星垣古文中的学识并没有影响性情的抒发,他在创作上追求随性而为,以不强作为宗,形成了不落俗套、不拘程式的文风。
在致金石大家黄易的信中,吕星垣阐释了自己对篆刻的看法,从中我们可略窥吕星垣在散文创作上的追求:
至心和意精,聚眉目真气于锋石相接之际,有天机焉。有兴会遽到,涌溢出之者;有兴会徐来,来即脱手者;有汩汩乎来者,数数焉至者;有兴会团结,不聚锋巅,不迎石理者。心手非不闲敏,目非不精,乃数十锋不接石,忽骤接之,意惬飞动,此为极致。
正如秋鹰盘空,百旋不下,非无所见,无当其意。意所满,虽斜飞浅落,增减无从;意所未满,即眇忽间,必须百遍摩挲,满其意,要以不强作为宗。[6]
少了绳墨规矩的束缚,其发文说理,自然能够自由申发,随性铺开。这种不落窠臼的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其深厚的家学底蕴有关,另一方面,吕星垣磊落洒脱、逸气凌云的性格,也对其文风有一定影响。
风格多样,不名一体。吕星垣因有多次游幕的经历,在京中求学时又以鬻文为生,故其文体裁全面。《文钞》中收录了序、跋、书、记、传、碑、墓志铭等多种文体,内容涉及游记、书信、寿辞、政治议论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皆能根据创作需求形成或诙谐讽刺、或体制纯正、或清新淡雅的风格。如《道场山宴游记》《龙井游记》一类记叙游览之作,安静恬淡,涉笔成趣,《复严明府论文书》《复李生书》一类说理之作,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力透真源,《诰封宜人管母王太宜人七旬寿序》《重修吴县学宫碑记》一类应制之作,体制完备,辞简理精,实属散文创作的全能手。
“内义外法”是吕星垣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独创的散文创作理论。在写给友人的书信和为他人文集所作的序中,他多次以“义法”为核心,阐述了自己对于文章创作的独到之见。在这套理论中,吕星垣提出“文者,道所载也”[6],强调文章的好坏与作者的人品不无关系;他继承了方苞义法说的内容,并进一步指出,义内而法外,义显而法隐,二者共同构成文章的骨骼与血肉;在文章语言风格上,吕星垣崇尚简洁峻峭的文风,但他否定为少而少,认为应该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让文章语言达到最简化的状态,这样的语言才会有吟咏不尽、意味无穷的特点。
详观吕星垣的散文篇目,不难看出“内义外法”说对其创作的影响。任大椿在《文钞序》中云:“余即其所出者言之,一以己出之义法。自为其义法,其凌高秉正,如从日星测圭,悬衡而分寸自合也;其逞奇制正,如驰车骤马,尽地之利;如捩柁植樯,走风水之便也。重为叹曰:非有己出之义法,曷至此哉!”[7]可见,理论对其创作影响之甚。此外,这套理论上承方苞“义法说”,下启阳湖文派的散文创作,是常州古文创作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叶启勳评价吕星垣古文:“规抚韩柳,而取径于震川,揣骨见真,足以自传。”[8]580遗憾的是,吕星垣散文在这之后便鲜少被人提及,不免令人惋惜。
三
吕星垣少年即以诗闻名乡里,故自视颇高,在当时诗坛上只推许洪亮吉与孙星衍。他四岁时便能续吟“玉露凋伤”一句,且一字不讹。五岁入塾,八岁读遍四书五经,九岁时已作古体诗40余首。遗憾的是其诗多散佚烧毁,现存诗集《白云草堂诗钞》共分三卷,收录诗歌约350首。前两卷大致以时间为序,记载了自己游览所及、与友人的酬唱赠答,为研究吕氏生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第三卷独分一卷,收录五古读史诗230首。
总体来说,吕星垣与毗陵诗派其他诗人一样,因家学之厚与才学之高,表现出“狂狷”之品。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以“奇”为宗旨,追求不落俗套的诗歌风格。吕星垣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式善评:“吕学博星垣诗尚奇险,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9]233洪亮吉与吕星垣同有七子之目,又从小一起长大,他在《北江诗话》中对吕星垣这一奇特品格有更详细的阐发:
吕司训星垣诗,好奇特,不就绳尺,曾用七阳全韵作“柏梁体”见贻,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后万古不敢望。”颇极奇肆,然古人无此例也。余亦尝赠以长句,末四句云:“识君文名已三载,才如百川不归海。银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沧溟欲相待。”亦颇寓规于奖云。吕又有句云:“桃花离离暗妖庙”;又《题博浪椎图》云:“人间十日索不得,海上大啸波涛声。”盖好奇不肯作常语如此。[10]13
诚如洪亮吉所言,奇特的诗风长期贯穿于吕星垣的诗歌创作。而在奇特之外,其诗又以乾隆戊戌年为界,在风格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诗歌40余首,包含了其幼年时期到26岁时的诗歌,除咏古诗之外,占所存诗歌的三分之一。这些诗歌多以五言、七言律诗为主,间有排律和古体诗。内容多围绕诗人的所见所学展开,主要为纪游写景、咏物抒怀、怀古议论,语言多清雄俊艳,直举胸臆,有唐音之风。童钰“如行天之月、出林之风,超然物表,毫端无尘氛,文外有仙骨”[11]、洪亮吉“宿雾埋山,断虹饮渚”[10]6,都是对吕星垣早期诗歌清雄俊逸风格的恰当概括。
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几次应试的失败和家境的逐渐衰落,吕星垣心智开始成熟,诗中开始慢慢融入对人生的思考,愈发沉郁。乾隆四十三年(1778),父亲吕扬廷去世,吕星垣诗风发生转变。曹仁虎在《诗钞序》中直接点明了这种变化:“大抵君诗直举胸臆,空依傍,清雄逸艳,不名一家,心太慧,骨太峻,才太豪,气太盛。故戊戌以前,多有横溢汗漫处,一变而以古文法驭之。”[12]
后期诗歌约90首,大都作于其父去世之后。这一时期,吕星垣为谋生计,远离家乡,客幕四方,诗中也多了一份疏苦瘦涩,以孤峭为宗。在内容上,依然有纪游咏物、抒怀议论之作,但随着所见增多,交游日广,酬唱赠答、纪事怀人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形式上,在律诗之外,古体诗的比例也较前一时期有所增加。这些古体诗篇幅甚众,形式自由,便于诗人叙事抒情,无论在体制上还是文法上都更类似于文,在写人记事的过程中,以文法写诗,体现了吕星垣诗文技巧的成熟,以及有意革新的诗歌观念。
诗集末卷咏史诗共230首,上溯太古开天辟地,下迄元朝灭亡,涵盖二十二朝的历史,内容涉及地理、山川、武备、盐法、民俗、吏弊多个方面,皆“识见超远,评论精当,悬之国门,实无一字可排者”[13]。诗歌不列诗题,按编年体例依次排列,又能根据需要进行变通,不完全被历史发展的顺序局限。这些诗全部采用五言古体,摆脱了格律平仄的限制,使作者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较少形式的限制和束缚,从而体现出“篇句字法,又峭洁雄秀,特甚开拓心胸,推倒豪杰”[14]的艺术特点。
对于咏史诗,洪亮吉《北江诗话》认为“虽许翻新,然亦须略谙时势,方不贻后人口实”[10]3,主张咏史诗应结合现实,这与吕星垣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此外,毗陵诗人重视学问和学识的共同特性,也在吕星垣的咏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总之,作为乾嘉时期的诗人,吕星垣诗歌既有毗陵诗派的地域特征,又因其性格、经历有其独特之处,既能在诗中体现自己的家学底蕴,又能将所见所学寓于笔下,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值得肯定,同时也是研究毗陵地方诗派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
吕星垣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除了古文、诗歌之外,还有小说、戏曲传世。小说《后红楼梦》是吕星垣托“逍遥子”之名所写的娱亲之作,是《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行之后的第一部续书。小说描写黛玉死后因有炼容金鱼护体,尸体未腐,后原体回生,有了掌管万贯家财的能力,并且提出了整顿贾府的十四条措施,重整了家业。宝玉得了进士,选为庶吉士,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宝、黛二人在黛玉嗣兄林良玉的支持下,以媒妁之言完婚。宝钗亦与黛玉同侍宝玉。贾府因惜春被选入宫,接替元春位置,重获皇亲国戚的地位,再加上黛玉管理得法,重新获得荣华富贵。小说对宝、黛、钗三人的命运以及贾府的结局都做了较大的改动,将宝、黛改造成符合封建士子阶层价值观的形象,二人的结合亦未摆脱当时文人在爱情婚姻观念上“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思想。它虽然在艺术造诣和思想水平方面都无法和原作媲美,但确是对《红楼梦》进行续写、改编的一次积极尝试。
乾嘉时期,常州戏曲创作异常繁荣,吕星垣亦擅长作杂剧。他早年曾为京城演员撰《芸阁赋》,虽已散佚,但钱维乔有诗赞曰:“才人笔偶赋樱桃。”[15]作有贺寿戏《康衢新乐府》,共分十出,分别为“万年辑瑞”“万寿蟠桃”“万福朝天”“万宝屡丰”“万花先春”“万里安澜”“万骑腾云”“万卷嫏环”“万舞凤仪”“万国梯航”。在艺术特色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盛世之音,歌功颂圣。万寿戏是为皇帝贺寿,其主旨自然是为了博圣上一笑,因此歌功颂德是《康衢新乐府》的主题。如第四出“万宝屡丰”上场人数就多达50人,通过农师、八谷星君、耕夫、樵夫、蚕女、织妇、牧童、渔婆之口,勾勒了一幅连年丰收、政简刑清、百姓和乐、官闲吏肃的太平景象,充分展示了统治者所希冀的太平局面,也彰显了泱泱大国的庞大气度。这样的主题不仅符合为皇帝祝寿的主旨,更体现了当时读书人的主流价值观,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师亮采序此剧曰“和声鸣盛,远媲虞球”[16],斌良亦有“笔花染处非凡艳,疑听钧天广乐回”[17]的高度评价。
规模宏大,场面壮丽。清代戏曲在嘉庆时期呈现日薄西山的衰落之景,嘉庆皇帝亦刻意节制,戏曲活动的规模已经大大减小。但作为宫廷戏,《康衢新乐府》的规模仍令人惊叹。如“万卷嫏环”中“场上设三层彩楼,悬嫏环福地匾”[18],“万宝屡丰”“万舞凤仪”中演员人数多达几十人,都可见其规模。这一方面体现了清代戏曲的盛况,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因为宫廷戏讲究排场,以迎合统治者心理的特殊要求。
服装讲究,仪式性强。服装和仪式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就为戏曲行业所重视。到清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外在的规矩愈趋规范,再加上雍正、乾隆等爱好戏曲的统治者的重视,便更加讲究。“万舞凤仪”中,丹凤、紫凤、青凤、白凤等不同角色乃至不同性别均有不同的服装,可见服装已经成为辨识角色的重要标志,成为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寿蟠桃 ”中西王母一出场,便以“吾乃西王母是也”[18]交代了自己活动的背景原因,为之后故事的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如此种种,都表现出吕星垣在戏曲创作方面的修养与根底,这无疑与其舅父钱维乔有关。钱维乔是当时常州地区有名的曲家,作有《乞食图》《鹦鹉媒》《碧落缘》三种传奇,以他为中心,几乎可以串联起乾隆中期常州所有的曲家,如吕师、董达章、庄逵吉等,作为其外甥,吕星垣自然也在指导交流的范围之内。在浓郁的创作氛围中,吕星垣与舅父做出同样的文体选择,并且孕育出精品,自然是不难理解的了。
舅父影响所及,吕星垣在艺术领域也颇具造诣。钱维城和钱维乔都是清代常州地区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均师出常州画派创始人恽格。钱维乔诗中多有钱维城送画给吕星垣的记载,有句云:“阿兄遗训犹堪告,一字家风不厌贫。”[15]可见,为振发家声,不坠家风,他们对外甥吕星垣灌注了很多心血。在这番教导之下,星垣自然书画俱精。其书法早期学苏轼,晚年则出入于黄庭坚、米芾之间。吕星垣文集中,亦有与钱伯埛探讨书法的书信,可见其在书法理论方面亦有钻研。绘画方面,吕星垣与其舅父相似,喜作淡墨山水,近法王原祁,远师黄公望,有画作《春峦耸秀图》传世,极尽物态之神妙,其《江山万里图》,林则徐以“殊雄劲”称之。此外,故宫博物院藏有吕星垣写给金石大家黄易的手札,札中吕星垣以后辈的身份阐述了自己对篆书、金石的看法,议论精当,文采飞扬。
总的来说,吕星垣自小受良好家风以及乡邦文化的熏陶,才德兼备,既工诗书翰墨,又俱济世致用之能。但他的科举仕进之路走得异常艰辛,穷尽一生却只终于小小县令。在性格上,他表现出文人特有的狂狷傲慢,追求自由独立,但从其人生选择及作品主旨来看,他非但没有任何冲破封建藩篱的想法,反而处处恪守儒家传统礼教,是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歌颂者和推崇者。他的人生经历的前后落差,以及性格上的内外矛盾,并不是其个人独有的,而是清代众多士子共同的特性,这一现象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