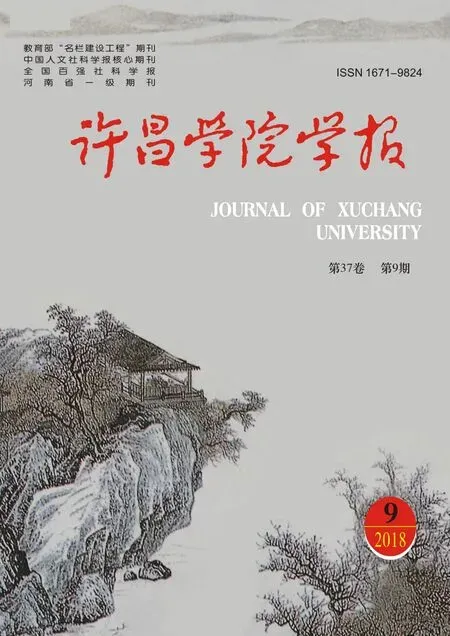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互文性
谢 占 杰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自翻译成中文出版至今,在我国一直拥有众多读者,有不少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解读和阐释。正是通过接受者兴趣不减的解读与阐释,这部作品作为当代外国文学的经典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互文性”可以说是这种独特魅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信息容量,扩展了文本的意义蕴含,使人有常读常新之感。本文拟就这部作品的“互文性”做一探讨。
关于“互文”与“互文性”理论,国外学者多有研究,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少研究、介绍。一般认为,互文是一种手法,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广泛存在。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互文并不是文学文本内部所独有的,它还存在于其他艺术门类,诸如绘画、音乐、建筑、雕刻、舞蹈、戏剧,甚至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而互文性作为一种理论,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我国。克里斯特娃认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是“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横向轴和纵向轴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语是另一些词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来,这两支轴代表对话和语义双关,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分别。是巴赫金发现了两者间的区分并不严格,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1]3-4。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其中也包含着文化文本的参与。就文学作品而言,由于作者不同,其艺术追求、思想情感的表达、叙事策略的运用也都不同,文本呈现出的互文性特征也有明显不同。一般而言,文本互文性特征越突出,令接受者引发的联想就越丰富,其所要了解和理解的疆域也就越宽,而不确定性因素、理解和阐释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但随之,阅读、研究的兴趣也会增加。
就昆德拉的创作而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读者来说,理解、阐释上的高难度,其所具有的引人探胜和寻味的魅力,可以说与文本的互文性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在这部作品中,互文性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典及其价值和意义
典故的运用,在中外文学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往往有自己特有的故事或史实,因为不断被提及,从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文本中,有两个典故的运用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圣经·旧约》中埃及法老的女儿救摩西的故事,另一个是有关俄狄浦斯的神话传说。(关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文本《俄狄浦斯王》与此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将在文本仿拟部分讨论。)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么一段叙述:面对特丽莎的到来,托马斯“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2]4-5。从第4页到第9页,在短短6页的行文中,捞起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一语句3次出现,这绝非偶然。这一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据《圣经·旧约》记载,以色列人逃到埃及后,生息繁多,埃及王不信任以色列人,不仅虐待、迫害以色列人,还下令为希伯来妇女接生者,凡男孩一律杀掉,女孩可以存活。一对利未人夫妇被迫把所生男孩放在涂了石漆、石油的蒲草箱里,搁在河边的芦荻丛中,顺水漂流,听天由命。后法老的女儿发现了草箱,可怜被遗弃的小孩,决定收养他,取名“摩西”。正因为埃及公主出于怜悯救下了这个孩子,摩西才能在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传授上帝十诫。托马斯感叹道:“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话都始于营救一个弃儿的故事!”紧接着,托马斯又联想到另一个有关弃儿的神话,他继续感叹道:“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最美的悲剧了。”[2]9-10这里出现了俄狄浦斯的神话典故。有关俄狄浦斯的神话典故,大意是这样的:多年无子的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到神庙求子,得到神谕,他将有一个儿子,但命运女神规定他将死在孩子手里。为逃脱命运的规定,他和妻子决定把生的男孩扔掉。但执行命令的牧羊人因为可怜这个无辜的孩子,把他交给了科任托斯国王的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又把这孩子交给了国王波里布斯。国王很同情这孩子,就嘱托妻子要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好生抚养他。正是因为牧羊人、国王波里布斯的同情心,俄狄浦斯才得以存活,其后演绎出充满传奇而又悲惨壮烈的故事[3]218-227。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典故在文本中的价值和意义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展深化现文本的意蕴,使表达委婉含蓄。首先,它暗喻了托马斯的责任感与同情心。无论是小摩西还是小俄狄浦斯,其命运都涉及弃与救。如果说“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残酷的行为,那么,“救”就是负责任的、富有同情心的行为。托马斯把特丽莎比作顺水漂来的孩子,他觉得他不能不负责任地就把这个女孩打发走,于是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正是背负着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托马斯用一生来陪伴特丽莎。尽管他在性行为方面并不忠实于特丽莎,但他真正爱的人只有特丽莎。托马斯“救”离家出走的特丽莎,与施救弃儿摩西、俄狄浦斯一样,体现出一种同情心、责任感。三者之间的联系,深化了托马斯这一行为的意义,虽然文本对此并未直接发表议论。其次,往深层次说,“同情”涉及生命伦理问题,涉及文化精神的承继,它在文本中构成一股潜在的精神之流,贯穿文本始终。这两个典故,一个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一个来自富有人文精神的古希腊传统。弃儿的施救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只是出于对弱小生命的同情。“同情”是人类深厚而又基本的情感,它作为精神之源,滋养着后世的文化。典故的运用,隐含着昆德拉对这一精神的肯定与赞颂,大大拓展了文本的视域,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不仅如此,昆德拉还让这种传统美德在文本中发扬光大。通过托马斯、特丽莎等人物的所作所为表达了他的肯定,又以此为尺度,对缺乏同情心的残酷行为给予批判,并细致而缜密地对“同情”进行了阐释,以此表达他对生命情感的深刻认识与体验。小说写到捷克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大清洗、苏联对捷克的悍然入侵、柬埔寨内战、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等,其间有无数无辜的生命因此丧失,还写到苏联人在入侵捷克后,组织那些想泄私愤的人,展开了对城市中鸽子和狗的猎杀,以及孩子们活埋乌鸦等。所有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质就是割裂、践踏或者说遗忘了人类美好的精神传统。在文本中,特丽莎救了那只被埋的乌鸦,托马斯和特丽莎收留了无人收养的杂种小狗,同情那些遭受磨难的人,这正与埃及公主救摩西,牧人、国王救俄狄浦斯一脉相承,体现着人类的美德——仁慈、同情心和责任感。昆德拉认为,“同情”不是可怜,而是不仅能与遭受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共苦),还能体会他的任何感情——欢乐、焦虑、幸福、痛楚(同感),这才是“同情”的高级情态。他还进一步把人与动物相处的准则与人与人相处的规范相联系,把人与动物的相处看作是对人类道德的测试。而在这方面,他认为人类的道德面临着根本的溃裂。毫无权力的动物就像无助的弃儿,对动物残忍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和践踏,而最终这种态度将指向人类自身,灾难也将降临到人自身。没有了同情心与责任感的世界是人间地狱,没有了同情心与责任感,更是个人及人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昆德拉的思考是沉重的,又是振聋发聩的。正是通过这两个典故,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以及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作者与读者、现实与历史,多个层面形成了多声部的对话,这就使文本的视域、接受者的视域大大得到拓展,其表现出的思想、情感、精神更具厚重感。从表达上说,又含而不露,因而更加耐人寻味。
二是,通过这两个典故的作用,引发诗意联想,使作品更具诗性魅力。托马斯与特丽莎一生的关系、生活中的许多故事,都始于托马斯那个美丽的比喻: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昆德拉说:“托马斯当时还没认识到,比喻是危险的,比喻不能拿来闹着玩。一个比喻就能播下爱的种子。”[2]10细细品读,才能体会到昆德拉的话有深意存焉。先从托马斯说起。正是托马斯的比喻让人联想到埃及公主救摩西的动人故事,因而有了跨时空的观照,有了情感的震动。托马斯也因为这个比喻,一下改变了被动局面,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人生态度。面对着突然到来的特丽莎,托马斯不知该怎么办,是留还是让她走?这个比喻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托马斯成为一个主动的施救者,他决定留下特丽莎,承担照顾这个像一个弃儿一样的孩子的重任,并和特丽莎走向了婚姻,走向了爱情。从特丽莎这方面来说,她离开专制的母亲,离家出走的状态,就像一个被弃的孩子。更有意思的是,她出门时带了一只大箱子。这只大箱子与弃儿摩西被放进去的草箱建立了互文关系,使读者产生诗意的联想。特丽莎不仅是个被救者,当她去救乌鸦、关心动物、精心照顾卡列宁时,她的身份发生了置换,转换成一个施救者。她的行为与身份一下子让人联想到那个美丽的埃及公主,特丽莎这一形象就成了现代社会的美丽公主。也正是互文带来的诗意联想,为小说文本增添了诗性与兴味,使其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二、“仿拟”及其意味与作用
“仿拟”又称“戏仿”或“戏拟”,多见于对某著名大家作品风格或具体作品的仿拟。通过改写、置换、故意模仿等,以一种幽默或夸张的方式,或表现熟悉的人物或情景,或表达新的思想,或传达某种神韵,或进行讽刺,从而构成对被仿拟对象的承继。 在小说文本中,最明显也最有意味的当属对《安娜·卡列尼娜》和《俄狄浦斯王》的仿拟。因仿拟的对象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意味和作用。
1.对《安娜·卡列尼娜》的仿拟及其意味和作用
小说写到特丽莎在去托马斯家那天,胳膊下夹着一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后来,他们两人结了婚,但托马斯仍与包括萨宾娜在内的其他女人有性关系,这使特丽莎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托马斯给特丽莎捡回一条狗。想起特丽莎去他家那天,胳膊下夹着的那本书,两个人就为这只小母狗起名为卡列宁——安娜的丈夫的名字。后来这条狗融入这个家庭,构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隐喻着不同的意义。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小说与《安娜·卡列尼娜》两个文本之间有许多微妙的联系,这些联系使小说文本具有丰富的内涵,也有着更耐品的趣味。
首先,它体现在两个文本“戏剧性的开始与悲剧性的结局”上。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渥伦斯基是在车站相遇的,当时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人死在车轮下面。这令安娜终生难忘,以致在她对爱情、生活绝望时,又想起这一幕,于是投身于车轮之下,结束了年仅23岁的生命。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特丽莎既没有和托马斯有很深的交往,也没有和托马斯事先约定,就把随身带的箱子往车站一放,只身去见托马斯。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她胳膊下夹着一本书,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他们的交往、生活就此开始。再看他们的结局,在他们相依相伴地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后,最终双双死于车祸。似乎特丽莎夹的那本书,从一开始在冥冥之中就预示了她与安娜相似的悲剧命运。虽然小说文本并不是对原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进行了改写、置换,人物、事件、故事发生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但在传达喜剧性、悲剧性的神韵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其次,它体现在文本幽默的意味上。仿拟中常常带有戏拟,即以夸张、扭曲的方式,制造幽默效果。昆德拉利用与《安娜·卡列尼娜》的互文,制造出机趣盎然的幽默,既传达了情意,又趣味十足。这在他描写托马斯、特丽莎给小母狗起名字的部分,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托马斯说给它起名叫“托尔斯泰”,因为他想到了特丽莎夹着的那本书,而且,他还想让狗名能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既然提到《安娜·卡列尼娜》,人们就知道它属于托尔斯泰,那么提到叫“托尔斯泰”的狗,人们就应该知道它属于特丽莎。这一不伦不类的比照十分好笑。昆德拉让他的人物用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来为一条小狗命名,似乎是对托尔斯泰的大不敬,但实际上,昆德拉恰恰是用一种玩笑的方式向大作家托尔斯泰致敬。特丽莎觉得给一条小母狗起个男性的名字不好,于是给狗起名叫安娜·卡列尼娜。表面上看,特丽莎起的名字照顾了狗的性别,实质上,不如说特丽莎对安娜记忆深刻,故以此来表达对安娜的敬意。但,问题还没结束,托马斯又说,女人(指小狗)不该有那么滑稽的脸,它的滑稽太像卡列宁了,于是就叫它“卡列宁”。这显然含有昆德拉对作为安娜丈夫的卡列宁的讽刺,但细细品来,又不限于对卡列宁讽刺。在原文本《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因为安娜的背叛而深陷痛苦之中,而在现文本中,特丽莎因托马斯的不忠而一生不堪承受。这种倒置暗含着对托马斯的讽刺和对卡列宁的同情。叫卡列宁的小狗对特丽莎特别忠诚,也与托马斯的背叛构成对照,对托马斯的讽刺意味更加明显。昆德拉通过互文制造的幽默并没有结束,小母狗的名字是定了,但特丽莎的担心也来了,她担心给一条母狗起一个男性的名字,会影响它的性机能。托马斯随口衍敷说可能会。特丽莎一本正经的担心让人忍俊不禁。用最轻浮的形式表达最严肃的内容,是昆德拉的一贯风格。在看似一场为狗起名的轻松对话中,昆德拉既制造了令人捧腹的幽默,又严肃地传达了他的意旨。互文的运用使作品显得委婉含蓄,趣味十足,内涵丰富。
2.对《俄狄浦斯王》的仿拟及其意味和作用
作为戏剧文本的《俄狄浦斯王》,与神话中完整地叙述俄狄浦斯一生的故事不同,它只是选取了故事中的一个时段,写俄狄浦斯作为国王为了给忒拜的百姓除灾,尽力追查很久以前杀死前国王的凶手的故事。真相大白后,他饮恨自裁,刺瞎双眼,流放他乡。戏剧文本重点表现的是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强烈的责任心及承担苦难的勇气。而这些都在昆德拉的小说文本中承载着更多的内涵。
首先,最明显的是俄狄浦斯与托马斯之间构成比照。托马斯喜爱这本书,他反复阅读,牢记于心。所以,有关弃儿的故事让他想起俄狄浦斯的故事,让他赞叹索福克勒斯以此写出了最美的悲剧。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原文本表现出的精神,构成了我们理解托马斯一生的一个重要支点。在小说文本中,托马斯的许多所作所为都与俄狄浦斯王有着内在的联系。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处死无辜之人却直到今天仍无人负责的情况展开了争论。托马斯认为,俄狄浦斯并没有因为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他承担起罪责。他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行为正是一种谢罪和致歉。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不能因为当时不知情,就对自己杀人害人的行为不负责任,就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无辜的。文章警示当局和所有人都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他写文章的动机和举动,表明他像俄狄浦斯一样,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人。后来,捷克被苏联占领,当局要求托马斯收回自己的言论,否则不能在医院上班。但托马斯宁可不当医生,也不愿自毁名誉,违心做人,所以他拒不签字。这便与俄狄浦斯对命运的反抗精神相一致。
其次,俄狄浦斯与特丽莎之间也有实质的联系。特丽莎是主动离家出走的。她离开自己的家,正如俄狄浦斯一样,体现着对命运的抗争。但小说中有改写和置换。俄狄浦斯出走,是为摆脱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特丽莎出走则是为了摆脱“被母所杀”的命运。原文本的主角是男性,现文本的主角则是女性。在特丽莎的母亲看来,天下女人的躯体并无二致,无须羞怯,无须耻辱,无须遮掩,但特丽莎却把裸身看成是集中营规范化的象征。所以,她要反抗,要出走,要寻找灵与肉的统一。但和托马斯在一起后她发现,托马斯不仅背叛了她的肉体,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托马斯背叛了她的灵魂。所以,她要继续反抗。非常有意思的是,她不明白托马斯怎么能够把性与爱分开来,于是就有了她和工程师做爱的小插曲。在这个插曲中,特丽莎发现,在工程师的书架上也有一本《俄狄浦斯王》,她觉得似乎是托马斯有意留下一丝痕迹,是托马斯有意安排的。小说文本这样叙述,是一种技巧,前后形成“巧合”,构成一种“小说的诗意”,进一步来说,是为了更深入地展示特丽莎的心理变化。她摆脱不了对托马斯的怨气,所以觉得这是托马斯有意安排的。进而,她决心体验一下,性与爱究竟是不是可以轻松分开。事实证明,她渴望的仍是灵与肉的统一,而无法将二者分开。这样,小说与不同文本之间,“性与爱”“轻与重”的主题之间,彼此交汇,彼此对立,又彼此阐释,构成对话,令人深思。在此,现文本对原文本《俄狄浦斯王》表达了敬意,原文本的精神和神韵到得了承继与发扬,也使得现文本的精神含量更加饱满,人物的内在精神特质得以凸显。
三、引用及其扩容与添新
引用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比较有代表性、有意味的有四点。一是对尼采“永劫回归”的引用,二是对巴门尼德“轻为积极,重为消极”的引用,三是对德国谚语“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像压根没有发生过)的引用,四是对贝多芬“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的引用。
巴赫金认为,一个语篇是多旋律和多声部的,在这个多种声音的汇合中,作者和引语作者甚至读者产生了对话和互动,从而产生了文本的活力和批评的张力[4]3-4。“引用行为”本身是具有改造作用的,一句话或一段话一旦被引用到另一个文本中,必然会由于“引用行为”在新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反响。在小说文本中,昆德拉所做的引用在新语境中赋予原文以新意义,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增加了作品的厚重和新意,留下了令人深思的话题和空间。
尼采的“永劫轮回”观是哲学话语。小说文本对它的引用,构成了作者与尼采、作者与读者、读者与尼采、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多声部对话。尼采希望人们同时也是警告人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历史上的很多事都会重演,尤其是那些恶。昆德拉对读者说:“事情在我们看来并不因为转瞬即逝就具有减罪之情状。”[5]4他以自己的体会,向世人发出了警告,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果忘记非洲十四世纪导致三十万人死亡的部落战争、不断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建集中营屠杀成千上万人的希特勒,或者不担心这些恶还会重演,这便“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5]4。在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有无法承担的责任重荷,想想这个前景就令人感到可怕,但这恰恰是昆德拉认可的“重”。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失去责任的重荷,“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5]5。小说文本将这一思考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尺度贯穿在作品之中,体现着昆德拉的存在之思。当昆德拉写到“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时,这是邀请读者参与到这场多声部的对话中。事实上,在阅读小说文本的整个过程中,对“轻与重”的思考始终伴随着读者。当昆德拉又引用巴门尼德的“轻为积极,重为消极”的话语时,对尼采的引用与对巴门尼德的引用之间又形成了暗中对话。昆德拉邀请读者对巴门尼德的观点发表意见,认为把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做出积极与消极的区分实在是幼稚简单。作者自己对巴门尼德的观点也持怀疑态度,他问道:“他对吗?”作者的观点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轻/重的对立最神秘,也最模棱两难。”[2]4理解小说文本,读者绕不开这些“引文”,它们是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股潜流,一种暗喻,与故事、人物、小说表达的主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又是间接的。这是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理解上有难度的地方。小说文本中托马斯的所作所为最明显地体现了“轻与重”的神秘对立与模棱两难。他曾经因为婚姻的不幸而离婚,于是他放弃了对家庭、孩子、婚姻的责任,与不同的女性有了性关系。他还宣传并践行一套所谓的“三三原则”,以确保这种“性友谊”长久。他很潇洒,很轻松。但特丽莎的到来,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特丽莎的爱、他对特丽莎的同情,促使托马斯这个浪子又走向了婚姻,负起了对“像顺水漂来的孩子”的特丽莎的责任。然而他的人生就像一曲“轻与重”的二重奏,他始终在“轻与重”的神秘对立的张力之上舞蹈。他担起了爱特丽莎的重,却不愿放弃性友谊的轻。他的性友谊的轻成了特丽莎不堪承受的重。在捷克被占领的大背景下,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托马斯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但当局让他收回、忘记自己写下的话,才能让他有工作,轻轻松松做大夫,他却无法承担这种轻,于是他选择辞职。而正是辞职这一举动,使他捍卫了人的尊严、良知,他选择了重。在自己儿子需要他签字支持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政治犯和保护特丽莎之间,他选择不签字。常识和理智告诉他,他没有能力保证签字能够让许多政治犯获得赦免,却可以做到(但也不能保证)保护那个把半死的乌鸦挖出来抱在胸前的特丽莎,至少让受到密探跟踪、提心吊胆、双手颤抖的特丽莎少受点惊吓。事实是,签字过后,更多的人成了当局迫害的对象,签字成了证据。他的选择是轻还是重?这不得不使人感叹,轻与重的对立是最神秘、最模棱两可的。对尼采和巴门尼德的引用,在新的语境中,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容量,使作品的内涵更为厚重。而特丽莎也与尼采和巴门尼德的引文有着密切关系。她的母亲把所有女人都视为毫无个性、没有灵魂和肉体的一样的人,她无法承受这种轻,她选择寻找灵与肉统一的重。她也无法承担托马斯与女人保持性友谊这种轻,她坚持她灵与肉统一的重。她无法承受人们对待别的民族、对待他人、对待动物的残忍,她选择了善良、同情和仁慈。
对德国谚语“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像压根没有发生过)和对贝多芬的话“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的引用,在小说文本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同样是多声部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全部人类历史还是个人历史,从来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重演。但相似的历史却在不断重演,尤其是那些恶行和悲剧。在小说文本中,对“Einmal ist Keinmal”的引用,与巴门尼德的话语构成呼应,与尼采的话语构成对立,也与贝多芬的话语“非如此不可”构成对立。这句德国谚语表达的是对所有发生过的一切的一种“轻”的态度,在小说文本中涉及个体,也涉及群体、族群、人类。从个体角度讲,主要涉及托马斯。习惯了与女人保持轻松关系的托马斯,面对特丽莎的到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于是引用了这句谚语。他想以一贯的轻松把他与特丽莎的关系也变成无须用心的关系。他与特丽莎相处的过程,也是不间断的对话过程,他在与特丽莎相处是轻还是重的摆动中,使重最终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在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的态度上,他的言行也与这种“轻”的态度不同,他承担了一个个人应该承担的“重”。从群体角度而言,对生活、对生命、对历史采取的是“Einmal ist Keinmal”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恰恰就是这种态度,让恶行不断重演,而又轻易被人忘记,被人卑鄙地原谅。人们会忘记非洲导致三十万人死亡的部落战争,忘记希特勒、罗伯斯庇尔,忘记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捷克、捷克大清洗等恶行。这才真正是我们人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Einmal ist Keinmal”这句引文,与对尼采的引用,构成一种对立,从正反两个方面,表达着小说文本至为深厚的思想潜流——对个体、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怀。小说文本中作者以调侃和挑衅的语调发表了自己的意见。“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人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如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2]237-238。这足以显示作者满怀忧思的人文情怀,显示文本“思之厚重”。“Einmal ist Keinmal”这一引文,与贝多芬的“Muss es sein”构成对立的对话。托马斯更多的是选择了“Muss es sein”。在小说文本中,昆德拉以诗意的方式,在托马斯与特丽莎第一次在小镇偶然碰面时,就把他们置身于贝多芬的音乐背景下,构成他们二人生活的诗意意向。瑞士的逃亡,托马斯因特丽莎的离开又过上了充满“轻”的逍遥日子。但不到一个星期,他对特丽莎的思念促使他放弃医生的职业,放弃逍遥的“轻”,“非如此不可”地返回布拉格,回到特丽莎的身边。为了保护特丽莎,他拒绝了儿子要求他在请愿书上签字的请求,拒绝了他人安排的“非如此不可”,选择了自己的“非如此不可”。特丽莎最喜欢听贝多芬的音乐,她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找到灵与肉的统一,希望在睡觉时能够紧紧握着托马斯的手安然入梦,对她而言,没有“别样也行”,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这样的“非如此不可”。贝多芬用“非如此不可”,奏响了一曲扼住命运咽喉的悲怆的音乐,托马斯、特丽莎,也用“非如此不可”弹奏出一曲令人深思、深切感人的协奏曲。
正如萨莫瓦约所言:“凡是文本都有互文,那么从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识别哪一类互文现象,而是衡量由词、文、言语片段引入的对话的分量。”[6]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充分体现了多声部对话的特质,体现了对话厚重深广的分量。由于多重意识、多重思想的交织、交融、对立与互补,小说文本的视域极为宽广,含量极为丰富,既跨越了古今,也跨越了东西方文化,既穿越了神话与现实,也沟通了现实与历史,并引领人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指向未来。毫无疑问,我们无法清晰地画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同文本之间、各种互文之间相互关系的分布图,但它们之间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从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开放网络,让读者在阅读中、在对话中,深受启发,并不断地读出新意。索莱尔斯强调:“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6]5作品的意义是不断衍生的,却不是独立发生的,它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网络结构,而不是线性的环环相扣的意义链条。“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7]译者前言27。“互文性的特殊功劳就是,使老作品不断地进入新一轮意义的循环”[6]11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互文性特点,使得经典的回声不断地响起,而它自身在与经典的对话中,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又产生着新的意义,有着新的艺术魅力,也进入了新一轮意义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