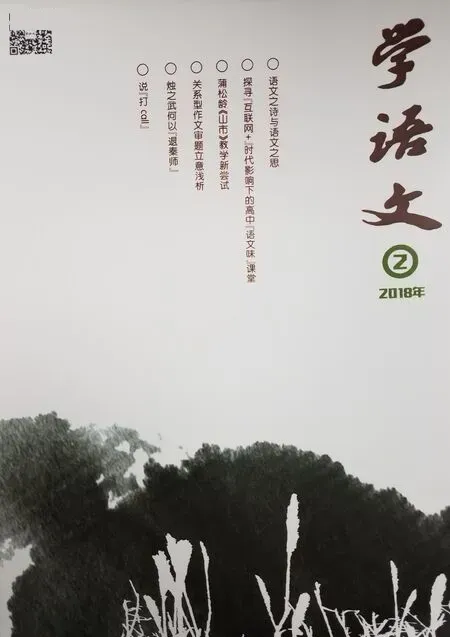从语言表达得体角度重新审视焦仲卿和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刘兰芝“举身赴清池”。千百年来,人们扼腕叹息他们的遭遇。多数人认为焦母是罪魁祸首,刘母和刘兄是帮凶,封建家长制害人匪浅。焦仲卿懦弱,刘兰芝美丽温顺,有情人“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如今重读文本,却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诗从兰芝对仲卿的一番倾诉开始。兰芝觉得自己在焦家生活很是悲苦,原因有三:一是常守空房,相见日稀;二是辛苦劳作,不得休息;三是婆婆嫌弃,故意刁难。面对兰芝的倾诉,仲卿既没有安慰,也没有责怪,而是找母亲询问。他原本是去求情的,结果非但求情不成,反而更加激怒了母亲。细究其因,除了焦母专横易怒以外,焦仲卿的语言表达实在欠妥,实属不得体。
俗话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焦仲卿说话的对象是强势专横的母亲,对兰芝怀忿已久的母亲,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他没有顾及母亲的感受,直言相问:“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其实是在指责母亲蛮横无礼,明显偏袒妻子,这令焦母情何以堪!势必让焦母以为:自己二十年养大的儿子,两年时间就被另外一个女人抢走了。焦母有错,仲卿按《礼记·内则》,应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然而诗中焦仲卿语气强硬,还语带威胁之意,等于是火上浇油,以致焦母“槌床便大怒”:“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母子闹僵,事情再无挽回的余地。再看焦仲卿“堂上启阿母”的话:“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始尔未为久”,也会使母亲伤心失望愤怒。在焦母的心中,焦仲卿“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换句话说,焦母对儿子寄予厚望,她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有美好的前程,自己也能母凭子贵,可仲卿却如此贬低自己,就是粉碎了母亲的美梦,岂不令母亲失望!焦母嫌弃兰芝至极,焦仲卿却说“幸复得此妇”,等于在和母亲唱对台戏,站在了母亲的对立面。他传递给母亲这样的信息:兰芝是上天赐给我的,我前途已经无望了,绝不能再失去她。你要休她,我就让你绝后。试想:如此强势的焦母怎能忍受儿子为了一个无礼、不听教训的女人自毁前程?仲卿过激的言语加重了焦母对兰芝的怨忿。倘若仲卿听到兰芝的牢骚后,先安慰她几句:“吾母年已高,汝勿生母气,母行有偏斜,请汝多担待”,再去安抚母亲:“兰芝尚年轻,令母多费心。勤心相教导,令其感母恩。吾不长居家,兰芝养汝身”,或许,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
求情不成,仲卿便遣兰芝回娘家,临别时告诉兰芝:“且暂还家去,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兰芝被休,仲卿认为只是回娘家暂住几天而已,他想象不到兰芝回娘家后的尴尬和难堪,显得极其幼稚。当兰芝说“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时,仲卿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担忧,也没有安慰,就那样轻易撒开了手,只留下几句海誓山盟的空话而已,其愚拙可见一斑。听闻兰芝要重新嫁人了,仲卿才“因求假暂归”。当兰芝伤心诉说变故后,仲卿无计可施,不是好言相劝,真心祝福,而是醋意十足,以语相激:“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段过激的话直接把兰芝引向一条不归路。如果不是仲卿以言语讥讽,兰芝或许不会走向绝路。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已经成家立业的焦仲卿本应是家中的栋梁,为母亲,妻子,甚至妹妹撑起一片天。但焦仲卿心智不成熟,他不能留住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庇佑自己的至亲。他虽已在官府工作多年,但智商情商都不太高,没有能力,没有担当。工作上,他只是一个小吏;生活上,家庭支离破碎。语言表达上,他更是偏激幼稚,愚不可及。他选择死亡,是在逃避责任。他解脱了,年迈的母亲无人赡养,年幼的妹妹无所依傍,焦家今后的日子将会是何种艰难!这些仲卿都不管,他愚拙的走向绝路,无能的选择逃脱。
兰芝是作者极力讴歌的对象:“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她多才多艺,美丽动人,头脑清醒,个性鲜明,似乎无可挑剔。但仔细品读她的语言,发现与其说她温顺,不如说娇纵任性。她很自爱,却不能自立;她要自尊,却难以自强。她需要宠爱,但焦仲卿给不了她,焦母也不给她。她既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温婉和顺,也没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她极力张扬个性,彰显自我,缺乏忍耐,最终走向毁灭。
焦仲卿一回家,兰芝就抱怨:“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埋怨仲卿重工作轻感情,二是指责焦母蛮横,三是自请遣归。试想:如果不是恃宠而娇,兰芝怎么敢在仲卿面前指责焦母?倘不是任性,怎能自请遣归?这显然是有违礼法的。她抱怨焦家生活悲苦,说明她不适应媳妇的身份及焦家的生活,已出嫁的女儿岂能还依恋娘家美好?不管娘家如何美好,那都是过去,自己的生活要自己面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但兰芝没有成功实现由姑娘到媳妇的蜕变。
从诗中,不难发现刘家的富裕非比寻常。兰芝离开焦家时交代仲卿她的嫁妆是“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再嫁准备嫁衣时“移我琉璃榻”,可见她的物品丰盈,而且华贵。她能接受那么多的教育,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做到的。在娘家时,母亲对她疼爱有加,又加上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刘兰芝应该是娇生惯养的。在她被休之后,母亲没有责怪她,也认可兰芝无错,及至媒人提亲,兰芝不愿改嫁,母亲也是听之任之,可见刘母对女儿爱护之甚。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刘兰芝,势必会养成娇纵任性的品行。从诗中她敢于对抗兄长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嫁到焦家之后,刘兰芝离开了温和柔顺的慈母,迎来了强势蛮横的焦母;放弃了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上了日夜苦辛、独守空房的日子。娘家的温暖富足和婆家的冷漠凄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样鲜明的反差,一个娇惯成性的娇娇女怎能适应?所以她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才敢自请遣归。她的自请遣归,既是清醒的认识,也是任性的举动。倘使她不那么任性娇纵,而是放下身段去诚心诚意侍奉焦母,以真诚博取焦母欢心,少些抱怨,多些行动,或许焦母会改变态度。但兰芝岂肯摧眉折腰?
兰芝离开焦家前,严妆打扮自己,与其说是维护自尊,体面地离开,不如说是向焦母示威以彰显自己。品读兰芝别焦母的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富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段话看似有礼有节,实则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话中带刺,语含讥讽。刘兰芝对焦仲卿倾诉苦楚时,自认为有教养,无过错,是焦母蛮横无理,因而她不可能真心诚意向焦母认错。与其说是认错,还不如说是变相讥讽。这些内容可能只是平日里焦母批评她的,她拿来维护自己,反击焦母而已。“念母劳家里”,言外之意是:既然你对我不满意,我干脆不做你的儿媳了,今后你就自己干活吧,我再也不看你的脸色了。一番不软不硬的话使“阿母怒不止”,也无可奈何。可以想象,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而已。平常生活中,焦母何止一次这样被噎着。兰芝是善言的,而且言语犀利,似刀子,如匕首,直指焦母。
兰芝任性,最怕人激,亦不喜人责。婆婆嫌弃,她针锋相对;兄长怒斥,她仰头回击;仲卿奚落,她以死相许。她以娇纵的性情,完成了最后的任性之举:“举身赴清池”。我们扼腕叹息兰芝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应反思:如果兰芝少一分娇纵,敛一分任性,事情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焦仲卿和刘兰芝就像两个任性的孩子,渴望自由,却不能自我强大;非常自我,却未能蜕变成熟,注定是一场悲剧。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