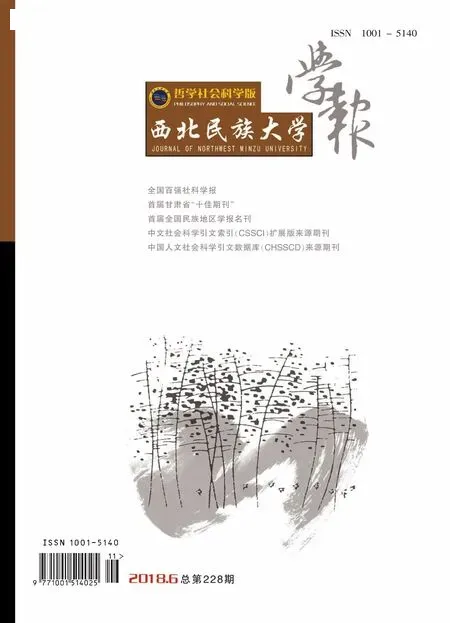基于文化圈理论视域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地图
洪美云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实事求是》杂志社,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既离不开一定的空间范畴,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概念。文化发展的系统构成包括空间系统的文化圈和时间系统的文化层,其中文化圈概念最早是德国文化学家格雷布内尔(FritzGraebner,1877—1934)于1904年在《埃塞俄比亚文化圈及文化层》一文中提出的,之后奥地利民族和语言学家施密特(WilhelmSchimidt,1868—1954)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圈的概念。理论界普遍认为,圈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文化圈主要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众多文化群体所构成的区域,文化圈强调的是区域文化特质的相同性或者相似性。文化圈理论注重空间研究,试图在重建古今文化关系的历史序列上找出具有同源性的规律[1]。层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正如考古发掘切开的地质层横切面一样,文化层主要是指在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中,代表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文化层次不断累积叠加所形成的文化历史的横断面。文化层理论注重研究文化的时间维度,对于我们了解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比较、研究、鉴别各个民族文化嗣续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2]。文化圈与文化层分别构成文化的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又相互转化,共同体现了人类文化生活与发展的内在时空特征[3]。基于此,对于文化的考察研究既可以从空间的文化圈视角也可以从时间的文化层视角切入。从空间范畴—文化圈视域梳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分布情况,可以窥见维吾尔族传统文化是在地域差异形成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此后,由于东西文化以及区域内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鄯善、高昌、于阗、龟兹四大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相互交织交融,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空间范畴—文化圈视域梳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分布情况,以期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比较清晰而系统的认知。
一、以自然地域划分的南北生态文化圈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规约着各民族对生计(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这种内在的关联使民族文化与他们所依赖和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新疆现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格局早在距今五六百万年前就基本形成,以天山为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天山以北分布着广袤的草原和半荒漠[4]1,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由于准噶尔盆地以西有山地缺口,使得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冷湿气流进入而带来降雨,有利于森林和草场的形成。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适宜发展畜牧业,因而天山以北多是游牧民族。天山以南在塔里木盆地周缘沿河流流过的地方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绿洲,冬季短暂,夏季漫长,属于暖温带干旱荒漠气候,由于昆仑山、天山等重重阻挡,海洋水汽难以到达,因此降水稀少,是我国降水最少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些高山终年积雪,消融后形成的众多内陆河浇灌着绿洲土地,生活在这些绿洲上的原住民发展了早期的绿洲农耕技术。正是在适应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天山为界,北部地区主要活动的是逐水草而居的塞人、月氏人、车师人、乌孙人和匈奴人等,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是典型的草原游牧、畜牧文化,“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寄穹帐”(魏源《圣武记》卷三),“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畜随草迁,居无常处,浪迹天涯;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及葱岭以东地区,居住着许多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居民和部落集团,以塔里木盆地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聚集地,居民主要是塞人、吐火罗人和羌人等,在此地域基础上形成的是绿洲农耕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化是在现实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因此,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都同其以前的文化形态有不可分割的渊源与继承关系,正是这种历史的承继关系,文化的发展才能持续不断,才有可以追溯的历史线索。由于历史继承性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才形成了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5]。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维吾尔族的先民在漠北草原时期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在继承天山以北游牧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开拓创造了灿烂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840年回纥(回鹘)汗国分裂,维吾尔先民西迁,在与当地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两个地方政权,逐渐由“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自秦汉以降,西域独特的相互依存、各具特色的游牧文化,特别是中原的农耕文化深刻影响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二、文化的交流交融衍生的东西文化圈
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通畅与繁荣,来自东西方的各种不同文化无限制交流传播、重叠交融,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在新疆也逐渐形成几大文化圈[6]。这些不同文化圈其实是在南北生态文化圈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交融叠加发展的结果。
在新疆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维吾尔族文化以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为界,分为前伊斯兰教(回鹘时期)和后伊斯兰教两个历史时期,前伊斯兰教时期又以回鹘人西迁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回鹘人西迁以前,在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围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圈,由于佛教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势力相互影响,渐次形成了次生的文化圈(鄯善、高昌、于阗、龟兹四大文化圈)。回鹘西迁后,突厥语族诸民族逐渐成为西域的主导力量,在地域自然文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次生文化(鄯善、高昌、于阗、龟兹四大文化圈)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回鹘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并存的局面,且长达200年之久,即以高昌回鹘文化(回鹘语)和喀什噶尔地区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文化(阿拉伯字母)并存发展时期。从此,突厥化与伊斯兰化逐渐合流,经过近300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天山南部民族与文化的重新整合。到16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基本完成了在新疆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在对伊斯兰文化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的过程中,之前诸多文化的影响沉淀成了底层文化,并以传统文化的形式继续影响着今天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
(一)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的四大文化圈
3-6世纪(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原文化的不断西传,在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文化圈的基础上,南部绿洲以汉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以佛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以各种途径相向进入西域不同地区,与当地文化传统结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不同文化特点的几个文化圈[7]。即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汉文化和犍陀罗文化为代表的东西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且末文化圈,东西文化交融的高昌文化圈。这一时期四大文化圈的语言文字各异,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国国文字各异”。于阗文化圈(包括巴楚,巴楚语言上属于和田塞语,但文化宗教上属于北部的龟兹文化圈),语言为伊兰—塞语,文字使用婆罗米文直体[注]目前学术界关于婆罗米文字有三种写法:写法一“婆罗米”,参见耿世民著《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页;写法二“婆罗谜”,参见黄文弼著《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7页;写法三“婆罗迷”,参见厉声著《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页。本文采用耿世民先生的“婆罗米”文写法,仅因参考版本不同,并无他意。,流行佛教大乘派;龟兹—焉耆文化圈从阿克苏开始,向北向东一直到吐鲁番地区,使用吐火罗语B,文字使用婆罗米文斜体,流行佛教小乘派;高昌文化圈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主要以汉族文化为主(4-6世纪),使用吐火罗语A,通行汉文和胡书;鄯善文化圈以古代楼兰文化为中心(今天罗布泊一带,公元前2世纪—5世纪),使用犍陀罗语,佉卢文[8]。
西域位居东西交通枢纽,是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诸文化交汇的地区,诸文化圈的形成及特点与西方(佛教)文化的东渐和东方(汉)文化的西传线路一致,越往西,东方文化的影响越小,西方文化的影响越大;越往东,西方文化的成分越少,东方和本土文化的成分越多。不同文化圈的形成只是这种汇聚、交融力量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而已,正因为如此,西域本土文化更具民族特点。
6-9世纪中期,南部绿洲文化到达鼎盛时期,文化交流、整合现象十分突出。龟兹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并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于阗文化受大乘佛教影响,尤其受犍陀罗艺术影响较浓,体现在佛教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同时与中原文化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文化进一步受到中原儒学影响。
1.高昌文化圈。高昌历来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重要门户,西汉时在此设戊己校尉,东汉设西域长史,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中原地区政治动荡和战乱,大量汉人由河西地区迁入高昌,这一过程持续很长时间,并逐渐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地方政权。唐设立西州屯田后,高昌逐渐成为西域汉文化的中心。高昌文化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以汉文化为主体、中西文化交融为特点、受游牧文化影响的高昌文化圈逐渐形成和发展[9]。
据《北史·西域传·高昌》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汉文字、汉语言通行高昌。当地学人经常阅读《论语》《孝经》,吐鲁番出土了大量汉文典籍抄本,为《北史·西域传》的记载提供了证明。高昌王室实行中原礼仪,供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画像,派贵族子弟去中原求学,研习儒家经典和中原礼俗,这些学子成为汉文化在高昌的积极传播者。高昌墓葬出土的女娲伏羲人首蛇身图也证实了当时的高昌普遍盛行汉地葬俗。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地方政权,经阚氏、张氏、马氏及麴氏,使高昌地区的汉文化十分浓厚,且占据主体地位。
高昌佛教在吸收印度、龟兹佛教的基础上深受中国化的中原佛教文化回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佛教文化。中原传统道教文化也传播到这一地区,道教和佛教在高昌地区汇聚,成为高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多种宗教融合并行的现象很突出。
总之,高昌是东西多种文化汇聚、融合之处,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经过数百乃至上千年的不断碰撞和发展,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以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并有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趋势[10]。
2.鄯善文化圈。鄯善即楼兰,西汉更名为鄯善,东汉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形成了东起罗布泊、西至尼雅的政治势力。随着西汉在伊循(古鄯善)屯田,以及魏晋时期在此设西域长史、派兵屯戍,以各种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为代表的汉文化便源源不断传入鄯善地区。中原王朝对鄯善地区的直接管理及派兵屯戍也使中原一整套文化体制移植于此,并与当地固有文化一起构成了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中原王朝与鄯善国王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是并行的,从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佉卢文简牍文书的内容来看,当地居民的有关事务大都由鄯善国王及其属下直接管理,有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为证;而魏晋以来的西域长史主要在当地进行行政管理及有关军队屯戍的事务,以汉文简牍为佐证,由此也导致鄯善文化圈中产生了东(汉文化)西(犍陀罗文化)两种文化并行的现象。
鄯善早期文化受中亚、印度文化影响极大,鄯善国的官方文字是佉卢文,语言是中古印度西方方言,属于印欧语系,又称“犍陀罗”语。魏晋时期,鄯善佛教盛行,信奉小乘佛教,国内僧侣达4 000多人[11],占总人口1/4强,可见佛教之繁盛。其佛教艺术也有深深的犍陀罗早期文化影响的烙印,以米兰地区西寺地下残存壁画以及斯坦因在米兰废址中的考古发现为例。
鄯善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在鄯善文化圈,越往西其西方犍陀罗文化影响越大,东方汉文化的影响越小,反之亦然。鄯善文化是汉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并行的文化,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简牍、黄历及标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纹样或字样的汉锦、服饰和日用品就是佐证。鄯善出土的佉卢文书记载,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为主,且犁耕技术已经广泛采用。在米兰还发现了庞大的灌溉渠系统,说明人工灌溉技术的发展,也说明汉文化在此地的影响。楼兰古城曾出土壁画墓彩棺,其主体花纹是云气纹,两端绘有日、三足乌、蟾蜍图案,分别代表汉民族创世神、女娲和伏羲。这类彩棺在甘肃的酒泉也有出土,属于魏晋时期墓葬,这已非单纯的文化交流,而是汉文化传播带来的信仰习俗的嬗变。
3.龟兹文化圈。龟兹是古代人们对今天新疆库车县、新和县、拜城县、沙雅县等地的称呼。龟兹文化主要指今天新疆库车绿洲一带区域汉唐时期以佛教为主背景的文化艺术类型。龟兹因为独特的龟兹文化而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文化中心。汉文化对龟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龟兹乐舞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宫廷乐舞的影响也很大[4]31。仅汉文文献记载的龟兹乐舞演奏乐器就有24种。龟兹乐舞广泛吸收了粟特人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的舞蹈元素。龟兹还有一批以苏祗婆、白明达为代表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音乐理论以及高超的琵琶演奏水平,丰富和发展了龟兹及中原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龟兹有与于阗、高昌等国不同的风俗,百姓剪短发,只有国王不剪发,在社会上层中流行生子用木头压头使之成扁状的习俗。库车苏巴什古城出土一具女尸,其头即为扁阔状,这或许是王公贵族高贵身份的象征。苏莫遮是龟兹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苏莫遮属于歌舞戏形式,以浑脱、大面、拨头等形式泼水相戏,龟兹的苏莫遮在7月初,其目的是禳厌驱灾。佛教传入龟兹后,苏莫遮被赋予了佛教内容,但原型则来自西域南部绿洲广为流行的乞寒习俗(实为乞水)。苏莫遮大约在北周时传入中原,至唐玄宗时盛行了130多年,先是成为宫廷内的娱乐节目,后流行民间,成为“比见坊邑城市”的民众娱乐活动。
佛教传入后龟兹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小乘佛教文化中心,标志是开凿了以克孜尔佛教石窟为中心的佛寺,塑造、绘制了供膜拜用的佛教塑像和壁画,还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佛学大师。龟兹佛教塑像和壁画经历从模仿到本土化的过程,先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后出现龟兹风的雕塑艺术。乐舞艺术和石窟壁画艺术是龟兹文化的代表。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始于3世纪,终止于12世纪,前后800多年,目前遗址有10余处600多个,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土拉石窟等,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中约有80个窟内存壁画,内容包括佛说法图、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等。龟兹壁画在充分吸收印度、波斯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具有中原汉地佛教的内容,其壁画经历了由中原画风到本地民族化的发展,如人物造型在晋唐时期已经明显有“头部较圆、额骨宽扁,五官集中”[12],具有龟兹人的头部特征。龟兹乐的源头是天竺乐,传入龟兹后经过吸收、改造形成了以五弦琵琶为主,由诸多乐器演奏,充分发挥合奏与和声艺术效果的龟兹乐。龟兹乐使用的乐器有20多种,吸收汉人的笙、排箫、筝、鼗鼓及羌人的羯鼓。6世纪龟兹艺人苏祗婆将“五旦七声”和琵琶技艺带入内地,给中原的音乐理论和器乐演奏注入活力,使中国传统五声阶(宫商角徵羽)得到补充。至隋朝龟兹乐被列为宫中七部乐之一。唐朝时定十部乐龟兹乐也在其中。唐朝诗人笔下“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反映了西域音乐对内地民间乐风走向的重要影响。同时,龟兹乐也是道教音乐的重要源头,还传播到南方和东南亚各国。
龟兹舞蹈同样对中原地区影响很大,在龟兹舞蹈艺术中最具特色的是《胡旋舞》《狮子舞》《鼓舞》等。《胡旋舞》源于中亚,其特点是突出一个“旋”字,飞速旋转的舞蹈场面在今天的新疆舞蹈中随处可见,经过不断改造最终沉淀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中。从隋朝七部乐到唐朝十部乐的“坐部伎”“立部伎”,龟兹乐一直在隋唐音乐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代大诗人元稹《连昌宫词》曰:“逡巡大遍凉州徹,色色龟兹轰录续。”
4.于阗文化圈。于阗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于阗国包括现今的和田市、洛浦县、墨玉县。于阗文化是典型的绿洲农耕文化,早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是过着农耕生活的塞人[4]25。有关于阗的民间文化《大唐西域记》载,“俗知礼仪,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国尚乐音,人好歌舞”[4]27。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于阗,此后佛教在于阗广泛传播,由盛到衰延续一千年。于阗佛教文化是佛教集造型艺术、佛教音乐、佛教经典、佛教寺庙建筑和佛教仪式为一体的宗教文化。《法显传》写道,其国民“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描绘的正是举国举行行像仪式的情景。于阗国的行像仪式是举国出动,成为全国性的盛大宗教节日[13]。
于阗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文化交流频繁,各种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唐统一西域后,于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汉语文、汉职官制度、汉族信仰习俗都在于阗流行。于阗王被唐王朝赐予李姓,其“衣冠如中国”。和田曾出土属五代时期的彩棺,四面绘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表明汉民族的民间信仰已传入于阗,并被当地居民接受。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仅中原文化影响于阗文化,于阗文化也在影响中原文化,其中美术上的凹凸晕染法是于阗大画师尉迟乙僧父子传入中原的,《历代名画记》曾给予高度评价,“国朝画可齐中古,则尉迟乙僧、吴道子、阎立本也”[14]。斯坦因在策勒县北唐代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幅壁画《龙女图》:画面中心人物是一裸体美女,她佩戴臂环、手镯、项圈等饰物,站在莲花池中,右手抚乳、左手置腹,池中还有两个裸体小男孩和一只水鸭。此画被研究者称为古代东方艺术的杰作,它向人们展现了四个地区艺术风格的巧妙结合,即印度本土艺术、犍陀罗艺术、西亚艺术和中原艺术。印度艺术影响表现在龙女的装饰是古代印度艺术作品中特有的;画面的女性以手遮乳和腹,是中原绘画艺术和传统观念的写照;犍陀罗艺术表现在壁画的形式和构图上,男女像比例不恰当,女大于男是犍陀罗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西亚艺术的影响主要是女性下身的遮羞叶,中亚和中原地区绝无此习惯。
吐蕃在于阗统治了半个世纪,于阗本土文化也被迫发生了一些强制性改变,吐蕃势力退出于阗后,还有不少吐蕃人留在于阗,其文化完全融入于阗文化,使于阗文化意蕴更加深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随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虽然于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较大的差异,但是传统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只是这种关系有时紧密、有时松散。
于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西方多民族、多文化汇聚的地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了各种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文化、以古代印度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和西域本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层层交叠[15]23-29。
(二)漠北蒙古高原时期的回鹘文化(840年回鹘西迁以前)
回鹘,唐代以前称袁纥、韦纥、乌护、乌纥等,起初为突厥臣属,隋唐之际当东突厥汗国日渐衰弱时在今色楞格河流域迅速崛起,744年骨力裴罗统一回纥各部,建立回纥汗国(788年改回纥为回鹘)。回鹘以游牧文化为主,“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16],国人“擅骑射”。后与唐朝建立了密切联系,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通过绢马贸易以及与唐“累代姻亲”等,内地农耕文明开始传入并影响回鹘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史料记载,“葛勒可汗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建筑了富贵城。”[17]《辽史》也记载了唐代好几个回鹘城和回鹘可敦城,这些城市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还有大片的农业区,说明回鹘人的生活方式已经由游牧转向半游牧半定居,汉文化已经对这里的游牧文化有了一定的影响。回鹘汗国建立之初甚至西迁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九姓回鹘可汗碑》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之后采取突厥儒尼文作书面语。回纥起初信仰萨满教,763年牟羽可汗带回了在洛阳传教的摩尼教僧人,摩尼教开始在回纥汗国迅速传播,之后摩尼教被定为国教。
(三)高昌回鹘文化圈与伊斯兰突厥文化圈(840年至16世纪中叶)
回鹘西迁是西域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840年西迁的回鹘,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高昌回鹘王国[注]西域三十六国以及高昌回鹘汗国、喀剌汗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今天的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高昌历史上早有汉人居住,汉文化氛围浓郁。而回鹘早在漠北时期已深受汉、粟特文化的影响,西迁后在与当地居民融合的过程中继承了当地各种文化成分,并加以改造发展,创造了以文化混同为特征的新民族文化形态。西迁之后高昌、回鹘的主体成为一个农业民族,但往日游牧生活的价值观仍被保留,汉文正史称其“俗好骑射”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受汉文化的长期影响,儒家的忠、孝观念和“天人感应”思想成为其道德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也逐渐取代摩尼教成为主要宗教。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王国,见高昌一城就有佛寺50余座。至今仍存在的很多佛教遗址、大量出土的回鹘文佛教经典都足以说明当年高昌回鹘佛教盛行。不仅如此,高昌境内还流传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萨满教等诸多宗教。王延德曾见当地人“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18],可见萨满巫术也十分流行[19]354。各种宗教文化并存,带动了整个王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回鹘文本《弥勒会见经》被认为是戏曲艺术的雏形,在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流行于民间的散文史诗《乌古斯可汗传》在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经加工整理定型,具有重要价值。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使迁居当地的大批操突厥语各族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入农业定居,同时操突厥语民族与当地土著民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当地土著民突厥化。伊斯兰教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开始渗入,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开始了操突厥语诸部族伊斯兰化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一种以操突厥语系各族原有文化特质为核心、以伊斯兰教为表象、吸收各种文化养分而成的新文化体系[15]377。随后喀喇汗王朝与于阗佛教王国之间爆发了宗教战争,经过长达40多年的战争,11世纪初于阗佛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兼并,伊斯兰—突厥文化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范围。之后在西辽政权(1124-1218年)时期,由于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在同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传播,尤其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迎来了第二次传播高潮。东察合台汗国(1347-1680年)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为笼络突厥语诸部,改信伊斯兰教,率领16万人皈依伊斯兰教,是最早归信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其继承者黑的儿火者汗继续采用强制手段在天山北推行伊斯兰教,佛教的文化防线被冲破,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北部、东部地区传播。
虽然两个文化圈基本都说突厥语,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其文化大不相同,高昌回鹘文化圈以多种宗教和多种语言文字并存为特点,喀喇汗王朝文化圈以伊斯兰—突厥文化为特征。直至16世纪中叶包括哈密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改信伊斯兰教,天山南北各地的畏兀儿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文化和心理素质逐渐趋同,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逐步统一,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开始逐渐形成,维吾尔族文化逐渐趋于统一。
(四)信仰伊斯兰教后的维吾尔族文化(16世纪中叶以后)
16世纪在叶尔羌汗国时期,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圈与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文化圈完成统一,至此伊斯兰教在新疆完成了整体化的进程,深刻影响着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影响不能根本改变维吾尔族的文化基质[20]。在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伊斯兰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民族古老传统文化积淀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十二生肖动物记年的民间历法、诺鲁孜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萨满教遗存在当今的民族传统中仍然随处可见。维吾尔族中仍有巴合西、达罕等萨满巫师占卜看相、念咒跳神、驱鬼治病的习俗,而达罕在跳神时舞蹈动作中有两手合十、莲花手等姿态,实际是源自佛教的娱神舞蹈。此外,萨满教的原始图腾崇拜、万物有灵以及各种禁忌和法术在民族传统风俗中均有大量反映。新疆文化具有传承性,虽然一些文化发生了断裂,如佛教文化,但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诸如民居文化、饮食文化的承袭以及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民族性格等,都通过潜移默化的内在化过程沉淀在新疆民众的潜意识底层。
三、结语
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不等于伊斯兰文化。在新疆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1000多年,对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等地来说,佛教文化甚至影响了约1500年。伊斯兰教从9世纪中后期传入新疆,其历史也只有1000年左右的时间,到16世纪中叶成为主要信仰宗教。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具有悠久历史、丰富的非伊斯兰文化遭到人为破坏,中断了具有1000年发展历史的文化、艺术传统。
维吾尔族传统文化是融合的文化。从维吾尔族的族源发展史可知,维吾尔族文化首先是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维吾尔族自始至终不是单一民族,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原住民与回纥(丁零、乌揭、高车、铁勒)等的不断融合发展。其次,维吾尔族文化是东西文化的融合。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聚在此,都对维吾尔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合。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在维吾尔族的发展史上相继登场,并影响深远,虽然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但是多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在维吾尔族文化中消失,只是成为底层文化仍然发挥作用,麻扎崇拜就是典型的例证。
维吾尔族传统文化是复合文化。它是原住民文化、汉文化与回鹘文化融合、后在伊斯兰教时期开始逐步伊斯兰化的复合型文化,其中既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影响,也有四大次生文化圈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层次的文化。新疆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多种文化类型并列的复合型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些文化类型受惠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汉代以来中央政权统一西域有密切关系[4]9-10。龟兹盛行小乘佛教,龟兹乐舞闻名于世,苏莫遮广为流行;于阗盛行大乘佛教,以尉迟乙僧父子为代表的于阗画派的凹凸晕染法对中原画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鄯善是两种文化并行的地区,但汉文化影响很大,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与汉代至魏晋时期屯垦有关;高昌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中西诸种文化大汇聚、大融合,通过移民、屯垦、通贡、经商等途径所形成的高昌文化圈内中原汉文化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大部分是自古就有的,也有从别的文化借入的,不论是外来的或是产自本土的,都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并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必然具有一定的“惯性”和相对的稳定性。自漠北回鹘时期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以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圈,东西文化交流交融不平衡形成的鄯善、高昌、于阗、龟兹四大文化圈,以及高昌回鹘文化圈和伊斯兰突厥文化圈的共同影响下逐渐形成,伊斯兰文化的传入深刻影响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这是客观事实,但伊斯兰文化并没有改变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新疆各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其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