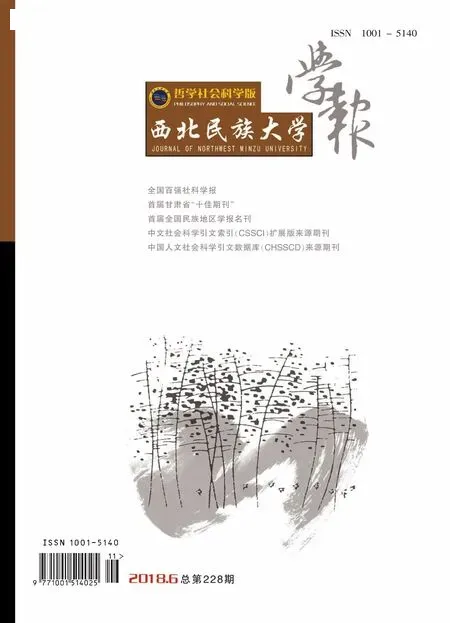汉语东巴经《五方五帝经》的发现及其价值
张春凤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241)
纳西族生活在西南滇川边界,周边少数民族聚集。纳西东巴经是纳西族的宗教经典,它不仅记录了纳西语,还记录了生活在周边的民族语言,著名的东巴文专家李霖灿把这类不记录纳西语的经典归入“异族语言经典”,他将此并分为西藏语文、汉族语文、民家语言、傈僳语言四类[1]。目前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西藏语文,和继全教授将此称为“藏语音读文献”[2]。从总量上来说,藏语音读文献数量最多,汉语文献次之,其他语言的文献较少。汉语文献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语东巴经,一种是汉籍东巴文译本。汉语东巴经是指用东巴文记录的汉语,直接采用的是音译模式。汉籍东巴文译本是采用意译的方式,记录的内容是汉族典籍,而记录的语言还是纳西语。如和继全发现了一本东巴文译本《玉匣记》之“六壬时课”,记录的语言是纳西语,该经典记录的也是一本汉文古籍。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汉语东巴经《五方五帝经》,虽然和《玉匣记》之“六壬时课”一样都来源于汉文古籍,但《五方五帝经》是用东巴文记录的汉语,只参杂了少量纳西语。
一、《五方五帝经》的发现
李霖灿先生首次在东巴经典籍中发现了汉族语文文献《五方五帝经》。他把汉族语文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用汉文,如“犬”“上”“下”等字都变成了么些族的音字。另一类文字则是用么些文字记录汉语的经文。《五方五帝经》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发现的全文用东巴文记录的汉语经典。除了李霖灿提到该经书以外,未曾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笔者在整理东巴经时,偶然发现了一本记录汉语的经典,经过辨别分析,当是李霖灿所说的《五方五帝经》。
(一)关于《五方五帝经》的考证

综合上述三个信息,笔者发现《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15卷《延寿仪式·送龙》前半本经书具备上述三个特征。该译注前有一段内容提要:“本古籍前半部分是以汉话送龙,由于读音和汉语差别太大,有的能译,有的无法译。不能译者,用译音处理。”[4]正文的内容提到五方五将军,亦有穿红袍,骑红马的句子。经书正文第一页钤印了“和世俊”,经书末尾跋语提到是梭补余登东仔的经书。梭补余登东仔正是和世俊的法名。经文中确实存在前文所述的为汉字“去”所造的东巴文。三个证据完全符合,因此可以证实《全集》中《延寿仪式·送龙》的前半部分即是李霖灿所说的《五方五帝经》。为了区分《延寿仪式·送龙》的前半部分经文和后半部经文,前半部分经书仍然使用李霖灿的译名《五方五帝经》。
(二)《五方五帝经》的内容
从《全集》中的释文来看,《五方五帝经》主要讲述了五方(东南西北中)龙喜欢人世间,五色(花、赤、白、青、黑、黄)将军穿对应的五色战袍,戴着五色帽,扛着五色旗,骑着五色马。东巴要把身穿五色战袍的大将军送回至各个方向,最后除秽祈福,念诵咒语。《延寿仪式·送龙》的后半本经书的内容是前半本的改编本,后半本记录的是纳西语,送龙时使用了纳西族本土的神灵系统,最后达到求福保佑的目的。
《五方五帝经》经文中出现的五方、五行皆借自汉族,所谓的“龙”也是汉族龙。[注]东巴文中的“署”,也可以翻译为“龙”,但更接近印度的“纳伽”,与汉族龙无关。可参见戈阿干《纳西象形文“龙”》,载于《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5期。祭祀五方五帝的习俗在汉族生活当中由来已久,根据《五方五帝经》的特征可以找到对应的道教文献《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
东方灵威仰,号曰苍帝,其神甲乙,服色尚青,驾苍龙,建青旗,气为木,星为岁,从群神九十万人,上和春气,下生万物。
南方赤飘弩,号曰赤帝,其神丙丁,服色尚赤,驾赤龙,建朱旗,气为火,星为荧惑,从群神三十万人,上和夏气,下长万物。
中央含枢纽,号曰黄帝,其神戊己,服色尚黄,驾黄龙,建黄旗,气为土,星为镇,从群神十二万人,下和土气,上戴九天。
西方曜魄宝,号曰白帝,其神庚辛,服色尚白,驾白龙,建素旗,气为金,星为太白,从群神七十万人,上和秋气,下收万物。
北方隐侯局,号曰黑帝,其神壬癸,服色尚玄,驾黑龙,建皂旗,气为水,星为辰,从群神五十万人,上和冬气,下藏万物。[5]
从《五方五帝经》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内容比较来看,前者更具口语色彩,是对后者的编写。其中《五方五帝经》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在五方的称呼、干支、颜色、坐骑、建旗等内容上出现了重合,但内容并非完全一致。[注]本人在比较了《五方五帝经》和《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关系后,得出《五方五帝经》的核心内容基本来源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但在故事主角和方位上发生了改变。《延寿仪式·送龙》下半册则是对《五方五帝经》的再次创作和改编,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差异较大。从李霖灿的文章中可知,这本经书是和世俊东巴创译的,是一个翻译和创造的过程。在《全集》第15卷经书《延寿仪式·仪式规程·是卢神所说的》是一本记录举行延寿仪式的规程的书,也是和世俊东巴所写,与《延寿仪式·送龙》属于同一套书。和东巴在跋语中提到:“这是一套延寿仪式的书,是自己写的,与其他人的书不一样。”[4]这里所指的不一样也包含这本《五方五帝经》的特殊性。《五方五帝经》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本东巴经中主体记录汉语的经书,在文献、语言、文字、宗教研究上的价值都不可小觑。
(三)关于经书的作者
和世俊,鲁甸新主村人。他不仅会东巴文经典,而且法事、书画和占卜样样精通,曾创造了记藏文的音字,并用之记《消灾经》一部。他写的《祭祖经典》被李霖灿先生当作民国三十二年调查么些族(即现在的纳西族)迁徙路线的主要依据[1]。从中可知,和世俊是一位善于学习和创造的东巴,不仅精通藏语,会汉语汉字,在此基础上还写了藏语东巴经和汉语东巴经。
二、《五方五帝经》的价值
(一)语言学价值
1940年董同龢最早记录的丽江汉语方言,记录的是丽江七河乡的语言[6]。尽管《五方五帝经》这本经书没有明确的纪年,根据和世俊东巴的生卒年(1860—1931),若东巴15岁开始抄写经书,可以大致推断出经书的抄写时代在1875年至1931年之间,记录的纳西汉语方言比董同龢调查的时间要早一些,记录的地点是鲁甸村。这是目前为止最早记录的鲁甸汉语的东巴经。
尽管东巴经的翻译和原东巴经之间存在语音差异,但是这本经书的释读者是和云彩东巴,他也是鲁甸村人,从记录的语音来说相对接近原貌。《五方五帝经》最为典型的语言变化是语音纳西化,记录的汉语都是单韵母,无阳声韵韵母,无介音。记录的声母还留存了中古汉语的印记。记录的汉语声调受到纳西语影响,变成了纳西语的四个声调。在语法上也受到纳西语的影响,语序上既有符合汉语规范的语序,也有受到纳西语影响后的语序,经书中还有语码转换的现象。经书语言通俗易懂,口语色彩浓厚。经书中保留了撮口呼,与昆明话差异较大,这也佐证了纳西汉语方言与昆明话的历史来源相异的观点[7]。
此本经书尽管记录的是汉语方言,但属于已经发生了语言接触后的汉语。它在语音(声母、韵母、声调)、语法上发生了变化,兼容了汉语和纳西语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它为研究纳西语汉语接触,纳西汉语方言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文字学价值
常见的东巴经中语言和文字对应关系复杂,文字单位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五方五帝经》用东巴文书写汉语,在行款布局、对应语言单位上都深受汉语和汉字的影响。使用的文字以东巴文为主,还掺杂了少量哥巴文。全文多数使用七言或者九言的句式,从行款布局上来说很规整,一般情况下,一栏分为两行,上下两字对应。全文采用假借的方式记录汉语,文字单位之间严格分离。从文字记录语言单位上来说,基本达到一字一音节的对应关系,即一个字符记录一个汉语音节。字词关系和行款布局的特点与藏语音读文献的情况非常接近[1]。
经书中还出现了特殊字,包括音变字和切音字,这些新字的产生正是为了解决东巴文记录汉语时产生的“不适应”而设计的,是文字接触的产物。李霖灿在《么些象形字典》谈到“古宗字”[注]古宗是纳西族对西藏的旧称。时说他字典中收录的都是和世俊东巴在写藏语东巴经时创制的切音字。这本经书虽然不是藏语东巴经,却也是记录其他民族语言的材料。和世俊不仅为藏语文献创制了切音字,还为汉语东巴经创制了切音字。
这本经书的发现为文字接触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探索文字兼用和文字借用现象有着重要意义,它为民族文字中切音字的来源,切音字的发生动因,切音字的流通范围提供了鲜活的实例。
(三)文献学价值
以往的东巴经研究关注的是纳西语东巴经,对于用东巴文书写的其他语言经典少有关注。藏语东巴经的发现开辟了非纳西语东巴经研究的先例,汉语东巴经的发现则丰富了东巴经的文献类型。以往认为东巴经语言和文字的对应关系受到时间、地域、体裁等方面的影响,《五方五帝经》的发现,说明东巴经的语言和文字对应关系还受到记录语言种类的影响,这也应成为研究东巴经典语言和文字关系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宗教学价值
纳西族信仰的宗教以东巴教为主,同时还兼容了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有些纳西族地区东巴、喇嘛、道士并存。《五方五帝经》这册东巴经的内容揭示了东巴教在宗教交流中引进了部分道教的经典,东巴学会了道教的经典及仪式,并根据纳西本土的原始宗教改编成新的经典《延寿仪式·送龙》下半册,可以说是和世俊东巴学习汉族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一个创举。由此可以反映东巴教与道教之间存在文化传播和接触。《五方五帝经》是研究道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材料,是东巴教吸收和借鉴其他宗教的佐证,是纳西族和汉族之间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