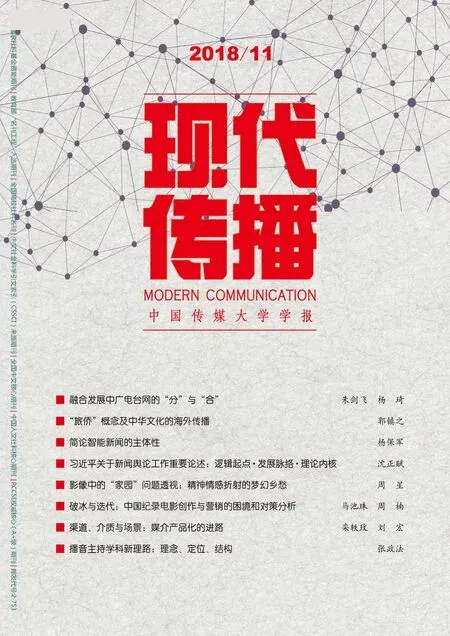从反映真实到象征架构:网络环境的信息可信度评估*
■ 潘 霁
数字媒介使线上的象征符号逐渐挣脱了本来在线下物质现实中的所指,大量“自由漂浮”在网络空间的信源符号,其原本对应的线下信息把关程序大多已经失去了效力。①符号与符号之间得以以更为自由甚至是“玩乐”的方式进行重新组合搭配,诸多新奇的交往和传播场景就此在网上不断涌现。与此相关,越来越多网络信息的原创来源、转发来源和网友个人再生产的内容同时混杂地呈现于同一交往空间中。传统媒体组织、政府机构、个人信源和基于计算机算法的技术信源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复杂的并置或多层的嵌套结构。多样化信源对信息可信度评估产生了影响也因此出现了多重的交互。具体考察某一特定信源对信息可信度评判的影响时,越来越难以脱离其所在的复杂信源结构来加以评估。最后,随着网络技术的使用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媒介使用对可信度评估的影响方式及其背后机制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媒介使用化作构成日常的多样化生活实践。作为后果,媒介本身在日常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不引人注目,而使用行为与特定地点的关联也愈发无关紧要。忽视这种改变使如何理解现有的研究发现充满了争议。为了能在“任何人能就任何事和许多人说任何话”的网络环境中生存,为了更有效度地考察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判,有必要对大众媒介时代媒介可信度研究背后的假设做出根本性的拓展和修正。②
现有网络可信度研究多以控制实验法检测特定的传播内容某些特定属性(语体、引用、语言等)或信源线索(媒体类别、个人权威等)对信息可信度评估产生的效果。③控制实验的逻辑背后,线上象征符号被假设为彼此孤立地存在于“真空”环境中,并逐一对应指涉线下物质性的“现实”。可信度的评判依据作为反映的符号与被反映的“现实”之间彼此对应的严格程度。实际上,数字网络技术的中介化过程已经使大量异质的象征符号不断喷涌而出,同时自由地漂浮在同一网络空间中。数字网络空间中象征符号的“狂欢”恰恰“松绑”了符号与实体所指间原被普遍认定为理所当然的纵向关联:象征符号与所指“现实”间的纵向关联及其本质上的主观任意性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化体现。这种本质性的纵向“松绑”使传播实践有可能更有创造性地以玩乐的形式重新设置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横向关联,并挪用人们早已熟悉的象征符号积淀生产出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诡异”的新社会交往场景。原有信息或交往被置于新的数字化场景后往往能生成新的意义。网络环境中同一交往时空由符号与符号间横向关系构成的象征结构,作为信息传播的社会场景对于信息的可信度评估正起到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虽已有文献讨论了网上不同性质的信源符号间复杂的交互关系④,但鲜有学者从更长时段着眼考察由数字技术生成的网络文化中稳定且重复出现的符号结构本身——更遑论这样的符号结构如何作为交往传播场景对信息可信度评估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现有可信度研究的文献也多将媒介可信度、信息内容可信度和信源可信度分而析之。⑤分析假设信息内容、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可以清晰地加以区分并彼此独立发挥作用。但在数字网络技术条件下,媒介技术渠道本身既可成为信源也有能力按算法生产信息内容,信息内容脱离了技术中介和信源根本无法理解,而媒介组织、网民个人和平台算法之间也越来越难分彼此。不只是技术渠道、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紧密地融合,连信息生产者、发布者和消费者角色间原本的“楚河汉界”也正迅速地瓦解。三分法的假设对理解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而言越来越得不偿失。最后,目前关于媒介使用如何影响可信度评判的文献大多认为,更多的媒介使用可以提高用户对媒体的参与度(involvement)或媒体粘性(affinity)并由此影响可信度的评估。⑥该解释假设媒体使用构成了与其他生活实践并列的特殊形式,对媒介全面融入日常生活的新技术条件缺乏充分的解释力。此外,媒介使用与媒介参与度的关联及媒介参与度与可信度评判的关系都亟需更为扎实的理论解释。
鉴于此,本文提出将特定社交网络文化中由网络文化原生的信源符号构成的稳定象征结构概念化为“媒介框架”。通过借鉴戈夫曼脉络下的框架理论,本研究旨在修正现有可信度研究中的“反映论”假设及研究对内容、媒介和信源的三分法,厘清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中特定信源符号与社交媒体符号环境整体间复杂的交互规律,并根据框架与其所属文化积淀的内在关联就媒介使用行为对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影响方式提出更符合网络条件的理论解释。
一、可信度概念及其解释力危机
一般说来,信息可信度被学界定义为“(信息)值得信任的程度”⑦。实证研究在对“可信度”概念进行操作化时,研究者常将“可信度”与“值得信任的程度”“真实准确”“诚实有信”“权威严格”“完整全面”“公正平衡”等具体指标关联起来。⑧详加考量指标含义,可以发现文献中可信度的指标大都指向了信息符号与物质“真实”之间彼此对应关系的不同侧面:这种对应关系的精确程度、涉及范围的广度或保证对应关系能长期稳定存在的体制化程序。作为可信度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这种对应关系循柏拉图的脉络预设了“物质真实”的首要性及符号呈现“依附”于物质真实的次要地位。信息可信度被设定为对象征符号与物质真实之间不对称关系的评估。
但数字网络技术尤其是经由社交媒体实现的传播条件从诸多方面刺激学者去反思质疑上述“反映论”视角。首先,数字技术从空间维度凸显并进而“解绑”了象征符号与物质真实间原本被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视而不见”搁置起来的对应关联。数字技术使信源符号更易篡改和模拟——数字化的篡改也更加难以察觉。⑨这使符号本身的“游戏”在网络空间中层出不穷。不少学者开始担忧随着网上符号与其线下能指间的对应不断松动,线下生活中各种传统的信息把关机制在网络环境中难以维系,网上信息可信度正面临大幅度下滑⑩——或者说这意味着对可信度的概念界定本身需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做出根本的修正。其次,数字化传播辩证地融合了异时和即时性的时间特征。网络化时间使物质真实与符号呈现之间彼此更为紧密地“无缝对接”。数字网络环境中,象征符号与物质现实间实时发生不间断的双向转换,符号的物质意义和物质的象征性都不断增强。象征符号与物质现实的纠缠联动,不断生成涌现出与之前断裂的离散时刻和新奇场景。与网络时代新的时空设置相应,研究需以特定时刻由同时在场的象征符号形成的符号结构替代物质真实与符号呈现之间原本非均衡的对立关系,作为可信度研究提问的基点。
与“反映论”关照下对“可信度”概念的定义一脉相承,现有文献对可信度概念的解析常将信源可信度、媒介渠道的可信度和信息内容的可信度区分对待。其中,媒介可信度涉及技术渠道和特定信息传播组织是否值得信赖。信源可信度常牵涉作为信息来源的个人特点(年龄、性别、教育、种族和信用记录等)。而信息可信度研究更多聚焦于特定信息内容本身的特征,例如信息的质量、准确度、及时性甚至内容表达的语言风格等。概念的划分为提高实证分析的精细程度带来诸多便利,但同时也无形中假设了信源、媒介和信息内容彼此独立——不少实证研究甚至证明媒体记者个人作为信源的可信度与媒介整体的可信度之间彼此独立,存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数字环境中媒介渠道、信息和信源的界线日渐模糊,上述三分法引发了难解的争议。首先,不同研究就三者之间的划分标准越来越难以统一。例如,Kiousis在研究中将可信度分解为媒介组织可信度、技术渠道可信度、个人信源可信度和信息内容的可信度。相比之下Flanagin和Metzger研究中涉及的媒介可信度仅指媒体机构或媒介组织品牌的可信程度,Metzger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媒介机构的品牌或者媒体平台在获得知名度后,受众对其可信度的评判过程和结果类似于对个人信源的评估。其次,社交媒体平台信源的数量和种类都更为庞杂,不同信源间形成的关系结构犬牙交错。原创信源和转发信源都可以是个人、组织或技术平台的算法规则。现有研究发现用户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信息时,信息的原创作者与多层转发信源时常同时同地呈现,共同构成了信息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信息的可信度评估最终常取决于由传递信息的各类信源与信息表现形式共同支持的整体体验。各类信源、多种媒体和信息的可信度彼此影响,大大增加了数码空间可信度评判的复杂程度。针对网络空间信源结构的复杂性,Hu和Sundar舍弃了原来的三分法,并提出按照信源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来区分原创信源和转发信源。他们研究发现网络信息本身的特点及原创信源和转发信源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用户对信息可信度的评判。与此相似,Johnson 和Wiedenbeck 在网络可信度研究中区分了“内部”和“外部”信源即内部信源原创信息和外部信源传递信息。
然而即便原创信源、转发信源和信息消费者之间的区分在网络时代也不再理所当然。社交媒体上信息发布的成本极低,信息消费者和转发者都能随时轻易地转变为信息消费-生产者(prosumer)。信息自身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过程本身会生产出作为信息构成的元数据(如浏览量、转发量和点赞等),进而影响使用者的可信度评判。当信息的消费者们被数字技术深度地整合到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去,当生产和流通过程再也无法截然分开时,要清晰地辨认出信息原初的生产者、传递者和信息的消费者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用信息原创信源和流通信源来替代可信度研究现有三分法的方案也面临挑战。
笔者针对上述状况试图突破可信度研究中“反映论”和三分法路径带来的局限。本文结合框架理论的视角提出数字技术的中介化过程和由此形成的网络文化积淀,将特定的符号类型以独特方式彼此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反复在同一交往时空呈现的符号结构。社交网络空间中由同时在场的信源符号共同构成的象征结构,作为整体影响了特定可信度线索身处其中时产生的效果。就此,现有实证研究的发现已凸显信源符号形成的稳定结构对可信度评判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本文观点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
二、复杂信源结构的效果
社交媒体海量信息环境中,为了对线上信息的可信程度迅速高效地作出判断,使用者常需借助可信度判断相关的认知线索(credibility heuristics)来帮助完成认知任务。相关实验发现不同的可信度线索可以通过征用和激活网民记忆中已有的认知结构,作为认知捷径有效地帮助人们判断网络信息的可信程度。社交媒体平台上,类似认知捷径包括社会推介线索(如朋友数、评论数、点赞和转发数等)、时间线索(如更新频率、发表时间和最新评论等)、声誉线索(业绩历史、第三方认证和诚信记录等)和数字媒体系统自身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字轨迹等。
更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符号线索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关联形成的稳定象征结构能改变对信息可信度的评判。其中,Melican 和Dixon等人的探索发现取决于媒介技术的中介化过程,不同的可信度符号线索会以不同方式构成独特、可辨识、重复出现且形态相对一贯稳定的符号结构。这种符号结构影响了用户对置于其中各类信息的可信度评判。一脉相承,Sundar的研究突出了这种象征符号结构作为元传播讯息(meta-communicative)的属性。Sundar强调存在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在特定的故事情节叙述之外”作为整体塑造了用户对网上新闻故事的可信度评判。换而言之,形成复杂符号结构的这些复杂“因素”是在信息传播的具体内容之外,以元传播讯息的方式在整体上发挥作用并影响可信度的判断。随后,Xu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象征符号结构不断累积组合的特征。通过实证研究,Xu发现社交媒体的社会推介线索和及时性线索对于信息可信度评判有“组合或累积效果”(combinatory or cumulative effect)。具体而言,Xu指出信源符号对于信息可信度评判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其他符号线索在同一平台上的组合结构以及这些符号结构长期获得的历史积累。“组合”的说法强调了各种符号时空并置的结构形态,而“积累”则提示了符号结构(或其构成要素)的历时性积淀对于当下可信度评判的重要意义。从更微观角度,Bucy考察了特定网络可信度线索在具体的象征环境中发挥效果的机制。Bucy揭示出特定信源对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当下所处的媒体符号环境是否与信源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一致。相比那些明显是被“嫁接移植”到网络空间中的“外生信源”,原生于赛博文化的“本地”信源在网络平台上对用户信息可信度评判能产生更大的影响。针对元传播符号结构的来源,Choi和Kim通过对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的分析将符号线索形成的结构与特定媒介技术的中介化过程关联。他们发现各种媒介技术中介化过程所特有的时间与空间设置塑造了用户对可信度的观念和评估。
通过回顾现有可信度研究文献,笔者发现不同学者已各自揭示出数字网络环境中的象征符号结构产生于传播技术独特的中介化过程,具有元传播、组合性和文化积累性等属性:符号结构与特定信源符号在文化根源上的一致程度决定了后者对可信度评估的效果。然而,这些实证发现目前还星罗散布在可信度研究文献中,并未被学者从统一基点入手将其聚合并催生出新的理论建构或分析框架。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基于概念反思和对已有研究的整合,将社交媒体平台上由信源符号线索构成的独特的象征符号结构概念化为传播内容背后的元传播“框架”。新媒体平台上的个别信源符号被视为置于框架中的认知线索。从戈夫曼脉络的框架理论出发,笔者提出了一组相应的研究命题以求开辟可信度研究新的路径。
三、框架塑造可信度评判
为了在可信度研究文献中对符号结构产生的效果进行理论化,笔者借鉴了戈夫曼脉络下的框架理论。循此脉络,框架被定义为“起中心组织作用的观念或能生产意义的故事主线”。究其作用,框架不仅提示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应如何诠释理解,更可以帮助人们“寻找、观察、标签并辨认”日常空间和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场景。根据具体社会场景或媒介文本,不同的“框架符号”(例如隐喻、关键词、信源线索和图片等)作为构成框架的显性表征标志了框架在社会情境或媒介信息传播中的存在。框架本身作为中心组织原则或主题则隐于文本背后以特定结构将这些显性的表征符号组织起来,形成内部逻辑一致的意义叙事。
由框架理论出发,符号结构形成的框架能影响人们如何界定和理解在框架统摄范围内发生的各种信息传播过程或社会交往。现实生活大多数传播过程都发生在各种框架中,框架产生于实践者与广义技术各种形态的耦合,其效力愈强则对于框架中人的可见度就越弱。隐于交往和信息传播背后的框架提示人们应按什么规则理解框架内发生的显性的信息传播或社会互动。据此,同样的信息或交流行为若置于由不同象征结构形成的框架中自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将此理论命题用于分析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判,可以推论社交媒体技术独特的中介化过程产生了特定的网络化交流实践和网络空间文化,源于网络文化积淀的符号结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框架影响了人们对特定可信度线索及线上交往活动的意义生产,而这种意义的生产转而改变了特定可信度线索对信息可信度评判可能产生的效果。
以上系列命题强调了符号与符号间横向的关系结构对信息可信度判断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提出上述命题,本文将更为复杂的“框架动态”(framing dynamics)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了信息可信度的研究,开拓出新的洞见和研究问题。“框架动态”包含了来源与不同文化积淀的框架结构之间从相互竞争对抗到彼此融合的各种可能。同一时刻处在同一网络空间中,异质象征结构之间的框架竞争(frame contestation)、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框架融合(frame merging)等更为复杂的框架动态关系都可能对框架中信息的可信度评判产生影响。引入关于框架动态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及概念各自相关的分析架构)为探索网络环境中原属异质框架的象征符号之间如何混杂共处,及多样符号混杂共处的复杂结构如何对网上信息的可信度评估产生效果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工具。此外,从框架理论入手提出的命题也将学者注意力聚焦到源于赛博文化积淀的各类象征符号本身在数码时空中的创造性关联。这一面向打开了可信度研究在“反映论”之外的新视野,将更多纯粹为象征符号层面具有实验性质甚至“玩乐戏谑”式的符号关联实践纳入了可信度研究的考虑范围。同时,这种象征符号间关联的语法规则又与数字技术独特的中介化过程密不可分。 最后,通过将不同符号间相对稳定的结构与传播技术的中介化过程联系起来,上述研究议题也将数字网络技术本身在架构传播方面的“语法”以及技术语法在符号层面的可视化呈现突显出来。
四、框架的文化根源与媒介使用
框架理论还提出作为框架的象征符号结构及其构成元素皆来源于特定文化中既有的符号积淀。戈夫曼认为“框架是特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被整合到(现有的)文化体制中”。作为框架来源的文化包含了有组织的符码、信仰、迷思、成见和特定群体成员共享的规范准则。构成框架显性部分的架构符号(framing devices)多来源于框架所属的既有文化积淀和符号资源。而作为框架本身的隐性组织原则和统领性主题则更多与特定文化社区既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价值意义直接相关。
依据框架与文化的关联,本文推导与框架所属同一文化的“原生性”符号更可能构成框架自身的符号结构,成为显性的架构符号标示出其背后框架的存在。相比之下,一眼看去明显非原生于特定框架所属文化的“外来”符号则更可能受符号结构框架效果的影响。落实到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本文提出特定网络空间具有独特的赛博文化。赛博文化中包含该网络空间交流中长期积累的共享符码、信仰、迷思和社会规范等象征积淀。当特定的符号线索被视为原生于该赛博文化时,更可能构成框架自身的象征符号结构(包括显性架构符号或隐形主题)。反之,当可信度符号线索明显自其他媒介文化“引入”而非原生于社交媒体特有赛博文化时,可信度线索对信息可信度评估的作用则更倾向于受到社交媒体框架整体效果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命题强调可信度研究有必要将信源符号与其所处网络本地文化间呈现出来的关系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引入。理论上,这个维度将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实证研究与针对各类赛博文化更为宏观的文化和历史分析关联起来;将网络中大量信源符号按其对可信度评估产生作用的机制细分为原生和外生性符号;并为信源符号与可信度评估间的关系在现有“认知捷径”激活假设(heuristic activation)外,提供了基于框架理论的另类解释。
更关键的是由于文化积淀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作为文化积淀组成部分的框架自然也外在于任何个人而具有一定的稳定一贯性。个人为了迅速调用特定的框架来生产意义以完成认知任务,就需对框架所涉及的文化过程和符号资源积累有一定的熟悉度。唯当个人对特定文化中某一框架所涉及的符号结构较为熟悉时,该框架才可能在个人需获得意义解释时被迅速激活并转换为可供应用的认知基模(schema)。由于个人常会下意识地调用记忆中早已熟知的文化符号资源对环境信息和互动交往作解释和理解,框架实际激活和应用的过程通常不动声色。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媒介使用通过改变人与技术生成的文化符号环境之间的熟悉度来影响其对可信度的评判。现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媒介使用与网络信息可信度间存在相关关系。有学者解释认为媒介使用可提高用户的媒介参与度或增加用户与媒介之间的粘性并进而影响用户对媒介信息可信度的评估。相比基于媒介粘性或媒介参与度的解释,笔者认为媒介使用和符号环境熟悉度间的关联更为直接,也牵扯更少干扰因素。现有研究发现对媒介技术(及其中介化过程形成的文化符号环境)更为熟悉的用户更能理解媒介技术的可信度和局限性;对信息和信源的选择更有把握;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且对用户与媒介互动的规则了解得更为透彻。与此呼应,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发现对媒介符号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影响用户如何解释网络平台上出现的可信度线索。对媒介符号环境更为熟悉的用户会更多调用系统自身产生的符号线索(system generated cues)形成可信度评估:而原生于特定媒介系统的线索常构成了媒介框架自身的组成部分。故此,本文提出媒介使用与用户对媒介符号环境的熟悉度正向相关,用户对符号环境熟悉度越高则媒介框架的效果越强,而框架效果直接影响了用户对框架中信息可信度的评判。基于象征文化环境熟悉度的解释针对网络媒体与生活实践全面深度的融合渗入,避免了将“媒介”视为特定的对象,转而以更符合现象学的视角直接关注通过技术中介化产生的象征符号情境本身。
本文拓展了框架理论的应用范围。在数字网络越来越深入全面地融入日常交往的技术条件下,媒介框架研究的视野需从单纯的内容框架回复到Goffman描述的交往场景概念。本文通过提出将“框架-符号线索”作为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的路径,避免了现有文献中对媒介、信源、信息的三分法在网络时代带来的诸多争议困扰。本研究提出区分构成框架的原生性信源符号与其他明显被移植到框架所属文化环境的异质文化符号,并基于框架理论解释了不同类型的信源符号对可信度评估产生效果的不同机制。基于框架理论中关于符号框架与文化积淀的关联,本文为媒介使用变量在可信度评估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注释:
① Metzger,M.J.,Flanagin,A.J.,& Medders,R.(2010).SocialandHeuristicApproachestoCredibilityEvaluationOnlin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p.60,pp.413-439.
② Callister,T.A.,Jr.(2000).Medialiteracy:On-ramptotheLiteracyofthe21stCenturyorCul-de-sacontheInformationSuperhighway? In A.W.Pailliotet & P.Mosenthal (Eds.),Re-conceptualizing Literacy in the Media Age (pp.403-420).Stamford,CT:JAI Press.
③ Sundar,S.S.,& Hastall,M.R.(2006).NewsCues:InformationScentandCognitiveHeuristic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 (3),pp.366-78.
④ Sundar,S.S.,Bellur,S.,Oh,J.,Jia,H.,& Kim,H.(2014).TheoreticalImportanceofContingencyinHuman-ComputerInteraction:EffectsofMessageInteractivityonUserEngagement.Communication Research,32(1),pp.1-31.Xu,Q.(2013).SocialRecommendation,SourceCredibility,andRecency:EffectsofNewsCuesinASocialBookmarkingWebsite.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0(4),pp.757-775.
⑤ Johnson,T.J.,& Kaye,B.K.(2004).WagtheBlog:HowRelianceonTraditionalMediaandtheInternetInfluenceCredibilityPerceptionsofWeblogsAmongBlogUser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1(3),pp.622-642.Johnson,T.J.,& Kaye,B.K.(2014).CredibilityofSocialNetworkSitesforPoliticalInformationAmongPoliticallyInterestedInternetUser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pp.957-974.Tseng,S.,& Fogg,B.(1999).CredibilityandComputingTechnology.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42(5),pp.39-44.
⑦ Tseng,S.,& Fogg,B.(1999).CredibilityandComputingTechnology.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42(5),pp.39-44.
⑧ Flanagin,A.J.,& Metzger,M.J.(2003).ThePerceivedCredibilityofPersonalWebpageInformationasInfluencedbytheSexoftheSource,ComputersinHumanBehavior,19,pp.683-701.Johnson,T.J.,& Kaye,B.K.(2000).UsingisBelieving:TheInfluenceofRelianceontheCredibilityofOnlinePoliticalInformation.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4),pp.865-879.
⑨ Carr,D.J.,Barnidge,M.,Lee,B.G.,& Tsang,S.J.(2014).CynicsandSkeptics:EvaluatingtheCredibilityofMainstreamandCitizenJournalism.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1(3),pp.452-470.
⑩ Flanagin,A.J.,& Metzger,M.J.(2000).PerceptionsofInternetInformationCredibility.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pp.515-540.Flanagin,A.J.,& Metzger,M.J.(2007).TheRoleofSiteFeatures,UserAttributes,andInformationVerificationBehaviorsonthePerceivedCredibilityofWeb-basedInformation.New Media & Society,9,pp.31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