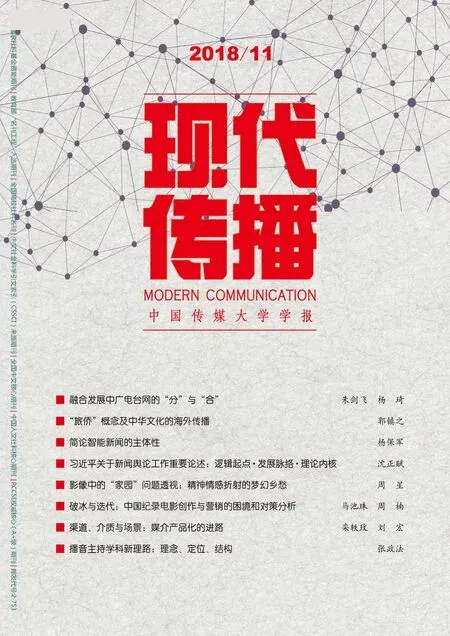作为信仰“装置”的秦汉石刻:一种媒介学的视角
■ 贾 南 芮必峰
石材是世界不少地区先民的符号载体,曾对人类的知识传播、文化传承起过重要作用。我国石刻文化肇自殷周,发展于战国,兴盛于秦汉并延及李唐。石刻范畴向无定论,金其桢先生认为石刻指刻有文字的石头,是石刻文字的简称,亦称刻石①。借鉴其观点,本文研究的“石刻”是指刻有可供识别文字的石质物体,且形式不限。
秦至两汉石刻繁兴,呈现碑、碣、摩崖、石阙、石经、画像题字等多种形式。据统计,秦至西汉(含新莽)留存石刻(有原石或拓本)30余种。东汉时碑碣云起,现存原石或拓本230余种②。借鉴前人汉碑分期,本文为秦汉石刻做粗略分期:嬴秦至汉武帝时期(前259年—前49年)可看作秦汉石刻的滥觞,有秦刻石、摩崖、界域石和工匠标记的各类建筑石料。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前48—106年)为秦汉石刻发展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开始形成;西汉元帝改庙祭为墓祭,东汉明帝改皇家墓祭为上陵礼,墓葬类地下地上建筑渐多;河平三年《麃孝禹碑》(前26年)是现存可考最早的有形制墓碑。东汉中期(106年—144年)为发展定型期,画像石题记仍为最大宗,汉碑逐渐定型;永建三年《王孝渊碑》(128年)是最早自称为“碑”的石刻,汉安二年《北海相景君铭》(143年)是现存最早的形制完整的汉碑。东汉后期(146年—189年)为汉碑辉煌期,碑刻大量出现,数量远超其它类刻石。国内学者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认为石刻(碑刻)作为载体的优势有:坚固耐久、传之久远、空间传播性、开放性以及神圣性的表意系统,其通过文化记忆过程实现文化传播,见证文化传承③。
一、秦汉石刻兴盛的历史背景
农业传统的文明体系中,历法往往是由特定地域耕种的农时决定④,对于历法的信仰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为固定的时间观念。秦时统一历法为《颛顼历》,事实上摧毁了非秦地人民传承千百年的历法信仰和时间观念。
秦汉时期人口大量迁徙,导致原空间观念的解体。首先,秦汉时期有大批农民因战争、政治原因被迫迁徙。秦时全国人口两千万,建阿房宫、骊山墓、筑秦长城、开灵渠等大型工程动辄征迁几十万人,每年兵役徭役征丁不下三百万⑤。汉政府亦数次徙民建设地广人稀的河西地区,据《史记》记载,汉时调上郡、朔方等郡田官和驻边军队60万至张掖、酒泉二郡屯田(《平准书》),后又设居延、休屠二县,征徙戍甲兵18万以拱卫酒泉(《大宛列传》);其次,秦汉户籍制度较战国时期松散。战国时各国以严密的户籍制度限制人户流动,如《商君书》规定“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⑥。而汉时农民却有更籍的可能,《居延汉简甲编》中记载徙民“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⑦。大批人口迁徙,促进了地域间的信息流动,偏向地域性的原始信仰丧失其社会整合力。
秦汉时期社会大变迁造成了时空失衡及信仰缺失,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吉登斯认为,对于变迁中的社会体系,其秩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时空关系的重组;“脱域”机制以“信任”为内在动因,能为时空转化带来的失序提供预期的心理保障。⑧这提示我们,在信仰破碎处重建“信仰”,势必能为社会心理整合以及时空“偕律”重构提供有效的心理保障。
二、石刻媒介与“大一统”空间观念的建构
史家认为夏商周三代奠定了华夏一统的历史基础。⑨李斯又言“天下赖陛下海内神灵一统”⑩。就空间观念而言,“壹家天下,海内一统”,方可谓大一统。
伊尼斯认为“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秦灭六国,建立制度一统的秦王朝。中央集权政治强化了空间控制力,相对统一的版图有利于交通速度和传播速度的提高。陆地交通方面,开拓之地渐广,骑者渐多于乘;水漕既便,海运亦开,已成河海连络之效。信息交通方面,一是设邮亭主传命、烽燧更速之;二是设官私驿传,负责日常信息传递。经历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和大秦建制,秦汉之际“大一统”观念逐渐成形。故董仲舒曰“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1.以一为尊、壹家天下
“大一统”观念“以一为尊”。《吕览·执一》曰“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墨家视“天下之义壹同”为大治,“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墨子·尚同中》)。封山起初是帝王以命名的形式建立人与地域的关系。先秦文献《穆天子传》载:“(周穆)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为了实践大一统的帝国信仰,获得皇权合法性的普遍认同,秦始皇效仿周天子,十年间东巡封禅,立七块刻石,分别为山东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位于河北的“碣石门刻石”和浙江绍兴的“会稽刻石”。
秦始皇刻石铭文极力彰显“以一为尊、壹家天下”的空间观念。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文曰“壹家天下,兵不复起”;作琅琊台,立石刻曰「皇帝做始;万物之纪;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二十九年登之罘「周定四极、经纬天下」;东观刻石曰「振动四极、阐并天下、远迩同度」。三十二年刻碣石门「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天下咸抚」。三十六年上会稽,望南海,立石刻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亲巡天下,周览四方。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
古时区域间和上下层级间的信息渠道不畅,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之于王土往往只是一种想象。而秦始皇封山刻石,旨在为帝国大一统的观念塑造实体化身。帝王巡守、刻石纪迹,在勾勒帝国版图的同时,大一统的王权威仪得以触及社会底层。
2.经略东西、海内一统
秦汉政府看重东极之地,多处立石、刻石标志界域,彰显权威。秦始皇二十八年「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二十九年「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至东观「逮于海隅,遂登之罘」,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西汉末年,政府在东海琅琊郡树立多处界域刻石,如苏马湾界域刻石、东连岛界域刻石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界域刻石。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始征伐匈奴,武功西域。武帝时惟一可考石刻是内蒙古阿拉善的《通湖山摩崖石刻》,刻文“汉武帝诏书、出塞远目、勒石纪焉”等字样,说明这是卫青、霍去病屯军此地抗击匈奴获胜的战功刻石。位于现蒙古国杭爱山的《燕然山铭》,是存世可考的东汉最早“勒石赞勋”石刻。《后汉书·窦宪传》载,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匈奴,班固随军作铭赞功,“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勒石纪功”有代汉封禅之意,“向天地神灵宣告以燕然山为腹地活跃漠北三百年的匈奴政权的瓦解,宣告大汉对此地的占领和征服”。四年后任尚在新疆哈密地区刻《汉平戎碑》以纪功。东汉顺帝时有《裴岑纪功碑》(137年)、《沙南侯获碑》(140年),均是汉兵将在新疆巴里坤地区抗击匈奴所刻立,立于边陲之地,表功之外更有空间上的标志性。
蜀道难于上青天,不与秦塞通人烟。战国时期秦国征蜀,逐渐辟通褒斜道。《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褒斜道作为南北经济战略要道,但逢战事时常被毁:刘邦退兵汉中烧毁栈道;公孙述为固守蜀地拆毁栈道。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汉中太守鄐君开通褒斜、石门,刻《开通褒斜道摩崖》(66年)。东汉中后期栈道屡遭战乱毁坏,亦多次修缮,留《石门颂》(148年)、《李君表》(155年)、《杨淮杨弼表》(173年)等几处著名的开道摩崖。
摩崖是指刻在天然山崖石壁上的文字,因刻字前要磨整石壁而得名。《开通褒斜道摩崖》铭文中记,工程“修路258里,建大桥5座、桥阁630间以及邮亭驿站等建筑68所”,开道实不易,故刻石颂功,也有宣示征服天险之意。如《石门颂》刻文:“坤灵定位,川泽股躬…八方所达,益域为充…禹凿龙门,君其继踪…上顺斗极,下答坤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我国现存最早摩崖是光武帝时《何君阁道铭》(57年),位于荥经(古称严道),是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重要关隘。这条西汉时期开发的商道,起于四川宜宾、经云南德宏至缅甸、泰国最终到达印度和中东。可见,秦汉石刻媒介活跃在中原腹地之外,建构“海内一统”的观念。
3.石刻媒介与大一统时间—空间观念的转向
对于集权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功在开疆拓土,而其志在千秋万世。《史记·孝武帝本纪》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封泰山“上石立之泰山巅”。未明言刻石,故后世皆传武帝所立乃无字碑。然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辞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因铭文以儒家话语“礼义孝仁”入文,且丝毫未受西汉后期至东汉兴盛的谶纬思想影响,说明其可能作于西汉中期。再者,应劭曾出任泰山郡太守(189—194年),故笔者以为记述有一定的真实性。搁置争议,单就文本来看,“四守为郡,八方咸服”,空间“大一统”的意义明确。
西汉末年王莽借“符命说”篡汉称帝,拟封禅泰山以正名。汉长安宫殿遗址出土《王莽拟封禅泰山玉牒》,通体黑石阴刻若干朱字,“封亶泰山、新室昌、万岁壹纪”,表明新兴豪强地主对于“一统之制”(壹纪)有了偏于时间的诉求(万岁)。《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铭文: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永兹一宇,垂于后昆…咸蒙祉福,永永无极。《后汉书·张纯传》中记载:(张)纯奏上宜封禅,曰「受命而帝、必有封禅,以告成功;宜及嘉时…封于岱宗;明中兴…复祖统;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光武帝封山刻石文及大儒张纯之奏书,对于复祖统、传祚子孙、万世传承的强调,表明东汉时期石刻媒介承载的“大一统”时空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时间转向。
三、石刻媒介与“大一统”时间观念的建构
《春秋·公羊传》开篇(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董)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说文》:“统,纪也”。“统”指世代相继、一脉相承,偏重“合其系”。
1.以“统”为本,传承统绪,大始而正本
秦景公墓出土石磬是我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上刻篆文有“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意在追溯祖先来历。《峄山刻石》中有“刻此乐石”,颜师古注“乐石”为乐器之石。柯马丁由此猜测周秦文化中“铭石”特指用于祭祀的石制乐器。周代祭器金文常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作结,如周厉王十六年成鐘、伯克壶、二十六年番匊生壶等。这种垂示“子子孙孙”的信念可能源于华夏先民的“祖先神”信仰——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尤甚,祖先“生时为人、死了成神”,庇荫后嗣。
秦石鼓十件,皆为上小下大、上圆底平的椭圆花岗岩形状,四周铭刻文字用以祭祀。汉代称其为“碣”,因形似鼓,唐代始称其为“石鼓”,沿袭至今。刘星父子在历代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释读的基础上,定铭文为十首祭诗,其主题为:《马荐》《汧殹》《霝雨》《虞人》《作原》《銮车》《田车》《而师》《吾车》《吾水》,是从前9世纪非子受封秦地至始皇创立帝业的大秦史歌。刘星认为秦始皇组织鲁地儒生创作颂诗并刻石,并供奉于秦庙,在祭祖礼仪中歌颂先祖烈公。秦石鼓、石磬体现了君王对于偏向时间的历史叙事的重视。历史叙事是统治者长久掌控时间的一种手段,出于信仰、关乎传承,其目的是“溯源正统、传承统绪”。
东汉统治者为正帝位,写帝纪重传承。汉明帝命班固等共撰《汉记·世祖本纪》,开篇为“光武皇帝讳秀,高帝九世孙也。承文、景之统,出自长沙定王发…皇考初为济阳令”。董仲舒曰“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受皇家“大始而正本”的时间观念影响,世家大族纷纷立碑追崇祖宗鸿业。如《鲁峻碑》有“君讳峻…其先周文公之硕胄,□□伯禽之懿绪,已载于祖考之铭也。君则监营谒者之孙,修武令之子”,《鲜于璜碑》曰“君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汉胶东相之醇曜,而谒者君之曾,孝廉君之孙,从事君之元嗣也”。东汉中后期,这种风气愈演愈烈,门阀豪强以编造贵族世系来维护特权,累世公卿权力垄断严重。
2.身没称显,名存不朽
一种文明若倚重延伸时间的媒介,它的最终追求必然是永恒的时间。嬴政自称始皇帝,冀望“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皇汉武都不懈地追求长生,这种对于时间的执念突出表现为追求不死、不朽。
《汉书·龚胜列传》载,龚胜不愿应王莽征召乃绝食而亡,后世刻石表其里门。刘勰曰“表以陈请”,指故吏门生上表君主,请求刻功德碑石褒奖师长。墓碑为墓主歌功颂德,也可看作广义上的颂功德碑。东汉时举孝廉成为科举选士的重要手段,门生故吏事师长“如事亲”,纷纷为师长立墓碑、功德碑,述美追功。东汉晚期一些墓碑如《孔宙碑》《孔彪碑》《鲁峻碑》《鲜于璜碑》均由门生故吏刻立。这些碑的共性在于:碑阳面刻碑主姓氏籍贯世系官职功绩,颂辞及立碑年月;碑阴铭刻立碑人籍贯、姓名以及出资金额等内容。
赵明诚《金石录》中描述《汉王纯碑阴》“题门生人名,自东平冯定伯而下,文字完好可识者,百九十余人,摩灭不可识者,又九十余人…各发圣心,共出义钱,埤碑石直,刊纪姓名”。故曰“自东汉以后,一时名卿贤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一碑既立,百八十人随之留名千古,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孔宙碑》题名62人;《张迁碑》碑阴题名41人并出资数,《鲁峻碑》刻3列21行,《景君碑》阴刻门生故吏五十四人,并“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蔡邕作《琅琊王傅蔡公碑》曰“身没称显,永遗令勋。表行扬名,垂示后昆”,大一统时间观念对浸淫其中的儒生官吏的影响可见一斑。
“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在豪富资财、士人倾力为名人树碑立传、求托碑阴以留名的媒介实践中,大一统的时间观念跨越阶级,成为集体信仰。
3.中央与地方时间观念的统一
西汉初年分封王国,诸侯国和中央帝国的时间并未统一。这主要表现为纪年方式相异。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始行年号纪年,但诸侯国仍行旧制。现存最早的西汉石刻是河北永平《娄山石刻》,释曰“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经考应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所刻。而《鲁北陛刻石》上铭文“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刘海宇等认为其刻于鲁孝王六年/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诸侯自有纪年显示出西汉初期诸侯王权之大。汉成帝时诸侯王纪年废止,至东汉诸侯王权势萎缩,更无诸侯纪年之说。如徐州土山1号王墓出土黄肠石题凑刻“官十四年省苑伯□□廿六”,王恺先生认为墓主为刘秀庶子楚王刘英,官十四年指东汉明帝永平14年。显然中央加强了对时间观念的统制。
四、连接时间—空间的石刻媒介系统
西汉初年,“各地方各有其所奉之神”;“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诸侯王势力被削弱,中央集权日益加强,政治上已显现大一统气象。武帝采谬忌之策,建构与现世大一统王权相通的信仰:以大一神为“统一至上”神,五帝为神佐。“元封二年及五年修封,祠大一及五帝于明堂,以高祖配”;行《太初历》,“大初元年…至泰山…冬至日祠上帝明堂”。自此,天子以时节封泰山祠太一神,成为汉家重大祭祀礼,汉代“以一为尊、神灵一统”的神道信仰的逐渐成型。《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说明汉时“大一之统”是制度也是信仰,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
社会大变迁下,人命如草芥、人生如浮萍,种种不安定与不真实感都指向一种时空在场感的断裂。石刻媒介建构了大一统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并凭借虚化时空或超越时空的形式勾连时间-空间观念系统,重塑信仰。
1.装置孝道信仰的石刻媒介
西汉中叶,汉武帝重用以董仲舒为主的儒生,以“公羊春秋”为基础,“天人感应”为核心,对儒学进行宗教化改造。为“化元元,移风易俗……加王心于百姓”,元朔元年汉武帝下诏“令二千石举孝廉”(《汉书·武帝纪》)。
西汉中后期改庙祭为墓祭,东汉明帝时,创上陵礼。《礼记·祭统》云“孝子之察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祀祖先是孝义的延伸,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灵魂不灭的笃信。《礼记·祭统》则曰“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可见,依礼为先祖称美是子孙孝道的体现。孝子贤孙修建石质墓祭建筑,题刻铭文美化墓主,借不朽石碑传之千古,显亲扬名,尽终孝义。
新莽-光武年间《孝经》成书,光武帝令期门羽林之士皆通《孝经》。自此与墓葬有关的石刻,以及祠堂前置石阙、室壁雕刻的画像石题记,常以宣扬孝道和子孙孝行入文。如新莽时期用作墓门上方压槛石的《鱼山刻石》铭文:“居欲孝,思贞廉,率众为善,天利之身体毛肤,父母所生,慎毋毁伤,天利之”;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铭》刻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感应章第十六》曰“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道”作用的实体空间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家至官,由亲至君;又因孝悌通神,所以可达虚拟空间“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关于孝的空间观念。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已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孝的时间观念贯穿人的终生,并延伸到子孙后世。《孝经·丧亲章第十八》又言,丧亲后,“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这样,“春秋以时祭祀尽孝”的“节奏”成定式。汉时皇家以时祭祀的制度为“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四时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汉书·韦贤传》)。如此上行下效,民间祭祀也颇为频繁。
孝的信仰源于血缘亲族,勾连宗法系统,直达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本质上具备维系空间观念的作用。依祭法以历法推演祭时,礼仪就这样固定了年月日时的行动节奏,如同贯穿人一生的“时间表”。“神魂通于四海,刻石得以不朽”,孝道信仰借助石碑、石阙等丧祭石建筑虚化了时空范围,甚至给人超越时空的幻觉。于是,时空的“在场”感变得虚无和不重要,心灵的空虚不安得到安抚,上层社会的运作得以维系,民间也因此加强了凝聚力。
2.石刻媒介的危机
以石头为主导媒介的文明,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控制,造就了庞大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刺激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其内部也埋藏着终极的不稳定因素。与热衷建筑金字塔来强化时空权力的法老统治遭遇的危机一样,这种文明最终必难承其重。
西汉后期大修帝陵、诸侯王陵甚至皇后陵,豪门大户亦大肆置办墓地,土地兼并愈发严重。东汉安帝恭陵高十五丈,其高远远超过茂陵。《白虎通义》有“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东汉时,普通官吏的坟墓入口处也大建石墓阙并刻画像和文字题记。恒帝时,《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记子孙为死者建画像石椁,“立郭毕成,以送贵亲。魂零灵有知,拎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嘉祥武氏石阙铭》记“孝子…造此石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狮)子,直四万”。
因孝道信仰和对于不朽的强烈追求,时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厚葬甚至倾尽家财。《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崔寔为葬父“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汉从事武梁碑》铭文曰“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前设坛墠,后建祠堂”。故《盐铁论·散不足》描述当时社会景象说“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合,垣阙罘恿”。
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总在不断调整中,而平衡往往是短暂的。东汉之后,纸张运用逐渐频繁。汉纸作为竞争性媒介的出现,开始动摇石刻主导的文化垄断。有士人严厉谴责这种的风气,王符《潜夫论·务本篇》曰“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後,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石刻媒介需要搭配更经典的内容物才能保持调整时空关系的效果——熹平石经应运而生。
3.装置经学信仰的石刻媒介
齐鲁地区在春秋时期成为儒家文化中心并辐射燕地楚地,成为秦文化一统最大的障碍。秦始皇东巡封禅刻石,七之有五在鲁地。五篇刻石文中,始皇使用儒家话语「孝、智、仁、义、恭、圣、道、德」“为自己标榜圣德,行教化之用”:「皇帝恭圣」、「孝道显名」、「圣智仁义、显白道理、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原道至明、圣法初兴」、「大圣作治、皇帝明德、作立大义、长承圣治、祇颂圣烈」。两汉尊孔,鲁地多有孔祠。如《乙瑛碑》(153年)和《史晨前碑》歌颂儒家事迹。碑刻所具备的权威性,使其成为后世刻立儒家经典的不二之选。
两汉恢复儒家经典,经籍传播日广,也因古、今经文字标准不统一争论无休。79年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兴汉礼、正经义”,辑成《白虎通义》,以钦定的形式对三派经义系统化整合。东汉晚期,作为定本的《兰台漆书》屡遭贿改。为了考试时评定正误有所依据,从东汉熹平四年(176年)至光和六年(183年),蔡邕等参校诸体文字经书,历7年镌刻四十八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正定经典的刻石,“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媒介学认为,集体观念和信仰通过仪式性聚集活动得以强化,同时也被“再镶嵌”进媒介叙事的地点中。后儒晚学为了得到官定版本的经文,自发聚集到经碑前观视摹写。在正定经文的神圣性、确定性、严肃性得以明确的同时,经典权威的信仰对碑刻形式的倚重也得到了强化,石刻成为了坚固耐久且崇高神圣的书写载体。自此,碑刻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正定经典的专用载体。
五、秦汉石刻盛行的媒介学解释
作为媒介(medium或称中介)的石刻至少包括三部分:物质载体、记忆方式以及传播的社会编/解码(内容方面)。因社会编/解码涉及文本内容,此处按下不表,只看物质载体与记忆方式两方面。
1.山石的媒介属性
玉石被华夏先民视作可通祖先神的神石。山地先民多山石崇拜。山石本一体,郑玄注《周礼·春官·山宗伯》曰“社之主,盖用石为之”,即祀石祭山神之意。另外,秦地多陨铁(石)为山石崇拜再添一重神圣性:秦文公时“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命曰陈宝”(《史记·封禅书》),专家推测此为极稀少的石铁陨石;《七国考》记“秦献公十七年,栎阳雨金”,是我国有关铁陨石雨的第一次可靠记载。天外陨铁(石)可炼制神兵利器,是威力的象征,故《汉书·律历志》有“石者,大也,权之大者”,这体现神石(山)的权威性。
蔡邕《铭论》有云:“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也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石材的主要特点是固不易朽。铜铁易锈,简牍易散,绢帛易腐,陶瓷易碎……所谓磐石之固、柱石之坚,作为石刻记录和存贮的物质载体,山石具有时空稳定性。
《吕氏春秋·求人》曰“铭功绩于金石,著于盘盂”,墨家亦有“书之竹帛,琢之椠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之说。铜是核心货币符号,丝帛轻软平滑但造价极高,“约十匹等于金一斤钱一万”;简牍整治麻烦数量少造价亦不菲。这些作为财富被统治者敛入私库,甚至作为陪葬深埋入土。相比之下,山石铭文具备公告性。
2.堪为夸张之具的文字书写
金石学家马衡说:“自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名器浸轻,功利是重。”于是“以字为夸张之具,而石刻之文兴矣”。文字之所以可为“夸张之具”,源自文字和书写的起源。古代默骨、龜甲上灼刻的文字皆称“契”,“契”字本义即指文字。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正表明汉字起源于“神灵对人们生活和行为的告诫和统领”。殷墟出土的大量作为卜辞的甲骨文书,证明文书最初来自对圣言(鬼神之言)的“听写”,“文书是圣言的托管人或注解”。事实上,文字本就是一种权力的“技术”。德布雷认为,在文字出现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圣言(Logos)信仰是群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精神只有通过一个可感知的物质性(话语、文字、图像)中获得实体,通过沉淀于一个载体之上才能作用于他人。”石刻载体具有神圣性、永恒性、稳定性和宣示性;文字刻于石上成为石刻“文书”,其实质是(文字)权力被进步的(冶金、采石、镌刻等)手工业技术加持并获得了强有力的实体化身,成为文化精神尤其是信仰完美的载体。
秦汉时期大变迁造成时空观念和信仰缺失,社会心理急需“脱域化”媒介的调节;而石刻媒介的媒介属性迎合了帝国集权统治的符号逻辑,在秦汉时期整合社会心理、重构时空“偕律”的社会需求下,石刻媒介成为帝国装置信仰的必然之选。
3.华夏信仰中的灵石观与两汉谶纬
“灵石观”根植在华夏文化血脉中。这种“灵”是通灵,也表现为灵活性。原始神话中,石是对抗自然灾害的神器:女娲以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这种源于先民玉石、神石崇拜的观念以口头传播的神话传说形式积淀下来,又被用到次生神话中,如山顶神石孕育神猴,补天神石化作通灵宝玉。
石(玉石)兼有灵性和灵活性,山川亦然。《春秋·说题辞》有“阴含阳,故石凝为山;山之为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神也”。《春秋繁露·山川颂》中,董仲舒假孔子说“山川神只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小者可以为舟舆浮滠”。华夏文化中的山川定神祇,滋养万物,可大可小皆有所用。
山石皆有灵,也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纬书中表现为祥瑞皆可化玉石,托言天命。《孝经·右契》中,孔子制《孝经》四卷并《春秋河洛》八十一卷,告于天,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刻文言命;《春秋·演孔图》有赤雀集落书上化为黄玉,刻辞“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尚书·中侯》说商汤“东观洛,黄鱼双跃出,黑鸟随鱼,化为黑玉也”。
《春秋·说题辞》曰“山含石,石之为言託也,讬立法也”。“灵石观”给图谶提供了载体依据,王莽篡汉,屡屡以“丹石之符”假托天命逐步谋权,符命大多以(玉)石为载体。石刻成为汉代符谶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是豪族大家篡权的重要思想武器。
六、结语
战国末年,随着周王室的退场,天子的神圣光芒泯灭,集体信仰已从上层社会开始坍塌——“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秦扫灭六国,建立起庞大帝国;大变迁进一步加剧时空失衡及信仰缺失,导致社会失序。汉承秦制巩固大一统帝国,迫切需要重建“大一统”的时空信仰,为时空转化带来的失序提供心理保障,促进社会心理整合以及时空“偕律”重构。
石刻媒介具神圣性、永恒性、稳定性和公告性,迎合了大一统帝国集权统治的符号逻辑。伊尼斯认为“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然而华夏文化中的石质媒介因“灵石观”而呈现显著的个性,挣脱了物理属性的限制,成为沟通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性载体。
秦汉时期,石刻媒介及其运作系统,作为孝道信仰和经学(儒学)信仰的物质载体,建构了大一统帝国的时间、空间观念。石刻媒介作为信仰的装置,以虚化甚至超越时空范围的脱域化效果,促进了社会大变迁下时空“谐律”的重构,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维系社会运作、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汉纸出现之后,知识垄断逐渐被打破。一世纪佛教传入,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里通过口头传播逐渐扩大影响力。但有赖于石刻媒介与圣书文字——儒家六经的结合,使得文化主体——士人群体成为儒学的中坚力量。这也是华夏文化之所以在秦汉奠定基调,并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媒介学阐释。
注释:
② 石刻数据和分期主要参考刘海宇博士《山东汉代碑刻研究》和金其桢先生《中国碑文化》。
③ 汪鹏:《碑刻媒介的文化传播优势及其现代功能转型》,《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
⑤ 韩喜凯总主编:《民本·贵民篇》,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⑥ (战国)商鞅:《商君书》,张觉点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7、38、35页。
⑦ 方行:《中国古代经济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⑨ 刘乃寅:《说“大一统”——兼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版,第234页。
⑩ 引文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