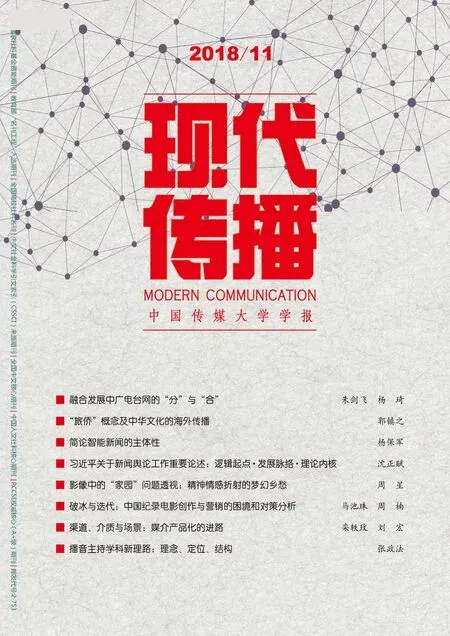书写“红色圣地”:世界新闻史上的“中国时刻”*
■ 曹培鑫 薛毅帆
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西行漫记》之名在上海“孤岛”出版。80年后的今天,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以斯诺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作家在1930至1940年代进入中国西北一角进行的采访活动,可以对那段新闻史产生新的理解。
在传统的新闻史体系中,我们习惯于把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人的新闻活动纳入中国新闻史体系当中。这当然是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框架下来理解美国记者群在华新闻活动的结果:美国记者群的新闻活动“使各国民主人士对中国人民反对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的勇敢、坚定和不屈不饶的精神而感动,从而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①这一史学书写(historiography)将美国记者们的采访活动作为中国革命的“国际精神支持”纳入“中国新闻史”的述评范畴,成为“革命的”中国新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上述历史书写的视角消解了对以下重要议题的探讨: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美国(事实上是欧美多国)记者群会如此集中地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西北角上的一座蕞尔小城②,关注这一隅上的一个红色政权?为什么美国记者群会对当时美国社会由于阶级意识形态对立而既成的“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的形象产生质疑,而有兴趣跋山涉水,去书写另一种“意想不到的赤匪”的形象?③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书写不仅突破先前广泛存在于西方媒体与国民党媒体上的负面形象,更突破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轴上西方世界对整个中国原有的“黄祸”“东亚病夫”的整体负面形象,原因为何?
本文力图转换记述与分析的视角,将这一段充满魅力却未被充分探讨的新闻史“轶事”放置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框架下重新审视,以期还珠于椟。
一、 美国记者群的红色书写
美国人玛格丽特·史丹利(Margaret Stanley)于1987年编纂了一本名为《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第三部分是1935至1949年期间,在延安、保安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进行活动的外国人名录。史丹利根据时间顺序给这些外国人进行了编号,一共统计出了145位外国人④,并提供了这些人的国籍、职业、去留时间。在这份名单中,可以确定为美国国籍的人士有92人,占总人数的63.9%,他们中有66人到访过延安,占总人数的45.8%。⑤
这份名单以1942年的“珍珠港事件”为节点,分为前后两部分。由于“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与中国正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人,包括记者、军人和政府官员,开始大批地进入延安。所以“史丹利名单”的前半部分中涉及到的美国人有20人,当中新闻记者与编辑有9人。⑥这9人可称为真正报道“红色中国”的先行者,斯诺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1936年,红军刚刚长征结束,在陕北落脚。在蒋介石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新闻隔离和形象丑化之下,共产党意识到了必须将政权的真实面貌展现给外界。于是,共产党委托宋庆龄推荐一名外国医生和一名外国记者到根据地来,以便将红色政权与红色根据地最真实的故事讲给外界。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陕北。实际上,在宋庆龄与中共把目光投向斯诺之前,斯诺自己也“早就打算去了,而且已经到上海来想实现这个计划”⑦。这次“一拍即合”使得斯诺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访问中共所在地的西方记者。⑧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西保安,斯诺来到保安后,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热情接待,“周恩来亲自前来欢迎,毛泽东开始同他长谈时,埃德的情绪十分高涨”⑨。随后,斯诺在这里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采访活动。1936年10月,斯诺从根据地返回北平,并开始为外媒和国内的外文报纸撰写有关他在红色根据地所见所闻的报道。这些报道散布在《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救国时报》《生活》杂志、《亚洲》杂志等新闻媒体上。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所有的报道写作。随后,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旋即被选入左翼图书俱乐部文选中,在出版第一个月内重印了3次”⑩。1938年1月1日,《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同年,莫斯科也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而《红星照耀中国》的流行,把红色中国的独特面貌展现给世界,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纪元”,也拉开了美国众多新闻记者赴身“红区”的序幕。
美国记者们走进红区的路途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困难与危险首先来自陕北的自然地理条件。尽管斯诺在远观时可以用一种浪漫的审美眼光将千沟万壑的陕北高原形容成“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然而,置身于其中,走在去往保安的“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上时,斯诺面临的却是“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的危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她的书中写到了她在去往一个八路军驻地的途中,遇到的是“树枝与稻草搭成的桥梁”“湍急的河水”“多石的山坡”“几条极窄的山谷”和“黄土的山壁”。这些对当时已经年过六十的斯特朗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其次,来自于国民党或日军的威胁也使得通往苏区的道路充满坎坷。这些威胁,对于斯诺的旅行尤其真实。斯诺1936年第一次进入红区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国共还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因此,国民党军队对西安到陕北的道路控制极其严格。斯诺知道在这段路途上“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对红区进行军事打击,“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疾病与语言隔阂也使得采访活动困难重重:“寄生在人体的虱子能传播斑疹伤寒,得了这种病的外国人死亡率很高。”“一知半解的普通话帮不了大忙,因为陕西方言是土腔。”
这些困难并没有妨碍美国记者们向黄土高原的深处挺进。红区的物质生活同样异常艰苦。史沫特莱在《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一书的自序中记录了当时生活条件之艰苦:没有纸张,缺少粮食,没有取暖燃料,交通工具基本是双腿与少量骡马,大部分人只有脚上穿的那一双鞋。但是,她也写到:“我向你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情况,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而斯诺认为“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幸福与现实的困境的巨大张力中,美国记者群的红区活动成就了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那么,美国记者群能够克服巨大的现实困难与危险,甚至将这段经历视为“最有意义”的事业,动力何在?我们可以在史沫特莱的书写中一窥问题的答案。在《中国的战歌》中,她写到这些美国记者们所讲述的故事当中的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正是对这个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却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新希望的新政权的憧憬,带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与理想。
那么他们笔下这个“新中国”“新”在哪里?与“旧中国”有何不同?这个“意想不到的赤匪”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二、 中国形象的三个转向
美国记者群笔下的“新中国”是一个之于“旧中国”的相对概念。通过将美国记者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书写——尤其是对“红色中国”的书写——与此前大约从“启蒙时代”开始(至于为什么将这个时间段的上限定在“启蒙时代”,将会在第三部分回答)对中国的书写相比对,我们会发现这其中经历了诸多方面的巨大转变。但从总体上讲,这些对于“新”“旧”两个中国纷繁复杂的描摹,可以大致概括为三对转向:专制趋向民主,停滞转向进步,野蛮走向文明。
1.从“专制”到“民主”
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并不总是一个“专制的帝国”形象。伏尔泰就将中国奉为最可以为楷模的“开明君主制”的国家。但是,启蒙时代以降,中国逐渐被收编进一个专制国家的队伍中——这个队伍曾先后容纳了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鞑靼、沙俄。到了黑格尔口中,中国已经是“君权神授的专制政制。国家是家长制式的,它由一个家长统治,这位家长同时决断一切,也包括我们看作是良心领域内的事情”。
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官员、记者开始大批进入中国。在他们的眼中与笔下,中国俨然是一个完全的“专制的帝国”。《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记录了一种在十九世纪对中国“很流行”的看法:“他们长时间屈从于专制暴君的统治,以及腐败而肆无忌惮的统治者们几乎无处不在的暴虐。”
直至1928年蒋介石角逐国家元首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仍在“专制的帝国”的谱系中继续断言:“如果蒋介石获胜,那么他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操纵中国的独裁者,而且南京依旧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首都。”蒋介石当权后,阿班在1930年出版的《痛苦的中国》中讨论蒋介石政权的性质时写到:“中国始终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的独裁国家,蒋介石集团只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谋求生存并维持其独裁专制。”
从这一条自启蒙时代开始的“中国形象”的观念谱系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在“专制的帝国”之底色上的“痛苦”的国家。
但是,就在阿班做出“专制帝国”断言之时,另一种对中国的书写悄然兴起。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记者们开始关注一个偏居中国最闭塞地区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政权,并将其描绘为一个崭新的“民主政权”。这在苏联建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共产政权充满恐惧与敌意的历史情境下,尤其令人匪夷所思。
在斯诺笔下,“红色政权”是一个“‘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而“年满十六岁的,普遍都有选举权”。所有的社会组织“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而且都与“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的领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大民主政治体制跃然纸上。
在“党、政、军”领导下的人民,并不是一种被迫的归顺。在斯诺看来,他们似乎是发自真心的认可了“人民的政权”与“人民的领袖”。斯诺经常用“悬赏金额”来说明共产党首领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毛泽东)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他(林彪)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然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把那些(红军大学)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尤其是对于毛泽东:“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
因此,斯诺意识到,“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的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但是共产党所做的却是“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
斯特朗在1937年来到根据地,她在这里发现了一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军队。这只军队在斯特朗的笔下是一支民主的军队,领导人对架子“漠不关心”,“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对八路军来说,每个普通士兵都是宝贵的”。
如果说,斯诺在1936年保安之行中写下的“民主共和国”还掺杂着对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生政权的美好遐想的话,那么他在1939年重回陕北的延安之行就应当是以更成熟、更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这个红色“国度”的。斯诺注意到了根据地的政制改革的新进展:苏维埃政府承认了各村镇的自治能力,选举权是普遍而平等的,四十二种杂税废除了,基层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农民愿意参加的运动。斯诺将这一切称为“民主政治的实验”。
延安的民主氛围对于长期处于专制社会中的中国人民来说难能可贵。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记录了一个离延安大约两小时车程的小村子进行村参议会选举的场面。一处细节描写言明了“延安式的”民主对于中国人民的可贵:“那些对奴隶生活记忆犹新的老年人,对这些事情(民主选举)似乎是奇怪得不可理解……我差不多理解他们的心情,那是一种为难、不信任以及感激真正关心一般人民福利的政府的混合感情。”在福尔曼眼中,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在一个漫长的“专制”的母胎中成长出来的可贵的新社会。而这种复杂的社会转型折射在人的思想层面,就形成了这种混合情感。作为一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他们也从对中国的复杂的印象与想法中积极地“分拣”出一种新的、正面的、不同于以往“专制的帝国”的态度。
2.从“停滞”到“进步”
“停滞的帝国”,这是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对清帝国的定位。这个定位大约从启蒙时代开始就被用于对中国的描述。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表现出任何发展和进步的地方”。而且,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也都从各自的角度提供大量的新史料来论证这个旧观点。
周宁认为:“进步是启蒙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它表现为一种知识化的信念:人类文明已经、正在而将会朝着一个可以预期的方向演进。这个方向可能是科学知识、民主制度与物质财富最终导致的幸福,也可能是一种绝对精神的实现。”但是中国似乎在这些可能的维度上都停下了步伐。从启蒙时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眼中就逐渐褪去了富庶、文明的大汗之国的面貌。中国在经济与物质财富上“停滞取代了繁盛,经济急剧衰退,缺乏进步”;在心灵上“对他们(中国人)来说,变化是令人厌恶、反感的……心灵便处于停滞状态……进步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动物一般”;在艺术与美学上,“似乎没有超过每一个民族早期文明的阶段,在纯粹形式的观念上,他们甚至落后于新西兰人”。近代的日本在进行民族命运抉择的时候,选择了“脱亚入欧”。“脱亚”的关键是脱离亚洲的代表——中国,因为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缺乏自由的生机、进步的动力”,以至于“停滞在世界历史的起点上或者世界历史之外”。
这些对于中国形象的描绘似乎都在为黑格尔的那句论断背书。形象越描越深,已成为一种文化。以至于,斯诺自己都“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但是当美国作家群亲临根据地的时候,所看到的却是一幅充满朝气的革命进取之地的景象。
在经济方面,斯诺用了一种“残忍的”对比,雄辩地道出了根据地的进步。在边区红色政权建立之前,“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灾难里,斯诺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斯诺)眼前活活饿死”,“二十岁的年轻人……像个干瘪的老太婆”,“儿童们……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许多土地荒芜”的同时,陕西的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税捐‘又占百分之二十’”。接下来,斯诺对比了红区在经济上的进步与变革:“在新区中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税租”,“大片大片地开‘荒’”,“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还进行了货币改革。放置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框架下,在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帝国,一个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已经习惯了森严的等级界限的帝国,一个古老且顽固如“化石般的”帝国中,这场从黄土深处所爆发出的变革堪称伟大。在这样的对比鲜明的事实材料面前,斯诺得出了结论:“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
在政治方面,美国记者们认为中共是一个积极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进步政权。斯诺和福尔曼巧妙地使用历史的隐喻阐明观点:“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在古代它(延安)是防范北方胡人入侵的重镇。”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描写是新闻写作中对于背景材料的巧用。此时的保安县依旧是“抵御”侵略的“要塞”,只不过入侵者变成了“日本”。这一系列与历史的有意勾连,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与曾经那种任人宰割、龟缩自保、畏惧反抗的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度。这个“新”中国充满了反击敌人的勇气和谋略。这种变化不仅是胆量与能力的进步,更是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国际意识的觉醒。
在斯特朗与史沫特莱的新闻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也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气象。妇女们开始“参加识字班、学习小组,讨论抗日救亡是怎么一回事,妇女如何出力”。史沫特莱预言“新”中国的“新妇女”从此成长起来,庄严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正面:“从此以后,她们不是过去的锅台转后门坐的深闺屋里人了,而是关心民族兴亡、复兴的出门跑的新妇女了。”
美国作家群们还注意到了一种“新文艺”——完全为抗战服务的进步文艺。一方面,文艺被用来反映中国军民革命斗争的事迹,“都是士兵们所熟悉的生活的写照”,比如丁玲的剧团用有北平风格的“大鼓戏”表演了“平型关战役”,而“该村在场的观众中有一半人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有关他们自己胜利的故事”。另一方面,文艺也被当作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士兵们需要学习的中日甲午战争和当时的日本侵华简史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戏剧做媒介教给他们的”。
美国记者群笔下的红色边区发生了“换了人间”似的巨大变革。“谁梦想得到在那社会停滞了两千年的贫瘠的陕西黄土岩中”,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艺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与曾经停滞不前的那个古老帝国完全不同的进步新面貌。
3.从“野蛮”到“文明”
与“专制”和“停滞”不同,“野蛮”既不是形容某一个政治体制的独裁性,也不是将一个社会定义为不思进取的懒惰,而是对一个社会与其成员的全面指称。“只有在野蛮的概念下,中国形象才全面陷入黑暗,野蛮作为套语的概括性,远胜于专制或停滞,野蛮所指的社会与人的否定性特征,几乎是无所不包的。”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国门打开,大量的西方人目睹了迥异于自身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疏远文明的野蛮形象是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溺杀女婴、酷刑、小脚、猪尾巴辫子、淫乱的一夫多妻制、吸鸦片、动物般的大量繁殖、满街的粪便、异教徒等等。似乎中国与中国人的一切都可以与“兽性”“未开化”“堕落”联系在一起。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童年回忆是“邪恶的;危险的;他们绑架孩子;从事白人奴隶买卖;在电影中总是坏人;古怪;可怕;他们会把你砍碎;阴险的;他们吃大老鼠;吸鸦片……”。中国人的“野蛮”不仅是社会文化、习惯、习俗等层面的“不文明”,更令西方人产生恐惧。因为中国人的“野蛮”被与暴力、残忍、人口众多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人的“野蛮”就成了一种对“文明的世界”,也就是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比如西方人就对俄国征服中国,并利用中国人征服欧洲的想象充满恐惧;再比如,马尔萨斯把“野蛮繁殖”的中国人当作世界粮食的无底洞,最终也会使文明国家陷入贫穷;十九世纪的若干起暴力教案也给中国人披上了一层顽固不化、不肯接受基督教文明的野蛮异教徒外衣。上述野蛮形象,在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突之中,唤醒了欧洲人对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恐怖记忆而走向高峰:“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中国人似乎永远都不会“文明”起来。
但是,当美国记者们来到红色根据地时,却看到另一幅景象:“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斯诺)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近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斯诺的这些见闻几乎逐一撕掉了曾经与“中国”或“中国人”捆绑在一起的野蛮标签。
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所实行的很多“文明开化”的改革措施在国民党的媒体上被形容为新的“红色野蛮”,比如“共妻”“妇女国有化”等丑化宣传。而斯诺称这些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他还用了一种“西方的尺度”——法制,来评价共产党在陕北的婚姻改革。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文明的标志。他用1936年在保安重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来证明,共产党所建立的婚姻制度并非是“共产主义式的”野蛮,而是一种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文明。《婚姻法》中的规定也的确有利于扫清中国传统婚姻中的一些封建意味浓厚的规约:“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禁止彩礼……离婚双方财产均分。”
教育事业也是共产党在根据地重点发展的“文明”事业之一。斯诺记录下这里开办的形形色色的学校:为小学教师开办的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工会学校、党校、技术学校、无线电学校、医科学校,以及一种发挥着重要社会教育功能的“社会教育站”。在这种教育站里,群众由一个共产党员或识字的人当组长,凭借有粗糙简单插图的识字课本来学习。
这只军队似乎不像历史上的其他军队,他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连日本人也要承认这支军队的“文明”。对于普通日本士兵,“上级一直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被捕,他们会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处死”。所以日本人会因为避免被俘而拼死抗衡。比如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主要来自于解除日本俘虏武装的时候,而不是实际战斗。但实际上,一位日本战俘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受到“礼遇”的故事:“我们受了伤,当了俘虏;我们想这下子完了。过去我们被告知,中国军队很残忍。可是事实上他们待我们很好,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一个叫做冈田吉雄的俘虏本来等待着受刑和被杀,但是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提出要遣送他回自己的部队。冈田拒绝回去后,不仅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一年,还为王震的部队建了一所日式风格的招待所,评上了劳动英雄,更在1942年加入了八路军。
在这些社会“文明”的改变之外,美国记者们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共领导人们的“文明”。从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就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负面宣传,比如“无知土匪”“强盗”“放火犯”。然而在美国记者群的笔下,周恩来的形象是“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贺龙不让自己的部下“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毛泽东是“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与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朱德的眼睛“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这一系列“文明的领袖”的形象与国民党的宣传——用斯诺的话说——“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总之,在美国记者们的笔下,“野蛮的帝国”文明化了。这种“文明”的根据地形象,是对包括国民党这些年来的政治丑化与西方长期以来的“种族鄙视”的双重否定,在他们的写作中,中国被寄予了成为崭新的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期望。
通过阅读美国记者们作品当中一种新的“中国肖像”,我们发现了潜藏在这些文本当中的“三个转向”:从专制到民主,从停滞到进步,从野蛮到文明。这些崭新的中国形象颠覆了贫穷落后、野蛮停滞的中华帝国的刻板印象,红色政权成为新中国的希望,预示着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此时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书写能够极大地突破此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中——西方世界对中国整体的负面形象书写?什么样的美国(或者说西方)历史语境能够产生敦促美国记者群在三四十年代如此热衷于构建一个“民主”“进步”“文明”的红色中国形象的动力?
三、 作为“他者”的红色圣地
索绪尔说,意义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被确定的。中国形象——关于“中国是什么样的”的描绘——而非中国本身,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持久地发挥着“功能性的他者”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博埃默所述:“正因为‘他者’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此处强调“功能”与“持久”恰好因为,西方、现代性等主体观念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就不得不在文化表征层面“相时而动”,不断提供西方主体性建构所需的对立性的文化观念与元素。
周宁说,中国历史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想象的他者,具有重要意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历史形象贯穿西方现代历史叙事始终”。因此,欲探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记者的红色书写,探讨其建构的崭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化与历史语境,研究者就必须重访作为“功能性的他者”的中国的文化再现的历史。
伴随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到来,中国形象从遥远陌生却充满魅力的东方古国转变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新的社会与文化价值体系互为表里。这种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话语体系是由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民主”等观念建构起来的。彼时的中国正好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上为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与确认的参照物。东方与西方、古老与现代成了绝妙的两副对子。“‘古今之争’确立了现代优于古代的观念,确立了西方现代性的时间秩序;‘东西之争’确立了西方优于东方的观念,确立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秩序。”隐藏在共时与历时双重对仗中的,是文明之间的尊卑优劣秩序。这种秩序所外化的社会表征,是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的转变:“中国从过去那个被称颂的文明优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被鄙夷的停滞、落后、野蛮的专制帝国,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此便开始黯淡了下去,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然而,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洗礼、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的中国,再次成为西方文明反思自身、想象可能的未来的文化坐标。而美国记者群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迷茫与寻找答案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出发,去探索一种未知却充满可能性的“另一条道路”。
他们在寻找什么,又能够看到什么,就取决于他们经历了什么,反思了什么。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历史“昨日”与“今日”的界线,“‘昨日’是一个安全、温馨、繁荣、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世界,‘今日’则是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的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得西方开始质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代议民主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直指代议制本身,战争是由“西方政府一手导演的没有民众参与的秘密外交”造成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认为根源在于此前让西方各国引以为傲的民族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源于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受到质疑。
其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中喘息过来的西方世界又在十年后遭遇了经济上的大溃败。一战给欧美发达国家造成了1700亿美元的损失,而经济大萧条却造成了2500亿美元的损失。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在饥饿之余开始对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进行反思,尤其是在与大萧条时代苏联的经济状况的对比之下,美国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大萧条期间正值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2年底,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一战前增长了334%。此间更有10万美国人申请移居苏联。“一次大战的发生,再加上大萧条的爆发,使自由主义陷入危机,许多人对它丧失信心,不相信它能解决社会面临的崩溃问题。”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在1930年代,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法西斯恐怖与新的战争阴云又笼罩了西方。西方国家在“何以解忧”的历史忧虑中再一次被迫反思自身,并通过寻找新的文化坐标重新确立自身的意义。
彼时的中国之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坐标,“另一种可能”。面对自身制度的缺陷,在“末路”忧患意识的驱动下,美国重新开始去了解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方国度,甚至还出现了有一定官方组织背景的“美国记者团”对中国的集中访问——开始了又一次书写中国的“神话”工程。
因此美国记者们将目光投向中国西北一隅、黄土深处的、与自身制度截然相反的新生政权,就显得顺理成章。不仅“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语),更因为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描绘的更加民主、进步、文明的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正是一个可以追求的“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充满魅力,正如冉冉升起的红星照耀中华大地。
至此,我们就能够对美国记者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的西北角,并用热情和赞美的笔调来书写一个共产主义新政权产生出一种超越于现有的中国革命新闻史的述评结论——在这种述评中,这些西方记者被做为中国革命的国际精神支持者被记述和评价——而呼唤出一种“美国社会新闻史”的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需要回归到当时的美国社会历史情境中来获得。在这种新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够更完整地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创作的文本和他们的传播行为。
注释:
① 胡龙:《试论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对中共形象的建构——以“三S”为代表》,《新西部》,2016年第6期。
② 自从1937年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延安便成为美国作家群重点关注的城市。但是,美国作家群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延安一城,如《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内容是1937年前对保安的采访。
④ 由于编号41的Pyotr Vladimirov和编号65的Peter Vladimirov是同一人,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的作者,所以有效人数为144人。崔玉军:《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
⑤ 崔玉军:《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
⑥ 包括:埃德加·斯诺(Edge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Foster·Snow)、厄尔·利夫(Earl Leaf)、菲利普·贾斐(Philip Jaffe)、毕森(T·A·Bisson)、哈多斯·汉森(Haldors·Hanson)、陆茂德(Maud Russell)。
⑧ 谭天:《斯诺、毛泽东与〈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0期。
⑨ [新西兰]路易·艾黎:《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载刘力群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⑩ 胡步芬、陈勇:《〈红星照耀中国〉的对外传播途径与影响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