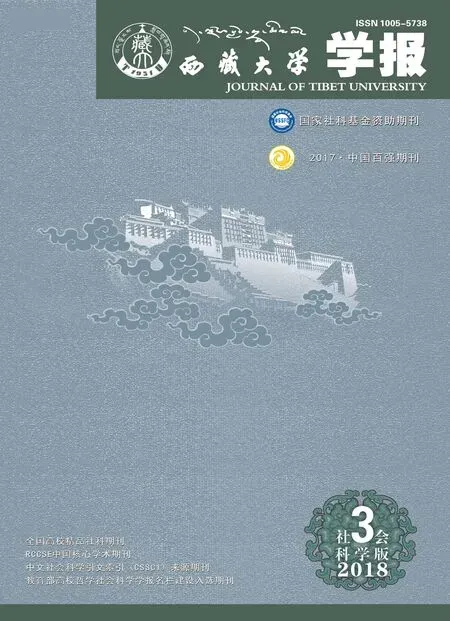识的“他证”与“自证”
——康德与萨迦班智达认识论的同与异
郑宏颖 阿旺嘉措
(①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遵义 221116 ②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自康德开始,“西方传统的‘元哲学模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1],认识论从此有了取代本体论哲学地位之势。康德把认识来源归为提供感性印象材料的物自体和提供先验认识形式的主体自我两者,从而将知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建立于人的先天认识能力之上。他继莱布尼茨之后,以非心理性的“统觉”作为先验自我意识。这一先验自我意识具有统合作用,它以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方式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体现主体能动性。藏传佛教萨迦派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以下简称萨班)在以《因明七论》为根据的《量理宝藏论》(以下简称《量理论》)中指出现量是根识对物的直接感受、比量是认识主体遵循逻辑概念推理的结果,它们共同形成了人的认识。在对认识的分析中,萨班与康德同样重视物质的刺激和认识主体的直观能力,并且都否认因果等逻辑概念的外境生成性,一致将之视为是主观能力的一部分。
在分析过程中,康德认为因果诸范畴具有先验性,它们是与认识主体不可分割的知性能力。萨班则强调因果等逻辑概念的虚拟性,认为它们虽然是隶属于心的一种能力,但是认识主体可以通过对“心”的认识而摆脱其束缚。此外,针对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何而来、自我意识是否能完成对其自身的考察等问题上,康德一概予以了不可知及否定性回答。认识主体只能在对客体的知识性定义中获得自我展现,它无法自证其存在——人所能体察到的只是本体自我通过内直观形式时间而展现出的经验自我,就如同人只能了解物自体通过内、外直观形式而展现出的现象一样。因此康德否认了萨班所持的识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证的观点,他认为经验中的认识主体属于依仗认知外物而才能证得自身存在的“他证”范畴。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萨班则基于心的自明性而在《量理论》中承许识能够进行自我反省,间接说明了个体可以通过认识而深入了解、体悟本体。他所强调的“圣教量立场”即是自证分发展的极致结果,“宗喀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因明看作达到内明的必由之路。”[2]
一、康德:由提供质料的物自体与提供形式的“我思”共同形成认识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希腊开辟出了一条使世界的存在依附于主体认知形式的哲学路径,由此建立了“人”的观照方式。西方哲学在希腊时期之后延续使用这一方式来认知世界,并进而通过该视角反过来再次确认和认识人自身。身处上述哲学传统中的康德则奠基了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大转向。
康德认为对象在感性经验中被给予于认识主体,这一给予过程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物自体提供质料以形成印象,人自身提供直观与概念先验形式对被给予的对象进行规范。由于“对象依照知识”[3],人于是可以为世界立法。对象依靠人的先天感性和知性能力才会成为经验现象,否则对象不但无法被认识,甚至连其存在与否也不可知。康德强调不能运用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证明任何未进入经验领域的对象的合法性,因为它们只是使对象经验化的先验必然条件,不能被僭越的使用于本体范围之中。对象在被给予和被认识时,它也随即失落自身而变为现象。现象背后作为对象的物自体并不可知,而这一物自体不仅包括客观之物,同时也包含了认识主体自身。
康德指出认识对象的统一性存在于能知觉且能思想的主体性“我思”中,“我思必定可以伴随所有它的表象。”[4]对象无法在不经由直观的前提下而被认识,作为物自体的本体自我也同样只有在通过时间的内直观调节而成为现象之后,才能成为被觉知到的执行认知功能的自我意识。相对作为本体的先验自我而言,现象自我是经由直观改造而形成的经验表象,“我却只是像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来认识自己,而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来认识自己。”[5]因此认识主体所知觉到的永远不会是本体自我,本体自我不可能属于合法的经验认识领域。本体自我的先验统觉能力伴随一切现象而存在,它是任何经验的必然永恒条件,但它自身却永远不能以对象的形式存在于经验中。因此康德才强调在能进行任何“综合”之前,自我意识不会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先验自我在这一尺度上并不具有自证能力。
康德认为一切没有被纳入知性规则中的经验都不具有意义,直觉式的存在不能被允许发生——无论这一直觉是心对物的直觉,还是心的自证直觉。经验能够得以成立必须是在被纳入知性范畴之后,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实在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中列出了作为知性普遍成分的十二个范畴,并将它们视为是规范认识能力与判断能力的先验条件。一切通过先验认识规则而进入经验的都是现象,一切现象也都必然具有知性尺度。康德因此推论出了异于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后者只关注认识主体思维中异于经验知识的先天原理。先验逻辑的规则决定了知性形式不可能同人的自我意识分开,这导致人遂无法对自身的先验能力予以反思,“因为它们是先天立法着的。”[6]在先天认知方式的困囿下,“物之在其本身永远不是我们的对象。”[7]因此康德才断定以自然科学方式无法解释自由,自由基于其自身的先验性而在经验知识范围之外,它只属于“实践”范围。同样,认识主体虽然不能通过知识分析而完成自证,但它却能经由实践而成为一个自由主体。
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康德延续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但是由于他主张自我意识虽能定义“物”的世界,却无法自行了知本体自我,于是就导致他持有一种仅限于认识论尺度的真理观。认识主体能够为世界立法,同时却使其自身成为被限制之“物”,这一悖论是康德认识论无法突破的阈限——人所能认识的只是“物”与“我思”的显现而不是“物”和“我思”自身,经验之外的本体对象是经验中的人永远无法了知的。在这点上,康德哲学显示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穷途,并迫使西方现代哲学走上了萨班《量理论》因明学中所承许的自证之路。
二、萨班:由无分别现量与分别比量共同形成认识
萨班在以《量理论》为代表的因明学中指出,认识主体通过分别识和无分别识的作用而形成认识。他将“识”定义为“识之法相(性相)即明知,”[8]主张“由境而言成多种,由识而言一自证”[9]。明了、觉知是识的性相,而其中关键又在于识可自证。《量理论》延续了法称《释量论》的观点,从而指出“缘取自相无分别、执著共相乃分别,其中自相有实法,共相不成有实法。”[10]萨班将缘取自相法的有境之识定义为“无分别识”,它依靠根和外物的共同作用生起,必须依靠对境才能产生;将执著共相法的有境之识定义为“分别识”,它以显现自境方式而形成,不需要依靠对境。同时“正量之识虽有二,然归唯一自证量”[11],所有正量识都可以被包涵于现量和比量之中,而现量、比量的最根本来源只是“自证”。无分别识照见外境时,正如康德阐述的认识主体接纳物自体的印象时一样,外境诸法的所有差别特征会一时全部顿现于根识前,从而形成现量。现量是不分别而且正确缘取外境的量,萨班否认了它具有分别性和决定性,因此由现量形成的印象不包含逻辑性的破立、分析。这意味现量不具备康德所说的“综合能力”。萨班认为能够进行“综合”活动的是第六分别意识,在现量引生了对外境的真实定解后,分别意识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比量推理。意识缘取共相进行破立时,它唯一依靠识的自身能力,不需要通过显现的方式照见外境自相。因此在比量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最根本遣余方式的“心识遣余”是认识主体进行度量的唯一方式。①此处参照了周贵华《唯识与唯了别——“唯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的再诠释》一文的看法。他在发表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的这篇文章中,将“识别与了别”作为“识相”,指出在佛教认识论中“了别作用虽具有主动性,但认识内容完全是外境直接引起的。但在经部,了别所直接呈现的境,虽有心外的实有物极微为所依,但实际是在心内,为心之所带相。这样,经部的了别所对之境的含义,显然减弱了独立于心的“外在性”,而了别功能带上了强烈的错乱色彩。到瑜伽行派,对了别之境的“外在性”予以进一步否定,彻底排除了离心独立的外境的存在,认为了别所呈现或显现之境完全是虚妄的。”
《量理论·观总别品》根据《释量论·为自比量品》而指出“比量不取有实法,故彼实法非应理,乃遣余故智者许,比量即以反体立”[12],强调比量遣余在以分别方式缘取外境总相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耽著于对境的自相;二是不具备任何真实有自相的对境。遣余由于耽著作为思考、言说追随目标的自相,从而不自觉地将该事物自相和其意识总相误作一体而进行思考和表述;三是具有现量的种子,它以自证现量曾见到、听到等的自相法作为自相续的引生种子。因果、必然等概念关系都需经由遣余识才能获得反体上的安立,它们在事物自相上并不存在。反体是与实体相对的概念,它唯是认识主体分别念产生作用的结果,并不具有物质性实存。《量理论》将上述过程总结为“遣除非彼之自性,于诸实法皆成立,彼即遣余之总相,误为自相行破立”[13],说明比量以遣余方式进行破立时,其所涉及的对境不具备有实自相。分别意识以遣余方式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建立,都是以遣除该事物自身概念之外的其他概念的方式而进行的,而遣除他法之后所余的也只是概念性总法。
萨班基于遣余观念而将因果诸“范畴”视为认识机制中的主观存在,排除了它们的实体性,这一与康德将先验范畴设立为主体认识先天机制具有相通之处。以遣余方式而形成的因果等总法不具有自相,它们只是认识主体所赋予事物的,并不是事物自具的属性。但是萨班不认可因果等观念的先验性,也不认为在人的认知活动中不能被剔除这些概念的作用。他强调现实事物自身与主体第六意识所生成的逻辑关系总相是可分离性他体关系。
在认识的产生过程中,根识对事物自相的无分别印象是首要条件,但这还不足以形成有序的认识。只有在认识主体通过遣余所形成的总相概念而对无分别印象予以整理后,整个世界才具有了可认知性和可言说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直接照见外境作用的是无分别根识,形成内观有序认识的则是分别识。识虽然可以从“境”的角度分为分别识、无分别识,从“体性”角度分为错乱识、不错乱识,从“趋入”的角度分为已入识、正入识和未入识,但上述诸识的共同根本特征便是自证。萨班遵循《释量论》“以是一切识,缘领受各异,同义是为缘,自显是领受”[14]的见解,认为自证是在分别识和无分别识之间进行联络的力量:五根识照见对境的当下,自证识也随即进行了知,之后这些特征经过自证能力而被传递给分别识,最后由分别识对获取的材料加以分别和取舍。萨班同时还延续了陈那将作为认识主体的“心”分为见分、相分和自证分的传统,认为见分和相分属于遍计所执而生的虚妄分别,唯有识的自证分才属于具有名言实在性的依他起。因此对识予以分别、无分别等作用性区分都是名言侧面的安立,诸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体的,而一切所知对境和能知有境从根本意义上最终都应归于识的自证,是为“乃至承认有外境,期间因称所取境。如若所知纳入内,境及有境皆不成”[15]。正源于承许识具有自证性,萨班才在其因明学认识论中为朝向对唯识本体论的阐述预留下了进阶路径。
三、源于本体自我不可知的“他证”性认识论与源于识可自知的“自证”性认识论
在对形成认识的印象和知识形式的探讨中,萨班与康德的见解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他们各自以无分别五根识、第六分别意识和感性直观、知性范畴对认识的方式予以了回答。他们同样认可无分别直观和由认识主体所形成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不同作用。萨班阐述的无分别根识“如哑具明目”般了然明现外境的过程正是康德指出的认识主体以固有直观能力取得印象的过程,而后者论述的知性范畴对认识过程的契入则是《量理论》引入第六分别意识的认识阶段。但是在考察认识主体时,康德认为认识主体同样是不可知的物自体,“这个自我意识后面究竟有一个什么实体在那里承担着它,我们是不能够认识的。”[16]作为“对象”的本体自我需要以成立认识现象的方式证明其自身的存在性。由于时间是内、外一切事物的先天直观形式,认识主体因此也无法摆脱这一直观形式,从而导致它在进行自我观察时必定会丧失了主体性和成为现象。与之相对,萨班在其因明学认识论中则强调认识主体具有自知性,主张与认识主体一味一体的“识”在无需佐以他物的情况下便可完成对自身的审查与认识。萨班的认识论遂由此获得了转向本体论探索的契机,使认识主体有可能实现对认识论尺度真理的超越。这一关要正是萨班因明学认识论与康德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分歧所在。
对认识主体能否自知的分歧导致了萨班与康德最终的差异性结论:康德通过对认识机制的分析而区分了可知的现象与不可知的本体,以此反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各自独断性。英国学者Roger Scruton曾在《Kant: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中将康德哲学中具有认知功能的先天自我意识称之“先验自我”,他认为康德在把先验自我当作一种视角和当作一种特殊的本体之物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当先验自我作为一种视角时,它的统觉综合能力使知识成为可能,任何知识的成立都需要自我意识能动性的作用。但是当先验自我作为本体自我而存在时,它却悖论的不能通过自身本具的感性和知性能力而得以自证。“我们人类只有感性直观的形式,而没有理智直观的形式。所以对我们来说,本体概念只有消极的意义,它是一个‘界限概念’,标志的是感性的界限。”[17]作为物自体的本体自我由于在其显现过程中永远无法摆脱内直观形式的如影相随、在被认识过程中永远必须接受知性范畴的规范,因此它唯能以经验现象的方式进入知觉并为人所意识。康德认为企图对具不可知性的本体自我进行认知而以期获得经验知识的倾向,正是理性行为的僭越-这种认知只能以仅在经验领域中才有效的方法为手段,而作为自在之物的本体自我并不在经验范围之内,因此它最终获得的只有幻相。幻相的形成正源于人误将主观条件视为关于客观对象的知识,从而试图产生关于本体自我的经验性知识。
相对于康德将本体自我归为不属于合法经验认识领域之物的看法,萨班在《量理论》中通过汲取假相唯识学思想而进一步承许和发展了识的经验性“自证”意义。他认为境与识的在本质上最终都可消融于内观时明清的识之自证中,从而许可唯识学将“相分”视为是“见分”的对象性证知、将“见分”视为是“自证分”的非对象性证知以及承认具有自身意识的“自证分”与“证自证分”二者之间有相互内向作用的观点,由此推论出认识主体在真正通达自心时,实际上也就能够如实了知万法。萨班《量理论》因此在阐明名言认识真理的基础上,间接论证了《释量论·成量品》以佛陀明了心之本性而通达万法来证明佛陀是世间唯一“量士夫”的观点。萨班这一源于自证式认识论而朝向本体论的努力,正同格鲁派宗喀巴提倡因明学中亦有成佛之道、宁玛派麦彭降央南迦嘉措强调《释量论》等因明论典同样包含了诸多佛教内明知识的见解一致。同时,这种将因明学视为是由认识论趋入本体论的桥梁的观点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藏传寺院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将因明学作为唯识学等课程教育的前期基础,也正源于在前者对名言真理的关注中必然会引发朝向终极本体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