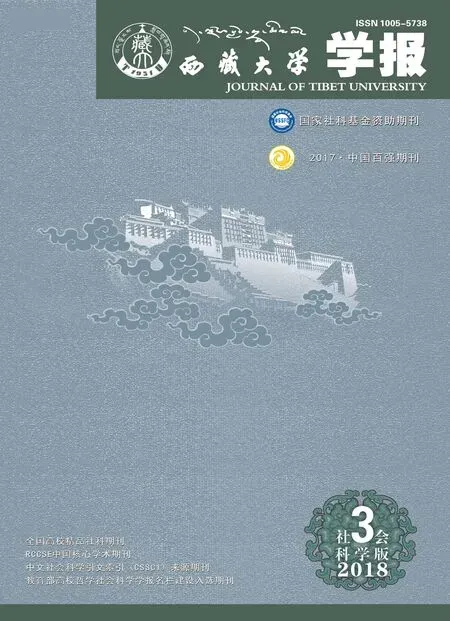一部鲜为人知的藏文历史文献:卫巴洛色《教法史》
米玛次仁
(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一、文本介绍
一直以来,卫巴洛色《教法史》被谬解为《韦协》的不同版本,其原因或许是该书末页损毁,加之抄写者失误所致。①《韦协》被视为西藏历史文献中成书时间较早的一部,因其重要性,后人在传抄过程中不断修改、增补,形成了《韦协》的不同版本,即广本、中本和略本。其中《韦协》被视为目前存世之较早版本。关于《韦协》及相关内容,参见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dBa’bzhed: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0;巴桑旺堆.《韦协》译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7.2010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韦协》不同版本的汇编,系“雪域文库”丛书第56卷,其中亦误将卫巴洛色所著《教法史》视作《巴协》(),这是该史书首次正式公开出版。[2]
笔者手持该《教法史》版本有三:一是西藏社科院巴桑旺堆先生向笔者提供的复印本;二是由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所编《藏文史籍传记汇编》第36卷中所收录之手抄本;三是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印刷本。上述前两种版本的字体、版式皆相同;第三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中明确交代了所依版本由巴桑旺堆先生提供,故而三种版本实际源自同一本史书。
自2012年范德康教授专门撰文公布后,被淹没许久的这部史书才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笔者在研读这部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其成书背景颇为复杂。通过对《教法史》和《韦协》进行对勘后,发现所谓“《巴协》”其实是一部摘自两部不同史书的“汇编”。首先,根据手抄本的页数,前4叶内容与《韦协》之前段部分基本相同,5a(第5页正面)至末页的内容系范德康教授所指出的“迄今未知的”(Hitherto Unknown)卫巴洛色《教法史》。可见,这部24叶的史书应是《韦协》和卫巴洛色《教法史》的“混编”。其次,从手抄本的字体和内容来看,全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经笔者仔细品读,发现史书内容存在段落间不能如理衔接的现象,显得语无伦次,故,笔者认定该手抄本之内容乃摘抄自不同史书。例如:
上文首先讲述了赤松德赞(718-785)派遣章·列斯等三人前往逻娑试探从印度迎请来的佛教高僧寂护(725-788),但因语言不通之故,三位大臣不得不从逻娑集市上找人担任翻译,从而找到婆罗门阿难陀的历史事件。其后的文本内容,将释迦牟尼三位弟子集结三藏,即佛教第一次集结事件与前文硬生生地进行了架接。笔者推测,该抄写者传抄过程中可能误将卫巴洛色《教法史》视为《韦协》。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巴协》”。②陈垣先生曾指出,“抄书容易校书难。”这句话应该是对这种抄写时所产生的失误的最精辟的总结。参见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M].陈智超,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
这里笔者所要探究的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巴协》”里第5a至24b(第24页背面)页上的内容。卫巴洛色《教法史》确切的书名不详③在一部名为《藏地人类之起源》的文献中,曾提到“卫巴洛色的著作《日藏》中记载,天赤七王皆从天而降,因此(示寂后)返回天界而无遗体,犹如彩虹般消失”。但笔者在其所造《教法史》中未发现相似的内容,所以不敢断言引文中所提到的书名就是这部《教法史》。佚名.藏地人类之起源[M].(手抄本):2.,目前所见除去抄自《韦协》的4叶内容外,剩余20叶皆为卫巴洛色《教法史》。关于“《巴协》”文本的基本情况,据《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的介绍,其载体系藏纸,字体为柏簇体,梵夹装,高7cm,宽35cm。④在图录中,该书编者仍旧将这部史书视为“《巴协》”,且认为是“元写本”,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卫巴洛色《教法史》成书于1340年,后来抄写者误认为是《韦协》,才出现了二种史书混在一起的情况,而元朝亡于1368年,因此,笔者认为这部“《巴协》”的抄写时间应晚于元代。参见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12;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91.从文献的保存情况来看,除了末页损毁外,整体保存较为完整。此外,该书第23b页有10行文字外,其余均为9行。
二、作者及成书年代
《教法史》末页损毁,跋文不存。所幸,该书末页残存字迹中依稀可辨有“卫巴洛色”()四字,且在正文《佛教住世之期限》一章中亦有所记载。⑤“卫巴”意为西藏中部人;“洛色”是简称,根据卫巴洛色所造《佛藏目录》卫巴洛色的全名应该是“洛追色丹卓贝森格详见卫巴洛色 .佛藏目录[G].(手抄本):80a;卫巴洛色 .教法史[M].317.
为了更进一步判断该《教法史》作者无误,笔者通过部分后期文献资料就卫巴洛色是否著有《教法史》进行了考证。
(二)智观巴·贡却丹巴饶吉(1801-1866)所著《安多教法史》中记载:“卫巴洛色著有《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6]
(三)至尊喜饶嘉措(1803-1875)所编撰的《部分稀有珍贵文献名录》()中记载 :“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和《大藏经》目录。”[7]
同时,在当代学者丹·马丁(Dan Martin)教授所编撰的《西藏的历史:对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研究》(Tibetan Histories: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Works)和康追·索朗顿珠编写的《西藏史籍名录》()中亦有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8]这一信息。①在《西藏史籍名录》中,收录了3篇由卫巴洛色所著历史文献的名录,其编号和名称分别是0102号“《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0421号《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和1991号《佛法在藏地的传播二章及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其中 0102 号与《安多教法史》中的内容相一致;0421和1991号的内容从表述上来看,并非书名,而是章节的名称,从所述内容与卫巴洛色《教法史》内容相比较,笔者发现,后两个编号应该就是卫巴洛色《教法史》某一章节的内容,而并非另外独立的史书。具体请参阅索朗顿珠.西藏史籍名录[G].21,84,393.
关于卫巴洛色的生平,目前未见有传记传世,仅在后来的史书中涉及纳塘古版《大藏经》整理、编目历史时才被人提及。如《青史》记载:
上文是目前所知关于卫巴洛色生平的全部内容,可惜这仅是其事迹的一小部分。卫巴洛色的著作除《教法史》外,在《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还收录了5部作品的名录。②《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所收录的卫巴洛色作品编号为其中第 1 和 2、5 和 6 为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 .哲蚌寺藏古籍目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此外,目前笔者手中掌握的署名卫巴洛色的作品共有19部。③笔者手中掌握的卫巴洛色的著作来源,一是目前收藏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的手抄本《佛藏目录》的复印件;二是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噶当文集》第3部中所收录卫巴洛色的作品5部,其中4部源自哲蚌寺藏书;三是国际著名藏学家E.Gene Smith先生所创办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所提供的卫巴洛色的两部作品集,代码分别是W2PD17520-I4PD1556-1-318和W2PD17520-I4PD1557-1-312。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卫巴洛色的作品,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教法史》外,正式出版的有《宗义注疏库》、《三十颂释》、《音势论释》和《古今词汇类别》参见喜饶仁青、卫巴洛色等.宗义[G].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萨迦派系列(10).北京: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244-483;卫巴洛色.三十颂释[M].音势论释[M].藏文文法汇编(1).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5-50;卫巴洛色.古今词汇类别[M].藏文文法汇编(25).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12.
至于《教法史》的成书年代,Dan Martin教授推测为14世纪中叶;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根据作者的生活时代,推断为“约14世纪早期”。[11]然而,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史料,卫巴洛色《教法史》的著作年代为藏历第6饶琼铁龙年,[12]也就是公元1340年。
三、结构和基本内容
自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史学亦然。11至14世纪西藏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种类上的多样性。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这一时期成书的一部重要的西藏佛教编年史,全书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文本共分三个部分,内分若干章节。
第二节佛教“中弘期”,则以沃松之子贝阔赞(925-955)修建敏隆等寺院为起始,之后对鲁梅等人及其弟子在西藏各地广建寺庙的信息进行了罗列,这
第三节佛教“后宏期”,以拉喇嘛益西沃叔侄修建古格托林和卡恰二寺等历史事件为起始,之后罗列了当时参与佛经翻译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录。显然,卫巴洛色继承了觉丹热智“三段式”的分期法,但又没有完全采纳这种做法,他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并不成熟的标准。虽然这种方法存在缺陷,但作为西藏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的一种“独树一帜”的分期方法,对后来“二段式”分期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该《教法史》的文本结构来看,卫巴洛色是以西藏佛教发展史为“脉”而著。文本开头部分对印度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但整体所述仍以“西藏部分”为重。卫巴洛色继承了早期西藏史学的传统,以“分段式”将全书划分章节,同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具有编年体史书的特点。
四、体例和叙事风格
传统历史叙述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纪传体。[15]藏文历史文献因其内容等的特殊性,故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分类法。②有学者将藏文历史文献分为: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传记、地理类、寺庙志、年表、名人录和全集等;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历史编年、教法史、宗教传记、自传和回忆录、书涵、闻法录和上师传承谱系;而最普遍的分类方法则是:王统记、传记、教法源流、法嗣传承、世系史、寺庙志和圣地指南等。上述几种分类方法,有的是从体例上区分,有的是从内容上区分,几乎涵盖了藏文历史文献的全部种类。参见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J].史学史研究,1988(2,3):32-38,41-49;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Jackson,“Editors’Introduction”Tibetan Literature:Studies in Genre,Snow Lion,Ithaca,New York,1996,pp30;东噶·洛桑赤列.藏文文献目录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0.纵观西藏史学,大部分史书出自佛教僧人之手,内容以记述佛教史为主,其中以“教法史”最为常见。③从藏文历史文献的发展脉络上看,“教法史”这种史书类型最早形成于11世纪,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教法史著作。参见Leonard W.J.van der kuijp,“Tibetan Historiography”,Tibetan Literature:Studies in Genre,pp46.
卫巴洛色《教法史》整体上以“编年体”形式展开,具体叙述时则以“人物”为中心,各章节荟萃了众多历史人物,并按年代先后顺序进行叙述。从史书总体所涉及的人物来看,主要分为两类,即历代赞普及其后裔和佛教高僧大德,其中赞普及其后裔的记述重点以佛教相关事迹为主。故,笔者认为这部《教法史》实则是编年和纪传的结合。此外,作者卫巴洛色在记述不同历史时,往往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佛法发展之基础(吐蕃)王统”时,采用的是“王统记”的叙事方式,这与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大事纪年》),[16]以及早期的两部王统记,即萨迦扎巴坚赞(1147-1216)和八思巴(1235-1280)分 别所著《吐蕃王统》()极 为相似。[17]
同时,卫巴洛色《教法史》还采用了一种罗列“名录”的叙事方式。如在记述历代赞普弘扬佛教功绩时,作者除交代历代赞普所建寺庙等信息外,还排列了当时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字。该《教法史》的这种叙事方式言简意赅,毫无“浓墨重彩”感,与之后的史书常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人物事迹形式大为不同。全书对于历史的记述“中规中矩”,亦无像后来史书那样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地塑造佛教高僧的高大形象。总而言之,卫巴洛色《教法史》虽囊括了教化功能性,但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记忆。
从文风来讲,文本最大的特点便是“精简”,这种记述方式在当时较为盛行,如《古谭花鬘》(和《大 教 法 史·法 幢》()等。[18]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仅用一页半十四行的内容来记述松赞干布的事迹;[19]在叙述佛教“后宏期”时,作者将当时来到藏地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本土译师的名字分两组进行排列,没有一字半句的展开。这种精简记述的史风,可视为早期西藏史学的一大特征。②梁启超先生所提出的史家四长,分别是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其中“史才”是指用剪裁、排列的方法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整理、组织的能力,以及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也就是所谓的文采。对史家而言,文采要注重简洁、飞动,而卫巴洛色在撰写《教法史》时,用极为简洁的语句叙述历史,虽称不上“飞动”,却别有特色。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34.
五、史料价值
卫巴洛色所造《教法史》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教法史》记载的历史较为完整,为研究吐蕃史及早期西藏佛教史提供了参考依据。吐蕃历史研究,学界除了仰仗被视为最基本资料的吐蕃金石铭文、简牍、敦煌古藏文文献和汉文史书以外,11世纪以来成书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尽管学界对出自僧人之手的史书褒贬不一,甚至认为充斥着“佛教史观”的史书不足为信史,但其所包含的史料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如《第吾贤者佛教源流》《娘氏佛教源流》《王统世系明鉴》和《贤者喜宴》等都是重要的史料。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同样专门设有“吐蕃史”,可与前述史书不同,卫巴洛色主要采用了“王统记”的叙述方法,即录入赞普家族谱系并穿插赞普生卒和执政时间。如在叙述吐蕃末代赞普达磨时,《教法史》载:
达磨(赞普)生于羊年,十六岁登上王位,三十二岁在拉萨被弑,也有人认为(达磨)被弑于昌珠。有人认为(达磨)至二十一岁间共执政一年半或两年半年;有人认为十八岁(执政)至被弑整整三年,而有人认为是一年半,更有人认为(其执政)十一年。[20]
引文中除了有达磨赞普生卒年,还记有其被弑地点和执政时间的不同观点。卫巴洛色并未给出自己的见解,却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部分史书记载,达磨赞普是在阅读碑文时被拉隆贝多射杀,[21]更有史家明确提出被弑的地点是在拉萨。[22]当代学者普遍认可后一种观点,[23]但是,随着对卫巴洛色《教法史》研究的深入,对于“达磨被弑地点”又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昌珠。虽然这种说法史源不明,内容亦值得商榷,却丰富了我们对进一步认识某些历史问题的视域。
还有,通常藏文史书中鲜有关于吐蕃王朝前之吐蕃地域的记述,但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却有所记载。③《教法史》载:“作为珍宝黄金的产地,(早期)吐蕃的地域,东至汉地切玛绛谷容()、南至印度朵贵昌仁容(西至大食候夏甲曲容北至霍尔森姆桑卡夏日容又,接尼泊尔于夏巴甲曲容接门于嘉斯崩巴容接绛于佐达甲昌容接象雄于贵贵聂隆容 ),(上述)即为八处地界哨所所在。”参见卫巴洛色.教法史[M].275.
第二,《教法史》中保存了部分已失传的珍贵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有的史料得以充分利用,如敦煌古藏文文献;④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不仅可探究藏文佛典的渊源流变,还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还可探索吐蕃语言文字的原始面貌。参见才让.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价值探析[J].中国藏学,2009(2):35-44;收录于同氏.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有的史料,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去发现和挖掘,如卫巴洛色《教法史》等。
卫巴洛色《教法史》广征博引,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现已难得一窥的原始资料,如《喇协》()。这一史书恐已失传,只是常在后来的史书中被提起。[24]卫巴洛色在其《教法史》中先后两次引用了《喇协》的相关内容,如:
(赤松德赞时期,出现了首批受戒出家的僧人)之后,又有三百六十人受戒出家。[26]
据《松巴佛教史》载:“巴·色囊和巴·桑喜等人整理出的桑耶寺志分别置于僧伽、藏王、大臣那里,各有所加减,出现了《喇协》《杰协》()和《巴协》三册,后来文字亦有长有短。”[27]可见《喇协》系《韦协》的不同版本。
第三,《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的分期法,有利于我们构建西藏史学史。目前,西藏史学史研究无论是其成果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除了要对史书个案进行研究外,综合性研究亦需引起重视。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前、中、后“三段式”的分期法,这与目前学界普遍公认的“二段式”分期法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两种分期法形成的时间顺序来看,前者要早于后者;从分期标准来看,后者要比前者分期更加明确、成熟。从“三段式”演变发展成为“二段式”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西藏史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有利于我们洞察早期西藏史家的史学思想及史学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