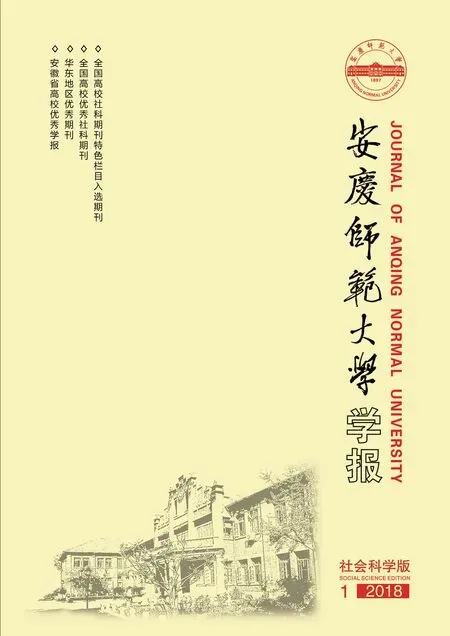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际会
王永坚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关系,学界多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之争”,而所论又多从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对立之处阐发,鲜有人注意到陈独秀与桐城派绝非仅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如关爱和在《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中说:“至此,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提倡者(作者注:陈独秀与胡适)都已把反对旧文学的矛头明确无误地指向桐城派及桐城古文。桐城派作为旧文学殉品、新文学祭物的命运,已无可逃遁。”[1]又如曾光光论说此事时说:“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将目标瞄准‘旧文学’与‘旧道德’时,桐城派自然会成为最好的批判靶子。”[2]因此,在论及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关系时,难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其实,陈独秀早年受桐城文化濡养,与桐城门人相交游;中年因“新文化运动”而与桐城派针锋相对;晚年回归传统,研究文字学。就其与桐城派的关系而言,陈独秀出自“桐城”,与桐城派颇有渊源,可谓是深得桐城之助。
一、出乎桐城与交游“旧”友
按旧行政区分,怀宁与桐城分属两县,但两地山水相抱,鸡犬相闻,人文一体,素有“桐怀一家”之说,属桐城文化圈[3]。怀宁深受桐城学风与文风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陈氏一族,受桐城家风、学风的影响不言而喻。
陈氏先世“习儒业十二世”,“长子藩,十一岁五经读竣,文理清通,固公之法教森严”,“公幕出家寒苦,依然附学不辍,师俸倍于人,自俸半于人。”[4]陈氏一族不仅有世代习儒的传统,族中子弟更是勤奋刻苦。而桐怀相距甚近,在桐城学风潜移默化影响下的陈独秀及其父兄学桐城古文当在情理之中。
陈独秀幼时由祖父教其读书,所学内容为《四书》《五经》及《左传》。《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凡是参加科考的士子均需认真学习。而在桐城古文的发展脉络中,《左传》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方苞看重《史记》《左传》,以为此两书为义法说之大源[5]129。除此之外,方苞坚守以程朱上接孔孟,以韩愈承继《史记》《左传》的道统文统[5]129。陈独秀在幼年时期就学习《四书》《五经》与《左传》,与程朱产生联系,由程朱再进一步靠近桐城派。陈独秀幼年丧父,母亲望子成龙,“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的一桩恨事。”[6]203“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6]205在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教育下,陈独秀自然得学习八股文章,而这是在其兄长的指导下进行的训练。陈独秀回忆说:“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还“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6]206。除此之外,兄长还需按时向母亲报告陈独秀学习八股文的进度与程度。尽管陈独秀一再表明自己鄙弃八股文,视八股文章与科考为灾难,但实际上他与众多士子一样,因科举考试而研习八股文章、做试帖诗,更曾对袁枚等人的制艺产生过兴趣。后来陈独秀年纪轻轻考中秀才,并参加了江南乡试原因全在于研习制艺、钻研八股。
清朝科考须做八股文,而八股文与桐城古文又关系紧密。“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也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7]科考士子为了避免文章千篇一律,便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为使文章脱颖而出,将古文的义理、神韵、考据引入时文之中,使时文气象一新。加之方苞身为古文大家,曾因善制艺而身居高位。鉴于此,许多士子认为学习方苞的为文之法——以古文为时文,求得耳目一新是中举的捷径。陈独秀既有世代习儒之传统,又有“桐怀一家”之优势,谓其文化底蕴来源于桐城,名副其实。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还在于他曾与桐城派传人交好,友谊深厚。作为桐城派大师方宗诚的后人舒芜,曾在自传中谈到陈独秀与其长辈的交往,说:“我自幼习闻陈独秀家与我们家是几世通家之好,陈独秀的父亲陈昔凡先生,与我的伯祖父方伦叔先生,我的祖父方槃君先生,以及邓绳侯先生,都是安徽学界文林同辈交游;陈独秀与我的几位伯父、我的父亲以及邓绳侯先生的儿子邓初(仲纯)、邓以蛰(叔存)又是同辈交游;我的六伯父方孝旭先生的夫人(方玮德之母)是陈独秀的表妹。”[8]舒芜的曾祖父是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祖父为著名诗人、书法家方守敦,外祖父为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父亲方孝岳毕生从事文学、经学、佛学研究,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陈氏与方氏两个家族之间的来往,不仅是人情的来往、姻亲的结合,更有文化的交流。舒芜作为桐城大儒的后代,“在家塾里读的《四书》《五经》、唐诗、古文,全得背诵”,“古文主要是读唐宋八大家的,实际上是把他们看作八股文的先辈或长亲。”[9]253而与桐城派相交的陈氏一族,对陈独秀的教育亦是与方家不谋而合。《实庵自传》中,陈独秀曾描述自己读书,“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6]202陈方二家教育情况如此相似,研读的书籍也是十分相近,当是两家在对后代教育一事上交流切磋,互通声气。陈独秀自幼年开始深受桐城家法的训练与桐城文化的熏陶更可由此处见。晚清桐城派虽呈西风凋零之态,但名气尚存。桐城派诸多传人皆有设席于各地书院的经历,将授课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如姚鼐曾担任敬敷书院山长,马其昶亦出任桐城中学堂长。由此可以说,桐城文人与教育、与学校有一种天然的融合与亲近。进一步说,桐城文人对教育、对学校的创新、发展和变革较学界他人有着更深、更具体的渴求和关切[10]。
作为桐城派传人的方氏一族具有善于教育的传统。陈方交好,陈氏一族面对丰沃的教育资源,必定充分利用。在陈独秀在与方孝岳等人的交往中,正是因为桐城家法融入陈独秀的血肉之中,才让陈独秀亲近、交往方孝岳等桐城派传人。当年方孝岳与其妻在京举行婚礼,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士都参加婚宴,除去私人交情外,更是因陈、方二人在文化上的联系。不仅如此,方守敦去世时,逃难四川的陈独秀送去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9]130挽联中,陈独秀语气谦卑,以同乡晚辈自居。既是因桐城方氏名气不薄,又因陈独秀与方氏家族交情颇深。
除却思想上接触桐城派,受桐城文化濡养,在现实生活中,陈独秀与桐城派大师马其昶更是联系紧密。清末,安徽大学堂更名为安徽高等学堂后,严复曾至此处任校长,该校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停办。在安庆除了有安徽高等学堂这样的官办学堂外,还有一些私立学堂。民国元年,陈独秀利用原安徽师范学堂旧址,创办私立安徽高等学堂,聘桐城马通伯为校长,陈自任教务主任,未及一年,因局势变化而停办,后并入私立江淮大学[11]。
1919年6月11日下午,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为便衣警察所捕。这一消息在第二天即传遍北京。在众多的营救人士之中,有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施以援手,即马其昶、姚永概等桐城派古文大师。马其昶、姚永概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尚为士林所推许。”除了对陈独秀学问人品的推崇,“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甚稔”。常常向人表示,“主张不妨各异,虽同是士林斯文一体,文字之狱,万不可兴云云。”[12]北京学界、教育界及舆论界等各界人士营救陈独秀在情理与意料之中,“陈君本教育界巨子,平日提倡新思潮”[13],盛名日隆。但身为“十八妖魔”传人的桐城后人,在旧学与新学激烈对立的艰难处境之下,居然为叛逆桐城的陈独秀摆脱囹圄而奔走呼号,既引人注目也令人深思。仔细推究,马、姚二人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彼此熟稔。出于同乡之谊,二人为陈独秀奔走确实无可厚非。然马其昶、姚永概之所以愿为陈独秀出狱奔走效劳,深层原因更在于此时的桐城派已衰落,难以为继,陈独秀虽百般为难桐城派,然其于桐城派实则意义重大。陈独秀幼时深受桐城文风影响,又因其家族与方氏家族过从甚密,深受桐城派教育方式的影响,打下深厚古文基础。在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学习其他知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塑造自身,桐城派功不可没。而后又携手吴汝澄、房秩五创办报刊,结下友谊,彼此之间相互砥砺。作为正宗桐城派后学的吴、房二人与陈独秀在创办报刊之余交流思想,陈独秀亦可再次走近桐城派。陈独秀更与桐城大师马其昶同在一校,朝夕相处,马其昶毕竟是桐城派大儒,思想见识更是超越方守敦等人。公务之余,二人交流探讨桐城派亦在情理之中。陈独秀自幼感触桐城文风,后接受桐城家法训练,这为他后来文章写作与文字学研究奠定基础。而这桐城家法下的训练正是他与马、姚二人得以相接的关口,其身上的桐城文化与桐城家法唤醒马、姚二人保全桐城遗种之决心。陈独秀血液之中的桐城文化因子更让马、姚二人意识到,凋零势态下的桐城派若要继续传承,陈独秀不可不救。以此观之,陈独秀之于马、姚,之于桐城派意义重大,实是桐城派最后的精神脉息。
二、新派领袖与旧学营垒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大主义,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在谈到今日中国文学之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并肩,原因就在于“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14]290。而妖魔又是何人?“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14]290。陈独秀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高呼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与立诚写实的文学,则必须要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与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在桐城派、文选派、江西诗派等旧文学之中,桐城派作为“一代文宗”,既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贵族文学,又是失抒情写实之旨要的古典文学。在进行文学革命的萌芽阶段,将桐城派树立为标靶,此后集中全力攻击标靶,此举意义深刻。倘若桐城派这一最大障碍被扫除,其他旧文学余孽望风披靡,不攻自破,无力与新文学相抗衡,那么新文学的建立便是水到渠成之事。在旧学中浸淫已久、接受过桐城派熏陶的陈独秀,言辞锋利地批驳桐城古文,“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力图褪去身上痕迹,去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在反叛桐城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提倡文体上的更新,陈独秀还对胡适提出文学语言的更新——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予以响应与支持。最初提出白话文主张后,无人注意。“新青年”们不得不主动出击,由钱玄同与刘半农共同演绎了“双簧信”。“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15]。钱玄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件大发言论,陈独秀也一一写信回复。“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谓文学界浮一大白!”[16]“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能和纯然白话不同。”[17]从回信可见,陈独秀欣赏钱玄同追随新文学的态度;对于推广白话文,陈独秀亦是大力支持。从陈氏提出“十八妖魔”再到钱玄同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陈钱二人结为盟友、互相支持,竭尽全力攻击桐城派。
推广白话文,就不得不扫荡桐城古文,皆因桐城古文阻挡了推行白话的道路。陈独秀以为古文是死文字,而白话是活的。古文是为封建王朝服务,而如今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那么再用古文必定不合适了。古文属于旧文学,如今推崇新文学,则一定要用白话。陈独秀深受桐城文化的濡养,对于桐城派的优缺点更是有旁人不可比拟之体会,新文化运动中他抓住桐城派的弱点,攻其软肋。桐城家法训练下的陈独秀,利用自己的桐城派旧学本领,抓住桐城派古文空疏、窳弱的缺点,深刻体会到桐城古文不及白话文。而这发现缺点,攻击软肋的本领也正是其在桐城派训练下的功力的积累,即便是攻击桐城派,还是借桐城派之助。另一方面,将桐城派作为标靶,使陈独秀等人有了批判的对象,这又是陈独秀得桐城之助的另一层面表现。
《新青年》同人以陈独秀为总司令,各显所能。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之于陈独秀更是意义非凡。胡适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8]287从文学进化的角度,肯定了推行新文学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推行新文学又有不得不攻击古文家之原因,“吾辈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而古文家则反对此观念也。”[18]287“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18]287文学处于不断进化之中,而古文家阻碍了此种进化,所以打倒桐城派古文实是大势所趋,是文学进化之必然结果。打倒古文家的原因更不仅限于此,胡适以林纾《论古文不当废》中“而方姚氏不之踣”一语不合文法,“则古文之当废,不亦既明且显耶”。
三、“小学”情结与回归传统
桐城文人历来重视“小学”研究,并写出大量有关“小学”的著作。方以智撰《切韵声源》一书,其子方中通撰《昔韵切衍》。值得注意的是,姚鼐的外甥马宗琏也写有多部“小学”著作,如《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说文字义广注》等。桐城文人推崇“小学”,并有不少桐城文人将“小学”著作视为学生启蒙的读本,以“小学”为基础,才可令学问扩而大之。由此可见桐城县内既有注重研习“小学”的传统,亦可知桐城先贤于“小学”研究用力颇深。
除桐城文人重视小学研究,桐城派门人也对“小学”研究用力颇深。“岭西五大家”之一的龙启瑞治古文辞尚桐城,更对音韵学与文字学研究颇有见解,撰有《古韵通说》《小学高注补证》。除此之外,方孝岳作为桐城方宗诚之孙,可谓桐城派嫡传弟子。然而方孝岳虽从事文学研究,成就最大处却是在音韵学,著有多部音韵学著作。龙启瑞、方孝岳作为桐城派传人,却对“小学”研究情有独钟,可见即便是与汉学家多有抵牾的桐城派,仍未尝废“小学”。“小学”对于桐城派门人来说,既可为研习古文奠定基础,也有助于考据,以达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境界。
193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入狱。陈独秀长期过着动荡危险的地下生活,其实就个人爱好而言,他更热衷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字学。狱中的陈独秀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著述计划,除了继续文字学著作外,还想在二三年内完成《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的撰写[19]。从陈独秀预备完成的作品中看,与传统文化关联的作品居多。而陈氏在狱中阅读之作品,也以历史传记与文字学类的作品居多。就陈氏在狱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说,可谓丰硕。其关于孔子的论述多有新解,辩证、客观地看待孔子及其影响,强调了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也是有价值的。“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20]164“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20]164—165孔子重人事而远鬼神,不深究鬼神无或有。孔子礼教的价值在于其“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20]166在传统观点看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反孔批儒态度鲜明,新旧之间没有妥协,只有极端的对立。作为一个激烈的反对者,陈独秀一向如此。殊不知,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实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
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反孔批儒,最初的动因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大行孔教会之活动,并由此得出结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21]不摧毁孔教,则帝制难以消除于思想之中;不摧毁孔教,学术亦不得进步。然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一文中说:“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由此,可见陈独秀并非反对孔子,他反对的是不适用于这个社会的孔教,他急于推行民主与科学,则不得不对儒家纲常名教进行批判。陈独秀反孔批儒,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了孔子及儒学的价值,陈独秀的内心对于孔子及儒学是极尊敬的。“孔学优点,吾未尝不服膺。”“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22]362“孔子精华,乃如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而在宗法封建时代,诚属名产。”[22]362由此可见,陈独秀内心深处尊崇孔孟,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为了推行民主与科学而不得不反孔批儒。而尊崇孔孟与桐城派的核心义理几乎一致,可见陈独秀内心深处与桐城派却是暗中相通。
对文字学研究执着热爱的陈独秀,不仅在南京狱中进行呕心沥血的文字学研究,晚年在江津,饱受生活磨难的陈独秀依然不改初心,将最后的生命奉献给文字学研究。这两个时段,是其研究文字学时间最长的时段,也是其收获最丰的时期。陈独秀在南京狱中的著述文稿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正式完稿,稍后送交《东方杂志》发表者,有《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实庵字说》《老子考略》和《孔子与中国》六篇;二是已完成的手稿(后刊有油印本)和未完成手稿(有的后来经改写出版)者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原韵表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和《甲戌随笔》等[23]。音韵学、文字学研究是陈独秀的兴趣,也是其专长。若追根溯源,这兴趣、专长与其自幼所受的桐城派教育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姚鼐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结合,如此则需佐以深厚的音韵学、文字学为基础。陈独秀深受桐城文风的影响,学习桐城派的为文之法,对考据一途产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其次,方孝岳研究文字学、音韵学研究,声名显赫。而方守敦的另一子孝博在大学曾讲授文字学课程,著有《文字学纲要》一书。由此可见,桐城方家当是注重“小学”的教育。追本溯源,方氏家族的教育乃是与桐城派教育一脉相承。陈方交好,陈独秀的教育深受方氏家族的影响,故陈独秀对“小学”的兴趣由此而来,而陈独秀在文字学上的功力,则是桐城派持久训练下的结果。
南京狱中,陈独秀联系自身所处环境、人民生活环境及国民党专制腐败问题等社会现象,创作了一组旧体诗——《金粉泪》五十六首,淋漓尽致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陈独秀为人激切,文笔锋利,在面对令其愤愤不平的事件后,为何不借用杂文来表达不满、批判社会,而是用古诗这一文体以抒怀?实因古诗蕴藉含蓄、寄托遥深,可发作者之所欲发。诗中蕴含作者感情,暗含作者态度,可使作者在激烈的斗争之中既保全性命,也保持立场。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陈独秀生于晚清,更是参加过科举考试,作诗是一个士子最基本的技能。以往因为政治革命、文学革命的需要,陈独秀有意抛弃传统旧学,提倡新文学与新文体。而如今身陷囹圄、举步维艰,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开始显现。古人历经忧患,心有所感,胸中块垒郁积,唯有诗与酒方能解其忧愁。狱中无酒,且陈氏亦不善饮,胸中不平之气只能借诗宣泄。所作旧体诗,既是旧学功底的显现,也是传统文化烙印不可磨灭之表征。更可看出陈氏在多年政治飘浮中,心倦人乏,始有淡出政治、回归传统文化之意。
晚年陈独秀深感实际政治运作并非其强项,在孤寂的晚年,他终于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24]。陈独秀最后来到四川江津,遍尝世态炎凉。先是慈母(即嗣母谢氏)离世,陈氏不胜伤感。后频繁更换住所,只能居住在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的杨宅。此时的陈独秀,生活贫困潦倒,只能靠稿费与友人接济方能过活。而又因饱受胃病与高血压的折磨,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磨难之下的陈独秀苦闷无处排遣,将精力投入到文字学研究之中,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问题,最终写成《小学识字教本》。《小学识字教本》书名暗藏玄机,“小学”既指包含文字、音韵与训诂的传统语文学,又指初期的识字阶段。此书内容翔实,大量征引古代文献与近代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由文言撰写而成,不同于早年积极推行白话文,晚年用文言写成巨著,回归传统文化之心态一览无余。政治失意、生活困顿、亲友离世、经济拮据、病魔缠身,陈独秀凭借对文字学研究的兴趣与执着,顽强生存。这份执着流淌于陈独秀血液之中,不论是在南京狱中、长沙岳麓山下,抑或是江津杨宅,陈独秀对文字学的热情与兴趣丝毫未减,反而更随着环境的恶化、生命的起伏越发明晰。
晚清桐城派虽有吴汝纶、黎庶昌之流,主张向西方学习,然亦不过是学习西方器物与教育,骨髓中仍印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陈独秀不但有保全民族文化之决心,且尊重他国文化。丝毫不像晚清名士文化优越感强烈,以天朝上国自居,藐视外域文化。陈独秀宣称,“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25]348不仅如此,陈独秀更有深重的文化危机感,“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就糟糕透了。”[25]348陈独秀深刻意识到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既要注重保护本国文化,更要防止他国的文化渗透。
在远离政治、寄情文字的幽静环境中,陈独秀冷静客观地反思自己过往对于传统文化失之偏激的态度,灵魂深处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复苏。而这愿望与行动的源头是浸入骨髓的旧学修养,唤醒了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信心与责任。而旧学修养恰恰又是桐城家法下的严苛训练,以及与桐城派文人交游而产生的思想共振。陈独秀在旧学修养之下,培育出尊重、保存传统文化的决心,而其对于文化的见解相较于桐城派诸人,更是青出于蓝。
要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桐城派后人的交游使得陈独秀接近桐城派,受其影响。推行抒情写实的白话文,扫除肤浅空疏的桐城古文及联手《新青年》同人,终使桐城派退居文化边缘。晚年陈独秀最终于艰难困境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温情与独特魅力,保存国粹之思想与文字学研究都彰显着其向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努力。无论陈独秀如何激烈反对桐城派,也无法与桐城派完全剥离,他与桐城派有着天然的联系,深入骨髓又难以割舍。叛逆的陈独秀用一生的经历去撇清与桐城派的联系,却在不自觉中诠释了自己与桐城派难以分割的因缘。
[参 考 文 献]
[1]关爱和.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J].文学评论,2004(4).
[2]曾光光.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江汉论坛,2009(5).
[3]张器友.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174.
[4]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M].安庆:安庆市图书馆,1981:58。
[5]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陈独秀.实庵自传[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2.
[8]舒芜.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M]//舒芜.舒芜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25.
[9]舒芜.未免有情——舒芜随笔[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10]吴微.从亲和到遗弃: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的文化因缘[J].东方丛刊,2006(3).
[11]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庆地区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5:930.
[12]汪诒年.传闻异词的陈独秀案[N].时事新报,1919-06-24.
[13]叶楚伧.陈独秀被捕之真因[N].民国日报,1919-06-17.
[14]陈独秀.文学革命论[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5]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艺之分期[M]//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
[16]陈独秀.答钱玄同[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96.
[17]陈独秀.三答钱玄同[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79.
[18]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M]//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字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287.
[19]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12.
[20]陈独秀.孔子与中国[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49.
[22]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3]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269.
[24]罗志田.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J].四川大学学报,2010(5).
[25]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M]//《陈独秀著作选编》编纂委员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